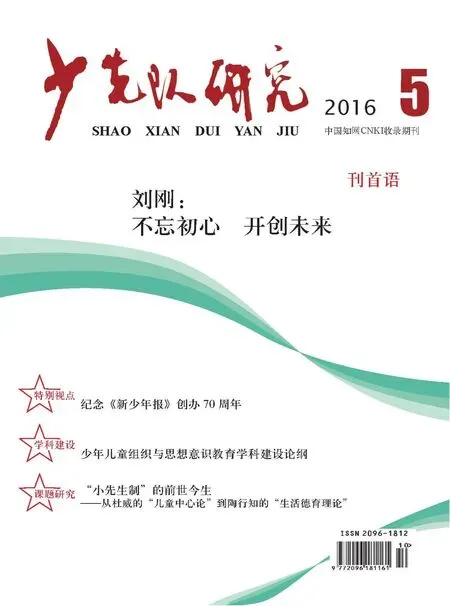《新少年报》影响了我一生
□ 当年《新少年报》通讯员 章大鸿
《新少年报》影响了我一生
□ 当年《新少年报》通讯员 章大鸿
编者按:《新少年报》于1946年2月16日正式出版。《新少年报》的诞生,犹如黑暗天空中划过的一道闪电,汇入解放战争的革命风暴之中;犹如漫漫严冬中炸响的一声春雷,预示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来到。今年,《新少年报》创办已有70周年了。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上向全党同志提出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要求,继承党的地下少年儿童运动光荣传统,着眼未来,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做好青少年教育工作。本栏约请几位同志撰写纪念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示。
我是个老编辑、老记者。是谁把我从小引上了编辑、记者的道路?是《新少年报》!
1946年9月,抗战胜利后一年,我考进了浦东洋泾中学。班主任曹文玉老师介绍我们看刚创刊半年的《新少年报》,要我们和她交朋友。
我看到报上一条消息:抗战刚胜利,中国人打了日本鬼子,现在又中国人打中国人!我马上想起日寇侵占上海时的苦难:外婆带我和姐姐逃难,老人病死在浙江乡下;日寇占领母亲做工的烟厂,不发工资。我妹妹生了病没钱医治,病死没钱丧葬,只能锯掉一副床板,钉了口小棺材,抛到炮台湾荒坟里了!我又想到日寇投降后,国民党的机枪、迫击炮部队在我念书的小学操场上一阵阵操练,都飞到东北打共产党去了!干吗要打仗?是谁要打仗呢?
报上又一条消息:上海市民、学生组织了和平请愿团,上南京要求国民党、蒋介石停止内战,却被国民党特务打成重伤。这使我联想起在东昌路东头农田边,亲眼看到一个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国民党军官,逃跑后被抓了回来,五花大绑被开枪活活打死了!呵!原来是国民党、蒋介石不要和平!
报上登的都是我想知道的事情,我爱上了《新少年报》。后来知道,这是中共地下组织为了引导白区青少年认清黑暗社会、追求光明前程,办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的一份少儿报纸。我要看《新少年报》,可家穷没钱订阅,只能一期期向曹老师零买。曹老师就启发我当义务小发行员,我当然愿意。在母亲的支持下,我不仅做好校内的发行工作,还让邻里小伙伴在他们念书的附近中小学校帮助我征订。在阿段哥(段镇)和常与我通信联系的祝小琬姐姐的启发下,我在陆家嘴许文龙同学家的新建柴屋里,办起了同学们自愿捐书、免费阅读的影光书室,这里也成了《新少年报》的宣传、发行阵地。
为了做好发行宣传工作,每期新出的《新少年报》一到手,我都认真看,还学着写文章寄给报社。没想到胡德华、吴芸红两位大姐以“编者按”的形式,在《新少年报》上指导我:“不经过周密的思索及详细具体的观察,往往使作品浮浅地让人只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例如章大鸿的《童年》,因此要求大家学习,学习,再学习!”于是我学习细心观察邻家铁匠铺里小学徒的悲惨生活,写了《小铁匠》寄去,这下被刊用了。两位大姐还在《给小作者》的按语中说它“有很丰富的爱与恨”,她们又指点我:“要产生这种感情,最要紧的是‘观察,观察,再观察’,更需要弄清造成这种悲惨生活的原因。”我到了张自强同学居住的芦花滩棚户区再次认真观察,人们关心的都是失业、涨价和内战。这使我联想到义父长期失业,母亲一人做工养不活一家人,只得把大我一岁的姐姐送给人家做童养媳;每到母亲发工资那天中午,我必须从学校奔到烟厂大铁门前,从门缝中接过上工母亲手中的纸币,再奔到街上买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要是等母亲放工去买,又涨价了。失业和涨价搅得百姓生活不得安宁,根子就在“打内战”。于是我愤怒地提起笔来,写下了《假如我是匕首》这首小诗:“看吧,/那狰狞的野心家/已燃起来了/战争的烽火;/暴戾的贪官污吏/把我同胞们的生活/抛进痛苦而黑暗的深渊中。/假如我是匕首,/为了挽回我同胞的自由,/誓以我自己锐利的钢刃/剁碎那/贪官污吏和/野心家/深褐色的心!”
《假如我是匕首》小诗交给报社已一个月,该出第100期了,可迟迟不见小陶哥送报来,突然收到从邮局寄来的第100期,竟是“休刊号”,只有一份。第二版上正登着我的《假如我是匕首》,还附来一封告别信:“我们被迫停刊了!……我们相信,黑暗定会过去!在未来的光明日子里,我们不会再有任何恶势力的阻碍。让我们为未来的再见努力吧!”
我明白了,《新少年报》被查禁了!
但是,地下党的斗争没有停止。之后,地下党组织又变报为刊,秘密编印出7期《青鸟》,把分散在上海各校的20多位小发行员、小通讯员骨干组织起“青鸟读书会”。一次次秘密集会,讨论《青鸟》上抗击恶势力的诗文,而后用“铁木儿”的名称成立了“地下少先队”。在地下党员带领下,我们地下少先队员给国民党军官、警察、宪兵、保长写警告信,张贴革命传单,调查敌人军营,绘制成地图,上交给地下党组织,为解放上海贡献力量。解放后我们受到市军管会的表扬。
是《新少年报》的地下党员们把我这个穷苦孩子培育成国家有用之才,他们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学习的榜样。解放后,我也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走上了编辑、记者岗位,在《儿童时代》《少先队活动》《大江南北》等报刊工作。大病退休后,我编写了《火红的青春》《报童之歌》《海纳百川新歌谣》《全国获奖儿歌集》等青少年读物。在整整70年时间里,新少年报社的老党员们都和我保持密切联系,都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帮助。《新少年报》影响了我一生!
我永记初心,师恩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