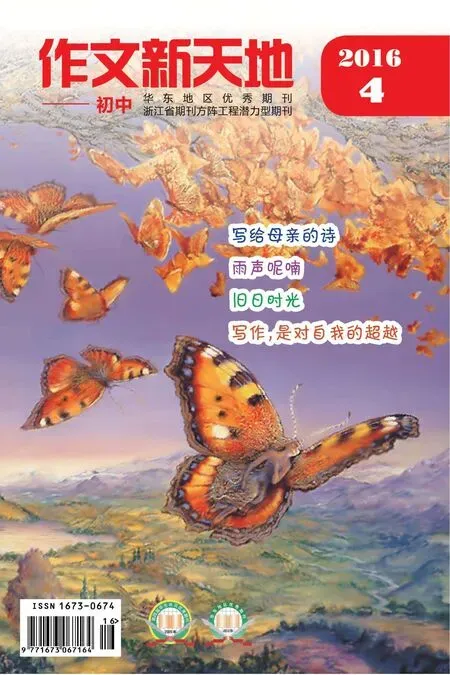道路以目(节选)
道路以目(节选)
◎张爱玲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们从家里上办公室,上学校,上小菜场,每天走上一里路,走个一二十年,也有几千里地;若是每一趟走过那条街,都仿佛是第一次认路似的,看着什么都觉得新鲜希罕,就不至于“视而不见”了,那也就跟“行万里路”差不多,何必一定要飘洋过海呢?
街上值得一看的正多着。黄昏的时候,路旁歇着人力车,一个女人斜欠坐在车上,手里挽着网袋,袋里有柿子。车夫蹲在地下,点那盏油灯。天黑了,女人脚旁的灯渐渐亮了起来。
烘山芋的炉子的式样与那黯淡的土红色极像烘山芋。
小饭铺常常在门口煮南瓜,味道虽不见得好,那热腾腾的瓜气与“照眼明”的红色却予人一种“暖老温贫”的感觉。
寒天清早,人行道上常有人蹲着生小火炉,扇出滚滚的白烟。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煤炭汽车行门前也有同样的香而暖的呛人的烟雾。多数人不喜欢燃烧的气味——烧焦的炭与火柴、牛奶、布质——但是直截地称它为“煤臭”“布毛臭”,总未免武断一点。
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十有八九是风姿楚楚的年轻女人,再不然就是儿童,可是前天我看见一个绿衣的邮差骑着车,载着一个小老太太,多半是他的母亲吧?此情此景,感人至深。然而李逵驮着老母上路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做母亲的不惯受抬举,多少有点窘。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坐着,满脸的心虚,像红木高椅坐着的告帮穷亲戚,迎着风,张嘴微笑,笑得舌头也发了凉。
……
有一天晚上在落荒的马路上走,听见炒白果的歌:“香又香来糯又糯!”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唱来还有点生疏,未能朗朗上口。我忘不了那条黑沉沉的长街,那孩子守着锅,蹲踞在地上,满怀的火光。
(选自《流言》)
【品读】
张爱玲的文字世界,色彩浓艳而细节丰腴。即使只是小小的一条街,在她眼里:“若是每一趟走过那条街,都仿佛是第一次认路似的,看着什么都觉得新鲜希罕,就不至于视而不见了”。生活随时随地都有新鲜事发生,关键在于你有无兴趣,有无留心。比如,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一个街上卖炒白果的孩子,是在“落荒的马路上”,而且“唱起来有点生疏”,可见这孩子刚刚走上社会,面对生活。然后,在那“黑沉沉”的长街里,作者又说“满怀的火光”,仿佛是希望之光,又似乎让人想到那个圣诞夜里,黑沉沉的世界上,那个划亮火柴的小女孩。此中之味,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所谓路上的风景,全在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