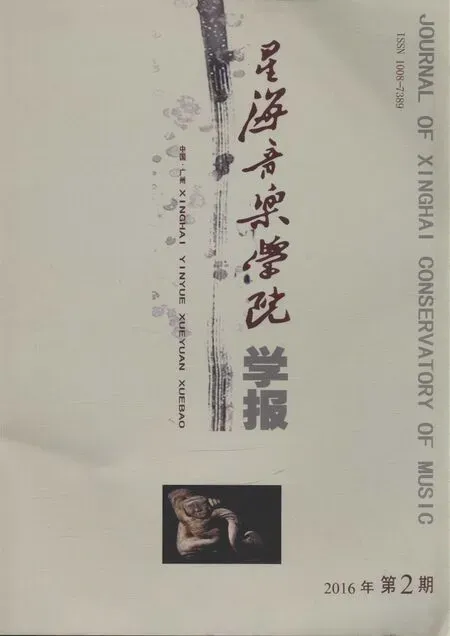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新作
——读李宝杰《区域——民俗中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
蔡际洲
(武汉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湖北 武汉 430060)
·书评·
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新作
——读李宝杰《区域——民俗中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
蔡际洲
(武汉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湖北 武汉 430060)
摘要:《区域——民俗中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是西安音乐学院李宝杰教授的新著,文章对该书的研究特点及其在当下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中的意义做出了评价。文章认为,该书视角独特,立意新颖,是一部既有新观点又有新材料,同时还有新问题的学术著作。此外,文章还对书中所涉及的有关民俗音乐定位问题与区域音乐文化分区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陕北;区域音乐文化;民俗;中国传统音乐;李宝杰;书评
不久前收到宝杰君寄来的大作《区域——民俗中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以下简称《陕北音乐》),感到眼前一亮。原因在于,该著不仅是与笔者的研究领域、学术兴趣相近,而且也与笔者对陕西这片土地的特殊感情有关*陕西是笔者的出生地,也是笔者父母当年求学和工作的地方。。黄土地的音乐,在国人的音乐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广泛影响。一方面,它传承了周秦汉唐以来作为华夏民族文化中心的种种基因;另一方面,它还积淀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传统。西安音乐学院的同行,在科研上抓住传统深厚的黄土地做文章,以彰显其学科特色,战略眼光令人佩服。
宝杰是笔者多年的老朋友,也是多年的学报编辑同行,深知他的为人与为学。作为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他还兼任学报《交响》常务副主编、科研处处长、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在繁重的教学、科研、行政工作之余,仍克服种种困难赴南京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足见其孜孜不倦的学术进取精神。几年来,他多次深入陕北进行实地考察,行程近两千公里,足迹几乎踏遍延安、榆林的各个县市。此外,他还研读了与其课题相关的大量文献,其中既有关于陕北传统音乐研究和其他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前人成果,也有文史类、方志类古籍文献和地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最新信息。《陕北音乐》即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面对近年来众多陕北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成果,宝杰的研究从何入手?这是笔者较为关心的第一个问题。通过初步研读《陕北音乐》,发现作者选择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区域—民俗”,并用其来观照陕北的传统音乐文化。作者认为:
区域问题的底层是其自然地理属性,人类各民族早期的发展无不以自然环境为根本,并形成各不相同的生存样态及文化基质。区域问题的上层,则是人类在逐渐摆脱自然地理条件束缚,通过借助自身的创造力和交通能力,把地属的、族属的文明播撒向异地,使之混融交叉发展并缔结出新的文明果实。[1]3
他还指出:
面对陕北这样具有特殊地理环境和浓郁民俗特征的文化区域,进行文化整体性上的考察与分析研究,应该更符合文化生成的事实和历史的延展。……认识陕北音乐文化,只有回到民俗生活层面,使我们的研究文本趋近文化存在的本源,才可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启示。[1]15
以上,是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选择“区域—民俗”视角的定位依据。
应该说,无论是硕士、博士论文还是学术专著,在选题确定了之后,其采用的理论视角如何,研究方法如何,将直接关系到该项成果的进展情况、原创程度,甚至成败。从这点上看,宝杰的写作立意或曰研究主旨,便与前人的各种同类研究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在现有陕北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成果中,更多的是对某一品种,或某一类型的“个体深入”,尚无以“区域—民俗”的角度对陕北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整体研究。
作者在为自己设定了理论视角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对全书的逻辑框架进行的总体设计的问题。通过阅读《陕北音乐》的目录,即可对全书的篇、章、节、目及其相互关系有一大体了解,从中也可看出作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思路。全书主体部分除了绪论、结论之外,本论由四章构成:第一章,陕北的文化区域构成及亚区划分;第二章,陕北音乐文化类型及区域性分布;第三章,民俗、信仰、方言中的音乐文化建构;第四章,陕北音乐文化的生存论张力。
第一章是全书撰写的基础,这也是陕北各类传统音乐文化生存的背景。其中,既有陕北自然地理概况的描述,也有陕北地缘关系(人文地理)的介绍。在此基础上,作者从文化的角度对陕北的文化亚区进行了划分。其中包括依据历史文献进行的“历史沿留的划分”,依据语言学和民俗学材料进行的“方言语音的划分”、“婚丧岁时民俗的划分”。第二章,作者以陕北代表性的传统音乐体裁、品种为对象(其中包括民歌、大唢呐、闹秧歌、说书、二人台、榆林小曲、道情、赛戏、道教音乐等),对其不同的区域性分布情况,进行了分类描述。根据作者的研究,陕北传统音乐文化的分布有“流传范围相对广泛”和“流传范围相对狭窄”两种情况,前者包括民歌、闹秧歌、大唢呐;后者计有说书、二人台、道情、榆林小曲等。第三章,作者分别以婚丧节庆、民间信仰、陕北方言为背景,把与其相关的陕北传统音乐置于这三种不同背景之中进行分类考察。作者在该章中,将背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象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如在第一节“陕北乡村民俗中的作乐样态”中,以“婚礼情景、丧葬仪式、节庆秧歌”为对象;再如第二节“陕北民间信仰中的仪式与音声”,作者分别从“还愿口与小儿保锁、横山马坊牛王大会、佳县白云观道教早晚课”入手,如此等等。
如果说,前三章作者重在实证性研究的话,那么,第四章则以思辨性研究为主。在这一章中,作者分别从“生存环境——精神原型缔构的前提”、“生命渴求——表现主题形成的动力”、“本真性——音乐文化的人类学归位”三方面,对陕北传统音乐文化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与解读。其中,既有对陕北传统音乐之意义与缘由的系统归纳,也有对陕北传统音乐之文化特征进行的提炼与总结。诚如宝杰的导师刘承华教授在序言中所说的:
他遵循“生存环境”—“生命表现”—“音乐品格”这一逻辑理路,主要抓住“干旱”、“窑居”、“放情”和“本真性”等几个关键词,描述出陕北音乐文化的内在逻辑。干旱导致人们对雨的渴望,产生“祈雨”、“祭雨”的仪式及其“雨号”音乐;窑居则以其空间的封闭性、以家庭为单位的特点,导致宗法制的相对薄弱和聚众结社、节庆庙会文化的发达,催生了乐舞的兴盛。而民俗中由“巫”、“情”、“礼”组成的三角文化构架,则以其互抑、互激的互动方式,形成陕北人的“放情”的生命状态。[2]
总之,这是一部以“区域—民俗”为视角,对陕北传统音乐文化进行整体观照的学术力作。全书结构合理,条理清晰,语言流畅。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陕北传统音乐文化的新认识,而且使该领域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读完全书,也有一些令人感到不满足的地方。如第二章中不同类型的区域性分布、文化亚区的区域性特征的归纳等方面,内容略显薄弱;再如有些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撰述内容的不同侧重,还有待进一步理顺,等等。
此外,对《陕北音乐》的研读,既是一个不断深入该书研究对象并获取新知的过程,也是一个促使笔者不断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思考、追问的过程。在该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现初步归纳其要,与学界同行讨论如下。
其一,关于如何判断民俗音乐的文化属性问题。
有关民俗音乐,音乐学界不乏讨论。在已有的相关文献中,更多的是讨论如何研究民俗音乐、音乐民俗的界定,以及民俗音乐在民族音乐学中的学术定位等问题*这类文献主要有:柘植元一著、王北城译的《民俗音乐与民俗艺能》(载《中国音乐》,1988年第3期,第25-26页)、乔建中的《浅议民俗音乐研究》(载《人民音乐》,1991年第7期,第38-40页)、薛艺兵的《“音乐民俗”界说》(载《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4期,第40-46页)、范晓峰的《关于民俗音乐研究学术定位问题的若干思考——兼及民族音乐学及相关问题》(载《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4期,第50-60页)等。,并未涉及民俗音乐的文化属性。所谓文化属性的判断,是指对民俗音乐本身的“身份”定位。比如,它究竟是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还是音乐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它究竟是一种民俗现象,还是一种音乐演艺现象?在《陕北音乐》中,作者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究竟应该是以“形态、技艺为先”,还是应以“文化、民俗为先”[1]16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对其属性的判断,不仅关系到我们对民俗音乐的进一步认识,而且还与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成果的学科归属有关。
研究民俗音乐,不仅关注音乐本身,而且还将其置于一定民俗活动现场进行观察,这在我国民族音乐学界应该说早已形成共识。但上述的孰先孰后问题,或在音乐与民俗之间各自如何侧重,恐怕看法不尽一致。依笔者的理解,在此问题上不宜绝对化。因为民俗音乐兼有民俗文化与音乐文化的双重属性*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性、包容性特征,许多传统音乐类型都具有这种双重属性甚至多重属性。如戏曲音乐之于戏曲文化、曲艺音乐之于曲艺文化、道教音乐之于道教文化、佛教音乐之于佛教文化等等。即使是以音乐表演为己任的“音乐会型”的传统音乐,也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演艺行为”。如售票演出面向市场的音乐会,其中自然不可避免“商业文化属性”的加入;而在高等艺术院校内部举行的各类音乐会,也因其属教学科研活动之一部分,而使之不可能具有纯粹的观赏性、演艺性。如此等等。。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民俗文化现象,也是一种音乐文化现象。作为学术研究,关键在于研究主体介入时所采取的研究视角。如果我们站在一个相对开放式的学术层面看,“形态、技艺为先”也好,“文化、民俗为先”也好,都不是一个“对错”问题。二者的区别在于研究主体的不同侧重,以及研究成果的学科属性——或民俗学,或音乐学。
作为民俗学者的研究,一般采取的是“文化、民俗为先”的学术立场。在民俗学者眼中,民俗音乐及其相关事项属民俗学中的一种研究类型。*如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将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分为“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游艺的民俗”等类型,其“游艺的民俗”中就包含民俗音乐(详参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此外,在《社会科学学科大全》中,民俗学词条下有:“民族民俗学、文艺民俗学、旅游民俗学、城市民俗学、地理民俗学、民居民俗学”(详参陈永香:《对民俗学与相关学科关系的再认识》,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47-50页),等等。以民间婚丧习俗活动的研究为例,尽管其中有音乐,但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婚丧仪式程序的进行情况、演唱中的歌词内容、参与者的角色身份与态度、音乐表演与仪式活动的关系,等等。总之,民俗学者的研究目的是从“讲唱表演活动中解析和透视民俗事象”[3]。那么,作为音乐学家的研究,当然一般是取“形态、技艺为先”的学术立场。仍以上述研究对象为例,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婚丧仪式中乐班的构成情况、乐器的形制、演奏演唱的技艺技巧、所用音乐的基本风格与不同类型、不同曲目的运用场合及其与仪式活动的结合情况,等等。音乐学研究当然还会关注一些其它与之相关的种种民俗文化事项,但其最终的研究指向,是为了解决音乐学方面的问题——即透过民俗活动来认识其中的音乐事项*笔者基本认同伍国栋先生关于“音乐事项”的看法,即“以某种或某类声音形态为核心而显现出的人间社会音乐生活万象”,详参伍国栋:《音乐形态 音乐本体 音乐事象——与研究生讨论民族音乐学话语体系中的三个关键术语》,载《中国音乐学》,2010年第3期,第63-68页。。
既然民俗音乐兼有民俗文化和音乐文化的双重属性,那么作为音乐学研究来说,除了上述关注重点之外,还可否在这两个学科之间的“灰色地带”进行探索,甚至作纯民俗学性质的研究呢?笔者的看法是,如果是学术兴趣使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我们音乐学界的奇才型学者赵宋光先生,就发表过不少关于哲学、美学、教育学,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文论。不过笔者想说的是,从事这类非音乐学性质的研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要格外小心。因为,无论我们进行什么样的“跨界”,都务必遵守一个做学问的基本原则,这便是学术创新。一方面,我们中间像赵先生那样具有多学科知识结构的人士毕竟是少数;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务必建立在对民俗学界相关学术成果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据冯洁轩先生回忆,他当年师从杨荫浏先生读研时,杨先生在看过一位同学撰写的音乐考古学论文后,还留有请考古学界前辈夏鼐先生阅后再发表的批语。作为音乐学界泰斗的杨荫浏先生,在对待“跨界”问题上谦虚谨慎的态度和对社会负责任的精神,可见一斑(详参冯洁轩:《驳周武彦君十文》,载《音乐研究》,1994年第1期,第61-71页)。另据台湾学者蔡宗德教授介绍,他们台南艺术大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在开题报告时,如有涉及其他学科的内容,在座的评审专家均要问及学生对相关“跨界”学科研究现状的了解情况。如果学生回答不出来或回答的内容不合要求,他们的规定是:不许“跨界”。。否则,其成果的原创性是值得怀疑的。
其二,关于如何看待音乐文化区划的不同研究方法问题。
在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中,将某种音乐及其相关事项按某种标准划分为不同地理空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陕北音乐》作为以“区域—民俗”为研究视角的学术专著,作者在其中就有大篇幅的关于音乐文化区划的内容。如,既有以“音乐要素”为标准进行的“陕北音乐文化类型及区域性分布”,也有以“非音乐要素”为标准进行的“陕北的文化区域构成及亚区划分”。以“音乐要素”为标准的划分好理解,但以“非音乐要素”为标准可能会有不同看法。尤其是划分的亚区(或副区)所具有的“非音乐学”学科属性,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有讨论的必要。因为,其中涉及如何看待音乐文化区划的不同研究方法问题。据笔者粗略观察,我国音乐文化区划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方法*笔者曾在《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载《音乐研究》,2011年第3期,第6-18页)一文中,把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中的“分布状态研究”按研究对象分大致为七种类型。与该文不同的是,这里是以研究方法为标准进行的分类。:
第一,以“音乐要素”为标准,以弄清某种音乐在不同地理空间之分布特点而进行的文化区划,如杨匡民、苗晶、乔建中等进行的民歌“色彩区”研究即是。在他们的研究中,或以民歌的不同“三声腔”为标准进行划分[4],或以“最具有本地特色的体裁或歌种为主要依凭”进行划分[5],等等。
第二,以“音乐的背景要素”为标准,以弄清某种音乐与不同背景(含自然的、人文的)的关系为目的进行划分。如杜亚雄对“汉族民歌音乐方言区”的研究[6],作者以音乐的人文背景要素——方言为依据,并按语言学的“七大方言区”进行划分,然后分类表述不同“方言区”中汉族民歌的音乐特征。再如蒲亨强关于“西南旋律体系”的探讨[7],作者将音乐的自然背景要素——地貌作为划分标准,把西南地区的旋律分别置于“平地、丘陵、高山”三种地理空间之中,然后再分别考察这三种不同自然背景中的音乐各有何特点。
第三,以“非音乐要素”为标准,以弄清相关“非音乐学科”的文化区域为目的,并将其作为音乐文化区划之参考的划分。这就是宝杰君在其《陕北音乐》第一章第三节(“陕北的亚区划分”)中所进行的探索。作者以历史文献、方言、婚丧岁时三种不同标准,分别对陕北地区进行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区划。即我们在该章节中看到的:陕北的历史文化区域、陕北的方言区域和陕北的婚丧岁时区域。
以上第一种是音乐学界基本公认的学术成果,迄今仍具有重要理论价值[8]。第二种虽然表面看来是运用“非音乐要素”进行的划分,但讨论的依然是音乐学方面的问题。如杜文的意义就在于,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全国汉族民歌在不同方言区中是什么样的提供了基础;而蒲文则告诉我们西南地区传统音乐的旋律,分别在“平地、丘陵、高山”等不同地貌中有何区别。无疑,以上第一、第二种类型均具有较明显的音乐学学科属性。第三种则因作者的研究取向不同,而分别具有历史地理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属性*作者在此进行的“方言语音的划分”应属语言学范畴,而非民俗学中的方言研究。有关在方言研究中民俗学与语言学的异同,笔者曾请教过武汉地区的民俗学家。他们的解答是,这两个学科有交叉,但也有差异。前者侧重方言的语义、内涵;后者侧重方言的语音、语法等等。。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第三种划分的学术意义是什么?作为音乐学专著中的一部分,是否有“去音乐化”的嫌疑?笔者的基本看法是:无论运用哪一种标准进行划分,也无论其成果具有哪一学科的属性,只要具有原创性,就有学术意义,只要与解决音乐方面的问题有联系,就不能算“去音乐化”。
不过,需要说明并值得我们注意的也有两点:一是与上文所述民俗音乐研究的“跨界”情况一样,我们也须“格外小心”——一定要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对相关“跨界”学科研究现状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或发现新材料,或提出新观点。否则,将无学术意义。二是要与自己研究中所要解决的问题——某音乐及其相关事项——“接轨”。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毕竟是音乐学研究,需要解决的当然是音乐学方面的问题。所谓“接轨”的意思,并不是一定要在其中具体分析音乐形态,或详细描述音乐过程,但至少,这种划分结果与作者所研究的音乐是一种什么关系,则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诚然,如果作者不是为了解决音乐学方面的问题,又与音乐学研究无关,则另当别论了*这类研究虽然不具有音乐学学科属性,但其成果可以考虑像赵宋光先生的若干论文一样,直接投给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刊物,详参赵宋光:《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奥秘》(载《现代哲学》,1986年第2期,第23-27页)、《黄河河套双主槽绿化工程刍议》(载《科学中国人》,1999年第10期,第30-34页),等等。。
以上讨论聊供宝杰君与各位同行参考。
综上所述,宝杰君的《陕北音乐》是一部既有新观点,又有新材料,同时还有新问题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新作。学问之道,甘苦自知。宝杰君能在如今较为浮躁的社会环境之下潜心钻研,努力进取,其精神可嘉。我们憧憬之中的中国音乐理论大厦,也正需要这些安贫乐道者的默默奉献,才能逐步矗立于世界民族音乐之林。笔者为宝杰君取得的新成绩而感到高兴,同时更希望他在这一领域有更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面世。
参考文献:
[1]李宝杰.区域:民俗中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
[2][转引自]刘承华.序二[M]//李宝杰.区域:民俗中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7.
[3]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346.
[4]杨匡民.民歌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J].中国音乐学,1987(1):105-117.
[5]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6.
[6]杜亚雄.汉族民歌音乐方言区及其划分[J].中国音乐,1993(1):14-16.
[7]蒲亨强.西南旋律体系及其文化内涵[J].音乐艺术,2005(3):89-96.
[8]蔡际洲.乔建中与中国音乐地理学[J].交响,2015(1):22-30.
【责任编辑:吴志武】
收稿日期:2016-03-28
作者简介:蔡际洲(1952-),男,甘肃宁县人,武汉音乐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
DOI:10.3969/j.issn.1008-7389.2016.02.016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89(2016)02-013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