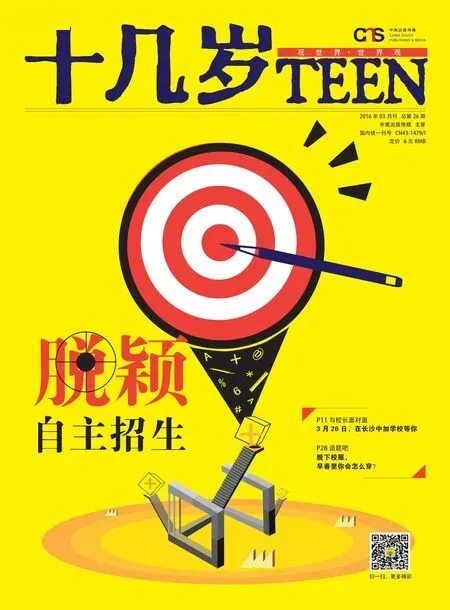沉淀
文/杨蕴之(长郡中学高1415班)
沉淀
文/杨蕴之(长郡中学高1415班)
山林中的原木,熬过了霜雪的冰封和太阳炙热的毒吻,经过匠人刀斧的打磨、削割,才成为有灵魂、有生命的工艺品。
我家墙上,挂着父亲年轻时弹奏的吉他。这把吉他用上等的枫木制成,表面镀了一层古铜色的烤漆。在阴冷的环境下,在沉淀的岁月中,留下了氤氲木香。
时光剥蚀了吉他发亮的外壳,隐约显现出其朴实淳厚的内在。当我捧起它,指尖划过的音符缓缓流淌,我听见它对我深情地诉说:“没有阳光照耀我,那我就感受鸟鸣;没有掌声赐予我,那我就内省发酵;没有欢欣鼓舞的岁月,那我就安静地等待,直到沉淀出我的真心。”我幡然感动:乐器坦然接受了岁月的打磨,岁月给了它更能拨动人心的曲调。
时光使吉他沉淀成为有思想的生命体。
我记得《月光落在左手上》这本书中,余秀华说:“我不是农民余秀华,也不是脑瘫患者余秀华,我是诗人余秀华。”这种自信与达观,是经过时光的打磨,岁月的沉淀,让自己更加成熟后的一种流露。
生活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内心的自我肯定与否定,才会变的有诗意。想起近期看的一部电影《时时刻刻》,讲述三个不同时代的女人和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达洛维夫人》千丝万缕的联系。时时刻刻,不仅是时光的流逝,也指这三个女人在精神的痛苦中熬过的点滴。她们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却都渴望冲破平庸生活的桎梏,渴求更有意义的生活,寻找生命的意义。除了各自的恐惧与渴望,甚至有过抛弃尘世的念头,她们依然坚持着,不让自己死去,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挣扎着、寻找着,渴望终有一日能够脱离平凡生活的泥淖。经历多了,就释然明白:在大千世界中,又有谁不曾熬过?在伟大的诗人面前,悲伤俯拾即是,遍地滋生。因而能够用“熬”的酸甜苦辣,酿成一壶醇香的酒。他们用一颗颗伟大的心灵,盛下了煎熬苦楚,输出了满纸的力量。
在最煎熬的时刻,我在小时代里抒写着个人的小情绪。波动起伏的心跳,像人生的高峰与低谷。我总是居高临下掠过高峰,在苦等慢熬中度过低谷。
又落泪了,像一壶慢炖的汤,时刻在沸腾,时刻在哭泣。可是当泪水蒸干,便是起锅之时。熬过了,成了经历,没熬过,仅是无味的弃水。我正经历寒冬,带上我耐严寒与酷暑的铠甲,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才会迎来不远的春天。
那几声蝉鸣,熬过了七年;那几丛葳蕤,惊艳了岁月。当我看到未来的光,才会想起这个痛苦。而我的汤,已放好调料,只等时光来添火。
琴声悠悠,时光悠悠。那几声动人的旋律,并不胜在响亮与绵长,而在于它经历的时光和沉淀下来的点滴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