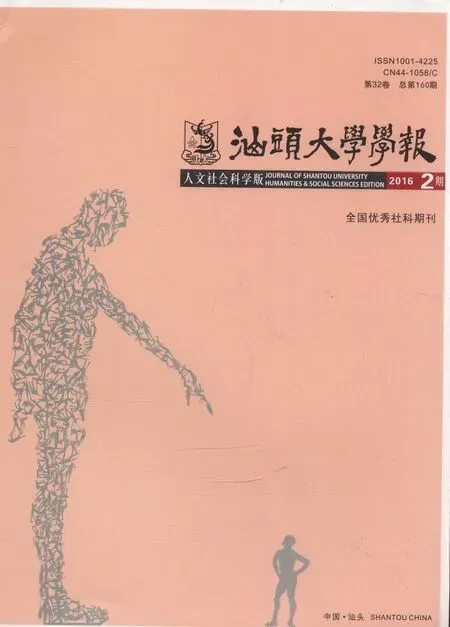论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
周艳云
(韩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论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
周艳云
(韩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广东潮州521041)
摘要:食物权已被国内外学界广泛认可,但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却鲜有学者论及,而它却是食物权得以保障和实现的关键所在。故对于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这一领域的系统化研究就尤为必要,其对充实与完善食物权的研究空白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确立与基准对于食物权的实现十分重要。前者的内在逻辑涵摄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的历时流变、理论证成、法律理据及其具体内涵,这些内容不仅可以论证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正当性,而且可以明确它的具象性。后者以基本生存、相对平等以及国家能力三个维度为基准对给付程度进行规范,它是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履行的关键。
关键词:食物权;给付义务;内容建构;给付基准
“民以食为天”的观念揭示了每个人的生存对于食物的天然依赖性;同时警示任何统治者,食物是民众关心的首要议题。但食物权作为人权的确立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流变。进而言之,食物权的实现还要有赖于国家义务的履行,尤为关键的是国家给付义务的落实。遗憾的是,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至今没有引起学界重视,更遑论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的确立与基准。因此对于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这一领域的研究尤为必要,本文专门针对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有关问题展开论述。
一、食物权给付义务的历史流变
人类历史上由于食物的匮乏性以及个体获得食物的不平衡,学界一直都在强调对民众食物权的国家保障义务,但从法律的强制性角度规范食物权的国家义务的做法还是现代的事情。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历经了从道德义务到法律义务,从法律的消极尊重、保护义务到积极的尊重、保护义务并积极的给付义务的转变过程。
(一)第一阶段:食物权的国家义务的道德属性呈现历时性存在
我国自古就有圣人之治是为腹不为目的朴素理念,后来发展为“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汉书·郦食其传》)的思想,它的真正目的是告诉统治者如欲统治长久、稳定,必须充分关注普通民众的事情,以被统治者的关怀——食物为其关注的重点。尽管这种思想的根本视角是统治阶级的统治的稳固性、长期性,但也隐喻了统治者对于普通民众食物的义务性。无独有偶,西方也有类似的观点,且这种思想在西方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如古希腊的一些城邦的法律规定,当一个人如果身体衰弱无法劳动且家里没有或只有很少的一点财产,只要经过了议事会的审查,就可以得到食物的补助津贴,其数量是每个人每天最多可以得到两个俄勃尔。[1]以现代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作“食物权”的保障最多是道德上的,在古代中国尤其如此。因为它是站在统治阶级观点为统治服务,它们的实现依赖于统治阶级的怜悯与同情,依赖于官吏升迁的需要;普通民众的“食物权”并没有法律上强制的国家义务。
(二)第二阶段:食物权从软弱的道德义务转变为强制的法律义务
食物权从软弱的道德义务转变为强制的法律义务是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美国思想家乔治·梅逊于1776年6月12日拟写了一份《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的报告,后来获弗吉尼亚议会通过,食物权的道德义务由此具有了法律的意义,不过它并没有以独立的形式出现而是内涵于财产的权利,“人生而自由与独立,享有某些天赋权利,他们在社会里不能因任何的契约而被剥夺这些权利;……他们享有包括获取与拥有财产、追求和享有幸福与安全的手段等生活与自由的权利”[2]。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2条也有类似的规定:“自由、财产、安全及反抗压迫等权利天然不可剥夺,人们结合的政治目的就是保护这些权利。”①http://www.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2366,2014- 10- 19。当然,食物的获得是其应有之义。这显示食物权终于从道德层面走入法律的视野,尽管还没有明确的以“食物权”三个字出现在法律上,然而毕竟预示了食物权存在的现实可能性。遗憾的是,资产阶级虽然在法律上宣示了食物权的间接存在,但在现实中并没有投入现实的力量,这告诉人们食物权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国家义务至多还是消极义务,国家尊重和保护私人获得财富包括食物的权利,食物权国家积极给付义务也是闪烁其词,还没有被国家主流认同,这一局势的改变还有待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三)第三阶段:法律上对食物权的确立和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强调
历史终于为食物权的确立及其国家给付义务提供了机遇,20世纪4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人们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严重影响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与发展,粮食短缺形成对劳动力生存的威胁,劳动力生存的威胁将导致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滞及社会的动乱;美国尤其如此,美国法律研究所的一个研究机构于1942年拟写一份人权法案的草稿,其第14条规定:“政府有义务采取确实有效的措施,切实保障美国国民获得生活必需品,因为获得充足的食物和住房是他们天然的权利。”第15条对社会保障权定义如下:“国家负有制定综合性计划促进民众健康的义务,提供医疗服务并为丧失谋生手段的人提供补偿,以此使民众预防疾病与事故。”[3]这份建议稿后来被提交到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人权委员会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时,吸收了“人们有获得良好的食物和住房的权利”,食物权正式明确地规定在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之中,即包括食物在内的适当水准权。这一权利后被联合国大会于1957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第1款所强化和丰富:“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后来对此详细地阐明:“满足个人的饮食需要的食物必须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要达标,且是无害的物质,并符合接受者的文化习惯。同时它还必须获取的时候是可持续、不妨碍其他人权的享受的方式获得。”②http://www.doc88.com/p- 3761644322259.html2014- 10- 20。国际性、区域性文件及其世界众多国家的宪法对于食物权的规定,宣示了食物权在法律上的确立及其国家给付义务的加强。
二、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的理论证成
食物权的发展历程向人们宣示了其现实的存在,那么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这个表象的存在是否有其必然性,还需要从理论层面对其证成,以展示其发展的必然性、存在的不可或缺性。
(一)食物权主体的内在本质性: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根本依据
根据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食物权主体的内在本质性又分为物质性与价值性,物质性是人作为一个自然存在物或人要生存下去必须依赖一定的物质基础——食物;价值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即人性尊严,只有二者同时兼备,人才是完整的存在。
1.基本生存: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物质诉求。食物是人们的最基本生理需求,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认为包括食物的需求在内的生理需求是人们最为基本的需求,并且还对于食物的需求进行了形象的描述,他说对于一个同时需要爱、安全与食物等的人来说,首当其冲应该是食物,尤其是处于饥饿到极端的人,此时他的全部活动的中心与主题全部都是食物,无论他是在做梦还是在醒着。[4]尽管马斯洛的论述有些偏颇,但他揭示了食物对于人们生存的重大意义,食物是每个人的最为基本的需求,故食物权是人们基本生存的根本保障。台湾学者许宗力提出了“绝对生存的最低需要”理论,它是指每个人存活的最低需要,这个最低需要必须国家予以保障。由上可知,食物是人们生存的最为基本需要,在人们自己穷尽一己之力还不能实现自己的食物权时,此时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无疑是实现人们食物权的最为有力的保障。并且,在通常食物并不匮乏时,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提出的食物安全也是极其重要的保障。
2.人性尊严: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价值始基。人性尊严其本质是宣示人之所以为人,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之所在。具体而言,每个人作为个体存在,其本身就是目的,这个目的表征为最大可能性地充分实现自己,个体其实现可能性的物质载体就是自己的身体,具有生命力的身体的持续存在必须有相对充分的食物,因此食物是人性尊严的基本条件之一。同时,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与现实社会中,食物常常表征着个人的尊严。尽管存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不平等,但一般人认为生活里具有丰富食物的人要比整天饥饿的人更有尊严。Alan Gewirth认为人性尊严是人权的原则性、普遍性的基础内容,人性尊严与食物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5]食物不仅通过生命显示人性尊严的现实性,而且还通过种类的不同、丰富的程度表征着尊严的有无、多寡。正因为人性尊严的本质价值,进一步提升了食物的重要性、基础性。食物首要指向的是食物安全,食物安全既包括食物的匮乏与否,也包括食物的卫生与否,在这两者之中,首先关注的是食物的匮乏与否,其次是食物的卫生与否,但无论何种意义上的食物安全,都需要国家积极地履行食物的给付义务。现实中因各种因素,尤其是天灾人祸,个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来维持自己生命的存在,这时国家给付义务的履行尤为关键。在古代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更多的是食物的匮乏与否的安全,在当代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投入更多精力于食物的卫生安全。
(二)食物权主体的外在语境: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现实要素
食物权主体的外在语境主要是指以社会的视角说明食物权主体的国家给付义务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法治国发展到社会法治国时代,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矛盾重重,许多人处于极端困苦地位,他们如果得不到国家的食物给付,正常生活将难以为继。这既影响政治的稳定,同时也造成社会、经济的恶性循环。社会法治国原则就是要以国家承担相应的责任,帮助那些生活困苦、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还不能脱离困难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得以生存,实现社会良性、持续发展,所以社会法治国原则是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固有涵摄。
社会法治国原则是指国家依据人民的请求或宪法根据,通过法律制度、司法机关、公共职能部门、提供给付等措施以确保整个社会的公平、公共的福利、以及安全等。[6]其肇始于19世纪,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的大生产、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造成了大量包括劳资在内的社会矛盾,许多贫困的人民无法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生存,更遑论发展了。这时资本主义国家信守的“守夜人”似的国家已经不合时宜,如果继续下去,矛盾激化将影响整个资本主义的安全与发展。因此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家的给付义务以确保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地位的人们能继续生存下去,以确保资本主义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及其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
虽然社会法治国原则是随着历史发展的被迫始然,但客观上确实使国家的角色与职能出现了变化,国家的职能由压迫者、管理者向服务者、给付者逐渐地转变,由于国家给付义务由隐性向显性发展,为弱势地位者尤其是极端贫困者提供给付,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了最低程度的相对平等,促进了人权的相对平等,因为食物权是基本的人权,它确保了每个人的基本生存、发展,对于每个人都极端重要、特别是对处于贫困之中的人更是如此。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社会法治国原则通过国家的食物给付义务给与处于困苦中的人食物帮助,保障社会稳定。台湾学者许育典认为,社会的衡平并不是简单的直接分配,它需要一种复杂的制度实现国家的给付义务;[7]国家给付义务的加强是社会法治国原则应有之义,它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共同进步、协同发展,同时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相对平等。
三、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法律理据
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虽然有了理论上的证成,但如果没有具体法律、法规、文件等规范性的制度载体,就只是空中楼阁,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力量。那么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在国际、国内的规范现状又如何呢?
食物权作为基础性人权,被很多国际、区域或国家的文件、法律所涉及。其中,较为密切且详细规定食物权的国际、区域性的文件有:《联合国宪章》第1条与第55条,《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第1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条第2段,《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第1款及其第2款、第11条的第12号一般性意见,《德黑兰宣言》、《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曼谷宣言》、《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条第2款、《儿童权利国际公约》第24条第2款第3项与第5项及其第27条第3款、1996年世界粮食安全的《罗马宣言》、《世界粮食峰会的行动计划》第2段、《美洲人权公约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补充议定书》第12条第1项、《非洲人权和妇女权利宪章附加议定书》等。①Guide on Legislation for the right to food.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rome, 2009:2。由于食物权对于个人的极端重要性,即使是处于战争等特殊情况,基于人道主义也要保证食物权的给付义务的实现,有关国际特殊时期食物权的给付义务实现的法律有:《有关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第26条、《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第55条、《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协议2)第14条、《〈1949年8 月12日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对国际受害者的保护〈协议1〉》等。不仅国际、区域性的文件对于食物权进行详细规定,世界各国宪法争相直接或间接地把食物权嵌入其中。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乌干达、乌克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尼日利亚、南非、巴拿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苏里南等国的宪法通过直接规定食物权是一种法律制度而赋予其强制力,而巴西、古巴、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巴拿马、巴拉圭、斯里兰卡、乌拉圭等国宪法则特别强调对于特殊群体的食物权的保护,另外部分国家,如爱尔兰、瑞士等国家宪法通过对于适当生活水准权的保护来实现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当然世界上还有部分国家通过对最低生活保障、健康权的保护等间接方式来规定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②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国家一级承认食物权》,载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07/j0574c.htm.2014- 10- 22。由此可见,无论从国际、区域性文件,还是从世界各国宪法,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已为国际社会所认可。
国内有关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规范大体有这几类:第一类是概括地规定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如我国宪法第45条;第二类是规定保障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中的食物来源的保障性法律法规,如《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三类是规定在特殊情况下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73条与第6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粮食储备管理条例》第38条与第31条和第32条、《防洪法》第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9条、《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第四类是特殊人群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49条、《残疾人保障法》第23条;第五类是针对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中的食物卫生安全的法律法规,如《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4条、《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由此可见,我国现存众多不同级别、不同层次的有关食物权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它们从不同的视角丰富了食物权的内容。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部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直接明确、详实地确认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具体内涵,故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内涵还需建构。
四、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内容的建构
在宪法学中,国家义务是基本权利实现的重要保障,由龚向和教授提出国家义务分为尊重、保护、给付的义务三分法为学界所认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给付义务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越来越处于核心地位,我国学者张翔认为国家给付义务是指国家以积极作为的模式为公民提供某种利益,其利益可分为物质性的、法律程序性的以及服务性的三类。[8]此定义导致了逻辑外延的不周延性,即国家积极的作为模式内涵既包括国家给付义务,也包括国家保障义务,因为国家保护义务又可分为预防、排除、救济等内容,而这些都是积极的作为行为模式。[9]因此国家积极作为的方式既有国家保护义务,又有国家给付义务。因此有学者认为:“只有这种国家以确保人之为人的尊严为出发点,给予物质和经济利益为主的积极作为方式,才是国家的给付义务。”[10]然而这种观点把国家给付义务主要限制在物质经济层面,无法涵摄国家其他方面的给付内容,有失偏颇。结合国内外学者对于国家给付内容的论述,我们可以把国家给付义务分为物质性给付、制度性给付与服务性给付。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虽然主要是物质性给付,但如果没有制度性给付与服务性给付,物质性给付的内容很难顺利实现;同时物质性给付、制度性给付与服务性给付的内涵各有侧重,价值上互有区别,故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物质性给付、制度性给付与服务性给付。
(一)物质性给付
为了实现人们的食物权,更是为了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国家必须给付物质或金钱等,或与之相关的权益。物质性给付的总体要求是基于人性尊严,免除饥饿、适当营养。在这里人性尊严含义有二:第一,给付食物时要充分尊重给付对象的文化传统与习惯,既包括他们的禁忌,也包括给付的方式,如信仰伊斯兰教的被给付者禁食猪肉,给付他们食物就不能包括有关猪肉的东西;第二,给付时不要附加条件,尤其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条件,古有不受嗟来之食,何况身处现代文明之中的人。换句话而言,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为了生存下去而使自己受到羞辱或被剥夺基本自由,例如通过乞讨卖淫或奴役劳动。”[11]免除饥饿是食物权的核心内容,[12]是指给付的食物数量要充分和质量要良好,这样才能到达维持他们生命的能量,潜在的内涵还应包括要有一定时间的持续,直到他们可以有其他条件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适当营养虽然不是要求给付的食物色、香、味俱全,但也要适当考虑食物的多样性,这样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同时注意被给付者的价值认同性。实际上,这样要求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获得充分且适当质量的食物的同时,能延习自己的文化传统,过着身体与精神健康、有尊严的生活。”①联合国人权事务:《食物权》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food.htm,2014- 10- 28。国家在给付金钱时,金钱的数值要能达到满足以上食物物质性价值的要求。与物质相关的权益指有关物质的运输、搬运等,因为对于许多被给付者,尤其对于丧失永久生活自理能力的人,如果没有与物质相关的权益,他们是不能实现自己的食物权的。当然,物质性给付既可以国家直接给付,也可以通过购买、招标等形式委托社会机构间接地实现国家的给付义务。在我国,由于国土面积广阔,各地发展水平相差巨大,且城乡差别显著等情况,我国食物权的国家物质性给付内容存在巨大差别,这还有待于国家进一步努力,尽可能地实现相对平等。
(二)服务性给付
食物权的国家物质性给付义务只是告诉人们可以从国家获得物质、金钱或其他有关物质的权益,但具体落实需要一定的组织、机构、团体等遵循一定的程序组织、管理等才能实现。因此食物权的国家服务性给付存在很是必要,它有助于食物权的物质性给付的实现。食物权的服务性给付不仅使物质性给付义务落到实处,同时使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得到进一步充实。服务性给付内容首先包括定期通过某种大众媒介播报食物安全情况以便民众了解相关食物信息,同时调查收集被给付人员的食物需求、贫困程度、告知给付食物信息、通知相关人员领取食物等;其次,设置公共设施、提供公共平台,以便民众及时查询了解给付信息、给付情况等,国家还可以通过授权、优惠政策或其他措施举办相关的职业技术培训,免费为受给付民众技术培训服务,提高他们获得食物的能力,做好给付的后续工作;再次接受有关食物权的申诉、控告,做好有关食物权的诉讼服务等,补救物质性给付不足的工作。
(三)制度性给付
任何行为如要获得长效性、规范性,就必须仰赖于一定的制度,因此食物权的国家制度性给付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它可以有效保证物质性给付与服务性给付的实现。食物权的制度性给付内容有三:第一,法律法规上确认食物权的存在;第二,物质性给付与服务性制度化,以确保二者的规范化,实效性;第三,保障食物权的行政救济、司法救济。食物权虽然已经确立,但具体内涵不是十分清晰,这需要立法机关进一步明确,以利食物权的具体落实。为了实现食物权,还需要相关的制度,如工作制度、调查制度、基准制度、发放程序、行政救济制度等等。
当前我国相关制度并不健全,这严重影响食物权的实现。如低保家庭的确定,没有一个正式的调查制度,而由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代为行之,然后上报;并且没有一个具有食物权可行性的基准制度,这使食物权的效力大打折扣。尽管每个人都耳熟能详“无救济则无权利”这一法谚,但有关食物权的救济却很苍白。虽然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了我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有从国家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没有直接确认公民的食物权。尽管也有具体的相关制度,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但是制度的具体可执行力较为空泛。尽管裁决权利的争端是国家必须承担的义务,[13]而我国公民鲜有提起诉讼,即使是行政申诉亦很少。其中缘由,既有我国公民受无讼传统的影响,也有制度性给付不足的原因,还有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缺乏相应基准的因素。
五、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基准的审查
虽然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内容通过建构得以确认,但如果这些义务没有相应的基准,国家给付义务也很难落到实处,因此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基准亟待确立。我们可以从横向与纵向两个视角来考量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基准。
(一)横向基准:食物权国家给付的对象
食物权的国家给付对象是全体国民,因为食物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必需品,因此食物权主体具有普遍性,任何人都不能因身份、地位、族群、性别被剥夺食物权。当然,通常人们认为食物权的国家给付对象只是那些处于生存危机之中的人们,然而由于每个人对于食物的需求性,再加上社会法治国原则,食物权的对象范围扩及到每个国民。即使如此,食物权的对象还是要有所区别,可以分一般对象与特殊对象,否则有失公平。一般对象主要是指在通常状况下,给付对象依靠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相应的食物,这时国家给付义务主要是食物权的国家服务性给付与制度性给付,主要是维护他们的正常食物水准,如食物的充足性、质量安全性、诉求畅达性。特殊对象主要是指公民在年老、疾病或因天灾人祸等因素丧失劳动能力,无法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足够的生存食物,这时国家在提供食物权的服务性给付与制度性给付以外,更主要是提供物质性给付,这时主要彰显的是公平。
(二)纵向基准:食物权国家给付的程度
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纵向基准主要是为食物权的国家给付程度划界,使国家给付有一个明确的范围,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值。这是因为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变万化;同时,不同时期发展程度有所不同,如果我们采取一刀切的方法,规定一个精确的数值,这反而是最大的不实事求是,不利于国家给付目的的实现。虽然我们给出一个给付范围,但并不表示它没有现实的执行力,因为我们为食物权的给付范围给出了上限与下限,同时又在上限与下限之间作出了相应的评判依据,即相对平等。这样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现实性。
1.最低生活标准为下限:食物权国家给付的基本标准。最低生活标准是一个人维持自己生存的基本食物,它的具体内容包括免于饥饿和适度营养,这是一个人维持起码生存的生活水准,也是一个人最低的生存条件,[14]现在我国就是根据国情执行此标准,但其难题是如何确定最低生活标准。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把确定最低生活标准的权力下放给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而地方政府制定标准相对简单,如河南省洛阳市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细则第6条计算城市低保家庭月人均收入的公式为:家庭前6个月实际收入总和÷家庭人口÷6个月,那么家庭前6个月实际收入总和又如何计算?同时,食物权的国家给付责任由地方政府承担,故最低生活标准又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及财政的影响,由于地方经济与财政水平参差不齐,现实给付水平偏低于低保水平已成共识。[15]因此最低生活标准的科学制定迫在眉睫。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先后实行过多种生活基准方式:基本标准生活费方式、菜篮子方式、恩格尔系数方式、差距缩小方式、水准均衡方式等。[16]结合我国国情,最低生活标准应该全面考量地区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当地经济发展等因素来确定。
2.相对平等为准则:食物权国家给付的价值标准。相对的平等是给每个人以发展的机会,这也是如哈耶克所说改进人们发展的状况采取的措施,清除发展的障碍,同等地适用所有人。[17]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平等,只有相对的平等。为了追求食物权的给付平等,人类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出现了形式平等、实质平等、程序平等……但任何的平等都是一定语境下的平等,既有其积极意义又有其不足之处,如无处不均匀,曾寄托着我国传统社会普通民众的食物的形式平等,其实这种平等没有考虑到个体的差异性的平等,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不平等。因此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在某种涵义上都是一种不平等,故世界上只存在相对的平等,不存在绝对的平等,对于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尤其如此。在食物权的国家给付对象上有一般对象的给付与特殊对象的给付,由于情况各异,其给付内容也应该各不相同;物质性给付的多少因对象情况的不同也应该相异,所有这些都是相对的平等,这种差别性处理,是为了达致实质的平等。[18]当然,这些处理的不同,并不表示在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不存在形式的平等,如大致相似的情况,物质性给付应该大体相同,另外制度性给付也应该相同,因为制度性给付是一种抽象、普遍性的给付,如果相异,就会造成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
3.国家能力上限:食物权国家给付的现实标准。国家能力简单地说是指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统治国家、管理社会、实现目标的力量。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是国家管理社会的行为之一,故它是国家能力的一部分。事实上,无论国家机关的存在还是运行,以及统治国家、管理社会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这里的经济基础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指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是国家能力的潜在基础;另一部分是指一国的财政,这是国家能力的直接基础。从实质上来说,经济规模的发展还只是国家能力的潜在基础,只有国家财政才是国家直接支配的经济基础。“国家财政规模的大小,与国家权力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19]职是之故,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以国家能力为上限,可转换化为其以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为上限。
正常而言,一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的关系,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保障水平也高,反之则低。[20]这是因为如果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保障水平过高,国家经济承受不起;反之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保障水平低,一些需要救助的人群得不到有效、充分、及时的救助,造成社会不公平。以上两种情况都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是社会保障的内涵之一,上述原理同样适合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是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度量的上限的客观基础。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还不是国家直接支配的财政,国家直接支配的经济必须通过税收等方式转变为国家的财政,这才能有效地保证国家给付义务的实现。因为没有国家财政,国家给付义务将无从实现。[21]在我国,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各地的救助义务由各地各级政府的财政承担,这就导致了各地救助的范围、标准各不相同,因为我国地域广阔,各地财政能力也各不相同。各地履行国家给付义务都是以各地的财政能力为限制,财政收入成为食物权国家给付度量的现实基准。因此,食物权的国家给付标准的上限要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财政能力大小为限制。
参考文献:
[1]夏正林.社会权规范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105.
[2]董云虎,刘武萍.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续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15- 16.
[3]刘海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207.
[4]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5- 16.
[5]Alan Gewirth. The Basis and Content of Human Rights,Morten E. Winston [M].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Right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88:237.
[6]法治斌,董保城.宪法新论[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81- 82.
[7]许育典.宪法[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6:79.
[8]张翔.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从基本权利分析框架的革新开始[J].中国法学,2006(1):26.
[9]龚向和,刘耀辉.论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J].政治与法律,2009(5):61- 63.
[10]龚向和.社会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84.
[11]艾德,等.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M].黄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53.
[12]Rolf Kunnemann.Violations of the Right to food [M]// T. van Boven, C. Flinterman and I. Westendorp(Ed).The Maatstricht Guidelines on Violation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Utrecht, Netherlands, 2005 SIM Special(20):165-191.
[13]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M].林荣远,冯兴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37.
[14]陈爱娥.自由-平等-博爱:社会国原则与法治国原则的交互作用[J].(台北)台大法学论丛,1997,26 (2):5- 6.
[15]杨思斌.中国社会救助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175.
[16]韩君玲.日本最低生活保障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65- 166.
[17]弗里德里希·冯·哈邓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111.
[18]大须贺明.生存权论[M].林浩,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4.
[19]猪口孝.国家与社会[M].高增杰,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18.
[20]郑造桓.公民权利与社会保障[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41.
[21]袁立.宪法劳动权的保障研究[D].福州:东南大学,2012:210.
(责任编辑:汪小珍)
中图分类号:DF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4225(2016)02- 0079- 08
收稿日期:2015- 04- 15
作者简介:周艳云(1979-),女,湖南衡阳人,韩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东南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农民宪法权利与中国城镇化发展研究”(KYLX_0078)潮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项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研究”(2014- A-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