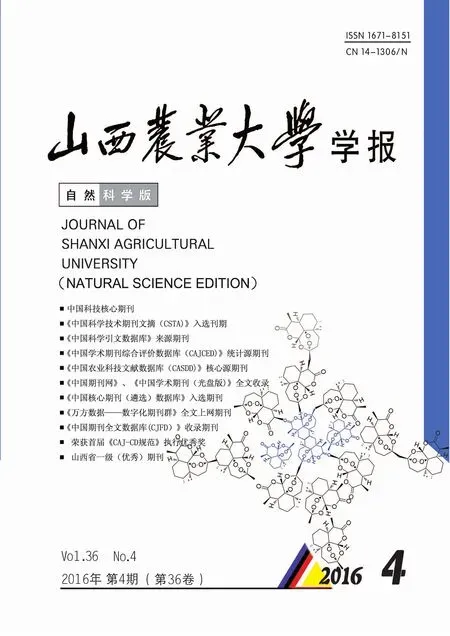几何形态测量学及其在半翅目中的研究进展
李荣荣,李生才,张虎芳
(山西农业大学 农学院,太谷 030801)
几何形态测量学及其在半翅目中的研究进展
李荣荣,李生才,张虎芳
(山西农业大学 农学院,太谷 030801)
摘要:几何形态测量学是基于笛卡尔地标点的形状统计分析方法。它能够完整地保留原始样本的几何形态信息,并配合使用复杂的统计学计算对生物形态进行分析。几何形态测量学在生物学领域应用广泛,其原理和方法在生物的分类、系统发育、昆虫监控及昆虫空间结构等研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对几何形态测量学的发展、重要概念、研究方法及其在半翅目昆虫中的研究进展做简单阐述。
关键词:几何形态测量学;半翅目;分类;系统发育
生物学中的许多研究都与形态有关,几个世纪以来生物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生物性状的比较,而这种研究方法主要基于形态描述。直到20世纪初生物学才开始从描述性阶段向量化阶段转变[1]。20世纪60到70年代,生物测量学家开始对生物形态中的线性距离、角度或比例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这种分析方法被称为传统几何形态测量学[2]。虽然它量化了生物的形态特征,并使用多元统计方法分析这些数据,但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它只能算是几何形态测量学的雏形。Slice详细描述了传统几何形态测量学的缺陷[3],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线性距离、比例及角度并不能真正的捕获并保存样本的空间形态信息。这是因为在对标本进行测量时,不同的形状可能会获得相同的距离数值。比如在对不同形态的昆虫进行测量时,尽管它们的形状并不相同,但它们的长和宽却可能是一样的。
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形态结构的量化及数据的分析方法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如何获取有用的几何形态特征,并在统计分析过程中尽可能完整的保留这种信息,Rohlf和Marcus称其为“形态测量学的革命”[4]。这门日臻完善和成熟的学科被称为几何形态测量学。几何形态测量学是关于形态定量比较的工具[5],目前,几何形态测量学倾向于使用地标点(Landmark)数据。地标点是位于标本上的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几何形态同源位点。每个地标点在笛卡尔坐标中都有着自己的坐标值,几何形态测量学正是利用这些坐标值来捕获生物形状并通过多元统计方法储存并分析这些形态特征信息[6]。
与传统形态测量学相比,几何形态测量学引入了坐标轴的分析方法,这不仅仅使它可以得到关于大小方面的信息,通过地标点间的相对位置还可以储存样本形状信息。同时它还使用多种方法使样本形状及形状差异变得更加直观[7]。
本文简要概述了几何形态测量学的发展历程,重要概念、研究方法及其在半翅目昆虫中的研究进展,以期为国内半翅目分类工作提供新思路。
1几何形态测量学中的重要概念
1.1形状(Shape)和形状改变(Shape changes)
形状和形状改变是几何形态测量学中两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物体的形状是一种与物体位置(Position)、方位(Orientation)、大小(Size)无关的几何性质。也就是说改变物体的位置、方位或大小并不影响物体的形状[8]。
形状改变是形状概念的基础,也是几何形态测量学所要揭示的内容[9]。许多统计分析(如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等)的结果可以显示形状改变。形状改变与形状差异(Shape difference)非常接近,但并不完全相同。形状差异暗示两个物体形状有所不同,但是并没有直接指明差异所在。而形状改变却直接指出原始样本和目标样本之间有哪些差异,比如性别二态性。由于形状对应于形状空间或正切空间中的某个点,形状改变就是原始样本所对应的点与目标样本所对应的点之间的动态变化,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具有方向和大小的向量。
1.2肯德尔形状空间(Kendall’s shape space)
在生物学研究中经常使用数学空间来表示两个复杂物体之间的关系[10]。肯德尔空间是几何形态测量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形状都对应于形状空间中的某个点,形状空间中的每个点也都对应着某一个形状。由于形状空间是曲面的,非欧式空间,因此使用线性的正切空间即欧式空间来表示样本在形状空间中所处的位置。这就像是地球仪上两点的距离,使用平面投影地图上的直线距离来表示一样[9]。在生物学研究中,经常会比较两物体之间的形状差异,使用上述方法非常有用。同形状空间一样,正切空间中的每个点也表示一种特定的形状,每个形状也对应于正切空间中的某个点。正因为这种一一对应关系,我们就可以在形状空间或切线空间中重构生物的生理形状。因此,这就使得抽象的统计结果和真实的物体形状可以相互转化。这正是几何形态测量学能直观地显示形状差异的关键所在。
2几何形态测量学研究方法
2.1图像的获取
用于几何形态测量学分析的数据可以从二维或三维的数码图像中获得。二维数码图像获取相对简单,但是由于照相系统自身在捕捉、储存及展示功能等方面都会有一定误差,数码图像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才能用于几何形态测量学研究。选择相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像素、精确度、色调范围、色纯度和精度、白平衡以及图像噪声等因素[11]。阴影以及物体表面的光线反射会遮盖标本的一些重要形态特征,所以推荐使用具有最佳可视性效果的光源。拍照时要注意以下几点:1.将标本置于柔软的暗色水平支撑面上,尽量保持标本处于水平状态。2.图像应该具有标本标签以及比例尺。3.标本与相机保持固定的距离,并保证标本位于图像中央[12]。
三维图像获取比较复杂,成本较高。目前,三维数据的获取方式有多种,既可以建立表面形态,也可以建立内部形态。利用表面激光扫描仪、原子力显微镜等均可以构建表面形态图像,显微CT、同步辐射CT、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侧共振仪可以构建内部形态的三维图像。通过仪器生成的原始图像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处理才能用于分析[13]。
2.2地标点的提取
得到数码图像后,可以使用专门的地标点提取软件进行提取。如Rohlf开发的TpsDig软件。地标点按Bookstein的选择方法一般有三种类型,亦被称为 “Bookstein three type of landmarks”:Ⅰ型地标点是指解剖学上代表不同组织、器官、骨骼或骨缝的联接点,如昆虫翅脉的交叉点;Ⅱ型是解剖学中结构的顶点,代表标本形态结构的几何特征,如翅的顶点;Ⅲ型是解剖学中结构的极值点,代表一个点到其它某一点的最远或最近距离、中点或直径距离的两端[14]。一般选择Ⅰ型或Ⅱ型地标点,因为这两种地标点很容易从每一标本的解剖学特征上准确找到,重复实现性很强。
地标点选择的标准:一是它们是解剖学上的同源位点;二是它们在解剖学上的相对位置不能移动;三是尽可能地提供最完整的形态信息;四是具有准确性和重复性;五是位于同一平面中[12]。但在实际研究中,有时标本结构中缺少可以明确定位的地标点,因此引入半标志点。半标志点是位于一条曲线上,并按照一定的规则(如按等长或等比例划分)确定位置的点阵[12]。滑动半地标点可以通过滑动将形态变异过程中出现的扭力达到最小[15]。
2.3叠加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标本的摆放位置、大小、方位等因素会影响地标点坐标进而影响形态差异的比较,所以在比较之前需要去除这些非形态差异。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是基于最小二乘法的普氏叠加(Procrustes superimposition),包括以下3个步骤:1.移动,将所有物体的地标点结构(Landmark configration)平移使它们拥有共同的中心(Centroid)。一般情况下会把中心移到整个坐标系统的原点位置。这个步骤可以消除样本位置对形态差异的影响。2.缩放,缩放地标点结构使它们拥有共同的质心(Centroid size)。这个过程消除了样本大小对形态差异的影响。3.旋转,在对两个样本进行叠加处理时,将其中一个置中并缩放了的样本轮廓沿着另一个轮廓旋转,直到同源地标点之间的欧式距离平方和达到最小。如果样本更多的话,就需要用到广义普鲁克分析(Generalized procrustes analysis, GPA),其原理与两个样本间的叠加一致。通过旋转可以消除由于摆放造成的非形态差异。
样本叠加后产生的地标点被称为普氏形状坐标(Procrustes shape coordinaters),样本同源地标点之间的差异就可以用来描述形状差异。通过普氏叠加会产生一个所有样本组的平均形状(Average shape),在这个由地标点所围成的平均形状周围散布着来自各个样本的对应地标点。个体差异与平均形状之间的差异叫做普氏残差(Procrustes residuals)。两组普氏形状坐标之间的欧氏距离被称为普式距离,并以此反映两组地标点形态之间的差异性或相似性[10]。
2.4变形网格
直观地展示形状差异及形状改变是几何形态测量学的最基本的目的。利用变形网格进行形状比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15年D’Arcy Thompson’s建立“Cartesian transformations”形态差异可视化理论。D’Arcy Thompson构建了一种变形网格,通过定位样本间同源地标点来展示一种生物相对于另一种生物所产生的形状改变[16,17]。1528年,Albrecht Dürer在其著作中也提到这种方法。Dürer和Thompson的方法虽然能实现差异的可视化,但其操作过程都是手动的,没有包括任何正规的算法。1989年,密西根大学的Bookstein提出了真正的有突破意义的差异可视化方法[18],即薄板样条分析法(Thin-plate spline, TPS)。这种算法取自于材料物理学,能够利用插值(Interpolation)的方法在样本间已知的坐标值间找到逼近值。薄板样条分析也是半地标点技术的核心。
薄板样条插值功能使得两个几何形状之间的形状差异或形状改变可以从该变形的网格中读出。在计算的过程中,薄板样条分析可以独立地应用于每个坐标轴,因此它既可以应用于二维坐标也可应用于三维坐标。但是实践证明变形网格在三维形态差异的可视化中效能较低。弯曲能(Bending energy)是两地标点结构间形状差异的度量,这个过程中并不要求进行普氏叠加。但是弯曲能不是对距离的数学测量,因此不能用于统计学分析[10]。
2.5统计分析
几何形态测量学的统计学分析是通过普氏形状坐标实现的。传统的几何形态测量学对距离、距离比、角度、体积等进行的多元统计分析基本不涉及同源性。几何形态测量学中,形状差异都包括相同的单元,这样分析也就基于相关矩阵。多元统计分析比如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多变量回归分析(Multivariate regression)、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 least squares)等的结果能够保存这个矩阵,并能够被视为原样本的真实几何形态。统计分析与二维或三维形态数据的数学基础是相同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一些在传统几何形态测量学中常用的统计方法如多元回归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典型相关分析(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和典型变量分析(Canonical variate analysis)不能等价地应用于几何形态测量学,最重要原因是它们不能保存普氏矩阵。另外由于它们的算法与地标点的协方差矩阵相逆,因此计算结果可能是不可靠的。而普氏形状坐标通常是高度相关性的,尤其是使用半地标点时,这样就只能产生单独的一种不可逆协方差矩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形态差异数变少,结果也不会受到干扰而且还能直观地反映形状改变。
典型变量分析(Canonical variate analysis, CVA)能够确定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类群的平均趋向有何不同,因而几何形态测量学中经常用来作为分类鉴定的工具。然而当变量数与实例数相近时,即使不同的类群拥有相同的平均形状,CVA也会将它们分为不同的两个类群。
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能降低所研究的数据空间的维数,是一种用低维度呈现多组变量数据的方法。其操作原理是对样本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分析及对代表样本间普式距离的数据进行刚性旋转。它相当于把原始数据的多维变量空间投射到二维或三维坐标平面上,而信息损失最小。特征向量或主成分包含着对多元变量线性组合的加权,并且可以看做是实际的形状变异[14]。但主成分是统计分析时根据实际样本组成人为选择的,因而不能被认为是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因素[19]。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当一个物种或类群的第一主成分包含了异速生长,即形状差异是由整体大小的差异导致的。当然这只是说异速生长差异作为影响数据的主导因素而言的,否则应使用多变量回归分析异速生长。
多变量回归(Multivariate regression)是一种分析单因素如年龄、药物剂量等对形态差异影响的方法[14]。研究相对于质心的形状回归是分析异速生长的最佳措施[20]。多变量回归不依赖于形状差异的数目或其协方差结构。
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是一种多因素变量对多自变量的回归建模方法。偏最小二乘法可以较好地解决用普通多元回归无法解决的问题。几何形态测量学利用它来研究同一对象的两组或两组以上变量之间关系的方法。PLS提供的线性组合能够最佳地解释各组差异之间的协方差并使各组形状差异的比较可以在低维度中进行。与典型变量分析不同,PLS算法中不包括逆矩阵,它能够被很好地用各种模型解释,并能直观地展示形态差异。当所有的差异组都使用形状坐标来比对时,PLS可以用来解释各解剖组分之间的“形态集成”[21,22]。
许多几何形态测量学分析方法如置换检验、bootstrap检验等都是以随机检验(Randomization tests)为基础的。许多参数检验要求特殊的差异分布(一般为正态分布),随机测验则不受这种限制。
总之,几何形态测量学中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保存了原几何形态的地标点结构,因此其结果也直观地反映了形状改变。
3几何形态测量学在半翅目昆虫研究中的应用
3.1几何形态测量学在昆虫学中的研究概况
在国外,Howell V. Daly[23]于1985年在其综述中首次提出将几何形态测量学应用于昆虫研究。此后在几何形态测量学不断的发展成熟过程中不乏科学家使用此方法来研究昆虫。自2000年以来,几何形态测量学日臻发展完善和成熟,其在昆虫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用昆虫相关研究的文献数量显著增加。研究所涉及到的昆虫类群广泛,包括了蜻蜓目(Odonata)、螳螂目(Mantodea)、直翅目(Orthoptera)、半翅目(Hemiptera)、鞘翅目(Coleoptera)、双翅目(Diptera)、鳞翅目(Lepidoptera)、膜翅目(Hymenoptera)。
国内昆虫几何形态学研究起步较晚,且主要集中于鳞翅目、鞘翅目、膜翅目、长翅目、蜻蜓目及脉翅目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关于半翅目昆虫相关研究的报道。我国从2007年白明等[1]系统地阐述几何形态学原理及应用之后才陆续有研究者参与进来。2008年潘鹏亮等研究了昆虫图像几何形态学提取技术,并采用几何形态学研究了7种蝴蝶的亲缘关系[24~26]。随后葛德燕与杨星科等结合DNA Barcoding及几何形态学技术对跳甲形态平行进化进行研究[27]。白明使用几何形态学对鞘翅目蜣螂后翅进化模式进行研究[28,29]。詹庆斌、王心丽等使用椭圆傅里叶分析法对五种蚁蛉翅的轮廓进行几何形态学比较,肯定了其先前分类的正确性[30]。白晶晶等对浙江临海地区常见的、形态相似度较高的4种蜻蜓的翅进行研究,从形态的角度,探究4种蜻蜓的翅型和翅脉变异规律及其形态的相似性关系[31]。花保祯等对几何形态学在昆虫分类鉴定中的应用做了相关阐述,并使用几何形态学分析长翅目蝎蛉科昆虫的翅形进行分析,并进行系统发育研究[32,33]。
3.2几何形态测量学在半翅目昆虫中的研究概况
自2000年以来,半翅目昆虫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相关研究的报道也不断增加。涉及到的类群有蝽科(Pentatomidae)、缘蝽科(Coreidae)、盲蝽科(Miridae)、猎蝽科(Reduviidae)、黾蝽科(Gerridae)。由于锥猎蝽是美洲锥虫病的主要媒介,所以目前对锥猎蝽的研究较多,也较为透彻。
半翅目昆虫几何形态测量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分类、系统发育、空间结构等方面。目前几何形态测量学解决的首要问题仍然是生物分类及系统发育问题。下面对几何形态学在半翅目中的应用举例说明。
Villegas[34]等使用几何形态测量学的方法研究翅形差异作为Rhodniusprolixus和Rhodniusrobustus(Hemiptera: Reduviidae)的分类依据,证实两者是相对独立的进化单位,解决了有关两者是否属于同一种的争论。Torres[35]等使用几何形态测量学研究缘蝽头部形态差异对Leptocorisaoratorius(Hemiptera: Alydidae)进行分类鉴定。 Carbajal-de-La-Fuente[36]等使用几何形态测量学方法区分猎蝽科锥猎蝽属的两个种Triatomaarthurneivai和Triatomawygodzinskyi(Hemiptera: Reduviidae),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并指出来自圣保罗的样本实为T.wygodzinskyi,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还有Márquez、Campos等[37,38]。
Dos Santos[39]等结合几何形态测量学、酶学和细胞学手段推测Triatomamaculata和TriatomaPseudomaculata(Hemiptera: Reduviidae)的进化关系,认为两者属于不同的进化谱系。Arnqvist 和Rowe[40]利用几何形态测量学研究水黾科(Hemiptera: Gerridae)15个种雌性和雄性间的形态协同进化关系,研究表明水黾两性间的腹部结构进化是相关的,并证实两性间腹部结构的进化应该是等速和双向的。
Dujardin[41]等和Abad-Franch[42]等将几何形态测量学应用于锥虫病源携带者Triatominae(Hemiptera: Reduviidae)的昆虫监控。Dujardin 等认为防控Triatominae的最大难题是能否辨认出其造成再次蔓延的起源,因此,他使用馆藏标本对几何形态测量学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几何形态测量学能够提供有价值的鉴别线索。Abad-Franch 等建立了一套多角度评价体系,对锥猎蝽的生态和进化趋势进行评价。其中使用几何形态测量学鉴别可疑样本并认为这个评价体系能够明显强化拉丁美洲的疾病监测能力。
Schachter-Broide[43]等使用几何形态测量学研究Triatomainfestans(Hemiptera: Reduviidae)的空间结构,研究表明栖息于村庄中的种群形态异质性不仅仅取决于生态环境和寄主种类,还与地理隔离有关。Borges 等[44]使用几何形态测量学和随机扩增多态性DNA标记技术(RAPD)研究栖息于不同环境(森林环境、半野生环境、家庭环境)中Triatomabrasiliensis(Hemiptera: Reduviidae) 种群的遗传差异,认为栖息于半野生环境中的种群既可以适应森林环境也可以适应家庭环境,增加了当地锥虫病爆发的风险。
最近,Batista[45]等使用几何形态测量学研究Triatomabrasiliensis翅形变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出翅形差异可能与表型可塑性相关。Nattero[46]等研究Triatomainfestans(Hemiptera: Reduviidae)形态对食源的反应,显示用不同食源饲喂的成虫头部大小和形态有很大差异,这项研究对选择合适的防控措施很有帮助。
4结语
毫不夸张的说,在过去的20年里几何形态测量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我们目睹了几何形态测量学在数据量化方面取得的重大转变。从形态差异统计概念的提出到形态差异数据的获取的过程中诞生了形态分析的标准方法,普氏分析方法的进一步扩展促进了新的生物学理论的诞生。如今形态差异可以被量化并进行比较,使用图形替代形态则更加有利于生物统计学的应用。
正如Adams在十年前所预期的那样[2],未来十年内几何形态测量学的发展会更加精彩。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方面有待完善。首先就是几何形态测量学在系统发育方面的应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系统发育研究始终是几何形态测量学的忠实受益者。正是由于几何形态测量学对形态差异的量化能力,才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其建立系统发育树。但是,目前为止,该方法与形状差异之间还不能很好地衔接[7]。其次,现阶段大多数几何形态测量学都是使用昆虫翅进行研究的,但是有些昆虫翅上存在黑斑或其他一些斑块会影响后续的地标点提取及分析。而用于几何形态测量学研究的标本一般都是干制标本或酒精浸泡的标本,这种标本通常都很脆,容易毁坏。因此,如何从这些极易破坏的标本上去掉对研究有影响的斑点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47]。最后,几何形态测量学在生物力学中的应用。几何形态测量学与生物力学的结合将是未来发展中最有前景的一个领域。在生物力学中,一般使用有限元分析(finite element analysis FEA)来预测有压力或负重存在时动物结构的性能。与几何形态测量学相似,FEA也是通过捕获动物几何结构上的地标点来进行研究。因此,有很多学者认为将两者联系起来是非常有意义的[48,49]。最近提出了很多能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分析方法,比如,使用薄板样条在现有物种EF模型基础上建立另一种生物的EF模型[50]。虽然这些方法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在实现这些美好愿景之前需要接受更加艰巨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白明, 杨星科. 几何形态测量法在生物形态学研究中的应用[J]. 昆虫知识, 2007, 44(1): 143-147.
[2]Adams D C, Rohlf F J, Slice D E.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ten years of progress following the ‘revolution’ [J]. Ital J Zool, 2004, 71:5-16.
[3]Slice D E,.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J]. Annu Rev Anthropol, 2007, 36:261-281.
[4]Rohlf F J, Marcus L F. A revolution in morphometrics [J]. Trends Ecol Evol, 1993, 8(4): 129-132.
[5]白明, 杨星科, 李静, 等. 几何形态学: 关于形态定量比较的科学计算工具[J]. 科学通报, 2014, 59(10): 887-894.
[6]Slice D E. Landmark coordinates aligned by procrustes analysis do not lie in Kendall’s shape space [J]. Syst Biol, 2001, 50 (1): 141-149.
[7]Adams D C, Rohlf F J, Slice D E. A filed comes of age: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in the 21stcentury [J]. Hystrix, 2013, 24 (1): 7-14.
[8]Mitteroecker P, Gunz P, Windhager S, et al. A brief review of shape, form, and allometry in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with applications to human facial morphology [J]. Hystrix, 2013, 24 (1): 59-66.
[9]Klingenberg C P. Visualizations in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how to read and how to make graphs showing shape changes [J]. Hystrix, 2013, 24 (1): 15-24.
[10]Mitteroecker P, Huttegger S M. The concept of morphospaces in evolutionary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mathematics and metaphors [J]. Biol Theory, 2009, 4 (1): 54-67.
[11]Loy A, Slice D E. Image data banks and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In: Nimis PL, Vignes Lebbe R. “Tools for Identifying Biodiversity: Progress and Problem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Paris, September 20-22, 2010”, Trieste, EUT Edizioni Università di Trieste. 243-248.
[12]Zelditch M L, Swiderski D L, Sheets H D, et al.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for biologists: a primer [M]. New York: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2004: 23.
[13]白明,杨星科.三维几何形态学概述及其在昆虫学中的应用[J].昆虫学报,2014:57(9):1105-1111.
[14]Bookstein F L. Morphometric tools for landmark data: geometry and biolog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5-52.
[15]Bookstein F L. Landmark methods for forms without landmarks: morphometrics of group differences in outline shape [J]. Med Image Anal, 1997, 1 (3): 225-243.
[16]Thompson D A W. Morphology and mathematics [J].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1915, 50: 857-895.
[17]Thompson D A W. On Growth and Form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7:719-777.
[18]Bookstein F L. Principal warps: Thin plate splines and the decomposition of deformations [J]. IEEE Trans Patt Anal Mach Intell, 1989, 11 (6): 567-585.
[19]Mitteroecker P, Bookstein F L. The conceptual and statis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ularity and morphological integration [J]. Syst Biol, 2007, 56 (5): 818-836.
[20]Mitteroecker P, Gunz P, Bernhard M, et al. Comparison of cranial ontogenetic trajectories among great apes and humans [J].J Hum Evol, 2004, 46 (6): 679-697.
[21]Bookstein F L, Gunz P, Mitteroecker P, et al. Cranial integration in homo: Singular warps analysis of the midsagittal plane in ontogeny and evolution [J]. J Hum Evol, 2003, 44 (2): 167-187.
[22]Gunz P. Harvati K. The Neanderthal “chignon”: Variation, integration, and homology [J]. J Hum Evol, 2007, 52 (3): 262-274.
[23]Daly HV, Insect morphometrics [J]. Annu Rev Entomol, 1985, 30: 415-438.
[24]潘鹏亮, 沈佐锐, 杨红珍, 等.三种绢蝶翅脉数字化特征的提取及初步分析[J]. 动物分类学报, 2008, 33(3): 566-571.
[25]潘鹏亮, 杨红珍, 沈佐锐, 等. 翅脉的数学形态特征在蝴蝶分类鉴定中的应用研究[J].昆虫分类学报, 2008, 30(2): 151-160.
[26]潘鹏亮, 沈佐锐, 高灵旺, 等. 昆虫翅脉特征自动获取技术的初步研究[J]. 昆虫分类学报, 2008, 30(1): 72-80.
[27]Ge D Y, Chesters D, Gómez-Zurita J, et al. Anti-predator defense drives parallel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in flea beetles [J]. Proc Biol Sci, 2011,278(1715): 2133-2141.
[28]Bai M, McCullough E, Song K Q, et al. Evolutionary Constraints in Hind Wing Shape in Chinese Dung Beetles (Coleoptera: Scarabaeinae) [J]. PLoS ONE. 2011,6(6): e21600. doi: 10.1371/ journal. pone.0021600.
[29]Bai M, Beutel R G, Song K Q, et al. Evolutionary patterns of hind wing morphology in dung beetles (Coleoptera: Scarabaeinae) [J]. Arthropod structure & Development, 2012,41: 505-513.
[30]Zhan Q B, Wang X L. Elliptic Fourier Analysis of the Wing Outline Shape of Five Species of Antlion (Neuroptera: Myrmeleontidae: Myrmeleontini) [J]. Zoological Studies, 2012,51(3): 399-405.
[31]张晶晶, 白义, 王贵虎. 基于几何形态测量学的几种蜻蜓翅的形态分析[J]. 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 35(1):66-70.
[32]闫宝荣. 基于几何形态测量学的蝎蛉科昆虫系统发育研究[D].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1.
[33]冯艳艳. 基于几何形态测量学的蝎蛉翅形分析(长翅目:蝎蛉科)[D].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3.
[34]Villegas J, Feliciangeli M D, Dujardin J P. Wing shape divergence betweenRhodniusprolixusfrom Cojedes (Venezuela) andRhodniusrobustusfrom Mérida (Venezuela) [J]. Inf Gen Evol, 2002, 2 (2): 121-128.
[35]Torres M A J, Lumansoc J, Demayo C G. Variability in head shapes in three populations of the Rice BugLeptocorisaoratorius(Fabricius) (Hemiptera: Alydidae) [J]. Egypt Acad J biolog Sci, 2010, 3 (1): 173-184.
[36]Carbajal-de-La-Fuente A L, Jaramillo N, Barata J M S, et al. Misidentification of two Brazilian triatomes,TriatomaarthurneivaiandTriatomawygodzinskyi, revealed by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J]. Med Vet Entomol, 2010, 25 (2): 178-183.
[37]Márquez E, Jaramillo-O N, Gómez-Palacio A, et al. Morphometric and molecular differentiation of aRhodniusrobustus-like form fromR.robustusLarousse, 1927 andR.prolixusStal, 1859 (Hemiptera, Reduviidae) [J]. Acta Trop, 2011, 120: 103-109.
[38]Campos R, Botto-Mahan C, Coronado X, et al. Wing shape differentiation ofMepraiaspecies (Hemiptera: Reduviidae) [J]. Inf Gen Evol, 2011, 11: 329-333.
[39]Dos Santos SM, Lopes CM, Dujardin JP, et al.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s based on genetics and phenetic characters betweenTriatomamaculate,Triatomapseudomaculataand morphologically related species (Reduviidae: Triatominae) [J]. Inf Gen Evol, 2007, 7 (4): 469-475.
[40]Arnqvist G, Rowe L. Correlated Evolution of Male and Female Morphologies in water striders[S]. Evolution, 2002,56(5):936-947.
[41]Dujardin J P, Beard C B, Ryckman R. The relevance of wing geometry in entomological surveillance of Triatominae, vectors of Chagas disease. Inf Gen Evol [J], 2007, 7(2): 161-167.
[42]Abad-franch F, Monteiro F A, Jaramillo O N, et al. Ecology, evolution, and the long-term surveillance of vector-borne Chagas disease: a multi-scale appraisal of the tribe Rhodniini (Triatominae) [J]. Acta trop, 2009, 110 (2-3): 159-177.
[43]Schachter-Broide J, Dujardin JP, Kitron U, et al. Spatial structuring ofTriatomainfestans(Hemiptera, Reduviidae) populations from northwestern Argentina using wing geometric morphometry [J].J Med Entomol,2004,41 (4): 643-649.
[44]Borges éC, Dujardin JP, Schofield CJ, et al. Dynamics between sylvatic, peridomestic anddomestic populations ofTriatomabrasiliensis(Hemiptera: Reduviidae) in Ceará State, northeastern Brazil [J]. Acta Trop, 2005, 93 (1), 119-126.
[45]Batista V S P, Fernandes F A, Cordeiro-Estrela P, et al. Ecotope effect in Triatoma brasiliensis (Hemiptera: Reduviidae) suggests phenotypic plasticity rather than adaptation [J]. Med Vet Entomo, 2013, 27 (3): 247-254.
[46]Nattero J, Malerba R, Rodríguez C S, et al. Phenotypic plasticity in response to food source inTriatomainfestans(Klug, 1834) (Hemiptera, Reduviidae: Triatominae) [J]. Inf Gen Evol, 2013, 19: 38-44.
[47]Lorenz C, Suesdek L. Evaluation of chemical preparation on insect wing shape for geometric morphometrics[J]. Am J Trop Med Hyg, 2013, 89 (5): 928-931.
[48]O’Higgins P, Cobb S N, Fitton L C, et al. Combining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and functional simulation: an emerging toolkit for virtual functional analyses [J]. J Anat, 2011, 218 (1): 3-15.
[49]Parr W C H, Wroe S, Chamoli U, et al. Toward integration of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and computational biomechanics: new methods for 3D virtual reconstruction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inite Element Models [J].J Theor Biol, 2012, 301: 1-14.
[50]Rivera G, Stayton CT.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of shell shape in the freshwater turtlePseudemysconcinnareveals a trade-off between mechanical strength and hydrodynamic efficiency [J]. J Morphol, 2011, 272 (10): 1192-1203.
(编辑:张贵森)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and its advances in Hemiptera
Li Rongrong, Li Shengcai, Zhang Hufang
(CollegeofAgriculture,ShabxiAgriculturalUniversity,Taigu030801,China)
Abstract:Geometric morphometrics can statistically analysis of shapes based on Cartesian landmark. It can retain the original shape of the sample and measures the shape feature quantitatively with the use of complex statistics.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is widely used in biolog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iological classification, phylogenesis, entomological surveillance and spatial structuring. In this paper, we briefly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important concept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The research advances of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in Hemiptera were also reviewed.
Key words:Geometric morphometrics; Hemiptera; Classification; Phylogeny
中图分类号:Q9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51(2016)04-0235-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31440078)
作者简介:李荣荣(1984-),女(汉),山西洪洞人,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通讯作者:张虎芳,教授,硕士生导师,Tel:13994250795;E-mail:zh_hufang@sohu.com
收稿日期:2015-12-03修回日期:2016-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