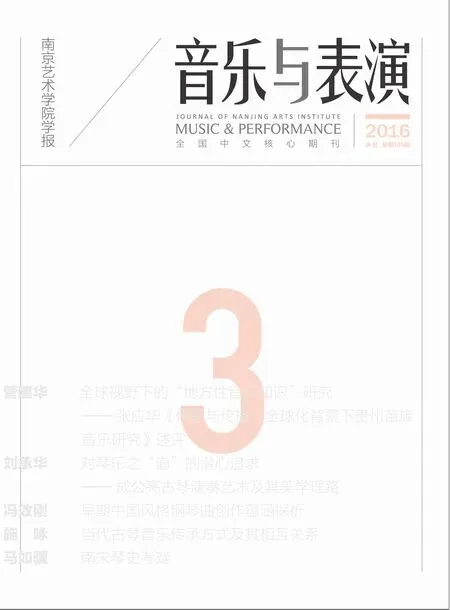《吕氏春秋》中的音乐美学思想研究①本文为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专项项目《秦汉乐论中的美学观研究》(项目编号:15ZWD04);教育部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思想史视域下的秦汉乐论研究》(项目编号:16YJC760053);齐齐哈尔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项目《音乐美学学科发展策略研究——以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为例》(项目编号:20141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王 维 (齐齐哈尔大学 音乐与舞蹈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0 )
《吕氏春秋》中的音乐美学思想研究①本文为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专项项目《秦汉乐论中的美学观研究》(项目编号:15ZWD04);教育部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思想史视域下的秦汉乐论研究》(项目编号:16YJC760053);齐齐哈尔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项目《音乐美学学科发展策略研究——以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为例》(项目编号:20141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王 维 (齐齐哈尔大学 音乐与舞蹈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0 )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中国的前夕,由当时担任秦相国的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写而成,其中有关音乐的美学思想既具有自然性也包含道义性,围绕音乐构筑起来的思想系统体现了《吕》书独特的认知形式,以及它包容天下的思想野心。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一体系的最终解释权实际上掌握在吕不韦等士人的手中,拥有了这一话语权也如同得到了政治形态的制约力量。尽管在政治斗争中,吕不韦最终“饮鸩而死”,但在思想史的价值上《吕氏春秋》为战国之后诸子百家的思想整合,为发挥乐论思想的文化功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太一;天;道;适;和;圣人
一、序 论
《吕氏春秋》成书于公元前241年,时为秦统一中国的前夕。[1]1-2该书由当时担任秦相国的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写而成,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部分,计26卷160篇,约二十余万字。
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者予千金。[2]
当代学者对于《吕氏春秋》的研究遍布于文史哲等各个领域,研究成果不计其数,但是从音乐美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章还不多见,本文仅攫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简要的论述。
牟钟鉴所著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一书中着重探讨了《吕氏春秋》的音乐理论问题,他认为:“《吕氏春秋》的音乐理论来自儒家又有所修正补充,其继承性是明显的,其变更发展的地方可以概括为:第一、引进老庄学说,强调音乐效法自然之和声,将音乐隶属于‘道’的概念;第二、它虽然也批判‘郑卫之声、桑间之音’,但它认为音乐的正邪之分主要不在于《韶》、《舞》与郑、卫之异,而在于君王是贤是昏,侈乐乃乱君之为;第三、它不仅对律吕相生之说有具体论述,而且用阴阳五行的思想,将十二律与月令和五行相配合,使音乐成为它那庞大的宇宙间架的组成部分。”[1]100-101
牟钟鉴首先把《吕氏春秋》的音乐思想认定为儒家,认为其主要发挥了《荀子》乐论中的观点,[1]98老庄学说是后来引进的。在关于《吕氏春秋》的思想到底是儒家、道家、还是杂家的问题?学界一直莫衷一是,原因就在于《吕》书将众多思想糅合一处,很难分清主次。本文无意在此处过多探讨,而是试图将视角转移到《吕》书中的各家学派之所以能够兼容并包的学理基础——生命本体论上,由于有了这一生命本体,道家的自然之理与儒家的道德伦理才有了贯通的可能(详见下文)。牟钟鉴概括的第二个内容是关于音乐的功用问题,他认为《吕》书乐论中的批判之语,不是用来教育平民百姓的,而是用来警示帝王君主的。能够利用乐论思想对帝王君主进行讽谏,足以看出隐藏在《吕氏春秋》背后的政治文化意味。这一思想也启发了本文的研究,随着分析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吕》书乐论中的确体现出了“道统”与“政统”之间政治话语权的对抗。牟钟鉴的第三个发现是对《吕》书中的乐论思想进行了宏观的总结,认为音乐是《吕氏春秋》“宇宙间架的组成部分”。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将视角深入到《吕》书八篇乐论中进行微观的比对,试图找到其相互间的架构模式和思想关联。
葛兆光著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3]第三编第二节论述了《吕氏春秋》的哲学内涵,其中有关音乐的思想如下:“《大乐》、《侈乐》两篇一正一反,要求治理世间的人要顺适人的情欲也要节制人的情欲。在《明理》中说道,‘凡生,非一气之化也,长,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这就仿佛自然界的万物,不仅仅只是一个自然生长的问题,也要避免风雨不适,甘雨不降,霜雪不时,寒暑不当,整个的生长是一环扣一环的众多因果关系所导致的,人虽然秉受于‘天’,但是如果缺少了夏天一样的教育、学习、管束、节制,他也不能顺利成长”。[3]240葛兆光认为《吕》书中的音乐思想既要顺适情欲(《大乐》)又要节制情欲(《侈乐》),因此需要教育、学习、管束。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矛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吕》书中认为人的情欲是秉受于天的,[4]①“欲与恶所受于天也,人不得兴焉,不可变,不可易”(《大乐》)。引自:[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59。文中所引《吕氏春秋》原文俱出于此书,不另行标注。人无权干涉天的行为,那么所有的教育、学习、管束、节制不都成了对天命的否认?《吕氏春秋》是如何解决天命与人义的矛盾的?本文将在后面的论述中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
蔡仲德著的《中国音乐美学史》[5]219-236第十章对《吕氏春秋》中的音乐美学思想分别从音乐的本源、音乐的度量、音乐的审美、音乐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该文认为:“《吕氏春秋》音乐美学思想的特色是用阴阳五行学说统摄儒道两家思想,而又以道家思想为其核心。这一思想的合理内核在于尊崇自然,尊崇理性,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艺术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人对音乐的审美活动必须有利于‘全生’、‘全性’,有利于人的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但它所尊崇的理性是外在于人的‘道’,它由此提出的准则是‘平和’而‘无太’,它规定人的审美活动必须‘平好恶’而‘行礼义’,这就使人与自然的统一、艺术与自然的统一带有消极、被动、保守的成分,使以此理性为准则的艺术成为对人的感情生活的又一限制,而仍不利于人的生命的存在与发展”。[5]235蔡仲德认为《吕氏春秋》乐论思想具有理性主义的内核,但这种理性主义并没有在生命的自由与限制之间找到绝对的价值依据。那么究竟如何评价《吕氏春秋》中乐论思想的价值意义?这将是本文重点思考的问题。
修海林、罗小平著的《音乐美学通论》[6]73-85中也对《吕氏春秋》中的音乐美学思想进行了研究,该书认为:“《吕氏春秋》从音乐产生的角度所谈‘和’、‘适’,基本上反映的是对音乐美的存在规律或者说是自然法则的认识。如果说,‘和’的存在,代表的是构成谐和音声应具有的特定关系的存在,其最终成果与人的听觉感知上的验证直接有关,那么,‘适’的存在,则代表的是之所以能构成音声谐和关系的规律和法则。这个规律和法则,在《适音》篇中被称为‘衷’”。[6]79
该书作者认为《吕氏春秋》中的乐论思想来自天道自然观,因此其中关于音声的关系也遵循着一种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按照这个逻辑,该书作者对《吕》书乐论中的“适”、“和”、“衷”等概念进行了合乎“理性”的解释,比如:“‘适心’,要遵从‘道’之‘理’”;[6]84“所谓‘以适听适’,就是讲的音乐听觉审美中的心声关系,即以‘心’之‘适’应乎‘音’之‘适’,两者相互应和,合乎人的听觉审美规律了,也就是合规律了,由此才能达到‘和’”。[6]81但是,关于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转化的?“心适”与“音适”之间建立联系的基点是什么?在该书中并没有给予解释。本文将在下面的论述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同时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试图进一步揭示《吕》书作者隐藏在乐论思想背后的政治文化功能。
二、《吕氏春秋》中的音乐美学思想
(一)“以适听适则和矣”:回归生命的自足本源
《吕氏春秋》中的音乐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仲夏纪》和《季夏纪》中,《仲夏纪》与《季夏纪》各由四篇乐论构成,分别是:《大乐》、《侈乐》、《适音》、《古乐》以及《音律》、《音初》、《制乐》、《明理》。《吕氏春秋》为何把有关音乐的思想放在了《仲夏纪》和《季夏纪》里?著名学者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的解释是:“仲夏后四篇、季夏后四篇言乐,乐者乐也,乐则体适而增长,故夏季十二篇系配合夏长之义”[4]3。也就是说,无论是仲夏还是季夏,夏季与万物成长有关,而音乐体现的就是这种生命活力的充盈饱满、自足快乐,即所谓“乐者乐也”。由此可见,《仲夏纪》和《季夏纪》为《吕氏春秋》的乐论思想定下了生命本体论的基调,生命的圆满自足是其乐论思想的源头,从这一源头出发,顺着《吕》书行文的向度,我们将试着层层揭开隐秘于中的音乐美学思想内涵。
《大乐》开门见山为乐的由来做了说明:“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这里没有从生命本体的角度直接解释乐的本源,而是说乐“生于度量,本于太一”,“生于度量”是说乐的产生依据是自然之理。“本于太一”则为乐确立了一个形而上的绝对实体,一个超自然的存在。真正与乐的产生直接相关的是下面这段话:
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合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
“声出于和”,声音的产生来自自然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在《吕氏春秋》中“自然”并不是指外在的自然界,而是一种生命的外显与表达(“萌芽始震,凝寒以形”),自然在这里被认定为生命的初始状态:“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太一”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实际上被悬置起来。之后,《吕》书从体验论的角度(“适”)为自然之和做出了解释:“和出于适”,“和谐”就是生命的“自适其逸”。先王定乐,同样来自生命自然的自我安适。生命本体论成为了作“乐”的基础。对于“适”的解释,在《侈乐》与《适音》篇中也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比如在《侈乐》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寒温劳逸饥饱,此六者非适也。凡养也者,瞻非适而以之适者也。能以久处其适,则生长矣。生也者,其身固静,或而后知,或使之也。
“寒温劳逸饥饱”之所以被称之为“非适”,就是因为生命的欠缺和不足,只有内心自逸满足了,生命才能成长(“乐之务在于和心”《适音》)。如此看来,只有让身心保持一种充盈满足的状态,才能“养性”,才能掌握“乐之情”。“和心”是如何做到的呢?《适音》一文说:“和心在于行适”,那么如何做到“行适”呢?
何谓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黄钟之宫,音之本也,清浊之衷也。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矣。乐无太,平和者是也。
“适”就是“衷”。“黄钟之宫,音之本也,清浊之衷也”,由这句话可见,所谓“衷”是指内在的本源,衷音就是“音之本也”,即音乐的本体。衷心就是生命的本体,即回到生命的本源,生命的本源就是那个自足圆满、没有欠缺的生命之本。所以“以适听适”,就是以圆满自足的心性来听本源之音,这样的音乐就是和谐的,这样的心境也是和谐的。先王作乐的根本就是要和心,要让人们的内心回归到原初的宁静、和谐,而沉浸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好恶欲望都成为相对的概念而没有绝对的意义,“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
修海林认为“和”、“适”,“基本上反映的是对音乐美的存在规律或者说是自然法则的认识”,[6]79但外在自然法则与人的内在感知之间到底如何达成对接?修文中并未给予说明,而本文认为从生命本体的角度看待“和”、“适”等概念,则能够将外在之道与内在之理一以贯通,避免了割裂地看待音乐与人的关系问题。综上所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是对“乐”之本体展现过程的描述,其内涵就是对自然生命的自足显发与自适其乐。但是,从自然之乐进入到历史之乐,出现了新的问题。
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大乐》)
“成乐有具,必节嗜欲”这句话,已经透露出历史之“乐”并不是完满的,这里的历史之乐与自然之乐不在一个层面。人的欲望总是在干扰着乐的完满实现,所以出现了亡国之乐。如何解决历史之乐的不完满?《吕》书的做法是取法“道”:“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意思是说,治乐的方法是平和,平和出于公正,公正则要取法于“道”。什么是“道”?此处《吕》书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描述了无道之乐的特征是“其乐不乐”,也就是说,只有令人快乐的音乐才是有道的音乐。什么样的音乐令人快乐?又回到了先前的语境之中,快乐的音乐就是不以满足外部世界的欲望为目的(“成乐有具,必节嗜欲”),而以主体自身的情感自足为依据(“必由平出”),没有差异性造成的情感张力(“平出于公”),这样的音乐才是怡然自适的,才是出于生命之本的音乐(“公出于道”)。所以本文认为,这里的取法“道”,就是回归生命自然的大化本源,沉醉于主体自足其乐的精神意向。但是,自然之乐与历史之乐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生命本体到底是自足的,还是欠缺的?《吕》书作者必须回答这一问题,于是, “天”这一具有人格性的神灵登场了。
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人弗得不辟。欲与恶所受于天也,人不得兴焉,不可变,不可易。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安由出哉?( 《大乐》)
“欲与恶所受于天”说明人的生命本体并不是自足圆满的,这与之前的“万物作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的生命本体论产生了分裂,那么,《吕》书的乐论思想还能否自圆其说呢?《大乐》篇在开篇就设置一个形而上的绝对实体“太一”的存在,由太一观念发展而出自然之乐、历史之乐(“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必须以重新统摄“太一”作为文章的收尾,《大乐》篇的整体逻辑才算真正的完成。
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欢欣生于平,平生于道。……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两也者从听。先圣择两法一,是以知万物之情。……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适,风雨时,为圣人。故知一则明,明两则狂。
由上可知,没有太一,大乐无从确立,掌握了太一,就可以做到生命本体的自足其性,欢欣平和,继而由内而外延伸到立身、立国成为具有神圣使命的最高统治者(圣人)。没有大乐,太一无从显发。大乐既是自然的(自然之乐),也是道义的(礼乐之乐),是建立个体自由、群体伦理、历史政治的内在纽带。但无论太一还是大乐,可以看出《吕氏春秋》的作者才是真正的天意解释者,他在超越秩序(太一)与现世秩序(礼乐)之间进行着某种弥合,而音乐恰好承担了这一中介者的角色需要。“太一”成了可以被人认识和把握的生命本体论证明,而“天命”所具有的神义权威实则也成为《吕》书作者的天理依据,尽管“欲与恶所受于天”的说法与生命自足的立论之本有着内在的裂痕与矛盾,但这种矛盾在《吕》书作者所营造的大乐的审美意象中变得完整和谐,“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天人之间的内在矛盾被乐的审美形式覆盖了。为了更好的将“太一”的绝对力量进行更彻底地推进,《古乐》篇中历代帝王的作乐历史成为了作者返回世俗世界的理论依据。
(二)“不闻至乐,其乐不乐”:一种政治信念的表达
《吕氏春秋》作者在《古乐》篇中叙述了从朱襄氏到周成王的古乐制度,借助对乐的掌握,古之圣王实现了对现实政治的绝对统治。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
《古乐》篇的结尾处写道:“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每个历史时期的古乐制度并不相同,这为《吕》书作者话语阐释权的确立埋下了伏笔,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掌握“乐”呢?“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大乐》),只有懂得天道的人才可与之谈论音乐,这等于在帝王之上又确立了一个价值存在——“道”,而“道”是由“得道之人”即《吕》书作者们进行解释的,只有这些人才能够懂得作乐的道理,而懂得了乐中之理也就具有了整饬天下的能力(“能以一治天下者”)。历史学者葛兆光认为:“《吕氏春秋》则把这种‘道’本身的依据凸显出来,将其置于自然法则的基础上,笼罩了社会政治与伦理的具体目标,并将其真正的实现与知识阶层的参与画上等号,这无异于在政治权利已经膨胀到极限的时代,以文化话语权利与政治话语权利对抗”。[3]251可见,《吕氏春秋》的乐论思想不仅仅是谈论音乐的自然之理与社会功用的问题,这里面还隐含着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利益诉求。
有了《大乐》篇的形上依据以及《古乐》篇的历史依据的叙述,《吕氏春秋》通过乐论所欲建立的思想结构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季夏纪》延续了《仲夏纪》中的思想结构并具体加以展开。《音律》篇,将自然之乐的产生紧紧附会自然之理,“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十二音律的产生来自天地之气的相生相感,而且人事、政治、历史都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天地人合的基础就是“生生之道”(生风、生律),即生命本体的显发。
《音初》篇,将历史之乐的产生与伦理道德紧紧相连。“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自然之乐过渡到礼乐之乐,具有价值形态的伦理道德成为了“作乐”的基本内涵。
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乐,和乐以成顺。乐和而民乡方矣。
“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乐”,要想在历史时间内判断善恶、闻声知风唯有依靠得道的君子。君子通过返回生命的原点,回到生生之道的生命大流之中,才能达到对德性的完善,以及对自足生命的彰显。“乐”就是生命之道的外显形式(“正德以出乐”)。而芸芸众生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为了活而活,却不懂得为什么活(“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侈乐》)。所以出现了“乱世之乐”、“郑卫之音”。只有得道懂乐的君子才能够起到对于民众的精神导向作用,“和乐以成顺。乐和而民乡方矣”。《吕氏春秋》作者在《音初》篇中指出君子的道义担当来自“反道以修德”,来自对自足生命的彰显(“正德以出乐”),这为君子政治话语权利的确立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而在后面的《制乐》篇与《明理》篇里,《吕氏春秋》作者再一次以神义化的隐喻为其验明正身。
《制乐》中举了三个天人相感的例子,这三个例子说的是商汤、周文王、宋景公由于改善自己的言行,并没有由于上天的灾异现象而临祸。举出三个例子的目的是说灾异现象虽然基于天地人的同气相感,但是真正的基础在于人,人的所作所为才是上天行使旨意的依据。“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极”。通过对天意进行解释,文人们以价值仲裁者的姿态获得了某种认识世界、把握现实的绝对力量。“欲观至乐,必于至治,其治厚者其乐治厚,其治薄者其乐治薄,乱世则慢以乐矣”,意思是说要看到最好的音乐,一定要到最有道德的政治当中。政治安定的君主他的音乐就厚重,政治紊乱的君主他的音乐就单薄。乱世的时候,就轻慢音乐。这完全是一副替天行道者的语气。
《吕》书作者借助灾异说将自然之理向道义之理进行引申,而话语解释权则握在君子、圣人、得道之人手中,或者说,握在编写《吕氏春秋》的吕不韦们手中。天人感应需要自然之理和历史依据作为支撑,但更需要有超越这些理性依据之上的神意权威作为终极支持。这与迷信无关,而与神权式的政治诉求有关。日本学者本田成之曾经在《中国经学史》中指出:“如果不能给予一种对于自然的形而上的说明的话,则无论哪种圣贤底教训,是不能传任何人底信仰的”。[7]秦汉士人需要对当时的时事政治给予一种形而上的诠释。
五帝三王之于乐尽之矣。乱国之主,未尝知乐者,是常主也。夫有天赏得为主,而未尝得主之实,此之谓大悲。是正坐于夕室也,其所谓正,乃不正矣。(《季夏纪·明理篇》)
意思是说:“五帝三王对于音乐的理解是最彻底的。混乱国家的君主不曾理解音乐,因为他们是平庸的君主。得到天的赏赐能成为君主,却不曾获得君主实际上应具备的品质,这是非常可悲的。这就像端坐在朝向不正的屋子里,其所谓的端正并不端正。”[8]《明理》篇中的政治诉求昭然若揭。利用乐论思想来表达某种秘不可宣的政治权利思想,颇有政治文化的意味,正如《贵公》篇所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而《明理》篇的结束句:“乱世之主,乌闻至乐?不闻至乐,其乐不乐”,也成了一种政治信念的表达——只有闻得至乐的人才可以成为治世之主。这样的言论无疑对国家权利的正当性形成潜在威胁,吕不韦最终饮鸩而死的结局,与其乐论思想中所隐藏的某种政治诉求之间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内在必然性。
吕氏之在当时,是否有取秦而代之意,今虽不易轻断,然东方宾客(齐鲁学人——作者按)在文化的见地上轻傲秦人,而秦人对东方文化亦始终不脱其歧视与嫉视之意,则为吕氏取祸之最大原因也。”[9]12
据钱穆所言,作为东方人的齐鲁学人在战国时期的文化地位相当优越,[9]5①“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此为儒墨两家所同。其后道家继起,其论学态度亦复同也。”吕不韦属于东方人(“不韦固亦东方人也”)[9]5,他希望通过文化精神的优越性占据秦国的统治地位与话语权利,而这也成为他“取祸之最大原因”。葛兆光对于吕不韦所代表的古代文人的这种政治斗争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任何时代中,文化精神在强权政治下都不可能获胜,……随着吕氏之葬,中国士阶层为帝王师之梦想也随之灰飞烟灭,但这种处士横议、自承道统的精神却在宾客门人的心底深藏,在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思想中时时呈现出来,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不屈象征”。[3]252
三、小 结
《吕氏春秋》为当时的思想世界构筑了一个可以容纳各路思想的时空框架,这些思想以生生之道作为本体依据,围绕着太一、两仪、阴阳、四季、五行、十二月等等自然运行方式不断展开,向上提升为道家的自然反本思想,向下延伸到儒家的礼乐治国政策,并以福瑞灾异作为神圣权威的历史启示。
“吕不韦”们在对音乐的自然性与道义性进行解释之后,最终以天意解释者的身份出现,体现出一种政治利益的诉求。“乐”的自然性与道义性已经为稳定的政治理想确立了方向,在如何行使这一政治话语的解释权,如何实现士阶层的利益诉求方面,则需要对乐论思想进行神义化的解释,因为通过对天命的神义化解释可以在世俗世界获得某种政治利益上的主动权。灾异说在《制乐》和《明理》篇中不断出现,这种神义论的话语并没有与《吕氏春秋》的乐论思想产生龃龉,反而契合了“不闻至乐,其乐不乐”的题中之意——成为一种政治信念的表达。
《仲夏纪》与《季夏纪》中的八篇乐论构成了《吕氏春秋》乐论思想的基本结构:《大乐》,确立了乐论思想的形上依据“太一”,通过对“太一”的把握能够实现文人对于天道的理解,这也为文人政治权利的确立奠定了学理上的基础。《侈乐》通过对乱世之乐的批判为世俗权利领域提供了价值依据,所谓“乐者乐也”,就是像士人一样懂得“乐之有情”,懂得养性,懂得回到生命的本源,“生也者,其身故静”。《适音》更像是回到“乐之情”的方法论证明,“以适听适则和矣,乐无太,平和者是也”,用回到生命之本的修身方法(心适)来听合适的音乐(适音),这样的音乐才是和谐的、不过分的。这里关于适音的思辨实际上是修身养性、教化于人的绝好方法,(“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古乐》是圣人作乐的历史叙述,不同的时代所作之乐各不相同(“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这也为朝代更替,实现士人的政治利益诉求提供了历史依据。
《音律》与《音初》两篇乐论借助音乐的“生生之道”将自然之理向道义之礼进行理论延伸,自然、气候、音律、社会、灾异等等一切事物都在生命本体论的基调下不断延展、相互感应,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结构体系,这样一种体系为士人话语权利的建立作了理论铺垫,(“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乐,和乐以成顺。乐和而民乡方矣”)。《制乐》与《明理》则通过灾异说为士人的政治话语权利进行神义化的解释,其目的是为立德治国的使命担当提供神圣支持。
总而言之,《吕氏春秋》的乐论思想用音乐打通了自然之道与历史之礼的关节,音乐既具有自然性也包含道义性,围绕音乐而构筑起来的思想系统让我们看到了它的独特认知形式,以及它所包容天下的思想野心。这一体系的最终解释权握在士人手中,拥有了这一话语权利也就如同得到了政治形态的制约力量。尽管在政治斗争中,吕不韦最终“饮鸩而死”,但在思想史的价值上,《吕氏春秋》为战国之后诸子百家的思想整合,为发挥乐论思想的文化功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7:1-2.
[2][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7:636.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4][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新校释[M].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
[6]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7][日]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 [M].孙俍工,译.上海:中华书局,1935:147.
[8]王宁,主编.评析本白话吕氏春秋·淮南子[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65.
[9]钱穆.秦汉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4:12.
[10]徐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1]刘小枫.纬书与左派儒教士//儒教与民族国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王晓俊)
J601;J609.2
A
1008-9667(2016)03-0013-06
2016-04-07
王 维(1978— ),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博士,齐齐哈尔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音乐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