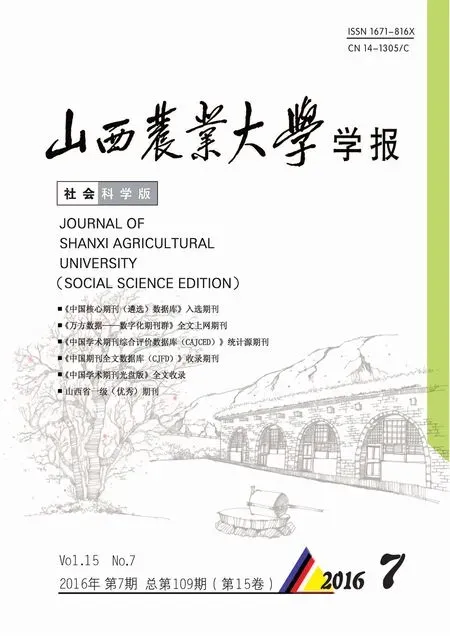隐喻·反讽·张力
——现代诗阅读札记
高蔚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隐喻·反讽·张力
——现代诗阅读札记
高蔚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隐喻和反讽不仅是诗歌语言与思维的基本原则,更是诗歌本体结构的核心要素。一首诗能否“借助矛盾和限定条件来表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讽、隐喻携带的张力以及相互间的作用。隐喻能促成一定语境中意义要旨的相互联系与融合,构造张力关系的各成份。反讽因语境压力形成的悖论能“修改”诗歌情感表达中的固有意义,挤压出潜藏于文本各处的深意,或维护文本与语义的矛盾性悖反,以构建诗歌结构应有的层次。
关键词:诗歌语言特征;诗歌本体结构;“有机统一”原则;悖论;复义
从诗歌本体构成的艺术发展历程看,隐喻和反讽都不曾一步跨进诗歌本体结构的核心位置。它们经历了从单纯的语言现象、语言修辞、一种语言形式,到思维特征、想象力的体现,再到帮助语言去揭示处于语言之外的“现实”和诗的本体构成的复杂认知过程。反讽还曾一度背负“一种狡黠的语言技巧”[1]的恶名。从语言修辞的发现,到直接参与“验证”想象力的艺术活动,进而成为诗歌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核心成员,隐喻摆脱了语言的附属身份和通过“转换”模式创造“新现实”的工具性;反讽也走出了“讥讽”、“嘲弄”等局限,“成了诗歌的基本思想方式和哲学态度”[1]。可以说,隐喻和反讽都是诗歌的“构成性”形式,诗歌只要想追求“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效果,隐喻和反讽就不可或缺。因此,对一首诗而言,隐喻、反讽无论作为语言实质或语言技巧,还是作为文本结构都尤为重要。
一
今天我们被富于创造性联想的诗句吸引时,很容易跳过一种语言构成形式来看待隐喻和反讽,我们会理所当然地接受这是诗歌本质属性的艺术事实。然而,诗歌毕竟是靠语言来完成其艺术使命的。若果真如新批评理论家所言,“诗歌不仅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媒介,还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2],那么,考察隐喻和反讽在一首诗本体结构中的具体功用之前,对作为“诗歌语言灵魂”[2]的隐喻、反讽有一个常识性认知,将有助于我们去“获得诗歌所生产的那种知识”[2]。
在一些语言学家眼里,语言的本质和起源就是隐喻的。在另一些语言学家眼里,人类的思维本身是隐喻的。因此,隐喻并不首先属于诗歌语言或艺术思维。我们在生活中时常能看到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词语用法,如棉布店的店铺名“布言布语”,口舌之争叫“唇枪舌剑”,“立春”时“吃春饼”叫“咬春”等等。这些词语结构,仿佛发现了不相关事物之间的某种原有联系,“复活”了尚在酣睡状态的联想思维,它们所体现的语言本质或思维特性其实就是隐喻。以“咬春”为例。这个说法实际上来源于一个基础隐喻:吃春饼就是咬到(住)了春天。咬到(住)了春天的意味很多,民间习俗是以此来迎接新春,寄望未来。就隐喻的符号性而言,“咬春”因“吃到”即“拥有”而标志了“吃”这个动作与“吃”对应的季节之间暗藏的某种尚未被挖掘的关联。人怎样咬“春”,这个“春”是何种形式,为什么要咬“春”,咬“春”会给人带来怎样的意义?显然,在“咬春”这个奇特的语象背后,隐含了与“春”的物质形态关系不大,与它的精神蕴藏关系多重的意义容量。如万物生长的肇始季节,人类农耕文明时代的根基。以至于它的延伸义:收获,时光,未来,希望,梦想,等等。无论“咬春”是咬到了一口“春”还是咬住了整个儿“春”,它都违反常规地让季节扮演了一个能够被触动的“物”,仿佛一个过去“离散的印象”通过想象力而重新聚到了一起[3]。
正因为如此,或许可以说,作为语言现象的隐喻为诗性联想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或者,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隐喻本身就具有诗性联想的性质。这正是许多诗句给我们以思维震撼的原因。如“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穆旦《春》),“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郑愁予《错误》),“亚洲铜,亚洲铜/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海子《亚洲铜》),“野火在远方,远方/在你琥珀色的眼睛里”( 舒婷《惠安女子》),“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 李金发《有感》)。显然,这些诗句因隐喻的语言结构而延伸或拓展了词语间的潜在联系,传递了常规语言不能表达的思想、感受,进而能够在多个层面上表达主题。以“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为例。人们对生命的见解纷繁多彩,但却无人关注生命的脆弱性与死神唇边的笑的相似性,李金发在这里抛开了人们多关心生命美好一面的常规思维,涉足的是生命的脆弱性、易失性、不确定性与变故时刻伴随人生等生命的另一面属性。诗人并不直接去界定生命的本质,而是运用了一个能够带来崭新意义的独特的比,将隐喻关系纳入其中。经过一物向另一物的“转移”,“死神唇边的笑”的物质属性便传递到“生命”形态的身上,生命“是死神唇边的笑”这个单一陈述随即饱含多义性与不确定性。诗句的言下之意是:生命固然美好,却不过是死神唇边的笑,我们不必得意忘形,无论多么鲜活的生命都离死神很近,纵然生命的蓬勃显而易见,但它时刻处于潜在的危机中。其间,在诗句的明确意义最终确定下来之前,由于“笑”的所指并不清晰,可以有多种意味,于是“生命”和“笑”之间形成了多个向度的张力,又由于有“死神唇边的”这个定语限制,原本已经向多个方向拉抻的力又被拉回来,后一层的张力使这个阴郁的“生命”理解变得十分确定。从语义学角度讲,任何语言都可能产生歧义,关键在于语境。是隐喻给了语句特定的情境,限制了词语潜在的歧义,使诗句既可以复杂多义,又能够“有机统一”。
无疑,诗人是在“语言的真正本质”[2]中创造自己的语言。如果有人能够抵御“当教堂的尖顶与城市的烟囱沉下地平线后/英格兰的天空,比情人的低语声还要阴暗”(多多《在英格兰》)带给我们的关于敏锐感知力与洞察力的诱惑,这种本质性的语言才会失去它应有的光环。这里,诗人用“阴暗”形容情人之间的低语声实际上是在词的本义上做文章。阴暗即昏暗,暗色调,所谓背阳为阴。“暗”亦即不明亮,引申义有隐秘、隐藏、不显露、不公开等。因此,说情人的低语声“阴暗”,情人之间说话方式的私密性便呼之欲出,表达十分精准。但英格兰的天空是什么样子,诗人没有明说或描画,而是用“情人的低语声”去比附,通过隐喻特有的语言结构方式,把“情人的低语声”的特性附着在了“英格兰的天空”上,这样,我们不再需要诗人去给“英格兰的天空”涂抹任何色彩,这天空的鲜明特点就已赫然摆在我们眼前,隐喻在此给了我们关于“英格兰的天空”的新认知。由于隐喻本身携带张力,两者之间的距离遥远或不属于同一义域,都能推开诗情空间,让“意义”不至于停留在一个层面。因此,作为《在英格兰》的开篇句,诗人借助隐喻意义的“延伸”,率先把想要传达的一个游子在异国他乡的孤独落寞、无处皈依的内心幽暗及压迫感点染开来,宛若一次出发,在举手投足的第一步就为整首诗表达的思乡情绪做好了准备。所谓没有隐喻扩展的“现实”便没有诗即如此。
优质的隐喻能带来诗歌语言在结构上的复杂组织,这种复杂组织“分离”了日常语言的原有属性重新结构,诗人得以通过隐喻中多种成分的意义联合,撑开诗意空间,为“复义”筑建安稳的栖身之地。在“热风如期而至/形成浪/开始榨取父亲瘦小身上/仅有的汗水”(汤松波《小暑》)里,诗句的复杂结构实际上是由多个隐喻和它的次隐喻共同构成的。“热风如期而至”,热风“形成浪”,热风“开始榨取汗水”,这三层隐喻实际上源于这样一些“基础隐喻”:“热每年都不会放过人”,“热浪滚滚”,“热是残酷的”。诗人调动自己的诗性想象,赋予了这些日常认知中毫无关联的事物以跨越原有范畴的某种联系,目的是等待两者相融后的诗性效果。三层隐喻并置,让“小暑”节气带给人的“热”的感受,不再只是以不好捉摸的个人“感觉”来空洞诉说,而是让“热风”变得可视见、可碰触、可邀约、可共处,仿佛一个狡诈、蛮横、贪婪的人如期而至,栩栩如生地描画了“热”给人的正常生活带来的威胁,“热”让人在心理上承受的压迫感,甚至“热”对生命施以的“罪恶”。正是这种隐喻所带来的语义的丰富性,让诗人制造并限定了“热风”与“邀约”,与“浪”,与“榨取”等词语间的张力关系。对阅读者而言,它刷新了人们对“热”的常规感受,贡献给我们关于“热”的感知觉的新知识。
热风“开始榨取父亲身上仅有的汗水”系一个隐喻与另一个次隐喻的组合。“汗水”既指人的生物性体液,也指人的劳作所得。热风对父亲的身体和精神构成了双重压迫,父亲因此除了“汗水”一无所有,父亲的劳作所得仿佛都被“热风”掠夺走了,这就在诗意的表达中嵌入了必要的重叠和矛盾,是典型的韦勒克所说的“词汇不仅本身有意义”,而且会引发在“感觉上或引申的意义上与其它词汇的意义,甚至引发那些与它意义相反或者相互排斥的词汇的意义”[4]。这种意义的重叠和矛盾是构造张力的条件,由于矛盾是隐喻造成的,隐喻也同时协调了矛盾的相互关系,并不会滋生歧义。因此,是隐喻的复杂结构造成了诗意的多重性,隐喻是构成诗句“复义”的常态,它能让词语的意义改变原有的模样,变得既清晰又模糊,既准确又多重。
反讽的情况要复杂一些。虽然作为语言修辞手段的反讽自身也携带张力,但它对语境的依赖十分严重。例如我们其实很讨厌一个人,但在特定的语境里,我们说出来的却是“我真是太喜欢你了”。如果没有特定的语境,反讽则不能达成。鉴于此,关于反讽在诗歌里的作用,放在下一节具体作品里探讨。
二
其实,在一些经典的诗歌作品中,隐喻并不总是一手遮天,而是时常与反讽联手合作。反讽的种类很多,但“不一定”都“是讽刺性的”,也不是一定要有“受嘲弄者”[5]。如果隐喻倾向于制造诗句的复杂结构,反讽则以“表象与事实”相“对照”的“基本特征”,制造文本自身的矛盾,维持文本“与语境中的事实相抵触”、相悖反[5],并以此“赋予所描述的存在以明晰、以形式、以意义、以价值”[5]。因此,在一些诗人、理论家眼里,不仅“没有隐喻就没有诗”[6],没有反讽也没有诗[2]。一首诗之所以“张力”层次繁多,情感空间开阔,“复义”拥挤,不仅仰赖隐喻的复杂结构和自身携带的张力所促成的一定语境中意义要旨的相互联系与融合,反讽因语境压力形成的悖论也至关重要。诗中的有些悖论能“修改”情感表达中的固有意义,挤压出潜藏于文本深处的更多意义,有些则能维护文本与语义的矛盾性悖反,为构建诗歌结构应有的层次做好准备。事实上,隐喻和反讽都能构造诗中张力关系的各成份,它们早已不仅仅是语言形式,而是文本构成的核心要素。以张执浩《高原上的野花》为例:
我愿意为任何人生养如此众多的小美女/我愿意将我的祖国搬迁到/这里,在这里,我愿意/做一个永不愤世嫉俗的人/像那条来历不明的小溪/我愿意终日涕泪横流,以此表达/我真的愿意/做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这首诗是写一个人被自己的审美直觉震撼而唤起的某种审美理想,也可以说是为这些审美理想许下的众多不可能实现的心愿。如果单从诗句使用隐喻的语言结构看,诗中的隐喻密度并不很强,仅“搬迁祖国”,“来历不明的小溪”,“小溪不愤世嫉俗”几处,但如果走进诗人为“心愿”设置的具体语境,我们就会发现,诗中每一个诗句都隐含着言外之意,诗的文本结构很有特点。
首句“我愿意为任何人生养如此众多的小美女”,生养小美女并不构成隐喻,但这里显然并不单指生养人,而是指高原上这些野花以及与“野花”所指有关联的一切美好的人或事物,如生命力、洁净、甘于被忽视、顽强的意志、不受主流价值观左右、随心绽放、坚执,等等。诗人显然是跳过了对偶然闯入眼目的具体景象的描绘,直接从“震撼”切入。隐喻式的语言结构一开始就让诗意在或明或暗的语义场中闪烁,同时,张力也进入蓄势状态。接下来,诗人构造了一个由深层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合成”[3]的“形式”变异:把祖国“搬迁到这里”才能“做一个永不愤世嫉俗的人”,“像那条来历不明的小溪”。言下之意:现实有太多不如意、恶俗、黑暗,甚至罪恶,以至于不得不时常愤世嫉俗。现在,不期而遇如此一个美丽的所在,这“美”足以令一个人奋不顾身地去打开梦想,因此,我要把祖国“搬迁”到这里来。在这一层意义段落里,“来历不明的小溪”其实是一级次隐喻,语境在此基础上倒装出另一个隐喻:小溪不愤世嫉俗。实际上,次隐喻和倒装出的隐喻是叠套在一起的,作用就是制造张力。两个隐喻自身都携带张力,诗情空间被撑开的幅度自然更大了。此时,套在一起的两个隐喻进一步挤压出潜藏的意义:这个“美丽的所在”一切和美,纯净,秩序井然,无须愤世嫉俗,所以我不必再像个“疯子”一样为一切不合理去据理力争,要“像那条来历不明的小溪”,即便无人知晓,没有身份,没有光环,也愿意安守本分,沉静地履行一个正常生命体的生命使命,以至于引发出尾句更加恳切、热烈的表白。由此我们看到,隐喻具有“组织”思想,形成判断,“使语言结构化”的“巨大的生成力”。[3]
如果说这首诗的情感内容到此为止,那么这首诗也没什么特别。但事实上,这首诗的情感力量十分强大,语境提供的言外之意格外丰富,诗中的“复义”推推搡搡、拥挤不堪,原因就在于,诗的结构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几乎每一句都被冠以了“我愿意”。如果这些“我愿意”就是单一的抒情热情,诗意也不会如此饱满。实际上,这每一个“我愿意”都构成了文本与语义的矛盾性悖反,这样,诗的结构就在不同张力的作用下变得有了层次。由于“把祖国搬迁到这里来”只能是诗意层面的,实现所有“我愿意”的前提不在现实里。心愿与心愿的不可能兑现之间已经形成了“差异”,同时,诗意层面的“纯净”与现实现状的污浊又相龃龉,于是,藏在语境深处的绝望情绪跳了出来。有意味的是,这个绝望情绪的展示形态以一种不乏“热烈”的表白形式深藏在这个“差异”里。因此,整首诗都是悖论形式的,里面并置了太多矛盾。语境压力“压出”的 隐秘的绝望情绪,与“热烈”表白之间形成的悖反,直接导致了对诗歌本义的“修改”,按照布鲁克斯的观点,这层被修改的意义就是由“反讽”构成的。[5]热望越不可能兑现,它与梦想间形成的张力就越强大坚固,以至于把尾句的极端情感拉进了言意关系的繁复形态中。可见,“反讽”在诗歌中也是一个制造张力的高手。
布鲁克斯甚至认为,诗歌使用“悖论”极其正常,诗人必须学会“借助矛盾和限定条件来表述”,因为隐喻并非一定“能处于同一层面”,也并非一定“能整齐地并置”,隐喻的各个层面会“相互交叠、互有差别,彼此矛盾”[2]。在现代诗中,隐喻和反讽带来的张力时常都不仅会罗织成一张网,控制和平衡情感力量各方面的关系,还能“与作品的整体秩序相协调”,最终迎来一个“既保证了多元又保证了统一性的”严整结构[7]。以里尔克《秋日》(北岛译)为例:
主呵,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让风吹过牧场。//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催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
这其实是一首写孤独感的诗。1902年,里尔克因工作需要离开家乡只身来到法国,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使他深陷浓重的孤独感和漂泊感中。全诗三节,诗人并未提自己内心的孤独,但诗中跟上帝对话,跟“秋日”独处,都泄露了诗人的情感秘密。同样是写孤独感的名篇,它与冯雪峰直接以“孤独”为题的《孤独》一诗处理情感的方式形成鲜明对照。《孤独》虽也因隐喻和隐喻制造的悖反性矛盾织就了一张布满张力的网,但它直奔内心的灼热情感:“哦,孤独,你嫉妒的烈性的女人!/你用你常穿的藏风的绿尼大衣/盖着我/,像一座森林/盖着一个独栖的豹。//但你的嘴唇滚烫,/你的胸膛灼热,/一碰着你,/我就嫉妒着世界,心如火炙。”《秋日》则不同,它并不浓墨重彩“孤独”,“孤独”二字却尽现其中。
《秋日》的前两节是一个意义层。从这两节的文本结构看,它是一个整体隐喻与局部次隐喻的组合。整体上,把上帝的阴影放到日晷上,便可以结束夏季酷暑的傲慢,迎来秋日舒适的凉爽,并让果实饱满成熟;如果全知全能的上帝能继续给南方两天好天气,还可以把属于“秋”这个季节的所有甘甜压进浓酒。诗人所写这一切秋日的“惬意”都来自上帝之手,抛开上帝与人类关系的隐喻,这里也是个整体隐喻。源自宗教信仰的观念性意识与大自然的惠赐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张力,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相信上帝的能量。因此,诗人对秋日祈望的描画看似舒缓平静,却因隐喻语言结构方式的介入,各种力量暗自涌动。而局部,“夏天盛极一时”,“把上帝的阴影置于日晷上”,“把甘甜压进浓酒”三个次隐喻从不同向度出发,使每一层语义因隐喻语言创造“新现实”的能力而生机勃勃、跃跃欲试,共同谋划着如何“激发”我们对季节的“想象”。与此同步,隐喻所伴生的张力开始工作,它先是抻开诗意空间,给所有言外之意筑巢,然后恪尽职守地把那些被一步步挤压出的“复义”接回家。
如果说这首诗上半部分来自隐喻的张力已十分雀跃,那么下半部分,诗人变换手法制造的诗意矛盾,则让这首诗聚集的内部力量更加沸腾。关键就在于“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两句。前者源自“秋日是房屋”这个基础隐喻,后者源自另一个基础隐喻“秋日是伴侣”。隐喻本身促使我们张开想象的网去捕捉诗人提供的秋日之美,这一层张力是瞬间生成的。其次,“秋日是房屋”、“秋日是伴侣”也只能停留在诗意层面,与事实完全不符,诗人在这里给出的这个“诗意”的“表象”与事实上的“不可能”之间形成鲜明对照,构成了一个层级的反讽,这两句还有第二个层级的反讽:诗人所言“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和“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显然不是文本的真实意义,语境暗示的是“秋日”令人向往甚至贪恋的理由,安享秋日的惬意与诗中所说“不必建造房子”,“就永远孤独”的文本至少不在同一个层面,形成的意义是相悖性质的矛盾,因此第二层的反讽实际上是个“总体反讽”[5],因为诗人用“诗意”的方式寄情秋日,也无法真正解决“忘记孤独”、“遣散孤独”的全诗主旨。两个层级的反讽使诗意“想要极力表达的”和“最终呈现出来的”形成的不和谐状况陡增,因此,摆脱孤独的努力与事实上的孤独构成了一种根本性的冲突,诗人越是挖空心思数说“秋日”的好,“秋日”掩盖下的心理窘境就越明显。惬意是表面的,深藏的孤独才是真相。
当然,复杂结构并不是好诗的唯一标准,但通过隐喻获得“张力”,通过“张力”产生“悖论”,并“有意运用悖论获得一种”明了和“准确”[2],是诗人们所追求的。只要希望意义增殖,隐喻关系的“毗连性”与反讽结构的意义“选择场”就会合力维护诗歌文本的结构层次。
参考文献
[1]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文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80,178.
[2][美]克林斯·布鲁克斯.精致的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8,11-12,5-22,12.
[3]胡壮麟.认知隐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9,71.
[4][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等译.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97.
[5][英]D.C.米克.周发祥译.论反讽[M].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99,81,113,15,100.
[6][美]华莱士·史蒂文森.高丙中译.遗著·格言篇,转引自特伦斯·霍克斯.论隐喻[M].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8.
[7][英]拉曼·塞尔登.刘象愚,陈永国,等译.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89.
(编辑:武云侠)
Metaphor, irony and tension: reading notes on modern poetry
Gao Wei
(CollegeofLiterature,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541004,China)
Abstract:Metaphor and irony are not onl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poetry language and thinking, but also the core elements of poetry ontology structure. Whether a poem "with the aid of contradiction and restriction to describe" greatly depends on the tension of irony, metaphor and their mutual effects. Metaphor can contribute to the mutual contact and the fusion of the gist of significance in certain context, forming ingredients of tension structure. Paradox formed by the pressure of context in irony ,can "change" the inherent meaning of poetry emotion expression, squeezing out the hidden meaning in the various parts of the text, or maintaining the contradiction or paradox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semantic to build the poetry structure level.
Key words:Poetry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Poetry ontology structure; Organic unification principle; Paradox; Ambiguity
收稿日期:2016-03-05
作者简介:高蔚(1963-),女(汉),河北辛集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诗方面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16)07-052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