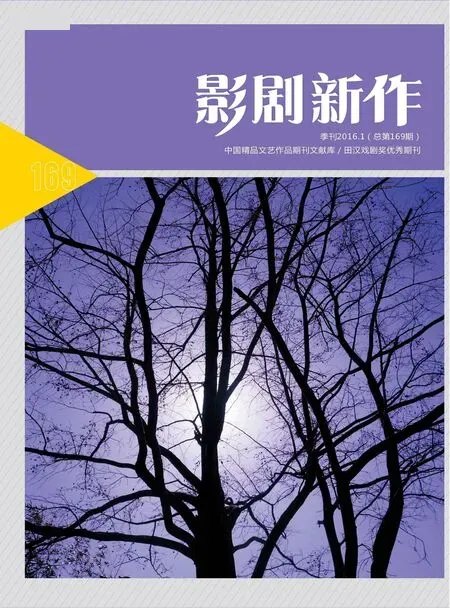旁观
——傅勇凡执导话剧《遥远的乡土》印象
胡小燕
旁观
——傅勇凡执导话剧《遥远的乡土》印象
胡小燕
第一次知道傅勇凡导演,是从别人的聊天中。大家都说他牛,连续三届获得文华大奖,《天籁》、《红帆》、《共产党宣言》,绝无仅有。
从前,我总是对别人嘴里的名人抱着怀疑。浮躁、张狂、乖戾、死作,当然还有长辫或光头,麻衣或布鞋,这都是常见的名人范。但因为《遥远的乡土》第一次见到傅导,完全颠覆了以前的看法。傅导一米八的个头,不肥不瘦,标准身材,没留长胡须,也没留长发,看上去就一普通机关干部。有时候戴副黑框眼镜,更像是一个老式的机关干部。虽然算是帅哥,但绝对没有常见的名人范。
接着有了和傅导一起吃工作餐的机会。点菜时他都说“点四个菜,别浪费”,有时吃到他喜欢的,他就会要求再来一份,然后告诉大家这菜是多么好吃,从小如何喜欢,身在异地又是如何想念……有时候他也会向大家讲述自己的从艺经历。从江西到广东,从地方到部队,一串串闪光的脚步。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时常讲到自己能够走上艺术之路,得益于许多师友的帮助和引领。我们有一位共同的舞蹈家朋友,傅导每次谈起,都称作老师,言语中透着真实的尊重。实际上,以傅导目前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他那些“老师”、“师傅”。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名人”是不会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和从前的师友摆在一起的,尤其是在业务上。由此看出,傅导虽已功成名就,但还接着地气。他是大导,但是平民大导,市民大导。
于是我开始一部部看傅导的作品。《天籁》、《红帆》、《共产党宣言》、《支部建在连上》、《朝天门》、《刘伦堂》,看得津津有味。他的戏,部部都好看。是那种普通观众认可的好看。不摆架子,不装样子,即便是严肃的革命历史题材,故事也讲得跌宕起伏,生动活泼。不像有些导演,架子搭得高高的,场面撑得大大的,一定要让人觉得他来头大,出身好,净拿些主题、概念、主义、风格吓人、唬人,严肃得无趣,深刻得空洞。
傅导的戏,有点像艺人说书,用故事、用细节、用动作、甚至用打情骂俏,让观众该笑的会心地笑、开心地笑,该哭的动情地哭、痛快地哭。哭过、笑过,他对人情世态的描摹、理解,就活在你眼前,印在你心里。你就不得不由衷地叹服他的聪明和高明。傅导最大的本事,就是能让观众看得进、坐得住、忘不掉。不知不觉中,他的人生经历和经验,他的军旅情结,他的乡情和乡愁,一下子就抓住了你。我觉得,他是把小聪明和大智慧结合得最完美的导演,是鬼才和天才兼具的导演。
傅导吃饭不讲排场,喜欢吃口味,拍戏也是这个风格。一般的大导,进了排练场就是阎王,傅导却很少板着面孔。他拍戏时,绝少大呼小叫,总是谈笑风生。台上的演员因此也少了几分拘谨,多了几分轻松。遇上愚钝点的演员,傅导也不批评,反复开导,循循善诱,实在一时不见成效,总是幽默一下就过去了,不肯委屈自己尴尬,也绝不委屈别人尴尬。所以,傅导排戏也是戏,极精彩的戏,可说是奇思百出,妙趣横生。导演和演员相互调侃,频繁互动,排练场笑语连连,其乐融融,艺术之树就在这和谐、欢乐的气氛中悄悄地长大。
有一回,轮到一个演员上场了,却见不着人。舞台监督说是变天去给孩子送衣服了。傅导听说,“哦”了一声,并不动怒,排练场中照常工作。
最好看的是他为演员做示范,惟妙惟肖,出神入化。他注重细节,近于苛刻,一个重音、一个眼神,一个调度、一个身姿,绝不马虎,一定要完全到位才罢休。现在的导演,一般是只导不演,只停留于动动嘴皮子,而傅勇凡是既导又演。《遥远的乡土》几乎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他都一遍遍示范。就一个下跪的动作,他不厌其烦地演示,照样膝盖撞得地板“咚咚”响。而演员们也很乐意接受他的示范,因为一句普通的台词只要从他嘴里一过,立即就像受了某种点化,产生出神奇的效果。最精彩的是他的表演,学小姑娘撒娇比小姑娘还娇,教演员推车挑担比农民还像模像样,让你不得不叹服。
于是就有了《遥远的乡土》的异彩绽放。那天看连排,一位老者边看边说:“这戏真写得好,完全是戏包人。”我不这样认为。戏固然是写的好,但导演的聪明才智让戏焕发了神采。这就像一位美丽的女孩,天才的摄影师放大、定格了她的美丽。这部戏,精彩纷呈的故事娓娓道来,观众就像走在繁花似锦的林荫道上,目不暇接。话剧我看过不少,《遥远的乡土》确实与众不同。它不是戏包人,也不是人包戏,它是戏与人水乳交融。演员们一穿上戏服,个个如神附体。母亲是那样慈祥,儿子是那样纯孝,女儿是那样动人,尊长是那样威严。不待开言,观众就充满了期待;一旦开言,观众便如醉如痴。
昨夜,我又看了一遍《遥远的乡土》,回到家已是深夜,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高高山上一棵桃”,戏中的主题曲总在脑海中萦绕不去!这个戏我已看过多遍,每次看都止不住泪水流淌。娘的苦心,崽的孝心,六叔的良苦用心,余九皋的虚荣之心,还有自芳妹妹的善良之心,张县令尚未泯灭的恻隐之心,无不让人感喟唏嘘。
而这一切,都和傅勇凡导演60多个日日夜夜的付出息息相关。
胡小燕:江西省群众艺术馆
责任编辑:周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