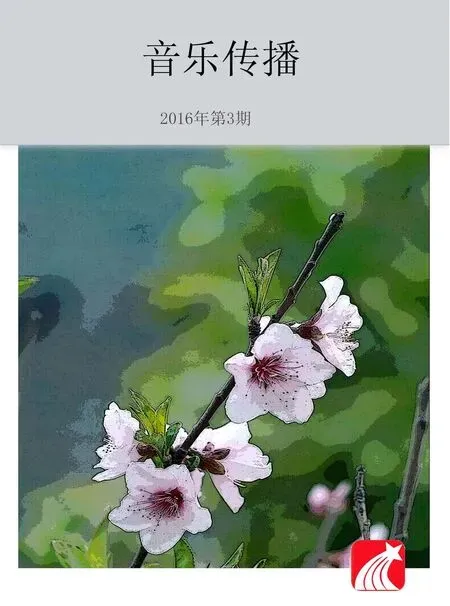网络传播时代的音乐著作权思考
■王赀兮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100024)
网络传播时代的音乐著作权思考
■王赀兮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100024)
自1709年英国议会颁布《安娜女王法令》以来,著作权法历经三百多年的发展,虽然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却始终无法跟上侵权行为的发展状况。而近几十年来,网络等新兴传播方式的快速发展又加剧了这一趋势,各种新的侵权行为层出不穷,刚堵上一个漏洞却又有更多盗版纷至沓来,著作权人的利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相较而言,“德治”比“法治”更为有效,更为治本,但最终敉平这一切的只能是时间。
盗版商业维权知行合一
当今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除了工业、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的考量之外,也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的比拼。互联网传播方式的普及,让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越发突出,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凭借其发达的文化产业,极大增强了其国际影响力。当然,发展文化软实力不是发达国家的特权,发展中国家也在奋起直追。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绕不开的环节,那就是著作权的保护。没有著作权的保护,文化产业的发展就没有保障,自然更谈不上文化软实力的积累和巩固。因此,著作权保护问题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仅就音乐著作权进行讨论。
一、音乐著作权保护的现状及问题
当今,随着互联网音乐的普及,传统唱片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CD的销量萎缩超过95%,从唱片公司到音乐人,甚至包括某些渠道方,都在“哭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音乐搜索在所有网络应用中稳居前三名之列,网络音乐所创造的年收入可超过300亿元人民币。海蝶唱片的总裁卢建曾经表示,我国音乐产业的年产值已经超过电影加电视剧的年产值总和,而由于著作权的缺失,传统唱片公司从中分得的利润却只占2%至3%,有时甚至连1%都不到,无怪乎连全球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百代唱片也会被收购,前太合麦田总裁宋柯甚至断言“唱片已死”并决意改行卖烤鸭。①参见佚名《音乐产业盈利唱片公司却在哭穷》,原载《东方早报》,转引自“凤凰网”,2012年3月30日(截至2016年5月4日)。http://yue.ifeng.com/neidiliuxing/detail_2012_03/30/ 13563936_0.shtml按:该资料网络版将海蝶唱片总裁的姓名“卢建”误为“陆建”。我们知道,一首音乐的录制要经过收歌、Demo确认、发编、过带、配器、配唱、和声、混音和母带处理等诸多步骤,从制作流程的复杂程度来看,其对质量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如果任由著作权缺失的情况继续下去,必将极大地挫伤音乐制作人的积极性,而表面上一片繁荣的音乐产业也将因失去其赖以发展的源泉而成为泡沫产业。
不过,维权谈何容易。且不说贩卖盗版音乐的人如过江之鲫比比皆是,单是音乐专辑还未发行,其单曲便已在网上流传开来,网民可随意免费下载无须担心惩处的事实,当下也是司空见惯。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交易体系模糊、版权观念淡薄、法规尚待完善,以及有关部门权责不清,这六点可以说是著作权生态中的六大顽症。
侵权成本低以北京地区而言,通常一家KTV门店如果未经许可而播放歌手的MV营利,维权方的取证成本一般在5000至6000元,维权成功后歌手大概能够获赔3万至5万元。①参见张璐晶《电影唱片老板诉苦版权如何致富》,载《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7月10日。就全国范围来说,这已经算获赔数额比较高的了,但对大多数KTV经营者来说,这仍然处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通常无法起到威慑作用。
维权成本高著作权人如果想挽回自己的损失,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高。如2010年,滚石唱片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称其旗下600多张专辑中的上万首歌曲被某音乐网站用来提供给客户任意试听、下载,并可被下载成手机铃声和彩铃。然而法院回复的公函却表示此案涉及专辑过多,须按专辑拆分进行起诉,也就是说此事要拆成600多件诉讼。对此,滚石唱片的代理律师感到“欲哭无泪”,他说:“仅仅要求侵权者停止侵权的诉讼成本就高达600多万元。”②参见彭涛、罗雨静、谭祖发《滚石诉一听音乐网侵权遭遇“诉拆拆”一个侵权案变身600多场官司》,载《中国质量万里行》2010年第1期。像这样的情况,大大降低了著作权人维权的积极性。而且很多时候,即使著作权人胜诉,也无法阻止侵权行为的继续。
交易体系模糊市场的不健全,使得唱片的交易缺乏统一的标准,这就给了侵权者许多漏洞可钻。如在KTV和音乐网站等领域,就很难弄清楚经营者是否已购买曲库,以及如果购买是通过何种途径购买的。笔者在撰写本文时,曾在“百度音乐”上搜索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单此一首歌曲就搜出344条链接,如果要对每首歌曲都逐一查证每条对应链接是否获得了授权,人力成本是很高的。于是,著作权人的利益也就在不知不觉中随之流失。
版权观念淡薄网民对通过搜索引擎或音乐APP找到未经授权的歌曲并随意下载往往也不在意。笔者曾随意询问过53名本校在读的硕士研究生,他们均表示曾借助百度搜索引擎下载音乐,且并不以为有何不妥。虽然这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统计调查,但笔者认为以此经验可以基本认定这种侵权现象是多发的。
这种“吃白食”的心理给著作权保护制造的阻力有多大,看看电子邮箱领域的发展也可窥见一斑。网民由于长久以来习惯于使用免费电子邮箱,因此自发形成了集体抵制付费邮箱的态势,导致诸多欲推行付费邮箱的网络公司不得不撤销这类计划。相比而言,音乐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即使所有网站一同推行付费下载,网民也大可以用“不听音乐”来抵制,迫使以获利为目的的网络公司妥协。因此,在网络盗版依然泛滥的当今,付费下载对绝大多数的音乐种类而言就几乎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
法规尚待完善现行的著作权法很难说是完善的,其中甚至存在比较明显的疑似有漏洞之处。如2012年的第三次著作权法修改稿草案中曾经广受质疑的第46条:“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48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一张唱片的制作流程之复杂,其中所包含的劳动价值之高,前文已有说明,更不用说其中还蕴含着创作者与唱奏者的心血与热情,而对音乐著作权的保护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让他们进行再创造的保障,是要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从而创作或制造出更多更高水准的、更有价值的音乐作品。上述条文虽然并未出现于最终的修订草案送审稿中,然而著作权法对唱片版权保护的重视之不足,或可由此隐见。
有关部门权责不清作为我国唯一的正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简称“音著协”)或许存在权责不清的问题。歌手胡海泉就曾表示,他所在的“羽泉组合”并不是音著协的会员,双方也没有合作机制,但他们就自己创作的歌曲举办一场演唱会,却要交大约10万元的“著作权人费用”,否则就无法完成报批。③参见佚名《胡海泉爆料版权保护怪相多唱自己的歌也交钱》,载“光明网”,2012年5月30日(截至2015年12月3日)。http://e.gmw.cn/2012-05/30/content_4244082.htm与之类似的情况是,2009年中央电视台也曾报道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简称“音集协”)两年间向KTV等行业收取了8000万元的版权费,但相关歌曲的创作者却只能拿到不超过40%的报酬。④参见佚名《音集协收巨额版权费歌手未分到钱》,原载《东方早报》,转引自“网易网”,2009年5月12日(截至2016年1月19日)。http://ent.163.com/09/0512/10/5940I86V00032DGD.html
笔者以为,作为一个大国而言,将著作权的管理权收归国有固然应该,但也应始终秉持保护著作权人知识产权的原则。如果不能严格地尊重这一原则,而著作权的管理又被少数机构垄断从而难以形成有效竞争的话,那么这些机构就很有可能被超额利益所吸引,与其设立的初衷背道而驰。在一些文化产业更为成熟的国家,类似于“音著协”和“音集协”的行业协会一般都有多个,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因此相对来说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保护著作权的宗旨。
二、音乐著作权保护的历程
当今世界,音乐类的著作权法虽然仍有待完善,但毕竟已经有了一个漫长的查漏补缺、不断演化的过程。因此,要讨论今后的音乐著作权保护,将其过去的历程进行一下简单的梳理是有必要的。①本节案例均可参见[美]杰弗里·赫尔著《音像产业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226页。
著作权即版权,主要指作者对其文字及艺术作品所享有的权利,最早出现在1709年英国所颁布的“安娜法”中,但当时的版权主要还是针对“印刷成册的图书”而言的。自19世纪80年代,埃米尔·柏林纳改进留声机、发明唱片之后,唱片版权的保护才逐渐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在唱片诞生之初,唱片公司对著作权人实行的是一次性买断。然而一首音乐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在其投入市场之前是难以预估的,因此创作者和唱奏者的权益通常难以得到保障。于是,在20世纪初,某些著作权人开始提出收录在唱片中的歌曲每一次出版,著作权人都应该获得相应的收益。然而,在1908年的怀特—史密斯唱片公司(White-Smith Music Publishing Co.)对阿波罗公司(Apollo Co.)的案件中,美国最高法庭就支持了唱片公司的意见,认为“歌曲在一定硬件设备的加工下,比如柱形或圆盘形唱片对歌曲进行了再加工,就不再看作该歌曲的拷贝,因为该歌曲不能从硬件再加工中视觉识别到”。这样的判决在今天看来实在可笑,因为作为听觉艺术的音乐竟然需要以视觉为参照来判定是否侵权。
不过,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1909年,美国版权法新增强制性机械许可条款,允许在给予版权所有者一定补偿的前提下,对后者已经授权允许硬件复制的音乐进行复录。虽然仍有人抱怨该条款使得唱片公司得以毫无节制地复录唱片,对创作者和唱奏者还是不公平,但版权所带来的利益不再是一次性买断的了,相较此前来说仍是一次很大的进步。
20世纪60年代,8声道盒式磁带的出现让音乐的复制变得极其简单,于是大量未经授权许可的盗版唱片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市场。唱片公司对此几乎束手无策,因为根据1909年版权法,盗版商可以在被发现之后再支付强制性版税,许多盗版商仅将此视为他们生意上的“不便”而已。各大唱片公司强烈要求美国各州通过反盗版法,然而国会从1962年开始讨论修改版权法,直到1966年才由众议院勉强通过,而直到新的众议院选举之前,参议院也没有通过这个新的版权法。事情直到1976年才初步解决:根据那一年的版权修订案,出于商业目的或个人经济利益的版权侵犯,处1年监禁和1万美元罚款。1982年,处罚提高至5年和25万美元,1992年又提高到最多10年和最高50万美元,但直至今日,盗版唱片仍然在市场上肆虐。
与此同时,唱片租赁业也逐渐兴起。因为磁带和光盘容易复制,因此许多消费者只要花很少的钱租一张唱片,再买一张空白唱片,就可以复制之后再把原片还给租赁店。唱片在磨损之前可以进行多次复制。这样,唱片公司的货物几乎只能卖给租赁店,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挤掉了前者的生意。针对这种情况,美国立法机构1984年出台《唱片租赁修订法》,禁止了唱片租赁,但并未提及私人复制唱片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仍然可以将购买的唱片借给亲戚朋友进行复制。解决这一问题的是1992年的《家庭唱片法案》,该法案允许家庭拷贝,但要求对数字录音机和空白数字媒介收取版税,并要求生产厂商给所生产的所有数字录音机安装防止用户进行多次拷贝的系统。
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通过回顾著作权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对唱片版权的保护是一个不断查漏补缺的过程,填补一个漏洞需要经年累月的努力。然而,常常是还没等一个漏洞被彻底补上,新的漏洞便又接踵而至。法律完善的速度似乎总也赶不上问题出现的速度,而且这种情况还可能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发展而出现得越来越多,因为网络音乐复制是一种带有高度强烈的自主性的复制,它打破了传统传播途径的界限,实现的是“点对面”的大众传播,而且几乎不受数量的限制。
其实如果稍微熟悉一点法律史就能注意到,著作权法的这种情况,在很多其他类型的法律与制度的发展历程中都会出现。《论语·为政》记载孔子的话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说,治理国家、社会,可以依靠法律,也可以依靠道德,但如果不推行德治,一切都以法律为标杆,则群众虽然不敢触犯法律,却没有廉耻之心,心里多少还是会有非分之想,因此就会不断寻求机会钻法律的空子,挑法律的漏洞,甚至铤而走险也不奇怪,这是治标不治本。想要治本,比较靠得住的是以德治国,让人“有耻且格”。“格”的解释很多,用孔子自己的话说也可以叫“思无邪”,而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将其诠释为“良知”。据《传习录》记载,王阳明曾提出:“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只要觉悟良知,恶念即成菩提。但这“一觉”不是自己口封的,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来体现的,因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一个人如果真正认识到了保护著作权的重要性,就自然会体现在他的言行举止中。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期克服人们常常会遇到的二重道德的问题。他一再强调,不能付诸实际行动的知,就不是真知。拿数字音乐来说,相信任何人都能随口说出许多保护著作权的理由,但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研究生也经常会在网上下载一些并未明示可以随意下载的音乐,很少意识到自己正在严重侵犯他人的著作权。试想,如果音乐无法为创作者和唱奏者带来合理的收益的话,今后又有谁来为我们提供高质量的音乐呢?当然,近年来随着相关法律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音乐网站开始实行付费制,然而长久以来人们已对免费音乐习以为常。只要大部分人还保有这种习惯性思维,网络企业势必优先考虑消费者的需求,而继续置版权所有者的权益于不顾。或许,只有当人们都懂得尊重和捍卫他人的合理权益时,著作权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而且这种解决并不是迫于法律或其他外界压力,而是自行消弭于无形。所以说,要想维护音乐著作权,最重要的还是加强道德教育,提高人的整体素质。
当然,如果话题停止于这里,则犹有未尽之言。《道德经》第三十八章①本文使用的《道德经》章次以王弼注本为准。——本刊编者注言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这话是说,没有道德也不会违背道德才是最高层面的道德。如果世上从未发生过侵权,著作权这个概念和相关的法律也就不会被提出,而相关规则的出现又从客观上促使侵权者挖空心思去钻法律的漏洞。《庄子·胠箧》中“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观点,表明庄子认为圣人与大盗不过是一体两面,二者都是道德沦丧的产物。这样的看法难免显得过激,但也说明以立德来对付不道德的侵权行为,其效果注定将是有局限性的。《道德经》第三十六章说“将欲翕之,必固张之”,暗示着如果强行推动事物发展,使其提前进入巅峰期,那就往往意味着衰退期也随之被提前。所以,仅从理论上说,最终的新秩序只能在音乐人无利可图、侵权者无版可盗时才会被真正孕育出来。
这种想法对只需要可实际操作的策略的人来说,基本没有意义。但是,顺着这个思路,我们至少可以意识到,一项精心设计过的制度虽然在创立之初通常都是优点多于缺陷,但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难免的。易中天在论及制度时曾说,“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也不需要后代人来努力了”。②易中天著《帝国的惆怅》,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音乐著作权的保护问题,恐无法在此成为例外。所以说,在侵权问题面前,我们可以借鉴哲学智慧,冷静认识其客观趋势。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固然是必要的,而在解决现有问题的同时又将不断出现新问题也是必然的。只有在正视这一点的基础上,方能对音乐著作权问题的未来做出清晰的判断。
[1]曾田力主编《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2]曾遂今编著《音乐社会学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李立主编《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蔡翔、王巧林等著《版权与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李零著《丧家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周月亮著《心学大师王阳明》,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7]刘潭洪《案例研究:从滚石唱片诉讼案分析我国版权诉讼中客观的诉之合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8]袁琳、郭登杰《数字时代唱片公司版权保护策略研究》,载《新闻传播》2014年第5期。
(责任编辑:魏晓凡)
王赀兮,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创作与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