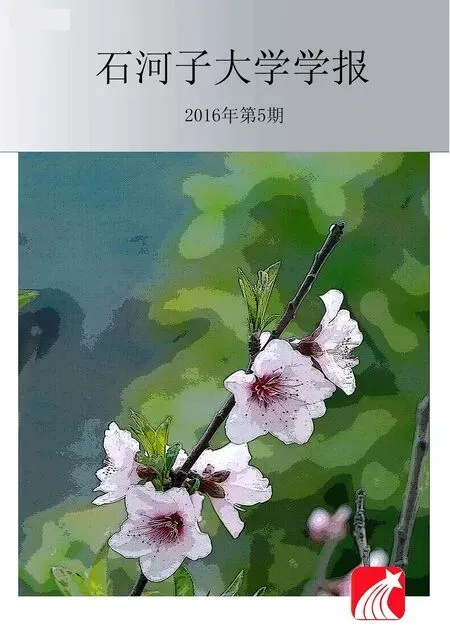穿行于维汉两种文化间
——阿拉提·阿斯木的汉语小说创作研究
何莲芳
(新疆教育学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3)
穿行于维汉两种文化间
——阿拉提·阿斯木的汉语小说创作研究
何莲芳
(新疆教育学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3)
阿拉提·阿斯木是从母语写作转向汉语写作的,他以汉语创作表现当代维吾尔族人的世俗生活,作品一方面昭示了红尘男女对财富、欲望的享乐主义追求,另一方面揭示了在精神的感召下,他们寻找灵魂和生命价值的自我救赎过程。他融汇汉维两种文化(语言)的特点,对小说语体进行大胆实践,颠覆了汉语言固有的能指之意,表现出语言的陌生化,显示了当代新疆双语创作的一种创新路径。
阿拉提·阿斯木;当代少数民族生活;宗教感召;汉语陌生化
URI:http://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61019.0122.020.html
阿拉提·阿斯木是新疆典型的双语作家,从母语写作转向汉语写作。他一方面使用维吾尔语进行创作,且创作数量大,在母语读者阅读圈和评论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近年来积极探索使用汉语进行创作,其代表作《蝴蝶时代》《时间悄悄的嘴脸》也获得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好评。他以汉语作为“媒介语”进行双语写作既有进行文学实验、开拓创作空间的考虑,也带着些许从边缘走向中心、以期获得更大创作效应的阅读期盼。阿拉提行走于两种文化(语言)间的创作实践,逐渐赢得了不同文化圈读者和评论者的认可,成为当代新疆名符其实的双语作家。本文所要关注的是:阿拉提·阿斯木从母语写作转向汉语写作的过程中两种文化对其创作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些影响所具有的启示性意义是什么?在双语作家创作中表征着怎样的信息?
阿拉提·阿斯木,维吾尔族,1958年11月11日出生于新疆于田。他务过农,当过报社印刷厂职工,先后在不同学校读书学习翻译专业,担任过报社维文编辑、伊犁州党委宣传部干事、奎屯市委副书记、伊犁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从事过政府和文化事业单位的不同工作。边工作,边写作,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时接受写作专门训练,是鲁迅文学院第12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随后任新疆文联副主席,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阿拉提·阿斯木的人生轨迹也是一个从母族生活工作圈逐步进入汉语文化圈的过程。民汉兼通双语人的文化人格特征给他的创作烙印上独特特征。同很多汉语写作的双语作家的叙事策略不同,他的汉语写作不是“民族志”书写,也绝不是一种“换装”后当代维吾尔族生活的简单复写,而是以当代维吾尔族人世俗生活为叙事对象,用汉语这一媒介语,表达作者对这个物质至上的消费主义时代人的心灵历程以及安妥灵魂的探寻。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既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地域性,也表现出深刻的当代性和普世性,在他的以汉语为媒介语创作的作品中常常呈现两种文化(语言)混成后的深刻影响,这种“混成”烙印着维汉两种文化交融后的印记。维汉两种文化的交融既体现在阿拉提·阿斯木小说创作的选材与取向上,也体现在他小说创作独特的语体色彩上。
一、在“时间”的长河中寻找灵魂的安妥
“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很少去写发生在久远的历史中的故事,选择的题材直指当下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从不回避生活的冲突和生存的艰难困惑,人性深层的善与恶及爱与恨在他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1]6。纵观阿拉提·阿斯木的汉语小说创作,他的小说特别集中地表现了现代红尘社会中维吾尔族男女对财富、情欲的疯狂追求。他们或为独吞财富骗亲失信(《最后一个男人》),或恣意挥霍青春与财富,疯狂追求财富和感官享乐,失去了道德和伦常(《阿瓦古丽》),或以青春和美貌作资本,混迹于男权社会,在身体与权力的交换中实现了自我财富积累,彻底沉醉于欲望之海(《蝴蝶时代》)。在《时间悄悄的嘴脸》中的艾莎麻利为最大化地攫取“玉”这一财富,不惜买凶杀人,不计后果,对手哈里同样为了财富,背信弃义,为实施报复,杀人夺宅;他的儿子尼亚孜则为富不仁,在为父复仇的过程中,手段卑鄙,道德沦丧,还有阿吉木头、琴手斯迪克、库热西走狗等等,阿拉提·阿斯木小说中每一个进入上流社会的人都手段卑劣、身体肮脏、灵魂堕落,他揭示了这个欲望化的“蝴蝶时代”人心的贪婪、人性的疯狂、灵魂的堕落,人格的卑下。这是他对现代文明世界“人”的异化的批判和揭露,是他作品社会批判的一面,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一面。阿拉提·阿斯木的深刻和过人之处还在于揭示了在“时间悄悄的嘴脸”下,纵欲者自我的灵魂拷问和心灵反思,在精神的感召下,迷途知返,心灵净化和精神重生。主人公发生“陡转”的动力和源泉主要来自于人物的宗教信仰,更显然也来自于隐含作者的宗教情怀。是作者秉持的伊斯兰教精神使笔下的罪人们洗净污垢,走向了精神升华和心灵宁静,从而蜕变为新人。阿拉提·阿斯木小说中人物的人生轨迹发展来源于母族文化的人生观和幸福观影响。
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创作中遵循着这样的叙事语法规律:疯狂纵欲,追求享乐和现世幸福(财富与情欲),但人物灵魂与精神空虚,为寻求出路,或自悟或受人启发与点拨,最终回归故乡与家庭,回归一个伊斯兰信众的正信与本意。他们一方面节制个人行为,远离声色犬马,深居简出,回归家庭与亲人;另一方面赈济穷人,回报社会,广做善事,甚至以德报怨,建立人和人之间或者个人和社会之间友爱关系、互助关系。纵欲—寻找—点拨—重生—回归,是其基本的叙事语法。宗教的力量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召唤和匡正作用。
伊斯兰教讲究信仰的实践性,提倡两世吉庆,不排斥世俗之乐和幸福,只要信众重视修行、敬拜真主、完纳天课、回报社会,灵魂自会走向天堂,这种对现世生活的尊重、对死后升入天堂以及获得幸福途径的生命观和幸福观对伊斯兰社会信众的思维、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在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创作中,才有阿瓦古丽新生后从周一到周五有节律的生活,包括谨守拜功、清心寡欲,广施财富,帮助最需要赈济的福利院的儿童和老人,最终,灵魂摆脱了罪恶,找到了幸福;海莎乳房在彻底疯狂后也结束了和大人物之间的买卖关系,终止了与男人之间的肉体与财富的游戏,认祖归亲,回归爱情和家庭,在洁净身体的同时,灵魂也取得了安宁;艾莎麻利对仇人哈里父子以德报怨,两次在其生命危急时刻出手施救,终于获得了仇人的宽恕和敬意,也获得了社会的敬意,最终回归家庭,开始以财富回报社会;好姑娘古丽巴哈尔在违背父母旨意自由恋爱后遭遇遗弃,身心迷茫而一时放纵自己,在经历了灵魂的反思和天使的启悟后,变成了一只渴望鸟。阿拉提·阿斯木对自我创作有这样的认识,“新疆这个地域是多民族的文化,我主要想表达这个地域的时间、历史、生活,维吾尔族人民现在的困惑、痛苦、幸福”①参见“别人眼中的作家: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专访”http//blog.sina.com.cn/u/1575714590.。
我们注意到,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里的女性,纵情于声色犬马的情欲生活后,在面向内心时,都有一种强烈的罪恶感,这也与伊斯兰教对女性贞洁的提倡与对私通的贬斥有密切关系,在《古兰经》中,“在那些乐园中,有不轨非礼的妻子,在他们的妻子之前,任何人和任何精灵都未与她们交接过”[2]402,强调女性极尽贞洁,宛若天使。而对于私通则认为是羞耻的,要受天谴。以此,真主可以毁灭了努哈的宗族,“以前,他毁灭了努哈的宗族,他们确是更不义的,确是更放荡的”[2]398,伊斯兰教对私通,充满了诅咒和贬斥。颇有意味的是,与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纵欲(迷失)—反思—寻找—重生相对应的是正面形象的塑造,无论是《好姑娘》中的麦尔艳,还是《时间悄悄的嘴脸》中的米娜瓦尔老太太,以及好姑娘古丽巴哈尔都有一个共有特征:勤劳贤淑、善于持家、热爱家人、乐于助邻、生性纯良、宽厚仁爱、恪守伊斯兰教义,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这些善与美的形象都围绕女性与家庭及邻里关系展开,尤其是对穷人的赈济,这些都是在宗教影响下作者对女性的想象性建构。
我们还发现,在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创作中人物回归、走向幸福彼岸的两个核心要素:故乡家园和宗教。他的人物最终在这里找到了幸福的归宿与灵魂的安宁。这显然与伊斯兰教重视家庭,强调长幼有序,提倡互帮互持,忠于家庭伦理道德有关。对于新疆维吾尔族这个典型的依托绿洲、主要从事农业兼及牧业的农耕民族来说,在长期的民族发展中,既受到中原农业文明的影响,也与伊斯兰教进入新疆本土后与戈壁绿洲的农业文明相遇后,着意家庭、重视人伦、强调伦理道德和女性贞洁有关;同时也与伊斯兰教在引导信众获得两世吉庆的生命观、价值观与幸福观,对信众世俗与精神生活两个层面的教化、规范和净化有关。显然,这对于阿拉提·阿斯木这样的维吾尔族双语作家思维的影响、叙事立场、价值取向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母族的“集体无意识”对作者的深刻影响。
正是在这样一种叙事语法规律下,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创作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哲理意味。小说中人物面对财富、欲望、亲人、友情、爱情,表现出鲜明的自省与反思,人物在心灵的自我辩驳中,思考人生之意、生命之价、家园之义。这种人物自我灵魂的拷问不仅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风,更显示出作者受到本民族文学的深刻影响。正如学者所述,“新疆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是一个善于思考的民族,他们的大量传说、民歌谚语、警句格言等,都包含了关于自然、关于道德的丰富而深刻的哲理”[3]32,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使人读后掩卷深思,从而审视心灵和人生。
二、强烈的民族文化色彩意象
在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中,人物直面死生是经常出现的叙事场景。作者往往将人物置于死生境地,在广远的时空中思考人生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使小说具有思辨与哲理气息,由此产生了普适性的审美价值。因而,作者对于死亡的叙述具有别样意味。与大多数文学创作将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结,表现为悲剧、正剧所不同的是,阿拉提·阿斯木对死亡的叙述充满了圣洁和恬淡的气息,这种圣洁和恬淡带着悲悯的态度,沉淀着伊斯兰教文化对生命的态度。因此,阿拉提·阿斯木小说对于死亡的叙述是宁静的,充满了回归的意味。如在《时间悄悄的嘴脸》中,对于米娜瓦尔老太太死亡场景及送葬过程的详细描述,作品写得干净、从容、清净、淡定,无论是死者的安宁、生者的悼念、送葬、生者对生命和人生的感悟和珍惜,作品突出了安然、圣洁的意味,这些都烙印着伊斯兰教“一切因于、归于真主”特殊的生命观。同样,生者对于死者的超度、在死者灵前的忏悔、反思,最终返璞归真,产生了生命的净化,使小说具有浓郁的宗教意味。如《在时间悄悄的嘴脸》中:“艾莎麻利瞌睡了,正当入梦乡的时候,一道强烈的光亮惊醒了他,七颗明亮的星星,从遥远的天空飘落,照亮了米娜瓦尔老太太的墓。……我们是王派下来的,吊唁米娜瓦尔老妈妈,人间的喜事丧事,我们都知道,我们为什么几万年以来,要固执地照亮你们人类呢?因为你们热爱生活,一个新生命降临时,你们祈求他长寿,一个生命享用完真主赐他的时间回归尘土时,你们满怀悲痛地送他们上新的征途。这一切,是我们离不开你们的理由。我们相信,米娜瓦尔老妈妈的灵魂是会升入天堂的。”[4]160这是艾山麻利在母亲墓前祈祷时心灵受到净化的场景。其中“王”“七颗明亮的星星”“真主”“天堂”等词语与伊斯兰教中的使者、真主、天堂意义多有符合之处,其宗教色彩不言自明。
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中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意象:水,以及作者对水的讴歌——圣水、洁净之水、洗去人生命的污垢之水、使万物焕发蓬勃生机之水、奔腾不息之水,给人们带来幸福之水。如“我们出生的时候是非常肮脏的,所以一生都不可能干净,一生都离不开水,我们会在某一个时期纯洁无瑕,但我们摆脱不了污水的浸泡,这是我们甜蜜的悲剧。”[4]87这里,水分净水与污水,水可以荡涤污垢。再如,“河北岸是千年的白杨树,是画家笔下的白杨树,笔直地留恋着伟大的苍天,在湛蓝的天空下代表远古的人顶天傲立,在风的见证和鼓舞下生生死死,世代繁衍,护卫着千古西域河,亲切的河水在白杨树的阴翳下喧傲长流,偶尔有候鸟懒洋洋地飞向静谧的南岸……永恒的河水神秘地流逝着,伟大的时间记录着像情妇眼睛一样耐看的暖水。”[4]295水在这里是祥和的、清净的,暖人的。上述“水”意象的出现和礼赞也不是简单的,而是有着深厚丰富的文化含义。它与伊斯兰教对于天堂的描述有关、与生命有关。《古兰经·月亮》真主帮助求助者:“我就以倾注的雨水开了许多天门,我又使大地上的泉源涌出,雨水和泉水,就依既定的情状而汇合。”[2]404《古兰经》中天堂往往在河边,河水潺潺、青草葱葱、瓜果鲜美,人与自然和谐,洋溢着勃然的生机。如“他们将在恩泽的乐园。许多前人和少数后人,在珠宝镶成的床榻上,彼此相对地靠在上面,长生不老的僮仆,轮流着服侍着他们,捧着盏和壶,与满杯的醴泉,他们不因那醴泉而头疼,也不酩酊。”[2]39水与河在伊斯兰文化中具有深厚、深刻、美好的能指意义。因此,阿拉提·阿斯木的汉语小说创作受到母族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三、融合汉维两种语言的特点
阿拉提·阿斯木的汉语小说,一个鲜明的审美特征是其语言的“陌生化”现象,即对汉语原有表达方式和固有之义的颠覆性使用。对此作者自述道:“如果我用汉语写维语生活,完全用汉语思维方式的话,那我表现不出本民族的文化、习俗、生活、情趣、伦理,如果我完全用维语的形式表现,也受到了汉语的限制。我现在努力想做的一件事情是,怎样把维语最通俗、最准确、最独特、最幽默的表现形式和汉语最优美、最美好、最清晰、最可爱的形式结合起来进行表达,把两种文化最精髓、最值得玩味的方面结合起来。我想这能不能产生一种新的阅读效果,一种新的实验?我想在这些方面有所探索”①参见“别人眼中的作家: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专访”http//blog.sina.com.cn/u/1575714590.。而“维吾尔人的说话、生活,在一些喜事上,在一些朋友聚会上,我们运用的文字,基本上都是那种意象性的、那种概括性的、那种想象性的,给人非常优美的赞美、非常优美的愿望,这些都是通过非常优美的、夸张的一些词语进行表达的……我用汉语写作时,我的思维是交叉的,有汉语的,也有维语的……有时候,我是把维语、汉语的表达形式糅到一块儿。既有汉语思维,又有维语思维,再加上我自己独特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如我写过这样的句子:‘时间语重心长地照耀我们’,这种表达在维语书写里是没有的,在汉语里也是没有的,但我把两种语言表达形式结合在一起时,加上我自己的一种认识、思考,我就想这样表达。我就想让语言形式、故事内容的表达有一些意思,在有意思的基础上,在表达上更丰满,在丰满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比较遥远的效果,不要让表达离人很近。要让表达远离我们的认识,能让我们多思考——为什么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认识得太容易,我想这可能失去了文学存在的价值。我想,把两种文化的同与不同,或者两者都不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糅合在一起”②同上。。由此可见,作者是将两种思维和语言表达方式糅合在一起进行汉语写作。
阿拉提·阿斯木承继着现代汉语的简白和流利,结合着维吾尔语固有的优美、夸饰、铺排、悠远、思辨的特点,对汉语固有的表达方式进行了突破和颠覆,形成新疆少数民族汉语表达的特点,形成了阿拉提·阿斯木小说语言的独有魅力。
(一)颠覆汉语能指,导致语言陌生化
一种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约定俗成,有其鲜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阿拉提·阿斯木汉语小说中有意颠覆汉语言能指,使其具有多向性、陌生化的特点。在《时间悄悄的嘴脸》这部长篇小说中,“嘴脸”这一在现代汉语中具有贬义色彩的能指被作者赋予了多重含义,别有特色、耐人寻味。试看,“一些嘴脸没法帮助她的时候,她想到了那句话,不要信卦,也不要不信卦”[5]5,“嘴脸”在这里是借代,即“走狗”“朋友”“帮闲者”之意。又如,“人的嘴脸吃饱后,开始张狂着咬人了”[5]54,“嘴脸”这里指身体、肚子。还有“这玉,说到底是个石头呀,……现在谁人让这个东西这么有嘴脸,这么有人气呀”[5]55,“嘴脸”这里指身价、价值之意;“我做不到,我的嘴脸不干净……我的嘴脸早已背叛了我的意志……像我一样吃吃喝喝的人,嘴脸基本上是被他人利用的”[5]55。前一个“嘴脸”代指内心,后一个“嘴脸”代指人格、心灵。“人是软弱的,我们的心在很多时候不代表我们的嘴脸”[5]56,“嘴脸”代指呈现于外的面目。“回新疆耍嘴脸以来,这是他最高兴的一天”[5]119,“嘴脸”代指手段,诡计。“地上的路,没有嘴脸,不会说话,不会指引你贪婪的脚”[5]156,“嘴脸”代指指导人生的明确的方法。“六十岁的泼妇装饰装饰嘴脸,就三十岁的舌头嘴唇了[5]176,“嘴脸”代指脸庞。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嘴脸”被作者赋予多重含义,确已颠覆了汉语固有的所指,使其具有别样的含义,从而产生了“陌生化”的阅读效果。
(二)打破汉语言的常规语词搭配方式,在奇绝反常的组合中产生表达的新意与陌生感
如“肾脏一样的朋友”中“肾脏”与“朋友”搭配,直接形象、突兀生动,比喻关系铁,十分重要;“你是我心脏的血库,是我的动脉与静脉”[5]86,小说表达的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极端思念、仰慕之情和须臾不可分离之感,以心脏、动脉、静脉这些人体重要器官表达爱得炽烈,直白火爆。“婊子一样亲切的夏天一天比一天美好”[5]74,这是男性视角下对夏天的某些特征的欲望化表达。
又如以绰号的方式揭示人物某方面特征时,采取“名字+绰号”的方式介绍人物性格。绰号由“名字+显示性格特征”的词组成的,如“艾莎麻利”,表现艾莎做事利落、有魄力;“海莎乳房”,以“名字+身体器官”,凸显其生存方式和特点;“居来提公鸡”,以“名字+职业”,显示其卑微下流的发迹史;“尼亚孜国民党”,以“名字+党派名称”,则有多重含义,既有人物职业的经历痕迹,也有对人物某些性格的暗示,这种绰号命名法既受到汉语言文学传统的影响也表现出他的创造性。如《水浒传》介绍人物时往往“豹子头林冲”“及时雨宋公明”“玉麒麟卢俊义”“一丈青扈三娘”“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等等不一而足,是“特征(职业)+姓名”的方式,而阿拉提·阿斯木汉语小说继承与变化并举了,有一定的意味。
(三)继承母语言文学语和交际语繁缛夸饰的特点,使语言具有装饰性、狂欢性和思辨性
阿拉提·阿斯木汉语小说语言具有繁缛与夸饰,铺排和诗意的抒情特点,这其实与维吾尔族文学语言,也与维吾尔族人日常交际语的渲染夸张有关。如,“是神的力量让我选中了你,在你的身上,流淌着你祖辈纯良的血液,这是人类非常珍贵的东西,也是我们鸟类非常珍贵的东西。你现在已经是永生不老的神鸟了,要热爱神赐你的时间,不要以为你已经拥有永恒的时间了,就散漫地放任你的时间,当你真正懂得了你的财富就是你的时间的时候,你的歌声就属于天下的一切角落了,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期盼的美乐,应该属于一切弱小的人和力量充沛的人。我们为人的繁荣活着,这是我们的前定,因而我们的形象,在人间的绿荫里舞蹈,播撒我们忠诚的旋律……世界永恒折磨我们的一个麻烦时,当我们虔心歌唱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面临雷鸣和电闪呢?当你看见玫瑰盛开的时候,你要窥视灾难的走向,用玫瑰的芬芳阻挡罪恶,战胜丑陋”[5]176。此段语言用夸饰铺排的诗意抒情语言将说教和劝诫融合在一起,显示着母族文化(语言)对作者创作的深刻影响,而以汉语表达这种审美取向与文学传统,同样产生了语言的陌生感和新奇性。
(四)对汉文学传统叙事方式的借用或化用
汉古典叙事文学往往在人物出场开展情节叙事时,先叙其出身来历,过往情景,以便为人物“行动”进行铺垫,讲究故事性和情节的起承转合,追求结局完整,人物皆有交代。这个传统自《左传》开启、《史记》发扬、“四大才子书”强化而固化,阿拉提·阿斯木汉语小说也具有这个突出特点。在《蝴蝶时代》《时间悄悄的嘴脸》等众多文本中皆如此布局。如米娜瓦尔的家事、经历与性情,阿瓦古丽的前世与今生,阿吉木头、居来提公鸡、海莎乳房等人物出场的方式等等都有这个特色。同时,作者或以倒叙或以顺叙讲故事时,作品中人物经历大开大阖,情节起伏曲折,结尾圆整饱满,都遵循此种叙事逻辑,表现出作者以汉语进行写作时,对汉语言文学传统的继承和顺应。
我们从阿拉提·阿斯木的汉语小说创作的叙事对象、叙事语法、意象选择、维化汉语(陌生化的语体)等,看到了维汉两种文化(思维、哲学、审美、语言)对他创作的深刻影响,作者在汉语小说创作中,实验着、探索着穿行于两种文化(文学)传统间,进行个人化的文学实践,取得了创作上的成就。尽管我们看到,虽然变换了一种叙事媒介语,母族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使作者的创作依然打上浓重地域的、民族的、时代的印记。但阿拉提·阿斯木的汉语小说写作为表达本民族的当代生活、精神世界提供了一种方式、一种途径,也为中国当代双语作家写作提供了一种可供思考和借鉴的经验。
[1]董立勃.不一样的精彩[M]//阿拉提·阿斯木.蝴蝶时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
[2]马坚.古兰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阿拉提·阿斯木.蝴蝶时代[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
[4]夏冠洲.新疆当代文学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5]阿拉提·阿斯木.时间悄悄的嘴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任屹立)
【翻译研究】
Between Uygur Culture and Han Chinese Culture:Research on Alat Asem’s Chinese Novel Writing
HE Lian-fang
(Elementary Education Institute,Xinjiang Education Institute,Urumqi 830043 Xinjiang,China)
Alat Asem’s writing changes from mother tongue to Chinese.His works on Uyghur mundane life wrote in Chinese show the hedonist pursuit of wealth and desire of mundane Uyghur as well as their self-redemption of soul and life value impelled by religious spirit.Combining both Uyghur and Chinese culutres,he carries out a audacious experiment on the style of novel,overturns the inherent meaning of Chinese signifiers and defamiliarizes Chinese to show a new path of contemporary bilingual writing in Xinjiang.
Alat Asem;contemporary life of ethnic minorities;religious inspire;defamiliarization of Chinese
I207.9
A
1671-0304(2016)05-0106-06
2015-04-15
时间]2016-10-19 1: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新时期以来汉语小说创作的乡土化研究”(13XZW020);新疆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新时期汉语小说创作的乡土化倾向研究”(12BZW081)。
何莲芳,女,浙江绍兴人,新疆教育学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乡土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