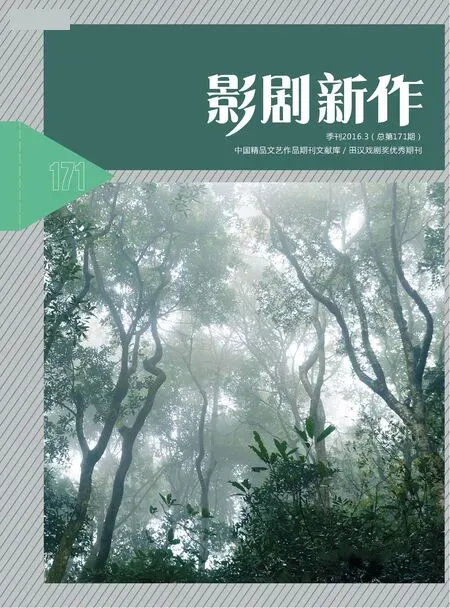歌剧《回家》的民族化探索
刘威利
歌剧《回家》的民族化探索
刘威利
歌剧《回家》在民族化方面作出了成功探索。展现人物情感时,运用了戏曲抒情性的表达方式,通过状物抒情和借景抒情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心理和塑造人物形象。表演上巧妙化用戏曲的程式动作,歌舞化的肢体语言有机融入其中,描景、抒情、写人浑然一体。在舞台呈现和场景表现上,较多借鉴戏曲的舞台处理方式,对舞台时空进行多重空间处理,转换自由,衔接自然,简洁流畅。
民族化 抒情性 程式性 多重空间
中国民族歌剧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一批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如《白毛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党的女儿》等,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然而,在近些年的歌剧创作中,鲜有值得称道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歌剧。江西省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歌剧《回家》让人眼前一亮,并且可喜的是,作为一部典型的原创民族歌剧,不失其现代性表达的同时,在民族化方面作出了成功探索。
民族歌剧《回家》表现的是台湾老兵罗旺篼38年锥心泣血的漫漫归家之路,此中饱含着深切的思乡之情。在情的表达方面,也就是在展现情节和人物的抒情性时,歌剧有其自身的艺术方法、艺术韵味和艺术风格,与戏曲对情的表达截然不同。而《回家》在塑造人物的情感时,并没有一味按照西方歌剧的手段,较多地运用了戏曲抒情性的表达方式,更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心理。这在第二幕《想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是罗旺篼思念家乡的一段唱,通过残月、乡曲、海风和长空雁的现实情境想起家乡的南山竹、青石路、山中花和门前田畈等,以曾经接触的熟悉之物进而引出思乡之切,并把这种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这便是充分运用了状物抒情这一重要的戏曲抒情手法,以与之相关的事物来抒发人物的思想感情。这比西方歌剧单纯地用歌唱技巧和咏叹调的渲染来刻画情感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并且有极强的带入感,同时也遵循中国传统美学原则。
借景抒情也是戏曲抒情性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主要通过人物在特定情境中对特定景物的感受以抒发其思想感情。《想家》一幕中,官兵们在中秋月圆之夜开阵地联欢会,规定要唱家乡歌,跳家乡舞。剧中选取山东胶州大秧歌、安徽凤阳花鼓和江西赣南民歌《斑鸠调》,在符合叙事情节的情况下,既活跃了舞台气氛,提高了观赏性,又充满了地域特色。更为重要的是,此景此情,激发了官兵们想家的强烈心理,把想家之情向前推进了一个层次,也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情感体验,随着剧中官兵们的思绪而波澜起伏,身处其中。官兵们的想家场面,也是为后面从暗地里描写长官想家做铺垫。长官训斥官兵不准唱家乡歌和跳家乡舞时,却是用自己的家乡方言说出来的,可以看出长官也是不由自主地受了想家场面的感染。他不许官兵们乱唱乱跳、胡思乱想,而自己凌晨3点却难以入眠,“意难平神不定心绪不宁”,从侧面反映出长官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凡之人,也是想念家乡的,只是不得不克制着思乡的冲动。他对官兵们越是大吼大喊,越证明他内心想家的巨大压抑。等到泅海被逮的罗旺篼唱起他教的“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这首歌时,他的一声大吼“别唱了”,把其想家的心理推向极致,从而也把全剧所展现的想家之情推向高潮。这就是借景抒情的手法所带来的强烈效果和表达张力。这种手段的运用在本剧中恰如其分,也为其他歌剧民族化的探索提供了借鉴和参照。
歌剧《回家》注重抒情性的同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除了唱以外,更加重视表演,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歌剧“重唱不重演”的问题。本剧时间跨度长达38年,剧中人物年龄跨度也相应较大,且都由一人饰演,这就对演员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显然只通过声腔的装饰和化装的改变是不太能达到塑造人物的理想效果的,且这些也不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该剧的主创们深谙戏曲“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的特征,从传统戏曲中汲取营养,在表现人物与刻画心理时,以肢体语言和眼神动作等,来达到塑造形象的目的。
主人公罗旺篼在本剧中的年龄跨度最大,展现的是其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的心灵轨迹。饰演者杜欢塑造的青年罗旺篼,在拜堂成亲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充满朝气和活力,但面对众乡亲时又表现出略羞的状态,这些都是恰当地通过眼神和面部表情的转换来实现的。同样是青年时期的罗旺篼,偷逃被抓被说成叛徒时,头微微一偏,两手一摊,面部表情略作委屈状,把一副无辜的样子刻画得生动形象。当被告知敌前逃跑当判极刑时,表现得又是那样的从容镇定,虽死无怨。而当听到要把失职的统统关押时,他一把挣脱押解者,疾步跑到首长面前,从首长口袋中掏出手枪作自毙状,呈现出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方刚血气。人到中年,曾经的首长介绍对象时,面对对方的理解偏差,他表现得又是那样的老成持重,见怪不怪,把一个中年人的心态呈现得惟妙惟肖。在表现老年罗旺篼时,他又化用戏曲老生行当苍劲的步态、缓慢的手势等身段动作进行刻画,把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年形象展露无遗。作为一名三十多岁的青年演员,杜欢能把年龄跨度如此之大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分寸拿捏得恰当妥贴而又不显得矫揉造作,准确地把人物一生的心路历程展现得富有层次感,实在难能可贵。
母亲这一角色由中年跨到老年,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表演手段来塑造的。饰演者邬成香本来就是采茶戏演员出身,对戏曲表演手段的运用得心应手。第三幕《安家》中,当听到捎来的消息说儿子已不在人世时,她先是一惊,然后双脚后退,紧接着小碎步急忙向前,双手伸颤,表演动作极具戏曲的程式性,鲜明地刻画出此时的心理状态。第五幕《回家》中,母亲的人物身份已变为老年,饰演者邬成香迈着经过化用的戏曲老旦的步伐上场,演得得体自然。当见到儿子的一刹那,又是急速的碎步向前,但这时的碎步动作已与第三幕中的截然不同,对人物年龄和情境规定性的变化,把握得贴切妥当。
当然,该剧在人物表演上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比如,罗旺篼经过三十八年艰难等待见到母亲的那一刻,跪着爬向母亲,着实感人,但如果化用戏曲程式中生行的大蹉步动作,由慢到快有节奏地一步步跪向母亲,也许更具感染力和画面感。另外,在表演方面进行民族化探索,并不仅仅是指人物的身段动作要借鉴戏曲表演程式,而在表现人物心理、铺陈事件和推动剧情发展时,也应该设置一些歌舞化的戏曲动作有机地融入其中。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的,描写的景、摹状的物和写人的情是浑然一体的。比如,罗旺篼迫不及待地到达生养他的故乡时,他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只是通过歌唱来表达此刻的情感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设计一段与此时气氛和情状相符合的舞蹈,以载歌载舞的形式表现出来,情感的刻画才能达到极致。这也正如《毛诗序》中所说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现在看来,该剧对歌舞化的把握和在肢体语言的表现方面还比较欠缺。
歌剧《回家》在民族化方面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舞台时空多重空间的处理。对舞台时空的特殊处理,是中国戏曲舞台的重要特征之一。本剧从戏曲舞台的时空处理方式中借鉴经验,来表现特定的叙事场景,有利于舞台呈现所需要的空间转换。第三幕《安家》中,罗旺篼和文竹各自重新成家时,二人在同一舞台上隔空对话的呈现就是对舞台时空多重空间的特殊处理。同一舞台分成两个表演区,在星光闪烁的夜空中,罗旺篼先出场,表达了对文竹二十年的思念之情和自己的无奈。然后罗旺篼的身影隐去,文竹在舞台另一侧出现,诉说了二十年的孤寂之情和对旺篼的念想。紧接着二人同时靠近舞台中央,以歌唱的方式表达各自重新成家的愿望。与此同时,二人背面的舞台后侧分别设置两对新郎新娘做出表达此时此刻心理情感的舞蹈动作。最后,二人转身同向舞台后侧并慢慢隐去。这种多重空间的处理,使得舞台时空高度自由,把二人在不同地点的同一时刻的心理直观形象地展示出来,心灵的交流和对话具象化,可视可感。这样的时空处理方法,该剧可以再多些,特别是罗旺篼几十年未和母亲相见,如果采用多重空间的对话,也许母子之情表达得更为深刻,更具感染力,也更能调动观众的情绪。
本剧对舞台时空的处理,还表现为对场与场之间的衔接和地点的转换。第五幕《回家》中,罗旺篼和妻子激动得赶往老家竹山村,家乡的美景尽在眼前,当他对妻子说到“走,回家”时,舞台天幕前面落下一颗大树的布景,而其他景物仍然保持不变,这样地点和场景却得到了快速转换,灵活流畅,利于后面情节的顺利展开。母子在村头的大树下相见后,让人拿上腌竹笋的一霎,天幕借助LED屏的变幻效果,立即变为祠堂的景致,大树这一布景升起,便交待了这是到了自己家的场景。这种便捷自然的处理方式,使得剧情的推进更加顺畅,层层相叠,环环相扣。
歌剧《回家》还值得一提的是,对LED屏的恰当、有效、合理的利用。LED屏是近几年新兴的舞台布景的一种装置,越来越多地运用到舞台剧的演出中。但很多情况下,与舞台上的景物设置和情节的发展等衔接得不太自然,甚至游离,特别是在戏曲舞台上,这种科技手段在虚实的处理上很不尽如人意。而本剧却较好地解决了屏幕之景和舞台上的布景的衔接,与剧情的吻合,做到了写景、叙事和抒情的统一。比如,开场的序幕,LED屏上闪现出“1939”四个数字,接着数字幻化出一副恬静幽美的田园风光,这时突然传来枪响,伴随着枪声,静穆的田园中幻化出火光满天。紧接着出现南昌会战的场景,此时的舞台上也出现官兵荷枪血战的场面,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其他几幕的连接中,几乎也是如此。本剧对LED屏的成功运用,为其他舞台剧目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也应当引起现今很多不切实际地滥用者的深刻反思。
[本文为2015年度江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原创民族歌剧《回家》的综合分析与研究”(项目编号:YG2015257)的阶段性成果。]
刘威利 湖北省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 范干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