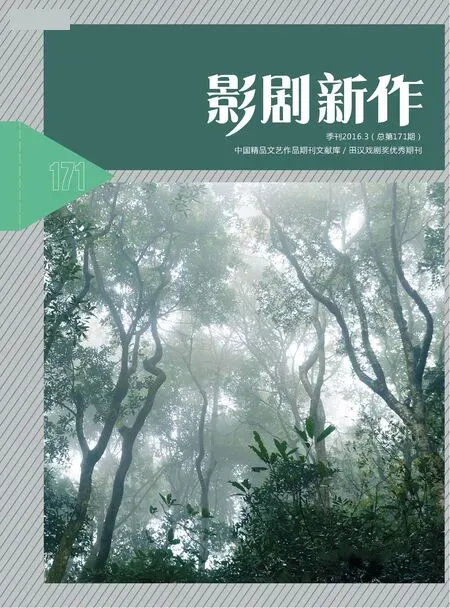严智龙绘画艺术访谈录
王洪伟
严智龙绘画艺术访谈录
王洪伟
严智龙,艺术家,男,1969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大型艺术学术展览和研究活动,作品《红与黑》系列、音乐系列、《床》系列、《春秋鸟》等意象系列作品获得美术界学术展览的多项奖励,得到社会广泛好评,2013年被中国油画学会评为向全国推介的“十大新青年油画艺术家代表”,作品被海内外博物馆、政府部门、美术机构大量收藏。完成专业学术著作六部,专业文章二十余篇,作品入选由中国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此访谈探讨了严智龙绘画中的色彩、图像背后的文化根基以及它们与艺术家个体经验、潜意识之间的关联,呈现了艺术家对现当代艺术脉络的审视、对当代艺术本质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当代艺术创作的思考。
王洪伟(以下简称王):你的色彩和图像都深深挖掘了传统文化的根基,让观众在阅读时停泊在精神的故园,很多观众在你的作品前迟迟不愿离去,是因为画面中曾经熟悉的片断吸引着他们,一种潜在的诉求促使他们去继续寻找民族内在的基因和脉搏,这是你作品整体氛围的关键因素,不难看出你在艺术与文化之间积累、寻找和思考的一个坚实过程,你怎么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严智龙(以下简称严):有没有支撑艺术的文化素养很重要,文化素养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性,四年大学的学习会使人明白人文的精神性决定了人的品格,不会走偏。我也是这样成长起来,跟着老师慢慢地将自己带到人文的思考中去。什么是人文呢?江湖文化是不是人文?文化有很多种形态,层次有高有低,把精神性放第一位的文化层次绝对不低,一定是高尚的。人文最初、最简单、最实在的不是唱赞歌,而是悲天悯人,是忧虑、忧患,看这个社会对人会担心,看到生命的状态感到莫名地忧患,这是人文最基础的情感基础,是人文里最起码的一种精神现象,连这个情怀都没有,人文就不存在。有了这个,才给它分类,分出层次来。人文的最原本的情感其实是宗教的,是善。真善美,真是真诚、真切,真理是前提,应该说哲学最初的思考是宗教的来源,我们所有的学科都是建立在哲学大的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宗教之前是巫术,是因为有了宗教的逻辑感以后才形成了宗教。但宗教的本质核心是使人性趋善,哲学来自于对世界的最根本的看法。真善美,美是最后,美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与艺术的关联性,这几个学科里面共同拥有的一种最原始的概念还是美好、圆满、求全,慢慢延伸到现在,宗教慢慢势弱了,艺术替代了宗教,完成了人性中对社会意识层面的再创造,这个再创造是用图像和其他方式揭示宗教的能量,这时艺术家个体就是宗教的,每个艺术家都是真理性的那个点。人文的真理性和科学的真理性是不一样的,科学的真理性是确定的、必然的、数据化的,人文的真理性是可能性、不确定的。当一个艺术家创造了一个图像系统的时候,就构成了一个图像文化,艺术家的真理性自然隐藏其中,不求它的稳定性、必然性和标准性,求的是它存在的合理性,任何一种艺术的存在都是为人文提供一个可能的范本。
王:艺术上升到文化要靠社会平台来完成它的转换,它必须通过文字、展览、传媒、影像等各种交流手段完成一个逐渐被社会接受并变成社会可以存在的一种现象的过程,这时艺术家的艺术就不再是他所专有了,它成了社会公共的一部分。
严:是的,任何单件作品是不构成价值的,需要一系列的作品形成气场,形成另外一个世界,观众看了以后才会开始发生变化。看展览一定要看个人展,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艺术的整体认识,艺术现象才会出来,比如“三驾马车”展,我们三个人每个人艺术系统的建设都是相对独立和明确的。成型是用自我的方式和语汇构成一个自我绘画的语境;成熟是不仅要按照这个感觉画出一张画来,而且可以画出2张、3张、4张、5张…20张、30张,一画就是这种感觉,在系统里完成我的情趣转移。艺术的成型和成熟都是艺术家自己可以完成的,但是成名、成家是艺术家个人完成不了的,艺术交由社会才能转换成文化。一个人成家了就能影响别人,别人又影响别人,到了一定时候,文化现象形成,就有更多人受到影响,因为你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创造力了。成家必须经过前面的成型和成熟,而成型和成熟是没有社会价值的。
王:真善美贯穿了宗教、哲学和艺术的发展关系和发展次序,你的解读给我呈现了新的视角。你读艺术哲学博士,进入艺术哲学研究思考阶段,这与我所熟知的与美术专业更接近的美术史、美术理论研究方向不同,而上述你的观点也正回答了你选择此专业的目的。
严:为什么我要去读哲学博士?不是因为我需要学历本身,所有的艺术家到了一定时候就希望用自己哲学的逻辑思维来看到个人艺术与文化和社会碰撞的时候所带来存在的意义,因为所有的艺术不上升到社会层面建构文化,它的艺术的存在就要受到质疑。
王:色调是图像绘画语境里最重要的面貌,你对红色极致的运用,首先奠定了你画面与众不同的意境。油画中对红色的如此运用很少见,你应该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探索和思考。朱其先生从色彩运用的特征把它归结为“野兽派的风格化的色调”,我从源头上看,认为这红色是植根于中国的传统中,力求在中国人心目中找到共识的语境,寻求精神上的归属感。你选择红色是不是有这样的归因?
严:观者潜在的文化情节被触动,这是作品达到的一个深层次的效果,循着传统的脉络去寻找色彩的归因是我的一个思考。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沉淀为一种经典的色彩不是偶然的,中国五千年文明有三千年基本上是王道论,颜色的使用在各阶层中是有界线的,如正黄色(色彩里叫棕黄)是皇帝和皇室的专属色,民间不允许用,一般用偏冷的柠檬黄,比如送葬的冥纸冥钱等;蓝、绿、青是老百姓通常用的颜色,属于草根颜色;而紫色,古代人是比较忌讳的,一般是红楼里用,平常人不太用;只有红色突破了一定的界线,最开始是王爷用的颜色,权贵和富商都能用,老百姓很向往,因为皇家不禁令红色的使用,久而久之,民间跟着王爷走,红色逐渐成为很常用的颜色,也是很有分量的色彩,而蓝色和白色在中国人的色彩里,没有分量,是飘的。红和黑放一起是典型的达官贵人的颜色,马王堆的辛追夫人墓中的棺椁就是这两个颜色,里面是红,外面是黑。
王:这两个颜色是中国古代大漆的颜色,古代的江西、两广和湖南湖北这一带种了大量的大漆树,红漆是大漆里面最重要的颜色,所以使用量比较大,绿色、蓝色等颜色是从矿物里提炼出来的,提炼比较方便,所以人们不觉得稀罕。大漆的颜色是要付出很多的劳动力才能得到的,老百姓用不起,富人和官商这两个阶层用量比较大,久而久之,才显得非常富贵。
严:对,而且这两种颜色有很强的稳定性,老百姓的蓝衣时间久了就风化掉了,但大漆颜色历经两千多年竟然没有太大影响,还能保持原有的色泽,这两种颜色在这个民族世世代代传承,可能跟它色彩的稳定性有关,而且当某个空间颜色比较杂乱时,把这两个颜色一放,立马就稳定了、平衡了,因此红和黑成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替代色彩是有道理的,就像你去马王堆里看到这两种颜色就会肃然起敬。
王:你画面中的鸟有什么象征性和隐喻性?你的鸟很隐晦,纤细、傲立的颈项,界线模糊的躯体,像是图腾散发出神秘感,它也有潜在的传统文脉中的影子,让人很想去追溯它的原型,你通过它在诉说什么,表达什么精神?
严:湖北曾侯乙墓中鸟的图形都是挺立的、向上的、纤弱的、傲视的和内自坚定的一种状态,我深受其感染,因为它对应了我自身的审美情节和生命状态,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图像系列里,我被它反照了,然后又把它重新再现。我画的鸟也是挺立的,从来不弯曲,不感觉委屈,我从来不画正面的鸟,你去看埃及的壁画造像全部是这样,正面身,侧面脸,它容易产生一种思考、审视和自傲的态势。贾科梅蒂是瑞士的一个当代艺术家,他雕塑艺术的造型也和东方人以弱示强的状态很像,他认为雕塑不需要像罗丹的雕塑那样大的体积,100米以外人的大小看起来更真实,所以他塑造的人都很小而且把人拉长了。贾科梅蒂在都市人的造型上有个人特点,他的造型也不弯曲,和我国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的那些鸟也很像,在人性的特质上有共同感,我喜欢这样的造型感,我的造型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他的造型文化意识的影响。但是他的是雕塑,而我是用线条勾勒出雕塑的那种感觉,在平面中呈现。
王:你作品中反复出现鸟、床和乐手的形象,并把鸟和床组合、乐手和鸟组合,黄铭先生从创作方法的角度,以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语言学的解构进行类比,认为你是把无关联的碎片事物经过重组再将画面事物构成平面化和符号化,从而形成一个完全陌生、悖论的艺术语境。我认为你借助床、鸟和乐手形象的精神意象和象征性意涵来表达你的情怀、个体经验和潜意识,床、鸟等的形象看似无关联,其实为表达你内在的需要,它们是关联的,如戏剧情节中的一个角色,它们被赋予了特定的功能和意义,在讲述你内在的境遇和诉求。
严:在床上,我们休憩、思考、孕育,与床相关的活动承载了人类的基础,床即是生活、现实和当下,床即是舞台,与鸟的理想性、象征性、隐喻性,共处于一个画面,对受众来说,会有超现实的精神意味和新观念艺术的引述。
王:你在湖北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就开始探索表现主义,经过毕业后的四年转承,在天津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学习期间开始了纯粹的现代主义形式语言研究,尝试理性绘画在当代主义支配下的整合,从具象绘画到表现主义,到现代主义语言,再到当代主义的观念,好像你在不长的时间里就经历了美术史里几个重要的阶段,伴随这一路走来的过程,你深层的思考是什么?
严:当尼采说:“上帝死亡了”,也就是说现代艺术形式美的探索在人类的文化图像研究领域里走到尽头了,特别是现代绘画走到至上主义时代,现代艺术就告一段落了。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抛弃了所有的具体形式,抽象得彻底什么也没有了,终结了形式美,也终结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紧接着开始了,西方的后现代艺术其实是从架上绘画转向了空间、材料、行为、多媒体等各种载体,将艺术的观念得以承载。架上绘画得不到延伸的方式在后现代艺术里全面展开,使得艺术变得无所不能,这就是西方人对现代艺术之后的,也就是后现代艺术的一个界定。这个时候艺术承担了哲学的思考,变得以观念主导。当代艺术都是在个体独立的活动范畴里完成了创作的思维线索的构建,而不是像原来的现代艺术是由心理和情感主导的,当代艺术更准确地说就是黑格尔哲学所说的“理念”。古典艺术是视觉性的,最多的是看像不像,描摹,它其实是一种叙事,有文学性,古典主义前期的宗教艺术就是典型的叙事;现代主义不再叙了,而是陈述,把自己的情感交代出来给别人,而不是交代那个事情的过程;而当代艺术是阐述,用思想、思辩、逻辑交代自己的看法而不是情感。现代艺术的语境是用形式绘画的方式找到对应的情感,当各种表现方式、各种形式语言都被现代艺术家玩够了,已经不能够再承受人类在情感上对应地开发时,现代主义终结了,所以斯塔尔死了,罗斯科也自杀了。
王:按这样的理解,中国当代艺术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重新让西方的绘画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里复活,把西方后现代艺术家的创作逻辑方法重新纳入架上绘画,真正实现了黑格尔所说的“绘画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尚辉先生认为在你的作品中看到了当代画坛上鲜见的一种自我意识和独特经验,读到了自我放逐、个性独立和对于世界的认知与把握。我认为这种解读很具体也很准确,而这种“自我意识、独特经验以及对世界的认知和把握”与你所说的“当代艺术的思想、思辨和逻辑”是不是一致的?
严:是的,思维是理性的,这个理性直接和你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人性、人权这一切相关,这些都在艺术家个人认识的范畴里面,形成他独特的思想,然后将思想的逻辑纳入到创作的线索里去,但手法可以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是古典主义的。在现代主义和古典主义艺术中,艺术观念都不是主导,这就是当代艺术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印象派以及现实主义不同的地方。当代艺术应该是个体思维决定一切,个体的思想主导一切,个体的真正的意识活动承载一切,我天天都在推进当下创作思维的价值观,我的大学老师如魏光庆、石冲、尚扬等,研究生导师邓国源,他们也一直都在遵循当代艺术的创作规律进行当代艺术创造。
王:你如何看待艺术的本质?
严:艺术等于绝对创造,不是创造的绝对不是艺术;艺术家的生命决定了艺术的唯一性,他画的一张画绝对没有第二个人画得出来,自己也没办法重复,在美术史上可以存留它的原创性;还有一个就是在文化领域里,至高无上的精神性主宰着真正的艺术,如快餐文化跟艺术没关系,艺术是由精神性决定它的价值高度,因此绝对创造、唯一性和精神性决定了艺术的真理性,从这三点就可以看到哪些是艺术,哪些不是艺术,你似曾相识的那些形式并不一定就是艺术,它虽然可能没有模拟谁的艺术形式,但是是由对某些艺术形式的记忆主宰的。
唯一性不是从基础层面里面找到自己与众不同的那么一点格调、那么一点形式,从而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术主义心态,就像现代主义旨在通过形式审美找到差异性,找不到呢,就像罗斯科按照自己的语境做,最后无法创造了就选择了自杀。与众不同的在哪里?在生命的特质。你与张三、李四不同,与古人、后人不同,你一定要找到自己哪怕那点心跳,你找到了,看清了,认准了,把它刻录到你的笔上去,然后通过这个形式找到与自己真正对应的生命价值,你就出来了。所以,我从来不让我的学生去临摹,因为把大量的时间浪费掉了,进得越深跳出来就越难。
王洪伟 江西省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 谢菁菁
——评《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