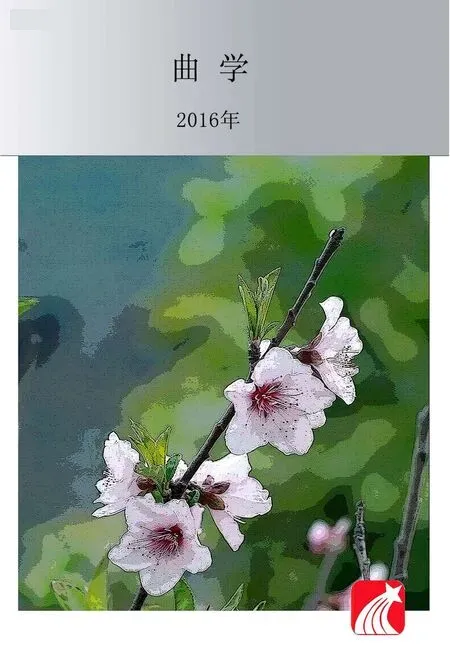张宗祥的“戏剧观”及其践行
徐宏图
《曲学》第四卷
张宗祥的“戏剧观”及其践行
徐宏图
王国维与吴梅,无疑是我国近代最有成就的戏曲理论家,只因受到时代的限制,他们的理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王国维的同乡、著名学者、原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在他的《中国戏曲琐谈》一书中曾诚恳地指出:
朋友中有两个人可惜现在均已亡故。一个是王静安国维,他是专从书本上研考古代戏剧的,有《宋元戏曲考》、《曲录》等书。一个是吴癯庵梅,他是专从声律曲谱上研究音韵唱法的,有《中国戏曲概论》、《曲学通论》等书。静安博而不切实际,有一点书生的老脾气,癯庵倒是一个音律专家。但是他们俩都用心在历代曲本,从不肯回过头来着眼到徽、汉、京等种种戏剧。*张宗祥《张宗祥文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05页。
在他看来,王、吴二先生研究戏曲,均未免脱离现实,只停留在历代曲本上,没有联系到当代剧种。同时他又指出:“虽然评论京戏的,坊间也出了若干著作,但是又不肯连系到旧时曲本上去,因此,我就不怕外行,大胆来写了此册。”他对王国维在《戏曲考原》中指出的“歌舞演故事”戏曲定义的这个著名论断作了具体化,更加明确地指出:“戏是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 有整套的故事剧本;二、 有具备扮故事的角色;三、 有后场调节帮助的乐器。以上三个条件不完备,这一种戏就算不得成立。”*同上,第407页。相对而言,由于他特别强调了戏剧的演出性,因而他的这种戏剧观又比王国维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对中国戏曲理论的巨大贡献。更为难得的还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戏曲实践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 精选曲本、红字批注
我国古代剧本,向有“曲海词山”之称,其中的稿本更是汗牛充栋,想要为曲界与普通读者提供一部合适的曲本,谈何容易!而张先生却做到了,且做得很好。
首先,选目独到。他在通读数以万计曲本的基础上,毅然选定姚燮《今乐府选》。据清冯辰元《复庄今乐府选总目序》载,姚氏当年为编此书,选录词曲四百余种,“晨夕手校”,“眉批手注,日给不皇”,被时人“叹为观止”,唯“书系手抄,未付梨枣,故世罕有见之者”。不久姚氏故世,书稿流落民间,几经周折,至1954夏,才由浙江图书馆从一个叫夏子良的人那里购得,可见来之不易。*毛春翔编《浙江图书馆乙种善本登记簿》,藏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全书共选金、元、明、清的诸宫调、杂剧、传奇、散曲等429种,其中包括衢歌5种,弦索1种,元杂剧91种,明杂剧25种,清杂剧40种,南戏2种,明传奇71种,清传奇174种,元散曲2种,明散曲8种,清散曲8种,耍词2种。每剧的行间、眉端、出末,偶有校语、评语,均为姚燮亲笔,对于研究中国戏曲史及阅读古代剧曲,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正如赵万里在《今乐考证·跋》所说:“《今乐府选》一共有五百卷之多,可算是元明以来规模最大的剧曲大选集,远非《群音类选》、《歌林拾翠》、《缀白裘》之类可比。举凡古今著名的剧曲,无不收入。姚氏在乾嘉以降狭义的经史考据学的气氛里,居然开发了一个老师宿所不屑去且不能去的文学资料的园地,真叫人钦佩不已。”*赵万里《今乐考证·跋》,北京大学民国二十五年影印马廉藏姚燮稿本。郑振铎在《姚梅伯的〈今乐府选〉》中更说:“像他那样的有网罗古今一切戏曲于一书的豪气的人,恐怕自古到今日还不曾有过第二个人!”*郑振铎《姚梅伯的〈今乐府选〉》,《中国文学研究》,作家出版社,1963年,第630页。张先生首选此书,可谓是慧眼识真金。
其次,编目精细,为读者便捷地查阅本书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原书校录整齐有序,有条不紊,例如用墨笔抄成,楷体,用姚氏自制的蓝格稿纸,单鱼尾,版心下有“大梅山馆集”五字;左右两边,除第一册原目录为半页10行外,其余正文均半页11行;全书大部分子目都是经姚氏亲自披校,每校一种戏,均在第一行右框外署上上校勘日期,如“辛亥五月初六日午刻校,时雨初霁,日光射棂”,年款后钤有“复庄”(阳文)或“复庄校读”(阴文)印。但由于原目只有子目书名与作者,入选的各种戏曲均不注明出数与细目,查阅起来十分不便,故张先生于购得此书之后,不顾七十三岁高龄,立即做出重新编目的决定,并取名《复庄今乐府选详目》,署“大梅山馆原选,张宗祥编”。编毕之后,末记:“一九五四年夏,购得姚梅伯选钞乐府一百一十本,苦无细目,因为录此。原书凡百九十二册,今逸八十二册。不知是否还在人间,真使人怅怅。海宁张宗祥记,时年七十三。”案: 《复庄今乐府选》原为192册,现存168册,分藏在浙江图书馆(110册)、宁波天一阁(56册)、国家图书馆(2册)三处,从未刊行。张先生编的《详目》除注明子目的名称、作者及所选折子的序号和名称外,还对每册最后一种戏曲细目的末尾用小字注明“以上第某某册”或“以上第某某册至第某某凡某某册逸”,对予逸的子目,则有朱笔在其上方打一直角,以供辨认。所用纸张用浙江图书馆自制的蓝格稿纸,半页10行,单鱼尾,版心下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七字。此外,还对入藏浙图的110册剧目文本,重新经过细致校勘,以补原著之不逮。凡经重校者,均用朱笔出校,每校一种戏,均在该戏末尾署上年款如“甲午五月廿五日,灯下,冷”。冷,即冷僧,张宗祥的号。总之,经过张先生重勘并配以详目的《复庄今乐府选》,极为精善,查阅非常方便,甚为学界称赏,徐永明已撰有《姚燮与今乐府选》一文于《文学遗产》2006年第一期予以详解,此不赘。
再次,批校准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复庄今乐府选》第五册关汉卿《窦娥冤》右侧原批:“辛亥七月十四日午刻挥汗校。”张宗祥红字批:“甲午五月初十日校,冷僧。此本与现行本完全不同,现行药死者为张驴儿之母,窦娥因下雪不斩。”案: 此剧为关汉卿第一名作,原本药死者为张驴儿之父,而现行本如京剧、秦腔、徽剧等均张驴儿之母,因六月行刑,忽天降大雪,巡按得知,平反冤狱,因而剧名往往改为《六月雪》,张先生所批甚是。又如第七册白仁甫《梧桐雨》右侧原批:“第二折[普天乐]云‘更甚那浐水西飞雁,一声声送上雕鞍,伤心故园,西风渭水,落日长安。’及第三折[殿前欢]一阕,俚能力重千钧,为《长生殿》所不及。”张宗祥红字批:“此即《长生殿》中《埋玉》、《迎哭》诸出情节,而词更沉着苍涼。”对照《长生殿》《埋玉》[缕缕金]“(生旦抱哭介,旦)魂飞颤,泪交加。堂堂天子贵,不及莫愁家。(生)难道把,恩与义,霎时抛下!(旦跪介)算将来无计解军哗,残生愿甘罢,残生愿甘罢!”及《哭像》[五煞](生捧酒哭科)“酒再陈,恨未央,天昏地暗人痴望。今朝庙宇留西蜀,何日山陵改北邙!寡人呵,与你同穴葬,做一株冢边连理,化一对墓顶鸳鸯”云云,确如张先生所说,比原作沉着苍涼得多。其例尚多,余不备举。
二、 关注剧种,撰写专著
中国戏曲从南戏滥觞至今近千年历史,大小剧种有300多个。要深入研究戏曲,就要关注这些大大小小的地方戏。为此,张先生撰写了一部专著,取名《中国戏曲琐谈》,着重谈戏曲的声腔与剧种。他分两步研究,先谈全国各省地方戏,再谈浙江各种地方戏。
关于全国地方戏,又分为“总说”与“分说”两步进行。总说时,用了一个十分形象而又风趣的比喻,将全国所有的剧种比喻为“菜蔬”,分“专菜”与“拼盘”两种。他说:
地方戏又可比方成菜蔬,一种是专菜,全鱼、全鸭,并无别种杂味,如粤剧之类,那就因为言语、风俗截然不同的缘故,非特制专造不可;一种是拼盘,盘内白鸡、火腿、皮蛋各色俱备,却没有放下锅去煮过,仍旧保持着各菜各味,那就是川戏、桂戏之类。原来四川、桂林虽然多有地方戏,苦于并不丰富,不够支配,不得不借光到邻舍人家去。或者因历史上的关系,他省的人民大量迁居其间,演戏的艺人,自然不能例外相随而去,因之就将甲地或乙地的地方戏随带了过去。*《张宗祥文集》第二册,第421页。
这里所谓“专菜”与“拼盘”,其实含有单声腔与多声腔的意思。此外还包含方言、土音等问题。所以他举例说:
记得今年婺剧在杭州演出时,卖座不及越剧,更远不如在金华时的热闹。有一金华友人语余:“且问婺、越两种戏剧的优劣?”我却回答了他两句话:“谁叫在杭州工作的人绍兴人多于金华人数倍呢?谁叫杭州人个个能懂得绍兴话而懂得金华话的却很少呢!”这就是地方戏迁地勿良的一个明证。有人提出了现在的越剧何以亦几乎同于京戏之有全国性,迁地勿良的证据恐怕不确。这一问题,我当在下文谈越剧的时候来回答,现在且分说各省重要地方戏的情况。*同上,第422页。
分说部分谈了高腔、徽调、汉戏、川戏、桂戏、粤戏、昆腔、京腔等剧种。因篇幅所限,恕不赘述。
关于浙江各种地方戏,首先谈“婺剧”,称它是“产生于金华”的一种多声腔剧种,其中高腔从江西流入,徽调从安徽流入,它们到了金华,一一被吸收,“却丝毫没有改造和陶铸过”,因此,虽然名为婺剧,唱昆腔依然是昆剧,唱高腔依然是高腔戏,唱徽调依然是徽戏,所不同的只是“唱音、道白掺入了金华土音而已”,所以婺剧很明显的是一只“拼盘”。其次谈“绍剧”,即“绍兴大班”,他将它产生的年代确定为“明初”,理由有二: 一是绍剧向来被称为“惰民”的专业,而“惰民”来源有断为宋将焦光赞的部曲反复背叛不定,因而编为惰民的;有认为即元朝的怯怜户,他认这两说在宋人、元人各种纪事中一无记载,实出后人推想,“惰民”真正出现应在明初,其时专兴大狱,如李善长、胡惟庸等狱,动辄诛戮数千、编管数万,将他们编为“丐户”,进而即被称为“惰民”,这些惰民们所演的戏即“绍兴大班”,即现在的绍剧。二是绍剧所唱的腔调类于秦腔、高腔,没有受徽腔、昆腔的影响,更可证明它在徽调、昆腔之前的明初前后产生。再次谈“越剧”,称其本名“小歌班”,又名“秧歌班”,就这二个名称来看,就可以清楚它是完全产生在农村中,极接近“山歌”、“小曲”的一种原始戏剧,“成班只须少数艺人,音乐只须小鼓、绰板,剧本只须街头叫卖用泥字来印成的《梁山伯》、《卖婆记》之类的唱本”。在详谈了它的发展史之后指出:“浙江地方戏中最有前途的是越剧。”六十年来的历史证实张先生的预言是符合实际的。接着谈睦剧、甬剧、湖剧、温州乱弹等,均不泛真知灼见。
三、 说文解戏,栽培昆伶
20世纪30年代初,张先生寓居上海。刚从苏州“昆剧传习所”出科转入“新乐府”昆班不久的周传瑛、姚传芗、张传芳、刘传蘅、华传浩等年少学员随班来到上海大世界游乐场演出,因脱颖而出,崭露头角,颇受张先生的关注,经常携带曲本去看他们演出,从发音、咬字到曲意,逐句校对,发现舛误即作出标记,待曲终人散之后为他们一一纠正。还经常特邀他们找一家小酒馆,围坐一桌,把盅“喝一口”,边饮边为他们说戏,从作者、剧情到曲文,说得既透彻又生动,令这几个小演员惊喜不已。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一片苦心在酒壶。张先生深知昆剧是文人之作,曲文秉承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学传统,唱词华丽,念白儒雅,表演细腻,舞蹈飘逸,鼎盛之后,难免附庸风雅,刻意追求,日益走向典雅、繁难的境地,对于这些初识文化、刚刚出科的十七八岁的学员来说,要透彻理解曲意谈何容易!而不通曲意则又如何表达剧情与表演水平?这岂不直接关系到好不容易才起死回生的昆剧能否继续生存的大问题?欲解此难题,务必先过文化关。一次,张先生又请小演员们小酌,兴来之时,推心置腹地对他们说,昆曲非其他剧种可比,文本深奥,肚皮里没有一点墨水,可勿来事咯。接着又咪了一口酒,笑着说:“我来教,你们看可好?”大伙拍手称好,说:“求之不得呢!”就这样,这爿小酒店就成了这几个传字辈小艺人的拜师之地,而位于上海大通路培德里的张先生寓所客厅则成了他们的课堂。为了省钱,他们从所住的马浪路尚贤坊宿舍出发,需步行四十多分钟才能赶到张先生家。每天上午上两节课,每节一小时,中午就在先生家用餐,免费供应,下午需赶回剧场演出。张先生为他们量体裁衣,挑选古代启蒙读物《幼学琼林》为课本,深入浅出地讲解成语典故、名人传记、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以及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释道鬼神等诸多故事及古今传诵的警句、格言等。还请了一位粤籍的昆剧爱好者许月旦做助教,每次上课,一般均先由许讲解,最后再由自己解惑指点。历时数月,直至把《幼学琼林》教毕,迅速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养。教学之余,张先生还为他们每个人取了学名,今知周传瑛叫“玉浓”,姚传芗叫“馨萼”,张传芳叫“友兰”。这些美好而寓意深刻的学名,寄托着张先生对他们无限美好的愿望与期待!
张先生借酒说戏,其壶底苦心不仅在于传授文化,还包括慷慨解囊,无偿培育艺术人才。1929年冬,曾出资以教一出戏付百元的高额酬金选派朱传茗、姚传芗、张传芳等向原全福班名旦丁兰荪学演《思凡》、《琴挑》、《絮阁》、《游园》、《惊梦》及《西弦秋·送客》等昆剧折子戏,得益良多,演艺日臻。其中朱传茗尤为出名,一时遂使剧界有“北梅(兰芳)南朱(传茗)”之称。1931年秋,“新乐府”昆班发生变故,迫于原经营者抽走行头,带走两名主角,不得不宣布解散。周传瑛等传字辈小兄弟们商议筹建“共和班”,正于为无线办行头之际,张宗祥闻讯,随即捐资一笔。不久,在昆曲史上享有盛名的“仙霓社”终于诞生,直至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才散班。
张先生对“传”字辈艺人的苦心栽培,可谓是终生不改。1953年,国风苏昆剧团招收了一批“世”字辈学员,根据昆剧文词典雅的特珠性,剧团要求演员在学识方面最终达到大学文科水准。为此,特聘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担任文化教师,时年71岁高龄的张先生,欣然受命。1954年是《长生殿》作者洪昇逝世25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世界文化名人,在张宗祥的策划下,于是年7月5日,浙江图书馆邀请省、市文艺界人士40余人,在文澜阁举行集会纪念。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副主席洪深出席了纪念会。会议由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主持并致词。由浙江国风昆苏剧团周传瑛、张娴夫妇等演唱洪昇《长生殿》中《絮阁》、《闻铃》、《惊变》三折。此前,为了开好纪念会,浙图与国风昆苏剧团均作了充分的准备。张宗祥亲自找了周传瑛商量,把演出任务交给了周传瑛,并与周传瑛一起选择演出曲目。先是试唱《密誓》、《小宴》、《埋玉》、《闻铃》四折,后又增加《絮阁》、《惊变》二折,最后选定《絮阁》、《闻铃》、《惊变》三折,由周传瑛唱唐明皇,张娴唱杨贵妃,王传淞唱高力士,包传铎唱杨国忠。排练场即选文澜阁。由于时间紧迫,距开会时间只有7天,因此一开排就紧锣密鼓地进行。那时昆苏剧团宿舍在孩儿巷附近的观巷72号,离文澜阁有一段较长的路,周传瑛等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就匆匆地出门,沿湖滨,过断桥,绕孤山,赶赴文澜阁排练。而张宗祥老先生也总是早早地在那里等候他们到来,开唱之后,还不时地给予曲意方面的指导。演出获得成功,受到田汉等人的表扬。会后,在张宗祥的指导下,昆苏剧团排演了全本《长生殿》,这是1937年仙霓社散班后首次恢复《长生殿》全本演出,也是建国后专业昆剧团演出的第一本昆剧。1956年4月,本剧还和《十五贯》一起晋京演出,首场演出于北京广和楼,据说这正是洪昇当年演出的戏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巧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观后,特地找出收藏多年的珍本《长生殿》亲笔签名后赠给国风昆苏剧团,一时亦传为佳话。
四、 编撰剧本,京昆不挡
张先生编撰的剧本现存有昆剧《浣纱记》节改本、《荆州记》、《平飓母》3种,京剧《卓文君》、《马二先生》2种,合计5种,可谓“京昆不挡”。其中《浣纱记》、《荆州记》两种用力最多。
《浣纱记》据明梁辰鱼的同名原著改编,原作共45出,改本为7出,依次为《谋吴》、《访施》、《教舞》、《进施》、《采莲》、《沼吴》、《泛湖》。演越王勾践面临吴国强兵压境之时,与夫人及范蠡、文种二大夫商量对策。范蠡访得美女西施,与之定亲,出于救国之需,教其歌舞,以越王名义献给吴王夫差,令夫差沉湎于酒色不可自拔,以至杀了忠臣伍子胥,越国遂乘机灭了吴国,范蠡功成不受禄,携西施泛湖归隐而去。备用的另有《回营》一出。完成后作者曾给周传瑛写了一封长信,谈了改编的缘起、宗旨、原则、存在的问题及角色分工等,从中可知他的一片苦心与美好的愿望。关于改编缘起,是因为原著影响甚大,是昆腔的开山祖师,主人公西施又是数千年来闻名全国的大美女,很有重新排演的必要;但由于出数太多,连台排演,需四五日方能演毕,加上原著以《吴越春秋》一书为底本,又参用其他材料,关目极为庞杂,一会儿说伍子胥,一会儿说王孙骆,千头万绪,反而把主题削弱了,非改编不可。关于改编的宗旨,一是演出时间“非在三四小时内解决不可”,二是“非把主题突出,使观众了然剧本意义不可”。根据这两点得出改编的原则是: 将所有材料围绕在西施一人身上,无关的一切删去,有关的可以在道白、曲文中反映一些,其他如预言、鬼神、报应等,一点也不留,这样既可以节省时间,又可以使观众完全明了“浣纱记”三字意义。而更深层次的意图还在于: 梁氏编剧时仅涉及复仇,启发一点狭义的爱国观念而已,而今天面临的是弱肉强食、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的时代,改编本即从这个方面着眼,改变了立场,让勾践夫妇仍以复仇为主,而主人公西施则改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人物。其次,《浣纱记》作为昆腔的经典剧本,凡唱昆曲的剧团均有责任排演,西施出于浙江诸暨,作为浙江的昆苏剧团当更要责无旁贷的排演它。由于张先生熟悉该团艺人的演技,所以于信末还就本剧的角色作了具体分工,建议由周传瑛、张娴夫妇分别扮演越王勾践与夫人,王传淞扮演伯嚭,朱国梁扮演吴王,包传铎扮演文种。至于范蠡、西施,因唱做多,应分两小生、两旦扮演,务必择选扮相好、身段佳方合适。
《荆州记》,题解为“诸葛亮深谋连吴国,关云长骄傲失荆州”。共6出,依次为《交印》、《刀会》、《拒吴》、《水淹》、《渡江》、《麦城》。演刘备入川,将荆州交付诸葛亮与赵云把守,入川后军师庞统贪功冒险中计,被乱箭射死,兵败落凤坡,急命诸葛亮与赵云入川救援。诸葛亮受命,即交印给关羽守荆州,并授其“东连孙氏,北拒曹操”八个字,称唯此方可保得荆州。诸葛入川后,关羽傲慢,不听其言,终于落得个荆州失守、败走麦城不成,只好自刎的下场。剧作揭示了骄傲必败的主题。同题材的剧作元代有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现存元刊本、脉望馆抄本两种。近代昆剧有《训子》、《刀会》,京剧有《荆州失计》、《麦城升天》、《白衣渡江》、《走麦城》等,滇剧、豫剧等亦有此剧目。张先生此剧虽然吸收了前人的某些成果,但更多的则是取材于《三国演义》第75至77回,重新谋篇制作,包括唱词与念,均从己出,故给人以全新的感觉。例如其中的《交印》、《拒吴》为各本所无,前者表现诸葛亮的深谋远虑,后者突出关羽的骄傲轻敌。《刀会》虽然取自关汉卿原著,却又与原作有所不同,除了删除乔国老与司马徽的戏外,还纠正了原作有关故事发生时间上的错误,即: 原著把刀会的时代放在水淹七军之后,依《三国演义》,这时鲁肃已死(正史同),怎么可以请关羽赴宴呢?本剧提至“水淹”之前,即避免了以讹传讹。
总之,张先生作为一位业余研究戏曲的学者,却集戏曲创作、评论、教师、活动家于一身,提出了以“演出”为中心的进步戏剧观,并通过自己的实践予以体验,这岂止是难得!对于今天的戏曲理论与实践仍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今年正值张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特撰此文以作纪念。
2016年,257— 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