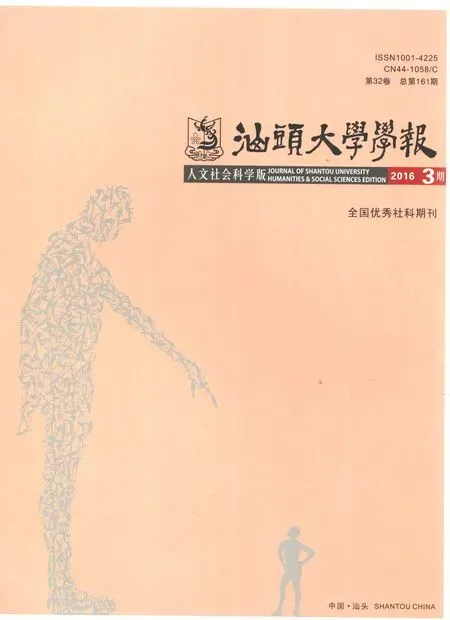占有保护理据的分析
——兼评我国的乌木占有案
罗时贵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8)
占有保护理据的分析
——兼评我国的乌木占有案
罗时贵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38)
摘要:占有制度先于民法制度,故占有保护的理据只能从民法之外寻找。古罗马法强调诚信、善意的占有主观元素;日耳曼法强调占有的外在功效。后世的大陆法系国家基本糅合了古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占有制度特征,作为占有保护的外在理据。而占有保护的内在理据则植根于占有本身的人格拟制的特征,占有是占有主体的自由意志的实现,对占有的尊重与保护,就是对人格自由的保护,从而维护人与人之间相安无事、和睦共处的关系。占有保护内、外理据的深度考究,为我国今后占有制度的重构找到了厚实的理论依托,以“民权理念”替代“王权思想”,淡化所有权的观念,规范占有的独立法律地位,构建“所有权-占有权”为中心的财产资源的配置结构,从而真正贯彻和落实我国《物权法》的“一体保护”原则。
关键词:占有;占有保护;理据;占有制度;制度重构
一般认为,占有制度发轫于原始社会末期,并成为私有制产生的标志,正如马克思所说:“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法律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1]意味着占有制度早先于民法的所有权制度,是事实构建规范的使能,然具规范意义上的占有制度则形成于古代罗马法和日耳曼法,并为近、现代民法中的占有制度奠定了基石。自占有制度问世以来,关于占有的性质、构成要素、占有的类型、占有的保护等诸多基本理论问题一直困扰着受众主体,其间争议至今未能盖棺定论。在诸多的理论争议焦点中,占有保护成为基本理论的核心问题,这可归结于人类社会私有财产的保护始于法律对自然占有的介入,进而揭示出“一种权利的保护、设定、主张往往反映一个社会物质、精神文明的需要,反映法律保护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和利益”之模态。[2]据此,占有保护所引发的问题是,为什么占有能得以保护以及如何保护?得以保护是探讨占有保护的正当性问题,如何保护是说明占有保护的实践规范问题。法理学的任务就是厘清和区辨这些问题,进行哲学化处理,抽象出基本原理和原则,形成内在的逻辑自洽性体系。故此,本文所贯彻的思路和方法路径为,对占有的制度史以及形成的要素进行综合分析,从内在的视角揭示占有应受保护的自由与人格因素,从外在的视角证立占有应受保护的经济、伦理因素,以及通过案例分析说明我国占有制度重构使然和设计思考,从而完成占有保护正当性的论证。
一、占有保护的内在理据
人类社会在原初状态下,自然资源匮乏,人的求生本能欲望,可以合理地解释以及历史地见证人类同样接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休谟认为:“人的欲望的偏私性,财产的稀缺性和财产占有的不稳定性都成为对凭借劳动所获得的所有物的享用的主要障碍,补救的方法不是由自然而来,而是由人为措施得来的”[3]566,即为休谟的稳定财物占有的法则。与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不同的是,休谟将“通过社会全体人员所缔结的协议使那些外物的占有得到稳定,使每个人安享他凭幸运和勤劳所获得的财物”,[3]530以认可协议的方式,承诺并尊重他人对物的占有,克服和避免了丛林法则的无序状态,反映了人类对正义观的朴素情感,即“正义是分给每个人以其权利的稳定的、普遍的态度”。[4]11社会原初状态下的人类对物的占有,基本满足于人类最低限度内的生存所需,其占有的份额和份量只能维持其基本生存的部分,在此情境下,占有的保护靠习惯法和自然法予以调整。
私有制在财产的过剩中滋生,也导致了贫富阶层的出现与对峙,财产的占有功能不仅限于个人的生存需要,而且过渡成为个人荣耀的象征。于是,剩余财产在个人之间就出现了“我的”、“你的”的判定符号,个体凭借对无主财产公然、公开占有的形式,以此当然地排斥他人对该物的占有,行使该物的占有权利。那么,其占有权利的理据何在,是丛林法则或是习惯使然,都不能作出妥当的解释,权利占有保护的原因必须从占有的历史发展进行寻找。梅因认为:“先占”是实物占有的有意承担;至于这样一种行为赋予人们对“无主物”享有权利的看法,不但不是很早期社会的特征,而且很可能,这是一种进步法律学和一种在安定的情况下法律产生的结果。只有在财产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在实际上长期得到了认可时,以及绝大多数的享有物件已属于私人所有时,单纯的占有可以准许第一个占有人就以前没有被主张所有权的物品取得完全所有权。[5]196-197梅因把占有的保护建立在权利推定之上,即“占有人”成为所有人,因为所有的物件都被假定为应该是属于某个人的财产,同时也因为没有一个人比他对这特定物件有更好的所有权。[5]197康德则从条件和原因的关系阐释了占有权如何获得保护的理由,康德认为,首先必须要占有该物,“任何人,如果他想坚持有权利把一个物作为他的财产,他必须把物作为一个对象占有它”,[6]57从而排斥他人擅自侵犯和侵害占有之物。其次,占有者必须是理性地占有该物,通过理性贯彻人对物占有的自由意志,并“通过理性的程序,权利的概念被引进到与这类对象的关系之中,以便构成外在的‘我的和你的’的可能性”。[6]64康德一方面为占有的实现构建了后世之说的“体素”和“心素”要件,一方面给占有行为注入了人格化的权利,成为黑格尔的“物内意志说”,即当个人把外在之物作为占有时,便注入了个人意志,并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占有物。“这种占有,就是人把他在概念上存在的东西转变为现实”,通过媒介物的标注形式,以此“排斥他人并说明我已把我的意志体现于物内”。[7]故对占有的侵犯,实质为对人格的意志与自由的侵犯。在康德看来,人格的意志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性的权利,是不容冒犯和侵害的,人可以通过道德律令调整内心的意志自由,通过法律调整外在的行为自由。据此,可以判断,对占有的侵犯,法律的作用力被有效地纳入占有保护的领域。
当占有内化为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并与人格关联起来,其应受保护的理据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耶林无疑地把物权视为人格化的权利,对他人之物的侵犯就是对他人人格的侵犯,“因此他们的行为并不止于侵害我的物,也是对我人格的侵害。如果说主张我的人格是我的义务的话,其义务也延伸到对人格存在所不可或缺条件的主张——即被侵害人通过保护其所有权而保护自身的人格”。[8]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自由、平等、私权神圣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私权神圣首先是人格权神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文明。人的自由、意志及人格不被不当干预与限制,当人以理性的自由意志而占有该物时,同时也将自己的人格赋予其中,对财产的侵犯就是对人格的一种冒犯和加害,霍布斯称之为人的自然权利:“就是每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9]同时,对占有物的尊重,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对方的自由意志,也是理性人所持的一种正直、正义、诚实的表现,这既反映了道德社会的情感需要,也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亦成为受法律保护的理由和基石。
二、占有保护的外在理据
古罗马既存的真正生活不犯他人各得其所的法则,优士丁尼大帝用法律戒条的形式予以固定:“诚实生活,毋害他人,分给各人属于他的。”[4]11卢梭把“每个人只能占有维持其生存的部分”作为占有的条件之一,占有财产多余的部分,通过纳税的方式进行调节,对“拥有多余的东西的人的纳税额,在必要时,可以达到足以剥夺超过其必需的一切东西的程度”。[10]17这是私有制社会状态下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要求,体现了人类互靠、相存的合理内在驱力,个人只能占有其能以生存的必需部分,超出的财物多占部分则可能背负不正义的道德指责。因此,占有法则谓之正义法则,体现和要求个人对人类资源之占有不得超过其能力或生存所需之限度,否则即为非正义。[10]17如此,占有财产的多寡与正义的评价体系关联起来,从而为近代民法的占有制度提供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理论支撑,这样一来,占有制度关联到两个问题,一是通过占有制度实现和保护社会财产资源的稳固,促进财产配置的正义需求;二是通过援引主观诚信及善意的道德条件,把私犯行为获取的持有之物排斥在占有的保护范围,以保护占有的道德性要求。
基于占有关联的第一个问题,可以从古代罗马法和日耳曼法中寻找一些原因。古代罗马法对占有的保护归结于维护社会财产秩序的和平与安宁,制止暴力侵夺他人财产,因为“一切暴力皆为非法,而此种不法通过令状而被撤销”。[11]8毋庸置疑,任何暴力都表现两个方面的法律判断,一方面侵害了公共秩序,另一方面侵害了个人,[11]37对个人的侵害会发生不利于占有人的事实状况的变化。[11]33对暴力侵夺的制止,是维护社会财产秩序和恢复个人占有财产安全保障的一体两面。因此,古代罗马法通过各种占有令状(如维护占有令状、现状占有令状、优者占有令状、制止暴力剥夺令状等①古罗马法对占有的保护是通过各种令状实施的,所谓令状是裁判官用以命令做某事或禁止做某事的程式和套语的集合。维护占有令状是保护占有人的占有免受暴力侵害;现状占有令状是保护占有人对土地的占有,排斥他人的暴力侵扰;优者占有令状是保护占有人对动产的占有;制止暴力剥脱令状是制止他人的暴力行为而保护占有人对不动产的占有。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著,徐国栋译:《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517页;【德】萨维尼著,朱虎、刘智慧译:《论占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330- 363页。)和占有诉权实现占有财产的保护。与罗马法对占有财产静态安全的保护不同,日耳曼法主要体现在使用、交易过程中的财产动态安全的保护,通过权利推定、以手护手(现代民法中称之为善意取得制度)的占有制度,维护财产交易过程中的动态安全。但无论占有是具有“以人为中心”特征的古罗马法或是具有“以物为中心”的日耳曼法,占有制度在维护财产自然秩序、定纷止争的功效方面是殊途同归的,对占有财产的保护,实质上也构成了对财产资源合理配置的认可。原初状态下的财产配置,只能按照最低的生活保障要求获取财产,摩尔根称之为生存性的本能占有,“占有欲望依靠纯粹归个人使用的物品而哺育着它那初生的力量”,[12]11生存性的本能占有只能按需分配(即按照人类所赖以生存的最低物质保障进行占有)。私有制的出现,财产的多寡成为权力与荣耀的象征,发展性的本能占有取代了生存性的本能占有,人类对财产占有的主旨在于谋求发展并进行财富积累。当占有发展为第二层次的财产需求时,对财产资源的占有与配置就与社会正义的判断关联起来,即占有符合正义时,占有才成为受保护的对象。但财产资源的配置结果如何体现正义却成为经济、伦理、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影响巨大的莫过于罗尔斯的正义论,与功利主义所持的“社会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不同的是,罗尔斯关注的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其正义的第二项原则要求“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13]302这样,“人们通过坚持地位开放而运用第二个原则,同时又在这一条件的约束下,来安排社会的与经济的不平等,以便使每个人都获益”。[13]61
基于占有关联的第二个问题,可以从古罗马法对占有的构成以及占有期间的孳息保护方面进行考究。如何完成一项占有的构成要件,形成了以萨维尼为代表的“主观说”和以耶林为代表的“客观说”,①主观说:除对物的体控外,还须有占有意思。何为占有意思,在其内部又形成不同学说:“所有人意思说”,须以所有权的意思占有该物。代表者为萨维尼和法国民法典;“支配意思说——客观说”,须以支配该物的意思占有该物,代表者为耶林,“相对所有人意思说”又称客观说;“自己意思说——折衷说”,须以自己利益的意思占有该物;代表者为日本民法典。客观说(纯客观说):占有仅为对物有事实管领力,无需考虑意思为必要。代表者为贝克和德国民法典以及瑞士民法典。参见:【德】萨维尼著,朱虎、刘智慧译:《论占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译者前言,21页;刘智慧:《中国物权法解释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708页;邹彩霞:《占有、占有制度及其功能》,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4期。其间的争议实质为对占有“心素”的要求,但无论是萨维尼以“所有的意思”或耶林以“支配的意思”进行占有,在占有须有主观诚信的要求方面是一致的。古罗马法依据占有的主观善意情形,“根据法律理由认为他对此物拥有所有权(基于善意以及正当原因),则他获得对于此物的孳息所有权”,[11]13这表明,主观上的善意使占有转换为所有和受法律保护的共同标准,古罗马法对符合主观善意的占有者赋予时效取得的法律效果,充分承认占有人对占有物及其占有期间所获取的孳息,同时以令状形式保护占有的事实状态。据此映证,善意占有(及其诚信观念)在古罗马法占有制度中导致两种效果:其一,无论是否属于本权占有,善意占有利益受到较强的法律保护;其二,法律基于社会公共政策的需要,当善意占有持续一定的时间时便转化为所有权,即理论通说中的时效取得制度的形成。[14]古罗马法对占有的诚信要求,实质提升为道德上的奠基,为现代民法中的诸如善意取得、时效取得、不当得利、占有等制度规则,注入了道德因素,纳入了伦理的调整领域,其诚信及善意的特质对后世民法影响巨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占有保护之民法理据并非产生于民法领域内部,而是产生于民法据以发生并获取发展动力之其他领域——伦理哲学与经济学”。[15]即占有制度先于民法的所有权制度,并成为后世民法所有权制度的基石,其受保护的理据并非囿于民法自身的内部体系,而是根植于道德要求的伦理学的外部证成。
三、我国占有制度的缺陷及其重构
占有制度的发展史表明,占有的保护理据在于经济、伦理的要求,是法律保护自然占有的结果。在整个财产关系领域中,占有是人类基于本能所形成的一系列规则,物权法以占有为基础,以权利为工具,对占有规则进行理性化、逻辑化的整理与建构。就占有制度而言,其涉及的法理学根本问题是:个人公平价值和社会秩序价值的冲突和协调问题,是占有的法律保护方式的设置适当与否的问题。[16]705在我国,对占有的法律基本问题诸如法律属性、法律的构成要件、法律保护的理由等出现认识上的分歧,②关于占有的性质,存在着“事实说”、“权利说”、“权能说”及“关系说”的分歧。参见:刘智慧:《中国物权法解释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703- 704页;房绍坤、马兰:《论占有的几个问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5期。这种理论阐释分歧的存在以及占有理论研究现状的不成熟窘况导致我国占有制度在立法体系与立法内容方面过于简陋,无法统摄社会实践的界域,典型的事例有四川彭州乌木诉讼案、江西修水乌木占有案,③四川彭州乌木案:2012年春节,四川彭州市通济镇村民吴高亮在自家附近地下发现7件大型乌木,并雇人对乌木进行挖掘。2月9日,通济镇政府获悉后,对埋藏于地的7件乌木进行暂存处理。经鉴定,该批乌木树种为“金丝楠木”,估计市场价值高达上千万元。据此,吴高亮与当地政府就乌木归属问题发生争议。吴高亮自称发现者,认为乌木归自己所有;当地政府认为乌木归国家所有。7月26日,吴高亮通过诉讼要求政府归还自己发现的乌木。一、二审法院驳回了原告吴高亮要求确认乌木归己所有的诉讼请求。参见:钟琴:《对彭州乌木案的思考》,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江西修水乌木发现案:2013年9月3日,江西修水县农民梁财在东山村的河道里挖掘出一根长达24米、直径1.5米、重80吨的疑似乌木,经过江西省野生动植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明确该木材为秋枫。当地政府通知梁财,该树木应归国家所有。事后因该树木的归属问题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争议。访问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3- 09/16/c_125391674.htm。此类案件反映了我国物权法律规范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裂缝与错位,其引发占有的法律核心问题为:我国物权法应给占有何等地位,是附属于所有权的一项权能进行保护或是独立于所有权并与之并列作为同级的保护对象?从物权法的内容和观念来看,我国民法一直以来就未给予占有应有的独立名分,仅把占有列为所有权的附属位置,未能将占有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从所有权制度脱胎和独立出来。因此,对占有的保护只能凭靠所有权的作用而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保护,无法给予与所有权同等地位的保护力度。究其原因,可能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财产公有的经济政策在法律上得以确认和保护,公有制经济模式促成了所有权的法律中心地位,决定和支配其它财产性的法律权利(如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债权等)的命运与归属。二是财产公有观念根深蒂固,我国自古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私有制经济没有滋生的土壤,法律更是拒斥私有财产的保护。然占有的结果必然催化私有制的产生,这与我国实行财产公有制度背道而驰,法律由此有理由漠视和疏远占有的存在,仅从我国现行《物权法》关于占有的零星规定可窥见一斑。上述案例引发的另一个致命的法律价值权衡问题是,占有能否对抗所有?个人占有权能否对抗国家所有权?对于发现埋藏物、隐藏物、漂流物等无主物归属问题,我国《物权法》第114条的立法态度非常模糊,由此造成上述案件发生。在此,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的理据何在?如果说是“王权思想”作祟的话,情以何堪的是《物权法》何以规定任何主体的财产同等保护原则,古代的“王权观念”与现代的“民权观念”在我国财产立法领域遭遇激烈对撞,巩献田教授为此曾疾呼管窥:我国《物权法》是一部开历史倒车、违宪的法律,尽管有些危言耸听,但可论断我国“民权思想”和“私有保护”的理念式微且渐行渐远。
我国《物权法》对个体财产的保护规定不尽如意,所有权制度的设计以牺牲民权为代价,直接威慑到个人生存与发展的财产权利需求。我们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倡导所有权为中心的法律地位时,不妨提升和发挥占有的地位和功能,以调和财产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窘境。
(一)提升占有的法律地位,发挥占有调节财产资源配置的效用功能
尽管占有性质在学说上存在“事实说”与“权利说”的分野,但在实践中并无太大的区别,二者均系赋予某种事实以一定的法律效果并加以保护,使占有人可以享受因占有所产生的利益。[17]即占有是基于法律保护的后果,而非法律保护的理由,这种情境使占有处于弱势法律地位,对其是否进行法律保护可以进行自由选择,法律上没有给出强力的保护理由。古罗马法对占有给予法律保护就设置了一定的条件,即要求主观上须以善意,从而对不同的占有类型进行不同种类的保护。另外,从法律地位来看,日耳曼法将占有视为所有权的占有,成为“裹着本权的外衣”,没有独立的权利地位。[14]耶林就此亦阐明:“占有是所有权之堡垒和基础,保护占有即为保护所有权”。[18]在我国,占有只是所有权或他物权的一项内容,并非一类独立的权利,占有权能成为所有权的附属品,没有完全从所有权中脱离出来,缺乏强力的保护地位。故此,应予提升占有的独立法律地位,参照日本的做法,将占有权与所有权、他物权并列,[19]真正把占有权能从所有权中独立出来,赋予其与所有权同等的法律地位,弥补所有权对财产调节功能的不足。形成所有权、占有权、他物权对财产的归属、收益、使用的三套马车的架构,在三者内部之间形成互补、协调的法律机制,调动、发挥财产得以充分效用的功能,达到物尽其用的合理财产配置,实现人享其份的和谐社会秩序。
(二)“民权理念”替代“王权思想”,真正实现物权一体化保护原则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谈私色变,“一大二公”的思想渗透各个领域,幻想“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太平盛世,希望把“无人不饱暖”建立在“无处不均匀”的分配基础上,[20]这种要求滋生了平均主义的思想,而平均主义必然仰赖于国家或政府的施行才能获得。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物质资源的分配来自于皇帝的恩施,但也可以随时没收个人的财产,人们能否获得财产特别是土地取决于对皇帝的效忠和功勋,由此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孝忠文化,亦体现了天下财富皆出皇权的封建“王权思想”。而与“王权思想”对立的“民权理念”,呈现为平等地关切和尊重个人的权利,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保护,特别是个人生存的财产权利的捍卫,如果国家在实施公共利益建设目标时,与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发生冲突时(如我国强拆),公民可依财产权利对抗政府的这项政策和目标,即反对政府的权力。[21]253德沃金把这种个人财产的权利保护上升到政治权利的维护之上,“如果,即使不利于其他政治目标或某一目标会因此受到伤害,也支持那些促进、保护个人可以在其中享有权利的状态的政治决定,或即使有利于其他政治目标也反对那些阻碍或危害这种状态的政治决定,那么,个人就对某种机会、资源及自由享有权利”。[21]127在当代,我国自然资源的分配仅限国家、集体两级主体享有,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自然资源(如土地、河流、森林、草原、矿产等)个人无权享有,并禁止个人对自然资源的侵夺,维护绝对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保护至上主义,他物权、债权均受制于所有权的约束,占有制度更是无栖身之地。如果说占有是私有制生存的土壤,是个人分享自然资源的自由意志行使的话,那么所有就是维护公有制,是国家独享自然资源的权力行使的必然。占有制度要求的是和平、诚实、善意、合理地分配和使用财产,发挥物尽其用的财产效益最大化结果,表明和体现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和睦的“民权理念”。国家财产所有权制度却扼杀了“民权理念”,助长了家长制的“王权思想”,任何财产的持有人只不过是国家财产所有者的代理人。因此,消解“王权思想”、淡化所有权的观念是今后物权立法、修法的一项重要议题。占有制度的介入,打破了现有财产使用、收益关系的平衡底线,对那些重要自然资源(如地下水、野生动植物,森林,草原等)可以通过占有制度进行调节,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充分利用且珍惜自然资源。诚然,人们也可以通过观念上的国家所有权,进行自我约束,防止滥用和浪费自然资源。故此,占有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仅可以解决我国自然资源所有权制度的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如小产权、准用益物权的法律难题),而且在提升个人权利、保障意思自由、弘扬社会正义、维护财产秩序等方面均有积极的意义。占有制度的设计,使个体与国家纳入了同等的资源利用平台,真正实现物权一体化保护原则。
(三)确立准占有制度,疏通财产流转渠道
各国在占有制度之外再设准占有制度(权利占有),其目的和意义在于把权利扩大为占有客体的范围,对有体物和权利(物权客体)给予同等的法律保护;另外,准占有制度有助于充分行使物权,发挥物的使用价值。[16]711罗马法关于权利(物权客体)的范围非常广泛,涵盖的权利客体有:继承权、用益权、债权、地役权(取水、放牧、挖沙等)、使用权及居住权。[4]137-145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观念上重视对有体物的保护,对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保护观念比较淡薄,反映在我国物权立法上,对物的界定范围仅限于动产和不动产,权利作为物权客体需有法律明确的规定,这样,把权利客体通过占有制度加以保护就难上加难,权利客体的保护就游离于物权法域之外,特别是奉行物权法定原则的我国物权立法思想,使得一些权利客体在物权法域内出现落空保护情况,如对居住权的保护问题在物权法中无法兑现,在实践中遭遇尴尬局面。不仅如此,而且对准占用的流转亦造成理论上的难题和落入实践交易的困境,如典型的关于农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由于农村承包地的使用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受到抵押、流转的法律限制,滋生了大量抛耕、弃耕的事实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后果是弃耕者丧失了权利占有,欲耕者无法取得权利占有,形成权利交接断裂、权利占有真空状态,耕地变成“荒冢”,造成的法律后果是:一方面因农地使用权流转受限不能发挥农地物尽其用的功效;另一方面因缺失权利占用的规则不能调节农地使用权的占有主体发生变更的法律效果。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对土地等重要自然资源归属国家所有理所当然,但通过占有制度,特别是可以借鉴古罗马法关于准占有制度和《德国民法典》第868条中的间接占有制度,即:“作为用益权人、质权人、用益承租人、使用承租人、保管人或者基于其他类似的法律关系而占有其物的人,由于此类关系对他人暂时享有占有的权利或者负有义务时,该他人也是占有人”,构成了德国法上所特有的权利占有制度,这项制度不但可以保证土地归属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而且通过权利占有制度进行调节占有主体之间对土地的充分、合理使用,解决所有权权能分离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因此,我国《物权法》在未来的修订中应确定和设立权利占有制度,以解决观念占有与实际占有所产生的实践冲突。
(四)加快占有制度的体系化建构,突出“所有—占有”并驱的中心地位
在古罗马,占有与所有没有严格的法律界限,占有权几乎可以与所有权等量齐观、平分秋色,而对这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马克思对亚细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考察:“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22]同时他还发现,土地的所有者并不亲自经营土地,租地农场主或租地农民拥有使用权,马克思称这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正如土地的资本主义耕种要以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和土地所有权的分离作为前提一样,这种耕种通常也排除土地所有者自己经营。”[23]这为马克思奠定产权统一与分离理论提供了现实素材,马克思产权统一与分离理论表明: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表现,所有制是所有权的经济基础。所有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等权利在内的一组权利束,一般情形下,各种权项统一于一个产权主体,即财产所有者,是一种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产权模式;但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有权的各项权利不断发生分解和分离。[24]在权利分离状态下,意味着财产所有权并不包括财产的全部权利项,不同主体之间可以分有不同的权利项。马克思这一分权理论,为“所有-占有”的分离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在制定法律时,不仅要考虑地域性和区域性的特点,而且要考虑该国的文化、历史、情感以及国民性格。[25]因此,萨维尼认为:“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最后,随着民族对于其民族性的丧失而消亡”。[26]9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民族性的特征,如对典权的存废争议就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反映了我国国情所需。“实用原则”成为我国物权立法的一个潜在观念,尽管遭到“逻辑结构混乱”的诟病,但不得不基于国情进行利益权衡的结果,牺牲严格的逻辑一致性以满足实践需要应成为法律过渡期间的明智之举,萨维尼亦认为:“并非科学逻辑一致的需求必然会因这样一个混乱的行事方式受到损害,因为这种一致性的利益必须隶属于生活的需要”。[26]632我国《物权法》关于占有的篇章规定既无逻辑体系一致性的要求,又无法满足社会实践的需求,简单的5项条款仅成为所有权的嫁妆,不能发挥其独立的社会功效。因此,一方面完善占有制度的内在逻辑体系,规范占有的取得和丧失要件,增加占有的保护类型,规定占有令状和占有诉权制度,确立准占有的规则,将占有的这些核心内容进行筛选、论证、取舍等理论化处理,使其在逻辑上协调一致,抽象出原理原则,并建构成一个逻辑上无矛盾的内在体系。另一方面,突出占有的中心地位,提升占有与所有并列的层级,弥补和解决所有权制度力不能达的范围,实现财产资源的充分效用,甚至必要时牺牲所有权而保护占有权,设定占有优先适用、占有对抗所有的规则,这有利于化解我国所有权与权能理论在实务中的矛盾起到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众所周知,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所有权权能的分离,保障和实现企业能够独立经营的真正目的,使企业能够承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律风险责任。但国家经常以所有权者的身份干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屡见不鲜,提升占有权的保护,就是赋予国有企业依据占有权抗衡国家(所有权)任意干预的权利,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主体。
尽管我国民事法律规范有占有、占有权能、占有权、善意占有等诸多提法,但“我国还没有明确的占有概念,更没有明文承认的占有制度”,[27]占有依附于所有权能而无法施展其调节财产的功效。从“所有权中心主义”逐渐向“用益权中心主义”发展时,占有制度才摆脱了所有权的枷锁,并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貌和自然的优势地位再现于人们的视野中。因此,在重构我国占有制度时,应汲取古罗马法和日耳曼法对占有制度设计的丰盛营养,分析占有制度赖以存在的理据,将其合理、可行的要素抽取出来,并结合我国民族特色和国情,构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占有制度和占有法则,并提升占有的法律地位,发挥占有的功效,在实现财产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也维护了财产配置的秩序与安宁,这是所有权制度无法能及的功效,或许,这就是占有制度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最佳理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82.
[2]刘智慧.中国物权法解释与应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705.
[3]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优士丁尼.法学阶梯[M].徐国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5]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6]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64- 66.
[8]耶林.为权利而斗争[M].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7.
[9]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7.
[10]卢梭.政治经济学[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1]萨维尼.论占有[M].朱虎,刘智慧,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2]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M].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3]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4]季境.占有制度溯源与现代民法之借鉴[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5).
[15]刘云生.占有制度的法哲学、法史学考察[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
[16]刘智慧.中国物权法解释与应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
[17]李湘如.台湾物权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172.
[18]周枏.罗马法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455.
[19]邹彩霞.占有、占有制度及其功能[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4).
[20]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7.
[21]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M].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40.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47.
[24]吴易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J].中国社会科学,1995(1).
[2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5,序译7.
[26]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M].许章润,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27]刘智慧.占有制度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1999.
(责任编辑:汪小珍)
中图分类号:DF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4225(2016)03- 0019- 08
收稿日期:2015- 08- 31
作者简介:罗时贵(1974-),男,江西南昌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