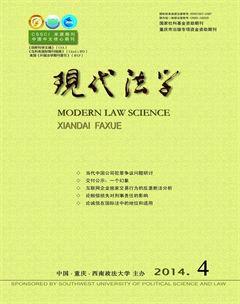交付公示:一个幻象
聂卫锋
摘 要:交付公示作为被继受而来的德国物权法原则之一,自清末被传统中国学界接受以来,散见于诸多著作、教材之中。但无论是现实交付,还是观念交付,都不可能实现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动产物权本身是否可以被公示也值得怀疑。交付公示原则的确立有特定的意志主义方法论背景,而实践面向的检讨则有助于形成新的制度设计理念。
关键词:交付;占有;交付公示;现实交付;观念交付
中图分类号:DF521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物权公示是物权法理论构建的起点与核心,物权法所确立的公示公信原则即是其在制定法上的反映。对于有体物,传统物权法以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手段,对于动产,则以占有和交付作为动产物权的公示手段,其中的交付即包括现实交付也包括观念交付。2007年《物权法》即依此理论进行了基本的体系架构,并体现在诸多的制度细节之上。
不动产基于登记而公示出来的在其之上的权利(物权)信息,由于登记制度的完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确保其准确性。尽管在例外情况之下也会出现登记权利人并非真正权利人的状况,但实践中的问题似乎并不多见,至少相对容易解决。异议登记制度即是对此方面问题的制度性回应。
对于动产而言,问题则比较复杂。占有是否具有动产物权公示的功能,学术界在讨论占有之功能时似乎并无定论占有之表彰本权功能,看似与占有之公示功能有关,但也仅仅是在推定意义上成立,并不能真正公示什么。占有在推定意义上表彰本权的功能,参见:龙卫球. 物权法政策之辨:市场经济体的法权基础[G]//龙卫球. 民法基础与超越.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7;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M]. 5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90;江平. 中国物权法教程[M]. 修订版.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27-28;刘家安. 物权法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224;崔建远. 物权法[M]. 2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4;孙宪忠. 德国当代物权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10;王泽鉴. 民法物权[M]. 2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63. 不过在德国学者的著作之中,则会明确指明占有的公示功能。(参见:鲍尔·斯蒂尔纳. 德国物权法(上)[M]. 张双根,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09;曼弗雷德·沃尔夫. 物权法[M]. 吴越,李大雪,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80-81.),但还是得到学者们的普遍支持,认为占有属于动产物权静态或者权利享有的公示手段。参见: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M].5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86;谢在全. 民法物权论(上)[M]. 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67-69;孙宪忠. 中国物权法总论[M]. 2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81, 370;江平. 中国物权法教程[M]. 修订版.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39;刘家安. 物权法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68.
不过,相比较于占有的公示功能,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动态或权利变动的公示手段,则几乎得到了所有学者们的认同参见:谢在全. 民法物权论(上)[M]. 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67;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M]. 5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86;孙宪忠. 中国物权法总论[M]. 2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81-282. 在龙卫球教授看来,只有物权变动才需要公示,并且只能通过“转移占有”的事实行为进行公示。(参见:前引龙卫球. 物权法政策之辨:市场经济体的法权基础[G]//龙卫球 .民法基础与超越.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7.) 不过,有学者也承认,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方法,实为无奈之举。(参见:刘家安. 物权法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68;江平主编. 中国物权法教程[M]. 修订版.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40.)
或许也正因如此,《物权法》第6条条文内容: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确立了动产物权交付公示的基本原则,第23条条文内容: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重申了这一点。
动产交付,尤其是观念交付,是否可以实现权利(物权)公示的目的?交付和占有,哪个才是动产物权公示的最合理判断标准?进一步而言,动产物权能否被公示?虽然中国的《物权法》立法文本已经遵从他国法律模板确立了基本的物权制度框架,但在笔者看来,一切并非如立法者所确信的那样,成为定论。对于这些问题的再探讨,仍然会有助于既有条文规范属性的认知,也可以为物权法的开放式发展和完善提供新的动力。
一、动产物权公示目的之传统认识
按照德国物权法的理论,物权之所以需要被公示,源于法学家们对于物权性质的界定。物权是绝对权、支配权,因此具有对世性、排他性、优先性、追击性等,对比于作为相对权、请求权的债权,后者仅具有相对性、平等性等特征。物权的绝对对世效力要求物权的具体种类具有可识别性,为了实现此目的,公示原则发挥了作用。参见:曼弗雷德·沃尔夫. 物权法[M]. 吴越,李大雪,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5.
公示原则的确立,也有生活经验作为其规范基础,此即“在实际生活关系中,物权在其外部通常是可以认识的:汽车的所有权人常是自己来驾驶汽车,也就是自己‘占有汽车;谁要是在一块土地上建造一幢房屋的话,则多半是这块土地的所有人。因此在一定的可能性上,可由——作为事实上持有的——占有状态而推导出所有权的存在”[1]。简而言之,公示的目的在于使人“知”[2]。
但如果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立场出发,可以对物权公示原则进行更为技术化的解读:
从权利保护的角度看,物权公示的目的在于,物权主体之外的所有其他主体都是消极不作为义务的承担者,因此权利信息需要进行公示,以让所有人都知道特定的权利主体针对特定物拥有特定的权利,故而不能够随意侵害物之状态及利益。
从权利行使的角度看,物权的追击效力、优先效力都对于其他民事主体的利益或权利产生直接的影响,公示出来的物权可以方便物权主体发挥其权利的威力,对潜在的第三人而言,也可以知晓与其对抗的权利内容究竟为何。
从交易安全的角度看,物权公示的目的在于,可以使得潜在的交易第三人知悉物权(所有权)的真正归属主体,从而使其可以放心地与物之占有人/控制人进行物权的交易——就动产而言,即包括所有权的转移,也包括质权的设定。
或者可以用类似德国民法学的语言加以表述,即物权公示的目的在于物权之公信,公信对于民众或交易当事人而言,构成了某种行为判断上的强制或诱因。类似的表达,参见:刘家安. 物权法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72.
对于财产法的体系不采德国物债二分模式的法律体系而言,虽然没有物权公示的术语和说法,但财产权所要面临的对于第三人效力的问题同样存在,因此同样需要法律确立规则以维持基本的财产法秩序。法国民法典早于德国民法典而制定,其财产法虽然同属于罗马法以降的欧陆民法传统,却并未采行类似于德国民法的严格的物债二分的体系构建方法其实财产法在法国的语境之下,本来就是把债法排除在外的,仅指大致相当于德国物权法所有权和用益物权部分的内容。(参见: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 法国财产法(上)[M]. 罗结珍,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87-92.),甚至《法国民法典》当中就没有物权的概念,尽管物权(le droit réel)和债权(le droit de créance)或对人权(le droit personnel)的概念也会频频出现在法院的判例与学术著作之中。参见:尹田. 法国物权法[M]. 2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5-55;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 法国财产法(上)[M]. 罗结珍,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法国财产法要解决财产权对于第三人效力的问题,并不从强调财产权一定要公示的进路出发,而是从财产权何以对抗第三人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参见: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 法国财产法(上)[M]. 罗结珍,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123-125,487-490.公示与对抗之间的实践效果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折射出方法论上的不同。
就动产而言,《法国民法典》以占有作为对抗第三人的要件《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规定:“在动产方面,占有即等于所有权证书。”只不过此此处的“占有”仅相当于直接占有,不含“不确定的持有”(le détention précaire),后者可类比于德国法上的间接占有。(参见: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 法国财产法(上)[M]. 罗结珍,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241-246.),第三人善意的判断标准则以“表见理论” 参见: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 法国财产法(上)[M]. 罗结珍,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123-127.或“外观理论”参见:罗瑶. 法国民法外观理论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13-117.
进行学理化解释。英美法系同样没有物债二分的模式,合同法、侵权法、财产法、不当得利法、信托法等,都属于各自相对独立的体系。就财产权而言,英美传统的财产法仅规范不动产(土地为典型)和动产,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则自成体系。英美法系在解决财产权对于第三人的效力问题上,采取了与法国法几乎同样的理论进路,强调财产权的对抗性。参见:劳森,拉登. 财产法[M]. 2版.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3,70.
尽管英美财产权制度与法国财产权制度都强调财产权的对抗性方面,但从理论化的角度看,二者还是存在法观念上的重要差别。前者并不强调财产权严格的绝对性,只是在具体的关系格局中判定不同民事主体之间谁的权利更值得保护参见:劳森,拉登. 财产法[M]. 2版.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47;冉昊. “相对”的所有权——双重所有权的英美法系视角与大陆法系绝对所有权的解构[J]. 环球法律评论, 2004, (4):455-457. 不过针对承担消极不干预义务的广大第三人而言,其实财产权还是具有绝对保护的意义,也即具有绝对性。,后者则仍然强调财产权本身具有的绝对性参见:尹田. 法国物权法[M]. 2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38-139. 在法国法上,从消极义务或“对抗效力”的角度看,实际上不单单是所谓的物权具有绝对性,即便是债权也处于如同物权一样的被尊重地位。(参见: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 法国财产法(上)[M]. 罗结珍,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91-92.),只不过在制度设计上并没有走向德国法的严格形式主义。
对比两大法系以及两大法系内部物权/财产权对于第三人效力的不同作用机制可知,对于物权/财产权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可以对第三人产生影响和发挥威力。至于物权/财产权在直接当事人之间的变动,仅涉及权属的变化以及未来相关收益的归属、风险的承担等等,与作为消极义务承担者的众多第三人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对于后者而言,不管谁是真正的权利主体,只要没有合法的法律关系支持其某种行为,都要对从他们的角度即义务人的角度承担不干涉的义务,哪怕仅仅是占有的状态。除非假设所有的动产都是无主物,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先占进行所有权的获得,但此种假设显然只能在废弃物堆积地或垃圾场才可以成立,与生活的常态不相符。
相对于不动产而言,动产由于其在物之功能、用途等方面的性质所限,基本上不太可能设定用益物权德意志法系各国民法立法中存在动产的用益权和权利用益权,但是据调查,在当代德国的物权法实践中,当事人之间设定动产用益权这极为少见。(参见:孙宪忠. 中国物权法总论[M]. 2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70;鲍尔·施蒂尔纳. 德国物权法(下册)[M]. 申卫星,王洪亮,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35.),动产物权之权利人对其权利的行使,也仅仅是占有动产、消耗原物或对动产所有权进行法律上的处分(放弃或让与)动产担保物权也是基于对所有权的限制让与或行使担保物权时的强行让与,其行使本身主要影响动产所有权人的利益,对于其他第三人而言则和所有权人本身行使权利没有任何之差别。,因此动产物权之权利人行使权利也不会积极干预到第三人的利益。即便是不动产之上设定的用益物权,其权利的行使也是不动产本身进行使用和收益,主要义务人是不动产所有人,不干预其他第三人的利益。不动产之上物权的登记制度,也可以确保所有的限制物权人知道彼此之间权利影响的状况,与其他第三人无关。不过,或许正是在不动产之上可能存在多个限制物权人,进而需要考虑多个限制物权人之间权利相互影响或限制的关系的意义上,不动产登记所具有的公示价值才有别于动产。
不过就这一点而言,其实动产物权的公示价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但对于潜在的交易第三人而言,知悉谁是动产之真正权利人非常重要,关系到其所获取的动产物权利益,是否具有最终的正当性。动产物权如果可以被公示,则有助于物权交易的安全、快捷达成。
二、现实交付:所有第三人的在场?
在动产交付的形态之中,首先面对的是现实交付,或又称为实物交付,是指基于原权利人的自由意志(含授权行为在内),把动产的直接占有移转给其他主体。史尚宽先生称之为“物上现实直接的管领力之移转即为直接占有之移转”[3]。在所有权转移的背景下,现实交付的指向对象是受让人,在设定动产物权担保的背景下,则是被担保人。不过在现代经济分工细化的背景之下,不一定完全局限在直接交易当事人本人及其代理人之间实现此等交付,也可以通过占有辅助人和占有媒介人[4]或被指令人[5]实现。不过对于后面这三类特殊的现实交付,必须具备三个要件:(1)在让与人方面,须完全丧失其直接占有;(2)在受让人方面,须取得直接占有或与第三人成立间接占有关系;(3)此项交付系依让与人的意思而作成[5]97。
在德国法的体系之中,动产现实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产生法律效力的重要条件,其设计的目的,用德国学者的话讲,就是“为了让所有权转移的过程公诸于众”[4]268, “使权利的变更能够从外部加以识别”[4]268 ,“因为所有权转移的可识别性只有随着物的实际占有的转移才能体现出来”。并且,考虑到德国物权法所采取的物权行为理论,交付必须与具体的(处分行为意义上的)合意相联系,才可以达到动产物权变动的目的。参见:曼弗雷德·沃尔夫. 物权法[M]. 吴越,李大雪,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66-273;孙宪忠. 中国物权法总论[M]. 2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09-310.
旧中国的民法学界,自清末起,通过日本后又自发继受德国法良多,新中国民法学界也受此影响。尽管在是否完全继受物权行为理论的观点上存在很大分歧,现实交付之于动产物权公示的观念,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支持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认为,在物权法上,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的交付,是当事人有意发生物权变动这种结果的意思表示推动的结果,或者说,是当事人之间为设定动产物权、移转动产物权这种确定的意思表示的表现方式。没有当事人之间这种确定发生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只有事实状态的标的物的转移,不能成为物权法上所说的交付,或者不能发生物权法上的交付的效力,即有效的物权变动的效力。参见:孙宪忠. 中国物权法总论[M]. 2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71.
反对物权行为理论学者,同样认为,作为交付常态的现实交付是动产物权变动(动态)的公示方法,并且只能作为基于法律行为的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如转让动产所有权或设定以占有为内容的定限物权(如设定动产质权)。参见: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M]. 5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93-94.
只不过,由于交付行为在债权形式主义的支持者看来,仅仅是一种事实行为,剔除了德国法中物权合意的成份。参见: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M]. 5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93-94;崔建远. 物权法[M]. 2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86.
在日本法之中,关于动产所有权的变动采取意思主义,交付仅具有对抗意义,而现实交付也作为可以形成对抗力的典型交付形态而发挥作用。参见:我妻荣. 我妻荣民法讲义Ⅱ 新订物权法[M]. 有泉亨,补订. 罗丽,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197.而在采行债权形式主义的国家,现实交付具有所有权转移的标志意义,尽管最终在权利公示的实践效果上,与“意思主义+交付对抗”的模式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综合上述不同动产所有权变动模式可知,现实交付行为本身尽管具有不同的理论定性,但其主要的目的是达致权利公示或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问题就产生了:现实交付的过程,到底是私密性的,还是具有公开性的呢?
现实交付公示的目的想要达成,按照基本的生活逻辑,即是该过程具有可知性,并且是对于所有的潜在的交易第三人或承担消极不作为义务的第三人而言,都具有可知性。但无需太多的理论分析,单凭直觉就可以对此给出否定的答案——因为,在具体的、很私密化的交易当事人之间的动产直接占有的直接移转,根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在场。即便是现代社会各类媒体、通讯工具非常发达,也做不到让所有的人关注到一个简单的桌椅、水杯、钢笔等的现实交付过程,即使能做到,也根本不可能在法律上如此要求。否则,人类的生活几乎完全没有办法运行。并且,移转直接占有完全可能是基于借用、租赁、保管等法律关系发生,假设法律可以要求任何潜在的第三人对所有的现实交付过程都必须保持持续的关注——此种假设显然是不可能成立的,如果不知道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着动产所有权变动的法律关系在德国物权行为理论的框架范围之内,当事人之间关于动产所有权变动的合意是动产所有权得以变动的必备条件,但该合意本身,即便在德国法学者看来,也只能是推定存在。(参见: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M].吴越,李大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67)或者承认物权合意的默示形式,参见:鲍尔·施蒂尔纳. 德国物权法(下册)[M]. 申卫星,王洪亮,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55.,则直接移转占有根本不可能实现权利公示的目的。或许有人可以在前面不可能具备的条件之上,再加上要求直接交易当事人在现实交付之际,“展示”或“宣读”他们之间的买卖契约或动产设质契约的条件——德国民法之中即强调交付必须与具体的处分权合意结合在一起,如此一来,似乎整个现实交付过程就可以实现权利公示的目的。但很明显,且不说客观上要求所有第三人都在场的法律上的可操作性完全不存在,依据当事人“展示”或“宣读”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类型所判断的动产物权(所有权)变动类型,所起到公示作用的也只是他们的“展示”或“宣读”行为,与直接占有的移转没有关系,或者不依赖于后者。有德国学者干脆认为,德国法强调所有权转移的外部可别性是确定性原则所要求的,而不一定直接对应常见的物权公示理论。(参见:鲍尔·施蒂尔纳. 德国物权法(下册)[M]. 申卫星,王洪亮,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77.)
否定了现实交付过程的公示可能性鲍尔/施蒂尔纳在此问题上态度比较犹豫,一方面坚持交付过程的公示性,同时又由于交易形态的复杂化,承认这一立法设想的非现实性。(参见:鲍尔·施蒂尔纳. 德国物权法(下册)[M]. 申卫星,王洪亮,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91.),并不能完全击破现实交付公示的理论,因为有学者也可能会强调现实交付的结果可以公示出动产物权的信息,而非现实交付的过程。对交付的过程与结果之于动产物权公示的“连贯性”价值,请参见:肖厚国. 物权变动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30-331.其实从现实交付强调对于动产事实上的管领力的移转的描述来看,很容易就可以得出此认识结论。
但现实交付的结果无非是一个民事主体对于动产的直接占有(甚至仅仅是占有辅助人的“持有”状态),此种占有状态虽然也受法律的保护,但该占有的本权基础并不一定是所有权,甚至不一定是基于物权,它还存在多种可能性,并且,在静态的直接占有之上也根本看不出权属变动的痕迹。本文写作过程之中,曾就文章主题求教于龙卫球教授,他特别提醒在西方国家,动产交易的发生往往伴随有类似的发票、小票等相关证据,这些证据可以证明动产所有权变动的真实性。但依笔者看来,这些证据的存在,恰恰反证了现实交付(移转占有)本身不足以起到公示动产物权变动的作用,而不是可以否定笔者所持的反对观点。特此注明。
如此一来,即便是现实交付的结果,也并不能起到动产物权公示的作用。汪志刚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认为,一个理想的法定公示方式至少应符合可识别性、可靠性、可操作性等三个标准,动产交付公示规则的确立属于历史选择的结果,以及强调物权行为的结果属于物权公示的结果等等,属于少有的对于交付公示原则进行正面维护的绝妙论证。但依笔者看来,同样未能经得起上文分析意见的检讨。(参见:汪志刚. 动产交付与所有权转让制度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69-190.)
三、观念交付:意识世界具有可知性?
在现实交付之外,作为交付之替代的观念交付,在经济分工越来越细化的时代,成为动产所有权转移的重要甚至主要交付形态。之所以如此,乃是传统商品经济或初级市场经济时段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模式,不再成为交易的典型,尽管实践中也还普遍存在。如果每个交易都需要当事人之间事必躬亲地进行移转直接占有的现实交付,经济运行的效率自然会十分低下,即便可以通过委托代理的模式延长当事人的手臂,在复杂的多手买卖链条之中,也并不是可以有效地提升交易的效率。因此,观念交付的最直接动因,即是方便货物/(主要是)动产所有权的转移。
观念交付的承认,解决了动产所有权移转的快速、便捷方面的问题,但对于强调物权变动的公示的理论体系而言,必然也要评估观念交付是否具备可以达到权利公示的目的。现实交付本属于交付公示所依赖的最典型示例,但其可能具有的公示功能却经不起深入细致、实践导向的检讨,已如上文分析。那么,观念交付的公示功能又如何呢?
中国学术界普遍承认或至少是默认观念交付的公示功能。梁慧星、陈华彬两位教授的著作之中,在阐述交付的公示意义之时,很自然地涵盖了观念交付在内,并未有特别的例外说明。参见: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M]. 5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93-95.
类似的立场,也见于其他学者的著作当中。参见:江平. 中国物权法教程[M]. 修订版.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39-140;刘家安. 物权法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68-69;孙宪忠. 中国物权法总论[M]. 2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70-371.
观念交付的类型,一般包括简易交付、占有该定、指示交付或返还请求权让与。在简易交付之中,直接占有的现实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由于占有之外法律关系的变更,使得该直接占有的属性由他主占有转为自主占有。在占有该定之中,动产直接占有的现实本身同样未发生变化,只不过由于买卖关系和租赁、借用等关系的存在,使得在动产之上创设除了一个间接占有,该间接占有归属于新的动产所有权人。在指示交付之中,直接占有本来就没有归属于动产的出让人,受让人基于与出让人之间的买卖关系,通过转让返还请求权的方式实现了所有权的转移,但受让人也并未因此而即可取得动产的直接占有。如果仅从占有的关系角度考察,在指示交付的场合,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实际上仅仅是实现了间接占有人身份上的互换,该动产的直接占有并未发生任何的改变。总结看来,观念交付的三种类型,都只是通过占有属性的改变,来实现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即如此,一个问题便产生,占有属性的改变可以达到物权公示的目的吗?
交付之所以被传统的民法学者认为具有公示动产物权的功能,依据的逻辑是,交付的过程外在化,进而可以使权利变化为潜在的第三人所知悉。但作为此种理论之模板的现实交付,其过程根本不可能具有所谓的公开性,因此权利公示的功能根本不可能具备。观念交付如果仅从占有属性更改的角度来描述,是否具有公开性呢?
直接占有按照通常的观点,具有一般交易主体、民事主体依据生活观念、交易环境可以大致辨别的现实性外观,相反,间接占有是需要依靠法律关系(占有媒介关系)的支撑,才可以在特定的主体之间于法律上形成。“间接占有人通过其与直接占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对物产生影响,该影响替代了间接占有人事实上对物的支配。”[6]尽管间接占有也具有法律上客观存在的价值和功能,但其属于观念世界的产物或存在,不具有直接占有现实性外观的特征。德国学者沃尔夫在其论著中对于间接占有也持同样的看法,有下述描述:“人们试图为这种被弱化的对物的关系寻求特征,将这种间接占有转为‘精神化的物之支配,与直接占有中对物进行事实上的支配不同。”(参见:曼弗雷德·沃尔夫. 物权法[M]. 吴越,李大雪,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83.)无需引用太多的理论著作即可知,只有现实性外观才可以证明或公示观念的构造物,观念性的事物属于逻辑上抽象出来的产物,从外观的角度看,具有不可知性。既如此,以间接占有的创设或更改来公示动产上的物权变动,岂不是等于让观念世界的事物去公示另外一个观念性事物?梁慧星、陈华彬两位教授明确承认间接占有的公示功能。(参见: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M]. 5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93;高富平. 中国物权法:制度设计和创新[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66.)
在德国法中,间接占有具有为间接占有人提供占有法上的保护、便于物权的取得等功能张双根. 间接占有制度的功能[J].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6, ( 2):44.,但间接占有是否可以和动产物权公示关联在一起,德国学者的著作之中观点则并不一致。比如,在鲍尔·斯蒂尔纳在著作中认为,间接占有人“他们对物的关系虽仅是间接的,也就是通过直接占有人(=占有媒介人)为媒介的,但这种间接的对物的关系,应是具有同等价值的占有”,“这种同等价值性,体现于——但在具体中有突破——占有所具有的全部功能中:保护功能、交付功能与维持功能。”[1]122其中的交付功能,链接到了占有的公示功能参见:鲍尔·斯蒂尔纳. 德国物权法(上)[M]. 张双根,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61-62.,此种公示功能在直接占有的场合,或可以勉强成立参见上文的分析,以及本文第四部分的讨论。,但间接占有是否真的和直接占有完全可以等同视之,并具备公示之功能(以及基于公示功能之假设发挥的转让作用、推定作用和善意取得作用),应该还是需要“对所涉及的各项规定进行解释时才能确定”[1]129。鲍尔·斯蒂尔纳也认识到,“物权公示原则——尤其是涉及其转让功能时——常被突破,这尤其体现在所有权保留与动产担保性让与中!”(参见:鲍尔·斯蒂尔纳. 德国物权法(上)[M]. 张双根,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62.)所有权保留和动产担保性让与的情形下,实际上即发生了动产直接占有与物权性本权之间的错位,公示的功能降低。遗憾的是,鲍尔·斯蒂尔纳既已考虑到如此细致之处,但却并未就间接占有的公示功能进行表态。
德国学者沃尔夫则直接认定,间接占有在动产中和直接占有一样原则上也有公示功能。在第930条、第931条中,法律规定间接占有的赋予即是所有权转移的外部标识。所有权推定也适用于间接占有人(§ 1006 Ⅲ)[4]85。韦斯特曼教授也主张:“根据《德国民法典》的理念,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是一个概念的两个形式。”(参见:哈里·韦斯特曼. 德国民法基本概念[M]. 16版. 增订版. 哈尔姆·彼得·韦斯特曼,修订. 张定军,葛平亮,唐晓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76.)
《德国民法典》第930条规定占有改定,第931条规定指示交付,这两种观念交付形态之下是否可以具有所有权转移的外部标识,按照笔者上文对于间接占有公示功能的分析,答案只能是否定的。第1006条则规定“有利于占有人的所有权推定”:(1)为动产占有人的利益,推定其为物的所有人。但物从前占有人处被盗、遗失或以其他方式丧失的,对前占有人不适用前句的规定,但物为金钱或无记名证券的除外。(2)为前占有人的利益,推定其在占有存续期间曾经是物的所有人。(3)在简单占有的情况下,这一推定适用于间接占有人。间接占有属于不可见的逻辑上存在,需要对其背后法律关系的知情,才可以进行判定,根本不可能发生从间接占有推定所有权的可能,只能是相反的认知路径——依据所有权关系来识别观念上的间接占有。就祖国大陆地区法学界而言,田士永博士早在2002年出版的著作之中,已经援引德国法学家的观点明确质疑了间接占有以及观念交付(或替代交付)的公示作用,尽管没有完全否定这种作用。(参见:田士永. 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以中国法和德国法中所有权变动的比较为中心[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87-188.)但2002年之后出版的物权法著作之中,还是不乏认同间接占有公示作用的观点。此外,高富平教授针对《德国民法典》第1006条的分析意见,与笔者的理解相一致。(参见:高富平. 中国物权法:制度设计和创新[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69.)
需注意的是,即便对动产所有权变动采取意思主义模式的日本法之中,虽然不强调观念交付的公示意义意思主义模式之下,为何还存在观念交付的制度,本来就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观念交付属于形式主义变动规则的例外,带有强烈的“意思主义”特质,本应属于意思主义的统辖范围。本文囿于主题所限,对此问题不做详细展开。,但却被赋予了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参见:我妻荣. 我妻荣民法讲义Ⅱ 新订物权法[M]. 有泉亨,补订. 罗丽,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197-200.
按照上文的分析逻辑,唯有外在的事实才可以具有推定权利的功能,观念交付以及作为其支撑的间接占有,从外观上不具有可知性。此处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所依据的,在日本法上应该是既为事实也为权利的直接占有占有在德国法、法国法上都只是作为(被法律保护的)事实,而在日本法上,被明确作为权利之一种。(参见:我妻荣. 我妻荣民法讲义Ⅱ 新订物权法[M]. 有泉亨,补订. 罗丽,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473-474.),或者说是直接占有背后的任何本权——权利本来就有对抗第三人的力量,而与观念交付及间接占有没有太多关系。
观念交付的公示功能或价值商业实践中,提单、仓单等作为动产权利标志而实行的“拟制交付”,也存在能否公示动产物权的问题,本文并没有涉及,但理论界也不乏探讨。(参见:杨代雄. 拟制交付在物权变动中的公示效力——兼论我国《物权法》第26 条的修订[J]. 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85.),确实只是个美丽的理论构造,如果不是虚构的话。就观念交付的所谓公示功能,孙鹏教授斥之为“彻头彻尾的概念法学思维方法”。(参见:孙鹏. 物权公示论——以物权变动为中心[M]. 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3:173-174.) 不过,汪志刚博士近年来的研究,则似乎在为观念交付的公示功能进行翻案。(参见:汪志刚. 动产交付与所有权转让制度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98-206.)
四、动产物权公示目的之实现:有无可能?
在对动产物权现实交付和观念交付的公示功能进行理论澄清之后,紧接着的一个问题迫使笔者不得不继续思考,此即动产物权公示之目的是否可能实现?
作为观念交付支撑的间接占有,不可能具有公示动产物权的功能,已如上文所述。现实交付过程的公示价值也只存在于理想世界,唯一可能具有动产物权公示价值的就是直接占有,不管其是静态的,还是作为现实交付的结果。现实交付之所以被法学家们认定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手段,其实也是基于占有公示效力的假设,并把此种公示效力置入到动态的权利变动过程当中。(参见:肖厚国. 物权变动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31.)
那么,直接占有是否可以公示动产物权呢?
在传统的民法理论和制度体系当中,(直接)占有作为动产物权公示或推定的方式被得到普遍的承认,并且一直被继受至今。参见:刘家安. 物权法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68;肖厚国. 物权变动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31;孙宪忠. 德国当代物权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10-111.
但即使不考虑现时代各国纷纷出现的动产抵押、所有权保留、动产让与担保等制度,仅考虑传统的所有权和动产质权,就不可能实现所谓的公示。很简单,也正如上文中提到的,从占有——对动产事实上的管领状态——的角度分析,是动产物权人还是动产相关债权人在实施控制,本来就不可能从外观上被得知。即便是直接占有本身,虽然作为自然事实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其是有权占有还是无权占有也同样
需要依靠法律关系来说明,法律只能进行某种推定——推定为有权占有,推定为所有权人(自主)占有,推定为善意占有,推定为和平占有,推定为公然占有等。 此乃学术界的公认,参见: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 [M]. 5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96-397;江平. 中国物权法教程[M]. 修订版.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50-51;崔建远. 物权法[M]. 2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42-143.
即便可以假定所有对动产实施事实上控制的人,都是物权主体,其本权基础到底是所有权还是质权也只能通过法律关系的说明才可以被知悉。对动产物权之所以没有办法进行公示,即源于动产之上物权的非唯一性,因为动产所有权和动产质权可以同时性地存在,相互之间并不发生存续上的冲突,具有“多种可能性”。
逻辑上的描述,或许不能形象地展现动产物权公示之可能与否,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面向,进行细化分析。
从动产物权之消极保护角度上讲,具体的动产物权类型也无需被完全的公示,因为即便是作为事实的占有本身也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直接交易当事人之间虽然不排除依据占有寻求权益保护的可能,但是各种类型的其他名义的法律关系无疑是当事人更方便更习惯的法律依据。动产所有权人或动产质权人固然可以在权利受侵害之际明确自己的权利依据,但这和该权利能否被公示完全是两回事。
从动产物权之行使的角度看,动产所有权的行使一般也只是自己消费、消耗、使用等,不关涉其他人的利益;动产质权的行使首先影响到所有权人的利益,但此种影响可以由动产质押契约的效力解释,属于直接当事人之间的事务,与物权公示无关。动产质权影响动产所有权人之其他债权人利益之时,所有权人本未直接占有动产,其所处的间接占有人地位缺乏可公示性,因此其债权人不可能知悉有其他的所有权存在,除非是所有权人以各种方式告知,但这与公示无关。动产质权人对动产质物进行直接占有,尽管该占有不能公示其质权,但是质权人在行使质权的最重要情形即拍卖、变卖质物之际,最佳、最符合经济理性的选择是所有人的姿态行使处分权,即便告知潜在买受人质权的存在,也是披露了法律关系基础,与物权公示无关。
从物权交易的角度的看,动产之上仅有的所有权和质权两类物权类型留置权是否被作为物权,尽管中国物权法承认,但德国法则持否定态度,笔者于此为了分析德国法的理论,暂且接受德国法的理论。,实际上也几乎无需进行公示。因为只有所有权才是真正的交易对象,质权从发生和转移的角度而言皆从属于特定的债权,不具有完整的交易品性即便在允许“转质”的法律体系当中,第三人所取得的“转质权”相对于原初的质权而言,也是新的物权,而并非质权脱离债权的单独转移。“转质”行为的成立,需要质权人表明其身份,这实际上已经不属于纯粹的外在公示,而属于前文提及的权利信息“展示”,故而此处也不再做详细探讨。,此种从属性本身也并不仅能从物权法理论体系内部得以解释。并且,质权的存在以质权人(通常是直接)占有质物作为前提,同时需要有效质押契约的存在才可以维系,后者并不具有公示性。对于实际控制着质物的质权人而言,若其主张自己对动产拥有质权,则还需举证质押契约的存在,这样倒不如直接主张自己拥有所有权来的方便,而对于动产所有权的存在,几千年来的制度史都以(直接)占有作为推定其存在的依据,因而也无须进行公示。交易第三人对于动产所有权人(或处分权人)身份的信赖,尽管需要结合交易环境或条件来判断,但如果其他信息不为交易第三人所知,直接占有无疑可以提供最佳的认知标准。
再者,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溯源至罗马法时代,在那个时候的民间生活或交易实践之中,动产的直接占有人与该动产的物权主体身份的一致性,可能具有相当高的概率,所以确定占有作为动产物权的公示手段也的确具有极高的实践价值。但在现代经济形态之下,动产的直接占有人与动产物权权利主体之间的不同步性在增加,所有权保留适用的范围非常之广,新兴的动产担保类型的出现,更使得动产上物权的状况更是增添了无尽的麻烦。如此背景之下,再特别坚持占有之于动产物权的公示价值,就失去了生活基础。
相反,不动产物权的公示可能性之所以没有太大的争议,主要在于发达、细致的不动产权利登记制度。不动产之上可设立的物权类型要远远超过动产,但登记制度却可以确保各权利可以和谐共处于不动产之上。虽然实践中还会发生登记物权与真实物权相背离的现象这里实际上触及到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即不动产物权与登记公示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不动产物权是否必须得登记,或者只有登记的权利才是物权。相关问题的探讨,参见:谢哲胜. 物权的公示[C]//王文杰. 变动中的物权法.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14.,但对于不动产潜在的交易当事人而已,对于不动产物权信息可以很容易知悉,各登记物价人也非常清楚自己权利的范围。其实,从不动产物权消极保护的角度上看,承担消极不作为义务的第三人群体,仅依凭他人直接占有不动产的事实就应该谨守自己的行为界限,无需不动产物权公示机制的运作。很难想象,承担消极不作为义务的第三人群体,会每天主动查阅或关注不动产登记簿的物权变化信息,以选择适当的权利空白期介入,或者,也很难想象,此类第三人群体会因为不动产物权类型的不同而进行选择性的干预。不动产物权的交易第三人,则可以很容易通过登记信息,掌握相关的不动产权利信息,知道其所交易的对象物权,归属于谁,权利内容为何。
综上可知,以直接占有直接占有作为占有的最初始状态,自从罗马法时代就要求“体素”和“心素”的同时存在才可能,否则只能构成完全作为“客观事实”的“持有”,因为“心素”同样不具有外在性。所以严格来讲,即便进行动产物权的推定,也只是基于“持有”的外观,甚至都达不到占有的高度,尽管“持有”的判断也需要考虑时空情势等周遭因素。本文暂且忽视持有与占有之间的差异。
为基础确立的动产物权公示理论,根本不太可能实现完全的物权公示在有的学者看来,动产物权之享有或者说处于静态时,不需要进行公示,动产物权公示仅与物权变动有关。(参见:汪志刚. 动产交付与所有权转让制度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172.) 不过,物权变动的公示,同样需要回到占有的基础之上,所以此处的分析结论并不受实质性影响。,最多只是对于“占有人——物权人身份一致”概率的经验性判断,法律并基于此确立了权利的推定制度,因而也无需特别强调动产物权之公示。参见:高富平. 物权法讲义[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3.
在相对迟缓、封闭的社会条件之下,“占有人——物权人身份一致”的概率会高一些,但在经济快速运转、消费方式多样化的时代,必须重新认识此概率的高低鲍尔·施蒂尔纳也意识到,“在今天,从占有上推断所有权反而比以往更缺乏正当性了”,但并没有放弃传统,认为“在实际生活中,交付还是被看做所有权让与已经进行的表征。”(参见:鲍尔·施蒂尔纳. 德国物权法(下册)[M]. 申卫星,王洪亮,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91.),或许至少应该对不同的经济领域分别
进行经验判断。肖厚国博士曾经在讨论占有之公示效力时指出,在民事交易和商事交易领域,应当区别不同的信赖结构。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强调对占有公示效力应该在民事、商事交易领域进行不同处理,但此种区分对待的思路值得赞同。(参见:肖厚国. 物权变动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41-342.)
五、交付公示原则确立的方法论检讨
在分析了动产现实交付、观念交付的公示性不足,检讨物权公示之可能性之后,自然而然地触及到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此即:依笔者的粗浅分析就可以得出的如此简单的认识结论,何以在德国法系之中却不被采纳,而是构建了复杂的交付公示理论来对社会生活现象进行抽象描述和再解释?
罗马法时期,对物之所有权的继受取得,虽然早已在要式买卖、拟诉弃权之外确立了(万民法领域适用的)交付移转的规则(C.2,3,20),但关于交付,罗马法同时承认了后世所称的现实交付(单纯交付)、观念交付(短手让渡、长手让渡、占有转让协议)、拟制交付(象征性让渡、证书让渡)等交付样态。参见:桑德罗·斯奇巴尼. 物与物权[M]. 2版. 范怀俊,费安玲,译. 纪蔚民,阿尔多·贝特鲁奇,校.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9-95.
罗马法上交付的法律效果,即包括纯粹的占有移转,也包括所有权的移转。对于后者而言,还需要其他几项要件:有权让与、具有转让和接受所有权让与的意愿、存在正当原因。参见:江平,米健. 罗马法基础[M]. 修订本3版.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05-206;黄风.罗马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37;陈朝壁.罗马法原理[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72-273;周枏. 罗马法原论(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63-366;比德罗·彭梵得. 罗马法教科(2005年修订版)[M]. 黄风,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59-161.
动产交付样态的多样化,以及动产所有权转移在交付之外所需要的其他条件,或者说因为“交付在法律上是一种透明无色的行为。它根据行为实施时的具体情况得到法律上的颜色”[7],这是罗马法的法学家们没有在理论上把交付确立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的原因,此点可从后世的罗马法研究著作中都可以得到某种印证。在以上所引罗马法研究著作之中,均未提及动产交付与物权公示之间的必然联系,虽然不能完全否认二者之间的关联,但显然可以印证交付公示并未被确立为罗马法的原则。
德国物权法理论构建的主要素材,源于对罗马法文献和日耳曼习惯法的融合,但不管罗马法还是日耳曼习惯法,都只是简单商品经济时代的产物,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简单商品经济时代,动产之上设立的物权种类非常有限,对于动产的使用方式或许也仅限于自主消费或自主使用此种假设其实本身也很难成立,因为至少从制度上讲,借用、租赁等契约类型,早已存在于古代的法律之中。,动产直接占有的移转(即现实交付)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标示着动产物权的转移,尽管该转移过程并不具有外在的可观性。如果说动产直接占有的移转可以勉强支撑动产物权交付公示原则的话,间接占有作为替代交付的最重要制度支撑,完全不具备直接占有的外观性,不管是交付的过程还是结果都只是在观念世界里运行,但德国的法学家们仍然坚持间接占有与直接占有的“等同性”。如此一来,就使得动产物权的交付公示原则越来越远离生活的常态,而生活经验的适当提取恰恰是民法及物权法理论构建的最直接渠道,过于脱离生活的制度构建就有可能与制度的规范意旨出现很大的裂缝。
对于动产物权交付公示原则的思考,或许最终还是要回到德国民法典、民法理论构建的方法论上来,而其中首先需要注意的问题便是物权法在德国民法典体系中的位置。
德国民法典在财产法方面的最大特色,就是实现了更加抽象的物债二分,物权和债权各自作为单独的一编而存在,这样,并且置债法(债务关系法)于物权法之前。此种体系安排的目的,用德国学者的话来说,就是要在交易过程之中实现或体现物权的价值或功能。参见:罗尔夫·克尼佩尔. 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M]. 朱岩,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42, 244-245.
如此定位物权法,对于不动产而言效果如何,本文暂且不论。对于动产而言,假若动产物权想在交易中保持其权利本质属性的固定状态,或者说在交易前后保持其权利状态的同一性,从而彻底实现动产物权的价值,逻辑上可行的办法就是使得交易的过程具有所谓的公开性、透明性——如此一来,交易前后的物权清晰性就得以维持不变。因为单就动产现实交付的结果而言,直接占有本身在动产物权变化前后并无外观上的本质差异,除非知悉物权转移的过程,否则不可能从直接占有的外观得知动产物权是否变动,上文已有论述。此外,由于动产之上可设置的物权类型极其有限,动产交易也主要在动产所有权移转(即货物买卖)的意义上展开,保证动产所有权主体的明确性就足以达致物权实现的目的。参见上文对于动产质权交易品格的分析。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交付公示的原则就被确立,不管其是否仅仅可以存在于逻辑之中。
此外,众所周知,在18、19世纪德国民法建构的过程之中,带有伦理色彩的自由主义成为法学家们普遍信守的教条参见:罗尔夫·克尼佩尔. 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M]. 朱岩,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1-46.,而此处的自由主义更多地强调意志的自由参见:罗尔夫·克尼佩尔. 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M]. 朱岩,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5, 62-66. 实际上,意志自由作为法律行为的观念性基础,几乎支撑了德国民法的整体框架和绝大多数具体制度的设计。,因此也可以直接称之为意志主义。意志主义法学发展至极致即成为备受后世批评的概念法学,耶林则调侃为“概念的天国”。按照维亚克尔的理解,自由主义(意志主义)的法观念不单影响到了债法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制度化,也影响到了德国物权法的制度设计。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 近代私法史(下册)[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461-462.
从私权变动的角度看,自由意志理论固然可以在逻辑和观念上证成私权(物权)变动的合理性,直至演变成为德国法上的物权行为理论,但占有转移的要件同时也一直被普遍要求。学术史方面相关知识的精彩说明,参见:朱晓喆. 论近代私权理论建构的自然法基础——以17世纪欧陆自然法思想为背景[C]//桑德罗·斯基巴尼,徐涤宇. 罗马法与共同法:第一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13-321.
不过,很明显的是,自由意志与占有转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强烈的紧张对立关系,前者乃是抽象的观念,后者则为具象的事实。从物权公示的角度来看,对前者强调的越多,离公示的距离就越远——最后,在意志主义观念支配之下,动产直接占有的事实上移转伴随着物权行为理论被赋予了所有权转移的任务,并且强调此行为可具有公示物权变动的功能——但在假定直接占有可以公示动产物权公示的前提下,前者本来完全可以从客观的角度进行认定,无需另外的“物权合意”就可以实现动产物权公示的功能,所谓的债权形式主义或许就是遵从这样的逻辑。本文无意全面否认物权行为理论,只是从动产物权公示的角度出发认为,物权行为理论反倒是增加了动产物权公示的解释难度,因为“物权合意”本身不具有外观性,尽管从物权公示所保护的第三人的立场来看,实践效果没有太大的差别。孙鹏教授早在2003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之中,即用相当的篇幅否认了物权行为与物权公示之间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参见:孙鹏. 物权公示论——以物权变动为中心[M]. 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3:99-106.)
故而,此种理论假设,在观念世界里或许可以成立,但在现实生活情景之中,动产之上的物权根本不可见,动产物权变动的“合意”也属于无色无味,除非当事人明确表示,否则只能是依据动产被管控的事实或其他具体情形进行一般性的推定参见:曼弗雷德·沃尔夫. 物权法[M]. 吴越,李大雪,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67.,所谓动态的现实交付过程更是不为交易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所知悉。
如果说现实交付的公示意义只是部分反映了意志主义的法学理念,那么,观念交付所预设的公示功能则完全只能存在于意志世界之中,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虚幻性”。如此虚幻的观念行为,却仍被赋予了权利公示的功能,对此,只能用意志主义的理论进行解释,因为如果从经验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根本不可能存在如此不符合生活常理的法律理论。
在意志主义法理念的主导之下,物权公示原则的确立实际上更多地是从物权主体或物权直接交易当事人的视角去看待物权的绝对性或排他性效力问题,认为特定人的行为就可以被他人所感知,或者其真实意愿可以被他人所了解,认为自由意志本身就可以或应当发生客观效力,或导致“物权取得人的积极信赖”。参见:汪志刚. 动产交付与所有权转让制度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91-198.但正如上文所述,物权公示的实践目的是为了方便潜在的交易第三人知悉物权的信息状况,或者为了潜在的承担消极不作为义务的第三人知悉物权的存在。如果法学家们或立法者站在上述两类第三人的角度进行思考,应该很容易明白,立法的焦点定位于确立物权可以对抗第三人的规则即可,而无需建立抽象的物权公示原则,更无需结合物权行为理论进行体系化解读。董学立教授也认为,公示不是物权行为的构成要素。(参见:董学立. 物权公示,公示什么?[J]. 比较法研究, 2005, (5):20.)
从第三人立场的角度,实际上是从物权义务人的视角来形成基本的规则,具有更明显的实用主义取向。
当然,意志主义在动产物权之上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完全消极的。现代经济条件下的所有权保留、动产让与担保等,尽管发端于市场或商人们的信用需求,但其法律上的构造或变化过程,毫无疑问需要所有权在观念上的变动所有权的观念属性及其变动,笔者另文有涉及。,意志主义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论证依据。法国关于财产权变动采行的意思主义模式其实本来也是意志主义法学的结果,但法国法学家们对于对抗规则的确定,完全可以进行实用主义或现实主义面向的解读;或者可以换句话讲,就财产法而言,法国民法实际上并没有走向意志主义的极致。
只不过,意志主义对于民法理论或制度的体系化构建作用,并不是完全可以解释民法制度上的一切,很多情形之下,或许还必须回到作为理论抽象之现实基础的生活经验上来,并检讨法律抽象的合理程度。如果不能从生活经验的视角认识民法的制度规则,那么相关理论研究难免就会失之于无用,或仅停留在观念世界当中。
六、结论:功能主义导向的制度设计
动产物权的交付公示原则,经由对德国民法学的继受或移植过程。被中国学者普遍接受,似乎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但经由实践面向的观察和对动产交付具体规则的解析,可以认为,动产交付似乎根本起不到公示动产物权的作用,无论是现实交付抑或观念交付,皆概莫能外。在笔者看来,德国法学家们之所以对动产交付赋予了公示物权的功能,属于意志主义法理念运用到极致的产物。尽管直接占有移转具有外观性,但过于意志化的解读使之承担了不应该承担的重任。对于动产而言,只有回归到物权法构建的前提——占有,才可以准确把握物权公示的精妙或命门,从而利于搞清楚物权公示与物权对抗力之间的区别、差异与联系。物权立法究竟应该采取物权公示主义的立场,还是对抗主义的立场,学术界本已有很多讨论,在笔者看来,实有再讨论的必要。
从物权公示的制度设计上讲,虽然不能否认意志主义观念对于体系构建的积极意义,但是在主体自主、财产权自由等观念已经被现代民法普遍接受,尤其是现代宪法学已经替代了民法学在价值宣扬方面的功能的背景之下,对于民法制度的设计,更多地应该从功能导向的立场进行评价。唯有面向实践,面向交易形态日益变化多端的经济环境,才可以认识清楚物权公示的价值之所在,及其作用机制运行的支撑点,或者才可以更新法理念。
参考文献:
[1]鲍尔·斯蒂尔纳. 德国物权法(上)[M]. 张双根,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61.
[2] 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M]. 5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85.
[3]史尚宽. 物权法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8.
[4]曼弗雷德·沃尔夫. 物权法[M]. 吴越,李大雪,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66.
[5]王泽鉴. 民法物权[M]. 2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6-97.
[6]哈里·韦斯特曼. 德国民法基本概念[M]. 16版. 张定军,葛平亮,唐晓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75.
[7]巴里·尼古拉斯. 罗马法概论[M]. 黄风,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23.
Abstract:Delivery public notice is a concept imported from German property law since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which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by Chinese academics and frequently cited in literature. However, either physical delivery or constructive delivery cannot attain the purpose of public notice for the change of title. It is still debatable about whether the title of property can be publicized. Establishing delivery public notice principle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particular methodology, while the review about the practice is good for the formation of new institution concepts.
Key Words: delivery; possession; delivery public notice; physical delivery; constructive delivery
本文责任编辑:许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