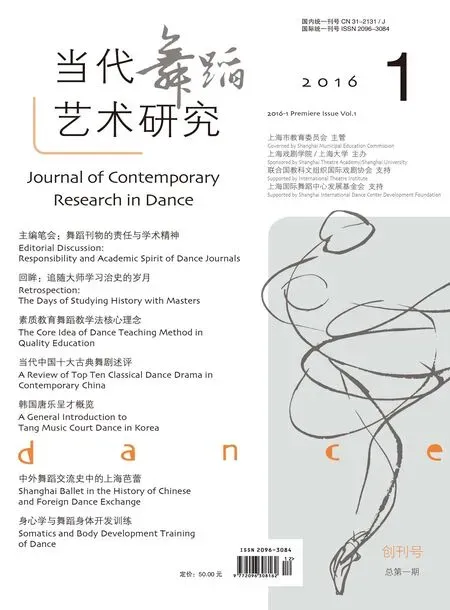舞剧《泥人的事》编剧谈
江 东
舞剧《泥人的事》公演了,作为该剧的编剧,目睹着、历经着该剧创作的全过程,不但感受到了舞剧创作的艰辛,也品尝了收获成果的快乐。
2013年末,在天津首演之后举行的研讨会上,来自京津两地的各路前辈专家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这给创作者们带来莫大的鼓舞。笔者虽然十分看重来自观众的强烈反响,但专家们对业界的熟知、对这门艺术的熟悉,却能带来特别的启发和别样的兴奋。特别是听到天津当地的戏剧专家、天津文化局前副局长高长德先生的评价,更是觉得十分受用。他说,多少年来,天津艺术界一直都在思考、实验着一个旗帜鲜明的主张和众人心中的理想,那就是在北京文艺界有了“京派”、上海文艺界出现“海派”之后,作为一个直辖市,天津应该如何探索和突出自己的艺术风范?虽然在地理上与北京为邻,但在文化上天津是否拥有与北京相异的文化特点?这些,都是天津艺术界多年来苦苦思索并努力实践但其结果却并不太尽如人意的问题。看过舞剧《泥人的事》,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上述那个在津门戏剧舞台一直没有太好结果的目标,却在一部舞剧中得到了相当好的回应和体现,这令他大喜过望。因此他认为,由天津歌舞剧院打造的原创舞剧《泥人的事》,不但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均达到了相当不俗的高度,也让沉寂多年的天津歌舞剧院歌舞团一举获得了“咸鱼翻身”的机缘,同时,这部舞剧在展现天津文化风味的层面上可以说是做足了文章,让“津风津味”实实在在地矗立在了艺术舞台之上。
对于这样一个评价,笔者是有些始料未及的。因为对于这样一个目标的认识和追求,笔者远没有像天津本地的艺术家那么自觉,那么用心。当然,《泥人的事》这部舞剧今天所取得的这样一个结果,最主要的功劳归于该剧的总导演邓林先生,正是他对舞剧艺术的精到理解以及长期以来建立的对于天津人文风物及其色彩的把控能力和力度,才让该剧收获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沉甸甸的果实。现在回想起这个剧目的生成过程,一切仍历历在目。
一、缘起
笔者和中央民族歌舞团国家一级编导邓林先生之间的合作,应该是基于两个基础:一个是邓林导演一直都在惦记着、琢磨着要为天津歌舞剧院歌舞团创作一部舞剧作品。这是因为他与天津歌舞剧院歌舞团的良好合作关系是由来已久的,之前他就曾应邀为歌舞剧院芭蕾舞团创作过一部效果不俗、评价不错的芭蕾舞剧——《精卫》,并从那时开始为歌舞剧院歌舞团的一台台晚会贡献了他的智慧和精力。歌舞剧院歌舞团领导希望邓林导演能为该院歌舞团创作一部舞剧作品,这个殷切的期望让邓林导演始终铭记于心。只是让他一直无法释怀的,是始终没有能够觅到一个适合歌舞剧院歌舞团演绎的舞剧合适题材,为此他一直都陷于苦苦的寻觅之中。
第二个缘由应该是我们之间的交谈。应该说,我们在一起聊天是很信马由缰的,也颇投机。当聊到对“民国风骨”的认同时,我们惊异地发现我们的观点是如此一致。要说民国时期的中国人活得是很精彩、很自在的,那个时期所特有的社会环境和健朗的社会风貌,是中国社会很难得的。从那个时期诞生的一批知识分子身上,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他们所具有的那种顶天立地的傲骨。对此,我竟和邓林导演有了共识。他希望,我们合作的舞剧应该从这个角度展开。
我想当时邓林导演一定是颇为高兴的,因为他终于为歌舞剧院歌舞团寻觅到一个十分对位、十分理想的题材。说这个题材对位和理想,是因为在偌大的中华版图上,能在民国时期这个角度上做文章并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或许非天津莫属。
可以说,20世纪之初,开埠的天津成为中国连接西方的门户。在这里,西式文明一时引领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风气,而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也让这一处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城市呈现出全新的发展势头。在那一时刻,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精英阶层与普罗大众等二元对立的概念及社会现象,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视野极为广阔的社会空间。这样一个社会图景,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它成为了我们舞剧故事的起点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和邓林导演都一致认为,我们的故事应该发生在这样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变迁之中。
邓林导演跟我提起过,他曾为歌舞剧院歌舞团创作过一个男女双人舞,叫作《泥人的事》,还获得过一个什么奖项。并表示,可否从“泥人文化”中寻找契机。应该说,今天《泥人的事》这部舞剧的整体走向和最终定名,都与他的这个点拨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因为从那一刻起,我们就确定了整个故事的基调和走向,并为这部舞剧确立了三个文化基点,分别是:天津风范、民国气质、泥人文化。
带着这一最初的设想,我们进入了创作。邓林导演首先专程陪我两赴天津进行实地采风。在歌舞剧院歌舞团领导层的鼎力支持下,我们在短时间内突击性地探访了天津文化的方方面面,虽然很有些走马观花的嫌疑,但这些颇接地气的具体考察活动,让我们不但对天津的风土人情和文化色彩拥有了最为直观的切身感受,更让我们对即将展开的舞剧创作本身有了更为脚踏实地的实际认识。
应该说,当初的第一稿与今天的完成稿,在故事脉络及其发展走向上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对我而言较为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能够完全按照我们之前关于“民国风骨”的那个思路展开,而是根据故事和人物的特定性和完整性重新结构出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脉络,之前那份让我们血脉偾张的知识分子情结,并没有成为我后来故事的核心,而是为了故事本身的可看性最终放弃了这个后来看起来有些过于理想化的原初想法。此举也让我后来意识到,有些情况,虽然出发点很好,但实际未必能够走得下去。
对于笔者的初稿,邓林导演的反馈显然很兴奋,不但很认可故事结构,还说其中有些情节甚至让他感动得立刻起了浑身的鸡皮疙瘩。显然,他心中涌起了难于遏制的创作冲动。他的这个正面反馈,可以说是一剂强心针,让笔者的心踏实了不少。
但接下来的情况并不顺利,在不断对剧本进行完善时,走了很多弯路,甚至二稿和三稿都渐行渐远。关键时刻,邓林导演提供了很有帮助的启示和点子,对在山重水复中不断迷失方向时重新找回正确的路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前前后后六易其稿,终于定稿。其间来自邓林导演的耐心和自始至终的信任与配合,让笔者至今都记忆犹新。应该说,我们之间的合作是颇为有效的,邓林丰富的编导经验和易于相处的性格,为我们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经过两个月的排练与合成,舞剧《泥人的事》这部承载着多少人梦想的心血之作,终于在2013年12月3日于天津大礼堂迎来了它的第一声啼哭。一部原创的大型舞剧,从此出现在了中国当代舞剧事业的生态环境之中。
不足两个月的排练时间,是邓林导演再次咀嚼剧本、不断完善剧本的一个过程,虽然今天有些情节的处理并没有按原先设计的方向进行和发展,但还是完全可以理解并支持的,因为他也是在吃透了剧中各人物的个性特点之后做出的这些决定,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对于其中某些环节,虽然我们之间也有分歧和争论,但并不影响对他所秉持的艺术主张和艺术想象力的敬佩。因为,正是有了像他这样能够坚守自我的灵魂式人物,才让我们在舞台上看到了这么一部不同寻常的舞剧作品。
二、作品
舞剧《泥人的事》,是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有舞、有剧。用舞说剧,透过剧来欣赏舞,这也是邓林导演的特别追求。他在以前的创作中,主要攻的是舞;而在这部戏中,剧成了考验他功力的核心问题。通过坚持和摸索,他不但希望能在舞剧的形式因素上有所开掘,更希望能创作出一部很接地气、受百姓欢迎、百看不厌的舞剧作品。于是,这部舞剧中“剧”的成分便对整部作品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故事的完整性和易于观者顺利而快速地融入,笔者在故事自身的戏剧性上动了很多脑筋。本着一波三折、大起大落、悬念不断、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些编剧原则,讲述出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同时通过这个故事的讲述让观者体会到人生的苦难对于人的成长和历练会有多么大的作用这样一个主题。
在《泥人的事》这部舞剧中,我们总共设置了六个主要人物,他们三对刚好来自三个背景差异很大的家庭。笔者对此设计的初衷是:“泥人齐”父女是天津劳动人民的代表,也是泥人文化的传承者,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个性的承传者;丁老板夫妇则来自城市新兴的买办阶层,他们的开明和教养是新型社会的榜样。这两家人之间所形成的对立关系,让故事本身便有了戏剧张力。第三个家庭是本剧的男女主人公,从山东农村逃难而来、到天津闯码头讨生活的一对农村小夫妻——小五和秀儿,他们的故事也很抓人,聋哑的妻子刚有了身孕便在兵荒马乱中被拐卖,而这个悬念一直让舞剧处在紧张的张力之中。于是,三个家庭彼此的关联和人物特定性格的反差,让这部舞剧有了很好看的故事基础。
几个主要人物的定名也是有一定寓意的。在津门泥人界,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是“泥人张”。而在我们实地考察之后,笔者决定为剧中的泥人大叔采用“齐”这个姓氏,赋予这个形象以中国传统伦理代表的象征意义。在他身上,应该体现和传承着典型的温、良、恭、俭、让的儒家精神。因此,从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提取出一个“齐”字,还是蛮贴切的。
他的女儿齐杨柳一角儿,在初稿中不曾有后来是邓林导演建议,设置一个与秀儿相对立的人物,以使剧中人物所反映出来的不同性格更加全面,才让笔者想到了这个人物。她的名字显然与我们走访盛产天津年画的杨柳青直接相关,甚至在笔者的原作中,还出现了“年年有余”的大头娃娃年画。而这个人物的性格基调,恰巧是我和邓林导演在天津的大街上偶然看到一位性格豁达开朗的天津大姐时捕捉到的。那位大姐身上所特有的“虎妞”范儿,让我们感受到了天津女性身上一种唯津门女性所特有的敢作敢当的气质。后来证明,这个人物还是相当出彩的,也帮故事完成了一些特定的叙事任务。
而丁老板姓氏中的“丁”字,是考虑到他是一个灵通八面的人物,“丁”与“灵”发音近似,同时行书方便,就此采用。笔者从一开始就没把这个人物脸谱化,在考虑人物的定位时,刻意避免了当下中国舞剧故事中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式人物设置,希望借助他们在故事中的行为及其线索来展现人物之间自然而然的关系和矛盾走向。剧中的丁老板,是一位受过良好西式教育的开明买办,绅士范儿很浓,家里的摆设也很西式、华贵。他的潇洒和圆滑与齐大叔的敦厚和踏实,形成了这两个人物在个性上的对比,同时也是我们所感受到的天津人性格中的另一面:精于世故、八面玲珑。
在舞剧中十分惹眼的丁太太这个角色,在笔者的最初设计中只是个陪衬,她身为一个大家闺秀,民国时期的良好端仪都极好地体现在她雍容的仪态之中。只是由于没有子嗣才让她变得心理暗淡而举止卑微,她内心无限的矛盾和纠结,让这个人物很有悲剧感。当然,对如今舞剧中这个人物的处理和表现,编导和演员的二度、三度创作和完善其功劳是极其明显的。
来自农村的男一号小五,之所以不是小二、小三、小四,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名字显示他来自一个旧时的多子农家,他是由于家中多子而没有起码的条件养活自己,才被逼外出谋生。
最后,小五的聋哑妻子秀儿,是我们这部舞剧中最动人、最有戏的一个形象。她楚楚动人的面容,坎坷多难的经历,让人最心酸、心痛。之所以名字中采用了“秀”字,一是因为这是中国农村妇女中最常见的名字,同时也希望借助这个字传达出这是一位容貌秀丽有加的女性,而正是这么一位秀外慧中的女性的悲剧,才让这部舞剧的悲剧意识和情感达到了令人心碎的制高点。
剧中的六个人物就是这么建构起来的,虽然所有这些名字在舞剧的表现中都不会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些名字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舞台上,但通过这些名字的设置,能够显现出当初笔者在为这些人物设计具体心路时的一些侧重。
整部舞剧的故事无疑还是要抓人。笔者在设计故事的各个情节时,始终本着一波三折的出发点,尽可能地提高故事的可看性。曲折迂回,环环相扣,一个又一个悬念的不断出现,让全剧获得了一个意料之外、但情理之中的故事走向,并最终重重地叩击了观众的心扉,让观众的眼泪情不自禁夺眶而出。故事是有些离奇的,但由于编织巧妙,又非常合理,这是笔者自觉比较得意的,也通过这个充满悬念的故事基本上传达出了本剧的基本立意:历尽磨难铸就如虹人生。今天看来,大家对这一点还都是认可的。
比较遗憾的是,虽然经过苦苦思考,笔者还是没有为这部舞剧找到一个更好一点的剧名,最终经过三思还是沿用了邓林导演之前那个双人舞作品的名字。之所以如此,也是想到了许多美国电影的名字本身实际上也都是非常朴实无华的,很多名字是经过了汉译的加工才有了后来的模样的。这么一寻思,《泥人的事》这个剧名虽不太响亮,倒也实实在在,有故事感。
三、创造
我们通过舞剧《泥人的事》的创作,交出了对于中国舞剧建设和发展的一个答卷。作为一名舞评家,笔者认为这部舞剧有许多闪光之处,当然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笔者对邓林导演的结构能力是极为佩服的,他对于舞剧结构的运筹和拿捏,让这部舞剧的结构十分流畅而舒服,既没有突兀感,也没有断裂感,而是一气呵成,既很好地叙了事,又突出了各人物的基本性格,还透过舞蹈表现出了难得的天津味道。这种驾驭结构的能力,显现出了大家风范。
还有一点让笔者非常喜欢的是该剧的舞美及其表现方式。最初被深深吸引的,是这部舞剧在舞美设计上的简洁和练达,那些在设计和制作上巧夺天工的布景极其富有空灵感和质感,让笔者惊叹它们在做工上的无比精美之余,更感受到了一分扎扎实实的天津味道,这让笔者对邓林导演的艺术品味和气质以及舞美设计者张定豪、刘小舟所具有的艺术灵性,有了相当的佩服之感。然而这还仅仅是第一步。当笔者看到舞美手段居然参与到舞剧的叙事中来,更大吃一惊。在这部戏中,所有的舞美元素都成了活的、运动着的语言表述,它们在虚实相生的自如变换中,将一份难得的、高级的艺术感受呈现出来。
“高级”!这是笔者跟邓林导演最初磋商时就做下的一个约定,我们彼此都希望通过我们的舞剧能为今天的舞剧舞台提供一个具有高级艺术形态的范例。虽然,尚不知我们的这份用心及其追求是否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和回应,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自鸣得意,因为我们不满意今天中国舞剧作品中的那些无谓堆砌,并试图透过我们的努力让其放射出更强的艺术之光。不敢说我们的这份投入是否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从眼下观众及其他专家的评说中,我们得到了初获好评的结果和感悟:我们的市场是需要这样的艺术作品的。当然,为了能继续获得一个更好的结果,我们还需付出数倍的努力。
感谢舞剧《泥人的事》让笔者收获了更多的艺术感悟!更祝愿这部舞剧能凭借着众人舞动的翅膀,飞向更高的艺术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