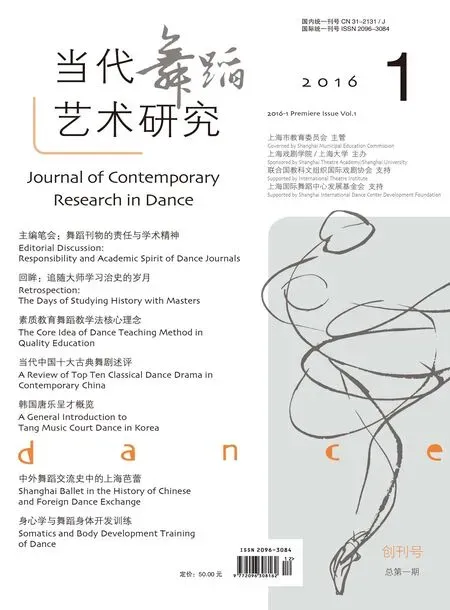当代中国十大古典舞剧述评(上)
于 平
引子:中国古典舞剧从学习传统戏曲遗产启程
从语言形态上来类分“中国舞剧”,我们通常将其分为中国芭蕾舞剧、中国民族舞剧和中国当代舞剧。相对而言,与中国芭蕾舞剧、中国民族舞剧有可以识别的“类型化语言”不同,中国当代舞剧是“非类型化语言”的舞剧。所谓“类型化语言”,是指这类舞剧语言具有特征鲜明的历史文化风格,积淀着一定区域、一定民族的历史文化。就“类型化语言”的中国舞剧而言,“中国芭蕾舞剧”其实是西方芭蕾、特别是俄罗斯芭蕾在表现中国题材时的“学派构建”;而中国民族舞剧,就目前的剧目构成而言,主要包括三类,即中国古典舞剧、中国民俗舞剧和中国少数民族舞剧。这里所说的“中国古典舞剧”,最初所依托的“类型化语言”,主要是来自京剧、昆曲的戏曲舞蹈;后来也逐渐拓展到由敦煌壁画彩塑、南阳汉画像石(砖)创生的所谓“敦煌舞”“汉魏舞”。今后是否还会有“昆舞”(昆曲舞蹈)、川舞(川剧舞蹈)、“高甲舞”(高甲戏舞蹈)等“类型化语言”来创生“中国古典舞剧”,只能由类型特征鲜明、语言表述系统、动态风格稳定的舞剧作品来自证了。
其实,“五四”以来的中国民族舞剧创作,最初用的就是“京戏的技巧”(田汉语)。姜椿芳先生在《创立中国舞剧的最早尝试》[1]一文中,认为这个“最早尝试”是俄籍犹太人阿龙·阿甫夏洛穆夫创作的《古刹惊梦》。这部舞剧1935年首演时叫《慧莲的梦》,由长期在上海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女作家华尼亚编剧,表现的是青年男女冲破封建桎梏而自由相爱;1941年已然逐步完备的演出版本定名《古刹惊梦》,聂耳在观看首演后曾评论说:“这是一个三幕哑剧,音乐的伴奏、布景、服装、演技可以说是根据着京戏的技巧,以较新的形式编制而成的……我想,‘改良国剧’从这条路跑去,也许是对的吧。的确,许多京剧里的舞姿、武行,要是给以音乐节奏化,着实可以发现一些中国音乐与舞蹈的新的知识。”[2]
也就是说,创立中国舞剧的“最早尝试”不仅是一部“根据着京戏技巧”的古典舞剧,而且是一部“冲破封建桎梏而自由相爱”的中型舞剧。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尝试”的中国民族舞剧,则是学习优秀戏曲遗产的小型舞剧,被称为当代中国民族舞剧创作的“头三脚”。据李百成《忆“头三脚”,并由此想到的》一文:“所谓‘头三脚’,指的是50年代中期,在舞剧《宝莲灯》上演之前,由中央实验歌剧院演出的三部小型舞剧,即《盗仙草》《碧莲池畔》和《刘海戏蟾》。”[3]新中国成立后,也即当代中国民族舞剧的“头三脚”,在题材选择上明显受传统戏曲“折子戏”表现形式的影响,在主题把握上则高度重视题材所寄寓的“人民性”。李百成在谈起“头三脚”时说:“从形式结构上看,更像是中西合璧的产物……1954年,苏联丹钦科音乐剧院来华演出,介绍了一系列苏联优秀舞剧,这就成了‘头三脚’(这三部小型舞剧)的催生剂——比如对于舞剧艺术基本概念的认识,对于舞剧结构方法、舞剧与姐妹艺术关系的认识,还有舞剧语言的选择与运用,舞剧中舞段的分类与布局,舞剧音乐的戏剧性结构以及运用现代舞台手段、发挥交响乐的强大表现力……都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3]这些“最早尝试”告诉我们:中国民族舞剧的“舞剧”概念是“舶来品”——是聂耳所说的“以较新的形式编制而成”,是李百成所说的“更像是中西合璧的产物”;而就其舞蹈语汇来说,是向传统戏曲遗产以及戏曲改革经验学习的产物。
一、《宝莲灯》:创造出反抗封建礼教的舞剧典型
说到大型古典舞剧,首当其冲的是《宝莲灯》。这部由中央实验歌剧院舞剧团首演于1957年岁末的“大型民族舞剧”,被《中国舞剧史纲》称为“公认它是鲜明成型的中国第一部大型的民族舞剧。[4]”也就是说,当代中国首部大型民族舞剧已问世半个世纪了。“史纲”第三章《民族舞剧的初建成型》一节中谈到了《宝莲灯》,指出“是根据传统戏曲剧目改编的……取消了戏曲中的蔓枝旁节,概括为《定情下凡》《沉香百日》《深山练武》《父子相会》《斗龙得斧》和《劈山救母》六场戏,集中表现三圣母为争取人的合理生活而斗争的主题……《宝莲灯》塑造了六个对比鲜明的舞剧人物形象:三圣母的温柔多情、刚毅果敢,为了争取婚姻自由对恶势力英勇不屈的、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品格;沉香稚气可爱的形象和勇武顽强的精神;霹雳大仙见义勇为、慈爱与豪迈的性格;哮天犬的阴险凶恶,以及对主子摇头摆尾的献媚丑态……(剧中)刘彦昌的文雅多情、二郎神的神威霸道的形象虽然比较鲜明,但其舞蹈的戏曲痕迹较重,‘舞剧化’不足。这也是民族舞剧最初的难题之一。”[5]
当年,对于舞剧《宝莲灯》最重要的剧评,就是隆荫培所作《试论舞剧〈宝莲灯〉的演出》。其中写道:“舞剧《宝莲灯》的改编,我认为基本上是成功的。保留了它原来积极性的主题及反抗精神,删除了存在于这个传说中的封建糟粕。由于舞剧这门艺术形式的特殊要求,编导者把剧情更加精炼与集中,取消了刘彦昌中状元、娶王桂英为妻,及沉香、秋儿打死秦官保和二堂放子等情节。(舞剧)在矛盾的发展和戏剧冲突的安排方面也是较为紧凑的:如第一幕第一场结尾,就正式展开了二郎神与三圣母的斗争;第二、三场紧接着使矛盾发展到了高潮,而且这个高潮是在大家欢舞作乐的气氛中宝莲灯突然被盗、二郎神捉走三圣母这样一种强烈对比的情景下造成的……舞剧作为一种戏剧艺术,它的内容不仅依靠情节的结构表达出来,主要还要看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舞蹈的处理如何……我认为三圣母的温柔多情和刚毅果敢是被演员赵青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了的;再通过她表情的细腻和感情控制的适中,就创造出一个典型的、在封建社会中举起对封建礼教反抗旗帜的生动的妇女形象……”[6]
在上述剧评中,隆荫培认为:“这个舞剧还不能给观众以欣赏舞蹈的满足。如第一幕第一场三圣母和刘彦昌的表演也多限于手势和哑剧动作,没有一段足以尽兴的相互抒发感情的双人舞……在第一幕第三场欢乐的场面里,显然编导者是注意和加强了对舞蹈场面的安排……但三圣母和刘彦昌的双人舞却显得非常不协调——本来‘舞长绸’是非常美丽动人的,可是三圣母却用长绸来和刘彦昌双人对舞……观众也都感到刘彦昌在这段舞蹈里是起着妨碍三圣母舞蹈和破坏长绸舞蹈画面的作用……”[6]首演后的一年多时间内,舞剧《宝莲灯》重点在舞蹈编排、特别是在三圣母和刘彦昌的双人舞编排上下功夫,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隆荫培在《谈修排后的舞剧〈宝莲灯〉》一文中指出:“三圣母和刘彦昌定情的双人舞比过去精彩多了……他们在互表衷情后开始进入热烈奔放的舞蹈时,三圣母随着一个向前的大跳动作,甩去了披在肩上的长绸。当然,甩去肩上的长绸更便于他们对舞,可是我觉得这个动作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它既象征着追求爱情自由的决心,也象征着她从精神上甩去了一切封建礼教的束缚……编导者在这段舞蹈里,大胆地加入了一些托举的技巧。这可能是企图来表现他们二人的激情,但可惜觉得它们好像还没有很好地融合在整个舞蹈中……从这里编导者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民族舞剧里的双人舞,究竟怎样才能够充分表达出角色的内心情感,而又具我们民族的风格?”[7]舞剧《宝莲灯》的编导是李仲林和黄伯寿。而据黄伯寿回忆,“整个创作过程是在苏联专家查普林老师、中国专家李少春老师关心指教下进行的”;目的是探索解决“如何在民族文化艺术的传统基础上,吸收外来的经验,创作新型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舞剧形式”[8]。
二、《小刀会》:开辟了“表现近百年来革命斗争”的新路
《宝莲灯》之后,作为“大型古典舞剧”的中国民族舞剧是《小刀会》。舞剧《小刀会》首演于1959年。1960年该剧进京演出,欧阳予倩先生在演出座谈会上说:“舞剧表现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是开辟了一条新路……这个舞剧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也很成功——运用了很多的民族舞蹈,在结构上采用章回体小说的手法,都使人看来容易懂,而且亲切”[9]。欧阳予倩对《小刀会》的这段评价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指出我们的民族舞剧创作开辟了“表现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的新路;二是指出“结构上采用章回体小说的手法”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成功。舞剧《小刀会》由上海歌剧院舞剧团创演,由张拓、白水、仲林、舒巧、李群集体创作。编剧张拓作为当时的剧院领导是从事戏剧导演工作的,他认为应当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科学演剧方法运用到舞剧排列中去,主张“先把舞剧脚本按哑剧形式试排出来……这种试排要求演员进入角色的规定情境,合乎逻辑地进行舞台行动,唯一的限制是不准说话却要使观众看得懂表演的内容。预定有独舞和双人舞的地方,要求演员准备符合角色性格的内心独白和潜台词;需要表演舞的地方则暂时由其他情绪接近的舞蹈代替……”[10]。
张拓在上述创作回顾中说:“《小刀会》在戏剧结构上,正是按照舞剧艺术的规律和李渔提出的‘始终无二事,贯穿只一人’的原则,参照中国观众习惯的‘前后连贯,顺序发展,原原本本,有头有尾’的传统戏曲手法来进行这部民族舞剧的艺术构思的……在剧本中设计了两条线:一条情节线,是刘丽川、潘启祥、周秀英为代表的中国人民一方同晏玛泰、阿礼国、辣厄尔和吴健彰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方所展开的生死搏斗;另一条是感情线,这就是周秀英和潘启祥在艰苦战斗中形成的真挚爱情和战斗友谊,这条线是按照历史可能性虚构的。”[10]就舞蹈语汇设计而言,《小刀会》体现出三个特点:其一,是借助戏曲行当的表演技巧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该剧的舞蹈语汇,主要是从昆曲中提炼出来的中国古典舞,如张拓所说“采用老生身段表现刘丽川的果敢老练,采用武生身段表现潘启祥的刚强勇猛,用武旦身段表现周秀英的英俊矫健,用袍带丑和架子花脸的身段来表现反面人物吴健彰既昏庸又凶险的两面性格”[10]。其二,是要求情节舞“舞中有戏”而表演舞“戏中有舞”。所谓“舞中有戏”,是指推进戏剧情节的独舞、双人舞等,必须准确地揭示规定情境中角色的内心世界;而所谓“戏中有舞”,是指穿插在剧中的色彩性表演舞,必须合情合理于舞剧的规定情境。其三,是大量吸收戏曲中的“把子功”和“毯子功”来表现战斗生活;并进一步向武术学习,创作了“弓舞”这样优秀的表演舞。
在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在《小刀会》首演30年后,舒巧曾表示对该剧以“开打”来构成“冲突”不甚满意。她在香港《新晚报》当专栏作家时写道:“《小刀会》七幕戏,幕幕开打。第一幕起义,‘起义舞’编不长,夹进一段清兵掳村姑;第二幕劫法场,大打出手,然后庆祝胜利,跳民间舞;第三幕领事馆一场戏,舞不起来,伤煞脑筋,三易其稿,最后仍是设法让男主角与洋兵开打终了;四幕是偷袭;五幕是守城;六幕女主角思念男主角——现在想来这正是可以大舞特舞发挥舞蹈的段落,但当时我们拘泥于戏曲动作,只得用哑剧手势表达这一环节。至于舞蹈,则编了一个‘弓舞’以补充。”[11]在这里如套用李渔的句式,那就是“始终无二事,最终只‘开打’”。以“开打”来结构“冲突”,其实不只强调舞剧的“戏剧性”更是强调其“可舞性”。彼时舞剧的题材选择,一个十分重要的审美坐标是看看有无人物外部动作的“可舞性”。正如张拓通过组织《小刀会》的创作而总结的舞剧原则:“第一,舞剧只能通过看到剧中人的舞台行动,使观众理解和欣赏。万不得已的时候,也要尽量用舞台形象手段加以补充。第二,舞剧的表现手段是舞蹈:包括独舞、双人舞和集体舞在内的‘情节舞’是主要手段;具有鲜明色彩的‘表演舞’是次要手段;‘哑剧’场面是交代情节并连接各种舞蹈的辅助手段。第三,舞剧难以表现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情节,这是舞剧的弱点。因此舞剧台本必须做到人物集中、情节简明、场景连贯、故事完整……应力求达到‘一看就懂,百看不厌’的目标。”[10]
这其实有点难为“舞剧”——什么“一看就懂”的东西还能“百看不厌”呢?这是《小刀会》追求“始终无二事,贯穿只‘开打’”的理由吗?!
三、《鱼美人》:探索建立中国古典舞与芭蕾舞互相补充的新体系
舞剧《鱼美人》也是首演于1959年,与《小刀会》一并成为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的献礼剧目。20年后的1979年,该剧由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重新复排上演,“在复排过程中,编导者把大部分女子舞蹈改用芭蕾的足尖,并丰富和提高了双人舞的托举动作;通过艺术实践进一步明确了《鱼美人》就是中国的芭蕾舞剧”[11]。但是,“创作出形象生动、风格新颖的舞蹈形象是舞剧《鱼美人》的一个特色:猎人的形象基本上取自戏曲舞蹈的身段、造型来表现人物的英雄气质;而鱼美人的形象则选择了古典舞的‘射雁’和芭蕾‘attitude’的舞姿,双臂在身后摆动表现‘鱼’的动律……”[12]而在35年后的1994年,北京舞蹈学院再度按“民族舞剧”复排《鱼美人》之时,邵府(即杨少莆)借《〈鱼美人〉与中国民族舞剧创作》一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鱼美人》之前中国已有舞剧诞生,如《宝莲灯》,那是在传统的中国戏曲基础上衍化出来的舞蹈剧。不仅语汇受着戏曲影响,内在结构、叙事方法和表达方式也都没有离开母体多远。可以说,《宝莲灯》从内容到形式是完全中国式的。因此,它也受到无形的束缚,没能朝向根本意义上的舞剧化迈出更大的步伐。对比《鱼美人》和《宝莲灯》,看到的似乎是中国舞剧的两个侧面——丰富的舞蹈表现却没有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注重传统文化根基又没能摆脱戏曲舞蹈格式的拘束。是不是可以说,中国舞剧成功之道正在于使二者结合呢?”[13]
我们注意到,当时一些重要的戏剧和舞蹈评论家如马少波、贾作光、隆荫培等,几乎都认为《鱼美人》进行的是一次“芭蕾民族化”的探索:马少波认为《鱼美人》是丰富了我们民族表现技巧的芭蕾舞剧,可以由此逐步形成我们芭蕾的风格[14];贾作光认为《鱼美人》在芭蕾舞民族化,也就是试创中国式芭蕾舞剧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劳动,从编导技巧、手法上可以看出运用了苏联芭蕾舞的经验[15];隆荫培则认为《鱼美人》比较出色地运用和借鉴了苏联芭蕾舞剧编导艺术的经验,同时努力使芭蕾的表现形式和中国传统的舞蹈艺术结合起来,以逐渐达到芭蕾民族化的实践。隆荫培在这篇《谈舞剧〈鱼美人〉的成就》一文中认为“成就”主要在四个方面:“首先,编导们依据舞剧艺术的特性……力求用舞蹈的语言来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表现戏剧的情节与矛盾冲突,有意识地避免冗长和琐碎的哑剧手势动作”;“其次,这个舞剧的故事情节虽然还比较一般化……但由于编导者在安排矛盾冲突发展的细节方面有着独特的处理和新颖的创造,同时又运用了鲜明强烈的对比手法,使人觉得并不平淡”;“第三,舞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都塑造得比较鲜明有个性……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在性格冲突中逐渐完成的,显得特别动人并有着强烈的感染力”;“第四,由于在这部舞剧中采用了我国的古典舞和民间舞,使得它具有了一定的民族色彩……虽然这些民间舞蹈(主要指二幕‘婚礼’一场中)还没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有的舞蹈和情节的发展还缺少必要的内在联系,只是一种插入性的表演,但是从中可以使我们鲜明地看到舞剧的民族特色。”[16]
正如前苏联专家查普林的编导教学理念催生了舞剧《宝莲灯》一般,舞剧《鱼美人》是前苏联专家古雪夫力图印证自己编导教学理念的作品。彼时担任古雪夫助教的李承祥,近40年后发表了《古雪夫的舞剧编导艺术——与舞剧〈鱼美人〉创作者的谈话》。其中写道:“我想通过《鱼美人》的创作为中国的舞剧发展做一些实验,探索建立一种新的舞蹈体系——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互相补充的古典、芭蕾体系。中国古典舞和芭蕾舞都有造型艺术上的共同特点。这两种艺术如果结合在一起,两方面都会有发展。芭蕾舞经过300年的发展到今天,很难出现新的东西;中国的舞蹈如此丰富,现在该是西方向东方学习的时候了。如果芭蕾能和中国舞蹈结合,肯定是世界第一。我们不妨拿《鱼美人》做个实验……”[17]请注意,当有些人视这种做法为“结合”,或更视之为“植入芭蕾”之时,古雪夫强调的是“西方向东方学习”。古雪夫特别对参与创作的编导班全体同学说:“你们在编舞中要充分吸收中国古典舞,但是要看到中国古典舞原本是中国戏曲中的舞蹈,它在戏曲中是和唱腔、道白在一起运用的。如果离开了唱腔、道白的强有力的表现手段,舞蹈本身就必须加强,必须丰富……你们一方面要充分运用课堂上的中国古典舞,另一方面还要创作出既是古典舞风格的、又是新的舞蹈……要不要吸收芭蕾舞?中国古典舞和芭蕾舞有造型艺术上的共同特点,两种艺术结合在一起,双方都会有发展。芭蕾只是一种技术,它在特定的民族特色中起特殊的美化作用;芭蕾作为戏剧性的舞剧,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整部舞剧是民族的,有一些其他舞蹈成分没有关系;双人舞可以吸收芭蕾,表现海底世界的一场也要更多采用芭蕾舞。”[17]《鱼美人》首演获得欢迎后,古雪夫给予了肯定:“首先,由于舞剧具有简单明了的内容,观众关心主人公的命运,被舞剧所打动。其次,舞剧的戏剧性、幻想以及色彩丰富的场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欣赏要求。第三,舞剧采取了现代的编导手法,也即用舞蹈的手法表现一切,尽可能地减少了生活模拟和哑剧。第四,芭蕾和中国舞蹈的融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17]其实从古雪夫的指导思想来看,舞剧《鱼美人》与其说“芭蕾民族化”,不如更准确地表述为“中国民族舞剧的‘舞剧化’”!
四、《丝路花雨》:从复兴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开辟新路
《小刀会》和《鱼美人》问世后,有人概括说中国民族舞剧创建的两种模式是“无说唱的戏曲”和“无变奏的芭蕾”。当然这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的初创期。到1979年,以中国古典舞剧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舞剧建设再掀高潮。由甘肃省歌舞团刘少雄、张强、朱江、许琪、晏建中等集体创作的《丝路花雨》挺立潮头。正如叶宁在《中国舞剧〈丝路花雨〉的艺术成就》一文中所说:“舞剧《丝路花雨》的演出,不仅在我国民族舞剧中创造出一个新水平,而且在舞蹈的继承和革新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丝路花雨》的创作,不仅完全摆脱了‘四人帮’时期流行的一套陈词滥调,而且也打破了长期以来束缚舞蹈创作的框框。他们既运用了戏曲舞蹈的技法规律,又突破了它的程式;既借鉴了外国舞蹈的创作经验,又完全不受它的拘束,致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独树一帜,从复兴中国壁画中的舞蹈开辟了一条新路。”[18]笔者曾在《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一书中指出:“舞剧《丝路花雨》的创作有两个着眼点:一是通过讴歌盛唐敦邦睦邻、开放门户的政策来为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推波助澜;二是力图通过‘敦煌舞’的复活来再现莫高窟敦煌壁画的辉煌。前一个着眼点在‘思想’,后一个着眼点在‘艺术’,由于两者在舞剧创作中寻求到最佳结合点,使得《丝路花雨》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其‘门户开放’的思想主题和‘敦煌舞姿’的民族形式,作为对‘阶级斗争’主题和‘样板芭蕾’语汇的反拨,激发了人们对舞剧创作的新展望。”[19]
那么,舞剧《丝路花雨》是如何“从复兴中国壁画中的舞蹈开辟了一条新路”的呢?该剧的主要编舞许琪在《我们怎样使敦煌壁画舞起来的》一文中说:“剧组在分批深入莫高窟生活过程中……深深被绚丽多彩、生动形象的壁画和佛教故事所吸引:飘逸的飞天,神往的凭栏天女,天真的莲花童子,尤其是那些美丽动人的伎乐菩萨更是千姿百态惹人怜爱——那身着石榴裙的女子仿佛是唐代舞蹈家的身影,那衣裙飘转发辫四散的定是‘四座安能分背面’的‘胡旋女’……”根据许琪的讲述,编舞者先是反复琢磨吴曼英所绘百余幅“敦煌舞姿”白描图,“大家不约而同地总结出,壁画静止舞姿一般都具有讲究曲线、勾脚、出胯、扭腰、手势丰富、头颈别致、表情妩媚等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舞姿的重心及动势,揣测每一个舞姿可能经过什么样的路线达到壁画上的那种样子,接着又可能怎样向下发展……”。许琪告诉我们:“就在这种反复实践中……我们顺着劲儿努力探索,逐渐发现了一种规律——就如同古典舞‘划圆’是它的主要运动规律一样,‘敦煌舞蹈’也有它本身特有的运动规律,这就是‘S形’的曲线运动规律。因为敦煌舞姿静止造型大都具有‘S形’曲线的特点,因此在使其复活中发现,动作过程也多经过类似‘S形’的运动而达到‘S形’的造型。只有充分运用了这一运动过程,编出来的动作才像,风格才对劲。所以我们才说‘S形’曲线是‘敦煌舞’特有的运动律。”[20]
舞剧《丝路花雨》之所以能在“我国民族舞剧中创造出一个新水平”,除发现并创生了具有独特运动规律的“敦煌舞”之外,也与它在舞剧结构方面取得的成功分不开。傅兆先《略谈〈丝路花雨〉的结构》一文写道:“总的讲《丝路花雨》编导们是研究了我国传统戏曲的特点和我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借鉴了中外舞剧的有益经验——他们采用了既注重情节曲折、生动、故事性强,又强调舞剧所要求的简练、集中、富有可舞性……《丝路花雨》的开场是新颖别致引人入胜……仅用‘飞天’‘六臂如意观音’‘驼队’寥寥三笔,概括出了天上、佛窟、人间的规定情景,清楚又含蓄地塑造出了盛唐时代、敦煌地区、古丝绸之路上中外友谊交往的典型环境……”傅兆先进而指出:“根据剧情内容的需要和舞剧这一艺术形式的需要,把冲突、情节、人物与各种舞蹈、哑剧、生活场面紧密结合起来,合乎逻辑地配置好它们之间的次序、比例、对比关系,使它们有一个完整、和谐、统一的布局,这是舞剧结构上的基础工程。《丝路花雨》的第一场,在‘舞’和‘剧’结合与安排上是有可取之处的……这一场以英娘的命运为主线,结构在一个场面中,曲折动人合情合理……英娘的独舞是这一场中核心的舞蹈,它是别具独特风格的‘敦煌舞’……(编导)以异国情调的‘波斯珠宝舞’作为这一场的第一段舞蹈,以此形成与后面舞蹈在民族风格上的对比;接着用观众熟悉的‘翻筋斗’中加上些敦煌式的舞姿造型作为过渡,再看英娘的独舞时就有了心理上的准备……这一场不游离剧情内容和舞剧艺术形式的需要,将复兴敦煌乐舞、颂赞中外人民的友谊,再现大唐盛世人民生活的史实这贯穿全剧的三大任务密切结合起来,使形式、内容、背景组成一个完整有机统一体。在其他各场围绕着英娘的命运各有不同的侧重,在结构上也不断出现新的东西……”[21]
五、《奔月》:全力以赴开掘主要人物的内心活动
在迎接新中国建国30周年的舞剧创作中,曾经奉献过舞剧《小刀会》的上海歌剧院舞剧团,倾力打造了舞剧《奔月》。《奔月》由舒巧、仲林、叶银章、吴英、袁玲集体创作,从这个创作集体就可以看出,仲林曾经是古典风格的中国民族舞剧《宝莲灯》《小刀会》的掌门人,而舒巧也曾在《小刀会》的创作与表演中发挥过主要的作用。当然,这个创作集体的“排名”也向我们暗示,舒巧的创作理念将会起到主导作用。《奔月》演出后,《舞蹈》杂志1980年第2期组织了《首都舞蹈工作者笔谈〈奔月〉》,其中资华筠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她说:“也许由于舒巧、仲林都是我所熟悉的老同志,又是舞蹈界颇有成就的编导,因此看过《奔月》之后,使我很自然地要和他们过去的作品及我对他们的艺术造诣方面的印象作一番比较。总的印象是:他们的编导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它们各自的擅长和特点如:舒巧的精于提炼语汇、设计舞蹈;仲林的富于想象和大刀阔斧地处理场面,似乎在此剧中得到了新的发挥,艺术上更趋于成熟……这是我的第一点观后感。第二,此剧人物集中,剧情洗炼、明晰、顺理成章;除结尾部分略显冗长之外,自始至终很少赘笔……《奔月》全剧以舞贯穿,以情感人;每个人物的心理矛盾、感情跌宕,通过一段又一段富于人体美的舞蹈,表现得那样强烈、动人……第三,编导为了避免‘似曾相识’,着力在追求‘一种’创新的实践……一般都反映这个舞剧较多地吸收了现代舞和现代芭蕾舞的手法……我感到这种吸收并不是生吞活剥式的,而是服从于形象地体现舞剧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起码看得出编导者对于这方面的创造性的努力。”
的确,由于舞剧《丝路花雨》以“敦煌舞”重塑“古典舞”的成功,观看舞剧《奔月》者大多认为该剧“较多地吸收现代舞和现代芭蕾舞的手法”。其实这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正如主创人员舒巧、仲林等在《探索——舞剧〈奔月〉创作体会漫谈》中所说:“现今的民族舞剧只是在我国解放后才发展起来的,历史很短。《小刀会》《宝莲灯》创作在50年代……这两个舞剧的语汇基本上属于‘戏曲舞蹈’,它只吸收了戏曲‘唱、做、念、打’中的‘做’和‘打’,加以发展,因之表现手段较单薄。去年看了戏曲移植的《小刀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不但保留了原舞剧中的独舞、双人舞、表演舞(演员亦能胜任),且在原结构中还很方便地加进了‘唱’和‘念’,演出效果也比舞剧好……这说明我们作为舞剧编导在充分运用舞剧这个独特的艺术形式时很不熟练,艺术上还颇幼稚。”[22]具体到舞蹈语汇的运用中,编导们认为:“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一些古典舞、民间舞素材,最多只能追溯二三百年的历史,仅生活习惯这一点就有极大的差距。山膀、提襟、护腕……与明清时代的服饰不无关系;圆场更是和三寸金莲、行不露足的习惯分不开。这些动作如何能照搬来塑造后羿、嫦娥这样一些原始人物的形象呢?况且,在表现《小刀会》《宝莲灯》这样的题材时,亦已感到舞蹈语汇不足,我们的古典舞语汇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整理与发展的大量工作……在这次创作中,深感平时对于民族遗产的挖掘、研究不够。单就戏曲舞蹈而言,学习广度很差,接触较多的只是武生、武旦,对老生、丑、花脸等学习、研究很少……一进入编舞,大有‘等米下锅’的狼狈之感……其实这次《奔月》的编舞绝大部分仍是依据中国古典舞,但由于变形较多,有人说‘这是现代舞不是中国古典舞了’。”[22]
事实上,舞剧《奔月》就舞蹈语汇的运用而言,是“变形较多”的中国古典舞而非现代舞。那么它为何要“变形”又是如何“变形”的呢?如其所言:“‘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的传说,情节曲折复杂,人物繁多。但从诸多繁杂的情节发展中,我们感觉到有一条始终如一、十分鲜明的线,那就是人们对后羿的爱戴和对逄蒙的恨。这一对人物的故事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并符合舞剧应线条清晰、冲突尖锐、人物感情强烈的要求……另外,嫦娥在原传说中被描写成是出于嫉妒和不安于人间生活,才偷吃了飞天药奔月而去的;但当今人民心目中嫦娥是美、善的化身,因此我们对传说做了重新解释,让她做了后羿最重要的陪衬人物……即使文学本比较集中,一旦涉及长度表及进入具体编剧时仍要时时记住开拓主要人物的内心活动,而不被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起舞、很有舞蹈发挥可能性的枝枝节节的段落吸引过去……”[22]既然是“要时时记住开拓主要人物的内心活动”,编导们确立了一个“干编双人舞”的理念,也即把那些陪衬主要人物的群舞统统“割爱”,“逼得编导全力以赴开掘人物和内心活动,以情取胜,以情带舞……”;同时,编导们进一步想到:“独舞、双人舞固然是用来塑造主要人物、揭示主要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要手段,但如何将集体表演性的舞段也调动起来为塑造主要人物、特别是揭示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服务呢?因为无论如何光靠一个人的四肢动作,再加上面部表情,表现力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如果把主要人物的内心感情、思维活动用形体动作放大、加倍,并调动群舞及整个舞台表现手段来表现行不行呢?想到这点,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22]正是“干编双人舞”以开掘人物内心活动,以及“调动集体舞”以放大人物内心活动,决定了舞剧创作对中国古典舞语汇的“较多变形”;这个“较多变形”又是从四个方面来变化“古典舞程式”——即变化动律的节奏;变化动作的连接关系;改变并重新协调原来舞姿上身与腿部的关系;变化舞姿、造型本身。详情如何,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1] 姜椿芳.创立中国舞剧的最早尝试[J].舞蹈论丛,1981(4).
[2] 谭雅涛.阿龙·阿甫夏洛穆夫和他的歌剧创作成就[C]. /中国歌剧艺术文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
[3] 李百成.忆“头三脚”,并由此想到的[J].舞蹈艺术.第25辑,1988(11).
[4] 中国艺术研究所舞蹈研究所集体编写.中国舞剧史纲[J].舞蹈艺术.第30辑,1990(02).
[5] 隆荫培.中国舞剧史纲[J].舞蹈艺术.第30辑,1990(02).
[6] 隆荫培.试论舞剧《宝莲灯》的演出[J].舞蹈丛刊. 1958(02).
[7] 隆荫培.谈修排后的舞剧《宝莲灯》[N].光明日报. 1959-9-9.
[8] 黄伯寿.回忆舞剧《宝莲灯》的创作过程[C].舞蹈舞剧创作经验文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
[9] 本刊记者.《小刀会》进京演出座谈会召开[J].舞蹈. 1960(7).
[10] 张拓.《小刀会》创作的历史回顾——兼论舞剧的发展道路[C]. /舞蹈舞剧创作经验文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
[11] 转引自于平,中外舞蹈思想概论《舒巧的舞剧创作思想》[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
[12] 陈铭琦.重看舞剧《鱼美人》有感[J].舞蹈. 1979(6).
[13] 邵府.《鱼美人》与中国民族舞剧创作[J].舞蹈. 1994(5).
[14] 马少波.再谈《鱼美人》[J].舞蹈. 1960(1).
[15] 贾作光.《鱼美人》的成就与问题[J].舞蹈. 1960(1).
[16] 隆荫培.谈舞剧《鱼美人》的成就[J].戏剧报. 1960(3).
[17] 李承祥.古雪夫的舞剧编导艺术——与舞剧《鱼美人》创作者的谈话[J].舞蹈. 1997(6).
[18] 叶宁.中国舞剧《丝路花雨》的艺术成就[J].红旗. 1980(3).
[19] 于平.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20] 许琪.我们怎样使敦煌壁画舞起来的[J].舞蹈艺术.第1辑,1980(1).
[21] 傅兆先.略谈《丝路花雨》的结构[C]. /炼狱与圣殿中的欢笑——傅兆先舞学文选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22] 舒巧、仲林.探索——舞剧《奔月》创作体会漫谈[J].舞蹈. 19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