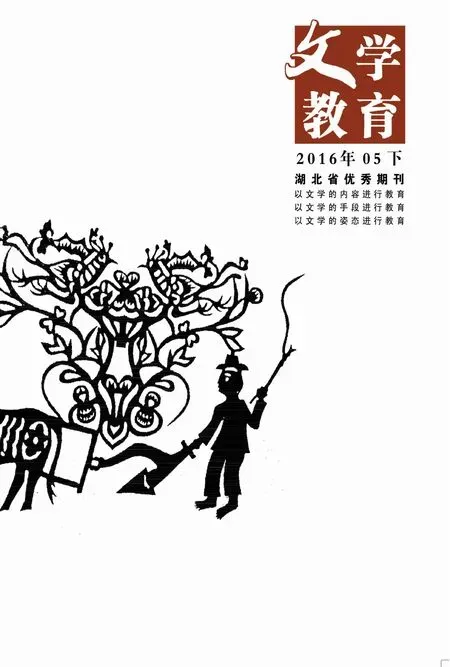《广岛之恋》的空间叙事与历史构建
高文婧
《广岛之恋》的空间叙事与历史构建
高文婧
内容摘要:《广岛之恋》是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经典作品之一。这部作品中渗透着作家强烈的空间意识。从拆解时间链条的空间叙事手法,到身体空间与历史空间之间的烛照关系,再到空间意象表征的社会历史内涵,作家透过个人叙事实现了对于“空间的历史”的构建,以空间表征实践为社会科学领域空前盛大的“空间转向”注入了文本动能。
关键词:空间叙事身体空间空间意象空间的历史
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创作历来蕴含着强烈的空间意识。从文本中空间场景的多元性和凸显感,到叙事中对于传统线性叙述手法的颠覆,她的创作整体上与约瑟夫·弗兰克在《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中对于空间小说的界定相吻合。而发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空间转向”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曾在1970年写给杜拉斯的信中吐露:“我在你的作品中失去了平衡,我被你的文字所捕获了。……你是我所需要的那种作家。”随后,在1976年,福柯即在访谈中表示:“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而且,它要比我们面对时间所产生的焦虑更为严重”。伴随着文学领域“空间转向”的兴起,近年来已有学者着手从空间批评视角出发解读杜拉斯的作品。然而,从空间路径出发解析《广岛之恋》仍属罕见。
《广岛之恋》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应导演阿兰·雷奈之邀而创作的电影剧本。在之后整理出版的文字作品中,杜拉斯将影片未用的部分加以保留,尽可能忠诚地呈现了自己的初始设想:1957年夏天,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法国女子在广岛参加拍摄一部关于和平的影片。回国前夕,女人和一个日本男人之间产生了一段过眼云烟的恋情。法国女人向他吐露了自己年轻时在家乡内韦尔与德国士兵的悲伤初恋。伴随着女人的叙述,故事在内韦尔和广岛之间交错展开。从拆解时间链条的空间叙事手法,到身体空间与历史空间之间的烛照关系,再到空间意象表征的社会历史内涵,杜拉斯透过个人叙事实现了对于“空间的历史”的构建。
一、时间碎片与空间膨胀
在西方思想的传统中,对于时间的关注始终优于空间。较之历史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一直处于附属或缺席状态。以线性的、因果的历史决定论为主导的思维意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空间往往被看作是承载历史时间演化的容器。二十世纪后半叶以降,空间问题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了一场可以被一些人如此描述的跨学科的空间性转向。这可能算是近两个世纪来的第一次,特别是批判性的学者开始像他们传统上阐释历史和社会、揭示人类生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那样阐释‘空间性’了。……一种再度兴起的、结合空间性的清晰想象的批评性视角,开始给历史和社会研究注入思想与阐释的新模式。”
在文学领域,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莫里斯·布朗肖在其著作《文学空间》中指出,文学空间并不是一种外在的景观或场景,也不是见证时间在场的固化场所,而是一种生存体验的深度空间,它的生成源自作家对于生存的内在体验。因此,文学空间是一种内在的、深度的、孤寂的体验空间,而写作正是要“投身到时间不在场的诱惑中去”。自20世纪早期起,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等作家已经开始尝试在作品中突破传统的线性叙述,构建一种“时间不在场”的空间化叙事结构。杜拉斯的《广岛之恋》正是一部灵活运用空间叙事技巧的典型作品:文本中包含三重叙事时间,即围绕法国女人与日本男人在广岛的爱情故事所展开的当下时间,广岛核爆炸的过去时间,以及围绕法国女人年轻时期与德国士兵在内韦尔的初恋故事所展开的过去时间。这三重时间界限模糊,文本在核爆炸的广岛、当下的广岛以及二战中的内韦尔之间任意切换,完全脱离了清晰严整的时间线索,时间链条的断裂随处可见。当“广岛火车站的高音喇叭在广播:‘广岛!广岛站到了!’”时,声音却在内韦尔的叙事画面上出现。内韦尔的爱情场景与广岛的爱情场景始终以交错重叠的状态存在。杜拉斯将自己的这种叙事特征描述为“一切都糅合在一起,并没有什么预想的原则,而是以一种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这类混合的方式进行。”借由这一叙事技巧,空间从时间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文本呈现出一种空间膨胀而时间受到压缩的叙事形态。
不可否认,这种类似拼接剪辑式的叙述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电影叙事张力的考量,但同时也凸显了作家的文学叙事的空间意识。日本男人的手犹如普鲁斯特笔下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将法国女子的意识流引向与德国情人的旧时情境:“就在她注视这个日本男人的双手时,猛然间,一个年轻男人的躯体浮现在他躺着的位置上,取代了他。……他的双手长得也很美,同日本人的那双手像得出奇。”广岛和内韦尔这两座经历二战洗礼的城市也如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场景一般,从纯粹的物理地点演化为影响叙事结构的重要因素。当日本男子随着法国女子的回忆,将自己与德国士兵视为同一时,亦即在法国女子和日本男子在交谈中提及德国士兵之处分别使用“你”、“我”时,关注共时性、在场、关系的空间叙事结构彻底打破了文本的时间链条,个体的爱情经历与战争历史的集体记忆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交融的形态。
本雅明认为,在线性历史主义的哲学根基中,线性的历史决定论往往把人类带到同质的、虚空的历史时间中,必然会斩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正联系,为此,他以当下时间为楔子洞穿历史,爆破历史的连续性。当下时间是当下存在所填充的时间,时间弥散于当下存在的空间里,成为“时间的碎片”。《广岛之恋》的叙事本质正是这种在当下和过去穿梭往复的时间碎片化,亦即时间的空间化。法国女子对于时间的感悟印证了作家的空间意识:“牢记时间的确切持续期限。弄清时光有时怎样过得飞快,接着又毫无意义地过得很慢,而且,还得忍受它的忽快忽慢……。”无疑,内韦尔和广岛的爱情经历与历史记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法国女子一生中过得飞快的时光。这些时光碎片得以从线性的虚空中跳脱出来,以并置和交错的空间化形式存在并生产意义。于是,时空的交错不仅打破了单一的叙述节奏,形成了多重画面,使叙述显得摇曳多姿,更使得历史记忆从时间的线性向空间的深度延展。
二、身体空间与历史记忆
杜拉斯对于历史记忆的空间构建不止于突破传统线性叙述的层面,空间意象本身也蕴含着对于历史记忆的烛照,是影响叙事结构的重要隐性元素。法国著名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告诉我们:“我的身体对我来说非但不只是空间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没有身体,对我来说也就是没有空间。”他在空间现象学理论中探讨了身体空间与客观空间的关系,认为从肉身化主体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空间都可被纳入身体空间与客观空间两个层次之中,而客观空间又最终奠基于身体空间。一切空间的结构与意义的构造都需要身体的参与。无独有偶,法国著名思想家昂利·列斐伏尔也指出,身体位于空间的核心处,身体在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构成空间的身位性,成为空间坐标的主轴,是空间的原点或焦点:“位于空间与权力的话语的真正核心处的,正是不能被简化还原、不可颠覆的身体”。
《广岛之恋》的叙事便始于这一具有奠基性质的身体意象,整个叙事都由身体空间生发开去。在文本的开端,核爆炸的“蘑菇”云在银幕上升腾而起,烟云下面,渐渐呈现出法国女人和日本男人赤露的肩膀。紧接着,杜拉斯让“镜头”在这对爱侣的激情缠绵与广岛核爆炸的残肢断臂等惨烈画面间不断切换,并最终回到这两副充满欲望、尽情搂抱的躯体之上。杜拉斯指认了这一身体空间的能指特征:“这种拥抱是如此寻常,如此普通,却发生在世界上一座最难以想象得到的城市:广岛。……一种特殊的光晕映照于每个手势,每句话,使其具有超出字面意义的弦外之音。”与广岛核爆炸交替出现的身体空间所传达的“弦外之音”,是其与战争历史的一种异质同构关系。恰如始于原始冲动的原罪也常被拿来理解群体的侵略倾向,身体的欲望宣泄与战争的野蛮粗暴背后流露出的征服欲望并无二致。作为个体的法国女子与日本男子共同构成的身体空间,裹挟着原罪,在集体身上开挖出一段残暴的历史记忆。当法国女子身着红十字会护士服出现在日本男子面前时,再度引起了男子的生理欲望。作家进而肯定了这类乔装打扮对于男性的普遍诱惑力,并将如此着装的女子比喻为“一次永恒战争中的永恒战士”。这一比喻同样暗示了被永恒的肉体欲望擒住的人类始终处于欲望的战场,“风流韵事”和战争一样无休无止:“女人们恐怕会生育畸形儿,乃至怪物,但那种风流事还继续干。男人们恐怕会患上不育症,但风流事还继续干。……我还知道。这种惨剧(即核战争)还将重演。”身体空间与广岛的战争历史巧妙地相互指涉。在法国女子参与拍摄的关于和平的电影里,一位动人的日本女子“坐在一辆彩车上。几只鸽子从她黑色上衣里(乳房隆起部位)展翅飞出。”乳房表征性内涵,充满死亡与悼念意味的黑色上衣,暗示对于战争的祭奠,鸽子则喻指经历战火洗礼的广岛重归和平,个体身体意象再次被表述为战争记忆的源头。
以身体意象召唤集体记忆,是文本隐含的叙事线索。建立在个体身体空间和集体历史记忆之间的相互指涉关系在叙事中俯拾皆是。日本男子曾对法国女子说:“你仿佛集千名女子于一身”。在法国女子参与拍摄的有关和平的电影中也有这样一幕:在游行的队伍中,儿童们满脸涂着白粉。法国女子询问日本情人为何要把孩子们的脸涂成这样,她得到的回答是:“为了使广岛的孩子们彼此相像。……因为被烧伤的广岛儿童都相像得如出一撤。”个体身体意象凝结着集体的伤痛,在身体空间与历史记忆之间架起桥梁。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那样:“整个空间都是从身体开始的,不管它如何将身体变形以至于彻底忘记了身体,也不管它如何与身体彻底决裂以至于要消灭身体,只有立足于最接近我们的秩序,即身体秩序,才能对遥远的秩序(国家的、全球的)的起源问题做出解释。”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提出“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在法国女子对于家乡内韦尔的回忆中,身体空间便铭刻着二战的惨痛历史。在内韦尔解放之际,德国士兵在卢瓦尔河畔的河滨公园惨遭冷枪射杀。文本多次描绘了他异常漫长的死亡过程,法国女子趴在中弹的德国士兵身上整整一夜。“我可以说,我压根儿就感觉不出他的尸体和我的身体有一丝一毫的区别……我只觉得这尸体和我的身体出奇的相像……”“一位年轻女子正嘴贴着嘴趴在他的身上。泪水从她的眼中簌簌流下,鲜血从他的口中汩汩流出,泪水和鲜血混合在一起。”杜拉斯说:“荒诞的战争正不加掩饰地笼罩在他们混为一体的身躯上。”在战争阴霾之下,身体意象作为牺牲品存在。身体空间的渺小与脆弱昭示了战争的残酷与无情。诚如福柯所言,身体是历史的铭刻物,各类社会实践的内容都是围绕身体而展开的,身体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地受到社会权力机制的分割、重组、控制。因此,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身体的历史,就是对身体进行规训与惩罚的历史。
三、空间意象的社会历史表情
杰拉德·普林斯在他的《叙事学辞典》中将空间定义为“能重现事件及情境的场所和地点。”可以看出,空间既充当了地理层面的能指,又担负起叙事层面的所指。《广岛之恋》回避对于公共历史的直接述说,但却巧妙地借助实体空间意象,以关于公共历史的个人回忆与情感体验的形式间接潜入公共历史的深层肌理。
杜拉斯笔下的广岛和内韦尔,既是地理名称,也承载着个人与历史的双重记忆。法国女子对于内韦尔的描述前后矛盾,在地理意义上,“内韦尔是座小城。……连一个小孩也能环城走上一圈。”在法国女子的心理层面,“内韦尔是座庞大无比的城市。……在内韦尔,追求幸福便是罪恶。”在文本的结尾处,面对与日本情人的分离,法国女子说:“广—岛。这是你的名字。”日本男子则回应:“这是我的名字。是的。我们就到此为止,仅此而已。而且,永远停留于此。你的名字是内韦尔。法——国——的——内——韦——尔。”杜拉斯对于这一结尾给出了解释:“事实上,在彼此心目中,他们仍然谁也不是。他们只拥有地名,这些不是姓名的名字。就好像一个在内韦尔被剃了光头的女子的灾难与广岛的灾难准确地互相映衬。”广岛和内韦尔作为承载个体体验的空间意象,使得历史创伤以个人声音和个人叙事的形式得以释放。
房间意象与杜拉斯的文本具有一种永恒的伴随性。它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主人公内心记忆的载体。法国现象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通过对家屋、地窖、抽屉、橱柜、窝巢、角落等空间原型展开现象学分析,揭示实体空间的诗性意义本源。巴什拉指出人可以借助外部空间来激活记忆,“空间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这就是空间的作用。……在此空间是一切,因为时间不再激活记忆。……是凭借空间,是在空间之中,我们才找到了经过很长的时间凝结下来的绵延所形成的美丽化石。”在巴什拉的理论中,在时间中寻找回忆的方式,是传记作品的关注所在,因此只和一种外在的历史有关。相较于传记,更为深刻的阐释学应该把历史从对我们的命运无作用的相连时间结构中解放出来。因为对于认识内心空间来说,比确定日期更紧要的是为我们的内心空间确定位置。在解放后的内韦尔,德国情人死去了,法国女人因为与国家的敌人相恋而被剃光了头发,被关在自家地下室里。地下室的空间体验在法国女人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它寒冷、阴沉、压抑又无情。在那里,法国女人疯了,她经常无意识地喊叫,舔舐自己手上的鲜血,还会啃食地下室的墙体。如巴什拉所言,“地窖是埋在地下的疯狂,被墙围住的冲突。”法国女人感到“所有人都在我的头上肆意践踏。当然……看到的不是天空……我看见这个社会在走动。……他们不知道我在地下室里。他们把我当作死人,远离内韦尔的死人。我父亲宁愿我死掉。因为我已名誉扫地,我父亲巴不得我死掉。”从福柯的权力政治学角度出发,地下室中法国女子疯癫的根源,正是战争历史的疯癫与荒诞:“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在《广岛之恋》中,地下室蕴含的空间政治规训内涵显而易见。女子的疯癫源于情人的死去,又不单是因为情人的死去,更是历史悲剧的一种微观表达。当日本男子将自己与德国男子视为同一时,问了法国女子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俩相爱,那你在内韦尔的这个地下室里会感到冷吗?”女子的回答肯定而坚决:“我会感到冷的。在内韦尔,地下室都很冷,无论夏天还是冬天,都很冷。”这一回答隐晦地肯定了地下室空间作为现代社会权利运作的场域,是福柯所指认的现代权力施以空间禁闭的场所。它以理性的名义制造疯癫,以监视的方式实行惩罚,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管辖,甚至于以爱的名义完成规训,凝结着历史对于个体命运的无情碾压。
福柯从空间化思考方式出发,认为缺少空间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并设想和期待一种“空间的历史”,以改变“时间的历史”的宏大叙事:“一部完全的历史仍有待撰写成空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权力的历史——它包括从地缘政治学的重大策略到细微的居住策略。”在《广岛之恋》的通篇中,杜拉斯以空间的共时性叙事形态瓦解了线性时间的链条,在身体的历史与空间的历史之间构建了一种内在的本质关联,同时赋予实体空间意象以社会历史内涵。她以自己的空间表征实践,填充了“时间的历史”的空间空白,同时也为社会科学领域空前盛大的“空间转向”注入了文本动能。
参考文献
[1]约瑟夫·弗兰克等.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秦林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贝尔纳·阿拉泽,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解读杜拉斯[M].黄荭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3]Michel Foucault. Texts/Contexts of Other Space[J]. Diacritics,1986,16(1):22-27.
[4]爱德华·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M].李钧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5]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M].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玛格丽特·杜拉斯.广岛之恋[M].谭立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7]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M].陈永国,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刘胜利.身体、空间与科学——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9]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0]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11]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刘北成,杨远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杜拉斯笔下‘情人’形象的嬗变研究”(14C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