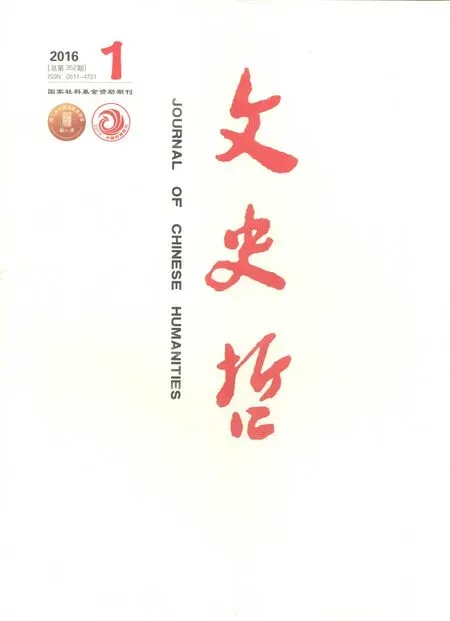儒家乌托邦传统与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
儒家乌托邦传统与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
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234)
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中的性善论导致了用道德主义解决一切问题的政治哲学。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对人性的预设确实有所不同。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张性恶论,这是关于人性的悲观主义的理解。既然人性是恶的,就不可能单纯通过道德教化来改造,西方文明因而发展出一整套基于历史经验的制度与法律,来约束人性中的恶。相反,儒家文化中的性善论则是关于人性的乐观主义预设。儒家相信人性本善,认为通过道德的涵育与教化,就可以把人内在的善的潜质(即儒家所谓的“性”)显扬出来,通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可以让人皆有之的内在的善的资源充沛于全身。如果全社会的人都能通过修养与教化,修炼成具有完善人格的君子,那么,理想社会就会到来。
儒家执著于道德治国。儒家经典中的“三代”,实乃由儒家所肯定的道德原则建构起来的乌托邦世界,它与夏、商、周的历史事实相距甚远,只是儒家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道德理想国的投影。儒家根据德治的原则,建构起一系列理想化的古代制度,并把这种制度附丽到“三代”上去。这种乌托邦建构的过程,类似于现代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过程。在后者看来,良好的制度可以经由人的理性,根据“第一原理”与道德原则设计出来。这一建构过程是纯理性的,与经验事实无关,与人在适应环境挑战过程中的经验与试错无关。这种思维方式也可称为“儒家道德建构主义”。
儒家通过它所描绘的“三代”告诉世人,先人曾经生活在非常完美的过去,只要按“三代”的制度去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自秦汉以来,人们真以为历史上的“三代”就是曾经出现过的理想社会。儒家的这种道德建构主义,如同人类各民族的乌托邦理想一样,像黑暗世界的一盏明灯,确实起到了用理想世界来批判不公正的世俗生活的作用。然而,这种建构主义思维模式,也成为中国乌托邦主义的根源。西汉末年的王莽与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对三代美好社会信以为真,于是他力图运用自己取得的至高权势,在现实生活中复古改制,结果造成了社会的大灾难。王莽的悲剧是乌托邦理想付诸实践而形成的悲剧。20世纪30年代,著名思想家萧公权先生认为,王莽改制是最古老的社会主义试验。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乌托邦主义政治实践最早的惨痛失败。
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康有为的乐观主义的人性论导致了乌托邦主义。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其深层的思维句法结构,可以说与儒家文化中的道德建构主义一脉相承。在《大同书》中,家庭、私有财产、国家、阶级、婚姻等等,举凡一切在适应环境挑战过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的产物,都被认为是罪恶的,或至少是不完美的。康有为认为有必要凭着人类自己的理性,按照他心目中的道德理想的原则,去设计一些人造的完美制度。在康有为看来,既然人类凭自己的理性可以发明精美的机器,为什么就不能发明适合于人性的好的社会制度?用完美来取代不完美,用无缺陷来取代罪恶与缺陷,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天经地义。康有为大同思想就是以这种乐观主义的逻辑为基础的。
在康有为看来,作为千百年来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国家、家庭、婚姻及种种传统习俗既然充满缺陷,那么,最理想的、最适合人类生活的社会就应该取消这些东西,而代之以他头脑中想象出来的、没有缺点的人造新制度。康有为在《大同书》里认定,因为国家之间会发生战争,所以要取消国家,代之以“世界政府”。因为阶级制度会导致社会不平等,所以要取消阶级。因为家庭导致婆媳争吵、兄弟打斗,是自私的温床、罪恶之源,只会带来无穷的痛苦,所以可以而且有必要取消家庭,代之以“公养”、“公教”、“公恤”。又因为婚姻造成事实上的女子不平等地位,所以要取消婚姻,代之以一个月至一年为期的男女合同制,等等。
康有为的自信,源于他的理性万能信念。他认为,经验会犯错误,理性则如同公理几何,不会出错。但事实上,康有为在运用他的理性时就出了问题。他把黑人诊断为“劣等种族”,继而主张:采用“黑白杂婚之法”,男性黑人必须与女性白人结婚,女性黑人必须嫁给男性白人,以便在“七百年至一千年”内,使黑人化为白人。这一荒唐的例子足以证明,观念人所信托的理性本身具有缺陷。
毫无疑问,这种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政治逻辑势必导致一种乌托邦倾向。康有为正是基于这一倾向,建构了通过对人进行教化以达到无私社会的政治哲学。
这种理想主义的社会蓝图,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谭嗣同的“冲决网罗”是20世纪激进反传统主义的先声。在他看来,传统就是“网罗”,就是束缚人性的东西,要实现一个符合人性与道德的社会,就必须冲决这些“网罗”,用观念中的完美主义世界取代现实。可以说,谭嗣同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把传统“妖魔化”的知识分子。当然,传统中有许多必须批判的东西,但“冲决网罗”则把传统符号化,使之被解释为没有积极意义与正面社会功能的东西。“五四”以后,全盘反传统主义取得优势话语权。谭嗣同的“冲决网罗论”为20世纪中国观念人的大量出现开辟了道路。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对“善”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时代、教养、性格、经历,特别是经受过不同挫折与痛苦的人们,会在自己头脑中形成不同的“善”的世界愿景。人们会以自己所理解的主观的“善”为标尺,对世界现行秩序进行重新建构。受这种乌托邦理念与思维模式支配的人们,存在着一种强大的重构人类新秩序的道德冲动。由此而产生的道德优越感、斗争意识与正邪两值分类,是激进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
事实上,用自己有缺陷的理性,去设计社会改造的蓝图,强行挑战人类千百年的集体经验——这种行事模式,正是近代以来激进主义的巨大悲剧之一。对康有为的《大同书》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20世纪激进主义的哲学基础与内涵。
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是,古代、近代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具有深层同构性,都是用道德建构主义重建世界。孔子、康有为、“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时代不同,价值观不同,但在思维方式上,却存在一脉相承的“道德理想国”传统。在儒家那里,道德王国在过去,即三代;在康有为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那里,道德王国则在未来。这三者具体取向不同,但思维方式却颇具深层的同构性与延续性。他们都崇尚人类经验世界中并不存在理想王国,都不承认现实中的社会是人类集体经验的产物,不承认这种历史产物是一方水土上生活着的人们在适应自身环境挑战中形成的。并且,他们都相信,可以用自己体认的道德理性原则来重塑新世界,前者的榜样在过去,因此趋向于复古,后者的榜样在未来,因此趋向于激进地反对传统。
以道德建构主义为基础的中国知识谱系,本能地拒斥经验主义思维方式。虽然中国民间文化中也有朴素的经验主义传统,但作为精英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却缺乏西方意义上的那种以人类集体经验为基础的经验主义政治哲学。美国学者墨子刻曾这样评论道:“在西方经验主义者看来,历史始终是一个神魔混杂的过程,社会中始终有着很多与人类理想相矛盾的成分。人类的生活一方面并不完美,另一方面也还是很有价值的,这个世界还是很值得留恋,是有趣味的。世界既不完美也还值得活下去,人们还有希望使世界变得比它原来的样子更好一些。既然人们对生活的要求既不太高,又不满足,这就不会走极端,就能心平气和地考虑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如果人们认同这样一个前提,那么,无论是要保守传统,还是要改革传统,都是对方可以理解与体谅的。”*参见萧功秦:《一个美国保守主义者眼中的中国改革》,《中国的大转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307页。
墨子刻还认为,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改革传统,是因为传统并不完美,保守传统,是因为传统值得我们留恋。它既不坏到哪里,也不好到哪里,这样,知识分子与国民就会形成一种保守主义与改革主义之间的持续的对话”*萧功秦:《一个美国保守主义者眼中的中国改革》,《中国的大转型》,第307页。。这就是西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西方的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变革,但反对以人的理性去设计建构一个新社会,反对以这种想当然的“新社会”模式来取代现实社会。而儒家的道德建构主义却相反,以道德理想国设计为好社会的蓝本。到了近代,这种思维模式与思维“句法结构”,自然而然与激进主义合流。一切激进主义都采取经验的反叛者姿态,以自己心目中的道德意象为楷模,试图从根本上颠覆、否定现存秩序。
我要说的第四个问题是,对极左思潮的反思:乌托邦主义为什么在中国盛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大灾难,这场灾难的发生有政治、历史与文化多方面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与本文有关的角度,对“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观念逻辑作大概的解析。这种极左思潮鼓吹“斗私批修”与“灵魂深处闹革命”,这种观念背后隐含着一种特殊的“道德建构主义”逻辑。这种建构主义的逻辑是:现行体制下之所以仍然出现“官僚主义”,问题不在所有制,因为所有制改造已经完成了;人的“私心”不是来自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而只能来自“腐朽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因此只有进行“上层建筑的革命”,才能解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问题。而在极左思潮的观念中,“上层建筑革命”的核心就是“斗私批修”,就是“在灵魂深处进行革命”。而要推行极左的道德教化,那就要“破私立公”,就要在“灵魂深处”进行“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革命。只有这样,才能造就“新人”,只有当这样的“上层建筑革命”完成了,革命才能实现最终的目标。
意味深长的是,早在七百年前的元代理学家吴澄的文集中,我们赫然发现“破私立公”这四个字。这种字句上的巧合并非偶然,而是表明极左思潮的道德建构主义,与理学家的道德建构主义之间,存在深层次的逻辑同构关系。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研究儒家思想时,提倡儒学的学者一定要注意到这些层面的问题。儒家的道德建构主义有着发展为文化浪漫主义的潜质。
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与中国的新左派学者,其价值取向虽然各异,思维方式中却都不自觉地存在着我所说的道德建构主义。这或许与人们不自觉地承继了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关。要克服思想中的片面性,还是要回到经验主义上去,限于篇幅,对此就不再展开了。
要之,性善论具有多面性。必须承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制度性宗教信仰的民族,性善论在历史上也曾起到社会道德标尺的作用,它有着激励社会成员通过合理教化,获得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的社会功能。性善论与道德建构主义的关系,以及道德建构主义与乌托邦的关系,是思想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这里初步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思考。从儒家文化中获取积极的精神资源,扬弃儒家传统中的乌托邦主义,是值得当今中国思想界关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