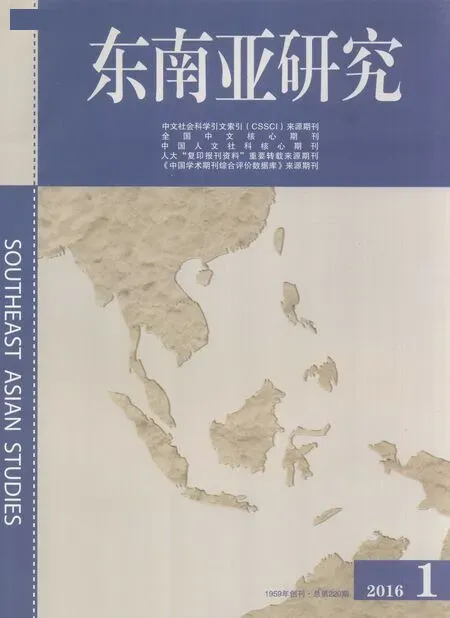天限南北 各帝一方——评《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
叶少飞
(红河学院红河州越南研究中心 云南蒙自 661199)
天限南北各帝一方
——评《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
叶少飞
(红河学院红河州越南研究中心云南蒙自 661199)
[关键词]《王室后裔》;中越关系;明清之变;宗藩关系;安南莫朝;高平莫氏
[摘要]牛军凯博士《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从越南的视角,对高平莫氏政权及其后的莫氏家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莫朝历史复杂而曲折,中兴黎朝毁弃莫朝文物,为莫朝历史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其巨大的史学意义和历史研究价值需要学者继续探索。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etnam,Dr.Niu Junkai conducted a more in-depth study on political power of Mac Family in Cao Bang and the subsequent Mac Family in his Royal Descent and Rebel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 Family in Vietnam and China. Dr.Niu put forward many new ideas,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deficiencies. The history of Mac Dynasty is complex and tortuous, and the Le Dynasty had destroied Mac Dynasty’s cultural relic, these brought great difficulties to the research of Mac historians, but the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need scholars continue to study.
牛军凯博士的著作《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以下简称《王室后裔》)2012年由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该书是作者在2003年博士论文《朝贡与邦交——明末清初中越关系研究(1593—1702)》的基础上,再广泛涉猎丰富的中外文献修改完成的作品。从标题的变化,可以看出作者实现了从“中越”关系到“越中”关系研究的转变。从越南的角度审视两国的历史交往,该书作者提出许多有别于过去中国学界不同的观点。山本达郎主编的《越南中国关系史》是以第三方学者的角度来研究中越关系,《王室后裔》则是当事一方学者的研究结晶。该书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高平莫氏政权研究,包括第一章“明朝对安南黎、莫双重承认政策的形成”,第二章“安南莫氏高平政权与明朝的关系”,第三章“南明与安南关系研究”,第四章“清朝对黎、莫双重承认政策的继承与放弃”。作者在探讨莫朝与明清政权相互关系的同时,也展示了广南阮氏、中兴黎朝与明清政权的相互关系,在政权变换时期的双方关系研究方面尤有创见。
第二部分为莫氏家族研究,包括第五章“后高平时期在华莫氏后裔的复国运动与清朝的政策”,第六章“逃亡的莫氏叛乱者——乾隆年间安南黄公缵投诚史事与清朝的政策”。莫氏历史并未因高平政权的崩溃戛然而止,这一部分作者爬梳史料,对没落的莫氏家族的活动做了细致的探讨,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以及对微观历史研究的把握能力。
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第七章“王朝变更与制度、礼仪的变化——以明清两朝对黎、莫政策为中心的研究”着眼于中越双方政权交替过程中朝贡制度的变化和礼仪的执行;第八章“边境土司、割据势力对中越关系的影响——以明清处理黎、莫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对处于中越王朝势力中间地带的边疆地方力量在中越关系演变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第一章之前的“绪论”对当前中越关系的理论研究和成果做了梳理,篇末的“结语”可视作经过研究之后对绪论的回应,根据明清时期安南黎、莫相争,中兴黎朝郑、阮相争的具体情形提出“朝贡家族”的概念,并对此时的中越关系做了解答。笔者将此归结为第四部分。
一《王室后裔》在越南史研究领域的突破
关于《王室后裔》的选题意义、学术价值和学术贡献,孙来臣《明末清初的中越关系:理想、现实、利益、实力》(代序)已讲述清楚,兹不赘述。《王室后裔》集中研究了莫朝崩溃之后高平莫氏政权,及高平政权消亡之后莫氏家族的活动,在越南史领域做出了巨大的突破。
(一)政治演变
1527年莫登庸虽然成功取代了后黎朝, 但1533年后黎朝老臣阮淦在哀牢重立新帝,对抗莫朝。之后莫朝颓势渐显,双方形成拉锯之势。阮淦1545年被毒杀,后黎朝大权落入其婿郑检之手。阮淦之子阮潢为求自保,1557年请出镇顺化、广南一带,后黎朝内部逐渐形成郑、阮两大势力。1593年黎朝攻陷升龙城,复国成功,莫氏退守高平。但中兴黎朝大权由郑氏控制,以王爵世代相传,黎氏仅为空头皇帝。1677年中兴黎朝攻陷高平,莫氏在安南的统治力量彻底消亡。
莫登庸篡权之后,安南国内的力量派系纷扰,政治演变过程也极其复杂。《王室后裔》的研究重点虽然不在莫氏本朝,但对郑、阮力量的形成和演变均有清晰的勾勒,对黎氏复国之后郑氏在北方、阮氏在南方的活动,也有深入的研究。但《王室后裔》最大的贡献在于对高平莫氏败亡之后莫氏成员在安南和中国的活动做了探索研究。
政治演变与政治势力的消亡并不完全同步,后者在政治演变完成之后往往趋于微末与隐晦。但隐晦之后既有如同后黎朝重立新帝、卷土重来成功反击的情况,亦有莫氏高平政权败亡之后彻底消散的情形。《王室后裔》对莫氏复国史事的钩沉显示了政治势力在末期衰退中的演变,对后黎朝如何处理莫氏族人的问题也做了探讨,莫氏后裔对复国的不同认知也体现了历史发展趋于微末之时的复杂性。
(二)对外关系
《王室后裔》对安南国内的政治演变做了清晰的勾勒,对各方势力与中国的关系也做了探索分析。通过对对峙时期的黎、莫与中国关系,黎、莫与南明的关系,郑、阮与中国的关系,安南各派势力在明清鼎革时期与中国的关系都做了详细的论述,条分缕析,尤其是对高平莫氏败亡之后莫氏后裔活动的深入研究,将莫朝之后安南的局势清晰呈现出来,使得这一时期的越南和中国关系研究摆脱了大块、笼统的描述,也使这一时期越南对外关系的研究趋于细致与精密。
二“王室后裔”与“安南帝室”
在中越关系史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其重要却容易被略过的问题,即安南历代称帝之事。自丁部领968年称“大胜明皇帝”以来[1],安南历代无不称帝建号。丁部领在国内称帝,但却隐瞒此事,派遣长子丁琏进贡宋朝,获得宋朝的承认,宋朝封丁部领为“交阯郡王”[2]。越南自此实行对内称帝,对中国则用中国封赠名号的政策与传统。安南对内称帝,建立了以安南为主的区域秩序[3];对中国则称臣,称中国封赠的名号,加入并服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4],这两个方面堪称中越关系研究的基本点。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等越南史书对历代国君的帝号和中国封赏的爵号大多同时记取。黎崱《安南志略》因在元朝撰写完成,因此不称安南历代君主帝号,只书以中国封赏爵号。越南历代史家对本国称帝亦做出解释。后黎朝太祖黎利建国,阮廌起草《平吴大诰》曰:
惟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封域即殊,南北之风俗亦异。粤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或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5]
黎圣宗时吴士连修《大越史记全书》也秉承此意,《大越史记外纪全书序》曰:
大越居五岭之南,乃天限南北也。其始祖出于神农氏之后,乃天启真主也,所以能与北朝各帝一方焉。[6]
《拟进大越史记全书表》又言:“粤肇南邦之继嗣,实与北朝而抗衡。统绪之传亿万年,与天罔极;英明之君六七作,于古有光。虽强弱时或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7]黎崇亦以此论南越武帝赵佗与汉朝的关系:“赵武帝乘秦之乱,奄有岭表,都于番禹,与汉高祖各帝一方”[8]。赵佗南越国在陈朝为越南国统之首,在《大越史记全书》中则为正统之一[9]。“各帝一方”即是越南史家对本国称帝所作的解释。
中国方面是知道安南君主在国内称帝的事情的。沈括《梦溪笔谈》记李日尊:“乃僭称‘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睿文尊德圣神皇帝’,尊公蕴为‘太祖神武皇帝’”[10];《安南志原》采用的越南史书方式称“纪”者皆称“伪纪”;《越史略》四库馆臣提要亦称之为“僭伪”。中国历代并未因安南在内部称帝而大动干戈,只要安南按照中国的要求、遵守中国确立的秩序即可。安南历代称帝一直被视作坚持独立的象征,在国内也形成了特殊的“南”和“北”的理论,即以本国为“南”,以中国为“北”。Liam C. Kelley[11]和西村昌也[12]分别就越南史中的“北”和“南”进行了研究。因此,越南史家所论的“天限南北”、“各帝一方”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已达成。
莫氏就任从二品安南都统使与其在国内称帝建号并行不悖,莫氏在安南国内的统治基础完善,与之前的丁、黎、李、陈具备同样的合法性。明朝削去安南国王爵号,其君臣虽然不忿,但对其国内统治的合法性并无大的影响。在莫氏之前,胡季孷篡夺陈朝,但因其称帝建号,史家亦有称其为“闰朔”者,即仍为一代之统,唯其不正而已[13]。
莫氏子孙在安南国内即成“天潢帝胄”,“王室后裔”实为中国角度的称谓。《王室后裔》以“王室后裔”作为研究基点,仍是从中国角度看待莫氏之事,因此对安南国内称帝之事即一略而过(183页)。《王室后裔》总结:“在越南,一个政治家族在国内取得合法政治地位一般需要做到以下五件事情:一、取得政治控制权;二、得到中国的认可;三、开科举;四、修庙宇;五;铸钱币。”(258页)
其中“取得政治控制权”是《王室后裔》所做的总体性描述,但结合全书从中国角度提出“王室后裔”的观点,作者可能忽视了政治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层级性。曲承美为静海军节度使,938年吴权称王,968年丁部领称帝,黎桓取代丁氏亦称帝,安南的政治层级已经从“王”一级上升到“皇帝”一级。吴士连以吴权作为《大越史记全书》“本纪”的开端,但武琼和范公著则因为吴权未称帝,而以丁部领为“本纪”的开端,称其开创了越史的“大一统”局面[14]。后黎朝自黎利称帝即在安南国内确定了最高的政治权力等级。中兴黎朝复国之后,黎氏皇帝虽仅有空名,废立亦操于郑氏之手,郑氏虽在国内执政,但对明、清外交却均以黎氏名义进行,且国内亦认为黎氏得天命。郑氏和阮氏始终未能废而自立,“郑王”和“阮王”虽拥有实权,但在名分上和“黎帝”政治权力层级是很分明的。中国方面给予安南的政治待遇也经历了交阯郡王、南平王、安南国王的过程,显示了宋代逐渐承认安南自主建国的政治历程。政治权力的层级直接影响到执政能力的深度和广度,政治影响力区别也很大。即以安南而言,“皇帝”一级和“王”一级差别极大,因此中兴黎朝的郑主和阮主虽然各自执政,但其权力等级却不及黎朝皇帝,虽拥有实际权力,其政治影响力则在黎氏皇帝之下。文贵在曲,“取得政治控制权”恐需进行细致性描述。
三“安南都统使”的名号及其在明朝藩贡体系中的位置
安南自开宝八年丁部领受封“交阯郡王”以来,先后得到“南平王”和“安南国王”封号[15],安南经历李、陈、黎三代,宋元明皆封之为“安南国王”。明嘉靖帝削“安南国王”为从二品“安南都统使司”,实为前所未有之举措。《王室后裔》第七章第一节“中越关系的调整与册封制度的变化”对莫氏“安南都统使”的来历做了介绍,后指出莫朝大臣甲海对“安南都统使”名号极为不忿,要求莫茂洽请封“安南国王”,中兴黎朝亦不满“安南都统使”之号(第180-187页)。
大沢一雄认为安南都统使司专为莫朝而设,是仿照明朝的土司制度而来,安南仍奉明朝正朔,留置于藩贡体系之中[16]。陈文源、李宁艳认为降级安南都统使是明朝“将安南国在体制内定位为内属之行政特区”[17],即将独立的安南王国降级为一个行政区划。“安南都统使”名号对安南并无实际影响,并未改变其在安南称帝及其合法地位。安南都统使的权力等级、政治义务和权利、辖区性质,均是相对中国而言,明朝对安南都统使司的设立与定位是之后政策执行的基础,是突破或遵循的依据,因此明朝对安南都统使司的贡奉时间和要求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以符合对安南都统使司的政治设计。因此“安南都统使”虽因莫登庸篡位而引起,专为莫氏而设,却延续用于中兴黎朝和高平莫氏。遗憾的是《王室后裔》只是陈述了“安南都统使”设立的过程,对这一首次出现的名号的具体来历和内涵没有讨论,也未对现有观点进行辩解。
(一)明朝对安南都统使的待遇
明朝降安南国王为从二品安南都统使司,使臣入贡接待当低于先前的安南国王时期。《明世宗实录》记载:
(嘉靖二十二年四月乙亥朔)乙未安南都统使司都统使莫福海善辖内宣抚同知阮典敬、阮昭训等分进谢恩脩贡表笺,赉纱罗彩币绢钞等物如例。礼臣以安南既废不主,则入贡官员非异时陪臣比,宜裁其赏赉。上曰:“福海既纳贡谕诚,其赉如故,第罢赐宴,稍减供馈以示非陪臣礼。”[18]
《王室后裔》论莫朝贡使的待遇如下(第190页):
名义上降低对安南使者的接待规格,但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嘉靖二十四年,“安南都统使莫福海差宣抚阮诠等奉表贡方物”,明朝对安南贡使“赏宴如例”。嘉靖四十三年,莫朝遣黎光贲等朝贡,贡使至京,嘉靖帝“嘉其恭顺,特赐宴如朝鲜、琉球二国陪臣例”。万历九年,莫朝四贡并进,明朝礼部认为,“莫朝四贡并进,忠顺可嘉”,因此明帝“诏赐赏宴,仍给敕褒之”。万历十八年,莫朝遣宣抚使赖敏等进贡,明朝“赏宴如例”。至此,明朝对莫朝态度具有了这样一种习惯,从理论上其贡使非陪臣,不能赐宴,但可以以其恭顺的名义赏赐宴席,与朝鲜、琉球等国使臣实质上同等待遇。
《王室后裔》参考文献只列了1962年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明实录》一种,并无他本(第298页),笔者检阅史料原文分别如下:
(嘉靖二十四年)安南都统使莫福海差宣抚阮诠等奉表贡方物,宴赏如例。[19]
(万历九年六月)安南都统使莫茂洽差宣抚司同知梁逢辰等赉捧表文,补贡嘉靖三十六、三十九年分正贡,万历三年、六年分方物。部覆:“茂洽并进四贡,忠顺可嘉。”诏赐宴赏,仍给敕褒之。[20]
(万历十八年八月庚辰)安南都统使莫茂洽差宣抚副使赖敏等进贡,宴赏如例。[21]
嘉靖二十四年和万历十八年分别是“宴赏如例”,万历九年则是“诏赐宴赏”。《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亦是如此记载[22],并无《王室后裔》采用的“赏宴”字样。莫氏使臣得明帝赐宴者仅两次,万历九年四贡同进之外,嘉靖四十三年黎光贲在广西滞留十五年之后进京,“上嘉其恭顺,特赐宴如朝鲜、琉球二国陪臣例”[23]。其余皆为“宴赏”,无“赐”字。嘉靖二十二年明帝指示对莫氏使臣“第罢赐宴,稍减供馈以示非陪臣礼”,也就是说去除了天子对诸侯藩国使臣的“赐宴”待遇,但远人来贡,仍需接待,故“稍减供馈以示非陪臣礼”,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之“宴赏如例”当以嘉靖二十二年的“非陪臣礼”进行。可见诸侯国陪臣得明朝天子赐宴为常例,非陪臣则得明朝礼部常规接待。“赐宴”与“赐宴赏”均得明帝旨意,“宴赏”则仅为明朝常规接待,二者的待遇差别是很大的,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待遇级别。莫朝使臣得“赐宴”仅两次,实属特例,其他莫朝使臣受到的宴赏为明朝常规接待,明朝仍以“非陪臣礼”待莫朝使臣。《明实录》中的“宴赏”与《王室后裔》采用的“赏宴”虽仅字序之差,但涵义差别极大。《王室后裔》进而理解“赏宴”为“赏赐宴席”,实为不妥。
(二)安南都统使在宗藩体系中地位的变化
从二品的安南都统使仍留置于明朝的藩贡体系之中,但与之前享有的安南国王等级差别极大,莫朝和中兴黎朝均不满此名号,其在藩贡体系中的位置愈发尴尬。“安南都统使”自嘉靖二十年(1541)延续至明朝灭亡,嘉靖、万历时期明朝藩贡体系尚能维护,安南、朝鲜、琉球使臣有机会在北京相遇交流,其互相评价正是藩贡体系内部运作的切实表现。朝贡国在藩贡体系中的位置及相互认知在明清时期始终存在[24]。清水太郎、陆小燕分别分析了万历二十五年中兴黎朝复国后冯克宽求取安南国王封号未果而仅获安南都统使名号的过程,并对冯克宽和朝鲜使臣李睟光的诗文交流进行研究,认为朝鲜使臣因朝鲜国王爵位远高于安南都统使名号,故而对安南使臣予以嘲讽和压制,以示自己诸藩之首的优越地位[25]。郑永常《一次奇异的诗之外交:冯克宽与李睟光在北京的交会》则与清水太郎相反,得出了朝鲜、越南使臣友好交流的结论[26]。万历二十五年冯克宽请封安南国王是《王室后裔》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33-35页),清水太郎和郑永常的论文分别发表于2003年和2009年,可惜未能予以参考,失去了从朝鲜角度对安南都统使在明朝藩贡体系中的位置进行研究的机会。
四高平莫氏政权的败亡
1593年后黎朝攻杀莫朝皇帝莫茂洽复国成功,莫氏退守高平,因明朝插手,高平政权方得以延续。但后黎朝无时不筹划彻底解决莫氏问题,以除大患。清朝延续明朝政策,对黎氏、莫氏均予以承认。康熙六年(1667)后黎朝攻占高平,莫氏向清朝求救,康熙八年(1669)清朝二品大员李仙根出使安南,强令退还高平,后黎朝不服也无可奈何,只好留待以后。《王室后裔》对李仙根出使和清朝的意图以及后黎朝的交涉有深入的分析,但对随后高平莫氏政权败亡过程的解读则有简略之嫌(第120-124页)。
《王室后裔》注意到高平莫氏政权的败亡过程中清朝的主导作用,论述了后黎朝所称的莫氏附逆吴三桂一事。《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康熙十六年(1677):
春,大举讨高平。先是,莫敬宇改名元清,求广西督抚司请于清帝,谕我还高平地,因据之。及清吴三桂反于云南,元清从伪号,资之粮草。至是三桂死,清兵入广西,王与廷臣议乘机进剿。先移书清将军罪状元清,命丁文左、阮有登等率将士讨之。申璇视师,段俊和参军事。[27]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记载内容大致相同,记清将军为赖塔利[28],《王室后裔》据此指出“1677年后黎出兵高平之前,即发文书给在广西的清朝将军赖塔利”(121页)。陆小燕分析这段史料:
吴三桂死于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并非康熙十六年;赖塔利当为大将军赖塔,《平定三逆方略》、《八旗通志·赖塔传》并未记载赖塔受安南传书之事。后黎朝康熙十六年春二月至八月攻灭高平莫氏的行动,主要原因就是吴三桂已死,后黎朝从何处得到这个消息,决定行动并传书赖塔?因史料未载已不得而知。中国典籍没有记载赖塔得安南传书之事,也没有莫元清逃入中国的具体时间。[29]
《王室后裔》则没有辨析这段史料,后黎朝在其间所做的周密安排遂隐而不见,对清朝在三藩之乱的复杂局面中做出的应对也就缺少相应的分析。无论后黎朝的外交活动如何开展,只有清朝认可方才取得成功,康熙二十二年周灿出使即代表清朝对后黎朝攻取高平的政治和外交承认。高平莫氏问题自康熙六年后黎朝攻占高平,至康熙二十二年周灿使安南,在后黎朝军事和外交两方面努力下,藉由吴三桂叛乱的时机,才最终完善解决。然而与《王室后裔》对康熙八年李仙根出使安南的深入研究相比,参考文献虽列入周灿《使交纪事》(第301页),但书中只引用了吴兴祚写的序,对周灿康熙二十二年出使则没有言及。此时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黎朝攻占高平,堪称皆大欢喜之局,与康熙八年李仙根《安南使事纪要》的激烈冲突有鲜明的对比。可惜《王室后裔》未作深究,难免有虎头蛇尾之感,对高平莫氏政权败亡过程的研究亦失之于简略。
孙来臣在“代序”中对李仙根《安南使事纪要》借题发挥,论述“中国对待越南又何尝不带有大国沙文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第31-34页),此时清朝急于确立自己在藩国中的权威,必定是坚决贯彻其主张,乃至态度蛮横。但康熙二十二年周灿使交州则无李仙根时的紧张气氛,双方融洽之极。“代序”只论一端恐亦未当。
五安南与“明清之变”
《王室后裔》的学术视野由安南扩展至朝鲜,在第三章《南明与安南关系研究》中专设一节《与朝鲜对南明态度的比较》(第104-108页),解释安南对明、清关系的政策和思想渊源,并将安南和朝鲜进行对比,从安南的角度研究“明清之变”。孙来臣在序中就此指出“安南与朝鲜的比较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还需要大力展开”(第25页)。
“明清之变”是16、17世纪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王朝对明、清的认知差别极大,同类研究中以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的研究最为深入精湛。遗憾的是《王室后裔》引用了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成果,而对这一思想史研究力作未加参考。
此节《王室后裔》谈到了宋明理学对安南的影响,“自立后安南最大规模的儒学发展是在后黎朝圣宗时期,但即使在圣宗时期,对中国儒学的继承和研究也没有深谙其精髓,更谈不上突破。所以安南的儒学士大夫没有真正得到儒化,如16世纪的著名儒学家、莫朝状元阮秉谦,其思想中带有不少道家的影响”(第106页)。作者这个结论过于武断了。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成书于黎圣宗洪德十年(1479),其以“史臣吴士连曰”的方式所做的历史评论即以儒家思想进行论断,其史论和史观深受司马光和朱熹影响[30];襄翼帝洪顺六年(1514)黎崇完成的《越鉴通考总论》则是按照纲常论、正统论、朱熹史学、张载理学撰写的一部历史哲学著作[31]。萧公权指出:“宋代理学家,就其渊源论,有援道入儒及援佛入儒之两潮流,邵雍与周敦颐乃前者最重要之代表。”[32]安南儒学既受宋代理学影响,“莫朝状元阮秉谦,其思想中带有不少道家的影响”,实属正常,以此来论“安南的儒学士大夫没有真正得到儒化”是不能成立的。阮秉谦一人亦不能代表明代安南儒学的发展潮流和思想。在阮秉谦之前,陈朝的黎文休、朱文安、范师孟、张汉超等,后黎朝的潘孚先、朱车、吴士连、武琼、黎崇等皆是儒学精湛的学者。
《王室后裔》谈到:“安南很早就认同清文化的儒化,因此安南对吴三桂、郑氏家族等的‘反清复明’号召就不会积极响应。”(第108页)16世纪以来阳明学风靡明朝,朱熹理学衰落,但朝鲜和安南仍然服膺朱子学。部分秉承朱子学的朝鲜儒者对阳明学极其反感,并延续至清代[33]。“清文化的儒化”究竟指的是清朝接受朱子学还是阳明学,亦或是满洲在入关前任用汉人大臣、部分推行汉文化,安南方面认可的又是什么,这样含混的描述无法说明问题。
儒学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即便同一时代的儒学也有不同的思想流派,不同流派的主张和内涵差别是很大的,不同的儒学流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不相同,儒学在中国、越南、朝鲜、日本传播的情况也不同[34]。《王室后裔》使用安南“儒化”和清朝“儒化”这样的泛泛之词,恐略显粗疏,仍需对安南和朝鲜儒学的流派与传承进行细致的分析。
后黎朝在吴三桂叛乱之中两不相帮,秉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兵攻占高平,广南阮氏则积极接收南明杨彦迪、陈胜才力量(第101页)。安南以实用的态度应对明清之变,谋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但其行为背后的文化和思想根源,仍需进一步挖掘和研究。总体而言,“与朝鲜对南明态度的比较”一节仍是中外关系角度的解读,虽然作者希望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但力有未逮。
六莫朝在越南历史研究中的史学价值和意义
莫朝在越南历史中有特殊的地位和史学意义。1527年莫登庸弑黎恭皇自立称帝,在传统史学中是“革命”,莫朝亦是国家政权;1593年后黎朝复国,莫氏遂成“叛逆”,莫朝亦成“伪朝”,1593年后的高平莫氏政权则是地方政权;1677年后黎朝攻占高平,莫氏政权败亡,莫氏残余力量遁入中国,是为莫氏家族。黎朝与莫氏对抗期间,黎朝内部郑、阮双方的力量分化亦告完成。莫氏经历了莫朝安南国家政权——莫氏高平地方政权——莫氏家族的过程,《王室后裔》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莫氏高平地方政权和莫氏家族,莫朝安南国家政权的研究虽然并非其重点,但却是研究基础和前提,很多内容也须在莫朝政权中寻找根源,黎、莫双方的力量对比与变化也是在1593年以前完成的。《王室后裔》关于莫朝历史的研究仅有“中越关系的调整与册封制度的变化”(第180-191页)和“万历年间钦州事件和中越各方的对策”(第230-237页)两部分内容,相对于莫朝66年的历史略有不足。亦因《王室后裔》的研究重点不在莫朝,故而对一些重要的、能够揭示1593年后黎、莫并存时期的资料未能使用。前文提到的“安南都统使”名号问题,李文凤《越峤书》对明朝调兵及莫登庸出降记述详细,作者虽列入参考文献(第299页),但未使用;而记载莫登庸事件更加细致的《苍梧总督军门志》则没有列入。大沢一雄《对十六、七世纪中越关系史的研究——以莫登庸政权为中心》分三篇先后在1965年《史学》第38卷第2、3号,1966年《史学》第39卷第2号刊出,1971年又在《横浜商大论集》发表了《明末中越关系的演变》。山本达郎主编《越南中国关系史》第六章“黎朝中期与明清的关系”为大沢一雄撰写,但远较原文简略,《王室后裔》将《越南中国关系史》列入参考文献(第318页),没有参考大沢一雄最初的论文。对莫朝历史整体研究的不足可能也是《王室后裔》做出“所以安南的儒学士大夫没有真正得到儒化,如16世纪的著名儒学家、莫朝状元阮秉谦,其思想中带有不少道家的影响”之类评价的原因之一。对于莫朝的评价,是越南历史最为重要的史学评论之一,其中尤可窥探越南史学思想。
(一)莫氏“逆取”
史学家登柄就莫氏篡权评论如下:
黎朝不幸中衰,至此极矣。故愚尝曰莫氏者黎朝之叛臣也,至黎帝即位于哀牢,始以正统纪年,以明君臣之分,正大纲也。是时莫氏奄有其国,而不以正统书之,何也?盖莫氏臣也,黎帝虽即位于外,没迹邻国,曾无寸土一民,而独以正统书之者,何也?盖黎氏君也,抑尝考之。古人有言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粤昔启封南国以来,历代明王贤主,有攻守而并吞之,有传授而世守之,皆继世而王,以有位号,乃以正统书之,曰本纪,曰正纪,曰前纪、后纪,曰中纪、末纪,皆其顺而已。至若悖逆篡弑而强自立,虽有名号称者,皆名不正,言不顺也,则编之为附纪,是其逆而已。世降以下,乱起纷纭,迭有兴废,不必言之。自赵越王之起,则本前李南帝之臣也,继南帝以有其国,而后始即政称王,以其臣能代君行政,如此顺也。丁先皇平十二使君之乱,而并有之,少帝微弱,弗能御敌,以国事委之大将黎桓,而黎桓承丁后之传,以有天下者顺也。及李之代黎,陈之代李,以有位者,皆其顺也。然则赵、黎、李、陈之四君,皆乘国中无主,或因群臣所请,或因女主之传授,国人之尊服,天与之,人归之,以有天下,皆其顺取以有之也。于莫则不然,观其所为者,登庸不过黎朝一大臣也,当黎朝主弱臣强之际,登庸能师古昔之圣君贤相,尊主庇民,如伊尹之辅太甲,周公之辅成王,其彰彰然伟绩,庶可嘉焉。何不效此,而反其道,是未免逼主称禅,篡国弑君,以图自立。及其有国也,殆六十七年之间,所为成为王莽,终不免诛夷,实于汉之曹、于陈之胡,皆其迹也。是愚所谓其逆取而有之也,故不得书为正统也。……[35]
划横线部分为《王室后裔》引用的内容,得出结论:“是为通过正取方式获得政权的为正统,逆取非正统,然而何为正何为逆,并不能明确地区分。越南正史确认的正统与非正统,只不过是后世史家编撰史学著作的标准,并不是当时社会的认可标准。”(258页)史学家登柄前半部分内容对正逆、何为正统已然论述明白,并引李佛子、丁部领、黎桓、陈太宗论何为顺取,莫氏以臣篡君所以不得书为正统,又解释了何以莫登庸称帝建号而为逆,黎氏不保寸土一民仍为正。《大越史记全书》中已有黎文休、吴士连、潘孚先等人很成熟的历史评论,黎崇《越鉴通考总论》则是专门的史学评论作品,越南历代史家对正、逆是辨析明了的,登柄关于莫氏篡逆的评论显然与前代史家有很深的思想渊源。《王室后裔》所言“然而何为正何为逆,并不能明确地区分”过于臆断了。
莫氏夺黎,如同李公蕴代替黎氏,陈太宗得国李氏,于传统而言即为“革命”。但后黎朝卷土重来,莫氏遂成“叛逆”。莫氏不仅对中兴黎朝君臣有所警戒,而且具有特殊的史学意义。黎朝中兴,郑氏世掌国政,虽有觊觎帝位之心,但终未能越雷池称帝自立;广南阮氏自成一国,却始终奉黎朝正统,未称帝建号。阮福映之国命实得自西山阮氏,非劫夺于黎朝。《王室后裔》对郑氏不轨之心(184-185页)和阮氏奉守黎朝正朔(124-128页)均有涉及,钩沉史料做出深入见解,但莫氏篡权建政数十年却最终失败,郑、阮亦因攻莫得以发迹,莫氏的惨痛教训对郑、阮当有极大的警示。
(二)莫氏“顺守”
莫氏以臣篡君,此为“逆取”,但如此行径越南历史上不乏前例。李公蕴夺权于黎氏,陈太宗得国于女主李昭皇,皆是以臣得国于君,但李、陈顺守,传国百年,李亡于陈,陈亡于胡,新朝革命,遂为“前朝”。即便篡陈的胡朝,也因亡于明朝之手,亦没有得到“伪”的评价。莫氏“逆取”已成定论,但莫氏传国六十余载,可称“顺守”。
丁克顺博士《越南莫朝历史研究》对莫朝的政治建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做了深入的研究,是莫朝历史研究的优秀作品[36]。《王室后裔》在论述莫氏高平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时对莫朝政治进行延伸研究,列举其成功之处(46-52页)。《大越史记全书》关于莫朝的史事记载,主要有两类,首先是黎朝与莫朝的互相征战及两家的政治演变,但记述多偏向黎朝;其次是莫朝开科举,记述较略。尽管如此,《大越史记全书》对莫朝政治仍有褒扬:
莫令禁内外各处,不得持枪剑及尖刀干戈兵器,横衡道路,违者许法司捕捉。于是商贾及行人,皆空手而行,夜无盗劫,放牧不收,每一月一点视。或有生产,不能识其家物。数年之间,道不拾遗,外户不闭,屡有大年,境内稍安。[37]
显然莫朝政治自有其成功之处。黎贵惇《大越通史·艺文志》记甲澂撰《邦交问答》十卷。《洪德善政》虽以黎圣宗洪德年号为名,但加入了很多莫朝大正、景历年间的律条[38]。莫朝景历七年(1555)杨文安在《乌州近录》“后序”中盛赞莫朝教化,移风易俗,言“由此天地便有此山川,有此山川便有此人物”,“洪惟胜朝,圣作明兴,天涵地育,正天地长盛一辰节也”[39],复知礼仪忠恕。可知莫氏本朝人物对本朝政治自多称赞。
中兴黎朝史家记述莫朝历史刻意回避了一个问题,即莫朝的国号“大越”,杨文安即称“皇越肇邦”[40]。自李圣宗1054年建国号“大越”以来,后续的陈、胡、黎、莫均未更改国号。莫朝袭取了前朝的“大越”国号,即继承了“大越”的法统和国统。尽管《大越史记全书》和《大南实录》均以莫朝史事系于黎朝编年之下,以示其“伪”,但对莫朝“大越”国号则略而不记,避而不谈。
相对于史家对莫氏“逆取”的评价,《大越史记全书》对莫氏政治及灭亡保持缄默,没有进行评论;黎贵惇《大越通史·逆臣传》记莫氏之事,但亦未评论。在中兴黎朝压制、毁弃莫朝的情况下,史家对莫朝“顺守”政治“述而不论”的沉默态度,可以看做是对莫朝政治的另类认可。
(三)黎、莫阵营之间的选择与转变
莫朝在初期政治稳定,保持对黎氏的绝对压制优势。1546年莫福海卒,莫福源立,大将范子仪谋立莫正中失败,并窜入中国劫掠,在1550年被明朝和莫朝联合剿灭,但范子仪之乱造成了莫氏内乱,莫朝和黎氏逐渐形成拉锯之势。黎、莫阵营均极力争取、笼络人才,亦有人在双方转移游走。莫朝景历三年(1550):
时莫福源听范琼、范瑶父子谗言,南道将太宰奉国公黎伯骊及其子普郡公黎克慎,文臣吏部尚书御史台都御史东阁大学士入侍经筵舒郡公阮倩及其子阮倦、阮俛等,各率本部兵百余,夜遁入清华关隘请降。[41]
阮倩为莫朝大正三年(1532)进士,黎伯骊在莫福源即位时曾协助击平范子仪之乱[42],二人均为莫朝重臣。莫朝光宝四年(1557)“莫降将黎伯骊、阮倩卒。倩子阮倦、阮俛等反迯归莫”[43]。1572年黎克慎反黎降莫,郑松杀其三子[44]。莫朝降将阮凯康被莫朝用计打败,复降莫,莫朝将其车裂[45]。黎莫对峙为双方人员提供了选择,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郑桧叛逃莫朝。1570年郑检病卒,世子郑桧继位,统领军政,但“自纵声色,志益骄佚,不恤士卒。于是将校离心,辅佐日寡,人心思异,各相生变,终成祸胎”[46]。将佐拥立郑检次子郑松,莫敬典知悉郑氏内乱,率兵攻打,大胜黎朝。郑桧逃入莫朝,郑松统领国政。1584年郑桧卒于莫,“莫使人吊祭之,复遣兵送柩,许家人亲母及妻子归葬。节制郑松亦差人迎接,殡于安定军安山之右,为设牲礼,上表奏帝恕其罪,赠太傅忠郡公,许其子郑森等挂孝”[47]。
1580年莫敬典卒,《大越史记全书》记:“敬典仁厚勇略,聪慧敏达,履历艰险,勤劳忠诚。”[48]尽管阵营敌对,但中兴黎朝史官仍给予了很高的评论。而莫朝大正六年(1535)状元阮秉谦深具兼济天下的理想,其为阮潢指出“横山一带,万代容身”计策奠定广南阮氏和阮朝的基业[49]。《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嘉靖二十七年(1548)“莫遣黎光贲等如明岁贡”,然而黎光贲却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正月二十五日方才回国:
黎光贲因范子仪之乱滞留南宁十五年,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一月至京引起了不小的影响,《殊域周咨录》记载:
有贡使至京,朝廷以其伪官,待查明白方许进献。行文去后,查无的音,其贡使不敢回。至今隆庆二年,大学士李春芳悯贡使久处邸中,且能敬守主命,为之奏受其贡遣回。使人在中国二十余年,青鬓而来,今回须发尽白,人以为比苏武皓首以归云。[51]
《殊域周咨录》成书于万历十一年(1583),记载黎光贲修贡事多有不符,听以传闻。但黎光贲至京引起宰辅大学士李春芳注意,认为能够“敬守主命”,实为忠臣。明人又将黎光贲比为汉之苏武,可见钦佩有嘉。黎光贲回国,莫朝遣吏部尚书甲海等至谅山边界迎接。然而历史的吊诡即在于此,因中兴黎朝毁弃莫朝,黎光贲青鬓使、白首归之嘉言懿行遂在安南湮没不显。
臣子士人在黎莫阵营中的选择与游走,及后世对当事双方人物所做的评价,其内容的深刻与思想的复杂远远超出史家对莫朝“伪”“逆”的评价,史学意义仍需探索。
结语
莫朝沿袭“大越”国号,继承了前朝的法统和国统,尽管明朝削“安南国王”为从二品“安南都统使司”,但并未影响莫朝在国内称帝以及统治地位。明朝则依据“安南都统使司”的定位给予相应的待遇。但莫朝“安南都统使司”的地位在以中国为主导的藩贡体系中却低于朝鲜的“国王”爵级,引起朝鲜使臣的轻视。莫朝引发的藩贡体系秩序的变化是莫朝历史价值和意义的重要体现。以莫朝为出发点的越中关系研究和以中国为出发点的中越关系研究有极大的差异,立场与观点往往相左,体现了越南在东亚区域历史研究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莫朝历史的特殊性、复杂性与中兴黎朝对莫朝的毁弃造成莫朝历史研究具有极大的难度和局限,作为莫朝延续的高平莫氏政权虽在明、清王朝的庇护下得以存于一隅,但在中兴黎朝的挤压下逐步灭亡,莫氏族人则继续活动。黎莫相争时期的对峙与人臣的选择,莫朝时人及后世史家不同的认识和评论,中兴黎朝对莫朝的诋毁,造成对莫朝的认识不足甚至错误。因此,应对莫朝——高平莫氏政权——莫氏家族做一个系统、整体的研究,体现莫朝在越南历史研究和对外关系研究中具有突出的史学理论价值和意义。
莫朝是越南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由此引发了之后的郑氏固守北方和阮氏南进开疆,随之而来的郑、阮百年战争进一步加大了越南的分裂,又导致了阮氏在南方的大力开拓,并最终由西山朝统一南北,实现了国土的“大一统”,也奠定了现代越南疆域的基础。《王室后裔》在莫氏政治演变、藩贡体系、代际转换时期的越中关系等领域均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鉴于莫朝历史研究的复杂性和突出的史学价值,其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1] 〈日〉河原正博:《丁部领の即位年代について——安南独立王朝の成立年代に关する一研究》,日本《法政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5号,1969年。该文认为丁部领称帝在乾德四年(966)。
[2] 参看叶少飞《丁部领、丁琏父子称帝考》,《宋史研究论丛》第16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
[3] 参看李焯然《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阐释》,《复旦学报》2008年第2期;王继东、郭声波:《李陈朝时期越南与周边国家的“亚宗藩关系”》,《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4期。
[4] 参看费正清主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中王赓武和张宝林的研究专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5] (越南·后黎朝)阮廌:《抑斋集》卷3《文类》,河内:通信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319页。
[6] 陈荆和: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卷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4-1986年,第55页。
[7] 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卷首,第57页。
[8] 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卷首,第84页。
[9] 可参看叶少飞、田志勇《越南古史起源略论》,《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年第2期。
[10] (宋)沈括著,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818页。
[11] Liam C. Kelley,“Narrating an Unequal Relationship: How Premodern Viet Literati Explained their Kingdom’s Relationship with ‘the North’”,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oundtable on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Relations among Asian Leaders and Polities from the 14th to the 18th Centuries”, 19-21 April 2010,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
[12] 〈日〉西村昌也:「ベトナム形成史における“南”からの視点——考古学·古代学からみた中部ベトナム(チャンパ)と北部南域(タインホア·ゲアン地方)の役割」,周縁の文化交渉学シリーズ6『周縁と中心の概念で読み解く東アジアの越·韓·琉』。
[13] 参看叶少飞《黎崇〈越鉴通考总论〉的史论与史学》,《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1辑,中华书局,2015年。
[14] 参看叶少飞《越南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编撰体例略论》,《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0辑,中华书局,2014年,第261-276页。
[15] 参看〈日〉片仓·穣《ベトナム·中国の初期外交關係に關する一问题——交阯郡王·南平王·安南国王等の称号をめぐって》,载日本《东方学 》第44期, 1972年7月,第40-105页。
[16] 〈日〉大沢一雄:《明末における中国·越南関係の推移》(《横浜商大論集》1971年第2月)一文于此论述更加详细。〈日〉山本达郎主编《越南中国关系史》第六章“黎朝中期与明清的关系”(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第363-364页)为大沢一雄撰写,亦有此论,但论述较前文简略很多。
[17] 陈文源、李宁艳:《莫登庸事件与明代中越关系的新模式》,《暨南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1期。
[18] 《明世宗实录》卷273,第5366页。
[19] 《明世宗实录》卷302,第5736-5737页。
[20] 《明神宗实录》卷113,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第2157页。
[21] 《明神宗实录》卷226,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第4202页。
[22] 《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2年,第799、801、803页。
[23] 《明世宗实录》卷540,第8745页。
[24] 参看〈日〉松浦章:《嘉靖十三年的朝鲜使者在北京所遇见的琉球使者》,载《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葛兆光:《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复旦学报》2012年第2期;沈玉慧:《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朝鲜使节与安南、琉球、南掌三国人员于北京之交流》,《台大历史学报》2012年12月。
[25] 参看〈日〉清水太郎「 ベトナム使節と朝鮮使節の中国での邂逅(3)——1957年の事例を中心に」,『北东アジア文化研究』第16号,2002年10月;陆小燕、叶少飞:《万历二十五年朝鲜安南使臣诗文问答析论》,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9辑,中华书局,2013年,第395-420页)。
[26] 郑永常:《一次奇异的诗之外交:冯克宽与李睟光在北京的交会》,《台湾古典文学研究集刊》2009年7月创刊号。
[27] 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卷之一, 第1008页。
[28]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之三十四,台北:“中央”图书馆1969年影印,第3090-3091页。
[29] 陆小燕:《康熙十三年安南使者的中国观感与应对——兼和朝鲜燕行文献比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0辑,中华书局,2014年,第256页。
[30] 参看叶少飞《越南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编纂体例略论》,《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0辑,中华书局,2014年,第261-276页。
[31] 参看叶少飞《黎崇〈越鉴通考总论〉的史论与史学》,《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1辑,中华书局,2015年。
[32]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8页。
[33] 参看夫马进《朝鲜燕行使申在植〈笔谭〉所见汉学与宋学的论争及周边》,《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9-87页。
[34] 参看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第二编《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35] 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五,第841-842页。
[36] (越南)丁克顺:《越南莫朝历史研究》,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37] 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五,第840页。
[38] (越南)丁克顺:《越南莫朝历史研究》,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0-11页。
[39] (越南·莫朝)杨文安:《乌州近录》,河内:越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17、219页。
[40] (越南·莫朝)杨文安:《乌州近录》,河内:越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18页。
[41] 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六,第851页。
[42] (明)欧阳必进撰,方民悦辑《交黎剿平事略》,嘉靖三十年刻本,1941年郑振铎辑入“玄览堂丛书”,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卷二。
[43] 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六,第855页。
[44] 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六,第866页。
[45] 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六,第856页。
[46] 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六,第863页。
[47] 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七,第881页。
[48] 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七,第897页。
[49] 韩周敬:《“横山一带,万代容身”考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第6辑,西安地图出版社,2014年。
[50] 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六,第860-861页。
[51]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6,中华书局,1992年,第233页。
【责任编辑:邓仕超】
The Heaven Separated the South and North, China and Vietnam Proclaimed Emperor on the Two Directions: Review onRoyalDescentandRebels—TheRelationshipBetweenVietnameseMacFamilyandChina
Ye Shaofei
(Internationnal Center of Vietnam Studies, Honghe University, Mengzi 661199, China)
Keywords:Royal Descentand Rebels;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Change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y; Suzerain-Vassal Relationship; Mac Dynasty in Annan; Mac Family in Cao Bang
[中图分类号]K3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6)01-010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越南古代史学研究”(15CSS004)。
[作者简介]叶少飞,红河学院红河州越南研究中心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5-07-10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暨南大学魏超博士、韩周敬博士的帮助和建议,在此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