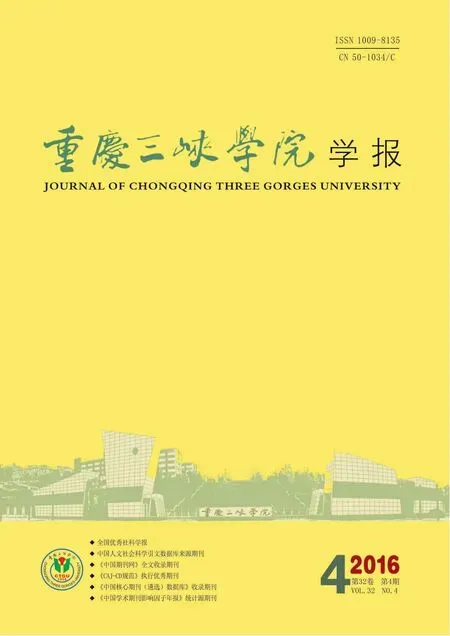文化工业与数据库:论广告的权力控制
叶蔚春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文化工业与数据库:论广告的权力控制
叶蔚春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摘 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通过广告、电视等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文化工业导致了文化产品的商业化、标准化与齐一化,人们在这种单向度的社会里成为了同质化的消费者,不再具有反抗意识,变成单向度的人。广告通过制造出虚假的需求来维护其意识形态,在信息时代,广告更是通过建构数据库来监控大众。数据库是一种全景监狱,它监控每个人的个人生活并对人们进行身份建构与定位,这种定位最终成为统治阶级对个体统治的依据。
关键词:文化工业;虚假的需求;全景敞视主义;数据库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通过科学技术、大众传媒、广播、电视、电影、电视剧、广告等更为隐蔽的方式继续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评价一则广告是否成功往往是看其所带动的销售量的多寡,因此广告通过消解个体的独立性思维,削弱其判断力来诱导消费者购买产品。广告通过制造出虚假的需求来维护其意识形态,为了达到控制消费者的目的,它甚至通过建构并监视数据库来监控大众。
一、承诺、自由与需求:虚伪的文化工业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是“从事精神符号和相关载体的独创性生产、大规模复制、商品化交换和体验式消费的一门产业。”[1]87电视、电影、广告、广播等符号化程度高的媒介,对载体的依赖度低,容易进行大量复制,因此居于文化工业的核心地位。文化工业的出现意味着文化商品化,文化领域也开始遵循市场交换原则并进入工业化生产轨道,采用现代工业的生产模式。在法兰克福学派里,本雅明关注的是技术对影像作品造成的异化,通过复制进行大规模生产,作品失去了灵韵,本真性、神秘性也随之消失,而霍克海默、阿多诺与马尔库塞关注的是媒介如何成为意识形态工具。
文化产品借助技术被大规模生产传播,虽然产品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但也丧失了审美价值,变成了没有独特性的商品,“文化工业……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2]121在这种趋势下,文化实现了标准化和批量生产,形式不再多元,符号变得更加单一和空洞。文化生产的齐一化导致了主体独立性的丧失,大众成为文化工业的俘虏,不再主动创造产品,“每个产品都是巨大的经济机器模型”。[2]114在文化工业的统治下,个体是原子式的个人,是可替换的、无差异的消费者,人们融入整齐划一的标准化中失去个性,被赋予消费者这一同质化的身份。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作为国家的传声筒传达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通过电影、电视、广告等形式对大众进行思想灌输和操纵。文化工业将影像、娱乐转变为现实的一部分,通过制造虚假的需求来控制大众,企图将其变为无差别的消费者。资本运转流通的过程中,需要借助媒介来对商品进行宣传与推广,表面上媒介是传播信息的载体,实质上媒介履行着思想控制、政治引导的功能,企图将统治阶级的声音融入社会生活,制造虚假的需求,塑造单向度的人。文化工业编造出社会公平的神话,承诺给人们虚伪的诺言,使处于中下层阶级的消费者们认为只要通过努力就能提升阶级地位,只要奋斗就能实现梦想。时下流行的娱乐节目《中国好声音》就不断强调参赛者的梦想,形成了一种只要自身努力、坚持梦想,最终就一定能成功的幻象。文化工业同时还通过提供娱乐活动来麻痹消费者,“快乐意味着什么都不想,忘却一切忧伤。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孤立无助的状态……快乐也是一种逃避……是要逃避最后一丝反抗观念”。[2]130文化工业不愿做出承诺,无法提供有意义的解释,它“把自己造就成蛊惑权威的化身,造就成不容辩驳的既存秩序的先知”。[2]133
相对于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有着人身自由,但这种自由是虚假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在形式上得到了保证,每个人从一开始就被禁闭在教堂、俱乐部、职业群体以及其他有关的组织系统之中,所有这些系统,构成了最敏感的社会控制工具。谁要是不想破产,谁就必须严格遵照这个机制的规定工作……从根本上说,人们的生活标准与阶级和个人同系统的结合程度有关”。[2]135-136因此,人们即便明白文化工业的欺骗性,也无法对其提出质疑,只有与其紧密结合才能融入社会。对文化工业的反抗意味着个人与社会间的剧烈冲突,为了保全自身,人们往往会避免发生冲突,也就是说,人们宁愿忍受文化工业对大众的欺骗,也不愿为反抗可能造成的冲突冒险,久而久之,人们便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与反抗精神,循规蹈矩彻底取代了独立思考。
在消费社会里,广告为消费者提供市场与产品的情况,这既有利于消费者在繁多的商品中快速做出选择,也帮助不知名的经销商卖出产品。生产者为广告所投入的成本最终也能在销量上得到补偿,因此生产者通过加大广告的投入就可以增强竞争力、打败竞争对手而不必非得通过更新设备、提高生产效率等较为复杂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种产品都不得不使用广告。“广告是一种否定性原则,一种能够起到阻碍作用的机构:一切没有贴上广告标签的东西,都会在经济上受到人们的怀疑”。[2]147对一些仅仅通过广告来宣传产品的企业(比如脑白金、黄金搭档)来说,不再对现有广告加强宣传会丢失已有的效果,因此它不得不加大对广告的投入,加大投入的同时也能证明其经济实力,增大消费者对其的信任。
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工业社会是单向度的社会,人们丧失了自由与创造力,不再拥有想象、追求另一种生活的能力,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在这个单向度的社会里,技术与消费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新形式,产品通过广告给予消费者虚假的承诺,表面上平等的消费也遮蔽了人们之间实质上的差距,统治阶级为了加强控制也将虚假的需求强加给人们。大众媒介常常把艺术、宗教、哲学等与广告混在一起,共同构成商品的形式,所以文化的领域也是商品的领域。为了避免企业干涉媒体,破坏其公正性,各国在立法时均倾向于将新闻、娱乐节目等和广告分开,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广告仍然成为企业控制媒体的工具。由于媒体的报导对消费者选择商品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商家总是竭力避免企业的负面信息曝光,一旦某家媒体得到了某企业的负面消息,该企业的公关就会与媒体进行沟通协调,动用各种关系来阻止节目的播出。如果阻止失败,就会以撤销广告为威胁,某些媒体为了播放广告时所能获得的巨大利益,宁愿丧失职业操守,撤下节目来包庇企业。除了直接在媒体上播放广告外,企业有时也会把相关信息融入综艺节目中来借机宣传。最为常见的是企业以节目赞助的形式来控制节目,有的节目甚至是为企业而设的,如央视红极一时的综艺节目《幸运 52》,比赛中用以表示参赛者能力的不是分值而是商标,屏幕上显示的不是参赛者所得总分而是具体的每个商标,这些赞助商标不断出现在观众眼前,构成了节目的组成部分。
在双向度社会里,人们既能顺从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也能反思统治阶级制度的不合理性,个人既活跃在公共空间里,又保存着私密的个人空间。然而在单向度的资本主义社会,私人空间不断被公共领域侵占,媒介齐一化带来的是人们失去了选择与决断的空间,丧失了否定性思维,变成单向度的人。统治阶级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带给人们商品、服务的满足,商品中包含的意识形态给人们提供了足够的思想、情感和向往,人们对既得利益感到满足,并且明白任何对现有制度的反抗都有可能失去既得利益,因此人们不愿反思,不愿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丧失了否定性思维和反抗的能力,屈从于制度的操纵。
人们没有反抗的原因还在于反抗对象的模糊化。在传统社会,社会的统治具体到人,最高统治者往往是人们反抗的目标,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细化到极致,具体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权力相互制约,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依然受到他人的制约,因此真正在统治人的是制度。人们虽然在这个制度里享受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个体感受到的挫败、痛苦与无助也来源于制度。制度不仅满足和控制了个体的需求,而且组织起了个体的生活,使得人们失去攻击的对象,“仇恨所遇到的都是笑容可掬的同事、忙碌奔波的对手、唯唯诺诺的官吏和乐于助人的工人。他们都在各尽其责,却又都是无辜的牺牲品”。[3]74-75即便是人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生活受制于制度,但由于大部分的人都与自己的境遇相同,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人们的愤怒不满很快就会变成心平气和的自我安慰。
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受到了广告的影响,将虚假的需求与真实的需求混淆起来。马尔库塞认为虚假的需求是强加给个人的需求,“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4]5-6之所以说它是强加,是因为这并非消费者的本意,而是广告通过提供虚伪的承诺与平等的假象所造成的幻象,让人们误以为购买可以建构自我、完成自我认同,因此由广告所引导的消费与娱乐是虚假而非真实的需求。真实的需求来源于消费者本身的需要,这里的需要就包含了马斯洛的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问题在于区分虚假的需求和真实的需求并非易事,购买商品既有可能是受到了广告的诱骗,也有可能是出于它的使用价值,社会有效地把外在需求移植到了人们体内,人们无法分辨自身的需求是真实需要还是由外在强加的。人是处于社会的动物,除了生理、安全等生物性需求外,大部分的需求是社会性需求。同一件物品,可以满足人不同层次的需求,这些需求既有可能是发自内心的,也有可能是外在的。人们购买汽车,可能是因为它可以体现出差异、地位,满足心理需求,也有可能是因为消费者受到了广告的花言巧语的诱骗,也可能仅仅是因为消费者真的需要一种代步工具。因此需求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应该由消费者自己来回答,但这种回答又难免带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只有当消费者在没有被灌输和操纵的前提下能够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回答时,这种回答才是有效的。然而,意识形态深入渗透社会的方方面面,自由或不自由,真实或虚假,其实早已无法区分。
法兰克福学派揭示的是文化工业与意识形态操控的关联,德波则指出了视觉影像控制下的社会秩序。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景观的无限堆积,它们遮蔽了统治的深层逻辑,诱导人们进入这种幻境。景观主要通过广告、娱乐、消费、服务等行业来麻痹、控制大众,在它们的作用下景观将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显现为一种表象,以隐蔽的方式支配着人们的欲望,使人们认同现有的统治制度。景观是一种隐性暴力,它消解了主体反抗与批判的能力,造成了人的分离,这种分离表现在人被异化为追逐利益的工具,财富的增长成为社会及人的唯一动力,由于劳动分工和生产机器的细化,生产者只负责某一步骤的操作,人成为某个动作的附属物,从而失去了个体的全面发展。因此,德波认为景观是“一种日益精确地将劳动分工碎片化为姿势和动作的自在发展的分离力量……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不断扩展的市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所有共同体和所有批判意识都消解了”。[5]8分离是异化在景观社会的表现形式,目的同样是揭示资本和意识形态操纵下的社会生活。
景观还通过支配非劳动时间来控制现代人,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个人用于谋生的劳动时间减少,用于个人发展的非劳动时间增多,劳动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然而景观对人的控制已经从劳动时间转向了非劳动时间、从生产车间转向了个人空间,它通过对人的无意识控制和制造虚假需求来驱动欲望,使得人们不断购买并非真实需求的商品。通过景观控制,资本权力在空间上与时间上都得到了极大地扩展,人们生活在福柯所说的全景监狱中,无处可逃也无法回避。
二、全景敞视主义视域下的数据库
电视广告将影像与声音结合起来,展现日常生活叙事性的同时也具有很高的拟真性,也就是说它既是真实的也是超真实的。广告的运作离不开创新与想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其实是一种无原作、无客体指涉的拟像。当今文化越来越多地由拟像组成,它们构筑的秩序是一种比真实还要真实的超真实,最有代表性的是鲍德里亚所说的迪斯尼乐园。迪斯尼通过建构虚拟的世界来吸引人们,游戏中的科幻、猎奇等都是对美国真实世界的模仿,通过参与游戏,虚幻世界变成了真实世界,从而唤起了游玩者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认同与向往。迪斯尼乐园内是拥挤的人群,乐园外是安静的停车场,园内的游戏、表演及热情的观众显示了人们的活力和生命力,狂欢唤起了人们的童趣,人们在短暂的幻境中远离现实,园外停放的汽车则一片死寂,这种强烈的反差显示了迪斯尼乐园的魅力和对人们的控制力。这种超现实魅力并不局限于迪斯尼乐园内,美国的许多居民区风格也以迪斯尼为样本,电影《加勒比海盗》也源于乐园内的游戏项目。
迪斯尼乐园既是生活的一种拟真,也是统治阶级控制形式之一,它是超级帝国的仿像,乐园里的一切都是受控制的,路线是预订的,步骤是一致的,即使是微笑也有弧度的规定,它掩盖了真实的世界,人们难以分清迪斯尼乐园中虚幻的美国与现实中的美国到底哪个是真实的。“问题不再是真实的虚假再现(意识形态),而是遮蔽了真实再也不是真实的事实,因此这是挽救真实性原则的问题”。[6]172一旦超真实变成了真实,“它所构筑的因素作为一种固定的自然秩序浮出水面并倾向于支配它的在场时,它们也就没有可以指代的原件了。社会变成人们可以随意进入(并付出代价)的主题公园的拼贴”。[7]65
数据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拟像。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个体的行为被随时随地地记录下来,人们的户籍信息、教育经历、服役记录、消费记录、通信记录、信用等级等数据信息被系统地收集在数据库中,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在统治者间传输、交换。与陌生人接触时,人们总是在暴露个人信息,用信用卡消费时,虽然面对的服务员是陌生人,但读取信用卡的系统却对消费者了如指掌,个体之间、个体与机构之间的关系被数据库逾越,隐私也不再存在。使用支付宝、微信付款更是将真实信息直接暴露给陌生人,这些本来是非常私密的信息由于被纳入数据库而留下了痕迹,而这些痕迹是被收集在个人名下的,因此数据库实际上形成了对个人活动有着详细记录的个人传记。数据库里的信息十分庞大,对于能查看数据库的人来说,个人就是一个数据集合,政府、军队、银行等机构不断地收集数据并相互传输,而数据所具体指代的个人却对此无能为力,他们甚至不知道这种数据库的存在。数据库可以带来可观的盈利,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信息,企业的命运常与掌控信息的多少联系在一起,在资本的角逐中,数据库变成商品,最终落入资本家的手中,社会开始由信息富有者来掌控。当数据库被掌控后,修改个人信息对控制者来说易如反掌,因此数据库的真实性也变得模棱两可。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用全景监狱来标示监狱的控制机制。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是福柯创造的一个术语,它源于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在这种全景敞视建筑中,瞭望塔只需一名监督者,通过逆光的效果,他可以从与光源相反的角度来观察四周房间里的动静。单独的房间使被监视者处在隔绝和观察的状态,也可以保证他们不会相互勾结、威胁,同时保证监视者的安全。被监视者是彻底被监视的,他可以看到监视他的是中心瞭望塔,但是在任何时候都无法确知自己是否被监视。为了确保被监视者无法知道自己是否被监视,造成监视者在场的未知,边沁建议瞭望塔的窗户装上百叶窗,大厅内部用隔板垂直交叉分割,各区域通行使用曲折的通道,避免光束或影子暴露监视者。事实上,当被监视者知道自己处在目光之下时,瞭望塔都是多余的,因为人们会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规范,最终促成统治者完成统治。
全景敞视监狱意指权力形式,它试图通过规训手段将犯人调整至能够服从监狱权威体制的程度,为了实现这一改造,规训机制里包括了详细的日常表现和对犯人的管理记录。规训不是预防和戒绝某种行为,而是对人的塑造和定型,关键在于对大众进行无时无刻的系统化隐秘监视。被监视者意识到只要行为与规范有所偏差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因此便不愿为此冒险,最终遵守制度就成为被监视者的主动选择,全景监狱也就构建了完美的犯人居民。事实上,监视者自身由于陷入自我定位中,他的行为也受到了规范的压力,“在这个管理的形式中,不存在一种单独的个人可以完全拥有、操弄而加诸他人的权力,在这个机器中,每一个人都被网罗,不管是权力执行者,或是受制者都一样”。[8]32数据库也是一种全景监狱,它给每个人都构建了身份,它对已有的个人信息进行分析,按照具体情况对他们进行分类处理,然后将这些信息在不同的电脑、系统间相互传输、补充,最终作出对个人的精确定位。这种定位很有可能会影响个体的生活,因为它可能成为个人被拒绝给予银行贷款的依据、成为警局对个人进行调查的证据、或者是成为拒绝个人居住申请等的根据。
虽然数据库里的信息并非正确或者公正(因为信息掌控者改动信息十分简单),也与个体的内在意识、自我界定等没有直接关联,但它却是社会针对该个体行动的依据,个人的身份是由数据库建构的,并且由于数据库的权威与便捷,个人对数据库给出的定位无能为力。政府、企业通过利用数据库加强对下层阶级的控制,维护自己的权力,随意处置数据库的特权也成了统治的重要环节。人肉搜索通常是由现实事件所诱发,以现实中的某个人物为搜索对象,查找并公布其真实信息的暴力行为,它之所以能搜索出个体的详细信息正是说明了数据库在对人实行监控与规训。信息时代的监控不再非得借助政治权力,只要得到对方的部分信息,通过追踪其在网络上的痕迹,将信息相互参照比对,最终就能得出真实信息,达到惩戒当事人的目的。
数据库如同全景监狱,它在暗中不断地运作、收集着个人信息并组建成个人传略。不同的是,数据库的犯人居民无需居住在特定的建筑内,他们只需继续个人的日常生活即可,因此数据库监控在表面上不会打扰人们。数据库中的人依据每一条信息与别人区分开来,大到拖欠银行贷款,小到借书过期。与以往的规训机制不同,数据库监控可以在瞬间布满网络空间,它与审查相比无需狱卒却更加地准确、彻底、详细,它使得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区分失去意义。信用卡消费是个很好的例子,消费者购买此物是私人的行为,可是当银联系统开始读取信用卡信息时这种私人行为就变成了公共记录的一部分。一个人对购物的选择,却变成了自愿参与的监控行为,人们提供给了监控者所需要的信息,销售人员只需输入极少的数据就能将信息补充完整,而隐藏在监控中的政治力量却因人们的自愿参与而逃脱指谪。零售商的数据库记录了个体每一次购物的数据,当购物次数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数据库就能准确地描绘出顾客的购物习惯图,并根据这个图来推测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为消费者推荐产品(亚马逊、当当网等大部分电商网站早已有了这种服务),掌握数据库对商家来说至关重要,商家可以通过选择特定类型的消费者作为目标群体,对他们投放广告,节省广告成本的同时也可提高广告的效率,增大购买力。
参考文献:
[1] 李辉.幻象的饕餮盛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5]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Mark Poster,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7] [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 [美]戈温德林·莱特,保罗·雷比诺.权力的空间化[M]//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陈志梧,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郑宗荣)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6)04-0099-05
收稿日期:2016-03-16
作者简介:叶蔚春(1989-),女,福建寿宁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
Cultural Industry and Database: The Power Control of Advertisement
YE Weichu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the ideology maintains the interests of the ruling class by mediums such as ads and televisions. Cultural industry had led to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s, in which people had become the one-dimension consumers. They had no longer the consciousness of rebellion. Advertisement succeeds to maintain its ideology by creating the false demands. In the information era,advertisements monitor the public by constructing the database. Database is a panoramic prison, which monitors everyone’s personal life and constructs individual identity or the position in society, which eventually become the basis of ruling class.
Keywords:cultural industry; false demands; Panopticism; datab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