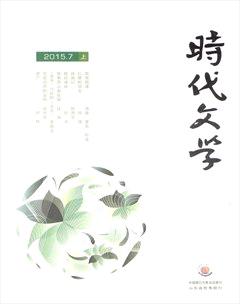仁慈的目光
阿成
黑龙江这个地方起名字都和当地的山、水、植物有关。这是很美的,预先便有了可视性。啊,你看这漫山遍野的芍药,你看旁边的那个小镇子,没错,它就是芍药镇。
芍药镇在一个平缓的坡地当中,周边的山丘,即突起的一丘一丘的平原,都长满了健硕妖艳的野芍药花。这儿的野芍药花的花球,朵朵都像鸡蛋那么大,而且生命力极强。我母亲活着的时候很喜欢野芍药花(这可能跟她是满人有关系,满人都特别喜欢花)。后来母亲走了。从那以后,凡母亲的祭日,我都要去野芍药坡那儿采来一束芍药花供在母亲的遗像前——半个月过去了,野芍药依然艳美如初,母亲一定会很高兴。
野芍药镇因醉人的芍药花,成了一处旅游观光的好地方。其实,在解放前,到了野芍药花盛开的时节,这里的游人就不断了。一方面是和喜爱的野芍药花有个约会,另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在战火四起的年代,这儿就像一处天赐的世外桃源,幽静,平和,安逸,安全。
野芍药镇虽然称之为“镇”,但版图并不大,小镇上像样的街只有一条。这条镇街类似今天的商业街,除了一些旅店和饭馆之外(包括我们现在称之为的“家庭旅馆”),其他的如药店、小诊所、鞋店、雨具店、邮局、浴池、服装店,还有书店和眼镜店(挺文化吧),正所谓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就是那家眼镜店的小老板。
记得那是一个芍药花含苞待放的时节,已经有游客陆陆续续地来了。小镇上的人们正满心欢喜地为游客们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这也是一年当中小镇人最开心的日子。只是万没想到,一架侵华日军的飞机飞到了小镇的上空,还投下了几枚炸弹。这一下彻底打破了小镇的宁静,让那些观赏野芍药的外地人大惊失色。不过,事后表明,这并不是日军要侵占和进攻的信号。只是到了今天我也搞不清楚,日军的轰炸机为什么要在这里丢下几枚炸弹呢?我们这一带既不是军事要地,也不是国军和共军的军营,不但在军事上没价值,就是在经济上,也不像那些有森林、煤矿、金矿的地方有利可图。它就是一片偌大的野芍药园而已。后来,有人根据日军的狼性推测,一定是小鬼子看不得如此美丽的风光,才扔下几枚炸弹破坏一下。也是警告这里的人们:日本人无处不在。
轰炸后的第二天上午,小镇又恢复平静了。我正在店里打扫灰尘,准备迎客。或许有人会插嘴说,芍药镇还缺一个眼镜店吗?况且芍药镇的人视力都很好,仅有老年人需要戴老花镜,但老花镜家家都有一副,代代传下去就够用了。说的没错,可是您想到了吗?在那些外地来的游客当中,有不少是戴眼镜的人。在那样的时代,能出门去旅游,特别是到一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芍药镇来欣赏芍药的人,如若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成行的。而且他们当中很多是文化人。您知道,有文化的人十个有八个是戴眼镜的。除了戴近视镜的外,不少游客为了防止强烈的紫外线照射,或者为了时髦、风度、酷,还会戴上墨镜(今人称“太阳镜”)。您想啊,千里迢迢地来了,又走这么远的路,鞍马劳顿的,难免他们当中的哪位,眼镜会一不留神出现一些损坏,怎么办?这就需要找眼镜店帮他们修好。我的眼镜店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开张的。没错,您也看到了,我的铺面不大,仅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堂铺。怎么说呢?以此维持生计倒也说得过去。毕竟我的主顾都是一些有钱人。即便是穷,也是穷大方的人。我喜欢他们,为修配眼镜的客人免费提供咖啡。
至于为什么我能够在这样一个几乎默默无闻的、幽静的小镇上开成一家眼镜店,这还要回到我的少年时代。少年时,由于家里生活清贫,于是,我就被父亲送到城里(离小镇大约有三天的路程)的一家有钱人家当小工,或称“仆人”。我去的时候 ,非常巧,正赶上这家的少爷准备去瑞士留学,为了照顾少爷的生活,老爷就安排我做少爷的小使唤,跟他一块儿远渡重洋去瑞士读书。还专门去成衣铺为我做了两套衣服,穿上之后,我的形象一下子变了。
我们去的是瑞士的首都,伯尔尼。伯尔尼同我的家乡芍药镇差不多,除了周边的风景好,重要的是那里没有战争。到了伯尔尼之后,开始的那一段日子,少爷在伯尔尼大学读书倒也安心。我虽说是他的仆人,其实就是他的一个伴儿。有时候少爷让我跑腿儿,去市场街给他邮信、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或者零食之类的(他怎么那么爱吃零食呢),其他就没什么事了。当然,毕竟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为了方便同西方人交流,我就陪着少爷一块儿学习当地的语言(主要是我问,他答)。瑞士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是说德语的。听说世界上最难学的那些语言当中就包括德语。可我倒是没觉得怎样辛苦。自然,我说的德语不能和少爷相比。但是那些普通的日常用语,仅半年时间我就能应付自如了,还能读懂街上商店牌匾上的字和一些商品的名称。
少爷很好,在我们一块儿出门玩儿的时候,去苏黎世,去日内瓦,去巴塞尔,去洛桑,去少女峰等地,他都严厉地告诉我,不准我管他叫少爷,叫表哥。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他的表弟了,他也是这样称呼我的。开始我以为这是一种友谊,后来明白了,这是少爷的一种心胸、境界、文化。什么叫文化,就是更广阔的胸襟。总之,在瑞士陪读期间,我和少爷处得就像亲兄弟一样,甚至连洗衣服、打洗脚水这样的一些本应由仆人做的活儿,少爷也不让我干。他告诉我说,你应当自立、自强,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我就嗤嗤笑,他看着我这副怪样子很生气。没错,他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不过,我们很快又和好如初了。记得少爷还挺感慨地说,青年人之间的事好办。中年人之间就麻烦一些。到了老年,一切都看开了,人也客气得很啦。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少爷的眼镜经常坏(他想事的时候喜欢摆弄眼镜玩儿),不是眼镜上的鼻托掉了,就是连接眼镜腿上的螺丝搞丢了。他还自圆其说,男人嘛,就这样。他这样,我就得去市场街找眼镜店为他修理坏掉的眼镜。不过这也挺好的,不然我在瑞士干什么呢?咋自立,咋自强啊?再者,我还可以趁机看一下伯尔尼这座静谧安详的袖珍城市。我喜欢走在那条16世纪的拱形长廊里,拱廊总共有七八公里长,里面是大商场、时装店、珠宝店、古董店、钟表店、工艺品店、甜食店、巧克力店、咖啡店和饭馆等等。没错,伯尔尼以“表都”著称,钟表商店比比皆是;伯尔尼也被称之为“泉城”, 而且每个泉都有泉柱塑像,像希姆逊喷泉、安娜塞勒喷泉、旗手泉、风笛手泉、摩西喷泉、黎夫里喷泉、射手喷泉等等。我最喜欢去看克拉姆街上的那个古老钟塔。正点敲钟时,钟盘下方就会有一个浑身披金的小机器人开门出来,用锤子敲打头上的钟,同时还有“时间老人”挥动手中的琵琶,一只公鸡出来打鸣,一对小熊也跑了出来,非常奇妙有趣。据说,这座钟的机件是16世纪瑞士制造,是瑞士钟表工业和海尔维希亚文化艺术的象征。
我经常去的是那家“仁慈的目光”眼镜店。那儿的老板都认识我了,我是他们这里的常客嘛,这样彼此很快就熟悉起来。我去那里不单单是修少爷的眼镜,连他同学的眼镜坏了,也会把修理的任务交给我(给我小费的)。通常,假如某个眼镜损坏得并不严重,反正我又没什么事,就坐在店里等。说实话,喜欢喝咖啡的习惯,就是在这样的等待中慢慢养成的。那家眼镜店的老板,还有他的女儿玛蒂娜·穆勒,对我这个来自遥远国度的东方人十分好奇,经常问这问那。遗憾的是,虽然我一下子跑了这么远的路到瑞士来,但对中国的那些名胜山川还是一无所知的。我只知道世界上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芍药镇,一个是伯尔尼。这样,我也只能给他们讲芍药镇的风光,讲小镇上人们的生活、风俗,怎么娶媳妇,怎么出殡,怎么看花灯,特别是在野芍药花盛开的季节,我们那里的美妙景色。他们都听直了眼,张大了嘴巴,觉得难以置信,对我的家乡芍药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就装腔作势地邀请他们有机会到我们芍药镇来做客。我还进一步地诱惑他们说,我会做一种用芍药花瓣做的小点心,不仅好吃,而且芬芳扑鼻。玛蒂娜·穆勒立刻尖叫起来,上帝啊,那是怎样迷人的美食啊。或者是因为我的故事对他们非常有吸引力,因此他们将我送去的每一副眼镜都修理得特别仔细,特别好。这样我们就不仅仅是熟人,也成了朋友了。
有一天,老板突然问我,年轻人,你为什么不读书呢?
我就撒谎说,我不喜欢读书。
他诧异地说,那你总得有一个吃饭的手艺啊。
我说,说得是啊。不过,车到山前必有路吧。
他想了想说,这样吧小伙子,你跟我学习修配眼镜吧,将来你就可以靠它来养家糊口了。
我说,这要回去问问表哥,他要是同意,我没问题。不过说实话,先生,我对修配眼镜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啊。
老板笑了笑说,我们还是先试试看吧。
就这样,我成了“仁慈的目光”眼镜店的一个不定时、不定期的小学徒。从那以后,我开始了解到世界上那些最有名气的眼镜,如德国的罗敦司得眼镜、意大利的古奇欧·古孜眼镜、美国的雷朋(鹏)眼镜、德国的bc眼镜、法国的法兰眼镜和意大利的宝格丽眼镜,等等。在这之前,我从没想到这些样子都差不多的眼镜,还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每当老板和老顾客聊天的时候,他都会自豪地介绍我说,瞧,这是我的中国学徒,多机灵的小伙子啊。而我呢,也很快进入了“学徒”的角色,并且渐入佳境。没错,那种感觉可真不错,特别是玛蒂娜·穆勒教我的时候。
大约在瑞士生活了将近一年零九个月之后,一天晚上,我正趴在窗户那儿听街上的那个醉汉唱歌呢,这时匆匆推门进来的少爷对我说,听着,我要去法国。
我吃了一惊,问,什么时间。
少爷说,明天就走。
我心想,难道少爷也像街上的那个醉汉一样喝多了吗?
少爷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对我说,在瑞士,有许多著名的革命家、科学家、诗人,都曾在伯尔尼居住过,爱因斯坦就是在伯尔尼发表了他的惊世之作“相对论”的。
我说,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到法国去呢?在这里读书你也能成为那个什么斯坦啊!
少爷说,我去法国,是为中国寻找改良的火种。
我问,中国怎么了?
少爷说,中国病了!
接着,他解释说,对不起,我并不能带你一块儿去。
我吃惊地说,你是说,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可临来的时候老爷再三嘱咐我了……
少爷打断了我的话说,你要继续留在这里,按时替我收取老爷子邮来的学费和生活费,听明白了吗?
我说,有点儿明白了。是不是不让老爷知道你去了法国?
少爷说,这件事咱俩必须保密,懂吗?无论如何不能让我父亲知道。
他说,这样,我写给家里的信会先邮到瑞士,就是邮到你这儿,然后再由你转邮给我父亲。听明白了吗?
我说,我这儿就是一个中转站。
少爷以手做枪不断地点着我说,你小子太聪明了。
说实话,我喜欢少爷设计的这种方式,一想到老爷被骗的样子我就想笑,真好玩儿。
少爷走了以后,百无聊赖的我真成了“仁慈的目光眼镜店的学徒了。其实这挺好的,毕竟还能让我挣到一点儿外快,积攒一些钱。何况眼镜店还负责我的中餐和晚餐呢(少爷走了以后,我不吃早餐了,像西人一样喝一杯咖啡了事)。但最重要的是,我对修配眼镜这一行有感情了,真心地喜欢上它了。在我看来,一副眼镜就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它们就像一个圆圆的月亮和一个太阳连在了一起,世界在它们面前变得纤尘毕见。
学徒的日子一久,我也能单独地做一点儿简单的眼镜修配工作了。活儿干完了,效果还不错。老板用他那只粗糙的手弄乱了我的头发说,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一切都按照少爷与我约定的方式,乐此不疲地玩着“欺骗”老爷的游戏。略微让人皱眉头的是,少爷在写给我的信中常常会夹进去几句法语,这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好在那些我曾帮助修理眼镜的大学生中有人认识法语。不然真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这种游戏一直延续到了“五朔节”,就在过节的这一天,我收到了少爷发来的电报,他同时还给我汇来了回中国的钱。他告诉我:回中国去吧。他说,父亲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已经了解到儿子并不在瑞士,而是放弃了学业去了法国。
看来事情明摆着了,作为一个仆人,我已无必要继续滞留在瑞士了。这也是老爷的意思。不过少爷说了,如果我愿意留在瑞士继续当学徒也可以。他说,好在你已经能够自食其力了。何去何从,你自己定罢。
我想我还是回家吧,一个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孩子。记得老板的女儿玛蒂娜·穆勒在黄昏时,在后院的那棵自由树下,曾给我念过的瑞士诗人施皮特勒的那首名为《女歌手》的诗:
梦幻中
手携着手
在我家乡行走
我虔诚地
跟随在他们的最后头
……
我心戚戚,恨意难消
身带家乡的风尘
决意和那歌声分道扬镳
……
是啊,离别总是让人伤感的。临行前,眼镜店的老板送给我一套修配眼镜的器械,没有什么比这更加珍贵的礼物了。在我即将登上火车离开这个伤心地之前,在站台上,老板紧紧地拥抱了我,并在我耳边说,我本打算把女儿嫁给你这个家伙的。唉——别忘了给我写信。
难怪有人说,伯尔尼人反应迟缓,谨小慎微。瑞士人还打趣说:“千万别在星期五对伯尔尼人讲笑话,不然的话,他会在星期天做弥撒的时候笑出声来。”
说完,老板摊开双手,做了一个无奈的手势,意思是说:瞧,这就是生话。
在火车如蛇一样地逶迤行进中,我在心里说,您为什么不早说呢?如果早一天说,我就不走了。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姑娘啊,我喜欢她那双清澈得像马祖尔湖一样的蓝眼睛,喜欢她亚麻色的头发,喜欢她在自由树下为我读诗的样子……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别了,伯尔尼;别了,“仁慈的目光”;别了,阿勒河;别了,市场街上我熟悉的每一家店铺,还有巴伦广场上的伯尔尼大教堂;别了,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别了,神秘的少女峰;别了,玛蒂娜·穆勒——我可爱的姑娘。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颊,泪水是凉的……
回到芍药镇以后,我凭借着在伯尔尼学到的技能,在芍药镇开了一家小小的眼镜店。这是1943年的事情。正像我在开头说的那样,即便是1943年,小镇依旧静谧、安详,游人仍然络绎不绝。
眼镜店的生意还算好。在眼镜店门口,我设了一个露天的咖啡茶座,完全仿造瑞士的风格。每张木桌上都放着一钵盛开的野芍药花,并免费为顾客擦洗眼镜。我的手艺和服务得到了顾客们的赞许(还有我提供的味道纯正的咖啡)。
这样平静安逸的日子,被侵华日军的战机丢在这里的炸弹破坏了。第二天上午,傻子来到了我的眼镜店。傻子是小镇上靠捡垃圾为生的人。其实他并不傻,“傻子”是他的绰号。他经常将拾到的游客丢失的眼镜送到我这里来。我随便给他几个钱,就收下了,然后摆在柜台里等人认领。如果一年后仍无人认领,我就自行处理。我正在擦拭柜台上的灰尘,傻子就进来了,然后打开了一个小布包,包里面足足有十几架眼镜,看来这一回他收获不小。
傻子撇着嘴说,真可怜,这些人正在芍药坡上野餐呢,不承想,被小鬼子扔下的炸弹给炸死了。这些眼镜就是我从他们身上摘下的。
说完之后他认真地问我,你说,他们到了阴曹地府还需要戴眼镜吗?
我嗫嚅着说,谁知道呢,或许不再需要了吧……
傻子高兴起来,如获重释地说,是啊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想,这些东西也许你用得着哩。
看着这些沾有血迹的眼镜,我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真是罪孽啊。好了,都放在我这儿吧。
打发走了傻子,我开始擦洗这些不幸的人的眼镜。当我擦洗到一架坤式眼镜时,不禁大吃一惊。我分明看到了一架名贵的眼镜,宝格丽。天哪,玛蒂娜·穆勒不就是戴着这样一副眼镜吗?我的手开始发抖起来,心想,天下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吧?如果这真的是玛蒂娜·穆勒的眼镜,那么,她到了芍药镇为什么不来找我,而是直接去了芍药坡呢?疑雾重重,谜团重重。
我立刻奔出了眼镜店,去找傻子。很快在河边找到了他。
我问他,你是在什么地方捡到这架眼镜的?那个人是洋人吗?
傻子想了想,说,这我可记不清了,反正是在芍药坡那儿,人都被炸得七零八碎的。
我问,里面有女人吗?
傻子说,有啊,嘿嘿。
傻子笑了起来,说,我想起来了,还有两个洋人,一男一女,都挺年轻的,死的时候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我问,都很年轻?
傻子说,对,说不准还是一对呢。
我迫不及待地问,你还记得那个女人长的什么样吗?
傻子说,阿弥陀佛。人都炸得没模样了。我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这些眼镜摘下来的。
我拿出了那副宝格丽眼镜,问他,这架眼镜你还记得在什么地方吗?立刻带我去看看。
傻子说,晚啦,人都已经埋了。镇长叫来了一些人,连夜把他们埋在了一起。就在芍药坡那儿。
我立刻朝着芍药坡跑去。果然,在那儿我看到一座巨大的新坟。有几个男人正坐在坟边休息。显然,埋葬工作已经结束了。他们看到我,都很诧异。
我问,全埋了?
其中的一个解释说,时间一长,尸体就烂了……
他旁边的人补充说,还有天上的鹰。
又一个年长些的人说,老板,你来得正好,我们几个还不知道在他们的墓碑上写什么呢,你给起个名字吧。碑上总得有字啊。
我拿着那副宝格丽眼镜,默默地离开了他们。
那个人还在我后面喊,嘿,你怎么不说话呢?
我心想,写什么呢?仁慈的目光吗……
回到眼镜店后,我将那副宝格丽眼镜放在了柜台最显眼的地方。从那以后,我几乎天天盼望着奇迹发生。随后,我给远在瑞士伯尔尼“仁慈的目光”眼镜店老板写了一封信。我知道这封信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在信中,我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生活,并郑重地邀请他们父女能在野芍药花盛开的季节,到我的家乡来。对,我没提那副带血的宝格丽眼镜。没提。
芍药花开了又败了,就这样一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接到他们的回信。这年的春天,从那个无名的坟冢上长出了一棵小树。可镇上的人没人认识这是什么树,他们从来就没见过。我认识它,它就是瑞士象征着自由的“自由树”。在瑞士,到了“五朔节”那一天,当地人会在树上挂上旗帜和横幅,在树顶上还会放上一顶绿色的帽子,而这顶绿色的帽子被他们称作“特尔的帽子”。“特尔”是瑞士历史上一名自由战士的名字。
那副宝格丽眼镜依然静静地摆放在柜台最醒目的地方,像一双清澈的眼睛,仁慈地注视着每一个人。
芍药花开了又败了,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
责任编辑 李春风
邮箱:sdwxlc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