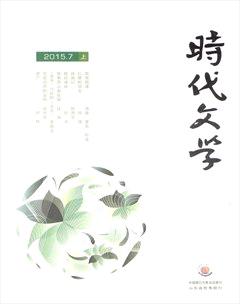父亲学木匠
李青军
我父亲生前是个出色的木匠,他老人家十八岁当学徒,二十二岁就开始带徒弟了。
在故乡,凡有众多木匠聚集做活儿的场合,就有我父亲掌尺划线的身影儿。他老人家一生教了八个徒弟,个个儿都是把好手。记得有一次徒弟们给我父亲过生日,酒席宴前,谈到当地同行,徒弟们都伸出大拇指赞叹道:“通过跟您四处做活儿,走南闯北,我们才知道,原来师傅您是彰武县以北,甘旗卡以南第一位掌桌的木工师傅啊,没人能比得了。我们作为您的徒弟,特别的自豪!”每逢这时,我父亲总是抿一下厚厚的嘴唇,微笑着慢悠悠地端起酒杯说:“那啥,你们是不知道哇,没看见当初我当学徒那会儿,彰武县东门外大掌柜老曾师傅对我那个严劲儿啊……”
二十世纪初,白马年,天下大涝。
遇上这样的灾年,庄稼人的日子会很难过,我爷爷因此在家里唉声叹气。我爷爷跟我奶奶说:“光指着地里的营生怕是不成了,老疙瘩业已年满十八岁了,壮壮实实的一条汉子,要不,送出去学点手艺?”
我奶奶说:“学手艺是好事儿呀,就是学徒费用太高了点儿,怕是咱家出不起啊。”
“多少呀出不起?”我爷爷疑惑地问。
“一年两石八斗谷,三年就是八石四斗谷呗。”我奶奶回答。
我爷爷闻听,猛劲儿磕掉锅儿里的烟灰,大声说:“只要是孩子他愿意去学,砸锅卖铁也送他去!”
听了我爷爷的话,我奶奶十分惊喜,马上说道:“你既是这么想的,我没啥可说的,那就赶快试试吧。”
我三姑夫在早在彰武县衙门口儿当过警察署长,跟东门外木匠铺掌桌儿老曾师傅交情颇深,听说我爷爷要借高利贷送我父亲去学艺,就来到我家对我爷爷说:“爹,您老别急着借那高利贷,年成不好,哪年哪月能还上啊?您执意要送我老弟去学木匠,不如让我讨一回脸皮,前去一试,赏脸更好,不赏脸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也不迟。”
我爷爷瞪着眼睛说:“那粮总得交吧?”
我三姑夫说:“问问再说吧。”
我三姑夫走后,我爷爷的俩眼圈儿就红了,两汪清泪热乎乎地噙在眼眶里。
第二天,我三姑夫就回来了。我三姑夫很高兴,进门儿就喊:“爹,娘,办妥了!办妥了!快给我老弟准备行装吧,明儿一早儿就动身。”
我三姑夫真有面子,老曾师傅跟他说粮可以不要,但有三条:一人体格得好,得有力气;二得老实巴交,还得不多言不多语;三得听话,最起码得叫东不往西。我三姑夫当场一一答应下来。老曾师傅又说,三年学徒期间可以白吃白住,但是不给开工钱。
我三姑夫交待完这些,就冷落着脸儿看我爷爷,等我爷爷的示下。我爷爷先是犹豫了一下,接着就爽快地说:“好吧,他三姑夫你咋办咋是。”
就这样,次日清晨,我父亲就顶着呼啸的北风,跟我三姑夫踏上了去彰武县东门外木匠铺的大道,从此拜在了老曾师傅门下当学徒。
老曾师傅的木匠铺开得特别的大,光作坊就有九十多间,大院儿里板材、圆木堆得像小山似的。老曾师傅整天耷拉着个脸子没有个笑模样儿。他的话很少,就像谁借了他黄豆还了他黑豆似的。可他人心眼儿不坏,是那种吐口唾沫就是个钉儿的主儿。
老曾师傅见到我父亲脸上就泛出了喜色,宽大的手掌“啪”地拍在我父亲的肩头儿上,说:“好体格!”铜钟般的大嗓门儿震得棚顶往下“唰唰”落土粒儿。接着就问一句:“十个木匠九个伤,你怕苦怕累怕受伤不?”
我父亲耸了耸肩,大声说“不怕!”说完就嘿嘿地笑了。
老曾师傅又问:“将来你是想领别人干活儿呢还是让别人领你干活儿?”
我父亲摸着脖梗子不知怎么回答是好。
我三姑夫在一旁笑了,悄悄给我父亲丢了个眼色。
我父亲定了定神儿,大声答道:“领别人干活儿!”
老曾师傅瞪大了眼睛,冷落着脸儿,盯了我父亲好一会儿,见我父亲没有一点儿心虚的表情,就乐了,又一掌拍下来,冲旁边儿喊一声:“张师傅?送给你一个“生牤子”(粗壮的三四岁公牛)。”然后,就把我父亲向前推了一把,说:“去吧,先去张师傅那里拉大锯。”
拉大锯是早年间木工做活儿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圆木只有通过大锯拉了以后才能成为板材或者方材等各种材料。“呲啦……呲啦……”一天拽下来,腰酸腿疼,更何况木匠铺大锯终年不撤,一拉就是一年。说实话,这种没完没了的活儿,很不适合我父亲那急于求成的性格。我父亲每天拽着大锯,心里就像着了火。拉了没几天,伙伴儿就有意见了,说道:“我说你能不能把锯拐子端起来点儿拉呀?你这么死拖死拉的啥时能学会拉大锯呀?你自己个儿受累不说,还拐拉得别人也跟着你胳膊腿儿地疼。”
其实,拉大锯真的是个有些技巧的活儿,掌握了,再拉起来就轻松多了。
有一天,我父亲拉大锯正拉得满头大汗,不知啥时,老曾师傅悄悄站在了他的背后儿。“涨梁!”老曾师傅突然吼了一声。把我父亲吓了一大跳,扭头看时,老曾师傅“咣”一脚踹在我父亲后背上,又吼一声:“哪瞅?跑线了!”我父亲面红耳赤,不敢再回头,就使劲儿地纠正着将要偏线的锯口儿。我父亲费了好大的劲儿,最后总算把锯口儿调整到了打在圆木的黑线上。大锯平稳地在木墩子上跳跃着。老曾师傅没有走去,一直站在我父亲的背后。此时,我父亲听到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接着铜钟般的声音又响起来:“水不来先叠坝,锯要跑线提前哪有不知道的?停下来找找原因就是了:一是锯料掰的不平,二是两臂使劲儿不均匀,三是涨压梁掌握得不准确。记住了?接着拉!”
老曾师傅说完了这番话,就头也不回地走了。按照他的一二三条,我父亲很快就掌握了拉大锯的本领。
木匠做活儿常用的是锛、凿、斧、锯,做起活儿来往往都是推、砍、凿、拉。内行的人看你做活儿的门道,看你是否经过了名师的真传,一看就能看出来。再有,看你活儿做得咋样儿,一看工具外表,二看做活儿的架势。老曾师傅认为:做木匠活儿没有好架势,做不出好话儿。
有一天,我父亲拿锛子锛圆木上的节子,“当当”地像握着一把刨地的镐,锛得深一块浅一块,木头渣子无规则地乱飞。老曾师傅看见了就过来骂道:“畜生!再锛,那根木头还要不要了?”劈把手就夺过我父亲手中的锛子,咬牙切齿地说:“我把你个没用的东西,看着!”我父亲双手抱着头,还以为师傅要用锛子刨他的脑袋呢。然而,老曾师傅却走到圆木旁边,轻轻地扬起锛子锛那节子。只听正面“啪啪”两声,反面又“啪”地一声,那节子就“噗”地飞落到后面去了。院子里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无不对老曾师傅的锛活儿发出“啧啧”赞叹。
其实,用锛子锛木头挺好学的,用上心几天就会。难的是用斧子砍木头。老曾师傅说:“千日的斧子,当日的锛子。”这话当然是实践中的精辟总结。使斧子手腕子得硬,还得软,抡不出花儿来,贴不住材料不行,砟泛不到线也不行。我父亲为了学会砍斧子,不知挨过老曾师傅多少骂。有一天,我父亲砍车大称,由于腕子硬度过大,一根好端端的柞木荒子,一斧子伤进肉里一寸来深。老曾师傅吼道:“笨蛋!告诉你多少回了?关键时刻手腕子要软活。软活,你懂吗!”老曾师傅嘴到手到,一记大耳光子扇到了我父亲的右脸上,接着又“咚”地踢了一脚,吼道:“搁下吧,别干了,去那边儿砍去。”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父亲拎着斧子走过去。那里有一大堆废板皮,五方杂木,薄的厚的都有。老曾师傅还在后边儿吼着:“今儿要是练不好你那腕子,不许回来!”
农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儿,过了小年儿就是木匠铺放年假的日子了。我父亲要回家过年,老曾师傅交待管事儿的给我父亲多带点儿粉条儿和猪肉之类的过年物品,并对我父亲说:“过了正月十五咱就开工,可别玩儿忘了上工的日子啊。”又说:“代我向你父母问好,给你爷爷奶奶请安,向你三姐三姐夫问好,说我老曾给他(她)们拜年了。”说着就从兜儿里掏出二百块现大洋递给我父亲,并说:“找个桶,到西烧锅老郛大爷儿那里灌一桶二锅头,带回去。”我父亲有些迟疑,没接那钱。老曾师傅吼道:“拿着!”我父亲不敢怠慢,接过钱再三致谢后就退了出去。
我父亲学艺那年的春节,是我三姑夫家和我家在一起过的。席间,酒肉丰盛,两家人欢乐异常。
正月初五那天晚上,我爷爷对我父亲说:“明天找两副犁辕子,投两副新犁杖,咱家那副旧的不好使了,换副新的,另一副投好了给你三姐夫家送去。”其实,我们家里那副旧的还能用,我父亲知道,这是我爷爷想看看他的手艺学得怎么样儿了。
正月初六一大早,我父亲就在早已备好的犁辕子堆里,挑了两副一弯三翘的黑桦木大犁辕子,然后就熟练地去皮、打节儿、挂线、凿眼儿;做犁拖拖、犁箭、犁底、犁把儿。“噼噼啪啪”,不到半天儿工夫就蹾上了犁铧儿。我爷爷一直蹲在院子里看。开始时,我爷爷的脸绷得紧紧的,到后来,就一会儿比一会儿地舒展开来,等我父亲蹾好了犁铧儿,穿箭插梭时,我爷爷一声呼喊站起来:“慢!”老人家走到我父亲跟前,抄起犁把儿,一拧个儿就把犁杖放倒在地面上,然后抓过一根小绳儿抻直了,一头儿放在犁拖拖底面,一头儿放在犁底底面,仔仔细细地量绳儿与铧尖的距离。我爷爷量完后直起腰,拍拍手上的土,满意地笑了。
春秋两季是木匠铺出售车棚的黄金季节。按照用户订做的先后顺序和特殊要求,选择该车棚的投料、计划工艺过程以及取车棚的时间。不管采用什么木料,加多少道工艺,做工过程都是一样儿的精细。用老曾师傅的话说就是:“差一点儿也不行!”
车棚质量的好坏关键在“拍”上,拍车拍车,拍不好,使几天就松懈了,甩厢了,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地响。这样儿的车棚售出去要是让老曾师傅知道了,不管用户使用了多长时间,一律收回来换新的。正是因为头几年接连换过几台质量不好的新车棚,再拍车时,老曾师傅就亲自把关。他骑在车辕子上,用手摸着车辕子眼儿两头儿留的凸边儿,翻过来调过去地看,并指点着说:“勒口大了。这是干辕条儿,收缩性小,大称拍进去,车辕子会崩裂的。”父亲他们就赶紧拿斧子、凿子整修那些勒口。老曾师傅问:“大称的榫头儿开好了吗?”“开好了。”“我看看。”我父亲他们就拿来车大称。老曾师傅一边挨个儿检查着,一边点着头儿说:“嗯,还行。不过,以后再开榫头儿时,不管什么样的榫头儿,都要留半个线。半个线懂吗?”他突然提高了声音,吓得我父亲他们立即回答:“懂了,懂了。”“哦,懂了就好。”老曾师傅一面自言自语,又一面“命令”我父亲他们:“驾过去,拍车!”
我父亲他们把车辕子平放在一溜儿漫圆形沙坑的地上。这是老曾师傅早就设计好了的沙坑,不多不少整十一个。这些沙坑深浅不一,是根据车大称的根数儿和长短尺寸设计的。两头儿的六个坑深一些,探出一块大称榫头儿穿车耳板子用;中间五个坑浅一些,榫头儿能透过车辕子外就行,长了,挡车轱辘害。这时候,单匹儿右手的车辕子眼儿里,我父亲他们就依次立上了长短不齐的车大称。接着又抬来左手的那一匹儿,摸着将其十一根大称上的榫头儿,依次按在眼儿里。有人抬来大板凳,放在车辕子漫圆形凹面的中间,人站在上面拍车时,可左右走动,榔头砸下去的重心刚好能落在车辕子要击打的部位上。
“哎嗨……耶……呀!”随着这一声吆喝,老曾师傅拎着十八磅木柄的铁榔头,轻飘飘地就蹬上了大板凳。我父亲他们几个人各自找个位置把着,还用绳子套住上边的车辕子,一只脚在绳套儿下边儿衬着,防止上边儿的车辕子进入勒口时,向上反弹。一切准备就绪,老曾师傅就高高地举起了榔头,随着一声声悠悠扬扬的“拍车歌儿”的节拍,铁榔头就有节奏地上起下落起来。
拍车啦哎嗨……耶……呀
拍车好快活
手中的榔头我高高地抬(哎)轻轻地落
拍好车(呐)哪怕那山高水长路坎坷
十吨八吨载得动(哩)
千里万里不学舌
啊呵呵嘿……啊呵呵
啊呵呵嘿……啊呵呵……
一曲唱罢,老曾师傅面带笑容,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儿,将那榔头握在手里,弯下腰去,面对上辕的底面,挨个儿检查眼儿榫儿的结合情况。末了就跳下大板凳,接过我父亲递过来的茶杯,“咚咚咚咚”灌下几大口温茶水,一抹嘴角儿喊了一声:“翻个儿!”我父亲他们就扛的扛拽的拽,把个车棚子硬是从沙坑里拖了出来,大翻个儿,按那十一个沙坑,将上匹排得整齐的大称榫子,分毫不差地投了进去。
这回,老曾师傅叫我父亲上大板凳。我父亲有点儿胆怵,但又不能不上。我父亲很沉着,前几个眼儿榫儿打得很顺利,几乎是三五下就合一个。剩下最后一个来了麻烦,居然砸了十多下没合。我父亲的手就有点儿抖了,气儿也喘得不是很均匀了。这时,老曾师傅说话了:“别慌,沉住气。”然后蹬上大板凳,手握一块方木垫在那眼儿榫儿旁边,喊声:“砸!”我父亲稳了稳神儿,高高地扬起榔头,但不是很重地落在方木上。“狠狠砸!”老曾师傅又是一声喊。这一喊,增长了我父亲的勇气。我父亲再次举起榔头,实实惠惠地砸了下去:当!“再来一下!”当!“妥!”老曾师傅扔了方木,拍拍手上的土,跳下大板凳,头也不回地回屋去了。我父亲他们忙弯下腰去,眼睛贴着那个捣蛋的眼儿榫儿细看,真的是严丝合缝了。我父亲他们当时非常纳闷儿:老曾师傅是凭什么知道眼儿榫儿合了的呢?
老曾师傅的木匠铺,除了做像车棚、犁杖、水车、磙框等应季的活计外,还承接建筑和日用品,如小板凳、大板凳、炕桌、地桌、箱子、柜子、椅子、办公桌、写字台、单双面儿洗衣板(那上面还刻有莲花儿、水草儿和鸳鸯等图案)、擀面杖、面板、菜板、菜墩等。建筑用品如门窗框、门窗扇、门眼龙、窗亮子等;有盖房儿的人家,先将这些买了去,再照这尺寸垒墙,省工省时省事儿。另外,还做装死人用的棺材。总之,好几十个木匠常年做活,很少有放假歇工的时候,故而库房里成品就堆得满满的,购买的人可进去随意挑选。
这一天,彰武县西南方向的高山台下,有户大人家要给老太太做寿材。这户人家有钱有势,讲气派,肯花钱。这家管事儿的前来洽谈时,呈上了东家写给老曾师傅的一封信。那上面写着:
曾兄您好:
多日不见,甚是想念,改日定登门拜访。
今有一事,拜托您:我家老太太虽说现身体康健,但考虑年岁已高,我想还是提早准备口寿材的好,您说是吧?
鉴于松木有味儿,采用柏木为佳。足四六,独底独天,内设凤床。怀头可采用榆木,有纹路,又喻前后有余、吉利、源远流长之意。寿材外表浮雕二十四孝图,不惜重彩。形状采用三圆式。
看在您我多年交情和老太太的份上,望曾兄以全力做此寿材。完工之日,乃是愚弟持以重金感谢之时。
见字如面,多谢!
士才上,三月十六日亲笔。
老曾师傅看完信,不免面泛红润,进而激动不已。想不到,官场之人也有求助于我这小小木匠的时候,遂觉有了地位,亦或受宠若惊,随即当场告知管事儿的:“请转告你家主人,此寿材落定将不出一月,当是彰武县近百里方圆内几十年来顶好的一口寿材也。”管事儿的当即抱拳说声:“谢谢!”便告辞而去。
要求如此之精良的这么一口寿材,我父亲他们从未见过,老曾师傅却应承下来了。可见这是个“硬活儿”。当下,老曾师傅就盘点师徒之中的“硬手儿人选”,准备木料。我父亲虽在当时不算什么“硬手儿”,但出于师傅的偏爱,也算在了里边儿。一月下来,寿材如期落成了。在这期间,我父亲实实在在地学到了一手儿攒寿材的“绝活儿”。
那天,宽大的作坊里的两根大方木上,搪着那口“奇材”。说它奇,当之无愧。不必说在朱红底色的衬托下,色彩缤纷的二十四孝肖像惟妙惟肖,也不必说那雄浑的柏木多么的得天独厚,光是那两边儿镶着水曲柳饰板的三圆式的榆木怀头和那内里安装的精美绝伦的柏木水纹凤床,就足够所有见到的人瞠目结舌了。在大家一片赞叹声中,老曾师傅乐呵呵地躺进去试了试,然后长叹一声说:“将来,我若是也能住上这么一口寿材,死了也不屈了。”说完就闭上眼半天没言语。我父亲他们听着,看着,就觉得好不凄凉,继而心里酸酸的,于是便连忙一齐上前将老曾师傅搀出棺外。
木匠铺里的活儿常年的做,倘若外边有人来请,也不推辞,仗着人多,大活儿小活儿全接。
这一天,彰武县西门外西烧锅财主郛大爷坐着一乘小轿儿就来到了木匠铺。他要在彰武县城十字街西北角儿盖个转角儿的楼房,亲自来请老曾师傅好好给他设计设计。老曾师傅摸着下巴颏儿笑呵呵地对郛大爷儿说:“咱老哥俩谁跟谁呀?还用说请?明天派人过去测测地基就是了。”“行,小工儿的活计我业已叫他们开工动土了,正好明天找准水平也好下返地槽。”
彰武县早先大买卖家很少,正街道就这么一趟十字街。十字街口儿就是这座小城的中心地段,也是最繁华的地段。西烧锅郛大爷儿家族从很早起就把持着十字街口儿西北角儿这一方风水宝地,世世代代勤奋地经营着买卖,很久以来一直生意兴隆。早年建成的拐角处的那两大溜儿土平房,几经翻修,到了郛大爷儿这辈上,终于推倒重建了。从此,彰武县就结束了没有楼房的历史。
那天测地基,老曾师傅是领我父亲去的。郛大爷儿家有个日本造的水平尺,可老曾师傅不让用。他说那东西好是好,但咱用不惯,咱还是用咱的水盆大碗得劲儿,三点成一线的方法觉着更可靠一些。老曾师傅叫我父亲盛满满一盆清水,稳稳地坐在建筑物中间的新土上。然后,在水里放一个空大碗,大碗在盆水中飘呀飘,盆两边儿粘上两块红纸。老曾师傅趴下身去,用两根秫秸秆拨正碗边儿,单眼调线,使两处粘了红纸的碗边儿对准地基角儿上的木杆儿。我父亲手持划尺子(老曾师傅发明的木工用牛犄角特制硬笔),守在木杆儿边儿上听指挥:“往上,再往上。好了好了。”我父亲于是就在那好了的点上横着重重地画上一道墨线,然后就转到另一个点上。“下,往下,再往下。”要找的点到了新返出的地面了,我父亲摇摇头刚要说话,老曾师傅一声喝喊:“挖!”我父亲立刻放下笔,扯过一把铁锹就挖起来。挖完了,又顺着师傅的视线铲了一溜儿沟槽儿,钉住了木杆儿,又开始测量。老曾师傅把每一个线点都看得非常仔细,怕大碗在秫秸秆的拨动下有误差,总是拨动一下以后,等水静了碗停了,才闭上一只眼睛,看那木杆儿上的点。由于测得认真、仔细,测这栋楼房的地基就整整用去了一天的时间,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才钉上四边的框儿,拉上水平线。于是,一个以水平线而勾画出来的楼房效果平面图,就清晰地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那天晚上,郛大爷儿差人将老曾师傅和我父亲请了去,肉山酒海地好一顿款待。老曾师傅一边喝酒一边说:“盖楼关键地基得打牢,地槽要一直往下挖,见到河卵石为止。墙壁呢要采用砖石结构,一层窗台以下是石头,垛为砖,上过木,钢筋混凝土过梁连着房盖儿;二层垛为木制排柱,连接大扇儿的窗户,窗上边鬏檩,檐雕龙刻凤,卷云脊,人字架儿,转角儿漫圆状如行云流水,门窗眼龙是戏水的鸳鸯,内装盘肠儿,六蜜夹菊……”老曾师傅说这话的时候,郛大爷儿的两只眼睛都直了。老曾师傅抬头看了看他,拿手在他眼前晃了晃,他才缓过神儿来,痴呆呆地问了一句:“真的?”老曾师傅一拍桌子吼道:“这还有假吗!”郛大爷儿当即喜笑颜开:“妥了妥了,这房子就当是你自己个儿的,使出你的绝招儿吧,拿出你的绝活儿吧,争取把这栋转角楼盖出特色!让全县城的人都知道是我郛大爷儿的楼房,都知道这栋楼房是你老曾师傅领着徒弟们盖的。来,为楼房的早日落成干杯!”
转角楼盖得很快。上梁那天,郛大爷儿差不多惊动了整座县城的大小官员、买卖人家和当街临街诸百姓,光鞭炮就从清晨一直放到中午,四面八方来道喜的人络绎不绝。临时搭起的凉棚里,煎炒烹炸正忙,香烟缭绕,香味扑鼻,顺十字街往街口儿看去,一路两排席桌摆放整齐,共一百二十张。
十点整,一阵激烈的鞭炮声过后,顷刻间万般寂静,只见黑压压的人群皆注目侧耳倾听。老曾师傅红布包斧,健步走上楼房架子顶端,徒弟们用事先准备好的滑车,吊上一根由郛大爷和老曾师傅俩亲自选定的脊檩。只见这根脊檩已经经过了特殊的包装,两头儿绑着鲜亮的红色绒绳,中间贴着花花绿绿的阴阳八卦图,另有用红绒线系着的筷子、铜钱之类的器物,很有些宗教仪式的味道。老曾师傅站定,清了清嗓子,挺起胸脯,敲一下脊檩,唱了一曲老百姓百听不厌的上梁歌儿《十次敲》。这歌儿喜庆、悠扬、梦幻,扑朔迷离,听了让人震撼,再加上老曾师傅那铜钟般的嗓音,更显得古朴、肃穆、庄严、厚重。歌儿中唱道:
上梁唻——
上梁啊先把脊檩敲
哎嗨……哟
哎嗨……哟
一次敲西山西海西森林(呐)
东山东海龙王庙
二次敲南山南海观音阁(呀)
北山北海黑龙泡
三次敲踏破铁鞋寻着了你(吔)
仙人指点你上房薄
四次敲灵山之木通古刹(了)
保佑东家逞英豪
五次敲锁住房梁公母扣儿(呗)
人丁兴旺邪气少
六次敲横托天上启明星(呢)
光宗耀祖尊天条
七次敲家居发福生财地(啊)
五谷丰登(吧)雨顺风调
八次敲指引东方一条路(唉)
艰苦奋斗康庄道
九次敲有时别忘贫时饥(咯)
勤俭持家人称好
十次敲吉祥如意年年有(哇)
一年更比一年高
上梁歌儿在十分热闹的喜庆气氛中结束了。房顶上的小伙子们呼喊着往上提吊上来的停在空中的脊檩。脊檩提到了人字架儿顶头儿上,放平,找准公母扣儿,“当当!”两斧子就扣严砸紧了,“妥了!妥了!”人们便纷纷到账房那里,把带来的礼钱往账桌上一放,看着由司仪官把随礼的钱数一一记到礼仪簿上,然后就涌入街口儿,坐在宴席桌边等候开席。
说起来那年真够顺利的了,刚盖完了郛大爷儿的转角楼,马上就有人来请老曾师傅去阜新市修造飞机场。听说是跟日本人在一起合作干活儿。老曾师傅当然不能错过这次锻炼徒弟们的机会,这次挑选的都是最精明强干的徒弟,由他亲自带队奔赴阜新。这个项目是辽西有史以来第一次与外国人合作建设的项目。师徒们真是大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老曾师傅的名声也由此跨出了彰武县,而酒量和脾气也随之涨了起来。
老曾师傅爱喝新出锅的二锅头,每天晚上都是我父亲提着锡酒壶到西烧锅现打,常年风雨不误。有天傍晚,天阴得像黑锅底似的,大街小巷很少有人走动,我父亲本来很害怕,但一想到是给师傅打酒,就咬咬牙壮起胆子,提起锡酒壶就上了路。然而,我父亲老觉得身边的黑暗处有什么东西在盯着他。我父亲急忙迅速向前跑去。不久,铜钱大的雨点儿就“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雨一会儿比一会儿大,风一会儿比一会儿猛,都九月末了,庄稼地里根本不再用雨。呸!死雨,无用的雨,凄风苦雨!
打完酒,雨仍下个不停。我父亲心想,老曾师傅正等着这酒吃晚餐呢,我得快回。于是,我父亲把锡酒壶嘴儿塞好,揣进怀里,一闪身就钻进了雨的夜里。
我父亲急速地往回奔跑着。雨水和汗水流进了他的眼眶儿,煞得眼珠子生疼。我父亲脱下湿透了的衣服蒙住脑袋,只露出两只眼睛。突然,一截断墙处“嗷”地一声嚎叫,吓得我父亲脚下一滑就栽倒在地上。借着闪电的亮光,我父亲看见是两只“叫羔子”(发情)的猫儿,正撅着尾巴在那里寻欢作乐呢。我父亲握着锡酒壶猛地蹿起来,骂了一句:“妈的,这么大的雨也挡不住你们撩臊儿。”
当我父亲像个落汤鸡似地喘着粗气站在老曾师傅面前时,老曾师傅的小炕桌上,早已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酒菜,白瓷酒盅也摆在桌上,烫酒用的大铁缸子里装有冒气的热水。我父亲二话没说,从怀里掏出锡酒壶就放进了热水里。
老曾师傅笑了,说:“去换件衣服吧,今儿晚上陪我喝两盅儿。”
我父亲坐在师傅身旁,给师傅倒酒。师傅说:“你也倒上,干一杯,驱驱寒。”我父亲无限感激,频频给师傅夹菜。酒过三巡,老曾师傅激动地对我父亲说:“我老了,快干不动了。我这一辈子教了几十个徒弟,最让我满意的就数你了。我要让你将来比我还强,答应我!”我父亲说:“师傅,瞧您说的,我怎么会比您还强呢?”“不!你一定要比我强!没看见人家日本人摆弄的那些个洋玩意儿吗?师傅我都没敢碰。但你们将来一定要碰,不但要碰、敢碰,而且还要使好它、使活它、使精它,还是那玩意儿出活儿啊!”我父亲握住老曾师傅的手,觉得他的手有点儿颤抖了。我父亲对老曾师傅说:“师傅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这就对了。”老曾师傅的嗓音有点儿沙哑了,眼眶里汪着两滴晶莹的泪水。他老了,身体已不胜酒力。在师徒两个的谈话中,老曾师傅的眼皮就有些发黏,不久就歪倒到炕头儿上“呼呼”地睡去了。
从此以后,我父亲几乎不离师傅左右。老曾师傅把他的“绝活儿”一件件全都传授给了我父亲。三年出徒以后,回到家乡,我父亲就边干活儿边教徒弟。他老人家一生总共教了八个徒弟,这八个徒弟个儿顶个儿地都是把好手儿,个顶个儿地都被乡亲们称赞为是乡村里的好木匠。
本栏责编 李春风
邮箱:sdwxlc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