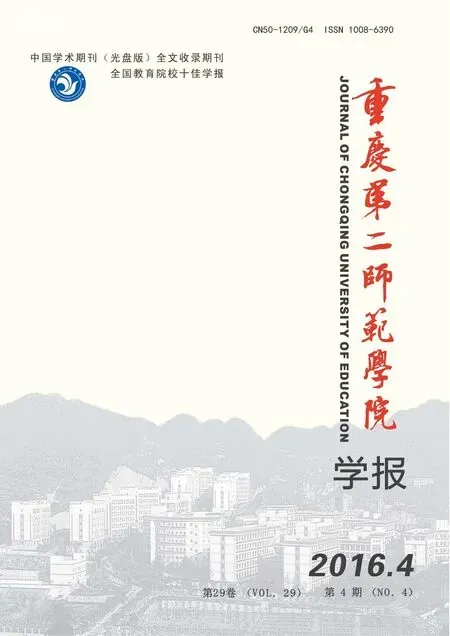历史与文本的互读——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解读谭恩美《接骨师之女》
谢 嘉
(广西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4)
历史与文本的互读
——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解读谭恩美《接骨师之女》
谢嘉
(广西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4)
“新历史主义”通过分析作品的故事文本与历史的相关性,关注琐碎、不为人知的“小历史”背后所体现的史诗性。谭恩美的小说《接骨师之女》在虚构的文本中展示不同时期女性的命运故事,将小说叙事空间从北京扩展到旧金山,在时空转变中完成了对中国女性隐忍不屈个性的歌颂。作品体现新历史主义学者所倡导的理论主张,因此可以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以期挖掘出被淹没的华裔群体的历史。
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引起人们重新思考文学文本与历史的关系,同时也令人们开始关注对旧有历史观念革新或创新与否的问题,这就是以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的意义所在。“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直接反对的是所谓‘旧历史主义’的学术研究。”[1]4在新历史主义学者们看来,历史不应再像学术界或者人们眼中存有的是一种正统而权威的记载,而应是许多琐碎、不为人知的事件的大集合。“过去的文学评论家对于文学研究的实践任务就是试图再现作者的原意、世界观以及当时的文化背景。”[1]4而旧历史主义学者们那套注重文学版本、校注等的研究工作已不能与现今的文学研究相匹配,他们将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抛在一边不谈,又假定过去与现在是有着必然、直接的因果联系的,旧历史主义者已经不能真正地理解与把握历史的效用,需要有新的、更内在的对于历史与文本关系的阐释与理解。同时,传统的旧历史主义者所认为的历史的“真实”实际上是人们观念构造的结合体,这种真实性只是人们单方面、主观能动的产物,具有想象的特质。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只是人们构造想象的产物,而普通人所经历的历史在新历史主义学者们看来更值得研究,小人物的历史由于是个人的切身经历且不为人知而更具有真实性。因此,新历史主义将一些逸闻趣事和普通人作为重点分析对象,通过挖掘他们经历的不为人知的小历史以刺穿传统历史的宏大叙事的堂皇假面,实现其反历史“真实性”的表述。在这种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倡导下,许多少数族裔作家通过讲述祖先或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的方式来引起大家对于那些被湮没与被边缘化的族裔历史的关注,为少数族裔群体建构属于自己的历史。
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于2001年发表的《接骨师之女》被认为是“谭恩美几部具有浓重个人色彩的作品中最突出的一本”[2]292,小说以半自传的方式讲述一家三代女性的不同际遇。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给予了历史极大的关注,通过呈现想象的历史事件与真实的历史相结合,可以看作是对历史与文本关系进行实践而得出的结果,所以可以从新历史主义学说所倡导的“历史的文本性”入手,来对《接骨师之女》进行文本与历史的分析互读。
二、历史的文本性
在新历史主义理论倡导者海登·怀特看来,历史与小说都是人们想象的产物,具有同构性,历史可以被看作是小说的一部分。在《接骨师之女》中,故事的主角选定在外祖母宝姨、母亲刘杨茹灵、女儿露丝这一家三代女性的身上,她们在完成血脉继承的同时,也将叙事空间从北京扩展到了旧金山,展现了中国女性隐忍坚强的个性。家族三代女性的命运由她们所经历的琐碎历史集结而成,大时代背景下的这三位女性的经历本是历史长河中不被人注意的尘埃,就这样由作者以讲故事的方式被放大而为人们所了解。无论是生活在美国现代社会中有着快速杂乱节奏方式的杨露丝,还是经历了北京怀旧气息生活以及目睹日寇侵华进而逃亡中转至香港,而后又在美国定居的刘杨茹灵,通过作者细致而周到的描写,人们了解了中国女性在跌宕时代中的隐忍与坚强,多角度的叙事方式让作品中的人物与读者一起成为作家构筑而成的“历史”的见证者。“茹灵在发现自己记忆力减退时,曾亲手写了一部记录自己家族历史的手稿,让过去永远地存在下去。”[3]远在大洋彼岸却仍不敢忘记民族的根,这部手稿展示的是华裔族群对于祖国的无限回忆与遐想,将家族命运与祖国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由此可见历史在作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它是小说里三代女性沟通中的结晶点,鲜活地保存了家族记忆,又能不断地延伸下去。
在《接骨师之女》中北京人的头盖骨被多次提及,它既是小说中的重要意象,也是典型的历史文本。这些头盖骨初始被认为具有医治百病功效而作为药引使用,随后便有考古学家发现这些“龙骨”其实是亿万年前的祖先“北京人”的头盖骨,更是出高价收购,引起人们争相开展挖龙骨行动。而宝姨家却因为拥有几块龙骨而被棺材铺张老板打劫导致父亲与未婚夫(即茹灵的亲生父亲)相继死亡。为了女儿茹灵,宝姨忍辱负重地活下来并以保姆身份陪伴茹灵。悲惨凄凉的生活境况被宝姨归结为龙骨所发出的诅咒,认为“不把全家人折腾死,鬼魂就没完。什么时候我们家人死绝了,才算完”[2]184。宝姨对龙骨满怀敬畏,但龙骨却被茹灵当作嫁与棺材铺张老板儿子的筹码泄露出去,宝姨为阻止茹灵嫁入仇家以及龙骨落入他人之手而愤怒自杀,并告知茹灵一系列真相。龙骨随后也落入了茹灵手中,似乎诅咒也仍在延续。在抗战爆发之后,茹灵的丈夫潘开京为了保护北京人遗址而被日本侵略军处决,这让茹灵更坚信龙骨的诅咒。最后茹灵为了能凑够船票钱去美国,以远离诅咒的困扰,而将家里的龙骨典当给了香港店铺老板。至于茹灵丈夫潘开京牺牲自己生命而保护下来的龙骨也完全失踪,不知散落于何处了:“骨头本该用火车运到天津,然后通过一艘美国船从天津运到马尼拉,但是船沉了。有人说装骨头的箱子根本没有搬上船。他们以为箱子里不过是些美国兵的东西,因此就把箱子扔到铁道上,让火车碾碎了……北京人的骨头失踪了。”[2]219历史上关于北京人头盖骨的记载与作者所描写的也有重合:大约从北宋时代起,北京周口店一带就有出产“龙骨”的传说。人们把“龙骨”当作天赐的良药,吸引了不少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来到周口店地区,进行发掘和考察。后经科学家分析证实,龙骨其实是人类祖先“北京人”的化石,而后进行大规模挖掘。1941年,由于形势严峻,北京人头盖骨被移交给即将撤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同年12月5日,该部队所乘火车驶往秦皇岛,但由于随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军队俘虏了北京、天津等处的美国兵,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4]将小说中龙骨的经历过程“药引——考古挖掘——诅咒——诅咒的延续——失踪”与史料所记载的龙骨历史“药引——考古挖掘——失踪”相比,发现小说中多出了龙骨诅咒的具体情节。“龙骨的诅咒”被作者放置在了不同人物的经历上,事件虽有不同,却都神秘地沿袭了“死亡”的相同点。大写的正统历史就这样在小说中具体化了,情节的丰富让读者更为真实地了解龙骨的坎坷历程,以及先辈们为了保护龙骨所付出的努力。读者仿若置身于这段历史之中,与书中人物共同经历了这一悲欢离合,所感受到的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情感与爱恨家仇,加诸读者自身的情感体验与情感投射,也让这段历史在不同的读者眼中变得更为主观,展现出的正是与历史的强有力对应,也呼应了新历史主义学者们所认为的历史是想象、虚构的产物这一主张。小说对龙骨的详细记载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摹写出历史事件对人们产生的直接的冲击,龙骨的坎坷经历正是中华民族的写照,散落四方的结果也与中华儿女(华裔族群)流散于异国他乡,希冀叶落归根而未果的哀愁相呼应。小说中出现了一些琐碎而具有神秘色彩的意象:接骨师对龙骨的迷信、经年战乱、美国现代生活的繁华迷离……这些都被作为历史载体延续的细节而传达出祖先之骨散落四方的悲剧感。
所以无论是茹灵记录的手稿,还是对于龙骨情节的叙述,都可以看作是作者依托了历史的客观存在性来对小说进行的建构,将新历史主义学者所倡导的用小写、复数(即主观、细碎)的历史来替换大写、单数(正统书写)的历史,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特征。
三、文本的历史性
著名学者王岳川先生曾经对新历史主义中“文本的历史性”表达了自己的理解:“文字在阐释历史时不要求恢复历史的原貌,而是解释历史‘应该’与‘怎样’,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最隐秘的矛盾,从而使其经济与政治的目的彰显出来。”[5]37这种解读强调的是文学文本对于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历史的某一节点或是对历史事件的还原;所关注的是历史背后存在的社会问题,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文本的历史性研究要做的是对社会存在问题的揭示,挖掘出背后的矛盾,通过文学文本的影响,找到新的历史建构模式。由此,谭恩美在小说中记述茹灵来到美国后以及女儿露丝的生活可以看作是文学文本主动参与历史意义建构的尝试。众所周知,在美国的国家建设中有不少是华裔,他们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但在美国历史文献、文学作品及其他文化媒介中,华人被描绘为懦弱、顺从、胆小,不是开餐馆就是开洗衣店或为白人帮佣,做的是女人活,缺乏英雄气概。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华裔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英雄、没有神话的族群”[6]。华裔族群所做的贡献却一直不被人们所熟知,反被美国人所误解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尴尬的处境让华裔族群变得无所适从,找不到倾诉的渠道,这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母亲茹灵来到美国生活大半辈子却仍是只能与当地人进行简单交流,将自己封闭在传统、仍带有中国生活方式与思维方法的世界中。通过女儿露丝来对过世的母亲宝姨招灵,以求自己曾经的过错能得到宝姨的谅解,殊不知这只是露丝碰巧猜中茹灵心思的一出恶作剧,茹灵得到的也只是自己心灵上的一个假慰藉;在对露丝的教育问题上,茹灵也遵循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对露丝的想法横加干涉,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随意指责美国人。由此看来,似乎茹灵也只是换了个地方,底子里还是在过着中国人的生活,无法融入美国当地人的生活之中。茹灵的遭遇其实也是美国第一代华裔移民生活处境的一个真实写照。小说的主人公露丝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移民,所从事的工作却是替别人捉刀写书的“书本大夫”,“在跟别人合作的这些书上,露丝·杨这个名字总是用小字体印在主要作者后面,有时甚至根本不出现她的名字……她希望别人能发现她的工作价值,赞赏她妙笔生花,沙里淘金的本事。当然,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没有人知道,要非常技巧地把散乱的思绪转化成清新流畅的散文是多么困难的事”[2]32。对于露丝来说,尽管她是一位作家,但却只是做着帮别人写书、传达他人思想的工作,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想法,甚至在写书过程中还会碰到沟通不畅的状况。小说中的露丝一直在努力地挣脱处于社会边缘的华裔身份的束缚,希望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但却碰到了很多障碍,想要成为受人关注的主体却不得,华裔族群的尴尬处境可见一斑。同时小说初始还提到了露丝每年都会有一个星期左右的“失语”,不能言语;其实,失语的又何止是露丝呢?母亲茹灵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失语者。作为较早的移民,茹灵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却仍然说不好英语,更不能与当地人很好沟通,只能通过女儿露丝充当传声筒与翻译家。丰富的思想与想法只能在历史时间的流逝中消失,这似乎也可以看作是华裔族群在美国历史进程中失语的一个缩影。在庸碌而逝的时间流之中,华裔族群所经历的默默无闻的琐碎之事与心灵受到的一次次撞击,无不说明了他们生活上的艰难。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将自己所经历的辛酸往事以及在美国这个异国他乡的生活与文化差异都刻画而出。在舒缓而哀伤的笔调之下,读者们看到的是大洋彼岸同胞生活的尴尬,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与知晓真实世界中的华裔生活,体现了文本的历史性中对于社会问题揭露的关注。
小说结尾处茹灵与自己的新伴侣唐先生坐在美术馆的青铜钟前,唐先生述说着对这个古老乐器的遐想:“最近我在某个活动场合有幸听到过一次中国乐师演奏的编钟乐……我觉得好像是穿越时空回到了三千年以前。我听着那时的人听过的声音,感受着同样的敬畏之情。我想象出那时倾听这乐声的人,我想那是个女人,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我心里想,也许再过三千年,又会有一个女人听到这乐声。虽然我们无缘相见,却因为这乐声而心意相连。”[2]281在这里,三千年的编钟乐声代表了历史,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成为表达人性本质情感的重要载体。在唐先生的遐想中,时间的不可能被文本建构成了可能且可行的事情,并为当下的判断与行为提供了基础。这在海登·怀特看来是一种“实用的过去”的体现,既能体现当下同时也为生活于现时的人们提供反思的机会,以求能为将来做参考,是一种联系着现在与将来的方式。
四、结语
新历史主义学者们认为:“历史已经文本化,它永远处在被叙述、被解释之中,处在种种已经写成的文本的互文性之中。”[7]9因此,历史与文本间的互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对话;这种对话是一种开放性的交流,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可以看作是这一开放的对话过程的体现。由于历史与文本都具有虚构性,将二者加以实践,对其结果所进行的分析又可以看作是对跨学科相互作用的一种阐释。《接骨师之女》通过对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的相互书写让被压制、被淹没的华裔历史浮出了地表,以普通人所经历的历史去反观大写的正统的历史场面,完成了“小历史”向“大历史”的挑战。传统历史主义学者们眼中所认为的历史是客观的,建立于事实基础之上的看法被作者攻击与质疑。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探索缺席的、尚未被书写与记载的历史,用想象的笔触展现出小人物历史的悲欢离合,让他们摇曳生姿、大摇大摆地走上了历史舞台。
作者所做的并不是重新创造历史,而是试图对过去时间予以多声部的、尽可能精确而细腻的表达。半自传体的小说,将一家三代女性一脉相承的坚韧串联起了一部中国的近代史。美籍华人后代所书写的祖先的历史,有了一种时空的错叠感,小历史背后所撩拨起的历史往事是一部宏大史诗,小与大的分界线被模糊了,更多地倾注了作者对于人们能够进一步了解华裔族群历史的希冀。作品的名称为《接骨师之女》,似乎与整部小说的重心有所偏差,宝姨才是接骨师之女,但是故事还与茹灵、露丝有关,这恰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因为故事所表明的并不只是接骨师之女的故事,还要接上的是远离了家乡与祖国而难以维系的母语与文字。“多年来,作为生活在美国这个所谓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中经历了太多的苦难,遭遇了太多的不公平待遇,她们(华裔女作家)痛苦过、迷茫过、失望过,但奋斗却从未止息。通过自传体写作,美国华裔女作家们回顾自己与先辈们痛苦的经历,重新唤醒华裔女作家被压抑的自我,努力发出自我的呐喊,反击主流社会对华裔女性群体长期存在的偏见与歧视,探寻自身独特的文化身份。”[8]这既是华裔女作家的写作目的,也是她们写作姿态的宣扬。作为一名华裔作家可谓责任重大,谭恩美曾经谈及如何定义“责任”一词:“以自我为中心,去走一条少人走的路,这时我的责任就是把这片地发掘出来并呈现到读者面前。”通过自己的小说呈现华裔族群中尚未被人了解的历史,挖掘背后的现实意义,这正是新历史主义学者所倡导的从不为人知的小历史角度着手进行书写。华人历史的艰难性与隐秘性是如此的错综复杂,“唯有借助美学的想象,才能对它获得一个现实主义的理解”[9]140。这也是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分析作品最为诱人的所在:“新历史主义所带来的基本变化在于:从将历史事实简单地运用于文学文本的方法论转变为,对话语参与建构与持存权力结构的诸层面进行错综复杂的理解。它打破了文学与历史间简单化的二元区分,而在它们之间开辟出一种复杂的对话关联。”[10]236这段话说明,只有通过对作品进行文本细节的考察来发掘其背后历史性与文学性的融合与互动,才能更好地探寻被记录在作品中的动人心魄的魅力。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谭恩美.接骨师之女[M].张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范开梅,张旭.异质文化下华裔女性的“声音”——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接骨师之女》中的“失语”与“文化认同”问题[J].理论观察,2012(2):47-48.
[4]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Y_XbIMTsReaty6L3S7O9FBJPQFm9xThqa9QYjJyncKZdOeNJ 8pQclMvL2tL6B2U-mKrcujKhzpprDtBCaJjnpa.
[5]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6]张明兰.汤亭亭《中国佬》的新历史主义解读[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118-120.
[7]石坚,王欣.似是故人来——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美文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8]高卫红,周春玲.自我身份的寻求之路——谭恩美《接骨师之女》的自传解读[J].文艺评论,2013(5):91-94.
[9]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10]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亦筱]
2015-12-01
谢嘉(1991- ),女,广西北海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文化关系。
I106.4
A
1008-6390(2016)04-01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