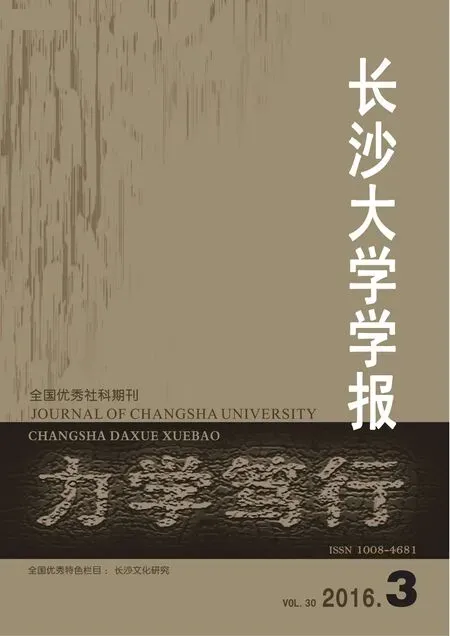梁启超对湖南新学传播的作用与影响
陈先枢
(长沙大学长沙文化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22)
梁启超对湖南新学传播的作用与影响
陈先枢
(长沙大学长沙文化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22)
摘要:梁启超是全国闻名的维新派人士,在湖南维新运动中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对湖南新学传播产生过重要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时务学堂的新式教育实践,二是对谭嗣同思想及湖南维新思想的支持与弘扬,三是对蔡锷政治思想形成及变化的影响。
关键词:梁启超;湖南新学;时务学堂;谭嗣同;蔡锷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湖南维新运动中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是全国闻名的维新派人士,与谭嗣同、蔡锷等湖湘杰士结下深厚情谊。梁启超对湖南新学传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新式教育实践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湖南官绅筹备时务学堂,陈三立和黄遵宪提议梁启超和同在《时务报》任职的李维格分别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和英文总教习。黄遵宪请熊希龄写信给当时在南京的谭嗣同,请他与梁启超与李维格联系。同时,熊希龄、江标、黄遵宪等都曾给《时务报》经理汪康年写信,劝说他放梁启超来湘。在汪康年同意放梁启超和李维格赴湘后,梁启超又提出,时务学堂的分教习应由总教习“自行聘定”,得到了熊希龄等的同意,于是梁启超自聘了同是康门弟子的韩文举和叶觉迈任时务学堂中文分教习,一同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来到长沙。
梁启超在到长沙后的次月即上书陈宝箴,提出了湖南自立、自保的主张。接着又向陈宝箴呈递了《论湖南应办之事》,对湖南办学堂、学会、报馆和其他新政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梁启超和其他几位分教习利用在时务学堂的讲学和批答学生课卷,大力宣传康有为的“素王改制”思想和公羊春秋学说以及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从而引起了反对派的极力攻击。
梁启超亲手制定了《时务学堂学约》,对时务学堂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于时务学堂的教育教学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学约”共十章,曰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读书、学文要求学生不能“只通一国之书”,而应“通古今中外能为世益者”之书,须以数年之力,“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肄力于西籍,夫如是而可谓之学”[1]。
关于教学方法,“学约”也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思想[2]。
第一,主张启发式教学。梁启超认为真正的读书应该是启发学生“深造有得,旁通发挥”,要使学生在读书过程中能联系所学的内容“发明新义”。他规定教习每天讲课完毕即向学生提出有关“目前事理或西书格致浅理”,或“各报所记近事”方面的几个问题,让学生“精思以对”,“各抒所见”,学生答完后,教习再加以解释说明。
第二,主张联系实际进行教学。梁启超认为读书应“切于今日之用”,“于当世有所救”。因此,他主张联系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进行教学,无论是中国经史,还是西方格算,既要穷其理,又要“为经世之用”,联系中国的现实或“目前事理”。
第三,主张中西比较进行教学。梁启超认为学生既要精通“中国要籍一切大义”,又要“旁征远引于西方诸学”。他主张将儒家“六经”及“周秦诸子”与“西人公理公法之书”、“历朝掌故沿革得失”与“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今日天下郡国利病”与“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进行对比,从中求“治天下之理”、“治天下之法”。
梁启超离开长沙二十六年后再次来到长沙,但仍无法释怀于他的“时务”情结。1922年刚任金陵东南大学教授的梁启超应湖南省长赵恒惕之邀来湘讲学,8月30日抵长,下榻省教育司(今教育街省民政厅)。次日即在任过梁秘书的李肖聃的陪同下专程去寻访位于今三贵街的时务学堂故址,并写下了“时务学堂故址二十六年前讲学处民国壬戌八月重游泐记梁启超”的条幅。9月1日梁启超分别在长沙东牌楼遵道会礼堂和省立第一中学作“奋斗之湖南人”和“湖南教育界之回顾与前瞻”两场演讲[3]。在“湖南教育界之回顾与前瞻”的演讲中,梁启超深情回忆了当年在时务学堂的教学及推动维新运动的活动。他说:
时务学堂,我觉得与湖南教育界有关系,而且于全国教育界有莫大影响的,在师弟同学间的精神能够结合一气,一群人都有浓厚的兴味,联合多方面来注重做事。……那时的青年皆有进取思想,高谈时局,研究满清怎样对不起汉人,及中国二千年来的专制恶毒。这班青年,都是向这二个目标走。而我们所做的事,分作四项,是:(一)办时务学堂;(二)组织南学会;(三)发刊《湘报》——日报;(四)发刊《湘学报》——杂志。南学会是公开讲演的机关,讲演社会上不以为奇怪的话。时务学堂则专研究怎样贯彻我们的主张。《湘报》与南学会同一作用,《湘学报》与时务学堂同一作用。……我在时务学堂,每天除讲三四点钟的学外,还要同学生谈话,及作种种运动,一天到晚忙个不了,因此成病,就往上海就医[4]。
二梁启超对谭嗣同思想及湖南维新思想的支持与弘扬
梁启超称:“晚清思想界有一慧星,曰浏阳谭嗣同。”[5]梁启超为何对谭嗣同有如此高的评价,这要从梁、谭二人的交情说起。梁谭交谊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6]。
第一阶段:1896年春,谭嗣同北游访学到了北京,在那里他结交了梁启超。还在北上访学之前,谭嗣同已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经过艰苦思索产生了“尽变西法”的维新思想,为了进一步开阔眼界,增广见闻,他于1896年二月北游访学,首先到上海,希望在沪能拜会康有为,因后者已经离沪南下而未果。对康有为“心仪其人,不能自释”的谭嗣同没能在上海了结自己的心愿,于是到了北京很自然地就会去结交康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梁启超向谭嗣同介绍康有为学术思想之源流及一切微言大义,受到后者的热烈欢迎,于是自称为康的“私淑弟子”。谭嗣同身为巡抚之子,能与康梁同一主张,自然引起梁启超的极大兴趣。他写信给康有为,盛赞谭嗣同“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公子之中,此为最矣”,可充“伯理玺之选”[7]。谭梁结识之后成为“讲学最契之友”。梁启超后来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说,他当时与夏穗卿、谭复生在北京住得很近,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8]。
第二阶段:1896年7月,梁启超在上海与汪康年、黄遵宪等创办《时务报》并担任主笔。这年8月谭嗣同结束了北游访学,抵达南京候补,需次金陵期间,谭嗣同集中主要精力从事《仁学》一书的写作。从这时起到1897年是谭梁交谊的第二阶段。谭嗣同在撰写《仁学》的过程中,“问月至上海”,与梁过从甚密,《仁学》每成一篇,“辄相商榷”,梁启超在《仁学序》中说他们当时“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究天人之奥,或彻数日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同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
第三阶段:共同参与湖南维新是谭梁交谊的第三阶段。1897年10月,梁启超应邀到湖南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受熊希龄之托为争取梁启超赴湘作过努力。l898年2月中旬,谭嗣同也返回湖南,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粱启超邀他和他的“二十年刎颈交”唐才常担任时务学堂分教习。他们还共同发起南学会,创办《湘报》,大力推进湖南维新运动。在时务学堂的教学中,他们共同举起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9]
第四阶段:1898年春,梁启超因患大病离湘赴沪就医,痊愈后入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开保国会。百日维新期问,梁启超和谭嗣同同被侍读学士徐致静所举荐。梁奉诏以六品衔办理泽书局事务,谭则以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从8月21日谭嗣同进京到9月23日梁启超出逃,这极不寻常的一个多月,是谭梁交谊的最后阶段。梁启超出逃日本的第二天,谭嗣同因袁世凯告密而被捕,几天后,9月28日便与康广仁等一起殉难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梁启超逃到日本不久,即在横滨创办《清议报》,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为宗旨,是继《时务报》之后影响深远的维新报刊。梁启超在该报的创刊号上,就开始连载《戊戌政变记》,他以感情激越的文字记述和颂扬包括谭嗣同在内的维新派的活动,辟专篇介绍“湖南广东情形”,称湖南绅士谭嗣同、熊希龄等“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在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中,梁启超为戊戌六君子立传,歌颂他们维新救亡舍身救国的精神,其中《谭嗣同传》以五千余字的篇幅全面向世人介绍了谭嗣同的生平事迹、成长道路、思想变迁、主要著述、维新事迹及其奋斗与献身精神,成为后人研究谭嗣同的必读文献资料。也就是在《清议报》上,谭嗣同“冲决网罗”思想的代表著作《仁学》开始与世人见面。《仁学》是谭嗣同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它以平等思想为武器批判君主专制,批判纲常伦理,宣传反满革命思想,“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10]。梁启超从《清议报》第二册起以连载的形式将其公开发表。梁启超在《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中称,“此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亡友浏阳谭君之遗著也”[11]。在《清议报》发行一百册之时,梁启超在长篇“祝辞”中,进一步指出:“其内容之重要者,则有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之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亦众生无价之宝。此编之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12]
梁启超对谭嗣同思想的弘扬不仅限于戊戌政变后的几年,而且终其一生。1920年,梁启超在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专辟一节介绍谭嗣同的学术思想。他将谭嗣同冲决网罗的精神与牛顿提倡“打破偶像”的主张相提并论,认为“《仁学》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真可谓极大胆、极辽远之一种计划”,“其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无庸讳,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梁启超对维新运动期间湖南推行的新政极尽褒扬之能事,他说:
时陈公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三立辅之,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丁酉六月,黄君遵宪适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铸又来督湘学。湖南绅士某某等踔厉奋发,提倡桑梓,志士渐集于湘楚。陈公父子与前任学政江君标,乃谋大集豪杰于湖南,并力经营,为诸省之倡。于是聘余及某某等为学堂教习,召某某归练兵。而君(指谭嗣同,下同)亦为陈公所敦促,即弃官归,安置眷属于其浏阳之乡,而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于是湖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擘画者,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天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于是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13]。
三梁启超对蔡锷政治思想形成及变化的影响
蔡锷以领导辛亥云南起义和护国运动而闻名于世,是中国近代史上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然而,他作为梁启超的学生,一生的思想受梁启超的影响甚深,在政治上与梁启超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当广泛的合作关系。从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来考察,可理清蔡锷政治思想演变的历程[14]。
蔡锷在1897年冬进入时务学堂头班学习,与梁启超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师生情谊和政治联系。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力主维新变法,以开通天下风气为己任,试图将时务学堂办成为变法服务的速成政治学堂。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梁启超以《公羊》、《孟子》教学生,宣讲康有为的孔子改制之说和大同三世说,鼓吹维新变法,这对年轻的蔡锷思想触动甚大。而且,梁启超等人采用教师批改学生札记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思想为之一新。梁启超自言:“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学生“日日读吾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他们象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15]蔡锷也正是在梁启超的思想熏陶下不断成长的。他“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16]亦深得梁启超的赏识。在梁启超的帮助下,蔡锷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具有真正意义的转变,即从传统儒学向变法维新思想的转变。蔡锷开始鼓吹仿效西法,指出“西法何?议院之制也。议院之制何?万心之推也”。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蔡锷也因时务学堂被解散,求学两湖书院遭拒绝,几经周折,于1899年6月考入上海南洋公学。7月,接梁启超来函相召,蔡锷偕唐才质、范源濂等人东渡日本,进入由梁启超主持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研究政治哲学。学校所用教材多采欧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说,使蔡锷耳目为之一新。梁启超与唐才常过从甚密。受唐才常的影响,蔡锷加入了“自立会”,并于1900年7月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旋起义失败,蔡锷虽幸免遇难,但受刺激很大,为此事,他曾赋诗十首,其中有云:“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并将原名艮寅改为锷,意在砥砺锋锷重新做起,决心学习军事,以拯国难。这时,蔡锷以学习陆军为念,屡请于梁启超,并坚定表示:“只须先生为我想方法得学陆军,将来不做一个有名之军人,不算先生之门生。”[17]梁启超利用他与日本政界的密切联系,帮助蔡锷实现了学习陆军的愿望。蔡锷先后毕业于日本东京成城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
留日期间,蔡锷曾投稿于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嗣又在梁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而《军国民篇》就是他刊登于该报的一篇代表作。在此文中,蔡锷沉痛指出:“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提出以军国民主义灌输于国人头脑,以培养“国民新灵魂”,来实现军事救国的目的。这种从军事人手进行改革的军事改良主义,与梁启超的改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西学的启迪,加以梁启超于1900年前后曾密谋与革命派合作,极力鼓吹所谓“破坏”,甚至认为“破坏之药”是救国的“第一要件”,“第一美德”[18],蔡锷受其影响,开始结交一批革命志士,并参与组织团体,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云南光复后,蔡锷被推为军政府都督,建立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都督府,并进行了若干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
清帝退位之后,蔡锷认为“破坏”已基本告一段落,下一步主要任务是团结各种政治力量,共图建设。1912年6月5日,蔡锷致电敦请恩师梁启超回国,电文称:“锷追随先生有年,觉其德行之坚沽,学术之渊博,持义之稳健,爱国之真挚,环顾海内,实惟先生之一人。”同年10月,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涯,体面回国,这与蔡锷不无关系。梁返国后,在“开明专制”思想的指导下,极力鼓吹“国权主义”,希望通过袁世凯建立强有力政府,推动国家建设。蔡锷亦主张建立强有力政府,与梁产生思想共鸣,他认为:“特以民权恒视国权为伸缩,必国权巩固而后民权有发展之期。总统当国家行政之中枢,负人民付托之重任,使因少数人之党见,减削其行使政策之权,恐一事不能为,必致陷国家于不振之地”,这与梁的“国权主义”同出一辙。
1915年8月,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公开化,梁启超和蔡锷一反过去拥袁的政治立场,转而筹备反袁。蔡锷与梁启超在反袁护国战争的组织发动及战争的进程中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8月14日,为袁复辟帝制摇旗呐喊的“筹安会”成立,15日,蔡锷便赶赴天津,与梁秘密策划反袁。蔡锷当即表示:“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他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19]他们共同商定,发挥各人特长,分别从文、武两条战线反袁。由蔡锷亲自回云南发动武装讨袁,梁启超则大造反袁舆论。22日,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收买,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明确表示反对帝制复辟。梁利用他在思想舆论界的显赫地位,联络各派头面人物反袁,是护国运动的一面旗帜。蔡锷每周都赴天津与梁共商大计,并召集戴戡等重要人物入京,部署一切。蔡锷利用他与各派政治力量之问所保持的良好关系,联络西南实力派,并与在美国的黄兴取得联系,秘密实施与梁商定的各项反袁计划。1915年11月11日,蔡锷设计秘密出京,历尽艰险,于12月19日绕道日本,抵达云南昆明,12月25日发动了著名的讨袁护国之役。
在战争进行当中,蔡、梁同舟共济,互相支持。蔡锷在军事上领兵鏖战,梁启超在思想战线等方面密切配合,共同推进反袁斗争事业。梁启超一方面向蔡锷指陈革命方略,策划与指导军事行动,诚如蔡锷所云:“锷在军中凡得先生八书,每书动二三千言,指陈方略极详。”另一方面,梁又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扩大反袁联合阵线,为云南护国军扫清障碍。在蔡锷最困难之时,梁策动桂督陆荣廷独立,促进了全国反袁形势的根本性转变。后来,梁冒着生命危险南下广东,策动龙济光独立,并使龙济光最终宣布独立,从而加速了袁世凯的失败。蔡锷认为:“先生亦间关入两粤,当锷极困厄之际,突起而拯救之,大局赖是以定。”高度评价了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梁启超在以后的岁月中一直以有这样一位反袁的学生为荣。蔡锷逝世六年后,即1922年,梁启超应湖南省长赵恒惕之邀在长沙作题为《奋斗的湖南人》的演讲,重点举了蔡锷反袁护国之例。演讲中说:
民国成立,袁世凯称帝,自以为布置周密,预料必可成功。那时蔡松坡离居在京,算已入了袁的樊笼,但他千辛万苦设法逃去袁的势力范围,突然在滇起义,以很单薄的兵力出四川,袁倾全国之力同他相持。结果居然摧倒袁氏,使他活活地气死。然而松坡也因为劳顿过度,得了吐血症,后来死在日本的医院里。那时出力的不止蔡松坡,同事的湖南人也很多[20]。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A].粱启超.饮冰室文集(二)[C].上海:广智书局,1902.
[2]彭平一.长沙通史(近代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
[3]陈先枢.梁启超题“时务学堂故址”始末[A].湖湘文史丛谈(集2)[C].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
[4][20]大公报,1922-09-03.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36.
[6]郭汉民.谭梁交谊与晚清思想[A].湖湘文化论集(下册)[C].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7][8][9][1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0]梁启超.谭嗣同传[A].饮冰室合集[C].北京:中华书局,1936.
[11]梁启超.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N].清议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2]梁启超.文集之六[A].饮冰室合集[C].北京:中华书局,1936.
[1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殉难六烈士传[A].饮冰室合集[C].北京:中华书局,1936.
[14]饶怀民,阳信生.蔡锷与梁启超[A].湖湘文化论集(下册)[C].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6][17]田伏隆.忆蔡锷[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8]李华兴.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9]梁启超.文集之三十九[A].饮冰室合集[C].北京:中华书局,1936.
(责任编校:余中华)
Influence of Liang Qichao on the Propagation of New Learning in Hunan
CHEN Xianshu
(Institute of Changsha Culture,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22,China)
Abstract:As a well-knoun reformer,Liang Qichao held the post of chief instructor during the reform movement in Hunan. H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pagation of new learning, and his influence includes:the teaching practice in Shiwu Academy, the support and spreading of ideas of Tan Sitong and reform movement, the effect on Cai E’s political ideas.
Key Words:Liang Qichao; new learning in Hunan; Shiwu Academy; Tan Sitong; Cai E
收稿日期:2016-03-09
基金项目:湖南省科技创新团队“湖湘文化与区域旅游产业开发”,编号:[2014]207号。
作者简介:陈先枢(1945— ),男,湖南长沙人,长沙大学长沙文化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区域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81(2016)03-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