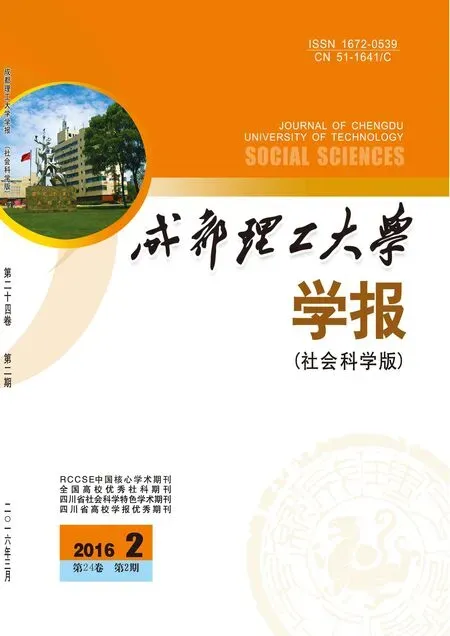自然语言现象的观念化过程重塑
肖福平
(西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39)

自然语言现象的观念化过程重塑
肖福平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610039)
摘要:在我们将语言现象视为自然形式的存在时,它所指向的对象就是作为普通语言学主要研究的内容;自然语言现象的存在说明不可缺失语言行为者的语言感知经验,而语言感知经验的发生则要基于语言能力的存在与应用,其心理成果体现为自然语言现象的各种观念。不论是涉及语言现象的简单观念,还是复杂观念,它们的产生必须出于后天的经验学习,即出于语言知性能力和语言感性能力的应用,唯有后天的经验过程方可带来语言现象观念的存在与变化。
关键词:语言现象;观念;经验
在《人类理解论》里,洛克提出的“知性”对象不在我们之外,而在我们之内,即作为心灵形式的“观念”存在,“就是一个人在思想时知性所涉及的任何物象”[1]5。基于洛克的“知性”与“观念”,在涉及自然语言现象认知的方面,我们同样可以使用“语言观念”来指称所有关于这种现象认知的心理概念,包括清晰的和非清晰的概念,以及使用“语言知性”来指称所有关于这种概念形成的“知性”能力;作为知性对象的概念,只要它是涉及了语言现象世界的想法或心灵印迹,只要它是涉及了我们大脑之中的语言认知过程的发生和呈现,它就一定要作为一种知性作用的对象内容而存在。在此,洛克的“观念”不仅是我们考察洛克知性成果的坐标与参照,而且是我们开启语言知性成果研究、特别是关于心理语言形式确立的重要坐标和参照。于是,洛克的“知性”与“观念”在自然语言现象的认知中就可以具体为一种“语言知性”和“语言观念”的联系。一旦我们参照洛克的观点来确立“语言观念”在我们心灵中的存在,并且在心灵经验的事实中我们又找不到任何否认如此“语言观念”的证明,“语言观念”就应该在说明语言知性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有效性存在地位。不论是从自然物认知的层面看,还是从语言现象认知的层面看,它们都要有联系于理性主体的能力作用,“观念”或“语言观念”的形成必不可少。“语言观念”的形成联系于语言现象的世界,但它的形成基础却一定要是认知主体的存在,即具有“语言知性”或“语言能力”的主体存在。探索“语言观念”的形成过程就在于取得一条展示“语言知性”存在下的自然语言现象的观念化之路。
一、 语言现象的自然形式感知与感知视域
在语言现象的经验中,如果我们将语言现象仅仅局限于普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世界,关于语言现象认知的观念路径就有可能被清晰地加以确立,尽管这样的“确立”会暂时将心理经验的“观念”对立于语言现象而非内在于语言现象(1)。一旦我们将语言现象看成为外在过程或自然过程的存在内容,我们就要通过自身的语言能力获取关于语言现象的观念,不论它是涉及简单的观念还是复杂的观念。语言现象的方方面面可以体现为不同的形式存在,它们凭借语言能力作用的不同路径形成各自的观念,而这里的路径就是不同语言现象形式进入我们大脑的路径,它要么表现为单一的路径,要么表现为复合的路径,并带来简单语言观念与复杂语言观念的形成。语言能力作用下所形成的语言观念无不体现出语言现象世界中的对象存在的刺激作用,无不体现出每一种刺激作用所产生的观念留存,以及这些观念留存所带来的心理呈现的经验方式。在语言观念形成的初始时期,它更多地体现为语言感性能力作用的成果,体现为具有简单感性路径和特征的简单观念形式。在语言感性作用的单一路径里,语言现象的刺激发生总是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某一单一的感官加以完成,而在复合路径中,语言现象进入我们大脑并形成简单观念的过程则要凭借两种或多种感官活动的发生;正是因为语言现象刺激和接受路径的差异,语言现象在我们的语言观念形式中才具有了音、形、义的划分,以及关于它们的连接和统一关系的确立(语言现象的单一刺激反应结果并非孤立的具备感性特征的观念,与它伴随着的还有其他的语言观念)。
如果我们认定了关于语言现象的感性观念源自于一种感官作用的结果,那这样的语言现象一定是满足了这种感官的作用要求,从而形成了相应的心灵中的感性观念存在。如语言现象世界中的汉语文字、英语单词等,如果它们只是就“形”的范畴而言,所有涉及这些文字或单词的感性观念形成就可以在“眼”的作用中加以完成,同样,就“音”的范畴而言,可以在“耳”的作用中加以完成,就“义”的范畴而言,可以在多种感官和直观意象的联系中加以完成。在这样的情形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将语言现象的感知区分为直接的感知和间接的感知。直接感知就是直接地将语言现象作为经验直观的对象,如文字或单词的形式,语音的形式等,如此的语言现象在其存在地位上具有自然物存在的特征;而间接感知就是关于直接感知的语言现象经验的扩展和升华,而这样的扩展和升华往往产生于语言现象世界与自然物世界的同在对比之中,往往产生于多种感觉器官的共同参与之中,如“温暖”、“寒冷”、“坚硬”、“柔软”、“香甜”等标示性质的内容,我们对于它们的感知不仅仅是涉及“形”和“音”的直接感知,而且是涉及“性质”的间接感知,以及涉及“眼”“耳”之外的其他感觉器官的作用,同时,间接感知也可说明于语言现象之外的世界,我们对于语词现象的直接感知也意味着我们对于自然物世界的间接感知,就如在感知“香甜”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既有关于自然语言现象的感知,又有关于自然物对象(如食品等)的感知。因此,在我们将语言现象感知划分为两种形式时,语言现象关联于所有的感觉器官,关联于自然世界的对象存在。如果说直接感知更多地关注了语言现象的自然形式特征,那么,间接感知则更多地关注它的隐喻和抽象性质特征。总之,不论是直接感知,还是间接感知,语言感性能力的应用,以及关于语言现象经验直观的发生,它们无疑成为了语言现象观念形成的前提条件。我们一旦缺失了自身存在的语言感性能力和经验直观的发生,我们所谈论的语言现象观念(简单观念或复杂观念)就会是空幻的、神秘而未知的,“任何思维,哪怕是最纯粹的思维,都必须借助感性活动的一般形式进行”[2]1。
二、自然语言现象的观念化与后天经验
不管是对于具有语言现象知识的人们而言,还是对于“文盲”而言,语言现象的存在对于两者都是现实而真实的,只是“文盲”并不能接受关于语言现象的形式化规定。只要我们具备了关于语言现象的感知能力,只要语言现象联系到了这种能力的实践作用,语言现象世界的对象就不仅被视为外在的自然形式对象,而且被我们的语言能力转化为大脑之内的观念对象。因此,语言现象的观念形成就意味着语言能力(语言感性能力和语言知性能力)作用的发生,也就意味着直接感知和间接感知的发生。那么,对于语言现象的感知本身又该如何理解呢?如果我们将语言现象感知的观念同自然物感知的观念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即语言现象的感知情形等同于自然物的感知情形。在语言现象的感知中,我们的活动总是发生在阅读、倾听、思考语言现象的过程中,只要我们对这样的过程具有反应,那我们就应该承认这种感知的存在,否则,我们所听、所读、所思的一切就会变得虚无,任何所涉及的语言现象使用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所有的语音或所有的文字符号就不会如当下的情形那样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关于语言现象的感知存在。如果我们在倾听了他人的言说、阅读了语言文字、思考了语言对象后不能知晓任何大脑中的印象或观念,那我们所从事的语言活动就不会具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活动中缺失了“感觉”。语言现象的经验就是感知的发生或“感觉”的过程。在语言现象的经验中,语言现象的存在与变化不仅仅涉及作为自然形式的语言现象世界,而且涉及我们大脑之中的认知反应与感觉,否则,语言现象自身对于语言行为者而言就会成为虚无,关于它的感性观念就不会到来。
在日常语言现象的经验过程中,我们总是能够熟练地列举各种语言现象的个体与组合、变化与规律、等同与差异,这样的结果除了产生于大脑的感觉之外,不会再有其他的出处。对于语言现象经验的感知或感觉存在而言,我们并不缺少说明的路径,当然,这样的路径只能是语言经验的路径。比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法回避关于语言现象及其相关感觉的存在,“这类感觉以及偶或产生的观念、看法与语词连接在一起”[2]26,而且,这样的感觉总是要伴随着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语言行为而产生,不管这样的行为涉及什么样的语言现象目标;只要我们聚焦并关注于某种形式的语言现象,我们就是在真正意义上贯彻了“听见”、“看见”、“体验”的要求;不论是语音对象,还是语词对象,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语言现象,只有关于它们的感觉形成或出现,语言现象才可在“我们的”意义加以展现,唯有如此,语言现象的存在才会既是自然的过程,又是我们人类大脑思想的过程。
当然,我们形成关于语言现象的感觉是因为我们具有语言感性的能力,任何对于语言现象的感觉必然联系于语言能力的存在及其应用过程。不仅如此,语言能力应用的经验对象一定要属于感觉者的意识范围,因为我们不能说某人在自己的大脑中产生了关于某个语音的感觉而又没有意识到这个语音的产生或经验;这就好比是在一个充斥着各种问题讨论的大厅,那里有无数的语音现象、无数的言说者、无数的语言表达形式,以及无数的语义呈现,如果我们置身于这样的语言环境,我们很难相信自己的感觉是关于所有发生的语言现象的,除非我们是万能的语言现象感知者。或许,我们的感觉会逐渐的扩展和完善,但不论如何扩展和完善,我们的感觉都是针对那些所听、所读、所说的语言现象而产生,所以,感觉到的语言现象应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现象,语言现象的存在并非等同于语言现象的感觉。关于这一点,只要考察一下小孩的语言现象接受过程,我们就可以获得充分的说明,即在一个相对的时间段内,语言现象的存在数量几乎没有变化,而关于小孩的语言现象之感觉内容却是一个变量,一个在观察的过程中不断增加的变量;显然,一般意义上所指的语言现象并非就是产生了感觉的那部分语言对象,它应该包含了所有人类语言活动所涉及的全部内容或现象。因此,关于语言现象的感觉只能是在我们关注了某种语言对象并加以了心灵的“留影”之后才出现的结果。
如果我们能够完善关于自然物世界的命名与标记符号创造,自然物之世界就完全可以使用符号系统来加以代替,这样的代替之物就可以成为我们所要思考和分析的语言现象体系。这样的代替过程不是要增加我们所要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是要更多地为自然世界打上我们人类语言能力作用的烙印,使之更加适合感性和知性作用的特征。当然,这里的感性和知性需要语言的限制,而且,语言感性和语言知性的作用并非要先在地为语言现象体系规定某种原则性的要求,任何语言现象的原则都应形成于语言现象的经验过程中,都应源自于语言现象的规律所在。人类的语言感性和知性可以在经验中发现这样的规律,但不能主观地创造这样的规律。或许,我们有时也会面对这样的情形:小孩在出生时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语言白板”,即他们或许具有关于某些语言现象的感觉和观念(这样的情况可以在语言现象的经验中观察到),但是,这种初生时的感觉和观念并不能证明它们就是婴儿所固有的语言原则,也不能证明任何生命形式之前的语言原则“注定”,它们所证明的只能是作为胎儿期生命形式的存在已经接受了某种语言现象的刺激,如特定语音的刺激、特定肢体动作的刺激、特定反馈信号的输入,等等,于是,小孩在它们初生之后就会自然地表现出拥有一些语言现象知识的“天赋”,就会对一些语言现象具有自己的“反应”和“观念”,尤其是对那些与温饱相关的语音现象和肢体语言现象。同后天通过感知器官接受语言现象刺激而形成的感觉和观念相比,所谓小孩的“天赋”语言感觉和观念只是其生前生命形式所接受的语言现象刺激的结果,它只是一种初期阶段生命存在所无法逃脱的语言现象的经验结果;如果我们将这样的结果视为无数语言现象原则掌握的开端,那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一定存在于语言现象的呈现世界,而不是我们心灵之内的任何自我创造发明,更不是某种伴随生命产生的先天必然。诚然,在语言现象知识的学习与掌握过程之中,即使我们没有精确的实证分析和精确的答案,我们也不能从合理性和可接受性上来否认这样的情形:我们能够想象语言现象经验过程中的语言感觉与观念的形成与差异,我们也能想象经验过程中的语言现象及其原则存在对于不同言说者的表现形式和个体特征,但我们却无法想象没有语言现象经验的人类生命形式如何可以形成自己的语言感觉和观念,以及如何可以获得关于语言现象世界的原则,同样,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刚出生的孩子会自然地对那些涉及温饱的语言现象作出反应(尽管这样的语言现象还不是规范化和知识化的形式),特别是那些来自母亲的肢体语言和相关声音。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无法确认小孩对于标示某种食品或某种环境的动作或声音具有何种清晰的感觉和观念,可我们不得不面对小孩具有相关观念存在的事实,只是这样的观念事实还没有接受成人化的文字符号的编码而处于一种初级观念的阶段,即使如此,这样的观念只能属于语言现象经验的产生结果,语言(现象)“自始至终携有一种生命的气息”[2]353。不论我们的生命形式处于何种阶段,也不论我们所具有的语言观念处于何种阶段,语言现象存在的影响对于我们人类的存在过程而言无疑要成为一种发生的必然,而贯彻这种必然性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语言感性的存在,它所导致的就是关于语言现象的经验事实。在我们日常的语言现象经验中,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语言现象的知识,都能在“知道”的意义上理解语言现象和应用语言现象;当然,不论我们如何看重语言现象“知识”的成果地位,我们都是将语言感性及其感觉存在作为了一切知识产生的首要条件。在我们仅仅将语言现象看成为自然的对象存在时,这样的对象存在作为印入我们大脑中的东西必定有其进入的途径,它就是我们的语言感性能力下的感觉产生进程;凭借我们对于语言现象的感觉,作为具备自然物质特征的语言现象就自然地成为了联系于人类的客体对象,不管它是作为语音形式、文字形式的存在,还是作为其他更为复杂的形式存在。所以,在我们谈论关于语言现象的知识时,我们是将这样的知识首先建立在对于语言现象的感觉基础之上的,而且,关于语言现象的感觉过程及其成果直接地影响着“知识”的范围和深度。显然,任何关于语言现象知识的存在事实本身都能说明语言感性能力应用的实际发生和感觉成果的实际形成,以及自然语言现象的部分内容的形成为我们大脑中心理经验内容的实际情形。总之,语言现象经验的感觉路径成就了其观念化过程的实现。
三、语言能力与语言观念的辨析
语言感性可以形成关于语言现象的初级观念,其“初级”之意并非要排除语言感性成果的观念性地位,而是要强调语言观念在起始阶段的存在特征,即初级观念总是要作为一种简单观念的存在,当然,这里“简单观念”的提出可以暂时性地淡化语言感性作用与语言知性作用的划分标准,或者,初级观念和简单观念可以地被视为语言感性阶段的观念。在语言现象的经验实际中,特别是在语言文字对象形式的经验中,语言感性能力所涉及的对象并非都是一个个单独的文字符号,它总是要以更为复杂的对象形式出现在我们的感知视野中,如词组与短语的形式、简单句子与复杂句子的形式、段落篇章的形式,以及其他的更为复杂的语言对象形式;如果说一个简单的文字或语词能够传递出一种简单的观念并表示一种简单的对象性质,那作为复杂语言对象的形式就一定要包含组成这一形式的所有个体部分的简单形式,或者,更为高级的语言现象单位所传递出的复杂观念总要建立在较小的或简单的语言现象单位的观念意义之上。不仅如此,我们人类自身的语言现象经验表明,语言感性能力下的初级观念总是要开启于语言现象的简单个体,而不是开启于更为高级和复杂的语言现象单位,如孩童的语言现象接受,不管是咿呀学音之时,还是文字诵读之时,他们的起点没有句子,更不会有段落,关于语言现象的个体对象总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开始,总是以一种简单的个体对象的观念形式进入到孩子的大脑之中。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的存在,如果一个小孩只是学习了一个文字对象,并形成了一个关于它的简单观念,如“树”,结果,只要我们给出文字“树”或与文字相联系的意义对象,我们就可以发现“树”之观念对于这位小孩的存在。然而,如果我们以更复杂的语言现象单位示之,如“一棵古树静静地生长在深山里”,我们就无法断言关于这个句子的观念组合对于这位小孩存在,因为他在除了“树”的观念之外无法取得其他成分的观念,更不必说各个部分相联系的整体性意义观念;作为句子形式存在的语言现象在以一种观念组合体的形式存在时,它已经是作为了一种比“树”之观念更为高级和复杂的观念存在,一旦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关于“一颗古树静静地生长在深山里”的整体性观念(思想)[3],那就证明了我们在句子构成的各个部分上都形成了相应的简单观念;从各个语词部分的简单观念到句子对象的整体性观念,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由相互区分到走向统一的观念变化过程,因为我们在直接地以语言现象为语言感性的直观对象时,我们首先直观的是关于“古树”、“深山”、“生长”等一些语词(它们同其自然对象的对应关系或许在语音的学习阶段就已经完成),而关于它们各自的观念形式总是相互独立和相互区分的。尽管语词“古树”、“深山”和“生长”似乎都可以刺激并进入我们语言感性的视角感官,但关于它们的观念却存在于明显的差异性之中,特别是关于“生长”的观念,它所关联的方面一定还有时间过程的因素,总之,文字的符号意义不仅是它本身组合形式和连接形式,以及其他的形式,而且是关于与之相关联的所有意义的集中统一。所以,关于文字或语词的观念绝非是单纯的符号层面的,它一定涵盖了与这样的文字或语词相联系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在接受句子“一颗古树静静地生长在深山里”时,我们所面临的是无限扩展的“观念场”,它由各个单独的语词和相互组合关系的观念组成,我们在获取句子对象的意义观念时,我们所凸显的就是“观念场”中的那种代表组合关系的观念,而且是刚好代表了句子对象整体意义的观念,这样的“凸显”不是对“观念场”中其他观念的否定,而是对它们地暂时闲置或搁置,因为它们没有消失,也不可能消失,它们在作为单独的简单观念形成时就已经在我们的大脑中留存下来。作为句子中的文字观念或语词观念一定是适合了句子整体的需要,一定是经过了无数的相关语言现象观念的分析与综合之后的结果;从“古树”的简单观念开始,我们既有与之相联系的语言现象世界的相关项,也有对应于语言现象世界的自然物世界的相关项,因此,每当我们在一个语言现象的复杂观念里确立了“古树”的观念,其结果只能是一种相对于其他观念存在的简单观念的确立。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语言能力的存在总能为我们提供关于语言现象的观念,而且总是起始于简单的语言现象并获取相应的简单观念。就语言现象的知识形成而言,那些作为语言感性成果的简单观念无疑成为了语言现象知识建设的必用之物,或者说,语言现象知识的复杂观念体系只有凭借无数简单观念的提供才可能得以建立。如果说语言感性能力在语言现象的初级观念提供中发挥了主要作用,那接下来的语言知识的主要构建作用就应该由语言知性能力所主导了。那么,语言知性能力的作用地位又该如何体现呢?诚然,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语言感性的初级观念作为进入我们大脑的语言现象的特别存在形式总是要成为我们语言知性的直接作用对象;只要语言感性的初级观念成为了语言知性的直接对象,这些观念就会在一种新的要求下被重新加以呈现和审视,并由此获得关于观念存在的归类与排列,以及关于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判别。
如果我们可以使用文学性的描述来加以说明,语言知性的职责就是将充斥着语言感性观念的混沌心灵带往清明的彼岸,使之沐浴在语言知性的阳光之中。语言知性的历程展开在一个无限的过程之中,它对于语言感性成果的处理并没有确定性的完结之时,只要作为言说的主体在自然世界的进程中延续存在,语言知性及其处理简单观念过程的存在就是一种自明的事实。当然,语言知性对于那些源自语言感性过程的初级观念或源自语言现象的简单观念的处理并非一种由简单到简单的作用过程,所有进入语言知性作用环节的简单观念都会在复杂性、抽象性、综合性等方面得到体现,即语言知性依靠那些来自语言现象的简单观念可以获得关于语言现象存在的复杂观念,如关于句子的意义观念。语言现象之复杂观念的获取无疑是作为语言知性能力创造的成果,它不能由语言现象的直观过程来完成,也不能由自然语言现象自身来加以完成,直观的过程与语言现象的自然过程所明示的就是语言经验发生意义上的最为初始的环节和条件,也是语言知性存在可以获得应用和说明的起点。任何关于两个初始环节的缺失和否定都会带来第一阶段的简单观念形成的不可能,更不要说语言知性的应用,以及那些复杂语言现象之复杂观念的形成。因此,不论我们如何具有语言现象的认知能力,也不论我们如何具有语言思维的抽象能力,我们都不可能在自身之内纯粹地凭借语言知性能力来制作某种纯粹属于我们自身的语言现象和简单观念。一方面,一旦离开了语言现象的经验过程及其简单观念的形成,语言知性本身的存在说明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一旦语言现象的经验发生并形成了关于它们的简单经验,语言知性的作用也就要必然发生,而且,语言知性的必然作用不是在于增加或减少那些简单观念,而是在于形成关于那些简单观念的观念,就此而论,语言感性所取得的初级观念在语言知性面前并不会遭遇添加和消失的命运,即语言知性在形成自己的复杂观念时只是以简单观念为对象,而非在于改变或决定简单观念的存在地位,简单观念的存在地位并不因为复杂观念的出现而消失。从语言现象认知的经验论方式出发,简单语言观念对于语言知性的应用而言总是要作为第一位的对象存在,任何语言知性的作用就在于对简单语言观念的分析与综合,就在于对简单语言观念的再现与统一,其过程只能说明从简单语言观念到复杂语言观念的发展,而非是关于简单语言观念的被消除或被否定,不管语言知性能够在多么复杂的层次上进行分析与综合,语言知性的复杂观念作为知性领域的成果存在,它一定要与作为“材料”语言感性的简单观念(2)相联系;简单语言观念可以被认定为语言感性的作用而存在,但认定本身不具备绝对的意义,我们对于不同观念形成的语言知性和语言感性的能力之分,更多地考虑了语言现象认知的阶段性划分,其标准是相对的。
在我们认知自然之物的对象中,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自然之物是如何“踏进”我们的心灵之内的,同样,在我们认知语言现象的对象时,我们也非常清楚语言现象是如何刺激了我们感官而形成我们的心理经验形式。不管我们着眼于语言现象的哪种对象形式,或语音的形式、或文字的形式、或符号象征的实物形式,以及心理经验的语言意象形式,等等,只要这样的对象形式对于语言现象的经验者是现实的,那认知这种对象的语言感性器官就在发挥着正常的作用,只要所有的接受语言现象刺激的感官正常地运转,语言现象对于我们而言就会整体统一(包括了音、型、意等多方面的综合统一)地被加以展现。当然,作为统一展现的语言现象并非要确立它的唯一性和不可分析性,即语言现象的全面性展示并非要否定它的个体性和单一性展示;在语言现象的经验现实情况中,其单一性或某一个方面的展示无疑会频繁地发生,而与之相关联的某个感性器官就会单独地承担着接受某一种语言现象的情况,比如,在我们进行阅读时,我们的眼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而此时所展现的语言现象主要是语言文字的形式;语言文字的凸显是一种聚焦于可见性特征的语言现象,而可见性特征又要作为视角感官的接受体现,因此,语言现象的呈现既可以是全面统一的展示,也可以是基于某一方面的凸显。如果我们仅仅以人类自身的语言现象经验现实为基准,语言现象的全面性所包括的方方面面对于我们而言可以是清楚的和确定的;对于语言现象的方方面面存在,我们总是习惯地使用听、说、读、写、思来将它们加以指向和经验。当然,语言现象除了作为这些学习行为的对象之外,也许还要作为其他行为的对象,但不论是何种行为,它都要必然地贯彻语言感性的应用,并首先体现为理性主体的感官参与现实;倘若有一种语言行为超越了我们现有的感知能力,从而产生一种特别的语言现象形式,这样的语言现象形式就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经验之中,这样的语言现象也不会属于我们的语言经验世界。
因此,在语言能力的存在下,自然语言现象不仅仅是作为自然过程的对象,它还会为我们带来心理经验的语言观念;从自然语言到心理观念、从简单观念到复杂观念,语言现象经验的过程就是语言感性能力和知性能力的应用过程,我们拥有的语言观念及其划分标准只能源于语言现象的经验。
注释:
(1)在“经验”的标准下,语言现象应该是关于自然语言形式和心理语言形式的存在;在传统语言学的定义中,它又常常被视为自然语言现象的存在。
(2) 这里使用“简单观念”来指称映像、感觉、表象等形式,主要考虑了其心理经验形式的存在特征。
参考文献:
[1]洛克. 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德]洪堡特. 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M].姚小平,译.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3]Frege.“On Sense and Reference” (1892), in A. Sullivan (ed.),LogicismandthePhilosophyofLanguage:SelectionsfromFregeandRussell, Canada: Broadview Press, 2003.
编辑:鲁彦琪

Natural Language and Its Conceptualization
XIAO Fu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39, China)
Abstract:when we consider language as natural objects, these objects are in fact belonging to the one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natural language should be analyzed from the experience of language sensation based on the activity of language ability, and the result of conceptualization is psychological concept,both simple concept and complicated concept are acquired from learning of language, and simple concept or sensitivity’s role is the first condition for the forming of language conception.
Key words:language phenomenon; conception; experience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2-0032-06
作者简介:肖福平(1962-),男,重庆璧山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语言哲学的研究。
收稿日期:2015-01-01
DOI:10.3969/j.issn.1672-0539.2016.02.006 10.3969/j.issn.1672-0539.2016.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