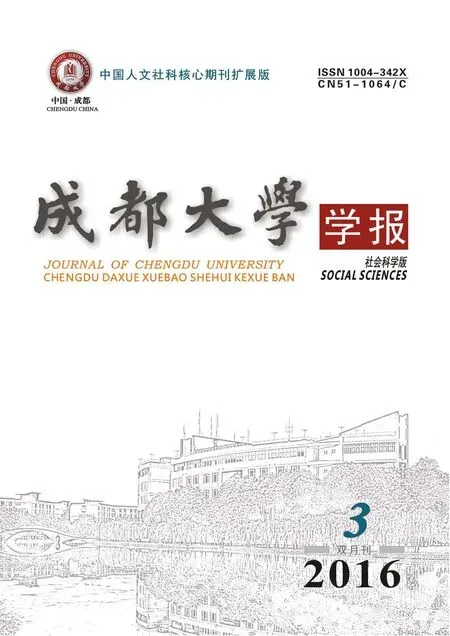川剧老艺术家口述史(四川卷续)之肖熙凤篇*
严 铭 万 平 包诗绮
(成都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口述史·
川剧老艺术家口述史(四川卷续)之肖熙凤篇*
严铭万平包诗绮
(成都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610106)
摘要:肖熙凤,国家二级演员,四川剧协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专工奴旦、花旦,兼擅闺门旦、摇旦。代表性剧目《柜中缘》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戏路较广,喜、悲剧演得好;表演细腻、自然,形象鲜明,风采动人。”导演过《花田写扇》等剧;发表作品多篇。
关键词:肖熙凤;川剧;艺术人生
肖熙凤,女,1941年生,四川成都市人,国家二级演员,四川剧协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专工奴旦、花旦,兼擅闺门旦、摇旦。1952年参加工作。先后在金堂川剧团、中国川剧团、成都市川剧院当演员。代表性剧目有《柜中缘》、《打渔收子》、《花田写扇》、《拷红》、《坐宫》、《秋江》、《母女欢》、《孔雀胆》等,其中《柜中缘》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中国艺术家辞典》“萧熙凤”条评价其“戏路较广,喜、悲剧演得好;表演细腻、自然,形象鲜明,风采动人。”导演过《花田写扇》、《生死冤家》、《三转乌纱帽》、《哑妇与娇妻》、《园丁之歌》、《斗硬》、《空瓶》、《活鬼》等剧;曾在《戏剧与电影》、《川剧艺术》等刊物上发表《我是一朵迎春花》等作品多篇。1984年导演并饰演《殷小姐取妻》,获成都市首届艺术节表演一等奖、导演二等奖;1985年指导的《花田写扇》获成都市青少年川剧比赛指导教师二等奖。
采写时间:2014年6月26日
采写地点:四川省成都市碧蔓汀肖熙凤老师家
采写:严铭万平
摄录:李忠彪熊蓉
严铭(以下简称严):今天是2014年6月26日,我有幸在成都采访肖老师,感到很高兴。首先想请您介绍介绍您从艺的基本经历。
肖熙凤(以下简称肖):我妈就是个川戏迷。她跟一个,最爱看川戏,就爱看哪些喃?周倩华老师啊,廖静秋老师啊,王国仁啊,司徒老师啊这些人演的戏。当时我才几岁,她们要看戏,为了方便,就把我带起去占位子,因为她们是很有文化的,是师范毕业的了嘛。我妈也是,这两个很漂亮、很年轻。她们选位子喃,不坐正中央, 也不坐堂子头,就选到那个耳楼喃,就旁边的耳楼的普通座,那个普通座既便宜,好像看得又舒服,后来我们在外国就发现那个耳楼是最好的位子。当时不晓得嘛,所以就常把我带起去,买个饼子给我,我就去占位子,就那个样,看了很多戏,丁点儿大,好像就才四、五岁的样子,故事情节看不懂哈,人我就记到了,那些人是咋样的。我就发现我妈她们,看了回来,走路、哪怕是上厕所,在马桶上,她们还要拍巴(掌),你说那会儿的川剧,把这些年轻的这些学生啊、教师啊,吸引成那个样子。比方说,她们最喜欢唱的是“马到关前难扎阵呐”,唱哦唱哦,简直就是个痴迷,所以后头的时候就那样子给我惯个瘾,我就读不得书了嘛,天天我就想看戏,我说起都笑人,我还要降班、要留级。最恼火的是我那个数学,就是弄不懂!那时毕业过后要办一台演出啊,我那时候丁点儿大,就机灵得很了,聪明得很,还把啥子围腰哦,大人的啥子衣服哦,扎起纸花花儿哦,做裙子哦、做披衫哦,还有把牙膏哦这些弄在脸上,觉得用它们花起妆很白。那会儿我就在树德巷儿嘛,那儿不是有个树德中学?树德三小。我后来又读过树德三小,就那儿里头有个竹园,就是那个树德巷儿走到底有个竹园,很漂亮。有两个院子,后头一个大院,包括两个小院儿,一个小院儿是一般生活的人,一个院儿喃就是黄埔军校的娃娃些,人家就很有钱。大家那会儿不分等级,分啥子富裕,娃娃些都团到一堆,有二三十个,所以我们就很好耍,就好想把人家舞台上的东西搬下来,给人家这样整,那样整。有一回,我们老祖母回来看到这个牙膏没得了,搞了半天,才知道我把牙膏拿来大家抹脸,把脸漤得来哦,又红啊又发烧啊,就说人家她们咋个漤那么白,就搞成这样子一种情况,就是说,我有点儿爱戏了嘛。
严:很小就喜欢上戏。
萧:很小嘛,才几岁,那个看戏,后头就读不得书了,简直把我莫奈何了,我妈还曾经把我从公立小学转到那个树德三小喃,私立学校嘛,好像要好些,又挨到我祖母近哈,哪晓得喃,开头考试啊,我硬是考不起,我妈还在外头去买一个纸,还帮我整假。我妈有文化,“这个凤娃儿考不起,咋个办哦?”那边要降级,就说把我转到这儿来,可还是不行。所以是我妈给我填起的,这样一考我就考第3名,前三名。考起了。哪晓得进去过后,还是读不得,降班了,根本撵不起走,一天就想看戏,就逃学了,所以我曾经写了个回忆录就是:戏迷。我妈也是戏迷,我也是戏迷,就老戏迷的小戏迷。
严:与您的妈妈对您的影响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萧:太大了。还有个九也是,她们都是很漂亮的人,都是很有文化的人,她们也就迷进去戏,也把我也惯到里头了,我们屋头没得哪个演戏,就只有是演话剧的,我后头话剧也看得多,这种情况下就奠定了这种爱戏,不然咋个突然就爱上戏了喃,但现在的娃娃些就看不到戏了。比方说剧场,现在就规定不准进小娃娃。我们就是丁点儿大就看起这些人的,尽是些名角儿,还有王国仁这些,后头,就有祝婉秋,我记得,他们轮换,有些走了,有些又来了。那时候最看得多的是周倩华老师和廖静秋,我对他(她)们印象有点儿深。丁点大就有印象哈,这种情况就爱上戏了,后头就是五二年,重庆的周慕莲老师,他来招学生,给他们实验学校招的。重庆有点儿远嘛,我们妈听到了这个消息。我们大伯伯(萧成树)二伯伯两个,写张条子。凤儿既然喜欢戏,就是说,学习不成了,读书不行了,她还爱戏,就等她去了。我妈就将就那个条子就把我带起考,就考起了。人家这个周慕莲老师,我没看到过她演出,但是很有名望。
严:当时重庆市有什么学校啊?
萧:戏剧实验学校,就是现在的好像就是黄学成他们那一批人(读过的学校)。听说的哈,他们那一批考的时候考了很多花样,比方说考下眼睛啊,眼睛那会儿很小噻,就做不来。我说我很勇敢,我会做对对眼儿,我就看到王国仁,演那个啥子戏的瓜娃子,他就做对对眼儿,你想这个印象好深嘛。我就当场做个对对眼儿,一下子就翻不过来了,我印象太深了,这个事情,他搞慌了就在背上拍了我一下,一下我就正眼子一下就对转来了,把周围多少人看到笑惨了。再因为还有个我们邻居,叫小丽,她跟我差不多大,她读得书,我读不得书,她后来是医生,她当时也想跟我们一路去,她没去看过戏,看见我眼睛弄成那样子,整不过来,吓倒了。“我不考了,我不考了。”她就没有考了。他们又看我们手杆哪,喊我们唱个歌啊这些,我还唱个儿歌,好像还唱些“月亮白光光,摘来投酱缸,聋子听了快起床,哑巴大声叫出来”,“做贼赶忙的赶忙”,就唱这些,净是儿歌,本来我妈又没有教过我唱这些。他说“咦,这个娃娃还可以”。看到虽很瘦小,还是有这个天赋,有点机灵,有点聪明,再加上还是这个纸条子哈,介绍了我,加上我妈。我那个回忆录还写了一句笑话就是,我说“要不是因为我,我妈都考起了”,因为我妈很漂亮,当时我记得到她扎个白绸子辫子,好小嘛。她还演过,她们一见面就泡那个茶,那个老师啊,就这样端起茶,多秀气,专门演那种女角儿,我看到很稀奇,我就紧把他看到,多秀气的,揭起茶盖子,呷一口。后头想到这些味道很绝的嘛。就这样,我妈也学到,也跟到来,大家都斯斯文文坐起。他们两个就问她,“其实我还演过戏的”,我妈说的,她就是在学校头演《珍珠塔》中的小姐,她也热爱这些,不是她咋把川戏看得那么入迷嘛。所以在当时,我就有很多基础,他们就把我收了。
严:您的妈妈是教书的?
萧:教过书。我妈是裁缝铺老板的女儿,她很享福,因为底下匠人很多,煮饭什么都不要她去做,她就专门在楼上攻书,所以说后头她的文化有点好。我后头离开她,但是经常去耍,我奶奶就不要我走了,把我留在她身边,就住在树德巷儿的。我的舅舅对我的影响很大,对我们这一家影响很大。
我考起实验学校后,我奶奶不要我走,说我到重庆去太远了,她说看到我又留级又降班的,天天都还逃学,实在没得办法了。我逃学还有个小插曲,有一回不晓得走到哪儿去了,总之,哪儿有戏就想去看了。稍微大一点了,就走到春熙路那儿啥子。还有一回被老师逮到了,那一次我进去了,因为有些时候我妈并没有去看戏,这个瘾太大了,简直是大得很,就跑到底下有栏杆的地方,底下那儿是普通座,普通座那儿有个当头,在那个台子边上,我就站在那个台台高头,本来个子就瘦小,就在那儿站到看,大概是《薛刚反唐》之类的,有点武打这些。有个老师就问我:“这个女子,你是哪个的娃娃?”他以为我是他们里头的,我就吓得打抖了,我说糟了,又没有买票,我就说不是得哪个的,我就吓得打抖,他看到我情况不妙,他就把我后颈提起来,“你是哪儿的哦”,“树德的”,“那么远。”他说了那么远,我才晓得我走了好远了。“你给我躲在这儿看戏来了,要完了,看把你踩到,多挤,快出去,快出去”,就把我拉出去了。我一路走一路哭起回去,就这种情况,就那么爱戏。前几年就碰到了一笑老师:“嚯,你当年拉到一个小娃娃就是我。”“哎呀,狗杂种,就是你索,早晓得嘛,你那么爱戏,那么我就不拉你出去了,我就招待你看嘛。”他很幽默,他是演喜剧的。因为我们奶奶不要我到重庆,最后是咋个的了,我就到了金堂去学习。她有个结拜姐妹,她姊妹的女就叫云裳,艺名就叫云裳,全靠她把我带走的。这个云裳她的本名就叫周倩华,成都人,当时那段时间,她正在成都她妈那儿养病,我奶奶就经常把我带到,就喊我喊她五姨婆。奶奶说:“算了,我喊你们五姨婆喊她的女(她在那儿当团代表)把你带起去。”我只要不学习,管得哪儿哦,就高兴得很,就去了。那是五二年的秋天,我就穿了个背背裤,穿了双球鞋,跟云裳老师我们两个,就喊的嘛,一起从成都坐到金堂赵镇。我很喜欢那儿,那儿很闹热。卖核桃的,卖花生的,摆堆堆,两分钱一堆,一分钱一堆,卖橘子的,娃娃家喜欢嘛。我就看到好多船哦。她们那里还是要通过考核的,我看到周边已经有很多娃娃了,当时都是一二十个了嘛。那些老师,是集体老师,小叶老师考我的时候,就唱“芽儿低低,门儿咪咪。”她是老方法的考试,这边就喊我唱个歌,周老师这边,重庆人,就喊我唱个歌。这一边就喊我唱“芽儿低”,就喊我吼出来,恰恰我就吼不出来那个“芽儿低低,门儿咪咪”,她们就笑这个是个寡母子喉咙的嘛,咋办喃,看到又黄又瘦,又小个子,又想到人家是团代表带来的,平时我就喊她,通过这个关系就把我留下来了。留下来当天还有个机遇,有个串吼班的没来,就喊我去串一个吼班。那个衣服太长,裤子从我脚上一拉就拉到脑袋顶上去了,衣裳袖子长了就给我挽起。我记得当时是罗金冠老师的《三打祝家庄》,这些吼班又是匪班,管他高高矮矮、肥肥瘦瘦的,都来了。又不是正规军队,所以就把我凑一个上去,然后就拿一个刀,那个刀那么长,刀柄都有那么长,我那个手好细,当时拿到,这个样子,十二岁了,一出场就把我吓倒了,就贼嚯嚯的这个样子,吓得抖,看到底下黑压压的人,都是仰的往上面看。第一次冲上舞台,我抬头看同我一起上场的伙伴们,咋她们也在抖喃。我就觉得奇怪,可那些老师说这个女娃子还会表演喃,她还晓得抖。人家《三打祝家庄》的人追来了,这些兵就吓得打抖,歪歪倒倒地跑。我就是恰到好处,实际上并不是我在表演在抖,我是心头吓抖了。他们还觉得很感兴趣的。第二天他们那个《合宫欢庆》,演苗妃的演员病了,就叫我去顶替。晚上,热心的晓阳老师给我认真地打扮起,欢欢喜喜地就上场了,我记得其中有个台词就是:“哎呀,你看,矮窟矮窟,像他妈个太和鸡,”当时演郗氏的老师指着我就说出这句台词,还气势汹汹的。嗨呀,我说我就矮得嘛,我就想到这个是骂我的嘛,我当场就哭了,这一哭台上台下的都逗笑了。他们越笑,我就越气,伤心到了极点。戏一完,我就跑到后台大哭起来。有的老师向演金妃的姐姐说:“郗氏骂苗妃,苗妃气得哭,郗氏骂你,你连一点表情也没有,像个木头人,以后向熙凤学习!”他这一说,我才明白那骂我的话原来是角色台词。
严:那您当时到金堂进的是学校吗?
萧:不是学校,就是金堂县川剧团,当时有文化局的人的嘛,五二年嘛,都喊我们学b、p、m、f,扫盲运动喃,让我们学文化了,学生都跟到老师些,老师学生全部都在学文化,但是我始终学不进去,就b、p、m、f我现在都不咋子懂,不过有些时候还是可以应付,就是剧本读得多嘛。
严:后来呢?
萧:后来组织上就抓到我进行培养。我们这些练功都是很努力的,非常吃得苦,老师最爱我。我们一批是女娃娃,睡个多大的寝室,男娃娃又另外睡个多大的寝室。金堂的老师些啊,好得不得了,她们艺术之高啊,她们所演的戏,她们的味道,相当不错。云裳,人家演闺门旦儿,还有个晓蓉老师,她是演摇旦子,又演男的女的,表演相当好,也时髦,她那会儿化妆都不画红眼皮,所以我后头一直都不画红眼皮,就是受的她的影响。生角又是刘洪祥爷爷,而且还有个就是张温刀老师的小生,还有曲峰、刘宗林,就是这些总根根些,他们的表演,她们的唱腔些就好得很。尤其是他们的品德高尚,为啥子我出了国都想回去,回金堂,到处都要了我的,我就想回金堂,我这个报恩思想也强,我就喜欢她们的嘛。我对哪个老师都尊重,而且我喃,还有个优点,我不骄傲,我多早就当主角了,都不骄傲。所以,她们对我相当好,又给我盖铺盖,没铺盖,都要把他们大衣脱了给我盖起。她们没得娃娃,就只有罗金冠老师和晓蓉老师是两口,生了两三个娃娃,其他的老师全部都没得娃娃,所以就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心肝宝贝。罗金冠老师他们两口也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心肝宝贝,所以我简直落到福坛里头了。我们睡的铺床在二楼上,多宽的,那个大家都铺在那头,那个罩子就是门了。有时拍板把人家地板拍响了,老师就说:嘿,女娃子,睡了睡了,这会儿不要你勤学了,我们要睡了。还有一次,练功嘛,就一批女娃娃,他们在那边,我们在这边,起倒夜了,就跑到公园后头喊嗓子,站到那个高上,那会儿要打人,枪毙人,有些时候枪毙的那些坏人些,没收尸走就在那儿靠着的。我们一群站在那儿高上一排排,伴起“咦~啊~啊,芽儿低低,门儿咪咪”。正在那儿咪,就看到两个眼睛,绿荫荫的,两个圆眼睛,“有鬼!”大家拔起来就朝后头回转跑,有些人跑绊倒了,扑爬跟斗地跑,跑起回去了,结果仔细一看是一个猫,把我们吓惨了。在练功的时候,练舞台步,从一转又练到两转,两转练到三转,最后要跑一百多转。在中兴大舞台高上跑跑跑,要跑平,等于是你端到水都不能浪,就教我们这些基本功嘛,每天都要这样子,练得好攒劲哦。然后练眼睛,眼睛就要左转右转,转圆圈圈,对对眼就不消说了,左转右转转圆,并不是把这儿的眼皮睁大,这样子就没有神,硬是要练出有神。还有练水袖,啥子都练了的。虽然是一个县剧团,却非常地认真,每一样基本功都练。
严:您在那儿都学到了哪些戏啊?
萧:我在那儿还是演了很多很多的戏。她们专门就抓住那些几个就培养,培养的时候抓住就不放。当时我就演了《拷红》,还有《拾玉镯》,也曾经中间演了《柜中缘》。《拷红》是晓阳老师和云裳老师教我的,还有我跟汪爷爷两个配,所以,我的打炮戏是《拷红》。《拷红》啊它有几个戏嘛,就是曲峰老师嘛,都是靠严了(配合好)的几个,把我也抬出来了。还有就是我们云裳演的《思凡》嘛,还有就是《夺三关》这些嘛,是刘鹏翔爷爷演的嘛。演得、唱得好得很,然后有晓阳老师,就是钱苍辉这些嘛,扮男装的,非常漂亮这几个,还有蒋文道老师,我就从他们这儿学了很多。不一定光是看到女角,小花脸等,你都有戏曲的。当然,你要以一个为主,我就是演她们女角的戏,我先给她们配戏嘛,原来我就是串猴子。演那些女角都是很重的了,就慢慢演这些戏了,所以说这个后头就给我排了一个《柜中缘》。我们尽演的是那些大幕戏,折子戏还是演得很少,就是说拿手一点的折子戏,自己觉得可靠一点儿的,喜欢点儿的就是《拷红》,还演《红楼梦》这些了,三天都喊我赶。因为几个剧团凑在一起了,我们多早就把剧目宣传出去了,哪晓得另外来了个县剧团,第二天就要演这个剧目。我们还卖啥子喃,就把我弄起去赶,好吓人哦,就关到一个楼楼上,喊了一个师妹师姐把我照顾到,饭端上来,三天,赶一个剧本,结果冲上去,两边一天都在演这个戏,那边演《红楼梦》,这边也演《红楼梦》。这边我喃,观众对我都有好感了,我跟张默都老师演嘛,这样子一演了下来喃,观众的评价是那边的贾宝玉好,这边的林黛玉好。当时就给我稳到了,后头就演的折子戏就是《三堂会审》这些,都是大幕啊。啥子角色都在喊我演,结果把我培养出来了。我的感觉就是,演员要多演,要啥子角色都要去,你才锻炼得出来。你看现在的,我就发现了,我才是呆得最多剧团的人。我正式调动只有三个团嘛,我回国回来就从金堂调到温江了,温江人民艺术剧院,就是现在的地区剧团。然后又把我从温江调到四川剧院了。我早就要回来了,我有个奶奶喃,80多了,她一个人,晚期和后期就是我们两婆孙相依为命。她为我付出很多,老了很造孽,老来就孤单了嘛。所以说是逼到我八六年调回成都的,就是四川剧院联合团嘛。后来又改行做起生意来。
严:您是从什么时候做的生意?
萧:我就八十年代,我还没有正式离开剧团,我也没有离开剧团做生意,因为调过来任务就不是那么重了。调过来,我只完成了好多事情喃?就是导演了一个现代大戏,没得模子的《活鬼》。这个剧本先拿给好多导演老师些,她们都没有愿意导嘛。最后她们说肖熙凤来了嘛,肖熙凤原来在温江导演了很多戏,现代戏。就交给我了,当然我才调来不久,我也不好意思推,但我也不愿意推,我就多高兴地接手了。接手了我就把它整出来了,后头导出来的时候,金光远演的主角嘛,效果还多好,反映很好,到处去演了的,北京啊,都演了的。都反映相当好,反正还登了一些报,开了这个座谈会,导演座谈会啊,文艺座谈会啊,在北京给我们举办讨论这个戏。所以我在北京还是整亮了几个事情。
严:您的这幅照片是什么时候的?
萧:这个就是国务院演的时候嘛,1959年,出国前夕,在国务院演《柜中缘》,朱德握手,你看嘛跟我握手照的。毛主席看了我们《柜中缘》专场演出后,跟我们一一握手,说:“辛苦了,演得好!”我们快要走出演出厅时,一位同志招呼我到毛主席那里去,我转身高兴地走走走,我又穿着一个演戏时的高鞋,一下滑倒了。毛主席顺手把我拉起,并亲切问我的住址姓名,我都作了回答。主席风趣地说:“啊,希望的希,凤凰的凤!”后头呢音乐响起,主席很礼貌地请我跳舞,我想要是主席问我的学习和思想怎么办,我平时又不爱看书读报,我就赶忙对主席说:“主席,我来北京的时候,剧团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叫我见到您时向您问好!”毛主席高兴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周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也都接见过我。这些相片一般得不到,还是那个邓先树老师给我的,他说的“我给你一个最好的礼品”,他没出到国噻,他在选演员的时候在场,他就送给我,我说的“好珍贵”,我就把它保留了。后头我还是演了几个戏的,从调过来起,导了一个大幕戏,又演了几个戏,其中有个戏,就叫《打渔收子》,我把它改过的,有些台词小改了一下,人家本来是在《母女欢》的基础上,就改了的,但是我们后头演这个戏的时候很好,我就和彭玲排,彭玲演妈,我演女儿的,她们就很满意。我们的化妆、服装,都是有点改革的味道,我们还是拿的老服装来穿,但我们穿法不同,就不像原来的,妈要穿个黑架子。我们就是拴个围腰,就是拴的裙子,就像打渔人家的打扮。我做了一个蓝颜色的一个帕子,中间挖个洞,拿来这样子扣上来,还有两个小飘带,戴了一朵鲜红花,反映相当好。这个戏,演了几十场(其他戏也演了,《坐宫》哪,还有几个戏也演了)。所以我爱钻这些东西,甚至于有些人说的,你那儿戴个红花,这儿是个蓝绿花,绿颜色配那么红的花,有点苕。我说就是要二苕二苕的,我太艺术很了就不是那种人了。她这种人就是河边上啊、路边上啊,摘了一朵野花来插起。我恰到好处,我就是这么倔。有些时候,不一定完全要听观众,有些可以要听,有些觉得不能听的就不能听,你自己要有一个打米碗。
后头,没有隔了好久了,我就做生意,为啥子去做生意呢,因为那儿七天演一场戏,当时团没合并,是一团、二团、三团哈,当时我在一团,我都觉得她们演员本身就多,本来调我来,我听到领导后头给我摆的,就是说他还是经过调查的,他就问过蓝光临,因为我们共过事,是去教学的时候,是北京那个李老师介绍我们好些人去昆剧传习所去教学的时候,我们在上海、无锡,待了一段时间。很有几个人,还有曾玉华老师,还有萼英老师、易征祥老师,许权老师有事,没有来。就有蓝光临,因为我和蓝光临很难得接触,没有拍过戏,当时还没有调来,你想嘛。他就观察到的噻,他说的,肖熙凤能独挡一面,这个人是很可以的,他就是这两句话。他又问彭玲,那会儿彭玲我也没和她接触过,但是她了解我了,我也排了一下就是这个《打渔收子》喃,我给她排的妈,也不是私人交易。她就说的,肖姐姐这个人应该要,她在温江现代戏导了很多。我调到成都后,由于人多,一个礼拜演一次,就是轮转转那样哈,照顾到大家都要有这个上演机会。有一次我看到罗玉中,他有个戏激动地不得了,我当时心头想的我说的罗师兄你咋个那么激动喃。我们拿到就无所谓的,我们演了好多戏。他都那么得行,那么有名望的人,有个戏他都那么紧张。他很喜欢我,他还想跟我两个整《翠香记》,排了两道的,后来他生病了,就没演成。我也很遗憾,他约了我两个戏,一场都没跟他配合到。
我觉得现在,哪怕是招的这些学生也好,没得演出的锻炼机会,还是很艰难,人家说的要培养好多个出来,要有锻炼的地点,要有实践才行,我们是后头好多戏堆出来的,说老实话。你说老师教你,她哪儿有那么多好的精神,你要看她演嘛,对不对,你还要挖她的心里边的体验,是不是嘛。我后头就有多余的时间,遇到我的一个儿子生病了,我生了两个儿子,老大生病了。又有点忧郁,我心头就着急,我的工资在温江,在当时来说,我是最高工资,都才两百多元钱,比哪个都高,但是,这个病不得了,当时要住医院的。这样子我又咋个办喃。我又没有脱离这儿。起初还没有完全下海,就在省电视台,去他们广告宣传科帮他们找演员,变得有点像剧务之类的。我就帮他们跑。因为我曾经就参加过一次,就是拍县上的一个小女孩儿,来拍《花田写扇》这个戏曲片的一节戏,我就有幸参加了,给他们当了一次剧务。所以他们就认识了我。有些人就觉得我很勤快,也不说是好能干,就非常勤快,非常会跑路,会找人,很麻利。他们很喜欢我。我是个急性子,又是个热心人。后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就喊我去当个剧务。在那儿就搞了三年,但是给我的报酬还是可以。
严:您说一下您最满意的剧目有哪些吧!
萧:我最满意的折子戏就是《拷红》、《打渔收子》、《柜中缘》这些。我是很活泼、很天真,演得很朴实、很勤劳,戏中的这些善良的女娃子,我就喜欢。像《花田写扇》这些戏喃,我比较有心得。比方丫头戏,我个子本身有点像,小巧玲珑,但丫头戏有好多,就要把她分开,比如红娘是相国府中的丫头,要成熟些,有档次点儿。那么《花田写扇》中的春莺,是员外的小丫头,她又要不同些,所以她的举止、行为、言语、表现的剧情完全不同,我要把她分开。《翠香记》的丫头儿又不同,她比红娘又要幼稚丁点,比这个《花田写扇》的春莺又要大丁点,因为她还可以给这个丘老爷开玩笑,就是说很可爱,是一个多善良、多可爱的为小姐办事的一个姑娘,所以又不同。还有那个写扇,她还是要为小姐做事,来约这个边相公,就约她在这儿写扇,她们就碰头了,碰头就一见钟情了。我演的丫鬟的角色比较多,掌握的比较恰当,他们原来就是写的报纸啊都说的我,所有的我都不同,还有我的上下场特别注意,上场下场我都要把它分开。就是不是丫头,她是打渔人家的女,她是农村头的女,我都注意她们的不同。如果是雷同了,就不好看了。我后头还演了《王三巧问媳》,也根据性格不同,个人的身份不同,我就要咋个把它区别开,这个事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会创新,人物才有个性。
严:您从艺经历当中,有哪些老师、朋友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萧:学戏时印象深一点儿的就是晓阳老师、云裳老师、张光斗老师、罗金冠老师等。还有一个张凤侠老师,他是男的演女的,他是教我们也教得很好的,有一次他教我他的拿手戏是《桂英打雁》,他付出很多,确实很不错这个人,他主动地教我这个戏,还给我串起吼班,他串起吼班老师,站到我旁边,生怕我掉了台词,好给我递。然后我就打扮起了,戴起了,弄起了。哪晓得那个箭,一射射反了。射到鼓师,那个鼓师狡得很,“哎呦,你这个人才会射哦,把我们这么大的雁都射到了”他就缩下去了。这下子就把内外场都逗笑了。我想糟了糟了,第一次唱折子戏,就出那么大的事。他才幽默:“你教下我,女子,咋个射倒了喃?”哎呀,笑人。所以说这些老师就好到那种程度,他串个吼班,就这么好。有些老师硬是给你拍板哦,桌子上给你拍起。有一回就是那个罗金冠老师,他给我念那个啥子公主戏,他就在他的桌子上,打拍子,他说“不要顶板哈”,他就找些代名词来带那个词,“掐吧掐吧一掐吧”,他是演小花脸的,“掐吧掐吧一掐吧”,我说这个掐吧掐吧就学到了,我不晓得他是用的代词,我也就“掐吧掐吧一掐吧”这下子妆上起一下子就搞忘了,“那个女子,嘿,我是给你用的代名词的嘛,给你理的是这个板,你咋个就把板板唱出来了。”就那么搞笑,有些时候把锣鼓唱出来了。云裳老师给我念了个《锦江楼》的翠妹妹,一出场就是“朵儿来求多”,我就把那个腔就放了,“嫂嫂带我做啥子哦,朵儿来求多”,一下就唱了锣鼓。所以从这么幼稚的时候人家教你,就像喂奶一样。一张白纸,老师们要费很多的力气,下好多的功夫。晓阳老师教我跑台步啊,弯手弯腰弯腿,你看嘛我们手好翘嘛,这些都是晓阳老师教的。她们就是不分工的分工,分工合作。简直好得很那些老师,给我的印象太好了,太有艺德了,不争风吃醋,又不得嫉妒。还有一次,省上来金堂搞创作的老师要看我们演的戏,当时罗金冠老师就给我排了一个戏,就是《南英思兄》。一个人唱的,是个闺门旦。唱了下来,他们几个就在茶园头坐到,来问:“肖熙凤是不是成都来的?”“是。”罗金冠老师就把我带到,“人家几个老师看到多喜欢你的,去见下她们。”我就去了,一位女老师突然拉着我的手说:“凤儿子,我是环的嘛”,我认不到了,萧宗环就是魏蓓媛的爱人喃,都是名导演、名演员,演话剧的,她的笔名都叫环子小姐,就在棉花街、太平街的那个市话剧院当演员,就那会儿年代哈,就在那儿。后头他们两口就到广州去了。我小的时候看了她很多话剧,但是我后头多少年就没去了,就在金堂学习。她抚摸着我的头说:“我看了你的戏,有前途,大家都说你演得真。”边说边把准备好的笔记本和一支金笔送给我,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表演艺术是永无止境的,但无论你演什么角色,都要感觉到像真的一样。”这话从此就成了我艺术上的座右铭。后头的时候,我们还是见到过面,我到广州去这些。
严:肖老师,您谈谈对川剧的继承和保护这一方面的看法。
萧:还是有一些看法,继承保护,我觉得,继承要扎扎实实地继承。像有些老师在做传承人了嘛,还是很不错,现在在抓这个了。有段时间我还是感到有点儿可惜了样的,我们热爱这个艺术的嘛,就觉得没得人在抓,现在政府在抓,还是很高兴。但是这只是极个别的,我觉得有的可以当继承人的还是没有当,应该胜任的没有胜任。比如黄学成这些,我们接触得多,我想起他那些身段,很认真,他都不是继承人。我是不能胜任,我晓得,因为我的东西靠不实,我总是在动荡,我的东西我要改。我有个想法为什么要改,老师们的东西要传下来,确实要扎实地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我们要根据时代,我们的演员进行改造创新,不能仅停顿在那个年代,百百年、千千年前,社会已经进步了,人们的思想、各方面都进化了。比方,铛铛铛扯,扯铛铛铛,你去走哇,你看还有不有人看哇。京剧都改了,以故事情节、人物出发,音乐、锣鼓都要改。我们现在川剧也在改,帮腔、领腔都是女的,原来是男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演员随时都要审视观众的心态。他们现在的思想是什么,喜欢什么,还要吸收什么,哪些他们不能吸收了,哪些还能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服务的东西,我们要加进去,我就是有这些想法,所以我的东西随时都在动荡。我举个例,近两年我整了一个戏《母女欢》,它和《打渔收子》是背靠背的。《母女欢》的本质是比《打渔收子》还要早,要早好多年,里头很多糟粕。它的语言有很多糟粕,很难听,我在这儿都不好说。所以就改了,改得相当好。《打渔收子》是很完整的一个打渔人家的剧目,是跟一个忠良之后结合了。什么数鱼啊,数很多各种各样的鱼,很快活,很舒服,我演了很多场,长期在演这个戏。我小时候跟小袁老师演的《母女欢》,现在我在一个火把班子上有个女的,她说这个《母女欢》还是可惜了,没有人演了,就像封锁了一样。她拿给我最老的本子,这些语言太肮脏,不舒服,要不得,我把它改了,把剧本大概的意思保留。我把台词完全变了,再加上现在有的东西。比方说,我那个妈在她年轻时丈夫就死了,她还是想重新找对象,但又有点介意。女娃娃已经大了,也到了要找对象的时候了。这两娘母在台词上要开点玩笑,我就加了一些“妈,您不要着急”,加了一些很现代的台词,到处去演的时候,我都试着看观众接受得了不。有些人开始接收不了,有些老的反而还接受了。
严:您那一改造,让它很有时代感。
萧:是的,很有时代感,符合了现代人的品位。老年人也是,我们在温江先上这戏,我问那些老戏迷。他们说咋这么久都没有在温江上演。我说:我不好意思来演,不晓得过得了关不。他们说,哎呀这个戏可以得嘛,你咋个没有演呢。我说,你们觉得要得,我又放心了,而且又是年轻人看,所以后来又到处演,农村、乡镇上都喜欢。
严:您现在还在演吗?
萧:在演,但最近没有演了。那天演了《思凡》后我就没有演了。前一个月,我感觉我人不好。还有跟我配戏的人的原因。我这人有个特点,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人,最怕人家东说西说的,外头的人就喜欢东说西说的。随便哪个我都合戏,我都愿意,我不嫌哪个,人家也不嫌我。比如朱恩亮,我们单位的,他很难得演戏,演折子戏就更难了。有时演只有几句台词的戏,串点什么的。他很积极地来找我合戏,我就满足他,同他合。比方说《秋江》、《钻狗洞》。《钻狗洞》最早是陈广忠演的,后来他去整电视剧了。后来,我又和谢顺成排,戏改得很好,寓教于乐。谢顺成病故,这个戏就放起了,没有人演了。我想可惜了,这么好的戏,它多有意义,是喜剧。然后我就把朱恩亮给排了。他很高兴,演了几场,突然过世了。好几个跟我排戏的人,都病了。苏先林病了,苏先林我们在温江拍了很多戏,他也生病,也很少演了。杨德华也生病也瘦了嘛,原来他专门演摇旦子,跟我演妈,演《拷红》的夫人啊啥子,我们合作了很多戏,后头彭玲没演的时候遭绊倒了,彭玲绊倒了,没演那个《打渔收子》了,就是她在演那个妈,你想演了好多场,是今年她病了,也少演了。我的身体我的精神,还可以演五年我都不怕,你看我的积极性哈,还有那么高,现在都在演女娃娃,非常活泼。虽说这脸门老点了,丑点了,身材变粗犷了,化妆还是可以的,可惜现在没得人配戏,没得人了。所以我就感到惊慌了,就这个危机,我就说的没得后继之人了。尽是我们这一批老的在演,而老的这一批,只有这几个在演。周素轩啊,我啊,还有县上的几个这些在演,还有个郭正娟啊这些在演。还有个广汉的张红勋跟我演戏,也是有两个戏的,也是很好的。也老了也是七十几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演啥子喃,哪个跟你来演嘛,找不到人来演了的嘛。
现在四川剧院喃也招了一批生。省川剧院报上登了嘛,招的多,招了还在外头进修,培训,培训了然后才回来演出。还有一个彭代秀,原来的芙蓉花仙团喃,现在我们才见了面没得好久,我们才聚会了没得几天,她也还在招生,我就问她分得出去不,原来培养出来,我很佩服,每一阶段,每一学期她都要培养几个尖子出来,来接到芙蓉花仙,我说现在你培养出来的有没有人要。她说有,尖子当然就有人要。我说像这样子情况,我就没有早先子那么担心了,反正都有继承人了。现在是观众我们还要培养,有些多爱看我们戏的老观众,好多就没在了,越来越少了,所以还是要培养一点儿年轻的观众的嘛。
严:肖老师,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再见!
(责任编辑:刘晓红)
收稿日期:2015-12-13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2YJA760062)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严铭(1967-),男,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万平(1954-),男,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K825.78;I236.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16)03-1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