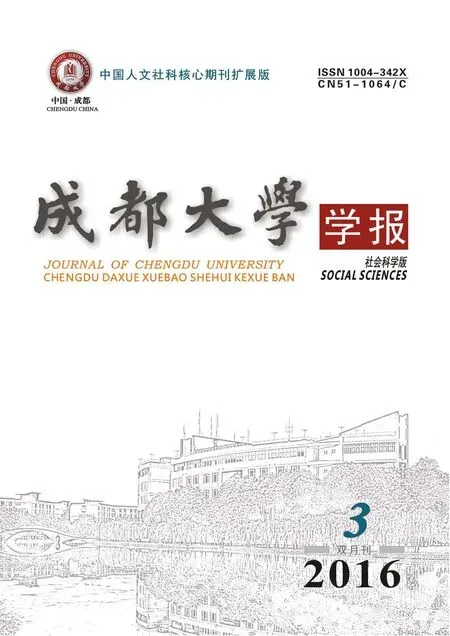民国初年性别秩序的松动与紧张
——历史与文学双重视域下的周静娟之死
蔡 洁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文艺论丛·
民国初年性别秩序的松动与紧张
——历史与文学双重视域下的周静娟之死
蔡洁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100081)
摘要:1913年8月,南州女校校长周静娟因与教员徐品花自由结婚,被父亲周钺逼死于江中。案件被曝光后,引起了上海各界的聚焦。上海县检察厅与华亭县检察厅围绕犯罪地点,对本案审判权展开了一场数月的争夺。尽管周钺最终难逃法律的制裁,舆论界对周氏父女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此外,周静娟与周钺在新旧之间徘徊的形象亦被文学作品所捕捉和书写。本文通过历史与文学双重场域所呈现的“周钺溺女案”,探究民国初年性别秩序重构中的松动与紧张,进而分析,女性在突破传统道德伦理方面,民初与“五四”之间尚有一段距离。
关键词:周钺溺女;审判权;性别秩序;新旧纠葛
周静娟,松江市华亭县颛桥镇人,在清末年间便走出家庭接受新式教育,并担任南州女校校长一职。1913年8月,周静娟因与男教员徐品花自由结婚,在身为江苏省议员的父亲周钺的逼迫下,玉陨香消于江水之中。随着司法界和文学作品的介入,“周钺弑女案”被推到了舆论风口浪尖。本文拟以周静娟之死为个案进行考察①,分析民国初年性别秩序重构中的松动与紧张,以及在此转型时期,兼具新旧观念的人士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结和彷徨。
一、父弑其女:周静娟溺水而亡
周静娟生于一个新旧参半的殷实家庭。父亲周钺为江苏省议员,拥有一妻数妾及十余个子女[1]。从新式学堂毕业后,周静娟任教于南州女校,后被推为校长。期间,一位被开出的教员为报私怨,散播周静娟与原校长徐品花之间不正常交往的言论。周家父母多次强逼周静娟归家,而周静娟却私自与徐品花在校园举行了新式婚礼[2]。随后,周钺率人前往南州女校,称婚礼不可草草举办,劝女儿一同前往姑父家重新商议婚礼事宜。从姑父家离开后,周钺又以筹办嫁妆为名,诱骗周静娟先行返回周家。然而,当船只驶至半途中时,周钺竟逼女投江自尽。周静娟方才识破父亲的骗局,但见势已迫只得含泪投江。船夫急用竹篙挽救,周钺竟夺过竹竿猛击周静娟,待到江面“血流水红”才释手归家。越日后,周静娟的尸体在黄浦江面浮起后被姑父送至周家。周钺原不愿接受,后勉强以一口薄棺草草收殓并弃于颛桥附近方家浜一古墓旁,不许将其纳入家族之墓。周静娟的丈夫徐品花闻此噩耗便将周钺告上华亭县检察厅[3]。
尽管华亭县检察厅迟迟未将周钺拘拿归案,但周钺江苏省议员的身份使得社会各界对“周钺弑女”案的关注度迅速升温。“溺亡”、“女尸”、“血案”等刺眼的词汇吸引了民众猎奇的眼球,以致该案上榜“上海春秋”的年度“趣人趣事”[4]。新民演剧社率先推出正剧《周静娟》[5],各界深受感染,尤以松江人士最甚,纷纷来函要求再次上演[6]。然而,时人对周家父女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一评论者“读周静娟事”,深感“可恨可叹……叹此巾帼良才,不得终其天年。”[7]前往采访的一位记者闻周静娟死于非命的惨状,深感痛惜[2]。有人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周钺称,“堂堂省议员,尚且如此不文明,何况市乡愚民……唯求执法者守正不阿,庶几可慰一般不平人之意。”[7]还有论者批评道,“禽犊微物犹知爱子”,而周钺作为文明之人怎能对亲生女儿加以残害?[8]此外,王钝根戏拟名为《讨爷军总司令通告问》的游戏文章,假借“讨爷军总司令”之口号召各界为周静娟报仇雪恨,并对守旧的家长提出忠告,以免遭受斩杀之刑[9]。然而,亦有对周静娟自由结婚的行为不表苟同者。如署名为“木”的作者称,周静娟实为“大逆不道”,假“自由”之美名将男女恋爱“举为天经地义。”[8]甚至当周静娟案落幕后,还有一张姓父亲借“周钺弑女”之事恫吓不遵父命的女儿,颇有欲效仿周钺之势[10]。
在舆论的推动下,周钺将会受到何种审判成为民众翘首以望的焦点。然而,华亭县和上海县两个检察厅围绕该案“审判权归属”问题展开的争夺,使得对周钺的审判屡遭搁置。华亭县检察厅接到起诉书后并未及时受理,毗邻的上海县检察厅则以周静娟遇害及厝棺之处均在上海县内为由[3],率先派出法警将周钺捉获,但因天晚之故,暂寄押在华亭县检察厅内[11]。徐品花闻悉便将状书转呈上海县检察厅[12]。华亭县检察厅为重新挽回对本案的审判权,也以案发地点在其管辖之内为由,拒绝将周钺押交上海县检察厅[13]。双方争执不下,便请示苏州高等检察厅核办[14]。苏州高等检察厅核定犯罪地点确在上海[15],令华亭县检察厅速将周钺押至上海县检察厅[16]。然而华亭县检察厅称“尚未奉到高等检察厅之命令”,再次拒绝交出周钺[17],并率先将证人收押厅内[18]。随着犯罪人和证人相继为华亭县检察厅扣押,上海县检察厅无法审判[17]。为平息两县的争执,苏州高等检察厅派员重新勘察周钺的犯罪地点[19]。上海县检察厅和华亭县检察厅分别依据周静娟姑父的信件[20]和周钺及证人的供词[21]以争取作为该案件审理机关的合法性。最终华亭县检察厅转败为胜,对周钺作出4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10年的审判[22]。
纵观争论的整个过程,双方的分歧集中在“审判权的归属”上,而非对命案的具体量刑。根据苏州高等检察厅公布的通令显示,各级检察厅皆存在经费不足的难题[23]。华亭县检察厅曾向周钺索取1200大洋的保释金[16],周钺虽强烈拒绝但受到审判后又不得不缴纳[22]。另外,对于邻县的案件,上海县检察厅屡次派员拘押犯人、证人以及勘察案发地点等诸多行动,难免显得过于积极。因此,双方争夺审判权的背后,应该存在着诸如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考量。
二、多元形象:历史与文学场域中的周氏父女
对于“周钺弑女”一案,上述两个县级检察厅着重关注“审判权归属”问题,相对淡化了对案件本身诸多细节的探究。若将周静娟本人留下的信件同周钺的供词进行比较,不仅可以看出周钺的言语多有不实之处,亦可窥见周氏父女对自由婚姻的复杂态度以及展示出来的伦理观念。此外,文章通过考察周氏父女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进而分析时人对自由婚姻的多元心态。
(一)自由乎?名节乎?
周静娟在结婚之前曾致信姑父刘子瑜,表明与徐品花结婚的缘由,并请姑父替其劝慰父亲接受这段婚姻。从信件上看,尽管不能确认周静娟与徐品花是否有爱情之实,但可看出双方走进婚姻殿堂并非简单的“自由恋爱”使然。周静娟因谣言流布,为保全名誉才向徐品花提出结婚的建议。徐初闻此事,以“校长与教员应避嫌疑”为由再三推脱,后在徐家人的劝说下,“方免(勉)强许诺”[2]。可见,周静娟在追求自由婚姻的背后,隐藏着对“名节”的重视。
与周静娟以“自由婚姻”的美名力挽名声的做法相似的是,周钺在供词中亦尽量将女儿“打扮”成“被迫成婚”且“自愧家庭”的“贞女”:周静娟在结婚之前,曾在信件中向父亲保证,“未经请求慈命,不敢造次擅便结婚”。当周钺派人到学校询问时,徐品花将周静娟匿藏起来,直至周钺亲自到校接洽才将周静娟放出。周静娟在回家途中,面对父亲的质问,“哭泣不止,语不成声”,只言结婚实出于徐品花的威逼,“不能自主”,后因深感“无面目回家见祖母、亲族诸人”,故“奔出船舱,投河自尽”[24]。对比周静娟留下的信件,可以看出周钺上述言辞存在多处谬误。其一,周静娟是因谣言而主动请求徐品花结婚,并非被徐品花强迫。其二,周静娟欲通过婚姻事实来消除谣言,与周钺所言的“因结婚愧于家庭”一节相矛盾。其三,周静娟是否为“自尽”一节尚需要考察,但周钺阻止船户的挽救和将女儿痛打致死等行为[3],终究难以摆脱故意“弑女”之嫌。
实际上,周钺将周静娟塑造成“被迫成婚”和“甘愿自尽”的无辜形象有其特别的用意。周钺强调校长与教员成婚有碍学风、有辱家门,流露出对自由婚姻不为苟同。因此,先逼迫周静娟投江,再嫁祸徐品花,最终达到维护周家门楣的目的,则是周钺心中真正的意图。此外,若将周静娟、徐品花以及周钺三者一同分析,则可看出,无论是周、徐自由结婚的出发点,还是周钺弑女诬婿的目的,都难以走出“重视名节”的传统道德伦理。
(二)一步三回头
周静娟在婚姻和父母两者的选择中充满了徘徊与惶恐。周静娟在信件中称,“深知家父严酷”,自感“罪过难逃,故不敢回家。”随后,周静娟在忙碌婚礼的同时,又深怕父母发怒,故恳请姑父“极力劝慰”[2]。当父亲提出重新举办婚礼时,已经完成新式婚礼的周静娟,竟又随同父亲归家准备重新出嫁。在民国初年新旧交替之际,周静娟敢于冲破传统家庭的束缚,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周静娟的内心亦颇感矛盾和纠结:此虽是为挽救名誉而采取的不得已之举,但违背了父命乃是不争的事实。周静娟力求通过姑父的调和,则是为达成婚姻和亲情两不相误的目的。可见,周静娟在迈出自由结婚这一步时,仍禁不住对传统孝道再三回首,这种复杂的心态亦是逐步走进父亲骗局的重要原因。周钺在“弑女诬婿”的精心安排上也凸显在新旧之间的摇摆。周钺将周静娟脱离家庭轨道的张力,严格限制在“接受新式教育”和“外出谋生”的范围之内。周钺未能阻止女儿自由结婚,是碍于法律的规定和江苏省议员的身份,故只能通过逼死女儿的方式来结束周家所蒙受的“羞辱”。随后,周钺面对华亭县检察厅的审问,尝试通过“诬陷徐品花逼女成婚”和“隐瞒棒打周静娟的细节”等方式,试图逃脱法律的制裁[24]。可见,周钺虽对传统女性的禁锢稍有突破,但对“父权为天”和“门楣至上”等传统道德伦理仍难以割舍。
(三)文学形象中的变形
“周钺溺女案”进入公共视野后引起了文学作品的介入,这与民初的文化生态不无关系。《申报》、《新闻报》、《时报》等报刊分别率先开辟了“自由谈”、“庄谐丛录”以及“滑稽余谈”等副刊栏目。此外,“逸史”、“文苑”、“艳史”、“哀史”等文学体裁在《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报刊上频登版面。民初报刊中“谐趣化”的文学现象,不仅为大众文化消费者提供了阅读资源,更为文字工作者以艺术的手法品评时政提供了自由的空间[25]。与司法界着重关注周静娟溺水的地点不同,文学作品在事实的基础上,对周氏的家庭环境、周静娟的求学和处事能力以及周父弑女计划的具体经过等方面进行了加工和重塑。《申报》“自由谈”栏目中的《哀史·周静娟》一文为我们解读周氏父女形象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文本[26]。
为寻觅周静娟悲惨命运的根源,作者将周静娟放置到一个旧式的家庭之中。其一是周钺对女儿外出求学的要求颇为勉强。周静娟有志求学,而周钺屡次“顽固不之许”。后来经亲属的再三劝说,周静娟方获其愿。其二是周静娟在家庭中未有可依靠的对象。生母年衰懦弱,“不敢有所主张”。庶母“悍毒”,与周静娟“为仇”。其三是周钺的横暴让周静娟颇感畏惧。周钺曾经以“嫌疑”之名杀死数婢。周静娟深知直接告知父亲其与徐品花的婚事,势必引起父亲的愤怒,故不得不转而请求姑父从中调和。作者对周家环境的叙述,表明周静娟走出家庭,追寻自由婚姻的艰难,亦暗示了周静娟悲剧的必然性。
在作者笔下,周静娟是一个知书达理、进退有度的大家闺秀。其一,周静娟是接受了新旧教育的才女。其“生而静婉,举止端庄,好读书,过目成诵”,年纪稍长后,文采“斐然可观……初入上海务本女塾,继入竞竞化师范,毕业后又入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复至英租界家公司学习机械缝纫,数阅月而尽得其艺”,后在南州女校“担任国文、历史、体操、缝纫等科目”的教习。其二,周静娟对教育和国家尽心尽责。在教务上,周静娟“悉心教授”,使南州女校“日有起色”,还“兼任近镇之三益、启陈两小学教务,奔走往返,终日,不以为劳”。对于南州女校,周静娟“尤为全身贯注,黎明必先起,庭户几筵躬亲洒扫……及夕料理账目,检点门户,诸事完妥,始就寝,终岁无倦容无矜色”。在对国家的牵挂上,周静娟曾欲“辞职赴沪参加女子北伐队”,在校长和学生的挽留下,又将积蓄的百元捐于北伐队,以表支持之心意。其三,周静娟谦虚随和,处事得当的美德颇受友人的称赞。周静娟“出自富家,而绝无闺阁骄懒习气……勤操作,耐劳苦”,故“乡里咸爱敬之”。在结婚当天,周静娟刚行完礼节,便“脱华服入厨下,指挥仆从,摒挡酒食,娱乐宾客”。对一少年的无礼戏谑,周静娟劝慰徐品花以礼待之。新婚之夜,周静娟将婚床让与七旬的证婚人寝睡,自己“依外房桌上,坐至天明”。作者在阐述悲剧之前,颇费笔墨地对周静娟高尚的品质进行书写,以期与周钺的凶残形成鲜明对比,更让读者为周静娟香魂消陨的命运扼腕叹息。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着重刻画了周静娟随着父亲的阴谋逐渐逼近,心理的变化历程。起先,周静娟从信中误以为父亲对婚事已经首肯,便私自在学校举办婚礼事宜。婚礼之后,周静娟从外办事归来,见“所有衣饰及重要书札”皆被父亲搜去,心里大惊,“初不敢入见”,后在旁人的劝告下,“明知父心叵测”,但仍勉强入见,“趋前鞠躬为礼,不敢仰视”,低声应答。当父亲提出到姑父家商议婚礼时,周静娟或是“战悚不敢声”,或是唯唯诺诺。临行时,周静娟对徐品花“呜咽含泪而别”,且对同伴称,“任凭如何大骂,吾惟忍受而已,决不至于决裂。”作者在前文着力诠释周静娟在校务和婚礼上独当一面的魄力,又于后文描写其对父亲的威严惧怕至甚,使得周静娟作为“新女性,旧道德”的形象跃然纸上。
紧随其后,作者还替周静娟写下了两首古体诗词,聊表周静娟对父亲的怨恨和无奈,以及对丈夫的留恋和悲恸之情。到达姑父家后,周静娟察言观色,“知已中计……恐有不测之变……悲从中来”,望着家中派来的船只,恐难再与丈夫相见,一腔哀愁便悠然而生:
“不见月当头,离人愁更愁。西归空泛棹,东望怕登楼。义重三生石,身轻一叶秋。遥怜同命鸟,江上作孤鸥。”
“惆怅驹光去似驰,百年眷属只旬时。却缘此日分飞早,转悔当初比翼迟。好事翻成千古恨,冤情惟有两心知。瓦金玉碎休相问,忍死须臾莫笑痴。”
在该作品中,周静娟明知父亲的“邀归”不怀好意,仍然走进父亲“弑女”的罗网。在作者笔下,周静娟虽欲与丈夫比翼双飞,但宁愿可怜丈夫将做孤身之鸟,即便怨恨父亲棒打鸳鸯,但亦只能把一片痴心放置在内心深处,或寄托于诗词之中。在父命至上等礼教观念的束缚下,周静娟只能仿古代“殉情”的方式,同时收获对爱情的忠贞和对礼教的遵从。在历史和文学场域,周静娟都是以“死亡”之举对父亲进行控诉,但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将周静娟逐步走向死亡的“无意”改成“无奈”的“再创造”,更突显处于民初新旧之间的周静娟,仍旧难以走出“发乎情,止乎礼”的时代困局。
对于故事中的男主角周钺,作者将其塑造成“惨无人道”的恶父。婚礼过后,周钺携数家人赴南州女校惩办周静娟。周钺在所雇之船上“架新式快枪五杆”,与家人“各怀洋炮,气势汹汹……伏于校外田岸”,等待周静娟“入网”。恰好周静娟外出未归,周家诸人“未遂其计,乃各以洋炮纳之皮夹,入校抄查女士卧室。”待周静娟归后,周钺“顿易其面目,假作和悦状”。在归家途中,周钺“忽嘱舟人返棹,泊长桥口”,指责周静娟所做之事将致周家颜面于何地,且逼迫周静娟在“洋炮”和“江水”两者中“自择死所”。趁周静娟哀鸣之际,周钺竟将女儿挟制至船头,推下水中。对待女儿的尸体,周钺原本催促徐品花前来领取,后在不得已之下,以一口薄棺随意装殓,并弃于荒野的古墓之旁[26]。作者有意将手无寸铁的女儿置于手持威力兵器的父亲手下,以达反衬之效。此外,作者在文中末尾还巧妙地设计了一个环节,展现周钺前后矛盾的行为实是别有用心,即周钺既不承认周静娟与徐品花的婚姻之实,又让徐品花将周静娟的尸体接回徐家,以掩饰自己“弑女”的目的。至此,一个为达自己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凶残且虚伪的文学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在读者面前冉冉浮现。
三、余论:民国初年性别秩序重构中的松动与紧张
若将“周钺溺女案”置于民初女性社会语境中加以考察,可以窥见民国初年性别秩序重构中的复杂生态。
周静娟接受新式教育、自谋生计以及追求自由婚姻等诸多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性别秩序松动的表征。民国初年,女性沐浴着时代的新风,在教育、职业、政治以及婚姻领域崭露头角。关于兴办女学的问题,有倡导者借鉴斯巴达和日本的经验认为,女子教育为国家富强之根本[27]。在此类言论的呼吁下,小学开始允许男女同校,部分中学、师范以及实业学校先后开设了女子教程[28]。在职业选择上,女性从晚清的医学、教育等行业逐渐向商业、银行和政府机关等领域扩散,甚至出现了一批以小说家为职业的女性群体[29]。有论者称,在服务行业中,“女子之和蔼可亲”,可以弥补男子之不足[30]。又如北京中国银行鉴于女员工“心思细密”,且“俸给可低于男子”,最先聘用女司账,成为一时的美谈[31]。在女子参政方面,唐群英、张汉英等“英雌”要求将女子参政权明确列入《临时约法》的举动,引起各界的轰动。赞赏者声称,民国“并非男子一方面独构成立者”,女子亦付出了代价,故对于“国事之赞襄,公民之权利,女子犹不应放弃之”[32]。在婚姻方面,城市中的青年男女甚至是寡妇,通过自由恋爱而结成姻缘的案例频见于报端[33]。女性在自由离婚中“胜诉”亦成为可能。其中,1913年在上海发生的“关瑞麟弃妻案”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关瑞麟在留学期间私自与外国女子结婚,归国后对妻子提出离婚。在妻子陈绚云的控告下,关瑞麟以“重婚”的罪名,被判五等有期徒刑[34]。老年夫妻请求离婚等新闻亦进入了公众的视野[35]。可见,从清末到民初,“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传统伦理观念开始发生动摇,推动着部分女性从家庭走向校园,从校园走向社会。
然而,在性别秩序呈现细微松动表征的背后则是持续的“紧张”。周静娟因自由结婚而死于父亲之手的案例,则是反映女性因迈出家庭而遭遇困境的一个侧面。社会上仍有不少人士对新式女子教育持批判态度。有评论者称,近来女子风气之败坏,是因接触外界“不良之习尚”,且“家庭与学校又不能施以善良之教育”,将导致“新知识不生,旧道德日丧”[36]。因此,时人多有发起回归“贤妻良母”论的倡导[37]。关于女子就业问题,对女店员和女招待的非议亦常耳闻。如有人指责称,酒楼“偏用女招待员数人”,乃是世风日下的反映。
女员工如“一般登徒之辈,如蚁附膻”[38]。关于女子参政问题,由于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馆和沈佩贞大闹《神州日报》馆的风波,“英雌”逐渐广为诟病,并随同女子参政权运动逐渐销声匿迹[39]。在男女关系问题上,除了自由交往广受束缚之外,女性能在自由离婚中真正取胜者实属少数。如上海一对男女因同乘黄包车,被冠以“伤及风化”之名,遭到司法科的查办[40]。又如上海一位女子控告丈夫对其虐待且有外遇等情,请求离婚,但并未获得批准[41]。可见,女性在教育、职业、政治以及婚姻等诸多场域中的受限境况,仍是民初社会的显著特征。
若将视角转向文学领域,尝试把《哀史·周静娟》这一文本置于“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思潮中进行分析,则可发掘在“事件史”以外,其于民初小说史中的意义。
在作者笔下,周静娟是民初“新女性,旧道德”这一形象的典型代表。周静娟在爱情与家庭之间的徘徊,折射出其在新旧伦理之间抉择的艰难。该文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与徐枕亚的《玉梨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徐枕亚以自身的感情经历为本,描述了一位小学教员与寡妇相恋的故事。寡妇既留恋与教员在花前月下的浪漫,又因没能为去世的丈夫“守节”而深感愧疚。这种困惑使得寡妇梨娘只能以死亡来埋葬这段不被世人认可的爱情,并维持其对丈夫的忠贞[42]。在这两部小说中,无论是周静娟对“名声”的维护,以及在其父亲威严面前表现出的“踌躇”,或是寡妇梨娘对“烈女”身份的坚守,皆是对民国初年“情”无法逾越于“礼”这一伦理道德准则的不同诠释。与此相似的是,喻血轮、喻玉铎在《蕙芳日记》和《芸兰日记》中呈现出矛盾的婚恋观念,即既反对自由结合又否定包办婚姻[43],均反映民国初年对“改良礼教”的呼唤。
“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是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基本态度。在他们看来,“发乎情,止乎礼”是恰到好处的爱情观,而对一味追求“自由婚姻”的“自由女”则持保留态度。譬如李定夷在《自由毒》中,描写了一位女子兰秀过分追求自由的悲剧。作者认为,尽管“男也无行女也荡”,但“自由误苍生”是无可置疑。因此,“鸳鸯蝴蝶派”作家笔下的言情小说,尽管批判礼教对爱情的过度束缚,但追求的是在伦理框架内最为圣洁的爱情[44]。周静娟对于爱情追求的“张力”冲破了父亲心中“礼教”的底线,自然沦为时代困局中的牺牲品。
直到“五四”前后,《贞操论》以及“易卜生号”在《新青年》相继推出,社会兴起了对贞操的存废、女性解放等问题的大讨论。易卜生的《娜拉的出走》《玩偶之家》进入中国人的视线后,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倡导男女公开交往以及婚恋自由等的呼声不断拷问着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此外,男女破除旧式婚姻禁锢的尝试逐渐增多起来。大学男女同校逐渐被社会接受,女子参政运动亦再次蓬勃兴起。在文学创作方面,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用细腻的笔法详细描绘了一个春心萌动的少女对一位男青年的红唇强烈的幻想,与《哀史》中的周静娟选择“退却”相比,彰显了“五四”青年在伦理观念上的大胆突破。因此,若将研究的视域放在民初到“五四”之间进行考察,亦可窥见,无论是在历史还是文学场域,周静娟突破传统的限度于“五四”尚有一定的距离。
注释:
①关于周静娟之死的研究成果有《婚姻观念变革不易》,见罗检秋编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105页。该文仅简单描述周静娟溺亡的经过,而关于上海县检察厅和华亭县检察厅对案件审判权的争夺一节,尚未展开讨论。此外,编者未能挖掘当时的文学作品对周氏父女形象的书写,且对该案件所反映的民初社会文化生态亦未作深入剖析。
参考文献:
[1][3]省议员灭绝人道续纪[N].申报,1913-09-14(7).
[2]周静娟之笔证[N].神州日报,1913-09-20(6).
[4]游戏文章·上海春秋[N].申报,1913-12-31(13).
[5]新民演剧社·正剧《周静娟》[N].申报,1913-10-11(9).
[6]重演好戏周静娟[N].申报,1913-10-14(12).
[7]自由谈话会[N].申报,1913-10-12(13).
[8]论周静娟案[N].时报,1913-10-4(8).
[9]讨爷军总司令通告文[N].申报,1913-09-06(13).
[10]张吟俊声明被诬[N].申报,1914-06-21(1).
[11]报告周铁铮逮捕情形[N].申报,1913-09-15(10).
[12]派员迎提议员[N].时事新报,1913-09-30(3/3).
[13]省议员灭绝人道四志[N].申报,1913-09-19(10).
[14]省议员灭绝人道五志[N].申报,1913-09-22(10).
[15]省议员逼女毙命案归沪讯办[N].申报,1913-10-08(10).
[16]溺女案管辖已定[N].新闻报,1913-10-08(3/2).
[17]周铁生尚未提到[N].时报,1913-10-09(7).
[18]逼女毙命案人证尚未解沪[N].申报,1913-10-09(10).
[19]会勘逼女投江案之发生地点[N].时报,1913-11-04(8).
[20]上海厅会勘周静娟死所之复文[N].申报,1913-11-21(10).
[21]华亭厅会勘周静娟死所之复文[N].申报,1913-11-30(10).
[22]周议员案将翻[N].申报,1914-01-18(6).
[23]检察厅之通告[N].时事新报,1913-11-08(3/2).
[24]周静娟投河之疑案[N].神州日报,1913-09-20(6).
[25]杜新艳.论民初报刊谐趣化现象[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2):80-85.
[26]哀史·周静娟[N].申报,1913-10-03(13).
[27]论女子教育之必要[N].顺天时报,1915-07-04(3).
[28]颁行新学制.罗检秋.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29]马勤勤.以“女小说家”为职业——清末民初小说场域性别秩序的松动[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5):50-60.
[30]论设店营业宜用妇女[N].申报,1912-09-28(9).
[31]将有女银行员出现[N].时报,1916-12-20.
[32]女子参政会纪事[N].民立报,1912-09-27(7).
[33]自由结婚[N].时报,1912-09-12(5).
[34]罪状之宣布[J].神州女报,1913(3):83-84.
[35]老夫妻亦求离婚[N].时报,1912-12-02(5).
[36]女界之风气[N].申报,1915-07-04(11).
[37]汤总长之女子教育方针谭[N].申报,1914-06-28(6).
[38]酒馆有女招待出现[N].时报,1913-06-02(9).
[39]高翔宇.事件·文本·社会——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历史事件与文学形象的考察[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04-119.
[40]男女同车[N].新闻报,1913-09-21(3/1).
[41]陈律师被妻控告续志[N].申报,1914-09-26(10).
[42]徐枕亚.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玉梨魂[M].上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43]喻血轮,喻玉铎.蕙芳日记/芸兰日记[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
[44]袁进.鸳鸯蝴蝶派[M].上海:上海书店,1994.
(实习编辑:徐雯婷)
收稿日期:2016-03-06
作者简介:蔡洁(1990-),女,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5;K2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16)03-6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