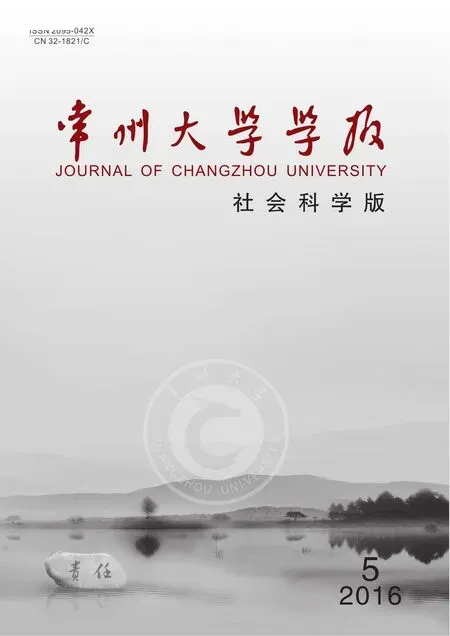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关联性论析
戴辉礼
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关联性论析
戴辉礼
“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既相互区别但又紧密联系。国家自主性理论历经从相对自主性到潜在自主性再到实际自主性的发展变化,侧重强调国家行为逻辑与利益的主体性和超然性。作为国家贯彻自身意志的能力,国家能力既可指国家拥有的基本“潜能”,也包括特定领域的“显能”,更强调的是国家自主行为的资格与条件。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内在关联,不是简单的正相关逻辑。作为都涉及程度差异的解释性变量来说,基础性国家能力是国家自主性的前提与基础,国家自主性对于国家能力有着增强或削弱的双重影响。两者对于分析现代国家建构具有重要价值,但作为需要准确解释的变量,两者的关联性更需以分析归纳法和比较历史分析为主要方法的实证性研究为支撑。
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比较历史分析
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重新回到政治学研究的中心以来,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问题不断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和“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成为政治学的两个重要概念。以西达·斯考切波、彼得·埃文斯等人为代表的回归国家学派从一开始就把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对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对外策略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而开拓出政治学研究新的学术路径和学术空间。但是,由于回归国家学派钟情和采取的是分析归纳法和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策略,因此很少在宏观层面特别明确地阐明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内在关联。此后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在对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关系问题上,或基本沿袭了回归国家学派的取向和态度,或将此作为不言自明的问题,因而也并没有给以明确而细致的回答。显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而伴随着以国家为分析变量的各类比较政治议题研究的深入,在宏观层面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也已成为可能。本文拟以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涵义比较为起点,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一、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涵义辨析
学术界对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内涵都存在不同理解,并且两者的影响因素也确具一致性,有必要仔细辨析两者的涵义。
(一)从相对自主到实际自主:国家自主性的理论演进
国家自主性的提出与对国家的理解紧密相关。在回归国家学派学者看来,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把国家看成一个争夺基本社会经济利益而展开冲突的舞台,因而无法形成国家自主性的观念。而实际上马克思早在分析法国的路易·波拿巴政权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国家自主性现象,一般被认为是国家自主性的理论源头,尽管只是把国家自主性视为特定历史现象。20世纪60年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概念。波朗查斯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了结构性分析,认为“国家对政治上的统治阶级或派别的相对自主性是资本主义形态中各个环节相对自主的反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相对自主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环节出现结构性分离决定的。另一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米利本德则认为国家显然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但是国家要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的话,必须真正拥有高度的自主和独立。国家获得了超越资产阶级特定利益的相对自主性。总体而言,波朗查斯、米利本德等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自主性的分析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概念内涵上,新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国家自主性指的是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及其支持力量的自主性,而不是相对于整个社会的的自主性;第二,在概念涉及的国家范围上,仅把国家自主性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但没有上升到所有类型国家的层面;第三,从自主性程度上讲,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自主性只是相对的而非完全的。也就是说,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有或需要自主性,在根本上是源于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仍是为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服务的。由此可知,新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自主性理论在根本上没有超出工具主义国家观和社会中心论的范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现实解释力。
随着“国家”研究主题的复兴,国家自主性问题得到新诠释。在回归国家学派学者中,斯考切波最早重新解释并定义国家自主性,将其作为解释社会革命的关键理论视角。在斯考切波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查尔斯·蒂利的集体行动理论的共同“错误”和理论缺陷就是,“都没有将国家看成一套具有自主性的结构——这一结构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利益,而不必与社会支配阶级的利益和政体中成员群体的利益等同或融合。”27而新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提出并看到了国家自主性问题,但是他们仅用功能主义方式或从阶级关系和冲突的一个方面来理解国家。斯考切波认为,只有将国家视为具有自主性的制度结构,即“国家是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并或多或少是由执行权威加以良性协调的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30,才能切实理解社会革命与社会转型。作为行政组织和强制组织的国家,在任何地方都具有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和社会势力约束的“潜在自主性”。在解释社会革命问题的基础上,斯考切波进一步指出,国家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控制权的组织,会确立并追求超越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利益之外的目标,只有如此才是真正独立的行为主体。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路径完全不同,斯考切波秉承的显然是马克斯·韦伯开创的“组织”意义上的国家观,即把国家视为在既定的疆域内垄断了暴力使用权的强制性组织。这种韦伯式的国家观用“组织论”取代了“工具论”,国家不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是作为拥有暴力优势的“特殊组织”而存在,而自主性正是这种“特殊组织”的重要特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自我逻辑与利益的国家能够不受统治阶级的支配,更遑论其他社会阶级力量。国家自主性不仅是相对于统治阶级而言的,更是针对整个社会而言的。作为组织的国家都具有“潜在自主性”,自主性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很明显,斯考切波把国家自主性置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分野的大前提下进行分析,更加突出了国家作为自主行为主体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国家才成为解释现实政治问题和社会现象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和视角。基于斯考切波阐述的国家自主性理论,逐渐成为回归国家学派的重要理论基石,进而推动了国家研究的发展。
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家自主性分析的重心又从强调国家之于社会的自主性转到国家究竟如何自主以及自主性程度。诺德林格(Eric A.Nordlinger)针对欧美民主国家的公共政策制定问题,对国家自主性进行非常精细的专门研究。诺德林格认为,单纯强调国家自主性是不够的,国家自主性更不等同于国家能力,重要的是国家是否能实现自主。“将一个国家产生的大量自我偏好视为自主性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除非它能够实践这些偏好。”23对于国家能否实现自主这样的现实性问题分析,必须首先给“国家自主性”确定可操作性的概念。诺德林格从个体的视角把“国家”具体化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以“偏好”为关键词来定义国家自主性,认为“国家在将其自身偏好转换成权威行为的范围以及公共政策服从公共官员资源加权偏好的平行四边形的程度,关系到国家的自主性”17。在诺德林格那里,国家自主性不再是模糊不定的描述性概念,而是可以且必须用来加以解释与分析的变量,民主国家的自主性程度及其类型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之间的关系。回归国家学派另一位学者埃文斯(Peter Evans)在研究国家与经济转型问题时提出了“嵌入性自主”的理论,认为国家制度嵌入于社会,必须实现国家和社会、市场的结合,因此国家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具有完全自主性。与斯考切波有所不同,埃文斯关注的重心是国家自主性的实现条件与程度。乔尔·米格代尔(Joel S.Migedal)更是对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中心主义路径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过于关注国家的自主性而忽视了社会对国家的影响,特别是无视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况,简单地把国家自主性理论直接应用进去,“犯了类似于只关注捕鼠器的设计而不了解老鼠的实际情况的错误”。第三世界国家与社会间复杂的政治博弈使得米格代尔认识到,国家并不能强大到能按自己的意愿渗透和改造社会。因此国家究竟能否自主,取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力量,取决于国家渗透社会的能力,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博弈。基于此,米格代尔进而开创了不同于回归国家学派的、以动态过程为取向的研究路径——“社会中的国家”(State in Society)。在米格代尔那里,国家自主性必须基于对特定国家进行具体动态分析的才有意义。当然回归国家学派实际上并没有忽略国家自主性的程度问题,只是关注的重心有所不同而已。
综上可知,国家自主性的理论实际上历经了从“相对自主性”到“潜在自主性”再到“实际自主性”的发展变化。尽管对国家自主性的内涵理解不尽相同,但回归国家学派所阐述的国家作为自主行为主体却是确定无疑的。不管实际程度如何,国家自主性至少意味着国家作为具有自我逻辑与利益的主体能超然于社会各阶级利益之上行事。
(二)国家能力:“潜能”和“显能”的统一体
国家能力实际上是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从最直观性的角度来看,国家能力很容易与国家实力(state strength)、综合国力相混淆,也容易被理解为“国家权力”。这说明国家能力与上述这些概念之间的确有密切关联。一些国家主义学者在研究中或把国家实力理解为国家相对于社会集团的自主性,或把其理解为国家代表自身进行干预的能力482,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能力涵义的模糊性和争议性。作为特定的政治学概念,国家能力显然有着相对确定的概念范畴。国家权力指的是国家制度所拥有支配力,国家能力重在表征国家权力的实际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权力只是国家能力的基础性条件。国家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含义基本一致,指的是一个国家建立在自然资源、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基础上的总体实力。综合国力的“国家”是“nation”的含义,而国家能力的“国家”相当于英文中的“state”,只能说国家能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和条件。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概念是从国家制度结构意义上而言的。其概念域严格限定在国家(state)的层面,有时候也可称为政府能力。
即使在国家能力的概念域内,其也存在多种不同解释。国家能力实际上一直暗含在国家议题研究中。但是概念的正式出台却是非常晚。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及并研究政府的有效性,强调政治制度的实际效度,但是并没有提出国家能力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回归国家学派的学者最早提出“国家能力”概念并作为研究议题。此后,学者们根据不同的研究取向给出了相应的“国家能力”概念。斯考切波在分析国家自主性时,发现其与国家能力密切相关,因此把国家能力粗略地界定为“国家实施战略与政策的能力”20,但实际上并没有给出更详细定义。很显然斯考切波意义上的国家能力主要指的是国家在特定政策领域的能力。埃文斯(Peter Evans)把国家能力重点理解为国家官僚机器有效干预经济的能力,他对国家能力的界定与其研究国家与经济转型的议题息息相关。乔尔·米格代尔是第一个真正全面研究国家能力的政治学者,他重点把第三世界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把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领导人通过国家的计划、政策和行动来实现其改造社会的目标的能力。很明显米格代尔主要是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理解国家能力的,依此他把第三世界的国家分为“强国家”和“弱国家”两种类型。当国家问题研究在美国正处于热潮时,中国学者王绍光也开始对国家能力进行了研究。王绍光认为国家能力指的是“国家将自身意志(preference)转化为现实的能力”,这种能力用公式表达就是国家能力=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由此可见,王绍光把国家能力当作受国家干预程度与范围影响的变量。很重要的还有,他特别强调国家能力指的是中央政府的能力,而不是泛指公共权威的能力。弗朗西斯·福山把国家能力理解为“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福山的国家能力概念基于区分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强度的基础之上,很明显基本沿袭了王绍光的思路,但他在定义中特别强调了国家的执法能力。黄清吉对国家能力问题进行系统理论阐述,他认为以往的定义都是基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家能力观,而这是不够的,国家能力需要从国家与社会和国际体系中他国相互作用的复合关系中去理解。因此他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从社会积聚资源并将之转化为可资运用的力量,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的整体效能。”此定义的特点在于突出了国家能力作用的领域和整体效能。
从上可知,学术界对于国家能力的有代表性解释各有特点,差异主要源于各自研究取向和目标的不同。实际上,上述关于国家能力的定义并没有在根本上超出回归国家学派的解释范畴。也就是说,上述对国家能力的涵义都基于马克斯·韦伯的组织现实主义的国家观,即都把“国家”理解为垄断了暴力使用权的强制性组织和行政组织。因此,国家能力无非就是国家作为权力组织所拥有的贯彻与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而不论国家能力具体是如何构成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关于国家能力的概念理解实际上不存在根本性差异。国家能力的基本涵义实际上还是比较确定的,但有失全面和完整。笔者认为全面准确界定国家能力的涵义,必须综合考虑下几个因素。一是国家能力具有客观性。因此作为重要概念来说,它是可以用来分析甚至是需要精确量化的变量。二是国家能力实际上涉及基本能力和实际效能两个方面。具备基本的国家能力和国家能力范围内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两个不同层面问题,即“潜能”和“显能”两个层面。三是国家能力既可以指整体性效能,也可以指特定领域的国家能力,即单项国家能力。四是从载体来说,国家能力主要指的是特定政治体系体现出来的制度能力。综合上述要素,在既有的概念理解基础上,更为全面地看,国家能力指的是作为权力制度结构的国家贯彻实现自身意志与目标的基本能力及实际效度。在政治学意义上使用的“国家能力”概念,实际上涵盖了国家拥有的基本“潜能”和国家实施特定目标的“显能”两个方面,是两者的统一体。
从国家能力的涵义可知,国家能力不仅取决于国家本身,还取决于国家权力所作用的客体——“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社会”统称)。因此国家能力的强弱从根本上讲是受到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中诸多因素的影响。大体而言,国家能力的强弱与国家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是否优化成正相关,而与社会性约束成负关联,即国家能力=国家结构和制度安排/社会性约束。与国家能力类似,国家自主性的实际程度也与国家、社会、国际环境等层面因素密切关联。正如回归国家学派所认为的,“国家究竟是否自主,取决于国家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和跨国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给定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等因素所组成综合形势。”483
综上可知,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是相互区别但又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或问题。从基本内涵上看,国家自主性更侧重于强调国家的利益超然性和行为主体性,而国家能力更强调的是国家自主行为的资格与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能力是国家自主性的基础。但是两者又都涉及到各自的程度差异,都是可用来解释的变量,在评估与影响因素上存在相似性,由此需要对其动态关联进行分析。
二、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辩证关联
厘清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既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也不能陷入简单的对应性逻辑,应基于辩证分析。
(一)基础性国家能力是国家自主性的根本前提
国家要成为自主行为主体,实现自身的目标,就必须具备最基本的前提性条件。这些前提性条件就是国家能力的体现。但如上面提到的,国家能力存在着“潜能”和“显能”之分。在笔者看来,“潜能”主要指国家的基础性能力,“显能”特指国家实现特定目标的能力及效度。在回归国家学派那里,国家能力并不是对国家总体性实力的代称,而特指的是追求特定政策的能力,或者说是实现特定目标的能力。“没有理由事先假定(一个国家)在所有政策领域都是同样的强势和软弱。一个国家或许没有能力改变其医疗体系结构,但或许却能够建造一个高效的交通网络。”“国家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不同领域的能力并不相等。”478特定政策领域的能力恰恰是最需要深入研究的对象。但尽管如此,任何特定政策领域的能力的前提无疑是基础性国家能力。没有基础性国家能力,特定政策领域的国家能力根本无从谈起。特定政策领域的能力并不是判断国家是否具有自主性的依据。也就是说,国家在特定政策领域的能力并不是国家自主性的基础。判断国家在总体上是否具有自主性的依据是国家的基础性能力,而特定政策领域的能力仅仅是衡量国家自主性程度的一个重要变量而已。因此准确地讲,只有基础性国家能力才是国家自主性的根本性前提。或者说国家的基础能力是国家具有潜在自主性的必备条件。
国家对暴力使用的合法垄断使得国家具有自主性的潜在可能,基于暴力的强制性能力无疑是国家能力之基础。但国家强制性能力只是国家自主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国家自主性的获得,还需要国家能够有效地渗入社会以获得认同,继而取得支撑国家统治的所需资源。因此,提取资源的能力和渗入社会的能力无疑是国家的基础性能力。任何能力归根到底体现在作为个体的人的行为上,国家自主行为主体主要是政治体系中的官员,因而各级各类官员的素质也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能力。由此可见,国家强制性能力、提取资源能力、渗入社会能力、官僚素质构成国家最为基本的能力,是实施任何特定政策领域能力之能力。正如斯考切波所言,“主权完整(sovereign integrity)与国家对特定领土的稳定的行政-军事控制,是一切执行政策之国家能力的前提条件。除此以外,忠诚且有技能的官员与丰富的财政资源是国家有效追求各类目标的基础。”21具备上述基础性国家能力意味着国家能够提出并实现与社会集团乃至统治阶级不一致的目标成为可能,也使得国家具备与他国展开竞争的资格。无论是国家强制性能力还是提取资源能力,无论是渗入社会能力还是官僚素质,都是国家基本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的绩效体现。基础性国家能力本质上是制度能力。以此来看,国家的暴力制度、财政制度、行政体制和官僚体制以及合法化制度,是国家自主性实现的制度基础。
(二)国家自主性对国家能力的双重影响
国家自主性对国家能力具有重要影响,但并非体现为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即国家自主性程度高,国家能力就强,反之亦反。实际上,国家自主性对于国家能力有着增强或削弱的双重影响。
首先,国家自主行为的二重性导致其增强或削弱国家能力。从国家自主性内涵可知,国家具有自我逻辑和利益,能超然于社会各阶级利益之上行事。但是,国家超然于社会利益的自我逻辑具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超越社会阶级和集团的特殊利益而代表社会普遍利益,另一种是理性地按照官僚机构和国家官员的自我利益行事。这就是国家自主行为的二重性。就第一种情形来说,国家能够代表全社会的普遍利益(或说公共利益),能克服形形色色的社会阶级和集团的特殊的、狭隘的利益甚至是支配阶级的利益羁绊,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地地行事。国家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代理人面貌出现,处理公共利益与特殊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从而达到维护与实现国家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意味着国家对社会利益进行最大限度的整合,国家的目标与社会普遍利益实现了重合。正因为如此,国家行为在根本上能得到社会最大程度的支持,国家自主性行为获得了更大的合法性,从而国家能力增强。从国家存在理由这个最低限度来说,国家代表社会公共利益行事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国家完全代表社会公共利益行事,意味着把国家当作公正无私的完美行为体,显然这是超理性的解释。国家即使不是完全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虚幻共同体”,但无疑具有自我利益。用理性选择主义理论来讲,那就是国家不是想像的存在,是由现实中的理性个体——国家官员——组成的,理性的官员又构成各种官僚部门和机构。所以第二种情形就是国家表面上代表公共利益,但有时候所谓按公共利益行事只不过是冠冕堂皇的自我说辞而已,而实际上是利用公共权力来服务官僚部门和官员自身的利益,形成部门利益和官员私利,公共理性变成了自利理性。这样一来,国家自主性蜕变为部门自主和官员自主,国家设定的目标由于官僚机构和国家官员的“理性经济人化”而导致难以实现。在现实政治中,由于公共利益部门化、公共利益私人化的障碍,使得社会公共利益无法实现是广泛存在的,形成所谓“中梗阻”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权力被官僚部门和国家官员俘获,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国家能力。国家行为具有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面,但同时又避免不了私利化,正是这种矛盾性造成对国家能力的双重影响。
其次,国家自主性程度差异影响国家能力的强弱状态。基于暴力优势和组织优势的国家,只是意味着国家具有自主性的可能,而“它们在实际上所具有的自主性的程度,以及所产生的实际影响,都因具体的场景而异”30。国家源于社会,并与社会保持距离,但国家并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国家作为“特殊组织”,要保证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稳定和提供公共服务,需要与社会持续互动,两者之间要保持必要的张力与平衡。因此,国家之于社会的自主性,都必须维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不能无限扩大。国家自主性限定在能够保持和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平衡,那么国家能力与社会力量之间就能相互提升,呈现出“强国家—强社会”的良性状态。国家自主性程度过高或过低,实际上都会削弱国家能力。一方面,如果国家自主性程度过高,超过必要的限度,国家权力就可能沦为任性的专制性权力。正如迈克尔·曼认为的,国家权力包括两个层面的权力: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和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专制权力指的是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专制性权力如果不受限制,任意地侵入市民社会空间,侵犯公民权利和掠夺社会资源,就会严重丧失合法性。因为合法性意味着认同,而认同的基本途径是民主。“民主的程序实质上是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沟通、协商的过程,它能使被统治者增强对国家的认同,从而增强服从国家法律的可能性。”失去了合法性的专制性权力,无法得到社会力量的认同,或者说国家自我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无法重合,因而无法有效渗入社会,无法转化为基础性权力,致使国家确定的任何目标都很难实现,国家能力的实际效度就十分低下。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性程度过高,也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活动范围过大。国家活动范围与国家能力不同。国家活动范围主要指的是政府所承担的各种职能和追求的目标。国家活动范围越大并不意味着国家能力越强。相反,国家活动范围与国家能力之间呈反向关系。因为国家活动范围越大,国家追求的目标越多,意味着国家承担的职能越多,国家职能的扩大必然使财政的压力不断扩大,到最后,由于财政的不可持续导致国家能力的削弱。欧洲福利国家的困境就是很好的证明。相反,国家活动范围有必要的限度,社会自主空间就扩大,国家能够集中力量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责,特定政策领域的国家能力就越强。按照迈克尔·曼的观点,专制性权力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导致国家活动范围任意扩大,挤压市民社会活动空间,导致合法性降低,进而增加国家贯彻其政治决策的成本。因此,从历史或现实中的国家政权形态来看,传统的专制主义国家、全能主义国家(totalitarian state)由于国家权力不受制约或者活动范围的过大,恰恰导致其国家的基础性能力和特定政策领域能力都羸弱不堪。现代国家建立在社会分殊的基础之上,国家职能必定是有限的。当国家自主性超出必要的限度,意味着现代国家已经发生变异。反过来说如果国家自主性程度过低,一方面表明国家的基础性能力很弱,无法将潜在的国家自主性转化为现实的自主性;另一面意味着国家在与支配阶级、其他社会力量的博弈中处于下风,要么沦为支配阶级的工具,要么被其他社会力量俘获,由此实际上失去了推行政策并最终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
三、余论与启示
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和命题,将两者简单地划上等号有悖于基本逻辑。两者区别明显,但又存在相互紧密且较复杂的联系,以至于两者的关系很容易被忽视。厘清两者的区别与关联,可以更好地认识国家特别是现代国家的特征、重要作用及复杂性,对于深化国家问题研究及比较政治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些许启示。首先,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都是分析现代国家建构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构建强有力的现代国家,是国家的基本追求,强大的国家能力是实现良好国家治理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实现善治的重要体现,更是国家在国际上维持生存空间的必要条件。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国家自主性既是其基本特征也是必然要求。从动态的角度讲,国家自主性程度实际上表征的是国家之于社会的状态。从根本上讲,自主性基于强大的基础性国家能力。但两者都需要通过制度建构来获得。因此,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虽有区别,但都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题中应有之意。对于很多还处在现代国家建构路上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建设尤为关键。其次,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都存在程度差异,都是需要被解释的变量。两者的具体程度实际上都需要进行比较准确的测量。正因为如此,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这两个概念适用性也常常受到质疑。因此,虽可以从宏观整体层面谈论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具体、微观的研究。正因为都是变量,所以细致比较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实际上也存在一定困难。第三,分析归纳法和比较历史分析是研究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主要策略和方法。正因为两者都是变量,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显得尤为关键,所以归纳法而非演绎法是其基本的研究方法。要研究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或者详细分析特定国家的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动态关系,具体而细致的比较历史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两者都具有特定的时空性。就此来说,回归国家学派学者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对于运用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来深化比较政治研究,分析归纳法和比较历史分析必不可少。
[1]杨光斌.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47.
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王宏洲,马清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87.
米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9.
EVANS Peter B. Br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埃里克A 诺德林格.民主国家的自主性.孙荣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乔尔 S 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5(前言).
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方力维,莫宜端,黄琪轩,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
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北京:三联书店,2007:5.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7.
黄清吉.论国家能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25-26.
KRASNER Stephan,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58.
MANN Michael.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Oxford:Blackwell,1988:5-9.
李强.宪政自由主义与国家构建//公共论丛: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北京:三联书店,2003:40.
法治评估专题研究(栏目主持人:李瑜青)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本刊以“法治评估”为主题刊发四篇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文章。通过对余杭法治指数的表达与余杭法治实践相互关系的分析,《法治评估实践的效度》一文认为,余杭法治评估在效度存在事实与宣传的背离,评估技术不完善、评估缺乏有效接纳是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针对实践中各级法院在创新社会管理方面呈现的模仿性与随意性趋势,《我国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的司法法治逻辑考量》一文认为,有必要明确将司法职业责任伦理作为我国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的理性考量,通过遵循法治建构的逻辑来保障创新社会管理功能的实现。对宪法基本概况、宪法权利及宪法义务等知识的掌握情况开展的调查显示,东部地区和华南地区虽然在经济上具有优势但并没有显现出应有的法治优势。《地域差异与公民宪法意识》一文认为,有必要对先发地区法治优先的判断加以检验。《论法治评估的立场与类型》一文对法治评估的类型及特点展开了研究,将法治评估区分为国家视角、社会立场及专家视阈三种类型,三者的侧重点分别为法治目标实现状况、社会利益表达及法治理念的落实。
An Analysis of the Relevance between State Autonomy and State Capacity
Dai Huili
“State autonomy” is different from “state capacity”, but they are closely linked. The theory of state autonomy which emphasizes on the subjectivity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logic and interests of state behavior has experienced changes from relative autonomy to latent autonomy to practical autonomy. As the country's ability to carry out its own will, the state capacity can refer to both the basic “potential” owned by the state and the “obvious energy” of a particular field, it emphasizes more on the qualifica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e state's autonomous behavior.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utonomy and state capacity is not a simple positive correlation logic. As an explanatory variable that involves varying degrees of difference, basic state capacity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basis of state autonomy, and state autonomy has a double effect on the strengthening or weakening of state capacity. Both of which are of great value for the analysis of modern state construction. But as the variables that need to be explained accurately, the relevance of the two is more supported by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methods of analytic induction and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state autonomy; state capacity;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戴辉礼,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科社(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政党体制与国家能力的关联性研究:以东亚国家为例”(2014M561395)。
D03
A
10.3969/j.issn.2095-042X.2016.05.004
2016-07-08;责任编辑:朱世龙,沈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