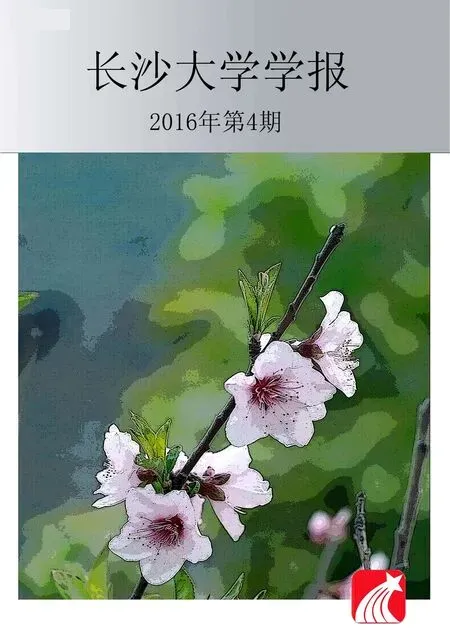行动、探究与知识
——论杜威对传统知识论的改造
蒋晓东(长沙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湖南 长沙410022)
行动、探究与知识
——论杜威对传统知识论的改造
蒋晓东
(长沙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湖南长沙410022)
传统知识论哲学是一种“知识的旁观者理论”,认识主体是独立于认识对象之外的旁观者,形成了静观求知的倾向和特征,以及对于绝对知识的崇拜和追求,这种知识论根源于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杜威以探究行动为中心,利用现代实验科学的方法和成果,对传统知识论哲学进行了批判与改造:放弃对于独立自在的静观知识的追求,真正的知识必须与实践活动和实用目的相联系;放弃寻求绝对确定性的形而上学知识体系,在实验探究行动中实现知识的创新与发展;放弃“划分知行界线”的形而上学传统,知识和行动事实上总是融合在一起的。
知识论;探究行动;实验主义
知识论问题是传统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学说称之为‘传统知识论’”[1]。变革传统知识论是杜威哲学改造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杜威哲学直面人的现实生活,以科学探究行动为中心,从知识的本质、知识的形成与发展、知识与行动的关系等方面对传统知识论哲学进行了批判与改造。
一 从静观的知识转向实用的知识
从本质上来说,传统知识论是一种既成性思维方式,知识的对象是外在于人的预先存在,知识的正确与否在于是否与预先存在的实在相符合。杜威指出,在传统知识论哲学中,关于认识问题的理论派别繁多,“唯心论者”与“实在论者”围绕着认识问题展开了激烈地争论。但所有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认为“被知的东西是先在于观察和探究的心理工作而存在的,而且它们完全不受这些动作的影响”[2]。在传统知识论哲学看来,认识过程中,作为认识者的主体只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认知者与“被知的对象”不发生任何“交互作用”,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是相互分离的。因此,在追求知识时,认识者所能够采取的最根本途径就是静观,从而形成了静观求知的倾向和传统。杜威把这种静观求知的知识论称之为“知识的旁观者理论”(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
杜威指出,“知识的旁观者理论”源于传统哲学认识论上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二元对立;作为认识对象的终极实在与实际生活的二元划分。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将作为知识对象的实在一分为二:终极实在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总是变化的、不稳定的、不完全的,而真正的实在是不变的、稳定的、完全的。与实在的两种不同领域的划分相对应,传统哲学也划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并且知识的正确程度与认识对象的“完全”或者“完满”程度也是相对应的。在传统哲学中,知识被划分为“完全意义的知识”(或“真正的知识”)与“意见”(或“信仰”)两种基本类型。“完全意义的知识”是“指证的、必然的——即确切的”,具有必然和不变的形式。“意见是与变化世界联系着的”[3],具有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实在’愈高而愈近于完全,则关于它的知识亦愈真愈重要”,“事物愈接近于绝无运动的境地,则知识愈明显,愈确实,而愈圆满——纯粹无夹杂的真理”[4]。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传统的观点,一些现代哲学家甚至断言,哲学的知识是比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更高一级的知识。在他们看来,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原始的、永恒的和自足的“实在”,因此哲学知识是“完全意义的知识”。尽管关于实际生活与日常事物也产生了一些平常的知识,但是由于日常生活充满着变化,是不完满的,因此,关于实用的事物的知识也是有缺陷的,不完满的,称不上真正的知识。
在杜威看来,传统知识论哲学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坚持静观求知,把真正的知识与实践活动和实用目的分离开来。因此,必须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来改造传统知识论。杜威指出,从根本上来说,“知识乃是通过操作把一个有问题的情境改变成为一个解决了问题的情境的结果”[5]。这也就是说,知识产生于一定的有问题的情境,是通过操作和行动改变有问题情境的结果。“如果观念、意义、概念、学说和体系,对于一定环境的主动的改造,或对于某种特殊的困苦和纷扰的排除确是一种工具般的东西,它们的效能和价值就全系于它们工作的成功与否。如果它们成功了,它们就是可靠、健全、有效、好的、真的。”[6]也就是说,如果某些概念、理论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有问题的境遇,那么它们就是真正的知识。在这里,杜威把知识看作是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反对形而上学的为求知而求知,强调求知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真正的知识应该与人的实用的目的相联系,一切真正的知识都是“实用”的结果。因此,“就一种深刻的意义来讲,知识已不是静观的,而成了实用的”[7]。
在知识的本质上,杜威反对“旁观者”的知识论,主张以行动中的现实主体取代传统认识论中静观的抽象主体,以行动及其效果来界说知识的本质:知识不是对于先在实在的被动反映,而是人们通过操作和行动改变有问题的情境的“实用”的结果。在知识论上,实现从传统既成论思维方式向现代生成论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
二 从绝对的知识转向探究的知识
在杜威看来,人生活的世界总是充满危险、充满着不确定性。“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8]。人们寻求安全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感情和观念上改变自我的方法”,与决定着他们的命运的各种力量进行和解,即改变自我而屈从环境;另一种是“通过行动改变世界的方法”,通过技术手段等利用自然的力量构建一座安全的堡垒,即改变环境以满足人的需要。
在杜威看来,传统知识论哲学对于绝对知识的崇拜和追求,与人们寻求安全的第一种途径如出一辙。从传统哲学对于知识的两种类型的规定来看,只有对于固定不变的事物的知识才能够帮助人们寻求到确定性,那种关于变化事物的推测和意见恰恰是危险的根源。杜威指出,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哲学就开始倾向于把知识的本质看作是对于绝对不变的实在的“唯一有效的领悟或见识”,“知识显然地和绝对地意味着脱离变化,转向不变”[9]。在近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哲学接受了近代科学的一些新的结论,但另一方面仍然保留着传统思想的一些要素:“只有在固定不变的东西中才能找到确定性、安全性”,而“知识是达到内在稳定确切的东西的唯一道路”[10]。这种绝对主义的知识观,在观念上一定程度地满足了人们在认识上寻求绝对确定性的需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并不能真正帮助人们应对这个充满风险的世界;在知识教育方面,知识只能当作“稳定的、完整的实在之确切表象”而被动接受。无论从理论方面来看,还是从实践方面来看,这种绝对主义的知识论既不利于知识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知识教育的开展。因此,杜威主张必须以现代实验科学的方法和成果来改造传统知识论。
杜威指出,随着实验科学方法的兴起,知识的目的“不在于界说常住不变的对象,而在于发现变化之间的恒常关系”[11],知识所涉及的不是终极的“高级的境界”,而是要探索“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的生活世界是如此充满着不确定性,而人的思维、知识正是源于这种不确定的境遇。“思维起源于恰如其分地称为叉路的境遇,这是一种不确定的进退维谷的境遇……只有处于这种不稳定中,我们才会遐想高瞻,去寻找观察新事实、获得对境遇的指导思想的立场”[12]。如果这种思想或者观念能够指导我们开始行动、进行探索,并且能够从这种“不确定的进退维谷的境遇”中摆脱出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那么,相对于这一特殊的境遇而言,这一行动就是成功的实践,这种思想或者观念就是真正的知识。否则,便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但是,一旦离开这一具体的境遇,这种知识又只能作为人们探究行动之前的假设而存在。在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看来,一切知识都不是绝对不变的,“知识不是某种孤立自足的东西,而是在生命的维持和进化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东西”[13]。杜威在这里指出,真正的知识不是对某种绝对不变的自足的实在的符合,一切真正的知识都不是认识的顶点,而只是探究行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总是面向未来的,并不断发展的。在人们应对环境的探究行动中,假设不断地被证实,知识不断被纠错,不断帮助人们解决生活的困难与问题,以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在这里,杜威对绝对主义的直观符合论进行了批判和改造,强调知识是在探究行动中对外在情境和主体需要的动态符合。但是由于片面地强调知识与个体行动和特殊情境的符合,否定了作为普遍原理的知识的存在,从而割裂了知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反对绝对主义的过程中又具有相对主义的倾向。在杜威的晚期著作中,他更倾向于用“被确保的断言性”(warranted assertability)一词来代替传统认识论哲学中的“知识”或“真理”概念。
三 从知行二分转向知行合一
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全部知识论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发展的历程中,一直存在着重理论思辨而轻实践行动的思想倾向和特征。亚里士多德将人类行为划分为创制、实践和理论三种基本方式。其中,理论活动以自身为目的,与人的闲暇相关联,是人类最高形式的活动;创制等物质生产活动往往与奴隶们的生产劳动相关联,是令人不愉快的活动,因而也是最低贱的活动形式。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截然二分。杜威指出,在传统形而上学体系中,“知识的领域和实践动作的领域彼此是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14]。唯理论与经验论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各执一端,争论不休。康德、黑格尔等著名西方哲学家,采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试图将两者统一起来,但都不自觉地陷入到理论哲学的窠穴,因此,这种统一工作总是收效甚微。
杜威哲学以行动为中心,批判了传统哲学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从现代科学出发对传统知行观进行改造。杜威指出,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更是一个现实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它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也是人生中最实际的问题。”[15]因此,杜威哲学从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出发,动态地考察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按照实验主义哲学的观点,知识起源于“不确定的进退维谷的”“有问题的境遇”,改变“有问题的境遇”必须依赖于人的探究行动。杜威指出,尽管探究行动是实验性的,具有风险性,但探究行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盲目的行动”,而是在一定的思想或者观念指导下的“明智的行动”。因此,在具体的境遇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生活中的行动问题,或者说就是“盲目的行动”和“理智的行动”的关系问题。杜威以“医生应诊病人”的探究行动为例阐述了“盲目的行动”和“理智的行动”的关系。病人作为医生认识的经验材料摆在医生面前,医生对病人进行了一系列的临床观察和手续。这些观察和手续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只有在医生所掌握的系统的医学知识的解释之下才是有意义的。”[16]这也就是说,杂乱无章的“盲目的行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有意义的“明智的行动”依赖于知识和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脱离了具体行动和造作的理论是空洞无用的”[17],脱离了理论指导的行动同样没有意义。因此,“只要人们认为知识的职能就是去掌握存在于探究操作及其后果之先,独立于探究操作及其后果之外的存在物”[18],那么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从现代实验科学研究的程序和发展来看,“认知过程已经事实上完全废弃了这种划分知行界线的传统”[19]。概而言之,在现实生活中,行动总是贯穿于人的认识过程的始终,作为人们应对有问题情境的一种手段,知识与行动总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并没有什么实际区别。
杜威哲学突破了传统理论哲学的局限,强调必须在现实生活动态地考察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阐释了知识与行动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融合。但是,在反对知行二分的过程中,由于片面地强调知识与行动的融合,否认了分别对两者的本质加以认识和区别的可能,从而否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异质性,体现了杜威哲学的反本质主义倾向。
[1]俞吾金.从传统知识论到生存实践论[J].文史哲,2004,(2).
[2][3][5][8][9][10][11][14][15][16][17][18][19]杜威.确定性的寻求[M].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6][7]杜威.哲学的改造[M].许崇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12]John Dewey.How we think[M].Lexington,Mass:D.C.Heath& CO,1910.
[13]John Dewey.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A].Jo Ann Boydston. 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Volume12)[C].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6.
(责任编校:作者本人校对)
Action,Exploration and Knowledge
JIANG Xiaodo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otical Theory Course,Changsha University,Changsha Hunan 410022,China)
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knowledge,the subject of learning is considered as a spectator of the object of learning,which is rooted in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John Dewey focused on explorative action,and modified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by using the method and result of modern experiment science.He insisted that real knowledge should be related to practice and practical aims,the metaphysical knowledge system should be abandoned,and knowledge is always integrated with action.
theory of konwledge;explorative action;experimentalism
B023.2
A
1008-4681(2016)04-0078-04
2016-06-0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实践哲学新诠释:马克思实践观与杜威行动观之多维比较研究”,编号:13YJC720019;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编号:13C1088。
蒋晓东(1977—),男,湖南邵阳人,长沙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实践哲学、文化哲学。
——访陈嘉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