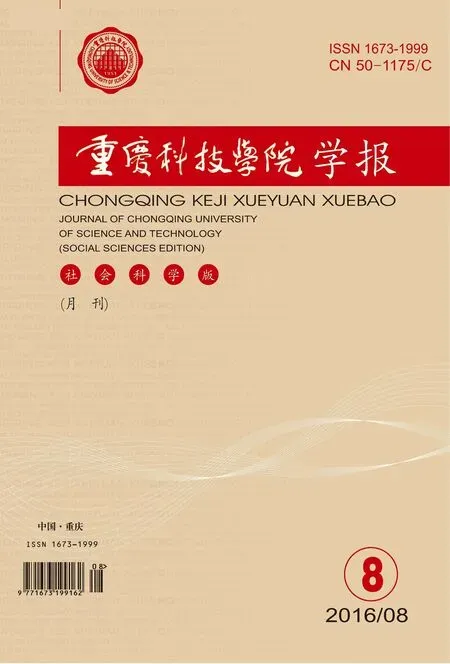马克思的“跨越设想”与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王兴华,严建新
马克思的“跨越设想”与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王兴华,严建新
马克思在1881年3月所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提出了一条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发展道路。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但不具有普适性。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过程,都与马克思的“跨越设想”没有直接关系,不宜把马克思针对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而提出的“跨越设想”拿来比照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社会形态;俄国“农村公社”;“卡夫丁峡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研究东方社会时,晚年的马克思特别注意到了俄国的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条件。1881年3月,他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提出了一条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发展道路。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三大改造”,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最近30余年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就是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学者们对此见解各异。我们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考察分析马克思提出“跨越设想”的历史背景和“跨越设想”的内涵,以及中国选择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
一、学界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的“跨越设想”。目前,这个问题仍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否跨越了“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一)“已经跨越”说
一般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指的是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基于这样的理解,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已完全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当前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仍然不够发达,生产资料所有制也非单一的公有制,但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存在任何争议。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既不同于还未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渡时期”,也不同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发达社会主义,更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1],而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建立的“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2]。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已经标志着“跨越”的终结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3]。现阶段我们的生产力水平的确还不够发达,但不能因为生产力水平不够发达而否认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4]。
(二)“仍在跨越”说
一些学者认为,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是紧密关联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认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完全跨越了“卡夫丁峡谷”。高级的社会形态并不等于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只有当建成了马克思所描述的有着先进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才算是完全跨越了“卡夫丁峡谷”[5]。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虽说是已实现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成有先进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过程[6]。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相结合的经济形态是市场经济,因而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实际上也包括跨越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7]。邓小平说过,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所谓“不够格”,就是指我们现实的生产力没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所要求的“资格”[8]。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易发挥生产潜力,也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与资本主义国家有较大差距,经济发展阶段并未超越资本主义。在曾经超前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生产关系实践失败后,还需将生产关系“向后调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框架内引入市场经济,鼓励非公经济的发展,允许多种分配制度并存,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些表明,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只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第一步,而非“已经跨越”。
(三)“无关跨越”说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背景与马克思“跨越设想”涉及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的“跨越设想”没有直接关联。“一切都取决于所处的历史环境”[9]765。马克思当时是依据俄国“农村公社”普遍存在的土地公有制而提出“跨越设想”的,对于其他并不存在土地公有制的民族国家如印度和中国,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不具有普适性[10]。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选择。况且,中国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只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远未完全实现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的“跨越设想”不直接相关,也就不存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11]。张亮亮通过对相关文本的互文性解读,认为“卡夫丁峡谷”指的是土地私有化和农民无产者化的过程,但20世纪初俄国的“农村公社”已完全解体,“跨越”的主体不复存在,马克思的“跨越设想”与之后的俄国社会主义实践也没有任何关系[12]。按照张亮亮的判据,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自然也和马克思的“跨越设想”没关系。
上述3种“跨越”说虽然都是从文本出发,但观点却有明显的差异。我们认为,判定中国究竟是否是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不仅需要分析马克思文本中的“跨越设想”的历史背景和实现条件,也需要分析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背景和实践过程。
二、“跨越设想”的历史背景与条件
(一)马克思“跨越设想”的最初指向
19世纪中后期,世界革命形势发生逆转。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调整使得激化的矛盾有所缓和,西方的革命热情日渐消退,而俄国却出现了革命信号。在马克思看来,俄国是欧洲唯一的在全国大范围内保存“农村公社”的国家,而且“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9]765,它天然的优势使它有可能走一条与西方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单纯从它可能延续的时间来看,在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9]767
针对俄国当时国内有关社会(村社)发展前途的争论,马克思反对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做法。他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9]340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俄国继续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它必将会摧毁原有的公有制村社转而发展私有制(资本主义),从而会遭受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灾难。从公有转而发展私有,这无疑是“辜负”了村社的“天然优势”。
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草稿里指出:村社的土地公有使小农个体耕种有可能逐步直接地变为集体耕种,它与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9]765。由此,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马克思认为,与俄国“农村公社”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为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因而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9]769。
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是直接针对当时的俄国广泛地存在公有制形式的 “农村公社”的情况而提出来的,他反复强调了“农村公社”在俄国“全国范围内广泛地保存下来了”的重要性。按照他的设想,保存下来的村社公有制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战胜私有制,从而跨越“卡夫丁峡谷”而获得新生。这是“跨越设想”的最初指向。
(二)马克思提出的实现“跨越”的条件
根据俄国当时特殊的社会现实条件,马克思提出了“跨越设想”,同时他也为该设想的实现附加了一系列条件。如果说马克思反复强调的俄国保存的“农村公社”使跨越“卡夫丁峡谷”存在可能,且俄国可以通过吸收利用同时代存在的“较高文明”,使俄国具备了“跨越”的前提的话,那么,实现“跨越”的具体条件就至少包括:(1)“农村公社”继续存在,且具有与资本主义私有化倾向较量的优势;(2)俄国革命必须与欧洲革命互补互助。
实现“跨越”的第一个条件是针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实际状况而言的。“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则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9]775。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虽是公有制,集体耕种,但它是原始农业公社遗留下来的,与共产主义中的公有制并非一回事,它还需要在引导中“进化”。俄国作为欧洲唯一的大范围保留“农村公社”的国家,它处于欧洲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大环境之中。自1861年起,沙皇政府的农奴制改革使“农村公社”不断遭受破坏、瓦解,工业化改革也使得俄国国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何把已有的有利因素集中起来,使农村公社继续存在,且“变为俄国社会的新生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将直接关系到“跨越”的能否实现。
对于第二个实现条件,马克思在为俄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中有明确的表述,即:“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度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3]在资本主义制度大环境中,俄国“农村公社”的继续存在必须有俄国革命的支持,然而,单凭俄国一己之力,情形则不容乐观。也就是说,如果只有俄国发生革命而西方却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俄国就不能真正吸收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从而最终失去“跨越”的可能。俄国的革命需要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呼应与推动,同时,俄国的革命也有助于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俄国的社会发展能否因为“农村公社”的存在而实现“跨越”,需要内部因素与外部力量的共同作用,缺一不可。
考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历程则会发现,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才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整个民主革命期间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都是在反抗有着“同时代较高文明”的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与颠覆企图。中国顽强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既没有像俄国那样的土地公有制的 “农村公社”基础,也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呼应与推动,完全不具备马克思提出的实现“跨越”的条件。
三、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背景
(一)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与过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都为救亡图存进行了一系列尝试,然而并未成功。直到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率领下才逐步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
1949年以前的中国为封建土地私有制背景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双重性质”社会(不包括解放区和实行农奴制的局部地区),外国列强轮番侵略,人民努力救亡图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却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在“洋务运动”与一战期间。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是客观存在的,并有所发展,直至新中国“三大改造”的完成。这意味着封建土地私有制背景下“发展不足”的资本主义,是中国实现“跨越”的起点。而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跨越设想”提出的依据,还是实现“跨越设想”的条件,都是指向以原始的土地公有制形式为起点,利用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公共所有制形式。在起点上,中国的“跨越”与马克思所说的“跨越”有着明显的不同。
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来看,中国是分两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内在地涵盖了两个阶段的革命运动,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但是,无论是在哪一个阶段,中国都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马克思所设想的“东西方革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局面,在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并未出现。不仅如此,新中国也未能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以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为前提实现“跨越”;相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在政治、经济上制裁、封锁新中国。可见,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过程与马克思设想的“跨越”过程也是完全不同的。
(二)中国的指导理论与发展生产力的途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都不是在马克思“跨越设想”的指导下完成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列宁“一国胜利论”思想的成功实践,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从开始照搬俄国的经验到后来明白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的道理,经历了一个极其艰难而教训深刻的探索过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了中国自己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新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非暴力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马克思的 “跨越设想”并未涉及与中国类似的情形。
马克思所设想的不通过“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13],其中的“共产主义”只是个美好而笼统的目标。公共占有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形式,它的真正实现还必须有先进生产力的跟进与巩固。除了提及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文明成果这一外部因素,对于俄国完成“跨越”后如何发展先进的生产力的问题,马克思没有进行阐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从自己的国情出发,经过曲折的探索,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途径,是中国共产党摸着中国国情的“石头”探索出来的,而不是在马克思“跨越设想”的指导下探索出来的。
四、结语
无论是从马克思提出“跨越设想”的历史背景来看,抑或是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选择与马克思的“跨越设想”都是没有直接关联的。“跨越设想”是马克思针对特定历史条件下俄国的村社发展前途而提出的设想,它本身不具有普适性。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基于中国不同时期和阶段的社会历史条件,实事求是地探索出来的,是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与马克思在“跨越设想”中所勾画的道路不具有同质性。因此,不宜把马克思针对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而提出的“跨越设想”拿来比照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人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14]。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领导人民作出的选择。当然,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也有启发意义,那就是我们应该主动吸收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1]张广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卡夫丁峡谷”[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3(1).
[2]张凌云.从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J].探索与争鸣,2013(3).
[3]陈康华,黄志高.“跨越”的终结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J].池州师专学报,2000(4).
[4]陈静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跨越”理论难题的破解[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5]马拥军.从“跨越”阶段到“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东方语境[J].江西社会科学,2005(3).
[6]高中华,姚倩.关于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新思考[J].江苏社会科学,2011(4).
[7]王增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越了什么:基于对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再认识[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
[8]张赛群,汤兆云.是社会制度的逾越,抑或是生产关系的逾越:马克思“卡夫丁峡谷设想”新解[J].科学社会主义,2012(5).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竟辉,王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三重超越性[J].求实,2016(5).
[11]段忠桥.对我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再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1).
[12]张亮亮.论“卡夫丁峡谷”隐喻的本义和转义:一种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互文性解读 [J].社会主义研究,2014(5).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1.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
(编辑:米盛)
D61
A
1673-1999(2016)08-0004-04
王兴华(1992-),女,广西大学(广西南宁530004)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严建新(1964-),男,博士,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科学社会主义。
2016-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