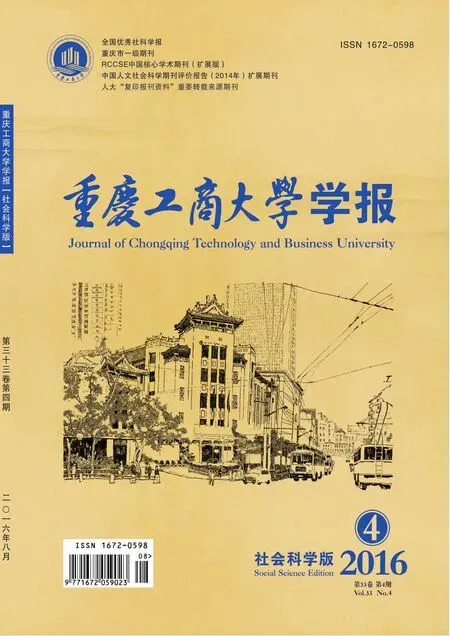“宏大叙事”的解构
——新写实小说的审美特征*
高颖君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宏大叙事”的解构
——新写实小说的审美特征*
高颖君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要:新写实小说对“宏大叙事”的基石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进行了解构,它从大写的英雄转向小写的凡人,从形而上的精神、理想,转向形而下的世俗、生活,将为宏大叙事所否定、批判、与“远大的目标”“伟岸的英雄”完全无关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放在了文本结构的中心位置上,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琐屑平庸、缺乏诗意的人生图景,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这在对宏大叙事主导下精神至上的写作立场进行反思、批判,为文学开拓更广阔的叙事空间之同时,也消解了在文本中建构精神、理想,表达形而上、超越性思考的可能。
关键词:新写实小说;宏大叙事;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解构
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寻根、先锋小说风行一时,但因为寻根小说过于注重对历史、文化的抽象思考,与现实生活相隔膜、疏离,而先锋小说沉迷于叙述方法、语言技巧的把玩,把文学变成了故弄玄虚的智力游戏,所以日渐远离读者、归于沉寂,整个文坛一片萧索之象。此时,刘恒的《狗日的粮食》(1986)、池莉的《烦恼人生》(1987)、方方的《风景》(1987)等作品,以迥异于寻根、先锋的姿态现身文坛,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的注意。《钟山》杂志又于1989年第3期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栏目,对这一文学潮流进行了倡导,于是在文坛上掀起了一股创作热潮,涌现出了一大批标榜“新写实”的小说。对新写实小说有推介之功的《钟山》杂志立场鲜明地将其归于“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不少批评家也认为它是对先锋派现代主义的反拨和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可实际上它所表现出来的不为宏大叙事作注脚,叙述平面化、日常化的审美特征,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有很大区别,而与后现代、解构主义的精神品格相契合。
美国学者弗·杰姆逊认为,文化形态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现实主义产生、繁荣于国家资本主义时期,现代主义萌芽、发展于垄断资本或帝国主义时期,后现代主义则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产物,而“在第三世界……便是三种不同时代并存或交叉的时代,文化具有不同的发展层次。”[1]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即是如此,尽管那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尚不发达,仍属于前工业化时代,但社会文化却表现出了一种“不同时代”文化“并存或交叉”的特征,在某些地区和领域已经具备了后现代文化生长的土壤。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市场经济在中国迅速蔓延、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结构,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它以日常生活的世俗性导引人们的思想行为,拒绝国家权力、知识精英主导的宏大话语,奉行一种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文化观念。这使社会的价值观念、意义系统发生了巨大转型,国家权力、知识精英从中心滑向边缘位置,市场法则、消费文化则成了社会普遍意识,而以追求精神、建构理想为目标的宏大叙事,则在消解精神走向物质,摒弃理想走向现实的市场经济浪潮中土崩瓦解,一种批判逻各斯、元叙事的解构文化开始流行。新写实小说正是在这一历史情境下产生的,它顺应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氛围,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
二
弗朗索瓦·利奥塔德认为,“元叙事”的核心源于黑格尔思辨哲学与法国革命这两套追求本真和自由解放的“宏大叙事”,而“伟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险情,壮阔的航程及其远大的目标”[2]是宏大叙事的基本构成要素。在中国文学宏大叙事的文本中,“伟岸的英雄”与“远大的目标”,即英雄和理想,也占据着中心位置。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追求神圣崇高的理想,挖掘形而下生活之外的形而上本质,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文学中有充分体现。而到了八十年代末,社会、文化发生巨大转型,正如金元浦所言,人们“不再关注政治历史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主题,而只关心生活和身边的‘小型叙事’”[3]。在这一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中,英雄、理想等与宏大叙事相关的范畴都被放逐或悬置,取而代之的则是消费、生活等“小型叙事”。与此相应,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新写实小说,也表现出了一种解构宏大叙事的冲动。小说中没有高大伟岸的英雄,也没有恢宏浪漫的理想,而只有一度为宏大叙事所否定、批判,与“远大的目标”“伟岸的英雄”完全无关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宏大叙事的基石——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被解构了。
卡莱尔曾将历史描述为英雄的业绩:“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4]近现代以来,“英雄”更是成了中国主流文化的基石之一,无论是为了民族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战争,还是为了新中国建设而开展的火热“战斗”,都是英雄文化滋生的土壤。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到社会主义改造、文化革命、新时期拨乱反正,都在召唤一个时代的英雄。在文学中,英雄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塑造社会主义英雄人物是文学的中心任务。无论是王老虎、周大勇(《保卫延安》),江姐、许云峰(《红岩》),少剑波、杨子荣(《林海雪原》)等革命战争英雄,还是梁生宝(《创业史》)、萧长春(《艳阳天》)、刘雨生(《山乡巨变》)等革命建设英雄,都以时代中心任务为己任,并将个人理想融于宏大的社会理想之中,为这一理想的实现而奋斗、牺牲,这种英雄主义包含着巨大的道德内涵。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一个“再叙事”的过程,作家们在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中,对英雄、理想等宏大话语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心理,在创作时总是力图摆脱五十至七十年代“宏大叙事”的文本模式,建构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但由于历史惯性作用,英雄并未退出文学的视野,而是在一些局部、特殊的题材领域中得到了沿承。朱苏进的《射天狼》、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等军事题材小说,仍以塑造英雄为主要特征,但却将英雄从超人的“神性”拉回世俗的“凡性”,表现出了一种解构宏大话语的冲动。这些英雄不再是五十至七十年代经过宏大叙事过滤、筛选,被人为地神化、净化的高大英雄,而是有着种种思想弱点和人格缺陷、带着更多人情、人性色彩的普通凡人。他们之所以成为英雄并非政治规训,而是人性中最宝贵的部分——道德良知自然延伸的结果。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新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改革小说,也塑造了一系列改革英雄的形象,他们以大刀阔斧的气魄,锐意进取的精神投身于时代大潮中,承载起国家、社会所赋予的使命,身上散发出一种强烈的英雄主义气质。这两类小说都在集体与个人、“大我”与“小我”的冲突和选择中,通过肯定、弘扬集体和“大我”,否定、牺牲个人和“小我”来成就一种英雄主义,这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的英雄主义并无不同。一种新质的英雄主义是伴随知青小说的出现而诞生的,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孔捷生的《南方的岸》、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知青小说的主人公,在摆脱时代“旧梦”走向人生“新岸”的过程中,逐渐从伤痕小说感伤、愤怒的情绪中走出来,重新燃起了一炬英雄主义之火。与传统的英雄主义不同,这种英雄主义包含着一种深刻的理性反思意味,及对自我实现关注、肯定的个性主义特征。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现代派小说的主人公是以与英雄文化决裂的面目出现的,他们的文化个性、精神特征不仅与梁生宝、林道静等这些在“人民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集体主义英雄不同,也与易杰、陈信等知青小说中有强烈反思精神的个人主义英雄有别,其“英雄主义”正表现在对英雄传统的否弃和对自我个性的坚守上。在此,英雄主义已经失去了丰富的社会、道德内涵和往昔的崇高、悲壮感,而成了离经叛道、标新立异的代名词,这预示着一种文化上的开端,一种去社会化、非建构性的解构文化开始流行。但现代派小说并未成势,真正摆开阵势、目标明确地对“英雄”进行解构的是王朔。他笔下的顽主们以一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狂妄姿态,将矛戈直接掷向了文学殿堂中的英雄。他们在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引导下,明火执仗地干着反道德、反文明,嘲笑理想、蔑视英雄的勾当。他们的“英雄气”不仅没有理想主义的烛照,还失去了道德正义的支撑,而那些真正的“英雄”则蜷缩于文本的边缘地带,成了一群被时代遗忘的多余人。
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似乎是一个宣言,宣告了英雄时代的终结。英雄的缺席是新写实小说的典型特征之一,占据其文本中心的不再是伟岸的英雄,而是一度被宏大叙事所压抑、遗忘的普通人,他们从根本上就与英雄的美感形态相背离:没有凌云的壮志和宏伟的目标,没有崇高的精神和神圣的理想,而是与芸芸众生和光同尘、共此炎凉,在世俗生活中与世进退、随时俯仰。他们在异己的力量与环境面前并未表现出超越、抗争的主体姿态,而是采取了一种妥协、认同甚至以恶抗恶的消极态度。他们不但没有英雄精神和性格中神圣、崇高的色彩,甚至失去了传统文学中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所应具有的思想情感、个性特征,成了抽象空洞的能指符号。池莉《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并不具备完整的人的精神内涵,而只是被世俗生活所日渐压倒、改造的一种生存状态的象征符号,正如作者池莉所言,他所代表的是“整个工人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工人”[5]。刘震云的新写实作品所着意展示的也是一种人的生存状态,而小林、元首等小说中的人物,只是作为特定生存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而方方笔下的七哥、小六子等人物,也是缺乏明确的生命、精神内涵,甚至连名字都不配拥有的抽象能指符号。他们也没有宏大叙事文本中英雄的文化个性、精神特征,印加厚(《烦恼人生》)在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子、为人师的“网”状生活中焦头烂额、整日奔波,不堪重负又不得不勉力支撑;三哥、七哥(《风景》)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摸爬滚打、心机费尽、投机钻营;小林(《一地鸡毛》)在机关的人事纠葛与家里的鸡毛蒜皮中啼笑愁苦、疲于应对。这些挣扎在平庸琐碎、沉重无奈的世俗生活中的小人物,在新写实小说中是以群体形象出场的,他们“更能代表时代的总量”,但却不再是大写的“英雄”,而只是小写的“凡人”。这一文学形象类型的转换,喻示着英雄时代的终结。
三
宏大叙事的另一向度是理想主义,表现为对世俗生活的超越和对精神理想的追求。在理想主义的视域中,世俗生活是一种生命的否定力量,唯有超越世俗生活,追求精神理想,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这在八十年代文学,尤其是张承志、史铁生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张承志的小说中包含着物质、世俗与精神、理想两种话语的冲突,前者被表现为一种非人性、非理想的存在,如嘈杂喧嚣的都市、琐碎平淡的日常生活等,后者则以草原、大坂、黄泥小屋、金牧场等带着浓厚的精神超越、理想象征色彩的意象呈现出来。精神、信仰是其小说的中心话语,超越世俗生活、寻找理想天国是其小说的基本主题,这正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表征。而史铁生小说的主人公多是有身体缺陷的残疾人,有终日在群山中为衣食而奔走的瞎眼说书人(《命若琴弦》),也有在太阳底下拼命摇动轮椅朝着希望之所行进的球迷(《足球》);有拖着跛腿走遍整个城市的寻鸽人(《山顶上的传说》),也有被时代抛掷到生命荒滩的下乡知青(《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尽管身体的缺憾阻碍了世俗幸福的实现,使他们认识到了生命的脆弱、渺小,但博大的精神世界和独立的生活追求又使他们不懈地与世俗生活相抗争,并最终实现了精神的升华和超越,这同样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表征。虽然张承志、史铁生超越世俗生活的方式不同,精神资源、文化背景也有别,但理想主义是其作品共同的底蕴。到了八十年代末,理想主义受到了全面的质疑和否弃,世俗主义成了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这在新写实小说中得到了体现。
新写实小说将对彼岸理想的追求还原为对此岸人生的凝眸。它对生活没有浪漫的想象,生活只是生活而已,没有金戈铁马的浩然正气,也没有荡气回肠的生死别离,有的只是一些司空见惯、散漫凌乱的日常生活琐事:恋爱、结婚,经济的拮据、住房的拥挤,气候的寒凉、菜价的上涨,夫妻间的争吵口角、婆媳间的鸡毛蒜皮……即便走出家庭这一空间领域,它所关注的也多是一些烦冗琐屑、枝蔓丛结的日常生活事件:上班、下班,打瞌睡、磨洋工,奖金的多寡、职位的竞聘,同事间的吃醋争风、领导间的明争暗斗……被宏大叙事所摒弃的日常生活被放在了文本结构的中心位置上,理想主义在这琐屑平庸、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叙事中毫无立身之地。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即以“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6]为叙事中心,对主人公小林在生活中所遇到的细小真切的烦恼作了细致呈现:夫妻间的争吵,单位里的怄气,为老师找医院看病却相助无力,为妻子调动工作送礼却碰壁被拒,为孩子入托寻找门路而四处奔波,为给幼儿园老师送礼而跑遍全城、买高价炭火……弥漫于小林生活世界中的都是一件件平凡无奇、琐屑至极,却又相当具体、不容规避的日常生活事件,这些未脱离基本生存需求的日常生活琐事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让他整日地奔波劳碌、费心伤神,使他捉襟见肘、疲于应对。他也曾有过宏图大志,可几年下来,这个朝气蓬勃、满怀理想的大学生在现实生活的磨折下,变成了一个“淹没到黑鸦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7]184的庸人,而他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被无奈的现实所击碎。他最终从生活中得到了这样的启示:“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有宏图大志怎么了?有事业理想怎么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7]184他对简单却又强大的生活逻辑也有了清醒的认识:“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7]230这是一个被生活默无声息地改造的过程,一个从崇高、理想向世故、平庸“还俗”的过程,一个向庸人的价值观念、人生信条一步步地妥协的过程。与李铁梅、林道静等成长型的英雄相比,小林在精神上经历了一个反成长的过程。到了最后,他觉得“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7]233这时的小林已经能对世俗生活泰然处之甚至甘之如饴,完全失去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勇气,成了一个被生活裹挟着前行的精神意义上的小人物。小说末尾,小林“半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年如日。”[7]232-233这一梦境是颇具象征意味的,生活就像一地鸡毛一般浩繁无边、琐碎凌乱,它是磨损理想、销蚀信念的无物之阵,可将高山夷为平地,会使英雄变成俗人。刘震云在《磨损与丧失》中说过:“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6]这代表了新写实作家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整体感受,可他们在反映这一生存状态时,并未表现出超越世俗生活、追求精神理想的努力,而是在理想与现实二元对立的价值选择中,站在了后者一方而对前者进行了解构。
八十年代文学中的爱情书写,表现出了一种共通的建构理想之爱的精神意向。在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主人公钟雨把爱情作为与庸俗婚姻相对照的至高理想来追求,她对爱情的信仰和坚守,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黄蓓佳的《请与我同行》、张辛欣的《最后的停泊地》等作品,也表现出了一种将爱情神圣化、理想化的倾向,反复倾诉着理想爱情不可得的痛苦和缺憾,并在追悔中对相濡以沫的爱情浅斟低唱。而新写实小说在对爱情进行书写时,既没有浪漫诗意的怀想,也没有执著坚守的信念,而是表现出了一种去理想化的解构姿态。它与宏大叙事文本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其叙事的终点并非不言自明的理想对现实的征服和改造,而是相反,现实的强大逻辑不断地改造人物,修正理想,使之进入世俗生活的轨道,如《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懒得离婚》《太阳出世》等。在池莉的《烦恼人生》中,主人公印家厚也有过对理想爱情的向往,他渴望与初恋情人相结合,有时甚至觉得找个情人也不错,可真正当让他有些心动,有“一张喷香而且年轻的脸”[8]48,“笑得很美,脸蛋和太阳一样”[8]48,在他看来是比自己老婆要“高出一个层次的女性”[8]49。徒弟雅丽对他表达了爱慕之情后,他却拒绝了诱惑,坚定地站在了那个“烫了鸡窝般发式”“憔悴的脸上雾一样灰暗”[8]35,却每天迎送他上班的老婆一边,且很快认同了这一选择:“老婆就是老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8]58,并以一种承认现实的态度来看待夫妻之间的关系:“少年的梦总是带着浓厚的理想色彩,一进入成年便无形中被瓦解了……他只是十分明智地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靠劳动拿工资而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入非非呢?”[8]58“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尽管做丈夫的不无遗憾,可那又怎么样呢?”[8]76在理想的“梦”与现实的“网”的冲突中,他有过挣扎和渴望、微喟与忧伤,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对爱情的浪漫幻想和理想追求,认同了现实生活的逻辑和原则,以一种淡泊的心态去企盼一份平实的感情。作者池莉对此也持肯定的态度,她为印家厚的选择做了这样的解说:“现实是无情的,它不允许一个人带有过多的幻想色彩。常常是这样:理想还未形成就被现实所替代。”[9]
池莉的《不谈爱情》也存在理想与现实二元对立的文本结构。小说一开篇便是庄建非与妻子吉玲的争吵,之后他走出家门,在夜晚独坐反思,开始追忆昔日的恋情。他想起了三年前与梅莹交往时的点滴:开会偶遇,互通姓名,共进晚餐……这些回忆在与平淡枯燥的婚姻生活的对照下,闪现出了一种浪漫、理想的色彩。这一追忆是以质疑不满现实、回望爱情理想为发端的,可他所不满的现实也同样是以理想爱情为起点的,于是又带出了一段美好回忆:大学校园樱花树下与吉玲的美丽相遇,冲破重重家庭阻力的恋爱结合,这一切都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无奈的现实击碎了他对爱情的浪漫幻想,使他认识到自己的婚姻结合,并非因为爱情,而是缘于充满世俗意味的欲望。他为此而苦恼,可后来又想通了:谈得完的是爱情,过不完的是日子,爱情、婚姻不过是过日子而已,不必追求什么浪漫,奢谈什么理想。于是,他最终打破了空幻的爱情寓言,服从于“不谈爱情”这一质朴的真理,带着一份并不完满的婚姻和已然破碎的爱情沉入现实人生,成功地度过了婚姻危机,完成了对现实的认同。
在市场经济时代,人们被生存现实所左右,为当下利益所驱遣,昔日感世伤时、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沉湎于形而上的精神思考,对理想的彼岸充满追寻的渴望。相反,精神消解了,理想远去了,对精英意识的反思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新写实小说即打破了附着于现实生活之上的诗意幻想,颠覆了知识分子自我设定的历史主体性,还原了与精英理想相对立的芸芸众生的生存本相,如《单位》《行云流水》《烦恼人生》等。《烦恼人生》展示了知识分子印家厚身处平民生活实境与精英理想梦境冲突之中的精神困境。小说以生活流的叙述方式再现了他一天中所遇到的种种烦恼:孩子半夜摔醒,老婆埋怨,排队洗脸,厕所满员,上班迟到,奖金分配不公,午饭里有青虫……他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人生现实,生活像一场沉重的苦役,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他在应对这一现实时又表现出了个人的卑微性,当儿子半夜摔醒时,他惊慌、内疚,还受到老婆的鄙薄、埋怨:“是男子汉,要老婆儿子,就该有个地方养老婆儿子!窝囊巴叽的,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算什么男人!”[8]31可他只能心酸地呆坐一旁无言以对。上厕所、排队洗漱时,面对邻居的责骂、哂笑,他也没有还嘴的勇气。当在车间得知久盼的奖金落空时,别人敢于不平则鸣他却不敢吱声。他不甘于这种卑微的处境,无比怀念过去的精英理想,可当他用精英的标尺来衡量现实时,却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个体生存的卑微性与精英理想的虚幻性。在这种困境下,他常以“梦”中的幻想来弥补现实的缺憾,这样的梦在小说中出现了六次。第一次在睡梦中他被儿子摔落床下的声音惊醒,这是一个笼罩全篇的隐喻式象征:精英之梦会遭到现实的无情拆解;第二次在睡回笼觉时他做了一个关于家庭的梦,但醒来后却忘了,这喻示了精英之梦如朝露轻尘一般,是模糊而易逝的;第三次在轮渡上他脱口和了一首与北岛《生活》同题的一字诗,正文即“梦”,博得了在场文学爱好者的齐声叫好。从中他仿佛确证了自己的精英地位,满足了一种精英对大众的精神优越感,一时间竟幻想出了一个人人平等的乌托邦,还“哈哈笑了,甩出一个脆极的响指”[8]40,觉得“生活中原本充满了希望和信心”[8]40。可这只是自欺欺人的白日梦,他很快就发现了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路边吃饭担心儿子回家告状,到幼儿园不得不向阿姨赔笑脸、进车间时讨好考勤员仍被记迟到。于是,“只过去了四个钟头,印家厚的自信就完全被自卑代替了[8]47”;第四次朋友来信提到女知青伙伴聂玲,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他“靠着一棵树坐下,面朝太阳,合上眼睛;透过眼皮,他看见了五彩斑斓的光和树叶”[8]57,“少年的梦”翩然浮现,这使他从恶劣的情绪中解脱出来,“自信心又陡然增强了好多倍”[8]59;第五次他在回家的轮渡上沉入梦乡,被女疯子“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了”[8]69的喊叫惊醒,发现梦的情节已经全忘,只剩下了一种难言的苦涩与辛酸;第六次他晚上睡前想起早上所做的诗,就对自己说:“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梦,你在做一个很长的梦,醒来之后其实一切都不是这样的。”[8]76在小说中理想之梦与现实的失败交织穿插,对比性地呈现了印家厚卑微的生存状态及其精英理想的虚幻性质。世俗生活像一张严密的大网,每个人都被固定在一定的网眼中,既不能冲破也无力挣脱,而只有认同它、顺从它,在它的规约之下挣扎、生活、行动。即便是像印家厚这样的知识精英,也被这生活之网束缚得不能动弹、无力喘息,被这烦恼人生折腾得焦头烂额、身心俱疲。他渴望超越世俗生活,热切追求精英理想,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他认识到,这不过是水月镜花,一场空梦。只有放弃脱离现实的精英理想,适应普通平民的世俗生活,才能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在业余作家四与小市民猫子价值观的交锋中,表现了追求人文立场、坚持精英理想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中所遭遇的尴尬和无奈,四成了一个备受冷落、嘲笑的多余人,而以猫子为代表的小市民则在世俗生活中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在《一地鸡毛》中,小林当年的大学同学“小李白”,如今得风气之先成了鸭店老板,从一个诗的虔诚信徒变成了暴发户。当小林问及他是否仍在写诗时,他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以一种大彻大悟的口吻开导小林道:“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蛋!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7]220“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7]220”在此,“小李白”对诗的嘲讽和调侃,是对精英理想的拒绝和否弃。在现实与理想、平民与精英、物质生存与诗性生存两种价值观的交锋中,前者才是胜利者。这与八十年代文学中对知识精英的书写有很大不同,如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尽管经历着与印家厚无异的“烦恼人生”:沉重的家庭负担、困顿的物质生活与超负荷运转的工作,但她却并未跌落到世俗生活的罗网之中,而是坚持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以坚韧的意志去寻求超越、坚守理想。
新写实小说对“宏大叙事”的基石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进行了解构,它从大写的英雄转向小写的凡人,从形而上的精神、理想转向形而下的世俗、生活,将为宏大叙事所否定、批判,与“远大的目标”“伟岸的英雄”完全无关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放在了文本结构的中心位置上,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琐屑平庸、缺乏诗意的人生图景,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这在对宏大叙事主导下精神至上的写作立场进行反思、批判,为文学开拓更广阔的叙事空间之同时,也消解了在文本中建构精神、理想,表达形而上、超越性思考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6.
[2]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6.
[3] 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J].文艺研究,1994(5).
[4] 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1.
[5] 丁永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J].小说评论,1991(3).
[6] 刘震云.磨损与丧失[J].中篇小说选刊,1991(2).
[7] 刘震云.一地鸡毛[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8] 池莉.池莉小说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9] 池莉.我写《烦恼人生》[J].小说选刊,1988(2).
(责任编校:杨睿)
Interpretation of “Macro-narration”——On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New Realism Novels
GAO Ying-jun
(ChineseDepartment,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New realism novels interpret the cornerstone heroism and idealism with “macro-narration”, from massive description of the heroes to simple description of layman, from metaphysical spirit and ideal to vulgar life, deny and criticize the events with macro-narration, put daily life and everyman without “ambitious objective” and “great heroes” on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he text structure, demonstrate the life picture with mediocre image without poetic meaning and express a kind of post-modernism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This narration recollects and criticizes the writing mode with metaphysical hero description, opens the more extensive space for literature and cancels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 and ideal in texts and transcendence in expression forms.
Key words:new realism novel; macro-narration; idealism; heroism; interpretation
doi:10.3969/j.issn.1672- 0598.2016.04.014
[收稿日期]2016-12-14
[作者简介]高颖君(1983—),女,河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 0598(2016)04- 0096-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