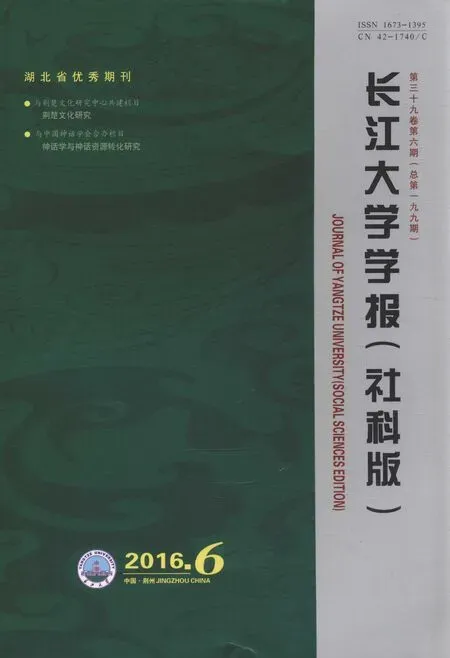畸形繁荣中的民国清吟小班
陈思琦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畸形繁荣中的民国清吟小班
陈思琦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民国时期,北京娼妓业分别于1912—1927年间、1938—1945年间,迎来了两次畸形繁荣。当时娼妓业中的头等群体清吟小班,也在两次畸形繁荣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小班妓女服务对象的改变、妓女整体素质的降低、服务项目的减少以及妓女生活水平的下降等方面。作为社会底层娼妓业代表的清吟小班妓女,其生活与社会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
关键词:民国;北京;清吟小班;繁荣
清末,北京的高级妓院被称为清吟小班。民国陈莲痕有云:“京师教坊约分四等,上者为小班……考小班名始于清光绪中叶,斯时歌郎像姑之风甚炽,朝士大夫均以狎妓为耻,而内城口袋底胡同处,均有蓄歌妓者,名曰小班,以与外城歌郎剧院某班略示区别。……至于今日,则于小班之上冠以‘清吟’二字。揆其意,若以地位身价,高于侪辈。清吟鬻艺,非专作夜度娘博缠头歌资者。”[1](P283~284)由此可见,其之所以在小班之上添加“清吟”二字,是为了凸显其高级妓女的身份,以别于娼妓集团中的其他等级。而名妓张文钧则指出,“清吟”二字是为点明小班妓女的来源地:“北京从清末到解放,一等妓院‘小班’一直是苏帮垄断,自称苏州人。‘清吟’是因其妓女大都来自苏杭一带……在警察局公开承认妓女是一种‘营业’以后,苏帮的妓院称为清吟小班,也表示以卖唱为主。”[2](P334)由此可见,民国前,清吟小班妓女与艺妓类似,卖唱卖艺而不卖身。民国建立后,中国各地的娼妓业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期。据美国社会学家甘博1917年对世界八大城市的公娼数目统计,公娼中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是上海,其次是北京。本文即以当时“公私娼寮几遍”的北京为背景,探讨清吟小班在1912—1927年和1938—1945年间两次畸形繁荣的原因,及其在畸形繁荣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一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全国娼妓业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北京清吟小班妓女人数,随着娼妓业整体的繁荣而不断上升。1912—1917年间,清吟小班头等妓女人数依次由635人、721人、744人、760人、729人上升为781人,其总计人数则依次由3096人、3184人、3300人、3491人、3500人上升为3889人。[3](P297~298)清吟小班的繁荣,究其原因,大略有三。其一,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1933年,北京男女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6:100,至1936年时,北京男女出生人口性别比已高达160.18:100。[4](P1355)由此反向推测,1912—1927年间,北京男女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应该偏高。人口结构比例失衡,致使聚集在城市的男性的正常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娼妓业的发展。其二,经济的落后。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党派之间竞争激烈。作为当时政治中心的北京,恰恰处于政权之争的核心地带。政权的频繁变更,使北京政府无心关注自身经济建设。此一时期,相比上海、汉口、广州等港口城市,北京的经济发展一直较慢,市场能为人们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这一现状,切断了处于贫困之中的文化水平较低的广大女性成为女工的谋生道路。加之政局动荡所导致的大众的彷徨无助,以及旧社会“笑贫不笑娼”的愚昧心理,也间接将处于贫穷与饥饿之中的女性推向了青楼。其三,民国政府狎妓之风的盛行。袁世凯当政时期,政府官员和富商经常出入于妓院之中。据名妓张文钧回忆:“袁世凯政府,从国务总理以下都是妓院的座上客……政界、银行界上层的衮衮诸公天天都在妓院摆酒请客,把妓院当作他们的交际场所,有些人甚至把妓院当作他们的办公厅,会客谈公事都在妓院。国会的议员们,从各地来到北京,纸醉金迷,天天逛窑子,住夜。”[5]北洋政府时期,清吟小班成了社会上层人物重要的社交平台。
清吟小班的繁荣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1928年南京政府建立后,北京丧失了政治中心地位,大量政界人物离开北京南下。因丧失了最为主要的客源,清吟小班妓女人数遂大幅度下降。1928年清吟小班妓女人数为445人,1929年则跌至328人,1930年则维持在324人左右。[1](P318)[3](P297~298)这一数字,尚不到1917年清吟小班妓女人数的一半。
二
“日寇侵入华北的第二年,北京的情况在表面上稍趋稳定,供给日寇发泄性欲的娼寮妓院也就生意兴隆。”[2](P381)1938年北京有妓院250家,1942年增至263家,1944—1945年则达460家之多。[6](P298)此一时期,有关清吟小班的具体人数虽无文献记载,但从北京妓院数量的整体增长,以及张文钧的相关回忆(“满春楼、环翠阁、群芳班、潇湘馆……都相继复业,家家门口还安上霓虹灯,留声机里放送的是日本流行歌曲”[2](P377))中,我们依然能够推测出,在这一时期,清吟小班迎来了第二次的畸形繁荣。
自1937年始,北京周边地区不断受到日寇骚扰,自然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大量农村年轻女性不得不投奔城市(北京)寻求生计,但在日寇的物资统制下,适宜女性工作的纺织、制革等“多数工厂停了产,仅皮毛倒闭者就不下百十家,一些手工业作坊,如食品、铁工、针织等作坊,亦多数停产”[7],年轻貌美的女性,或因求职艰难或因生活所迫或受金钱诱惑而进入清吟小班。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清吟小班的第二次畸形繁荣。
从北洋政府时期开始,全国各地虽都开展过禁娼运动,但娼妓业可观的妓捐收入,使禁娼运动大都成效不大。1937年,北京进入日伪统治时期。日伪政府一反先前国民政府的做派,大力扶植北京娼妓产业,甚至对妓院实行特殊保护。这一政策,直接为日伪政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缓解了日寇在华北地区资金紧张的局面。而“日本鬼子主要是利用妓院维持它市面的繁荣,让妓院作为他们‘慰劳’炮灰的工具,同时还可以麻醉许多中国人的抗日思想,让他们醉生梦死,昏天黑地腐烂下去”[2](P394)。于是,八大胡同便成为北京城“温柔旖旎的地带”[8]。日伪政府接管北京后,北京局面趋于稳定。在日伪政策对北京娼妓业的默许和保护下,清吟小班不仅重新找回了北京沦陷初期一度丢失的商界客源,而且有大批的日本人成为其新的客源。此外,北京娼妓业的繁荣,必然促使妓院老板不断扩大妓院规模,或与他人合开高级妓院,如名妓张文钧的母亲便在1938年与掌班阿春在百顺胡同合开了一家鸣凤院。需求的刺激与老鸨的趋利心态,是清吟小班在北京沦陷期走向畸形繁荣的另一重要原因。
三
1912—1927年间,由于北京特殊的政治位置,清吟小班成为北洋政府的政治活动场所,其所服务的对象,亦由晚清的士大夫和附庸风雅之人,转为军阀与北洋政府官员。到1938—1945年间,在日伪政权的统治下,清吟小班所服务的对象,又从北洋政府军政大员一变而为日本人、汉奸与战争投机商人。随着服务对象的变化,清吟小班妓女的艺技水平不断下降。清吟小班妓女逐渐从以卖艺为主的艺妓,彻底沦为单纯操皮肉生意者。清末至民初时,“在北京娼妓群体中,头等妓女提供陪酒、歌舞表演等服务”[9],清吟小班中“南班的养家对买来的妓女从小即教其笙管丝弦或书画。所以苏扬妓女多善苏州名歌及民乐,杭州妓女除善民乐外,有的还会水墨丹青、书法或略谙诗词”[2](P322)。由此可见,清吟小班中的妓女,最初都是擅长吹拉弹唱的艺妓。至民国时期,随着娼妓业的畸形繁荣,妓女需求量增大,各小班竞争激烈,妓院老板因注重成本和利润,遂无心培养妓女的基本功。此时,清吟小班妓女“所谓学也只是学那么几段,甚至会四句散板几句流水也可以算一段,字眼儿更是马马虎虎,反正拉起胡琴能跟上拍子直着喉咙喊几句就算不错了,一般都谈不上什么韵味”[2](P345),“各艳株手不能弹,口不能唱,舍皮肉生涯外,无一技足显者,比比而然”[1](P284)。
最初,清吟小班戒律森严繁杂,所谓“妓院是末等饭,头等规矩”,即就此而言。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妓院成为社会上层人物的社交活动场所,清吟小班为客人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均收取较高的资费,如茶资1元、打牌20元、请客51元、唱戏2元、饭局5元、进城10元、住宿12元等。[10](P259)嫖客若想与高等妓女发生性关系,往往要费很多周折,如初次来打茶围、打牌,平日饭局,节日请客,这些固定活动项目一个都少不了。得益于此,这一时期,清吟小班妓女生活优越,“每逢农历正月十五灯节、端午、中秋节及其他很多节日,客人们为与姑娘捧场,均须肆宴设席,行各种娱乐,……挥霍大量的金钱”[2](P462),清吟小班中“一个红姑娘的皮斗篷,至少要有若干件,今天出条子穿这件,明天如果再穿这一件,就有点不体面了。身上穿的衣服,讲究一点的,都要到力古洋行买进口的衣料……但红一点的姑娘,手上短不了要戴一两个钻石,至少是宝石的戒指”[2](P351),“小班的妓女逛公园,看电影,吃小馆……都是很平常的享受”[2](P391)。而到了1938—1945年间,虽然还有部分来清吟小班的客人,“请他们吃饭时,也要叫条子、敬酒、唱戏。他们还把清吟小班的妓女当作日本的艺妓看待”[2](P391),但清吟小班所接待的头等客人日本顾问和大商人,大多情况下只是把清吟小班当作慰劳所。在这种情形下,清吟小班为客人开展的服务项目大大减少,主要以接待客人住宿为主,其规矩也变得松散起来。嫖客若想与妓女发生性关系,再也不必经过之前的打茶围、打牌、请客这样一系列繁琐的流程;而多数日本人来妓院,更是为了纯粹的人肉买卖:“日本的大公司定期在妓院里‘慰劳’他们机关里的职员,这时,总是二十多个人同来,一块拉铺。”[2](P392)当日本人一次来的人太多,头等妓女人数不够时,清吟小班还会分批接待,或临时找二等妓女充数。与这一时期妓女人数增多、妓院规模扩大的畸形繁荣表象不符的是,随着清吟小班高利润服务项目的减少,妓院的额外收入受到冲击,于是,老鸨开始大量克扣妓女收入或降低妓女生活标准,清吟小班妓女生活每况愈下,“妓女几乎每个人头上长了蚤子……蓬松的云鬓里却爬满了上万成千的蚤子”[2](P391)。清吟小班表面的繁荣,实则建基于妓女的惨淡生活之上。从卖艺不卖身沦为单纯操皮肉生意以维持生计,已成为此期清吟小班多数高级妓女的无奈选择。
在民国政局动荡以及日寇野蛮侵略背景下走向畸形繁荣的清吟小班,其巨变的背后,实则隐藏着无数妓女的血泪。在日寇侵华时期,清吟小班所迎来的畸形繁荣,虽难免令人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叹,但如果跳出男性精英话语的拘囿,单从妓女这一群体本身角度而言,其实则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当此之时,陈寅恪所称的“理解的同情”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而言,无论是清吟小班所代表的娼妓业群体,抑或无数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职业群体,其在历史巨变中的相关经历与变化,都应该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
参考文献:
[1]王书奴.中国娼妓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2]《文史精华》编辑部.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上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3]武舟.中国妓女生活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
[4]杨子慧.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
[5]张超.民国娼妓问题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5.
[6]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M].黄艳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7]荣国章.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北平的经济掠夺和压榨[J].北京社会科学,1991(3).
[8]王显成.论沦陷期伪北京市政权的淫化政策[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9]刘荣臻.“危险的愉悦”:浅析近代北京的娼妓业——以1912-1927年为范围[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1(10).
[10]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韩玺吾E-mail:shekeban@163.com
收稿日期:2016-04-11
基金项目: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5KRM105)
作者简介:陈思琦(1995-),女,陕西咸阳人,硕士研究生。
分类号:K251;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16)06-0084-03
On Government Absolutions for Debt and the Opposed Clauses of Tang Dynasty The Abnormal Prosperity of the Qing Yin Clas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Chen Siq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00)
Abstract:In the Republican period,the Beijing bawdry industry respectively in 1912~1927 years,1938~1945 years,there were two abnormal prosperity.As a small class prostitution in Qing Yin was the first group,great changes also occurred in two in abnormal prosperity.This chang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small class prostitute service object (clients) nature of the change,the whole quality of the prostitutes decreased,service project of reduction and prostitutes living level decreased.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derlying social prostitution,lif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 Qing Yin class prostitutes are closely related.
Key words:the republican period;Beijing;Qing Yin class;prospe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