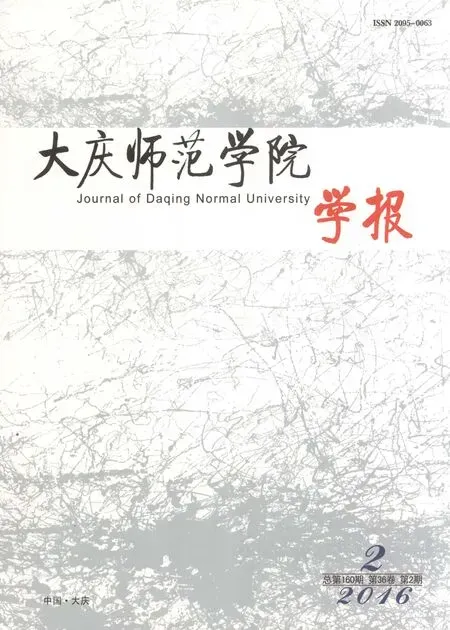科学证据及其应用问题探讨
刘宇飞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科学证据及其应用问题探讨
刘宇飞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学证据在诉讼活动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科学证据具有促进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积极价值;另一方面,科学证据的不当运用也会产生侵犯人权,拖延诉讼,甚至造成错判的消极影响。这需要对科学证据的涵义、价值角度做重新分析,对我国科学证据的应用需注意的问题进行重新探讨,以使科学证据在司法实践应用中引起高度重视。
关键词:科学证据;价值分析;诉讼制度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与生产能力的同时,也被应用到司法领域中。面对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各种犯罪,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将科学技术引入司法证明过程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其目的在于提高诉讼证明的技术含量。我国台湾著名证据法学者蔡墩铭教授指出:“今日刑事审判不应再只重自白,而应重视物证,尤其藉法科学进行采证取得之物证,亦即科学证据。从而所谓证据裁判主义,于今日法科学应用之时代,应改称为科学证据裁判主义。”[1]该学者表明科学证据在诉讼中的积极价值,即科学证据的运用有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促进实体公正的体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科学证据也存在失真与错误的可能,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和案件事实的准确查明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甚至成为错案的“帮凶”,需要高度重视并防范。本文通过对科学证据的深入分析,并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探究科学证据在刑事诉讼应用中所需注意的问题,期望能对我国科学证据制度的完善有所帮助。
一、科学证据的涵义
(一)域外学者关于科学证据含义的认识
英美国家尽管出版了大量的有关科学证据的著作,但都没有直接明确的定义“科学证据”的含义,而大多数只是列举出“科学证据”的范畴,然后对这些科学证据的运用再逐一进行研究。例如由英博和莫森斯合著的《刑事案件中的科学证据》一书认为科学证据包括如下领域:(1)醉酒的化学分析;(2)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神经学;(3)枪弹证据和比较显微检验;(4)法医病理学;(5)毒理学和化学;(6)指纹鉴定;(7)显微分析;(8)中子活化分析;(9)可疑文书;(10)照相、电影和录像;(11)声纹鉴定;(12)车速的科学鉴定;(13)测谎检查;(14)麻醉分析和催眠术;(16)其他科技证据,如素描技术、民意测验等。[2]45
美国著名的证据法学家乔恩·R·华尔兹教授则从以下诸方面对“科学证据”进行了论述:(1)精神病学和心理学;(2)毒物学和化学;(3)法庭病理学;(4)照相证据、动作照片和录像;(5)显微分析;(6)中子活化分析;(7)指纹鉴定;(8)DNA鉴定;(9)枪弹证据;(10)声纹鉴定;(11)可疑文书证据;(12)多电图仪测谎审查;(13)车速检测。[3]
与英美不同,许多日本学者试图对科学证据作出明确定义,依石井一正教授的观点,科学证据就是利用科学的统计学的概率原理来进行科学证明的证据。[4]三井诚教授指出:“科学证据系指活用各科学领域之知识、技术、成果所得之刑事法上之证据。科学证据当然不限于经过科学搜查活动所得致者,然而实际上乃指科学侦查活动结果所得之证据居多。”[5]
(二)国内学者对科学证据含义的不同认识
虽然科学证据已经在司法实践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但国内学界对什么是科学证据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见解,观点不尽统一。笔者从中选取一些代表性观点,归纳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有通过科学方法所获得证据都是科学证据,其主要包括鉴定结论和视听资料”;并认为“科学证据是与认证、物证、书证和司法检验并列的一种证据形式”[6]。
第二种观点认为,以“语义结构和证据功能”为分析框架,认为“科学证据是运用具有可检验特征的普遍定理、规律和原理解释案件事实构成的变化发展及其内在联系的专家意见”[7]。
第三种观点认为,“凡是借助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收集到的证据材料以及借助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揭示出其证明价值的证据,都属于科学证据。相反,不是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发现、收集和揭示出来的证据都不属于科学证据”。该学者进一步指出:“科学证据是指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发现、收集和揭示出来的证据。其内涵是运用科学技术获取的证据;其外延包括所有用科学技术手段获取的证据,既包括过去,也包括现在和将来运用科学技术手段获取的一切证据。”[8]
第四种观点认为,科学证据是一个包含众多证据形式的证据种类。由于几乎每一种科技证据从产生到走进司法程序,都经历了一个长时间不停争辩的过程,所以,科技证据应当是指“具有一定技术水平,但同时要么由于其技术的可靠性难以得到科学界的一致肯定,要么因其对人权的巨大侵犯而被许多法学家所排斥而导致其容许性经历或正在经历一个不断肯定和否定的反复过程的证据种类”[9]。
(三)科学证据涵义之我见
国内外学者关于科学证据的不同定义,实际上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启迪意义。通过对国内外学者不同观点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科学证据定义产生争论的原因关键在于大家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必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笔者更倾向于从科学证据的价值角度考虑——为何司法实践中需要运用科学证据?简言之,有了科学证据,我们便可以更加准确地探知案件事实的真相;科学证据是准确判定高科技犯罪的案件事实不可或缺的证据,缺少科学证据,高科技犯罪之类案件的侦破与证明便陷入困境。基于以上思考,笔者认为,科学证据是指能够帮助人们证明案件事实,具有科学技术含量,而且不与诉讼效率、人权保障等价值相冲突的一类证据。
二、科学证据的价值分析
(一)积极价值
1.科学证据可以促进实体公正
作为科学技术在诉讼中运用的科学证据,是以追求客观真实为根本目的的。在刑事诉讼中,办案人员运用科学证据能够更好的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科学证据与其他证据相比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原因在于司法人员通过运用科学技术来提高诉讼认识,借此避免认识主体受到感性认识上的不良影响,同时增强了认识主体理性认识的能力。相比言之,科学证据在发现事实真相上的作用主要有:(1)打击高科技犯罪。对于当代越来越多利用高科技手段实施的犯罪,都具有犯罪主体智商高、反侦查能力强、犯罪地点多变、社会危害巨大等特点。因此,国家对付这些高科技犯罪的必要手段就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利用高科技手段调查收集证据,达到控制科技犯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有利局面。(2)对付传统犯罪也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现在公安部门建立的指纹数据库、DNA数据库等数据库为侦破一些传统犯罪提供了巨大便利。这些数据库的建立,可以将犯罪现场遗留的人体物证与嫌疑人比对,使得侦查人员迅速识别、认定犯罪分子。同时,现代社会大量使用各种监视录像、闭路电视,对于准确快速地认定犯罪分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3)可以用来发现和纠正错案。例如,1986年,英国中东部发生了两起强奸并谋杀英国女学生的案件。警察在犯罪现场提取了精斑检材和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血样,由刚刚发明“DNA指纹图”的遗传学家阿莱克·杰弗里斯进行DNA对比。杰弗里斯证实两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但是罪犯并不是警察拘留的那名嫌疑犯—一名厨房的勤杂工。这名厨房的勤杂工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用DNA证据证实的无辜者。
2.科学证据可以促进程序公正
科学证据的广泛运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和保障被追诉人质证权的行使,从而促进程序公正的实现。一方面,科学证据的广泛运用可以帮助追诉机关尽可能的摆脱对被追诉人口供的依赖,从而可以减少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保证程序正义的实现。刑讯,作为刑事司法程序上最大的不公,使得犯罪嫌疑人在定罪前受到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张氏叔侄、佘祥林、杜培武等重大冤假错案,都与刑讯逼供密切相关。因此,在刑事证据程序公正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刑讯逼供的防范。对此,陈学权教授指出,根治刑讯逼供的最有力办法不是使追诉机关不能进行刑讯逼供,而是使追诉机关主观上就觉得不想、也感觉无必要刑讯逼供。而要实现此目标,唯有开出“中药”——向科技证据要破案率![2]142可以预见,随着科学证据的普遍运用,追诉机关的破案压力将会逐渐减轻,刑讯逼供必然会逐渐减少,届时我国刑事司法在程序公正方面必将会取得巨大进步。另一方面,通过视听技术,有助于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确保被追诉人对证人进行质证,从而促进程序公正的实现。不可否认,虽然证人通过视听技术作证有利于改变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但是与要求证人亲自出席法庭作证相比,显然不利于法庭和控辩双方“察言观色”。尽管有缺陷,但就我国而言,在实践中证人几乎都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通过视听技术让证人作证,与在法庭上直接宣读侦查阶段的证人证言笔录相比,已算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保证被追诉人质证权的行使,从而促进程序公正在我国的实现。
(二)消极价值
1.科学证据的运用可能侵犯人权
2012年,第二次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2条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任务。显然,科学技术在现代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也必须符合人权的要求。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勘验、检查时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如果犯罪嫌疑人拒绝检查,侦查人员认为必要时,可以强制检查。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作为物证需要专家利用科学技术进行解读才能显现价值,然而这种生物物证的提取,稍有不慎,便会与人的隐私权、身体健康权等宪法权利之间产生尖锐冲突。房保国教授指出:“强制采样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如,强制没有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到指定的场所接受采样,是对被采样人人身自由的限制。”[10]实际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科学证据必然会受到一系列人权问题的挑战,这也提醒我们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科学证据必须保持一定的限度。例如杜培武杀人冤案中测谎异化为刑讯逼供的帮凶进而造成错案。杜培武就是因拒不承认犯罪,被侦查人员带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心理测试,结果测试表明杜否认杀人的供述90%以上是谎言。于是,侦查人员便对杜进行“生不如死”的刑讯逼供迫使其“承认”罪行。鉴于此,笔者认为对于测谎结论这类科学证据在取证阶段要坚持自愿性原则。即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测谎之前,应征得被测谎人的同意,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如果进行强制测谎可能会得出可靠性较低的结论,催生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人权。
2.科学证据的运用可能导致诉讼拖延和成本增加
科学证据在实践中的运用可能会导致诉讼陷入停滞状态中,与诉讼效率目标产生冲突,同时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带来诉讼成本的不合理增加。一方面,科学证据的生成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在司法审判中,有些科学证据从程序启动到证据的产生再到法庭上的质证和最终采信,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这些时间无论是否计入审理期限,都会造成案件迟迟得不到解决,使得诉讼过分迟延,在公正与效率之间无法得到平衡。况且案件的复杂和专家证人作证技巧的高明经常会导致审判法官面对“似真似假”的科学证据陷入难以分辨的泥潭,本来用于发现真实的科学证据在对抗制度下却成为发现真实的障碍。裁判者难以做出裁决,也导致了诉讼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对于司法机关来说,科学鉴定证据的生成需要使用大量高科技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费用昂贵,开支巨大;同时,由于法官作为事实的审判者在有关科学专业知识领域是门外汉,面对科学证据难以定夺,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来认定事实,使得案件久拖不决,影响法院其他工作的开展,浪费司法资源,造成诉讼成本不合理增加。对于当事人来说,科学证据的作用日益重要,有时直接影响诉讼的成败。因此,聘请专家、不惜代价聘请“一流”专家做出有利于己的鉴定证据已经成为一种必要的诉讼开支,势必会给当事人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3.科学证据的失真可能导致错判
由于科学并非是绝对客观以及运用过程中一些人为因素的影响,科学证据也可能失真,从而可能产生误判,成为发现事实真相的阻碍。首先,科学证据的规范性和技术性要求非常高,但是在其收集、采样、保管、鉴定等多个环节都可能出错。例如在保管环节,收集完的物证将会随即进行空间和时间的转移,在移送的过程中,其中任何一次交接不清都可能导致待检材料的混乱或受到外环境污染,一旦保管不善将会导致其证据证明力的丧失。其次,科学证据本身并非绝对权威,诉讼主体过于迷信科学证据。被奉为现代“证据之王”的DNA证据,在实践中都被办案人员视为“铁证”,以为弄一个DNA鉴定证明嫌疑人犯罪就“铁证如山”。事实上,DNA鉴定也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人体基因本身的不确定性;人为操作的失误;DNA数据的概率统计错误;DNA鉴定人员资质参差不齐。在实践中,存在不少因DNA鉴定导致的错案。如1998年发生在河北省邢台市的徐东辰强奸杀人冤案。侦查人员将徐东辰的血样和被害人阴道提取的卫生纸精斑进行DNA鉴定后得出“不排除死者阴道擦拭用纸上的精斑是嫌疑人徐东辰所留”的结论,警方据此认定徐为犯罪嫌疑人并屈打成招,迫使徐东辰认罪,并最终被判死刑。正是公检法三机关对于DNA证据确信无疑,从而最终导致案件发生错判。这表明,科学证据并非绝对可靠,有时反而妨碍了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我国刑事司法实务人员不应盲目轻信DNA的证明力,在刑事案件中不能仅仅凭借DNA鉴定结论来认定犯罪事实。
三、科学证据的应用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确立理性看待科学证据的态度
科学是柄双刃剑,科学证据也有其两重性,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无法忽视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和时代性,同时,那种迷信科学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科学证据的科学性,承认其对常识证据的超越。科学证据依托强大的科技力量,能够更为准确地判断事实是否发生以及发生情况,为司法活动服务,为事实裁判者带来更为准确的结果,从而推动司法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在承认科学证据科学性的前提下,我们要认识到科学证据本身的缺陷,以及运用科学证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科学证据本身不可能达到绝对客观与中立,并且相关专家在生成科学证据时可能受自身的主观倾向影响或操作失误,造成误差甚至完全错误,从而导致错判让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
科学证据时代的到来是时代潮流的趋势,科学证据有其明显的积极功能,我们的法律工作者应该顺应科学证据时代,学会利用科学证据查明案件事实,追寻真相,但是同时也必须认识到科学并不是万能的,科学证据不可能完全取代经验常识。因此,法院应慎重对待诉讼中的科学证据,法官应成守望者,清醒地看到科学证据光明之下的阴影,用公正、合理的证据规则才能去除司法的阴霾,让科学证据走下神坛,回归理性,与其他证据携手共同维护司法的公正。[11]
(二)确立惟科学证据不能定罪原则
上文提到的徐东辰案件,司法办案人员仅凭DNA证据便认定徐有罪并最终导致错判。对此,我们认为,一方面,包括科学证据在内的任何一种证据都不能保证绝对的100%的准确无误,即便是在科学证据准确无误的情况下,还存在着该证据证明力问题。例如徐东辰案件中的DNA鉴定,即使该DNA鉴定结论完全准确,但也只能证明徐东辰可能曾在某特定时段内与被害人发生过性关系,同时也不能就此排除其他人在案发时与被害人发生过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加无法直接或间接证明杀害被害人的凶手就是徐东辰。另一方面,一旦在立法或司法实践中确立了“科学证据是证据之王”的类似规则及理念,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诉讼实践中过分迷信乃至不择手段地获取科学证据的危险。因此,针对司法实践中过分倚重科学证据证明力的问题,有学者提出确立“惟科技证据不得定罪规则”,即指在只有一个科技证据证明被追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不得仅凭该科技证据认定被追诉人有罪。[2]321笔者对此观点十分赞同,因为科学证据大多只能作为间接证据,刑事司法实务人员不应盲目轻信科学证据的证明力。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在只有一个科学证据证明被追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又没有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不得给被追诉人定罪。只有当存在充分的证明犯罪事实的其他相关证据时,并且这些相关证据与鉴定结论相结合能够组成闭合的证据锁链,对所认定的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条件下,法庭审判人员才可以据此做出有罪判决。
(三)科学证据的收集应遵循的原则
证据收集,是指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及其律师等享有收集证据权利的各类主体,通过侦查或调查,依法发现和取得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材料的活动。对于科学证据而言,其收集包括鉴定基础材料的获取,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等实物证据的获得,以及技术侦查措施等。所有科学证据的收集都应遵循如下取证原则:(1)合法性原则。科学证据的收集应当符合法律的要求,遵循法治原则。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54—58条明确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非法收集的科学证据,一律应当予以排除。(2)及时性原则。收集科学证据必须迅速,不能错过最佳的取证时机,否则会导致所取证据丧失真实性。针对某些容易被删除、修改、污染甚至毁坏的科学证据,应尽可能在其被破坏之前迅速收集。(3)利用专门技术设备取证原则。科学证据的发现、收集和保全,尤其是用来鉴定的检验材料的收集,离不开专门的技术和设备。(4)专家参与原则。科学证据以现代高科技为依托,科技因素比较多,因此,在取证时,需要有关科学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参与,并且要与法律工作人员互相配合,一同完成收集工作。(5)收集过程监督原则。科学证据取证的整个过程都必须接受监督。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有合法、规范和完整的笔录以证实取证的合法性、真实性。
(四)鉴定人义务的完善
为了防止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鉴定结论作假、鉴定人操作失误等原因导致科学证据失真造成错案的情况,笔者认为,应当完善鉴定人的义务。首先,鉴定人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完成鉴定工作并出具鉴定意见。但是,仅仅在鉴定书上注明鉴定结论是不够的,鉴定人还负有制作规范、标准的鉴定文书的义务。这是因为,无论是案件的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公诉人还是法官,都需要通过鉴定文书来了解整个鉴定过程,进而才能判断鉴定意见的可靠性。笔者认为,为了确保司法鉴定文书的规范、标准,防止鉴定人违反相应的说明义务,应该规定鉴定人违反制作规范、标准的鉴定文书义务的后果,对于鉴定书中未说明法定事项的,司法鉴定文书无效,法官应当排除该鉴定意见作为证据使用。其次,必须强化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义务。科学证据不能取代法院的司法裁判权,科学证据对于法官和陪审员来说并无法定的拘束力,都应该受到法庭的审查。法官作为事实裁判者需要辨别科学证据的正误,而鉴定人出庭作证义务能够有效帮助法官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原因外,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应就鉴定过程进行释义:说明鉴定材料的收集程序、鉴定实验的过程、运用的科学方法、获取鉴定意见的科学依据,接受当事人双方和法官的提问。将鉴定的启动到科学证据产生的整个过程暴露在“阳光下”,这有利于法院做出公正的判决。
[参考文献]
[1] 蔡墩铭.刑事证据法[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4.
[2] 陈学权.科技证据论 以刑事诉讼为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3] 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M].何家弘,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456.
[4] 石井一正.日本实用刑事证据法[M].陈浩然,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10-11.
[5] 王彬.论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判断标准及构建[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8(4).
[6] 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3.
[7] 张斌.论科学证据的概念[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6).
[8] 何家弘.证据学论坛:第四卷[M].北京:中检察出版社,2002:380-381.
[9]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287.
[10] 房保国.科学证据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38.
[11] 刘建华.让科学证据走下神坛[J].中国司法鉴定,2011(5).
[责任编辑:才璎珠]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Problems
LIU Yu-fei
(Kenneth Wang School of Law,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0, China)
Abstract:As high-tech develops rapidly, scientific evidence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edings. It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entity justice and procedure justice.Meanwhile, the improper use of scientific evidence also violates human rights, delays litigation, even leads to wrong convictions. Therefore, the concept and value of scientific evidence should be analyzed again, and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evidence in our country calls for people's attention.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evidence should b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Key words:scientific evidence; value analysis; litigation system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63(2016)02-0066-05
收稿日期:2015-11-02
作者简介:刘宇飞(1991-),男,江苏连云港人,诉讼法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从事诉讼法学研究。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6.0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