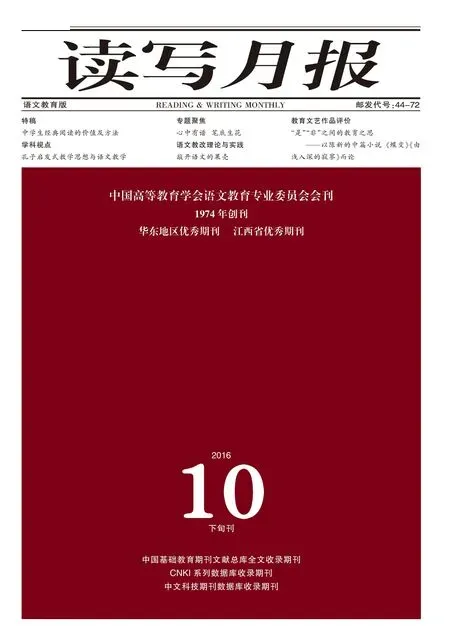教育的失落与回归
——论东紫的中篇小说《红领巾》
吴竺静
教育的失落与回归
——论东紫的中篇小说《红领巾》
吴竺静
教育,即教化培育,《礼记·学记》中认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1]可见,教育作为人的培育事业和文化事业,自古以来都在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2015年第10期的《北京文学·精彩阅读》选载了作家东紫的中篇小说《红领巾》。小说以“红领巾”引发出的一系列事件为线索,聚焦小Q一家进行描述,引出了现实生活中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的诸多问题。空洞的教育内容、贫乏的教育方法,致使教育活动愈加朝着表层的功利性和实用性方向发展。而另一方面,在某种精神情感的传承上,教育本身的内涵、意义和价值却愈加显得单调而空虚了。这与时代大背景下,人们精神世界的贫瘠及人格修养的匮乏不无关联。而在教育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学校、老师及家庭等,遵循着时下某种“约定俗成”的说教,更有甚者,单纯地将自身所接受的庸常教育再移植至对后代的教育中,这种狭隘的思想意识及其行为举动就进一步促成了这样的一场 “教育危机”。
一、教育目的的功利化与教育方向的迷失
东紫在《红领巾》中表现出来的教育批判意识,很大一部分正体现于其对传统教育的反思之上。作为教育领域中的一个思想流派,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区分不纯粹地以时间为标准,直至今日,传统的教育思想仍然存在于当代教育中。中国的传统教育,则“属于偏执于‘文行忠信’式的伦理道德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始终是中国正统教育的中心和主流,它对于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人格塑造,心性的提升,甚至安邦定国都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2]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潮流推动人的思想意识持续前进,每个时期对“教育”的理解也在不断翻新。正因人们思想认知的逐步提高和日趋成熟,或者人类思想意识和逻辑思维的愈加复杂,传统教育开始显现出它的弊端,例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八股取士科举制度,就严重阻碍了文人学子的个人写作风格的形成。某些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如重德行教育,重集体利益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对于青少年的人格养成和人生理想的追寻也起到了较大的引领作用。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争愈加激烈的今天,传统教育的某些局限在社会转型中表现出的不适应性也就更加明显,教育的意义尤其是教育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则更多地被曲解或抹杀了。中篇小说《红领巾》中,作家东紫是寄寓了上述关涉到的这样一种“无力感”和“无措感”的。
教育是文化的事业,教育也是“人”的事业,教育的内涵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人”的自身生命活动的扩展与提升。正是基于“人”的这一根本属性,教育必须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健全人的生命品格为目的,以生命教育和德性教育为方向,并将“以人为本”作为教育活动的根本出发点。然而,小说《红领巾》所映射出来的现实教育状况则是,在很大程度上,教育活动朝着这个理想发展的趋势在当下却并不明显。就以“红领巾”为例,它作为一个被赋予特殊的革命内涵的象征性符号,其独特的教育价值,即在于使学生产生精神和情感世界的共鸣,进而也能形成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个体可以坚守的行为准则及德性追寻。但实际上,“红领巾”在东紫的笔下,或者在更为贴近我们自身的现实生活中,却已然成为了一种“形而上”意义上的规训:学校的执勤生和大队辅导员每天在校门口 “蹲守”,为“抓住一个没带红领巾的”[3]而沾沾自喜;由于小Q没有佩戴红领巾,班级被“扣了三分”,于是,小Q乖巧、懂事、有组织能力等竞选班长的优势被班主任全盘否定了;Q妈想去帮助被抓住没戴红领巾的小Q,却想起越过家长止步线会扣班级的分而退缩了……于是,“红领巾”不仅成了成人世界自审的“皇帝的新衣”,而且还能由此洞见当代社会的种种复杂问题:“红领巾”早已失去了它的话语权威性,然而它又与功利性相联系,被各种规训和惩罚所束缚。[4]具有历史意义和高尚表征的这一意象的理解和阐释被架空,越来越流于表面,而当其内在的深刻意蕴和受教育者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隔阂时,我们可以推断,教育促进人格的完善,促成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和目标也在时间的漩涡中卷向了迷途。教育表面上的神圣和实际上的功利,使得越来越多单纯的“小Q”,甚至越来越多“现代人”产生精神上的困顿与迷惘,最后,只能像Q妈一样,一边空洞地标榜某种“高尚”,一边把这种“高尚”当成擦掉秽物的“抹布”。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下,原本就偏离航道的教育目的和方向,就变得愈加暧昧不明。《大学》开篇便说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5]其实,教育的宗旨也是如此:弘扬正大光明的品德,使人弃旧图新,使人达到最为完善的境界。这里的完善,就不仅仅指简单的知识堆砌,还在于人格修养的完善。教育的本质,“就是要能不断发掘人的潜能,始终指向更广阔的前方。”[6]在这个条件下,教育的人文性就亟待完善和充实,需要用真挚的情感和恰切的实践才能实现其内涵中的人文性的扩展。
另一方面,教育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主体性活动,它培养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人格。[7]教育之于人的思想意识的重要意义,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尤其是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也决定了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教育,面向个体的教育,而且是面向生命和德性的教育。小说《红领巾》中,作家东紫向我们传达的,是以学校和家庭为代表的教育者片面、粗暴地将教条化的思想知识等灌输给孩子的教育现状。首先,这种在历史上有着某种高尚象征的意义的事物已经僵化,教育者只是在向受教育者“洗脑”,反复出现的“红领巾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在这里却并没有带上实质上的精神教育,反而作为一种洗脑的口号而显得愈加空虚和无聊,这与教育 “面向未来”的方向是相悖的,是停留在过去的模式化的“教”和“授”。真正的教育,应该在精神教育的实质中寻求与当下、与未来历史发展更为契合的方式。教育是变化灵动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次,真正的教育也应充分重视每个个体的独特个性,“因材施教”,不但在于对书本知识的习得,更在于对每个富有特色的个体给予相异的教育。在个体与集体之间做选择是没有意义的,但教育完全忽视受教育者的个人特性,而过度地标榜集体利益,这样显然不是恰当的做法。小说中,小Q的学校“没佩戴红领巾将给班级扣分”,以及时刻把班级和学校利益放于首位的做法,显然并不与教育面向个体的发展方向契合。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将学生的精神教育量化为具体的数据和规训,并且只以“做班长”、“扣分”这种功利的形式来定义教育,也明显是与生命教育和德性教育相违背的。生命和德性教育,首先在于对于人类个体的尊重,以此为前提而进行的各种精神、道德教育活动才是真正可执行的、有意义的。
在当下,对教育人文性的重视,以及在当代语境下将传统文化与现实境况相结合并合理运用,培育人的主体人格和独特人格,显得尤为迫切。单纯地停留在过去,局限于当前的视野,一味搬运文字,木讷地单一讲述,只能造成教育的狭隘,教育目的的功利化和教育方向的迷失。与此相对的,在精神及道德教育中注入更有厚度的生命意识,融入更为贴切的生活体验,才能形成强烈的、真挚的、有价值的情感认同和生命品格,教育才能站在更加宽广的高度,以更加清晰的视野朝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前进。
二、教育内容的空洞与教育方法的贫乏
教育的方法和内容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途径,教育者选择一定的知识、经验和情感共鸣,通过教授、沟通等方法,达到某种教育的目标。这是一根链条上相互连接的环扣,教育的内容、方法和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实是在相互作用着的。但正如前文所述,《红领巾》中所反映出来的,或者说是我们自身所处的现实世界中所映照出来的教育目的的功利化和教育方向的迷失状况,使得与其相互作用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也出现了异化现象。
作家东紫在《红领巾》的创作谈中说到,自己写下这部作品的缘由,正是因为在儿子的教育中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儿子与同龄人亲近反遭欺负,对方家长却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儿子在幼儿园被打,跟老师反映时,老师却“只是‘鞥’了一声”;上小学后,包括儿子在内的许多学生,因为知道了红领巾“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而拒绝佩戴。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她在孩子面前的“无力感”和“无措感”愈演愈烈。[8]就如小说中Q妈所说的:“按照正确的教育吧,怕吃亏上当,按照歪的教育吧,怕学坏。”“红领巾”和“烈士”,在某段历史时期内具有特别而高尚的意义,是革命叙事的一个表征。在那样的年代,这类物品和称誉所表达出的,是对革命的信念,对战争胜利、国家强大的期许,也寄寓着青少年对革命事业的崇高信仰,引导着几代人的精神走向,在情感道德方面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然而,小说中表达出来的是另外一番尴尬处境——现今教育语境中,“红领巾”的革命意义相当程度上被架空,而成为一个空洞的符号。学校将佩戴红领巾作为一种规训,而人选的标准却降低到几乎每个孩子都可达标。更为讽刺的是,作为更高标准的“共产党员”的Q爸、Q妈和爷爷奶奶,一方面说着“要是有敌人入侵我们国家,我也会立马冲上去消灭他们”,一方面却违反交通规则乱停车,对在超市门口摔倒的叔叔视而不见不肯施以援手,还说 “不能管闲事,怕人家赖着咱”。这样的现象,其实就如同制作红领巾的材料变化一样,从“纯棉的”到“腈纶化纤的,戴不上两回就成缕了,电熨斗都熨不开”。教育的内容逐渐变质为低劣的虚伪外衣,内在的价值和意义被掏空,教育的真谛和价值,也在呆板的、没有创新的单一内容传述中渐渐地失落沉沦。“它因为我们赋予它的意义,让主宰我们的人可以拿它上纲上线,用它衡量一个孩子甚或一家人的精神面貌和政治立场,也可以在不约而同的亵渎中消解它所谓的意义,成为一种无意义的捆绑。”[9]
而另一方面,教育方法的贫乏也是造成教育失落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的教育实践中,施行道德教育的做法还是停留在以说教和灌输为主的基础上,教育者仅限于用单一的道德价值观去影响受教育者。”[10]小说《红领巾》中便表现出这样一种贫乏的教育方式。事实上,学校、Q爸Q妈和爷爷奶奶,多个角色的教育方法可谓千篇一律:学校与Q爸的教育方式相似,即简单、粗暴、急切地单向施加给孩子,在这种的思维模式中,作为受教育者的孩子只要接受自己的教育便可,这是不科学的,不合理的,也是不符合生命教育的要求的;Q妈,虽然善于循循善诱,富有耐心和爱,但自身的思想局限仍旧限制了她的教育方法,即前文中叙述的,一边要求自己的孩子能够体会到这种“高尚”,另一方面,却在自己的行为中不加以道德约束,甚至一边标榜这种虚伪的高尚,一边用这种高尚擦拭秽物。这样不基于自身生活体验的教育方式,无论如何是逃脱不了虚无和贫乏状况的。
教育者将陈旧的教育内容通过野蛮而粗俗的方式施加给孩子,事实上是与教育的原初期望相违背的。“道德教育本质上是人格的、生命的、完整生活质量的教育,绝不是通过空洞的口头传述就可以实现的。”[11]在空洞的教育内容和贫乏的教育方法中,与人的精神世界与人格养成紧密联系着的“教育”,变成了虚假的神圣和人为的高尚,成为披着华丽外衣的“假道学”。
三、温情与爱:教育回归之初探
“人与生俱来就有探索创造的冲动,有与人联系、交流的欲望,有对秩序、格局的敏感。”[12]在《红领巾》里,小Q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创造性和独特思维方式的个体,他根据一个现象或一种说法,进而衍生出自己的稚嫩观点甚至一系列问题,形成自己真诚的情感意识和道德认知。我们知道,“道德感”是人类情感认知的一部分,对中国传统教育而言,对伦理道德的重视一直以来都是其重要特征,而受到影响的中国现代教育也由此重视道德教育的发展。但在经济高度发达、社会急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整个教育,尤其是德育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东紫在《红领巾》这部作品当中迫切地想要呼喊出来的,就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孩子的教育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在整个故事中,东紫从“红领巾”事件入手,写小Q一开始佩戴红领巾时的兴奋,到被老师告知“红领巾是战士的鲜血染成的”之后对红领巾的抗拒,再到一家人看所谓的“抗战剧”时所引发的“烈士”问题,最后以自制红领巾和魔术 “变”出红领巾来结束这个故事。看似滑稽而啰嗦的叙事当中,是传统教育模式下教育目的的功利化、教育方向的迷失、教育内容的空洞和教育方法的贫乏所造就的一场危机,以及这场危机最后的,与原有方式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法。
“教育要做的主要是为个人提供条件和支持,可是我们现在强加的、一厢情愿的事太多。外部人为强加的东西反倒容易泯灭和消解人性深处的一种潜能。”[13]与这样的“强加”和“一厢情愿”相对,以沟通交流为主的双向互动就成为一条有效途径。所以,小说中的Q妈,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与小说中其他人物有差异的。Q妈是充满母性光辉的形象,与Q爸相比较,她习惯于通过沟通解决问题,能够耐心地与小Q交流。在母子交流互动的过程中,教育产生的生命的温情体味、人的内心深处的“爱”的体验,如果能够得到合理的、科学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向的引导,能够建立在饱满并充满生活体验的教育内容之上,它们是能够成为教育的有力武器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给教育带来一种新的面貌和情感体验。
在小说末尾,东紫“试图以梦想和宽容给曾经的理想主义符号赋予新的意义,即尊重所有曾经美好的东西,在新语境中赋予其新的‘正能量’。”[14]Q妈带着小Q一起制作红领巾,失败后又让圣诞老人用魔术给小Q变出一条红领巾,“只有最幸运最乖的孩子才有红领巾”的表述代替了“红领巾是战士的鲜血染成的”这个说法,最终使得小Q重新戴上了红领巾,并产生了情感认同。一起制作红领巾,其实就是一个有趣的亲子互动。在今天,许多幼儿园、小学设立亲子课堂的做法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以实践来产生、获得生活和情感体验,其实原本就是教育最有效的一条途径。而在读者看来,这样的亲子互动场面,也要比小说前半部分许多成人对小Q的硬性、单一的说教要温情和温暖得多。故事的最后,Q爸和Q妈利用一个魔术来结束了这个“闹剧”。也许这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也许这正是作家本人在教育孩子的谜团中不得自拔,只能试图找寻一条新的出路的表现之一。但值得肯定的是,这是一个拥有童趣和爱的结局,没有所谓的高尚的粉饰,也不再执着于“红领巾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夏丐尊先生就曾说:“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15]教育如果变成了陈旧的、空虚的说教,便意味着没有了爱和温情,也就成为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至上的某种机械性的传承工具,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化人和培育人的具有人文意义的事业。
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一切固有的文化逻辑都遭受着巨大的冲击,在波涛汹涌的浪潮中,教育的内涵与走向都必须迎接洗礼从而走向重生。如何定位教育的走向和目的地,如何将有价值的教育内容以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传达给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对教育者自身的审视,也许,这是在“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这样的固有而又相对单一的思维方式之外,寻求更为单纯和本真、更为丰富、充满梦幻和温情的新的表达方式时,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注释:
[1][5]孟子等:《四书五经》,中华书局,2009年,第379页,第47页。
[2][10]刘颖洁:《中国传统教育价值观与现代教育的冲突与融合》,《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242页,第244页。
[3]东紫:《红领巾》,《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5年第10期,第63页。该作品引文出处下文不再一一标注。
[4][14]房伟:《“小叙事”中的“大问题”》,《文艺报》,2015年11月20日,第2版。
[6]宋芳、王玉:《教育的目的——止于至善》,《科教导刊》(上旬刊),2010年第11期,第68页。
[7]黄成涛:《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新课程》(下),2011年第6期,第32页。
[8][9]东紫:《面对孩子,我们何为?——〈红领巾〉创作谈》,《小说月报》(微信专稿),2016年2月2日,http://www.yangqiu.cn/kingdee_dalian/799972.html。
[11]朱小蔓:《教育的问题与挑战——思想的回应》,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6-287页。
[12][13]朱小蔓、朱永新:《中国教育:情感缺失》,《读书》,2012年第1期,第4页,第4页。
[15]转引自朱小蔓:《教育的问题与挑战——思想的回应》,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22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辑:舍予
责任编辑: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