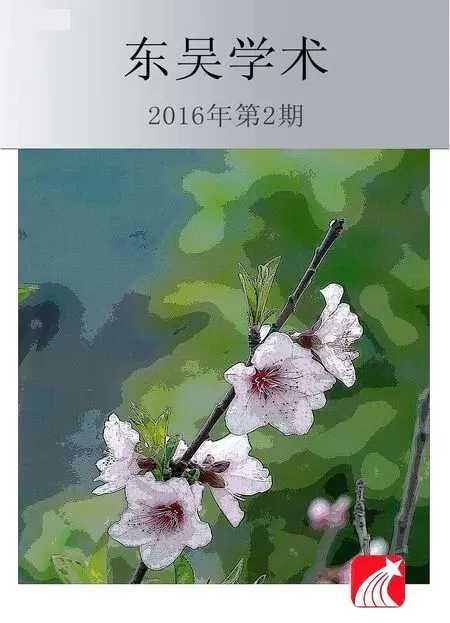金理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
李德南
金理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
李德南
对于理解金理来说,学者与批评家,是两种不可或缺的身份。社团研究、青年构形研究和现代名教研究者这三种研究,文学“实感”论与“境况中”的文学论这两种论述,多样的文学批评实践,使“学术境界与生命境界合致”的学术理想和批评理想,是理解金理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的重要维度。
现代名教;青年构形;实感;存在论
在“八〇后”一代青年学者和批评家中,金理是较早发出自己的声音、已有丰硕成果的一位。他在大学时代曾写过小说,却没有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而是选择了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成为一位“文学性知识分子”。①关于“文学性知识分子”,见金理《“文学性知识分子”的批判力——关于郜元宝及其〈小批判集〉》,收入《一眼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迄今为止,他已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大量文章,并先后出版了《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与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历史中诞生:一九八〇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青春梦与文学记忆》、《现代记忆与实感经验:现代中国文学散论集》等多部著作。学者与批评家,对于理解金理而言,已然是两种不可或缺的身份。
一、三种研究
这里不妨从他的学术研究谈起。金理的学术研究范围也比较广,既有文学史的研究,也有思想史的研究。就主题而言,他用力较深的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社团研究。二〇〇六年,东方出版中心推出了由陈思和、丁帆共同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书系,研究对象包括南社、栎社、语丝社、创造社、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等文学社团,金理也参与其中。他将这一本专著命名为《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拟从社团的角度,以人事为主,采取社团与人互为参证的方式,研究从‘兰社’而‘璎珞社’而‘文学工场’而‘水沫社’、直至《现代》杂志的演变,探讨这一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为核心成员(后来又加入刘呐鸥)的文学社团的聚结、发展、离散过程。”②金理:《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第1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这个课题,既是金理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也是作为青年学者的他的第一次重要出场。如今回头细看,是能够从中看出金理在学术方面的潜质甚至是气象的。他在这一课题中所显示的耐心和谦逊尤其宝贵。文学研究需要广阔的知识背景,因此,中文系的学术训练往往重视广博而非专深。中文系的学生又多少有些才气,才气对创作来说非常重要,舍此绝无可能成为大作家;可是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过于倚重才气不是好事。学术研究需要做很多实证的工作,也需要周密的思辨能力,需要有对问题持续打量、反复推敲的耐心,需要费心费时了解相关问题的学术传统,过于依赖才气的话难免会轻视上述功夫,难以一一完成上述步骤。这是许多中文科班出身的青年学者的软肋,但金理并无这方面的问题。
另外,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在研究中提出新见是相对容易的,毕竟是初出茅庐,有胆识,感受也新鲜。更有难度的,是对史料的处理,是如何让初涉学术课题而产生的一闪灵光得到周密的论证,是如何在证实与证伪相交织的过程中反复辩难,对纷繁的奇思妙想作出合理的取舍。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取“史从论出”的路径相对容易,可是这并不是学术研究的最佳方法;“论从史出”,以冷静、审慎的态度切近研究对象,始终坚持“绝没有硬要事实迁就观点,而是让观点以事实为依据”的学术精神,①[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18页,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在熟知对象的过程中得出新知,是更好的同时也是更为艰难的路径。《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一书,则体现了金理选择的是更为艰难的一路。丰富的史料,对问题的耐心梳理,使得他的这一研究著作有了厚重的品格,至今仍是理解《现代》杂志和施蛰存等人的文学历程的重要著作。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研究,也是金理用力较深的领域。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已结集为《历史中诞生》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二〇一三年出版。按照金理的说法,之所以取“历史中诞生”的书名,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任何小说文本和青年人的形象,既需要建立起纵向的文学史考察视角,也应该在横向的、特定的历史空间中语境化,这样才能还原出文学创作过程中多种因素的互动。”②金理:《历史中诞生: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第1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这段话,既是解释命题形成的因由,也是对个人所取的基本研究方法的说明。这本专著,既讨论了文学与社会互动中的青年文学,也以铁凝、王安忆、路遥、毕飞宇、叶弥、魏微、葛亮、郑小驴等人写青年题材的作品为例,探讨一九八〇年代以来青年文学与文化心理的变与不变。所关注的问题,既属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课题领域,又带有文学批评的性质,行文和立论既有文学史研究的厚重和审慎,也不乏置身于现场的敏锐和果断。金理的学者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在这本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彰显。此外,金理在二〇一四年出版的《青春梦与文学记忆》一书中有一个小辑,重点也是讨论青年文学和青年形象的问题,比如《宅女,或离家出走》一文,以青年作家马小淘的《毛坯夫妻》和张悦然的《家》为例,讨论当下青年写作中的宅女形象与离家出走的青年形象,进而追问青年如何重建个人的主体性。这些文章,亦可视为对青年构形这一研究课题的延伸,不妨与《历史中诞生》一书放在一起阅读。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现代名教的研究与批判,也是金理用力颇多的领域。二〇〇八年,金理博士毕业,当时所提交的论文便是对现代名教的研究,题为《抗争现代名教: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关于现代名教的来龙去脉,他在《“名教”的现代重构、讨论方法及其批判意义》一文中有较为详细梳理。“名教”本来是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其实质是围绕正名定分并以之为教化来建立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秩序;近代以降,在谭嗣同、章太炎、冯友兰、胡适等人在具体论述中,“名教”的含义则有所变化。在金理的论述中,现代名教大概有两层内涵,“首先是指一种‘名词拜物教’,关心的不是具体语境具体问题而只是空洞的符号;其次它指向一种消极的思维方式,本质上是现代迷信,‘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往往演变为对于‘绝对真理’与终极教条的迷信,而拒绝在历史和社会的行进中向实践开放。”①金理:《“名教”的现代重构、讨论方法及其批判意义》,《青春梦与文学记忆》,第9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迷信名教的危险,首先在于它会造成思想(观念)与实际行动、生活世界的割裂,因过分强调思想的优先性而本末倒置。这种危险,是金理在研究中持续吃紧,丝毫不肯放松的。对于现代名教,他主要是持批判立场。除了揭示现代名教的种种问题,金理的研究还有非常精彩的地方,那就是以非常细致的方式重构了章太炎、鲁迅、胡风、胡适等知识分子在不同语境中如何对待同样的问题,并作出不同的选择。观念的阐释总是抽象的,金理的研究则将阐释融入到具体的事件当中,使之获得鲜明的、具体的形象。他的研究,也为理解这些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偏重从文学的角度进入,也使得金理的名教研究与其他学者的有所不同。
而类似的名教崇拜与名教批判,在西方思想史中也同样存在。黑格尔曾这样批判康德对认识论问题的重视:“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主要观点,即在于教人在进行探究上帝以及事物的本质等问题之前,先对于认识能力本身,作一番考察功夫,看人是否有达到此种知识的能力。他指出,人们在进行认识工作以前,必须对于用来工作的工具,先行认识,假如工具不完善,则一切工作,将归徒劳——康德的这种思想看来异常可取,曾经引起很大的敬佩和赞同。但结果使得认识活动将探讨对象,把握对象的兴趣,转向其自身,转向着认识的形式方面。如果不为文字所骗的话,那我们就不难看出,对于别的工作的工具,我们诚然能够在别种方式下加以考察,加以批判,不必一定限于那个工具所适用的特殊工作之内。但要想执行考察认识的工作,却只有在认识的活动中才可进行。考察所谓认识的工具,与对认识加以认识,乃是一回事。但是想要认识于人们进行认识之前,其可笑实无异于某学究的聪明办法,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切勿冒险下水。”②[德]黑格尔:《小逻辑》,第49-50页,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这其实何尝不是一种名教迷信——它所迷信的,是在思维层面讨论形而上的认识论问题的优先性。近代哲学重视讨论认识论而轻视存在论的问题,由此而造成认识论和存在论的割裂,正是典型的名教思维所导致的。“‘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往往演变为对于‘绝对真理’与终极教条的迷信,而拒绝在历史和社会的行进中向实践开放”,正是这种认识论哲学的最大问题。而马克思、海德格尔等人所做的,也正是金理所说的“破名”的工作。以海德格尔为例,他先是借助现象学或解释学来试图克服近代形而上学与科学所造成的运思上的问题,到了后期却又意识到过于强调现象学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因而试图在东亚思想比如道家学说中寻找资源,试图让个人的运思保持“无名”状态,甚至拒绝以“哲学”来命名之。任何的思想观念,如何不能从生活世界出发,并最终回归到生活世界,都难免会缺乏足够结实的地基,有凌空虚造的嫌疑。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对生活世界的强调,用意也正在于此。
如果我们把他们与鲁迅、胡风等人放在一起观察的话,便可以发现,虽然这些不同国别的思想者的思考语境有所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也有差异,但所采取的策略却是相似的。合而观之,则可以发现另一个同样值得关切的问题:自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地朝向西方寻求新知,甚至唯西方之名是举,殊不知西方也自有其问题,西方思想家也尝试从东方寻找思想资源。这种显得有些错位的“思想取经”,直到现在也并未中止。这一点,我们在德布雷和赵汀阳最近的系列通信中亦可看出。如德布雷所言,“正当我们转向中国传统智慧和文化、帝王时代的智慧和文化(孔子、道家、传统医学、《易经》等)的时候,你们的知识分子背向它们而采取我们的价值(比如说在一九一九年或者一九四九年)。这个旋转门是个大误解,导致了双边的失望”。③[法]德布雷、赵汀阳:《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第203页,张万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由此也可以看出,如何破除名教思维的限制,更恰切地在实践中开放,仍旧是每个现代知识分子都要面临的问题。
二、两种论述
金理的社团研究和青年构形研究均已有专著出版,与之相比,现代名教研究仍带有未完成的性质。但我个人觉得,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学术工作当中,最为扎实且最为重要的,当属现代名教研究。如上所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史课题,对于当下的文化建设也同样迫切。另外,对于理解金理的学术研究乃至文学批评的特点来说,其现代名教研究也是非常关键的。正是通过现代名教研究,金理找到了或是进一步明晰了他从事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的运思方式,找到了属于他个人的方法、资源和立场。这又首先在他关于文学的两种论述——文学“实感”论与“境况中”的文学论——中得到体现。
如果说现代名教研究主要是属于思想史范畴的话,那么《文学“实感”论》这篇文章则更多是带有文论的性质。文学“实感”论的提出,其实仍旧是以对名教的批评作为背景和前提的,是金理批判现代名教之后的合乎逻辑的扩展与延伸。在这篇文章中,他先是以诗人翟永明和于坚的遭遇为例,来说明文学创作与接受中被名教思维所束缚的处境:在一次会议上,翟永明朗诵了自己写给母亲的诗《十四首素歌》,朗诵结束后,却有读者表示不能理解。因为这位读者习惯于把母亲等同于祖国,却失去了将母亲还原为具体形象的能力。“将祖国比喻成母亲无可厚非,危险的是,任何试图将母亲还原为原始语义、具体形象和私人命名的努力,会招致‘听不懂’‘缺乏现实感’的责难。”①金理:《文学“实感”论:以鲁迅、胡风提供的经验为例》,《同时代的见证》,第154、158-159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于坚在文章中也曾感叹想要在文学创作中直接面对原初意义上的大树、乌鸦、玫瑰等事物,已变得异常困难,因为这些具体事物已经被隐喻思维所缠绕,以致于人们只能看见其形而上的、经过升华之后的含义。为了回到事物本身,就必须拒绝隐喻。通过这一类例子,金理则看到了文学可能遭遇的一种处境:名教形成了一种思维上的压制机制,使得文学无法面对具体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而只是符号和观念的抽象演绎。因此,金理强调具体的感官参与对于创作的重要性,认为比之于哲学、科学,文学的最大长处在于它能够提供“实感”。“所谓实感,首先是指主体对‘具体事物和运动’的直接的、实在的‘经验’与‘感觉’”,“‘实感’力图呈现出具体事物和生活世界的原貌,昭示着一种‘回到事物本身’的力量;但它又并非是简单地如‘白板’一般无损耗地复制原貌(事实上这也没办法做到),‘实感’无法戒绝主体的介入,它本身就是一个同主客体‘融然无间’的化合过程紧密结合的概念。”②金理:《文学“实感”论:以鲁迅、胡风提供的经验为例》,《同时代的见证》,第154、158-159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文学“实感”论》虽然主要是以鲁迅和胡风的文学实践和思想实践来谈“实感”经验,但它也是金理本人的文学观念和运思方式的最好说明。从运思方式而言,金理是反本质主义的,不承认存在着一种具有普遍性质的真理,也不相信存在一种针对问题的一次性的解决方案。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金理则非常强调研究对象的具体性,不认为存在着一种包打天下的“武功”。那么,个人该如何具体地开展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呢?在《“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与“外部的批判支点”》这篇文章中,金理提出了他的看法。
这篇文章有个副标题叫“‘境况中’的文学及其释读”。“境况中”的文学指的是“处于特定历史时期内的文学作品、命题与思潮,其表述并未构成一个相对完备的系统,这并不是说‘境况中’的文学表述就不准确、不挑剔,‘而是说对这一准确和挑剔的认识没有一个处于相对封闭系统中的有机上下文为其提供特别条件,而只能把它置回该言述所依托的事件境况和话语境况中’,才能体会其意涵”。③金理:《“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与“外部的批判支点”:“境况中”的文学及其释读》,《青春梦与文学记忆》,第193页。在金理看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绝大多数的思想命题和文学,均属于这种“境况中”的知识型,它们都不具备“超社会”、“超历史”的有效性,并不是不受“世界观”制约的“纯理论”。面对这样一种思想命题与文学,金理强调后之来者应基于如下的原则或方法来进行研究:“首先‘设身局中’地了解‘境况中’的历史要素,在何种社会构成、意识形态与知识状况中,压抑性机制产生,其间人们曲折复杂的精神生活,他们把握了何种新起的契机,尝试了何种策略,获得什么样的效果与意义……对这些都应有‘了解之同情’与周彻观察。尤其是通过‘回置’来体贴在当日语境中所承担的机能与创造性,探析‘回置’所取得的经验在今天话语条件中是否具备转化、激活的资源与可能。其次,采取‘外部的批判支点’,照亮原有观察中的洞见与不见,将‘境况中’的特殊经验经由‘原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而‘向一般化开放’。”①金理:《“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与“外部的批判支点”:“境况中”的文学及其释读》,《青春梦与文学记忆》,第193页。
这样一种解释原则的确立,与金理的现代名教批判是暗合的。它们对于理解金理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来说,也许仍显得有些抽象,却是根本性的。在具体的研究中,他未必时时以此作为参照,但我们能借此理解金理大致的学术路向与批评路向。
三、多样的文学批评
金理的文学批评,也同样值得注意。
对象的多样和宽广,是金理的文学批评的一大特点。如刘涛所言,“金理对中国当代作家的论述视野广泛,他研究过王安忆、贾平凹、严歌苓、张炜、阎连科、迟子建等文坛中坚,也研究过盛可以、哲贵、甫跃辉、郑小驴等青年作家,大都持论公允,言之有物”。②刘涛:《80后批评家的时与命》,《大家》2014年第2期。他尤其是强调批评的同时代性,主张要与同代作家同步成长。③周明全对此已有详尽分析,这里不再重复。具体论述可见周明全《金理:同代人的批评家》,《大家》2013年第5期。在表达方式上,金理的文学批评也较为多样,不同阶段也有不同变化。
二〇〇三年,金理开始在《文汇报》写作“期刊连线”专栏,讨论彼时刚刚发表不久的、优秀的中短篇小说。这个专栏,一直持续到二〇〇六年。他为这个专栏所写下来的文章大多篇幅不长,写法上较为率性自由,有许多个人的新鲜感受和即时判断。理论思辨的成分,还有文学史的视野,自然也是有的,可是金理在写作时有意淡化之,以更为直接的方式说出个人对文本的看法,也借此为作家和普通读者牵线搭桥。
此后,金理还在《小说评论》杂志以“小说的面影”为题开设了两年的专栏,以盛可以、朱苏进、迟子建、余华、胡风等作家作品为例,讨论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与“期刊连线”相比较,这个专栏的文章显然加重了思辨的力度。比如,他曾经以盛可以和迟子建等作家的作品为例,来讨论现象叙事和价值叙事的区别,并重申价值叙事的意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曾经非常强调文学服从政治,强调小说在政治、道德教化方面的功能,严重地损伤了小说叙事的可能性与丰富性。作为对这一观念的反叛,不少作家后来倾向于认为作家的天职仅仅在于发现并揭出生存的真相,而无需给予读者任何的慰藉,甚至认为写作跟道德或政治完全是没有关联的。这未尝不是一种矫枉过正,是从一种偏至走向另一种偏至。针对这些问题,金理有很多精彩的论述。尤其是在《温情主义的文学信仰》一文中,他将迟子建视为“价值叙事最为出色的论证者”,“迟子建的创作指向生活的‘应然’,指向‘另一种生活和世界观’:无论在何种境遇里,你都可以选择;而你的选择,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价值叙事的意涵中,人们决意过一种符合伦理的生活,决意成全人性,人们感到需要有一种比现在更美好的生活、更健全的人性。更重要的是,价值叙事相信人们有能力争取上述两者的实现,这是可能的”。④金理:《温情主义者的文学信仰:以迟子建的创作为例》,《一眼集》,第147页。这样的阐释,不仅为理解迟子建的创作提供了独到的视角,也有助于作家们调整视角,转变观念,形成更为整全的精神视野。自然,作家可以选择成为无预设的“现象学家”,面向事物本身,写出事物复杂、暧昧的全体。但是,在面对这个参差多样的世界时,作家还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伦理立场与实际承担。真正好的作家,总是既能写出恶的可怕,而又能让人们对恶有所警惕。只有当一个作家既不刻意简化“现实的混沌”,又始终有自己的伦理立场和道德意识,他才真正建立了自己的、健全的主体性。也只有兼顾这两个方面,作家才不会在虚无中下沉,读者也才能从中获得教养。
“小说的面影”专栏中的文章,虽然在体例上显得较为学术化,读来却有直指人心的魅力。与之相比,《反躬自省的“医生”与拒绝被动的“病人”——从这个角度讨论文学中的医疗与卫生话语》、《〈平原〉的虚和实》与《心态•身份•际遇——小说中的阅读史分析》等文章对作家作品的解读,还有对相关问题的阐释,要更为学术化。它们都不是感悟式的、印象式的解读,而是非常注意借鉴前沿理论,或是将作品放在文学史或思想史的视野中进行打量,也注重引入其他学科的话语。由此也可以看到,金理的文学批评有非常学院化的一面。这种批评特色的形成,跟金理的经历不无关系。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金理都是在复旦大学度过的,毕业后又留校任教。长期浸润在复旦大学深厚的学术与人文传统中,恒定的学院生活,使得金理会注重与学院的同行进行对话,也多少会受到学院学术体制与批评体制的塑造与影响。
在《古代哲学的智慧》一书中,法国哲学家阿多曾这样谈及今天之大学学院生活的状况:“大学机构倾向于使哲学教授成为公务员,他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在于训练其他公务员。大学的目的不再像它在古代时的目的那样,训练人们作为人去谋生,而是训练他们作为职员或者作为教授的职业生涯——就是说,作为专门人才、理论家和多少是隐秘知识特别细节的保存者。然而,这样的知识不再与生命整全有关,就像古代哲学所要求的那样。”①[法]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281、282页,张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阿多注意到,现代哲学家普遍倾向于将哲学看成是一种有体系的理论科学,“从黑格尔到存在主义兴起,随后是结构主义的风行,观念论对整个大学哲学的支配,极大地滋养了这样的观念——只有理论的和体系的,才一定是真正的哲学”。②[法]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281、282页,张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的确,重视理论,重视知识学的建构,重视方法论的探寻,是现代以来学术研究的特点,也是学院批评的重大特点。阿多所说的“观念论”的支配性作用,在文学批评尤其是学院批评中,其实也是随处可见的。尤其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院批评家普遍开始重视借鉴海外汉学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模式,藏匿、克制、牺牲个人的性情与感悟,加重理论干预的力度,注重遣词造句的“严谨”、“规范”,力求“科学”、“客观”而诉诸具有抽象性与普遍性的术语范畴,文学批评甚至还大面积地转为文化批评。这些尝试,并不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错误的。比如说对理论的重视,理论作为系统的观念体系,运用得当的话,是可以给阐释问题营造视角,新人耳目的。至于重视知识学和方法论的建构,得当的时候,也可以让批评活动和学术活动走向纵深。这种运思方式不好的一面,则是使得不少文章存在着理论过剩、术语超载、言词晦涩等问题;等而下之者,甚至成了自我封闭的知识生产,繁琐无聊的概念演绎,沦为一种门槛很高的、复杂的话语游戏,一种在体制内赢取象征资本的手段。它最大的危害,则是让学术活动或批评活动成为一种僵死的学问,而跟“生命整全”没有什么关系,研究者和读者都不能从中获得生命层面的教益。
对于学院批评的这些负面作用,金理是有所反思有所警惕的。比如对于文化研究,他也写过类似的文章,却很快就注意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此后不再涉足。对于学院批评其他方面的得与失,他也有自己的认识。他试图入乎学院批评之内,将学院批评话语的效能发挥到极致;同时又出乎其外,不受其藩篱约束。这种审慎和清醒,的确给他的批评带来了不一样的面目。
四、一以贯之的学术理想与批评理想
金理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无疑具有独立的意义,值得重视。同样不应该忽略的,是他“压在纸背的心情”。是将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视为一种纯粹知识学式的思辨活动,从知识到知识,从学术到学术,从纸上到纸上,还是在此之外,也强调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之于人生、之于生活世界的意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向。读金理的文章,让我时常有认同感的,除了他针对某些问题的具体看法,还在于他很好地兼顾了上述两个方面。不管是关于现代名教研究也好,还是社团研究和青年构形研究也好,最终都能返归自身,回落到生命层面。也就是说,在进行知识论方面的梳理或建构的同时,他也会重视学术活动和批评工作在存在论层面的意义。
这里不妨举个例子:张新颖教授在《见证一个人的成长》这篇文章中曾经谈到,在参加金理的博士论文答辩时,曾提醒他“论文都是在一个方向上分析(章太炎、鲁迅、胡风),而在二十世纪以来的思想和文学中,名教批判的脉络不止这一脉,还有别的方向的批判”。①张新颖:《见证一个人的成长》,引自金理《同时代的见证》,第2页。此后,金理一直尝试放宽视野,从之前所忽略的方面入手继续梳理这一问题,以至于博士论文迟迟没有出版。经由这个细节,多少能看出他在学术态度上的严谨,以及他的情怀所在。迟迟不肯交付出去,是为严谨;最初都在“同一个方向用力”,正是因为研究对象的言路与金理本人的心路是契合的,是心之所念,读之砰然心动,才会格外重视。
而金理的文学批评,其实也是自觉地往重视认识论和存在论的贯通这个方向走的。他曾这样谈到自己的批评观:“文学批评是我个人的生命和文学发生关系的一种方式。它关涉着‘生命的具体性’……所谓‘生命的具体性’,在我的理解,是不将‘个人’凝固成一个自外于现实世界、一尘不染的封闭‘自我’,而是置身于纷繁复杂的现实(哪怕它们是平庸、烦琐的)中,通过‘完成切近的具体事业’来沟通、担负个人在现实世界的责任,而文学批评正是这样一种‘具体事业’。这个时候,批评(好的文学同然)应该化成批评者的血肉存在,甚至是一种生命机能,‘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见证其在岁月流转中的生命履历,表达批评者浑然的存在体验,个人对现实社会和宇宙全体的直面与担当。”②金理:《“新鲜的第一眼”与“生命的具体性”》,《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视批评为“个人的生命和文学发生关系的一种方式”,不断地学与思,以言行事,既增进学术层面的理解,也借此丰富对个体生命的自我认知,所强调的,正是批评在存在论层面的意义。
除了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金理现在也在从事文学教育和编辑学术刊物等工作,身份日益丰富,但变之中也有其不变的所在。学者赵园在谈论黄宗羲时,曾有这样的评议:“在黄氏,正是心性之学提供了学术的意义源泉,使学术境界与生命境界合致;而那种‘江汉源头酣歌鼓掌”式的精神发越、情感陶醉,应是其后的乾嘉学人所难以体验的吧。”③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4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对于金理来说,始终不变的,一以贯之的,也许正是他有志于成为一个“文学性知识分子”的本色与初心;而使“学术境界与生命境界合致”,使“人”与“学”合致,也正是金理所一路寻求与坚持的。我想,这种日渐增进的合致,学术、批评与生命的互相成全,会越来越成为金理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的魅力所在。
(责任编辑刘浏)
李德南,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学哲学系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哲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兼任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评委、广东作协签约作家。曾发表各类文章约六十万字,著有《途中之镜》、《遍地伤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