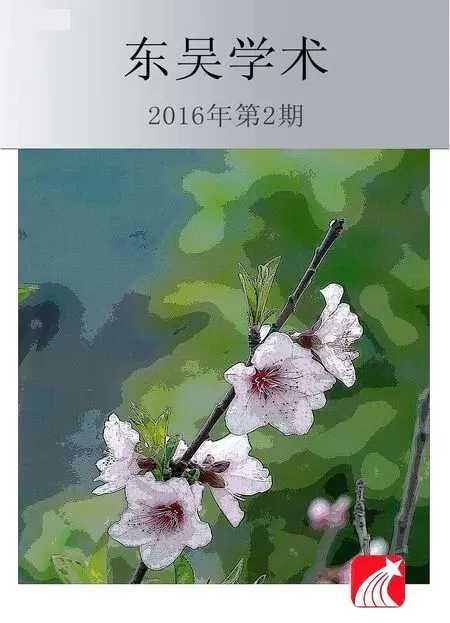杨键与统计美学
[美]罗鹏(Rojas Carlos)
杨键与统计美学
[美]罗鹏(Rojas Carlos)
本论文考虑张大力、艾未未、以及杨键的一些作品,认为他们都用一种匿名化的过程来关注或纪念一些边缘性的人物,像当代城市里的民工或五十年代饿死的人。换言之,在本文所分析的作品中,这些艺术家跟作家先把边缘性的人物看成一种匿名化的群体,然后通过这个群体表现他们试图重新面对原来人物所代表的意义。本文管这种表现与观察的方式叫“统计美学”。
杨键;张大力;艾未未;匿名化
二〇〇三年张大力曾进行一个规模很大的艺术创作。他用民工当作模型,创作了将近一百件真人大小的树脂人体雕塑,然后就以这些裸体的雕塑做成展览。结果就是呈现了一种十分典型的就弗洛伊德所说的“诡异”(德文的“unheimlich”,英文的“uncanny”)的感觉,因为雕塑既非常陌生(张大力经常把这些无生命的人体雕塑倒挂在展厅中),却也同时古怪地熟悉(雕塑毕竟是非常逼真的人体像)。
作品名为“种族”,张大力的这个雕塑系列表现的是一个抽象化与匿名化的过程。一方面,每个雕塑都是以不同的民工的身体当作模型,如兵马俑,每个雕塑的表情与姿势都不一样。因此,每个雕塑都可以被看成一种个人的表现。在另一方面,每个雕塑是通过一种匿名化的过程造成的。每个雕塑上看不见原来做成模型的民工的身份,而张大力在每个雕塑上都烙上同样的印记:作品版数号,作品名,以及张大力自己的签名。

张大力 种族
“种族”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作品刚好是通过这种匿名化的过程——通过它强调雕塑与现实模型之间的距离——它才能够非常有效地指出当代中国民工的处境。这是因为虽然每个民工都拥有自己的身份、背景、家庭等等,他们却在当代中国经常被看成是一种无名的群体。处在城市的边缘,中国的民工经常被看成一种无名的体力。正刚好用一种类似的匿名化的过程来关注浙西民工的状况,引起观众去注意这些民工正在面对的苦境。

张大力 种族
二○○八年四川地震以后,艾未未进行了一个接近一年的调查,试图查到每位死在地震的学生的具体数据(学校、姓名、年龄、班级、家庭住址、家长联系方式)。艾未未二〇〇九年用九千个学生背包,覆盖了德国慕尼黑艺术馆的外墙,以此悼念四川地震中死掉的学生,他也以儿童背包做了一种纪念性的艺术作品,以九千个不同颜色的背包代表在地震死掉的几千个同学。虽然这些背包直接象征死掉的孩子,不过作品也是通过一种匿名化的过程造成的,因为每个背包也是匿名的,不代表任何具体的孩子。同时,刚好是由于这种匿名化的过程作品才可以有力地纪念那些被地震埋葬的一群孩子。
发展于十九世纪的统计学也依靠类似的一种逻辑。统计学是把具体的事实数据化,以便用这些抽象的统计来对现实得到一种更完整,更全面的了解。对于人口来讲,如果观察的人只依靠他们亲自认识的人的具体信息,就无法得到一种可靠并且完整的对社会的了解,不过如果先用统计学的方法把人口匿名化跟抽象化,就可以对自己社会得到一种更客观的了解。这样看来,张大力跟艾未未前面所描写的两部作品都利用一种美学化的统计学逻辑。虽然作品强调的不是一种数据分析,不过他们依靠的匿名化过程刚好也是统计学的关键前提。
虽然杨键在二○一四年《哭庙》关注的不是当代中国的民工或汶川地震中的伤亡,而是五六十年代被历史忽略的人物,但他利用一种很相似的匿名化做法引导读者关注一段经常被忽略的历史与历史人物。长达几十万字的一部“史诗”,《哭庙》纪念的是土地改革时期的一群伤亡者。
书被分成上、中、下卷,名为“哭”、“庙”、与“庙之外”。特别是中卷以一种坟墓上碑铭的形式来纪念那时期的伤亡者。中卷中名为“东墙”的部分有许多以“某某之墓”为题的诗。比如,“地主高士楠之墓”:
他们说我有罪,说我的罪是
经常去万寿寺,取梅花上的雪,
埋入地下,来年做糕点,
他们说这个罪是很大的。(65)
还有,“地主严宗周之墓”:
你来了,
我活在一条裂缝里,
这是一条多么狭窄、破败、可耻的裂缝啊。
我曾经撞死在你面前来震撼你的可耻。
我曾经是一只蟋蟀,
在古瓮里,
除了天地,谁也不往来。
你来了,
一条路,
背起母亲去逃亡。(65)
还有,“地主王文兴之墓”:
我一无所有地走在偷偷回老家上坟的田埂上,
田埂上散着一股浓重的丧乱味。
我跪倒在父母坟前,
无法说清被毁灭的家的痛楚。
我跪下时感到有个人
跟着我跪下。
我站起,
他也跟着站起,
清秀温润,智勇双全,
好像是我几十年前的仆人。
他死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还跟着我?
他不是那天被打死了吗?
我重又跪下,
遥祭这一份忠心。
我的国家是我的魂,
我的仆人是我的魄,
我已魂飞魄散了,
只能长跪不起。(66)
虽然这三首诗都用伤亡者的(虚构的)姓名为题,其余的诗有好几首甚至具体的姓名也没提。比如,“一个婴儿之墓”、“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儿之墓”、“一个六岁小女孩之墓”、“一个十一岁小女孩之墓”、跟“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之墓”。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匿名化的过程,先用一些虚构性的人物纪念当年所谓的“地主”的伤亡者,然后用一种无名的方式纪念当年儿童的伤亡者。
中卷中名为“西墙”的部分用类似的形式来纪念当年的所谓“犯人”伤亡者。比如,“西墙”的诗包括“地主姚政之墓”、“地主焦恕之墓”、“犯人王永寿”、“犯人吕复白”、“犯人挑牙虫者之墓”、“犯人汪斋公之墓”、“犯人白春仁老人之墓”、“犯人敬一师”、“犯人刘姓戏子之墓”等等。虽然这些诗都是以(虚构的)姓名为题,不过体味“塔”的部分有一首题为“犯人”的诗:
一九五一年在淮河挑土,
一九五二年妻子来信离婚。
四年后,
去内蒙古,
挖包兰铁路,
每天,
开山,挖土方,修铁路,
漫长的六年呀,
只因他给一个杨姓国民党军官的女
儿做过英文家教。(198)
虽然这首诗的题目没有提到具体的姓名,不过诗有个诸事说明诗的内容是来自于历史记者白伟志的一本名为“一个镇反人员的别样人生”。
这“塔”的部分有许多其他关于所谓的“犯人”的诗,有一些提到具体的(虚构的)姓名,也有一些的关于无名的“犯人”,比如:“刘姓犯人”、“小犯人”、“犯人常德谱之墓”、“犯人高思诚老人之墓”、“犯人赵开聪”、“犯人季在诚之墓”、“犯人刘尼姑”、与“犯人孙其”。
还有一首名为“犯人们”:
死的收银台里,
坐着一个长得像妇人一样的男人,
他给我们每一个人
发号码——
十号,
十一号,
十三号,
二十号。
我们
每个人的胸前
都挂着自己的号码。
我低下头来,
看着我的号码。
我记住了这号码,
如同我记住了小时候的座位。
这号码特别小,
在我的脑海里又特别大,
逐步逐步
淹没了
我脑海里的国土。(203-204)
这首不仅是以一个无名的主题,而且其内容描写的刚好是一种匿名化的过程:叙述者以给犯人发号码的过程比喻成给学生定座位。
这种匿名化的过程表现的很明显在“钟鼓楼”的一首名为“没有碑”的一首诗。这首挺长的诗提到许许多多历史任务,都是五六十年代饿死的,埋葬的时候都没有碑:
刘向东饿死时,
没有碑。
杜文化饿死时,
没有碑。
王仲英饿死时,
没有碑。
黄和凤饿死时,
没有碑。
邓文星饿死时,
没有碑。
王宝怀饿死时,
没有碑。
李占元饿死时,
没有碑。
周文立饿死时,
没有碑。……
章宏根饿死时,
没有碑。
陈士达饿死时,
没有碑。
那个年月,
怎可能有碑?
现在也没有。(215-217)
这是伤亡者都落在历史缝隙中,没有碑,而这首诗本身刚好在替代伤亡者本来没有的纪念碑。换言之,这首诗首先强调伤亡者经过一种匿名化的过程——死掉以后因为没有纪念碑所以很容易被历史忘掉——而同时也在纪念他们,确认他们所代表的历史事实。
在名为“大殿”的部分中,全书最长的一首诗,“我的愿望之十”也表现类似的一种逻辑。这首诗总共有一六一行,每行都有同样的结构,都提到那段时期死掉的所谓的“地主”、“犯人”或“饿死鬼”,包括许多《哭庙》已经提到过的(虚构)人物:
我愿死去了但是没有安息的地主高士楠从此安息,
我愿死去了但是没有安息的地主严宗本从此安息,
我愿死去了但是没有安息的地主王文兴从此安息。(161-171)
这样,这首诗强调这些历史人物死掉后“没有安息”,而且被忘掉,而同时在用诗本身纪念他们,给他们提供一种象征性的“安息”。
“我的愿望之十”强调的不仅是这些几十位“没有安息”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当作叙述者的“我”。杨键在《哭庙》中的另一首诗,名为“两个梦”,对这个“我”作了更深的探索:
我梦见自己是一滴晶莹的雨,
落在蟾蜍苍老的怀里,
我还梦见我家院子里的大缸开口说话了,
在墙角那么多年它一句话也没说过。
醒来后我对我面前的松树感觉到陌生,
对我自己也感觉到陌生,
我好像是路边遗失的一只鞋子,
又像是小时候在我舅舅家经过的墓地。
墓地很大,很多坟集中在一起,
密密麻麻,不知有多少。
在你降下的灾难里,
我还没有醒转过来。
这首诗中,叙述者的“我”以及自己的环境都被匿名化,变成一种陌生的他者:“对我自己也感觉到陌生”,不过跟弗洛伊德所说的“诡异”一样,这种陌生感却也包含一种超级熟悉的感觉,因为这个“他者”确实是自我的反面。
张大力艺术中也有同样的特点。他开始“种族”系列之前,他最有名的作品创作是九十年代名为《对话》的艺术活动,在北京废墟墙壁上画了一种代表自己的匿名人头像。
通过这一系列的匿名人头像,艺术家与自己的社会环境并且跟艺术家自己能够进入一种(反讽的)“对话”。换言之,跟杨键一样,他是通过一种匿名化的过程就对自己以及自己的社会环境能得到一种更完整的并且更尖锐的理解与反思。

张大力 对话与拆
罗鹏(Carlos Rojas),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美国杜克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近现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研究。出版专著 有The Naked Gaze:Refl ections on Chinese Modernity(《肉眼:反思中国现代性》)(哈佛,一九九八)、The Great Wall:A Cultural History(《长城:文化史》)(哈佛,二○一○)、Homesickness:Culture,Contagion,and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离乡病:现代中国的文化、疾病、以及国家改造》)(哈佛,二○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