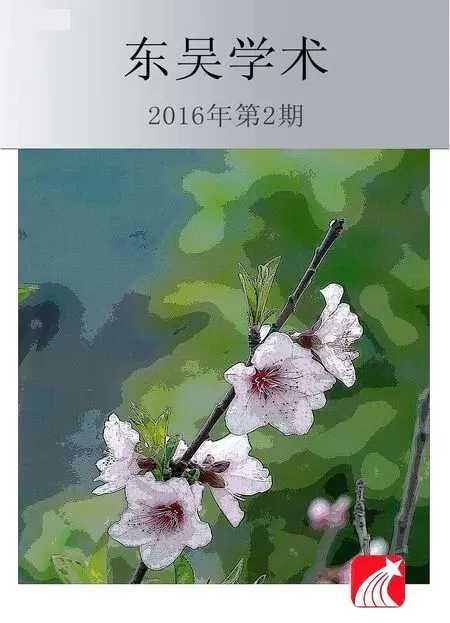翻译虚构类作品/翻译诗歌
[法]林雅翎(Sylvie Gentil) 著 黄雅琴 译
翻译虚构类作品/翻译诗歌
[法]林雅翎(Sylvie Gentil) 著黄雅琴 译
诗歌建立在其他规则之上,它自有其构成规则,散文对此并不陌生,但对诗歌而言则是最根本的,因为这些规则直接脱胎自诗歌的本质。粗略说来,诗歌包含了形式以及意义。散文也是,但诗歌的形式和意义会相互作用,意义建立在形式之上。节奏、音色,甚至还有韵脚(如果这首诗歌有韵脚)都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构成要素都是译者无法绕过的坎。
音乐;节奏;情感
翻译一本小说,翻译一首诗歌,从根本上来说难道不是一回事?所有文本,不限题材,难道不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和润色?翻译小说和翻译诗歌不都需要字斟句酌,力求精确,既忠于原文的风格,还有对原汁原味的敬畏?
只是……平心而论,这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两种入手方法完全不同的工作。诗歌建立在其他规则之上,它自有其构成规则,散文对此并不陌生,但对诗歌而言则是最根本的,因为这些规则直接脱胎自诗歌的本质:视觉感观方面,尤其是西方语言,我们常常很难复制;从口语角度看,所有(好的)文本都能经人背诵、朗诵,所以无法提供完全的对等翻译,除非是情感上的对等。
“同一篇文章交给十名翻译,你会得到十篇不同的译稿。”我们常这么说。翻译诗歌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译者的主观性在其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撇开译者的个人感受不谈,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时间维度:每位译者脱离不了生活的时代,每位译者是在为同代人翻译。因此,时代变迁,我们会看见不同版本的唐诗翻译,在我看来,都非常优美,但两相比较也别有一番趣味。第一批唐诗译本,据我所知,源于一八六二年……
下文的译本选自《唐朝诗歌》(根据一九七七年Champ libre出版社的版本),Hervey Saint-Denis侯爵将杜甫《梦李白》头两句诗“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译作:
Si c’est la mort qui nous sépare,je devrais rendre ma douleur muette;(如果死亡将我们分离,我会让我的痛苦缄默;)
Si nous ne sommes séparés que par la distance,mon chagrin doit élever la voix.(如果生离将我们阻隔,我的悲切会提高嗓门。)
一百年后,Jean-Pierre Dieny和Yves Hervouet(《中国传统诗歌选》,伽利玛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出版)一脉相承:
La mort m’ôte-t-elle un ami,j’avale mes gémissements;(死别夺走了我的一位朋友,我咽下呻吟;)
Si c’est la vie qui m’en sépare,je le pleure indéfi niment.(生离将我和他阻隔,我为此泪流不止。)
二〇一五年出版的《中国诗选》(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Florence Hu-Sterk则译为:
Séparés par la mort,sanglots ravalés;(死别,强忍抽泣;)
Séparés par la vie,tourment infi ni.(生离,无止尽的折磨。)
即使不懂法语,我们也能立马听出差别!前面两个版本差异较小,不过第二个的两位译者多注意在忠于原文的努力上又力求精炼语句。此外,他们也注意到了视觉感受:通过逗号来标出诗句的节奏,而逗号也能制造出中文版隐含的顿挫效果,第二个法语版还保持了和中文版同样的音步数。两位译者还是遵循前辈的逻辑,比如,都不约而同地加上了“我”,而中文是会巧妙地省去这个“我”,两人的译本力图靠近法国诗歌中所谓的“美”的理想形式。第三个译本就很现代了,我们马上明白到,语言在进化,翻译理念同样如此。那个大名鼎鼎的“我”消失不见了。这样的诗句在耳畔响起,当然是更加“悦耳动听”:可以说,这是文化全球化的一个积极效果,我们学会了收敛自己的语言,让其贴合源语言,教会它尊重源语言的独特之处,并让读者感受到这种独特(中国诗歌作为一门艺术得以发扬光大并且形成理论化,这尤其要感谢陈抱一先生,一九七七年他在门槛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诗语言研究》)。散文也是如此,我们的翻译法在进步,革新领域也前所未有的广阔:重译的译本试图使用现代化的语言来贴合原文,消弭译者(或出版社)在文本中任意妄为造成的断层,而这种任性的行为在不久前还是存在的。
在不同的目标语言之间,翻译方法和译者的主观意志也千差万别。二〇一四年,我在为《Traductiere》杂志工作时,他们出了一本三语版(中、法、英)的中国诗歌特刊,我通过翻译太阿或者胡续冬的诗歌得以验证了自己的看法。散文完全是另一码事:如果我用另一种语言阅读我翻译的书,除了细枝末节的差异,法文和另外的译文是没多大不同的。经过翻译的诗歌则会让作每个译者的语言天赋立马有了高下之分。(经过翻译的诗歌让每一个语言的特有天赋表现的更明显,或者说,把它赞扬?)
粗略说来,诗歌包含了形式以及意义。散文也是,但诗歌的形式和意义会相互作用,意义建立在形式之上。节奏、音色,甚至还有韵脚(如果这首诗歌有韵脚)都有决定性作用,这些构成要素都是译者无法绕过的坎。
遗憾的是,鉴于目标语和源语言在语言学上的差异,翻译抑或诗歌的传输只能是有限度的行为。音色不会一样,而我们工作的本质,诚如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转输出最大的相似性,不一定能传递出原诗的音乐感,但至少要用另一种语言学体系来表达出那种情感。
我们需要不断地做出抉择。有节奏还是没节奏?是放弃节奏来贴合内涵,还是通过准押韵来传达出那种音乐感?翻译古典诗歌时,是否该相应地采用工整的法语古诗体,还是选择自由体?第一种解决办法会造成一种又常常陈腐老套又假的熟悉感,它在形式上太过法语化……第二种,唉,无法表现出绝句或律诗在视觉上的美感。
以杨键最新的诗集《哭庙》为例,其中的《七咏》开头这样写道:
如此之多的人眼、牛眼、猪眼、婴儿眼没有闭上,
如此之多的是非善恶没有分清,
如此之多白天如黑夜,
如此之多的怀疑、恐惧、出卖、告密、揭发、判决……
如果是散文,翻译起来就方便得多。只要找到一个一个相似的字,经过润色之后,就能得到:
Tellement d’yeux,d’hommes,de bœufs,de porcs,de nourrissons qui ne sont pas fermés,(如此之多的人眼、牛眼、猪眼、婴儿眼没有闭上,)
Tellement de confusions entre le vrai et le faux,le bien et le mal,(如此之多的是非善恶没有分清,)
Tellement de jours semblables à la nuit,(如此之多的白天如同夜,)
Tellement de doutes,de terreurs,de trahisons,de délations,de dénonciations,de verdicts…(如此之多的怀疑、恐惧、出卖、告密、揭发、判决……)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所在,无论是眼观还是耳听,译文都是另一码事了,译者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翻译。我们不过还有“运气”,因为原文是自由体,不用考虑韵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现代诗歌下的一个赌注:需要更加精确地还原原文情感。
警惕各个诗句之间的长度关系。
甚至还要一丝不苟地遵从标点符号,应该是照搬,不仅出于视觉原因,还有音乐的缘故,因为标点能带来节奏。让我们看看,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有哪些方法可以让诗句更加忠于原文。
第一句有点过长。如果中文是一句话,那译文就该略微精简。
Tous ces yeux,d’hommes,de bœufs,de porcs,de bébés grand ouverts,(所有的人眼、牛眼、猪眼、婴儿眼都睁开着,)
修改后的译句既合了原文的意思,又有了节奏感:无论是听觉还是视觉,不同词语之间达成了平衡,保住了原文的识别度。从译者角度来看,这句话不难翻……尽管bébé在意思上更接近“宝宝”而非“婴儿”,但含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至于用tous ces(所有的)替代tellement(如此之多的),只是稍微加强了含义而已。为了减少音步数,更好地发挥法语中的音乐性,我没有逐字逐句地翻译成“没有闭上”,转而选择将含义稍稍“滑移”(以我的感悟,我认为法国读者会觉得这样的译句更有感染力),翻成了“睁开”。
第二句的难题是:如果将“没有分清”直接译成confusion,confusion是个阴性名词,要用toutes ces,而不是tous ces,这就会破坏句首的一致性,既不漂亮,也不忠实。必须要找到一个近义词,一个类似的词。遗憾的是,我无法保持原文中限定词—被限定词的顺序,法语只能颠倒过来。此外,第二句应该比上一句更短。
Tous ces quiproquos entre mal et bien,vrai et faux(所有善恶是非张冠李戴)
虽然法语结构有点破坏了节奏,这是逗号的过失,但逗号在法语中是必须的,无法替代。如果说中文能轻而易举地混用,法语多数情况下是办不到的,如果不是译诗的话,这个难题会显得更加棘手。
Tous ces jours semblables aux nuits,(所有白天如黑夜,)
不做修改,译句像是浑然天成出自源语言,很难想出另一种译法。但还是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点东西:当中文说起“白天”、“黑夜”,在法语中是不会联想到“jours blanc”(白色的天)和“nuits noires”(黑色的夜)。
第四句是最难翻的。我们听得十分真切,一个一个单词笨拙地放在一起,丝毫没留出缓口气的间隙,节奏全无。译句太长,中文是两个字的词组,而法语变成了三个音节的单词,译句顿时变得平庸之极。还要筛选一堆近义词和相似词,但法语词汇自有其限制,我们不得不面对痛苦的选择,也只能让自己凑合过关。首先,省去指示形容词,除了第一个,因为是必须的(要符合语法规则),但这样处理之后倒是让法语版的前几个单词拥有了近似中文的双拍子:
Tous ces doutes,ces effrois,ces parjures,…(所有的怀疑、恐惧、出卖)
接着,因为别无选择,只能用了两个三音节的名词(但没用指示形容词,这能减少破坏),再跟上双音节名词verdict(判决),这个强有力的单词能突出诗句的含义,名词前面的et(和)和ces(这些)能进一步烘托verdict(判决),同时实现了整句句子在视觉上的平衡。
… cafardages,délations,et ces verdicts.(告密、揭发,和这些判决。)
这样翻译出来的仅仅是初稿,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会继续润色、修改,但译本呈现出的形式和节奏已经非常接近和忠于原文,在含义和精神上皆是如此:
Tous ces yeux,d’hommes,de bœufs,de porcs,de bébés grands ouverts(所有的人眼、牛眼、猪眼、婴儿眼都睁开着,)
Tous ces quiproquos entre mal et bien,vrai et faux,(所有善恶是非张冠李戴)
Tous ces jours semblables aux nuits,(所有白天如黑夜,)
Tous ces doutes,ces effrois,ces parjures,cafardages,délations,et ces verdicts…(所有的怀疑、恐惧、出卖、告密、揭发,和这些判决。)
这只是一个草稿:译诗需要反复推敲,字斟句酌,一边生活一边翻译。理想状态下,再短的文章最好是半年后再看,最长一年。在脑海的某个角落里,为这首小曲辟出空间,时不时地有一个点子福至心灵,在经过反复尝试之后,或许某天就有了最终版的译稿(总会觉得差口气),但至少会有一时片刻的心满意足吧。
【译者简介】黄雅琴,上海译文出版社。
林雅翎(Sylvie Gentil),法国人,中国文学翻译家,从一九八五年以后常住北京,曾翻译了莫言、徐星、棉棉、阎连科、刘索拉、冯唐等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二〇一〇年,她因翻译了中国作家阎连科的作品《受活》获得了法国阿美迪•皮肖翻译奖,该书由菲利普•皮基耶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出版。最近翻译发表有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全文,李珥的《花腔》和阎连科的《炸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