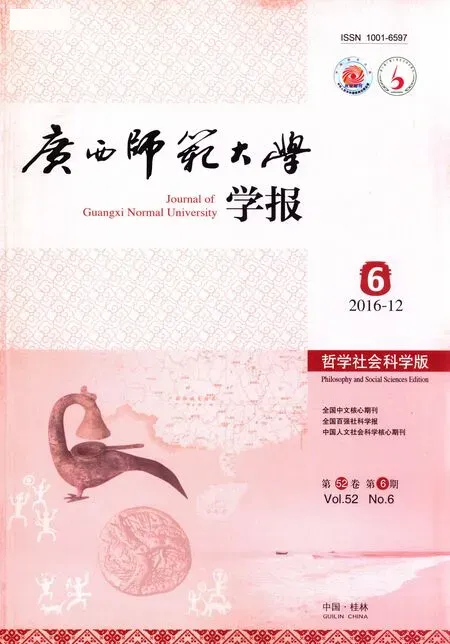论《文选》与《文心雕龙》工作量之可比性诸问题
力 之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论《文选》与《文心雕龙》工作量之可比性诸问题
力 之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文选》与《文心雕龙》因性质不同,故难以比较两者工作量之大小如何。然《文选》与《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却有着切实的可比性。编纂《文选》的工作量要远小于撰写《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的。完成同一工作量虽会“因人而异”,然在两者有可比性的部分,不管从哪一角度看,其均无太多之“异”。即昭明太子编纂《文选》所花时间仍相应地要比彦和撰写《文心雕龙》的少。撰写《文心雕龙》要比人们想象的费时,而完成《文选》的工作量与难度则被某种程度地放大了。
《文选》;《文心雕龙》;昭明太子;刘勰;工作量
弄清楚《文选》编纂工作量的大小如何,对深入研究《文选》的编者问题、成书情况以及古代诗文总集的编纂情形,均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然对这一问题,向似没有学者进行过具体的研讨。笔者此前虽撰写过《关于〈文选〉编纂“工程”的大小问题》[1],然该文仅着重于通过将《文选》与《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中的“选文以定篇”比较来考察《文选》编纂“工程”之大小,至于这两书在工作量方面的可比性问题与同样大小的工作量如何因人而异方面的情况,以及撰《文心雕龙》之工作量远大于编纂《文选》之其他相关证明如何,则没有展开研讨。故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另作一文以究之,以奏“1+1>2”之效,以更好地破解这一难题。
一、关于《文选》与《文心》工作量之可比性问题
众所周知,《文选》是诗文选集,而《文心雕龙》乃理论著作。故乍一看,从工作量的大小这一层面上说,两者似无什么可比性。不过,就两者之整体言虽如此,然整部《文选》与《文心雕龙》的“论文叙笔”部分却具有切实的可比性。《序志》篇云: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2]1924-1930
观此,便不难明白:不管是就《文选》整体还是其中的某部分,其与《文心雕龙》之《原道》《征圣》《宗经》《正纬》《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镕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养气》《附会》《总术》《时序》《物色》《知音》《程器》等20多篇,两者着实难以比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均缺乏可比性。因之,我们要比较也实在比较不出什么来。《墨经》云:“异类不吡〔比〕,说在量。”[3]215此之谓也。近人谭戒甫先生云:“推类致误,多由于异类相比之故。常人见理未真,动将渺不相涉之事物,杂糅牵合,认为同类而相校比;以致乖谬丛生,不可究诘。若知异类不比之理,则推类之难,当可大减。”[3]216-217是的然发其“微”矣。然尽管如此,这正如三国时无称“巨象”之称,而曹冲以“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之法,却能“校可知”[4]卷20之一样,我们据“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说衡之,便知《文选》与《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明诗》第六至《书记》第二十五)有着实实在在的可比性。又,毛庆先生在其一殊厚重的书中,分别比较了屈原与孔子、老子、韩非、墨子的文化心理[5]63-103,十分出色,“而方法论之意义存焉”[6],是亦一极佳的例子。
当然,我们知道此整体与彼部分之比较是不对称的。问题是,通过这一比较,却能证明编纂《文选》的工作量小于撰写《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的,而这一结论不仅对我们探究《文选》编者诸问题有着重要而独至之意义,对探究刘勰撰写《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的情况亦有特殊的价值。可惜的是,不管是在“选学”界还是在“龙学”领域,似向均没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而究之(牟世金先生曾认真考察过《文心雕龙》的撰写情况,其所说多有价值[7]52-54,然那是另一回事)。
二、撰《文心》之工作量远大于编纂《文选》补说
上面,我们说《文选》与《文心雕龙》的“论文叙笔”部分有切实的可比性,且此前笔者主要在“选文以定篇”的范围内,曾具体细致地比较过这两者。[1]下面,拟再在“论文叙笔”之“域中”举例以补说这一问题。
关于《序志》篇之“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说,黄季刚先生曰:
“原始以表末”四句:谓《明诗》篇以下至《书记》篇每篇叙述之次第。兹举《颂赞》篇以示例:自“昔帝喾之世”起,至“相继于时矣”止,此“原始以表末”也。“颂者,容也”二句,“释名以章义”也。“若夫子云之表充国”以下,此“选文以定篇”也。“原夫颂惟典雅”以下,此“敷理以举统”也。[8]221-222
这是恰当的。试看《颂赞》篇,其“颂”的部分如下: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释名以章义”)
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备。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雅容告神谓之颂。风雅序人,故事兼变正;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鲁以公旦次编,商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燕飨之常咏也。《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高,并谓为颂,斯则野颂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原始以表末”)
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深浅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又崔瑗《文学》、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及魏晋杂颂,鲜有出辙。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选文以定篇”)
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敷理以举统”)[2]313-335
我们此前将《文选》“颂”“赞”“史述赞”三体与《文心雕龙·颂赞》作了比较,后者主要限定在“选文以定篇”内。然即使如此,“综而衡之,舍人为此,务巨于昭明太子为彼”。[1]而无此限定之各类比较如何?结果不言而喻。这里,我们再就《文选》“颂”体与《文心雕龙·颂赞》之“颂”(仍以“选文以定篇”为“域”)略加比较:前者收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杨子云《赵充国颂》、史孝山《出师颂》、刘伯伦《酒德颂》与陆士衡《汉高祖功臣颂》共5篇作品,后者则见上面所引《颂赞》之“颂”的第三段。两者均涉及《赵充国颂》与《汉高祖功臣颂》,即彦和于此没有提及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史孝山《出师颂》与刘伯伦《酒德颂》三文,却比昭明太子多做如下工作:一,考察“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之所本,而断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二,说明“班、傅之《北征》《西征》”何以“谬体”、“马融之《广成》《上林》”怎么“失质”,而“崔瑗《文学》、蔡邕《樊渠》”能“简约乎篇”;三,辨“挚虞品藻”之得失(“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云云,则为彦和之未为得[9]);四,概论“魏晋杂颂”的情形。当然,其说有本之挚虞者,《文章流别论》论“颂”有云:
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鄂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10]卷588“文部四·颂”
彦和认为“挚虞品藻,颇为精核”,然即使如此,两者亦时有不同。至于挚虞“杂以风雅”云云,彦和与挚氏之异者就更不用说了。此其一。其二,就“精核”言,昭明太子同样可从“挚虞品藻”等中吸取“营养”,而非彦和所得而私。因之,从这一层面考察,也毫不影响我们的结论。
又,叶长春释“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有“案”云:
兹举《明诗》篇以示例,自“大舜云”起至“莫非自然”,此“释名以章义”也;“昔葛天氏乐辞云”起至“其来久矣”;“原始以表末”也;“自商暨周”起至“而纲领之要可明矣”,“选文以定篇”也;以下“敷理以举统”。[11]118
叶先生之说亦得其要。不过,其关于这“四者”起始的划分,不无可商之处。然而,由于这一分法不碍我们的讨论,故兹姑仍之。[12]48-59《明诗》篇云: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谋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释名以章义”)
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原始以表末”)
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选文以定篇”)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圆通。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敷理以举统”)[2]171-218
同一文体,由于《文选》仅“选”(分类,则《文心雕龙》亦然:《序志》之“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与《文选序》之“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类),故《文心雕龙》比其多做的工作,除“选文以定篇”中之评文外,还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敷理以举统”三项。而这三项工作,非研读该体作品便可完事,甚至非作品本身所能范围。关于《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这四者之每一项,詹锳先生分别释之云:“‘原始以表末’,是论述每一体文章的起源和流变”;“‘释名以章义’,是解释各种文体名称的含义,就是从每一体文章的命名上来表明这类文章的性质”;“‘选文以定篇’,是选出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品来加以评定,就是评论每一体文章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敷理以举统’,是敷陈事理来举出文章的体统,就是说明每一体文章的规格要求,或标准风格”。[2]1926-1927这是符合实际的。又,邓国光先生云:“‘选文以定篇’,源于孔子的‘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这是企效孔子的实在功夫,不容空言,必须要披沙拣金,保存菁华。”[13]是可谓见灼而入深者也。观此,我们便可大略知道:《文心雕龙》仅“论文叙笔”部分,其比之《文选》选文具体多出哪些工作。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文心雕龙》“选出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品”与《文选》之“略其芜秽,集其清英”,两者实为同类——可以作比较。又,牟世金先生云:刘勰的“论文叙笔”中的“各篇的基本内容,则如《序志》篇所说,略有四个方面:‘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在具体论述中大都是首先简释文体的名称以说明其意义,然后以主要篇幅叙述该体的发展始末,结合评论历代有代表性的作品,最后总结这一文体的基本特征和写作要领。由此可见,所谓‘论文叙笔’,主要是分体总结前人的各种写作经验。不少研究者认为这部分具有分体文学史的性质,是很有道理的”。[14]203是亦得其大者。而以此比观《文选》与《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的工作量如何,亦易知后者之为大。至于“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敷理以举统”三者,其总的工作量与《文选》比较大小与难易如何,虽难以得出具体的结论,然合这三者的工作量于“选文以定篇”,刘勰完成《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加《辨骚》与《才略》二篇,其难度与工作量大于太子完成整部《文选》,则更应是没有疑问的。[1]简言之,据舍人“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云云,《文选》选文(编纂)与《文心雕龙》“论文叙笔”所为便不是“异类”,即非墨家所说的“木与夜孰长”之“异”[3]215,而是“昼与夜孰长”或“木与竹孰长”之类——高享先生云:“‘木与夜孰长?’树木和夜晚是异类,树木的长短属于空间,夜晚的长短属于时间,其本质不同,其数量不可相比度。如果问:‘木与夜孰长?’是不合逻辑的。”[15]26这一解释是恰当的。此其一;其二,此外,舍人还做了“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等一系列《文选》所无的工作。因之,尽管这部分的工作量有多大,我们难以究知,然这部分的工作量加上“论文叙笔”部分的工作量,其大于“论文叙笔”部分的工作量乃不证自明之常识。当然,就具体的文体对应比较言,“选编《文选·诗》比撰《明诗》篇的工作量或许大些”,然这恐是唯一之例外——我们此前将《文选》与《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别为17项进行比较,结果是:一者,“诗”一项而外,仅有2项《文选》的工作量充其量与《文心雕龙》相应的等,而其余14项的工作量则不仅《文心雕龙》的大,且多数限于“选文以定篇”之范围内仍然如此。二者,“当拿《才略》篇合《明诗》篇再来比较时,情况便出现了大的不同。……就同一人言,撰《明诗》与《才略》两文,显然要比选63位诗家的诗分23类(“乐府”已另计)编在一起的难度大”[1]。
论证了编纂《文选》的工作量远小于撰写《文心雕龙》的,我们再考察既然完成同样的工作量会因人而异,那么,昭明太子编纂《文选》所花时间可否相应地远少于刘彦和撰写《文心雕龙》的这一问题。
三、从因人而异的层面看《文选》《文心》成书之难易
我们既已论证了《文选》选文(编纂)的工作量比撰写《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的小,比之整部《文心雕龙》更是如此,便不难明白:就通常的情形言,编纂《文选》所用的时间自然要比撰写《文心雕龙》的少。当然,我们也知道:由于同样的工作量会因人而异,故其大小在不同的人那里所需时间之长短就未必与之相应。《文心雕龙·神思》云: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掇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沉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鞍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唯有短篇,亦思之速也。[2]989-992
不过,这主要是就写作之“迟速异分”说的。即昭明太子撰《文选序》与彦和撰《文心雕龙·序志》或存在这方面的差异,然就《文选》选“文”与《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之“选文以定篇”看,则恐另当别论。就整体的写作言,我们很容易如是观——“《文心雕龙》五十篇,总计三万七千余言,以刘勰之才力,其文如行云流水,首尾一贯,谅不需六七年之久”[7]51;然就选“文”言,无论是《文心雕龙》“选文以定篇”所说还是《文选》所选,均极具识力,而于此更关键的是识力如何而非类《神思》篇所说的“思”之“缓”与“速”。故于此,“思之速”与“思之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下面,我们再分别考察一下昭明太子与刘彦和之学养及相关情况。《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云:
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天监)八年九月,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高祖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16]165-171
又,同书卷五○《文学传(下)》云:
刘勰,字彦和……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
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文集行于世。[16]710-712
两相比较,就学习环境之优越与拥有相关书籍之多言,彦和是无法与太子比的;就作为选家言,虽不好说太子优于彦和,然我们恐亦难找到太子不如彦和之什么证据,而就《文选》与《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之“选文”考察,二者均极为出色。故《文心雕龙》虽撰于彦和三十出头以后(《序志》云:“齿在踰立……乃始论文。”),而昭明太子编纂《文选》当始于普通4-5年之23-24岁间[17]。即彦和尽管有更长的人生与为学历练,恐亦会因学习环境之远不如昭明太子而有所抵消。总而言之,合此数者观,昭明太子选出《文选》所载之“文”,其工作自然要比彦和“选”出《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提及之“文”而略加评点少且易。此其一。其二,我们知道,此前出现了不少有利于了解历代诗文精品的文献。如傅玄《七谟序》与《连珠序》、陆机《遂志赋序》、挚虞《文章流别集》及其《论》、李充《翰林论》,以及大型诗文总集及单体总集与来自这些总集之小型同类总集(前者若是“全”,后者则是“选”;而前者已是“选”,后者则为“选”中之“选”——更为精品),等等。问题是,若说这些文献大有助于彦和“论文叙笔”时之“选文以定篇”,其同样亦可使昭明太子“选”诗文时奏“事半功倍”之效*饶宗颐《〈文心雕龙〉探原》云:“盖自《书记》而上为上篇,所以‘论文叙笔’……彦和以前论文体者,若曹丕、陆机、挚虞、李充,已极赅洽……然有一事为历来所忽略者,即分体之总集,至于宋齐,各体皆备,彦和席其成规,但加品骘而已;毋庸搴择而归纳之也。……是彦和此书上半部之侈陈文体,自非空所依傍,自出杼轴;其分类之法,乃依循前规,排比成编;加之仲洽《流别》,李充《翰林》,并有成书,矩矱具在,自易措手。《昭明文选》,成书更在彦和之后,其分析文体,姚姬传深病其碎杂,不知乃远承往辙,与彦和取径,正有同然。”(邝健行、吴淑钿编选《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1950-2000)·文学评论篇》,第3-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恰当的。。不仅如此,《文心雕龙》不可能从自身与其后的《诗品》那里得到之“帮助”,然《文选》却极有可能从这两部著作中吸收“养分”。即由此不可能改变撰《文心雕龙》的工作量远大于编纂《文选》的工作量之“实”。其三,两书均撰者用力所成(彦和更是寄托“遥深”)——《文选序》之“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18]卷首及《序志》之“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果载心,余心有寄”[2]1903-1938,均为明证。其四,“论文叙笔”部分的全部工作量必多于其中之“选文以定篇”的,而撰写整部《文心雕龙》的工作量又自然多于撰写其中之“论文叙笔”部分的。其五,《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各篇之“选文”,当分别进行而来自或主要来自单体总集而非别集;然《文选》编纂亦可如此*笔者在《关于〈文选〉所录诗文之来源问题》一文中曾云:“《文选》乃合‘首选’与‘再选’为一体之书,且当以首选为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4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首选”,包括从大型的诗文总集与单体总集中来者。。其六,萧统虽为太子,然其自序《文选》有“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之说;而彦和如《梁书》本传所说的,依沙门僧祐,其时还做着定“定林寺经藏”方面的相关工作[14]61。其七,据杨明照先生《梁书刘勰传笺注》考证,彦和撰写《文心雕龙》费时四载左右[19]404-405。因之,“以彼例此,昭明太子凭一己之力不能编纂《文选》之说,断非圆照”[1]。即就“选”(“选文以定篇”)的方面言,据上所述的情况考察,昭明太子与彦和有异也异不到哪里——准此,昭明太子编纂《文选》所花时间比彦和撰写《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的仍然要短,遑论整部《文心雕龙》;而就《神思》篇所说之“思”(写作)言,无论昭明太子与彦和二人“缓”“速”之别有多大,因除了《文选序》外,昭明太子未做这方面的任何工作,故此均不成为问题。换言之,“因人而异”之因素,不管从哪一层面上说,都难以改变编纂《文选》的工作量要小于撰写《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的之另一种形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所花时间要比彦和撰写《文心雕龙》的短。问题是,学者或未能注意到这一点,故云:
有的文章认为既然刘勰能够独自一人完成《文心雕龙》,则萧统亦能独自一人完成《文选》,因为《文心雕龙》工作量远远大于《文选》。诸如此类,论据与论证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面对相同材料极易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20]*此文时有不可思议者在,如说:“关于《文选》是否为仓促成书,力之有《〈文选〉非“尚未最后加工定稿之书”辨》……等文,认为‘编《文选》的工作量至多为撰《文心雕龙》的一半;《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而非仓促所就。’王晓东表示反对……曹道衡、王立群亦支持《文选》乃仓促成书。”实际情况是:晓东先生《〈文选〉系仓促成书说》载1997年出版的《文选学新论》,而力之在2002年第2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关于〈文选序〉与〈文选〉之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一文对其“仓促成书说”提出异议;其后,曹先生在《文史》2005年第3期上发表《关于〈文选〉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未辩驳力之此文之观点而提出《文选》“是尚未最后加工定稿之书”说,力之则复在2007年第1期的《东方丛刊》上发表《〈文选〉非“尚未最后加工定稿之书”辨》一文对其说提出不同看法。问题是,经其作者这么一“弄”——尤其是在如此权威的刊物上,是非被完全颠倒了。此文又说:“此外还有三十九类说,依据南宋陈八郎刊五臣注,再增‘难’类。台湾游志诚《‘文选学’之分类评点方法》、《论〈文选〉之难体》有详细论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论定不但陈八郎本,而且各种“五臣”注均为三十九类……’该说得到曹道衡等资深学者的关注。”显然,此文作者并未看过《‘文选学’之分类评点方法》一文,其实该文“详细论证”的非“依据南宋陈八郎刊五臣注,再增‘难’类”;至于“关注”云云,则缘作者不知“陈八郎本”亦是“三十七类”而非“三十九类”所致。
比观我们前面所说,此可谓未达一间者也。因为,这里的关键是《文选》的工作量是否如《文心雕龙》那样,仅凭一人之力便可以完成。即《文选》的工作量与完成《文选》的难度,充其量是否如《文心雕龙》的那么大。而这一问题,如上所述的,由于《文选》选文(编纂)与《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并非“异类”,故将这两者比较便可知之。此其一。其二,据我们前面所作的比较可知,完成《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的工作量与难度比编纂《文选》的要大。因之,尽管我们难以弄清楚完成《文心雕龙》这部分的工作量究竟有多大,然撰整部《文心雕龙》的工作量大于撰其中之“论文叙笔”部分的,乃属常识。同理,既然撰写《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的工作量与难度比编纂《文选》的要大,那么彦和完成《文心雕龙》,其工作量与难度就自然要大于昭明太子完成《文选》。
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有三:1.《文选》与《文心雕龙》工作量之大小如何虽难以比较,然《文选》与《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却有切实的可比性;2.通过比较可知,编纂《文选》的工作量要小于撰写《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的,比之撰写整部《文心雕龙》,其更是如此;3.“因人而异”之因素,难以改变昭明太子编纂《文选》费时要比彦和撰写《文心雕龙》短这一相应于工作量大小之形态。另外,通过与《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比观,不难想象,《文选》之编纂更有可能的是选好一体之“文”,即编纂一体。而这样一来,《文选》所选作品来自该作家别集之比例恐要比此前研究者们(包括笔者在内)所想象的低。此其一。其二,彦和完成《文心雕龙》,尤其是其中的“论文叙笔”部分,恐没有人们此前所想的那么容易;而《文选》的工作量与其完成难度则在“不知不觉”中被放大了——需要注意的是,这与《文选》本身的价值如何无关。即这丝毫不影响《文选》一书在我国文学史上原有的崇高地位。
[1] 力之.关于《文选》编纂“工程”的大小问题[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2]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 谭戒甫.墨辩发微[M].北京:中华书局,1964.
[4] 卢弼.三国志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 毛庆.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6] 力之.略论毛庆先生对当代屈原研究之贡献[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7] 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M].成都:巴蜀书社,1988.
[8]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 张灯.《文心雕龙·颂赞》疑义辨析举隅[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4).
[10] 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1] 叶长春.文心雕龙杂记[M].福州:福州职业中学印刷工场,1933.
[12] 杨明.文心雕龙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3] 邓国光.《文心雕龙》文体通义[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14] 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5] 高亨.文史述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7] 力之.《文选》成书时间考说[J].文学遗产(网络版),2010(2).
[18] 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影胡刻本.
[19]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0] 石树芳.《文选》研究百年述评[J].文学评论,2012(2).
[责任编辑 阳 欣]
On Comparability of Workload between Wen Xuan and Wen Xin Diao Long
LI Zh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1, China)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nature, it is difficult to compare the workload of Wen Xuan with that of Wen Xin Diao Long. However,when it comes to and the part of “narration and argumentation” in Wen Xuan and Wen Xin Diao Long, they are comparable as a matter of fact. In this respect, the workload of compiling the book Wen Xuan is much less than that of Wen Xin Diao Long. Even though each person may spend different amount of time to complete the same workload, in this comparable part, it is so much the same in different way. Namely, the time spent by Xiao Tong to compiling Wen Xuan is less than that of Wen Xin Diao Long by Liu Xie, which is more time-consuming than expected. While the workload and difficulty in completing Wen Xuan are exagerated to a certain extent.
Wen Xuan;Wen Xin Diao Long;crown prince Zhao Ming; workload; comparability;the whole is greater that the sum of the parts
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6.011
2016-01-21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文选》成书考说”(10XZW010)
力之(1956-),男,广西北海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I206.2
A
1001-6597(2016)06-006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