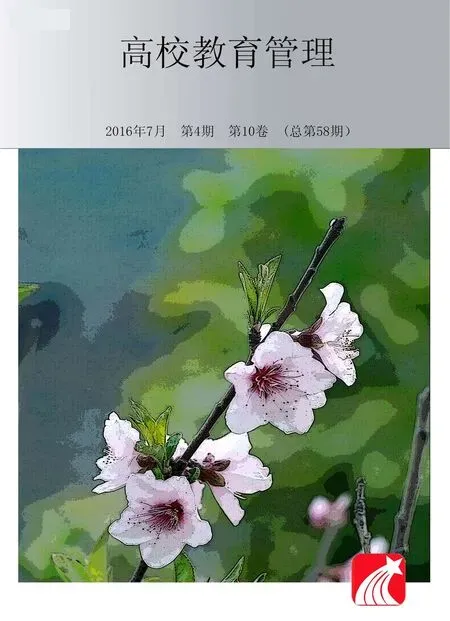国外大学海外分校发展的特点分析及经验借鉴
薛卫洋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国外大学海外分校发展的特点分析及经验借鉴
薛卫洋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大学海外分校热。文章通过对国外大学海外分校发展的研究,发现其创办动因复杂多元;经费保障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学科专业设置服务区域发展需要;高质量办学是输入国主要诉求。鉴于这些特点,作为国外大学海外分校在我国实现形式的中外合作大学,在发展中应坚持公益性办学导向,明确教育活动本质;积极构建多元化筹资模式;科学、合理设置学科专业;不断提升办学质量。
关键词:大学海外分校;学科专业;中外合作大学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动下,跨境教育发展日趋蓬勃,其中又以大学海外分校的发展格外引人注目。大学海外分校作为新兴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出现与发展有着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但也与输出国的主观推动和输入国的有意引入不无关系。虽然大学海外分校在本质上被视为彻底的教育机构,但并不能排除其天生所携带的各种附加工具价值。作为跨境教育的世界最大输入国——中国,近年来国外大学海外分校在我国日益兴起并蓬勃发展。目前,国外高校在我国不得单独设立分校,国外大学海外分校在我国以中外合作办学形式举办。由于大学海外分校概念认识的不一和便于研究对象的确定,文章将国外大学在我国的海外分校仅限于法人设置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即中外合作大学。通过对国外大学海外分校发展的研究,可以形成对大学海外分校的科学合理认识,并总结其特点,为中外合作大学的健康发展提出有益建议。
一、 国外大学海外分校的发展概述
目前,对大学海外分校的定义尚无统一定论。英国“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以下简称OBHE)认为,大学海外分校是一所高校的离岸实体,以外国高校名义由主办高校独立运营或与他方合作运营,颁发母校的学位[1]。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跨境教育研究小组(Cross-Bord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以下简称C-BERT)认为,大学海外分校是高校在海外独立或与其他机构联合举办的机构,使用母校名称,学生获得主办高校学位,教学必须包含面授[2]。国际知名比较教育学者阿尔特巴赫(Philip G. Althach)则简要地将大学海外分校概括为高校在海外办学的附属实体,授予母校学位[3]。总结这些定义可以发现,在输入国拥有实体机构和授予输出国学位,是大学海外分校有别于其他跨境教育类型的两个基本要素。
具备上述两个基本要素的大学海外分校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主要是在欧美国家范围内开展,以美国为主要输出国,如1955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意大利创办的分校。早期的大学海外分校总体而言,办学规模较小,数量也较少,其主要目的在于服务本国在外公民的教育需要。大学海外分校真正的蓬勃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学生规模较大、数量剧增是这一时期大学海外分校的主要特点。有统计显示,到2005年,全世界大约有100多所大学海外分校,学生数达到5万名[4]。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减少,以及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实施,将教育划归为服务贸易的组成部分,直接推动了西方高校纷纷涉足海外教育市场。
随着大学海外分校的迅猛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高等教育发达的欧美国家为主要输出国的局面;输入国则是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高等教育实力较为薄弱的新兴经济体国家。C-BERT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0月14日,世界上共有230所大学海外分校在运行中,24个在筹建中,27个已经关闭;共有32个大学海外分校输出国,75个输入国;输出大学海外分校较多的为美国(81个)、英国(37个)、俄罗斯(20个)、澳大利亚(15个);较多的输入国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32个)、中国大陆(27个)*注: 因统计口径不一致,C-BERT在统计我国大陆地区国外大学海外分校时包含了部分非法人设置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二级学院),所以该机构对设在我国的国外大学海外分校统计数据高于本文统计数据。、卡塔尔(11个)、马来西亚(9个)[5]。
二、 国外大学海外分校发展的特点分析
(一) 创办动因复杂多元
大学海外分校蓬勃发展的背后,有着复杂多元的动因。从输出国来看,原因主要有三。其一,获取经济收益。这是西方高校创办海外分校的主要推动因素,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高校。1984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杰克逊报告”,明确表示要把教育服务贸易视为一个重要的新兴产业,海外分校成为澳大利亚大学占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市场的重要手段。有统计显示,2012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8所大学的海外分校获得了16.8亿美元的收入[6]。其二,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注重培育学生的国际体验、国际视野和国际交往能力,以及提升大学国际化办学水平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高校的共识,海外分校被认为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例如,美国纽约大学为“建设美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网络大学”,在中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分别设立了海外分校;美国杜克大学希望借助国际化进程,弥补在本土难以打败哈佛大学的遗憾,甚至不惜投入五千万美元与我国的武汉大学合作创办昆山杜克大学。其三,服务政治利益需要。这种以俄罗斯为代表。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后一直致力于巩固其在原苏联地区的影响力,大学海外分校被俄罗斯视为对独联体国家影响的重要手段之一。根据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部公布的数据,目前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已经开设了58所分校[7]。当然,一所大学海外分校的设立,并不纯粹是这里所列出的某一类原因。一般来说,大多西方高校创办海外分校,都有着多种因素的复合作用。
作为大学海外分校的输入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促使这些国家在自身高等教育难以满足的情况下将目光投向了国外大学的海外分校。通过引入国外大学海外分校,不仅可以迅速提升本国高等教育水平,同时还能吸引国际知识移民,改善本国劳动力结构,推动本国成为区域的科研、教育中心。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卡塔尔、迪拜等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均面临着经济发展转型的要求,纷纷提出引入世界一流大学创办分校计划,希望国外大学的分校成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中心和助推器。而作为跨境教育最大国家的我国,则希望引入国外大学分校丰富国内教育资源供给,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发挥“鲶鱼作用”助推国内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等。
(二) 经费保障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国外大学海外分校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发展困难,甚至不得不关闭。国外大学海外分校关闭的主要原因是资金链断裂。OBHE的一份研究将大学海外分校的创办模式分为三种:一是母校独资;二是外部投资,又分为输入国政府提供资金和输入国或输出国私营企业等机构投资;三是输入国政府或企业提供办学设施。该研究还指出目前前两种为大学海外分校的主要创办模式[8]。母校独资或外部独资,造成了大学海外分校资金来源的不独立,母校财务状况、输入国政府的态度、企业经营状况等给大学海外分校的资金来源带来很大风险。例如,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科技学院的马来西亚分校,就是因为其合作伙伴(当地企业)陷入经营危机而导致分校资金链断裂而不得不关闭[9]。
另外,大学海外分校作为一种新兴的高等教育机构,一般独立于输入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大多难以获得输入国政府的经常性财政资助,造成大多大学海外分校的经费来源以学生学费为主,一旦生源数量难以支撑大学海外分校运转成本,则面临着关闭的局面。例如,澳大利亚的中央昆士兰大学斐济分校,便是由于生源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学费无法支付运转成本而被迫关闭[9]。同时,一些西方高校本身抱以营利态度创办海外分校,如果分校的经营难以获取利润时,母校也会选择关闭分校。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掀起的美国大学分校热,仅5年后就大部分被迫关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10]。
(三) 学科专业设置服务区域发展需要
作为大学海外分校的输入国,大多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向知识经济、服务经济的转型,因此,大学海外分校的学科专业设置,明显地体现出服务区域发展需要的特征。新加坡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后,确立了淘汰低端加工制造,向高新技术经济、服务经济转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力图成为亚太地区的物流集散中心和金融中心。1998年,新加坡政府提出“十所顶级大学计划”后,成功吸引了8所世界顶尖大学在新加坡开办分校,这些分校的学科专业基本以经贸管理为主,甚至直接以这些专业命名分校名称。例如,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建立的亚太物流学院,美国宾夕法尼亚沃顿商学院参与创办的新加坡管理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创办的管理学院,法国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创办的新欧工商管理学院等。同样,以石油经济崛起的海湾国家自20世纪末开始逐渐意识到石油经济的不可持续性,继而希望以发展高科技、金融、旅游、服务等产业实现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因此,这些国家引入的大学海外分校在学科专业上,表现出明显以工科和商科为主;另外旅游和健康护理也是该地区大学海外分校设立较多的特色专业,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对提高石油工业品质、建立国际自贸区和旅游区的人才需要。
(四) 高质量办学是输入国的主要诉求
从目前国外大学海外分校来看,其主办母校基本为世界一流高校,鲜有不知名的高校创办海外分校。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输入国对大学海外分校高质量办学的诉求有直接关系。为了确保大学海外分校办学的高质量,输入国采取多重措施。其一,目标瞄准世界一流大学,从源头上保证大学海外分校的办学质量。基本所有的输入国均表示引入大学海外分校的母校需具有国际一流水准。例如,新加坡的“十所顶尖大学计划”;越南政府设定政府邀请国外大学创办分校必须具有国际教学水平;印度政府更是明确表示引入大学海外分校的母校必须是世界前400名高校。其二,提供大量资金支持。给予大量资金支持是不少输入国为吸引世界一流高校创办分校的做法,例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政府为了吸引美国纽约大学举办分校,开始即预付五千万美元作为定金,并承诺负担分校运行的一切费用;同时,还为分校吸引国际一流生源提供巨额奖学金,2015年中国武汉的一位学生就获得了该分校的180万元人民币巨额奖学金。其三,重视质量保障机制的构建。例如,越南政府对大学海外分校的师资做出明确要求,“在经济管理、自然科学和外语专业最大生师比为30∶1,而技术和理工类专业最大生师比为15∶1”,海外分校“举办5年内教师中外籍教师比例不能低于55%,10年内不能低于30%”[11]。
三、 对中外合作大学的借鉴
按照文章的研究界定,国外大学海外分校在我国以中外合作办学形式举办,为法人设置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即中外合作大学。截至2015年10月,我国已经设立或筹建的中外合作大学已经有10所*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教育机构与内地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的,参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因此,香港与内地举办的法人设置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本文也被视为中外合作大学,但长江商学院在《条例》颁布之前设立,无外方合作教育机构,故本文不纳入中外合作大学统计之列。,分别是:苏州港大思培科技职业学院(2005)、宁波诺丁汉大学(2005)、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2005)、西交利物浦大学(2006)、上海纽约大学(2012)、昆山杜克大学(2013)、温州肯恩大学(2014)、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14)、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筹,2015)、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筹,2015)。
中外合作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新生事物,已经运行的几所也不过办学十余年。总体来说,中外合作大学对拓宽人才培养途径、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助推国内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外合作大学的办学仍处于探索过程中,还面临不少的困境和障碍。为促进中外合作大学的更好发展,基于对国外大学海外分校发展的分析,文章提出几点建议。
(一) 坚持公益办学导向,明确教育活动本质
从国外大学海外分校的发展中可知,输入国引入海外分校的目的基本在于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需要;而输出国则表现得复杂多元,经济利益是大多数大学海外分校输出国的主要诉求,一些西方国家在教育输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因素,将教育输出视为外交手段的补充。作为大学海外分校输入国的我国,必须全面、科学、理性认识外方高校在华合作创办中外合作大学的动机,要坚持中外合作大学的公益办学导向,明确中外合作大学从事教育活动的本质属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均规定我国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作为“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也明确规定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因此,中外合作大学必须始终坚持办学的公益性导向。值得肯定的是,目前在运行中的几所中外合作大学在注册时基本选择不要求合理回报。但近年来,由于中外合作大学运行成本高昂所致的学费较贵,也引起了社会的一些质疑。对此问题,中外合作大学应坚持办学的公益性,正面回应社会顾虑,推动办学成本的阳光核算和财务对外公开,为自身发展营造有利社会舆论,让社会认识到其办学活动的公益属性。
意识形态的渗透问题也是大学海外分校发展中较难规避的问题,中外合作大学的发展也需要注意此问题的存在,必须始终保障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与国内普通高校有党委组织领导来保障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同,中外合作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未有党委组织设置的硬性规定。中外合作大学要对党委组织的地位和价值有科学认识,要意识到党委组织的存在对学校办学具有方向的引领作用和对学生的教育作用。同时,中外合作大学明确教育活动本质属性的根本,要落实到对学生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引领,培育具有“中国芯”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
(二) 积极构建多元化筹资模式
国外大学海外分校的发展经验表明,稳定的经费来源是海外分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中外合作大学的办学经费投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看。在创办初期,地方政府一般是中外合作大学的主要投入者。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创办前期,深圳市政府注入10亿元资金;温州肯恩大学的筹建过程中,仅温州市政府就拨付15亿元专项资金。近年来中外合作大学之所以数量不断攀升,重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中外合作大学在后期运营过程中,办学经费基本以学费收入为主,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的临时性补助,目前尚无国家教育财政的经常性补助。
毫无疑问,中外合作大学以学生学费作为办学经费来源的单一化局面是不利的。中外合作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突破单一化的资金来源现状,积极构建多元化筹资模式。中外合作大学作为“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也在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应组织有关力量对中外合作大学投入体制进行科学研究,尽快完善对中外合作大学投入体制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地方政府是中外合作大学发展的重要支撑,不能仅在中外合作大学的创办初期给予土地和经费支持,应将对中外合作大学的经费支持制度化,避免因地方政府任职人员的变更造成对中外合作大学支持态度的摇摆。作为中外合作大学自身,要树立多元化筹资的意识,积极争取国家和地方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的经费支持;同时,积极利用自身拥有的智力资源和科研优势,大力引入社会资源,加强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学习西方大学基金会筹资、投资运作模式和机制,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三) 科学、合理设置学科专业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海外分校在学科专业设置上,基本是对接新兴经济体国家产业转型需要的。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新常态,经济结构要求逐步升级优化,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式进一步转变,发展动力要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作为整体、成建制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大学,必须适应和服务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大局[12],必须适应和服务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要通过科学合理地设置专业,为我国经济发展由低端制造向高端创新迈进培养大批高素质国际化人才。
从中外合作大学的所在地来看,均是经济富裕地区,但近年来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型升级,诸如深圳、苏州、宁波、温州等地,均面临着由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加工产业向知识密集型的高端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转型,上海纽约大学的坐落地上海更是致力于打造“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目前,中外合作大学的外方合作高校,整体资质优良,但在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方面也存在差别。例如,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外方合作高校英国诺丁汉大学,农学、法学等是强势学科;上海纽约大学的外方合作高校美国纽约大学,商科位居全球前列;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外方合作高校香港中文大学,以人文社会科学擅长;昆山杜克大学的外方合作高校美国杜克大学,医学、法学、文学等位居全球前列。中外合作大学在学科专业设置的选择上,要做到三方面的动态结合。其一,注意引进外方合作高校的优势学科和强势专业;其二,着眼于办学所在地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其三,瞄准当前国内新兴和亟须的学科专业领域。只有将这三方面动态结合,才能实现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中外合作办学的根本目的,也才能使中外合作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拥有独特价值和重要地位。
(四) 不断提升办学质量
“质量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生命线。”[13]中外合作大学能否实现其自身肩负的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重任以及发挥“鲶鱼效应”助推国内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使命,根本在于其办学质量的高低。通过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海外分校发展特点分析,也得出办学的高质量是大学海外分校输入国的主要诉求。就我国而言,对中外合作大学的办学质量要求十分明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中外合作大学的发展作出顶层设计,要求“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14];2013年12月10日,《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工作的意见》更是明确指出,中外合作大学“要借鉴外国教育机构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实现高端引领”[15]。可见,我国对中外合作大学高质量办学有着明确要求。
中外合作大学在我国发展已有十余年,总体来看,办学质量得到了社会认可。近年来,尽管在中外合作大学学费较为高昂的情况下,仍然有大批优质生源踊跃报考便是例证。这种良好局面的形成,得益于中外合作大学明确的办学定位、高质量的教育教学以及对人才培养模式、方法的不断探索创新。但中外合作大学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不少国家都在世界范围内竞争优质教育资源,一些大学海外分校的输出国也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办学扩张,例如,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外方合作高校英国诺丁汉大学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设有分校;上海纽约大学的外方合作高校美国纽约大学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也设有分校。国外大学在全球多地的分校扩张,不可避免地带来其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比如师资。中外合作大学如何在全球竞争中最大化引进利用合作外方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是中外合作大学不断提升办学质量的关键问题。这需要中外合作大学牢牢把握不断提升办学质量的意识,始终坚持对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引进与有效利用,进一步探索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机制,让中西教育资源在融会中实现升华和超越。
参考文献
[1]Becker R.The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 New Trends and Directions[J].InternationalHigherEducation,2010,58(Winter):3-4.
[2]苏洋,赵文华.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海外分校的特征与启示[J].教育发展研究,2013(23):33-38.
[3]Althach P G. Is There a Future for Branch Campuses[J].InternationalHigherEducation,2011,65(Fall):7-10.
[4]McBurnie G.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Programme and Institution Mobility[EB/OL].(2006-10-25)[2016-01-20].http://www. oecd.org/dataoecd/51/8/37477665.pdf.
[5]Quick Facts[EB/OL].(2015-10-14)[2016-01-20].http://www.globalhighered.org/index.php.
[6]Victorian Auditor-General’s Office. Tertiary Education and Other Entities:Results of the 2012 Audits[EB/OL].(2012-05-23)[2016-01-20].http://www.audit.vic.gov.au/publications/20120523-Tertiary-Ed/20120523-Tertiary-Ed.pdf.
[7]CIS Branches of the Russian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EB/OL].(2014-12-25)[2016-01-20].http://en.russia.edu.ru/zvuz/1067/.
[8]Verbik L,Merkley C.The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 Models and Trends[EB/OL].(2007-05-30)[2016-01-20].http://heer.qaa.ac.uk/SearchForSummaries/Summaries/Pages/INT22.aspx.
[9]赵丽.澳大利亚发展海外分校的实践与经验[J].全球教育展望,2014(8):74-82.
[10]叶林.美国大学在日分校的历史、现状和将来[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1):27-33.
[11]林金辉,赵叶珠,周勤健.越南、印度、以色列涉外合作办学政策与管理的考察报告[R]//林金辉.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管理与质量保障.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279-288.
[12]林金辉.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33.
[13]林金辉.规范·健康·有序——论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管理[N].人民日报,2010-08-27(18).
[1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0-07-29)[2016-01-20].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38/201008/93704.html.
[15]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工作的意见[EB/OL].(2013-12-20)[2016-01-20].http://cfcrs.xmu.edu.cn/s/184/t/633/38/48/info145480.htm.
(责任编辑刘伦)
doi:10.13316/j.cnki.jhem.20160614.013
收稿日期:2016-01-29
作者简介:薛卫洋,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外合作办学、跨境高等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381(2016)04-0085-06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University Branch Campus and Its Enlightenment
XUEWeiya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Setting overseas branch campus is becoming a worldwide trend for universities in recent years. By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university branch campus (FUBC),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y are established for complex and various reasons; guarantee of funds is the key to FUBC’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sciplines and majors are set adapting to needs of local development; high quality education is the main demands of input nation. In view of these, the development of Sino-foreign university should insist non-profit and keep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actively build diversified model for funding raising,set disciplines and majors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continuously.
Key words:university branch campus; disciplines and methods; sino-foreign university
网络出版时间: 2016-06-14
网络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2.1774.G4.20160614.1605.0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