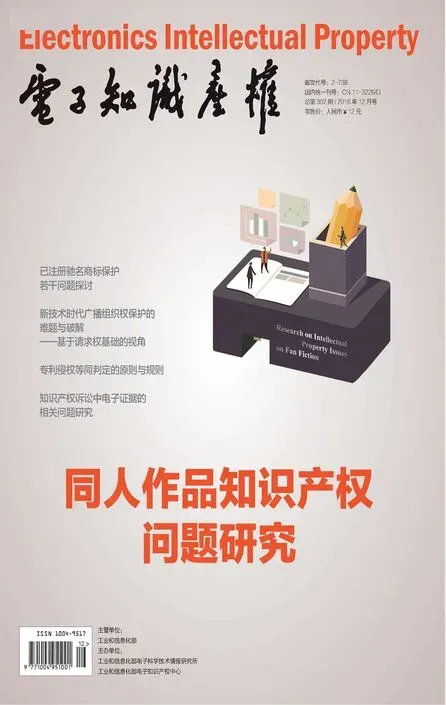同人作品的文化层累功能及其与在先作品竞争法上的法益关系
——以《此间的少年》为例
文/龙文懋
同人作品的文化层累功能及其与在先作品竞争法上的法益关系
——以《此间的少年》为例
文/龙文懋
《此间的少年》这类“架空”利用原作的同人作品,既不违反现行著作权法及商标法,也不构成对原作竞争法上的法益侵害。这主要是因为同人作品一般对在先作品不造成替代和竞争,相反,多数同人作品与原作是互相支撑的关系,甚至会造成“同人逆迷”的情况。另外,同人作品还具有文化层累的功能。基于尊重创作规律、有利于文化生成的考虑,同人创作对于在先作品之“搭便车”不应被法律普遍禁止,只有在涉嫌抄袭、剽窃等特定情况下才应加以规制,而著作权法对此已经加以明确,不宜在竞争法上扩张保护。
同人作品;竞争;替代;搭便车;层累
今年1王迁:《“此间的少年”不在少数,为何有的胜诉有的败诉?》,载上观网2016年10月25日,http://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34506。0月11日,金庸向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作家江南(本名杨治)《此间的少年》(后文简称《此间》)对于其几部武侠小说构成侵权,要求江南及有关图书出版发行单位停止复制、发行该书,封存并销毁库存图书,在媒体致歉,并赔偿经济损失500万元、维权合理支出20万元。一石千浪,本案迅速引发各方热议,也将同人作品的知识产权问题置于舆论焦点。
本文认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难以认定《此间》侵犯金庸的著作权,对此王迁教授的分析堪称周至,此不赘述。1王迁:《“此间的少年”不在少数,为何有的胜诉有的败诉?》,载上观网2016年10月25日,http://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34506。而由于《此间》对于金庸小说人物名称的利用并非商标性使用,加之我国法律中对于作品人物的商品化权尚无明确规定,也难以认定其侵犯小说人物的商品化权。那么《此间》究竟侵不侵权、侵权的话究竟侵犯何种权利呢?笔者认为,目前最靠谱的分析是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后文简称《反》法)第二条兜底条款为依据,主张江南侵犯了金庸竞争法上的法益(而不是权利,所以“侵权”之说在表述上有欠严谨)。“首先,同人作品的作者和原作者当属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而‘非演绎类’同人作品(该文作者将演绎作品归入同人作品中——本文作者注)作者未经原作者授权即创作该同人作品并商业发行的行为主观上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恶意的,同时其未经允许的使用原作品人物名称等元素有‘搭便车’的嫌疑”。“如果在诉讼中,金庸先生还能拿出在发行《此间》时出版方对于《此间》的报道中含有诸如‘金庸小说人物的校园生活’之类宣传语的证据(攀附商品),那么将对于不正当竞争层面的诉讼十分有利。”2邱政谈、孙黎卿、翁才林:《金庸诉江南——同人作品侵权谈》,微信公众号“知产力”推送,2016年12月1日。但是,这类分析存在的问题是:首先,且不论将小说作者认定为“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是否适当,即便认可不同的作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具体到本案,他们“经营”的作品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扩而言之,同人作品与在先作品是互相竞争的关系还是互相支持的关系?其次,利用在先作品的元素进行二次创作,是否必须经由作者同意?第三,如果未经作者同意,上述行为是否构成竞争法上的“恶意”?第四,利用在先作品的元素本身固然有“搭便车”之嫌,但是这种搭便车是否是法律明确禁止或者应当禁止的?消除一切“搭便车”是知识产权法的应然目标吗?在实然层面上,法律能否彻底禁绝一切“搭便车”的行为?基于上述疑问,笔者对于金庸能否依据《反》法第二条主张竞争法上的保护持保留态度。
本文认为:首先,除涉嫌剽窃、抄袭的作品外,同人作品大多与在先作品是互相支撑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关系;其次,利用在先作品元素创作同人作品,不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第三,上述未经许可的行为不构成竞争法上的恶意;第四,与商标法不同,著作权法不一般性禁止搭便车,这主要是由文本和文化生成的规律使然。著作权法通过规定作者的权利(及其它权利)明确划定了禁止搭便车的范围,除此之外,其它搭便车都是合理的,既不能以“搭便车”为由认定侵犯著作权,也不能认定构成竞争法上的法益侵害。上述结论主要是针对《此间》这种类型的“架空”同人作品作出的,但是可以适用于多数同人作品。本文认为,以上四个问题中,第一和第四个问题是比较关键的,因为一旦认定同人作品与在先作品构成竞争关系、搭便车构成侵害,则可以推论出利用在先作品必须获得著作权人许可、否则构成恶意。所以本文主要围绕第一、第四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本文认为,要认定同人作品是否与在先作品构成竞争关系,应当从同人作品与原作的关系、它的作用和功能方面加以研究。而搭便车是否构成侵害,在现行法律规定中是找不到确切的依据的,因而我们需要作法理上的推究,从“知识产权法保护什么样的著作法益”(著作法益一部分在著作权法中加以保护,一部分在竞争法中加以保护)入手加以研究,而研究这个问题又必须结合文本生成的一般规律及同人创作的作用加以考虑,因为知识产权法应该有利于创作以及发挥创作的正面功能,这是知识产权界的共识。以上原因促使笔者暂时搁置知识产权法上的问题,转而研究同人作品与原作的关系及其作用、功能。本文认为:第一,同人性质的创作古已有之,它是传统文化生成、传承的基础,在互联网时代,同人创作是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主要手段,是公民文化权利的体现和运用。由于同人作品具有文化“层累”功能,它与在先作品的关系主要是互为支撑的、而不是互相竞争的。第二,为了发挥同人创作的正面价值,知识产权法应将利用在先作品元素的权利普遍性地赋予社会公众,仅仅对某些不正当利用的行为加以禁止,这些行为在著作权法上已经作出明确界定,不宜利用竞争法扩张禁止的范围。当然,对于不正当利用在先作品的行为也要加以规制,这方面著作权法已经预为之计了。在同人作品著作法益保护方面,应当防止“过度保护”的倾向。
一、历史研究中的“层累”说及其对于文化生成规律的揭示
“层累”说是史学大家顾颉刚提出的一种史学理论。1922年他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写历史教科书,其间发现:“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的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顾颉刚据此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3顾颉刚编著:《古史辨》( 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2 页。1923年5月,他将该观点公开发表。该观点认为,先秦的历史记载是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 如同地质构造那样,又如同积薪,后来居上,所以越后出的历史记载,追溯的历史越向前延伸,也就是“时代愈后, 传说的古史期愈长”。4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同注释3,载顾颉刚主编书,第 60 页。并且“时代愈后, 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5同注释4。。比如对大禹的记载: 在西周的文献中, 禹是一个为大地铺放泥土、 主管山川的神灵。到春秋时期, 禹被说成是个国王, 开始从神变成人。在战国中后期,又出现了许多关于禹的详细记载, 描述禹治水的功劳, 和尧把权力让给舜, 舜把权力传给禹的过程,禹变成了夏朝开国的圣贤君主。6同注释3,载顾颉刚主编书,第 62-65、 第106-134 页,转引自袁征:《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 的重要创见 ——层累造史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载《广东社会科学》2001 年第 3 期,第77页。也就是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对于历史人物的添附会日趋丰富。
顾颉刚的理论一经提出,不啻在学界投放了一枚原子弹,它不但带来史学研究方法的革命,也冲击了国人信古、好古、尚古的传统,由此引发了关于古代历史的大辩论,该辩论被胡适称为新文化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两大辩论(另一个辩论是科玄之辩)之一,而“古史辨”这一学术流派也因之形成。7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同注释3, 载顾颉刚主编书,第 189 页。余英时评价顾颉刚层累理论的意义时说:顾说“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在史学观念上 ……突破了传统的格局”,并因而指出“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8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载《明报月刊》, 1981年第5期,转引自王学典、李扬眉:《“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第102页。。
层累理论不但给史学研究带来革命性变革,它也具有一般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对于文献学、文学、文化人类学乃至法学研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比如胡适受到层累说的启发,对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加以研究,指出这类小说不是创作者横空出世创作出来的,而是长期“层累”出来的:创作之始只有一些短小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也比较简单;经过长期发展,故事篇幅不断扩展,情节日趋复杂,人物性格也趋于丰满,从而演化成今天我们看到的长篇小说。胡适运用历史演进研究方法,对于《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等10部小说(其中也包括《红楼梦》这种文人创作的小说)加以研究,令人信服地展现了文本流变的过程及文学发展的脉络。9参见胡适《〈三侠五义〉序》、《〈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等,载《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 中华书局1998年版。
再比如有人对传说出自卓文君手笔的《白头吟》文本加以研究,指出该诗可能并非出自文君,而是诗歌层累的结果。10曹艺凡:《文君因赠白头吟?——以〈白头吟〉为例浅析中国古典诗歌的生成与层累》,载《语文学刊》2016年第9期,第101-103页。
又比如有人研究了少数民族傩舞傩戏,指明其“层累”的过程。11蒲向明:《论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的文化层累现象》,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69—73页。
又比如有人研究了少林武术偶像体系的“层累”过程。12程大力:《论层累的少林武术偶像体系》,载《体育学刊》2013年第6期,第12—16页。
甚至有人研究了中国民法中的“层累”现象。13刘颖:《中国民法中的“层累现象”初论》,载《东方法学》2015年第2期,第37—51页。
以上各种“层累”研究实际上是在进行“知识考古学”的作业,对各个学科的知识进行实证的检验,而层累研究具有普适的方法意义。
“层累”说不但提供了对于各个学科普适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知识和文化生成的一般规律:任何知识、文化都是通过层累生成的,是相关群体集体实践的结果,层累是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方式。
二、同人创作的文化层累功能及其与原作的关系
同人创作古已有之,比如上文所举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即具有同人创作的性质。同人创作产生的作品称为同人作品。有论者认为“‘同人作品’是‘同好者在原作或原型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活动及其产物’。其创作主体是 ‘同好者’,即某一原作的拥趸者、粉丝; 创作方式是‘原作上的再创作’,即通过借用原作人物,设置新环境,描写新情节来诠释新主题; 原作领域则包括文学影视、动漫游戏或其他流行文化;常见的作品种类有文学作品,漫画插图, MV,电子游戏和广播剧等。”14徐丽苑、曹莉亚:《论同人作品的出版现状及其发展前景》,载《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61页。这种概括大体反映了同人创作、同人作品的内涵和外延,本文暂时借用,不另下定义。
随着网络时代到来,文本交互活动变得非常便捷,同人创作也迅速繁荣起来。就笔者所见,同人作品利用在先作品元素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15以下对于同人作品类型的分析、归纳得到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研究生刘晓丹、徐涛、曹延征等的帮助,在此鸣谢。:1、原作的前传或后传,以原作人物和时空背景为基础展开新情节。2、使用原作人物名称、性格类型,但是另外设置时空背景,这种作品中的人物实际上已经不是原作中的人物,只是与原作人物同名同姓而已,人们称之为“架空”人物作品,《此间的少年》即属于这类作品。3、利用原作设置的时空创作新的人物、故事,比如写宋代的故事时提到郭靖黄蓉守襄阳这一金庸小说中的情节,但是小说主人翁、故事情节完全是另外构思的,借用在先作品中的时空设置主要为了增加作品的真实感。《侠盗一号》利用《星球大战》设置的时空展开故事,人物和情节与《星球大战》迥异,也是属于这种情况。4、以在先作品的主题为主题,重新设置情节、时空、人物,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乱伦主题与《雷雨》类似,而《雷雨》的写作又是受到美国戏剧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的影响,而《榆树下的欲望》的主题则来自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16乱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禁忌,围绕它组织文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它在西方文化中却是一个文化母题,曹禺写作《雷雨》显然是受到西方戏剧和文化的影响。5、戏仿作品。这类作品在同人作品中非常特殊,它往往是对在先作品的解构和反讽,一些论者把它作为对原作进行批评的特殊的方式看待。17苏力:《戏仿的法律保护和限制——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切入》,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第3—16页;季卫东:《网络化社会的戏仿与公平竞争 ——关于著作权制度设计的比较分析》,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第17—29页。6、以小说等为基础衍生出来的诗词歌赋等,比如另行创作的针对《红楼梦》中黛玉赋诗的和诗。7、诗词等剪辑聚合而成的文本,比如笔者近日就看到一首以唐诗宋词为基础的新“三句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有毒。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有雾。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A股。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要拆。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豆腐渣。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收费。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空巢。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公费。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来呼不上船,双规。”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将演绎作品也归入同人作品,本文认为演绎作品确实具有同人创作的性质,但是由于著作权法已经将其类型化,有关演绎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已然作出明确规定,而同人作品的知识产权问题法律上尚不清晰,为讨论方便,讨论同人作品相关问题时不包括演绎作品。
从文本生成的角度看,同人作品依附于在先文本,属于“次生文本”;从文化生成的角度看,同人文本与在先文本互相支撑,共同参与着某种亚文化创造,影响着大众文化的生态和样貌,诚如识者所言,“同人作品对于研究当代大众文化、性别文化、青少年亚文化、网络文化以及文化全球化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18同注释14。更准确地说,同人创作及作品是网络时代文化生成的重要方式。有人揭示同人创作对于文化生成的意义说:“特殊社会群体的建立,则揭示了意义生产的集体性,它跨越了个体的 、零碎的 、分散的解读,在不同个体间引发共鸣,形成意义的文化场域,从而彰显出迷群的社会文化力量。这些现象印证了约翰 · 费斯克所说的‘快感的来源’。他认为,快感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包括了:辨识的快感(对原初文本的语境和意义的辨识),再产生的快感(玩味新的文本语境,进一步从事再生产)、以及产生的快感(在再生产出的意象 、‘迷’对动漫的知识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三者之间生产出有意思的关联 )。他还指出,大众的快感的两种主要的运作方式是躲避(或冒犯)与生产力。因而,生产是迷群获得快感的方式 ,也是意义获得的方式。”19曹询:《虚拟社区的动漫迷文化实践模式研究——以 〈圣斗士星矢〉 动漫迷为个案的质化研究》,载《青年研究》2011年第4期,第80—81页。说得多么中肯——文本的再生产产生快感,进而形成意义的文化场域——这揭示了同人文化形成的原因和机制。(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上面引文中的“迷”、“迷群”及后面引文中出现的“迷”都是指的迷恋某文本的“粉丝”或“粉丝”群体。——笔者注。)
这里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同人创作历来就是文化传承、生成的主要方式。首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支柱——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都是通过以文化“元典”为中心的同人创作而传播、发展的。以儒家为例:儒家的开创者是孔子,而孔子开创儒家的关键性行动是确定了儒学的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六经中乐经不传,故此处只言五经)。史传孔子删削六经,也就是整理了六经,但是他“述而不作”,并没有创作自己的作品,而是通过阐释六经教授学生。儒家后学继承了孔子开创的传统,“以述为作”,通过注经、解经传承和发展儒学,薪火相传,绵延不绝。这些发挥经典之“微言大义”的作品,依附于经典文本,无疑具有同人作品的性质。可以说,没有以五经为核心的同人创作,就没有儒学。当然这些创作侧重于思想方面,而不是文学方面。不独儒家的文化传承依赖于学派内部的同人创作,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也是如此。其次,从文学层面看,古典小说中的经典大都是“层累”而成,可以说都是同人创作的结晶,诗歌中也有一部分是历经多人之手“层累”而成的,至于独立创作的诗歌,用典、转化等借用他人作品元素的手法也是常用技法。再次,从历史记载层面看,如顾颉刚等人揭示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也是“层累地造”的结果,可以说是民众集体参与的“同人创作”的产物。纵观中国文化史,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同人创作”。
如果说同人作品与在先作品共同营造了某种亚文化、甚至主流文化的话,那么它们之间是否可能相互替代、进而产生竞争关系呢?也就是说,从文化的角度看两者互相支撑,是否意味着它们之间不存在替代性竞争关系呢?笔者认为判断是否造成替代,主要要看在后作品的表达与在先作品是否可以替代,也就是表达有多少重合或者是否近似、等同。从现有情况看,与原作表达替代度较高的同人作品主要是戏仿作品,这使得某些戏仿作品的侵权判断一波三折,美国The Wind Done Gone一案就是如此。20该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该作品是Gone With The Wind的续写,而在该续写中大量利用了原作的具体情节设定、表述,构成侵权。二审法院则认定该作品是戏仿作品,利用原作的元素属于“合理使用”。参见GONE WITH THE WIND DONE GONE:“RE-WRITING” AND FAIR USE,载115 Harv.L.Rev.1193,来自West Law。虽然仿作与原作在表达上可能高度相似,但是一般认为对其进行了“转换性使用”,产生了新的意义,构成“合理使用”。21同注释17。前述7种作品中还有一种作品可能大量运用了原作的表达,即最后一类作品——“聚合”类作品。通过上文所引新古诗可以看出,该类同人作品可能大量采用了原作的表达,只作了少许改动,却形成了全新的意思,这种作品不但涉嫌替代,还可能涉嫌侵犯著作权,此类作品在著作权法上是否正当值得深究,限于篇幅和能力,本文暂且搁置该问题。除戏仿作品和聚合作品外,前述7种同人作品大多没有大量利用原作的“表达”,一般不会导致对原作的替代,所以与原作并非竞争关系。当然,以上分析排除了剽窃、抄袭等情形。
多数同人作品不但不对原作构成竞争性替代,相反会起到支撑原作的作用,甚至产生“同人逆迷”(即因为喜爱同人作品,进而爱上原作)的现象。比如“圣斗士的同人文化十分发达,其影响力已超越了群体内部,使得很多原来不了解或不沉迷圣斗士的人通过同人作品也加入到这一群体中。这一现象笔者暂称之为 ‘同人逆迷 ’ 现象 ,即本来是因为喜爱原作品而创作同人作品,而现在却是因喜欢同人作品而喜欢上原作。”22同注释19,曹询文,第77页。所以认为同人作品与原作构成竞争关系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具体到《此间》,由于该作品属于“架空”原作人物的作品,情节、人物与原作均截然不同,更没有利用原作的表达,因此很难对原作产生竞争性替代。
三、“搭便车”是否必然构成法益侵害
主张《此间》违反《反》法第二条、对金作构成法益侵害的另一个主要理据是《此间》搭了金作的便车,有攀附之嫌。这又涉及一个问题:在著作权法方面,“搭便车”必然构成法益侵害吗?本文认为,在商标权方面搭便车、攀附他人商标往往构成不正当竞争或者侵权,但是在著作权方面,利用他人作品元素的搭便车行为并不必然构成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这是由创作的特殊性导致的。“研究表明,从中世纪一直到文艺复兴,写作实践较多体现集体意识与合作意识。一般而言,新作多将其自身价值和权威奠基于前人作品。此种观念一般认为写作是对前人的引申和发挥,而非脱离前人作品的凭空创造。”23Martha Woodmansee , ON the Author Effect: Recovering Collectivity, in Martha Woodmansee & Peter Jaszi, ed., The Construction of Authorship: Textual Appropriation in Law and Literature(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and London, 1994), P14。转引自黄海峰:《知识产权的话语与现实——版权、专利与商标史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版,第34页。不特西方如此,在中国更是如此,借鉴前人是创作的普遍性基础,否则会被目为游谈无根、缺乏价值,中国人对好的创作有“无一笔无来历”之夸赞,是对此种观念的印证。强调作者在创作中独到的贡献是十七、十八世纪才出现的观念,福柯认为它是一种浪漫的构建,并没有反映现代写作实践:“福柯指出,人们习惯认为作者是作品的天才创造者,作品凝聚了作者无穷无尽的意义世界;作者不同于任何其他人,在语言方面如此卓尔不群,以至于作者一旦下笔意义便开始无限的增生扩散开来。在福柯看来,此种未经省察的平常观念正好与现实相反:作者实际上并非作品意义的唯一来源;作者只是现代文化中的一项功能性概念,借助作者这一概念人们得以为限制、排除和选择;简言之,借助作者这一概念,人们可以阻止文学作品的自由流动、自由使用和自由的构造、结构和重构。”24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in Josue V.Harari ed.,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m Criticism (Ithaca &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41—160。同注释23,转引自黄海峰书,第33—34页。
事实上,任何创作都不可能脱离前人的作品,完全空无依傍的作品是不存在的。现代著作权法只是对于缺乏最低限度的独创、盗用他人作品的行为加以规范,对于正当利用在先作品的行为并不禁止。换言之,著作权法并不泛泛反对搭便车,只是要对恶意搭便车的行为——包括抄袭、剽窃等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规制。因之创作中的“搭便车”并不被普遍禁止,只有特定的搭便车行为才构成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这类情形已经在著作权法中作了规定。也就是说,借鉴前人是创作的普遍性基础,并不被一般性地禁止;因而在著作权法上允许“搭便车”是普遍的,禁止“搭便车”是例外。
此外,同人创作对原作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产生了新的意义,“意义生产的基本表现是迷对于原文本的填充、拓展 、阐发等,统称为对文本的诠释。原作品到了受众手中便成为‘读者式文本’—— 一种被不断抽空原有意义又不断填充进读者理解的开放性文本。经由迷的理解消化之后,原文本被重新分拆,成了一些支离破碎的素材,又经过改装、重组,形成新的文本意象。这些被重新诠释的文本,才是迷之间进行交流的主要对象。正如费斯克的比喻——原作品像房主,读者像租客,租客居住时,尽管房子不是自己的,但至少具体的居住实践是自己的,可以移动家具 、进行一些装饰和打扮等等。”25同注释19,曹询文,第81页。(此处“迷”指同人迷,即迷恋某文本的“粉丝”。)同人迷不但消费原作,更主要地是消费重新诠释的文本,并通过文本的交流交换意义,这时所有的作品都是他们言说自己的中介:“也可以说,表面上在言说偶像,实际上在言说自己——自己的情感 、好恶、道德评价 、个人欲望与幻想等等。”26同注释19,曹询文,第81页。这种对原文本的创造性转化当然不应受到原作著作权的限制,因为这既顺应了文化生成的规律,也符合著作权法保护创造的主旨。
结语
总之,《此间的少年》这类“架空”利用原作的同人作品,既不违反现行著作权法及商标法,也不构成对原作竞争法上的法益侵害。首先,同人作品一般对在先作品不造成替代和竞争;其次,同人创作对于在先作品之“搭便车”并不被法律普遍禁止,只有在涉嫌抄袭、剽窃等特定情况下才应加以规制。
The Cultural Layer-accumulated Function of Colleague's Works and the Legal Interest Rela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 Earlier Works on Competitive Law——Take “The Juvenile Here” as an Example
Colleague's works such as “The Juvenile Here” does not violate the current copyright law and the trademark law, nor does it constitute an infringement of competitive law interests of the originals.This is mainly because the works of colleagues generally does not cause substitution and competition for the earlier works, on the contrary, most of them support the original works, and even turn those who do not love the originals into fans.What’s more important, the colleague’s works has a function of culture layer-accumulated.Thus, in order to forwar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free ride should not be forbidden except for plagiarism.
Colleague's Works; Competition;Substitute; Free ride; Layer-accumulated
龙文懋,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