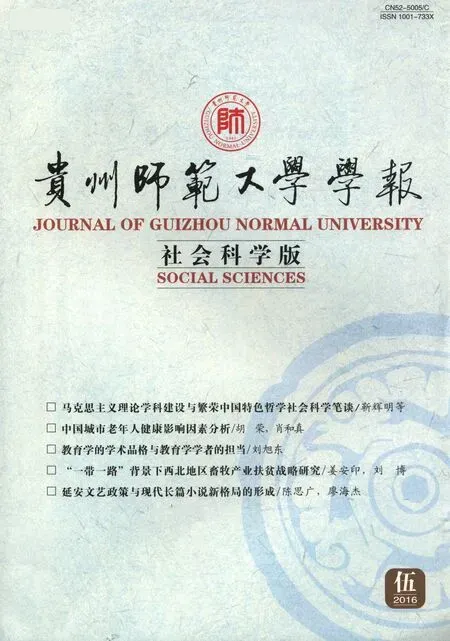教育学的学术品格与教育学学者的担当*
刘旭东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教育学的学术品格与教育学学者的担当*
刘旭东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教育学是具有家国社稷情怀的学问,原本就具有哲学的气质、优雅的气度、智慧的品格和生活本质相一致的文化内涵,充满人文关怀,它能够介入公共领域,参与公共事件。然而,在技术理性的钳制下,教育学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失却了,缺乏文化使命和担当。教育学学者要有坚定的学科意识和学科担当,关心公众利益,坚持批判的立场,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坚守自身的学术品格。要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尊重生命价值,能够在充满人文气息的语境中讨论教育问题,通过自身的专业化努力来展现其独到的专业工作领域。
教育学;学科;文化使命;社会责任
教育是天底下之于人的存在与发展关系最为紧密的社会活动,与一个人在社会中能否安身立命以及顺利成长密切相关,同时也关涉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正因为教育与人的存在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它特别需要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的滋养,如果教育活动缺失了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它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就会受到质疑,而对教育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的呵护和拓展,就是在孜孜不倦地发掘人类发展的可能性。作为以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研究为己任的教育学,它是“人类社会一切教育现象的理论形式”[1],担负着科学合理地构建教育学知识体系并能科学准确地诠释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的学科任务,在人类精神世界的塑造中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它需要以专业化的努力来展现其工作的独特价值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其独到性。然而,在体制化的条件下,作为实现体制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教育无以摆脱具有功利性的体制目标的制约和影响,常常会困扰于教育原有的理想和抱负与体制化的限制与要求之间,当其自身的力量不能与体制抗衡时,对人的发展的无限希望会在无形中被压缩为有限目标,而这亦就可能转化为教育学的知识目标。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有一股力量及时帮助它辨清方向、有一个声音及时呼唤它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教育活动就有可能摆脱干扰,教育学就仍然会坚守自身的学科方向和责任。在技术理性和强势学科的影响中,假如这一转化没有受到文化理性的批判或质疑,教育学就很可能以强势学科为模仿参照对象,将学科和知识作为目标,从关注现实的人的存在和发展转向逻辑(学科体系)和知识,沦为操作手册、工作程序般的条文,失去文化价值。而如果教育学不能坚守自身的学科立场和特性,其学科的文化理想和旨趣也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同时,在学科的社会建制不断完备的情形下,教育学要求得到自身的学科地位,就必须不断强化自身的学科性。但教育学的学科特性并不能简单地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它需要从自身的特性中去寻找,否则,所获得的学科性就可能是仿效其他学科的结果而并非是教育学的。教育学可能发生的这些变化,无不与教育学者的努力和工作目标有关,当教育学以及教育活动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困惑时,教育学学科都要反思自己的文化使命和社会担当。
一、教育学的学科品性
(一)教育学是具有家国社稷情怀的学问
自从有了教育活动,就有了对教育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总是在宽广的社会和人生的视野中看待教育,对教育的理解都与对人对自身发展的期待凝结在一起。回溯人类的教育认识的历史可以看到,人类文明伊始,人就不是通过把教育置于客体的方式来辨识它的,而是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认识教育,向往美好生活、以更好地适应生存作为教育的需要,在诸如“伏羲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的论述和“当儿童年龄稍长的时候,男子就教他们投枪,使用石斧、使用树皮制的盾、棍棒,教他们攀树、掘土、学习用(渔)网”[2]的描述中,都可以看到对教育的社会功用的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在历史的起点上,教育是关乎每一个个体生存及其质量的活动,它的目标内容以及方法都指向人自身的发展和提升人对生活环境的适应能力,具有鲜明的生活化特征,对教育的认识与对人和社会的认识相关联,对教育的理解是全景式的。后来,无论是儒家抑或智者派的教育思想与实践,都是在身体力行的亲力亲为的实践中展开的,鲜有离开具体的实践在书斋中空发议论的教育讨论。人是社会的人,是在与他人的交往和沟通中成长的,理解与把握与人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偏离这个基本点。纵观历史,但凡对教育问题的讨论,都没有离开对世界人生和社会的观照,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学本来就是一门与生活同构、和社会文化历史等与人的成长密不可分的要素息息相关的学科,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基于教育的原点考虑和认识教育问题时,充盈于教育活动中的智慧和情感以及与教育的生活本质相一致的文化内涵和浓郁的人文关怀就会无可遮拦地涌现在人们心中。
(二)教育学是由关怀和希望引导的学问
关怀和希望是教育的内在生命力,是其之所以成为教育的核心。无论哪个时代,教育都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其社会理想和抱负的,作为反映人类教育实践水平和能力的学问,教育认识和教育理论要揭示人类成长的法则,勾勒出人类未来的发展蓝图,这也是教育学要把握的基本学科逻辑。尽管历史上也曾出现把对教育的认识窄化为“授—受”或者仅仅以某种功利性目标看待教育的观点,但这毕竟是偏离教育原点、昙花一现式的,并不能成为教育学的主流学科价值观,在质的意义上,人类对教育的理论认识都是指向教育本体、指向人的发展的,它关系到人的精神的建构和理想人格的塑造,摒弃物化的教育认识,以致人们对爱是教育的出发点这一认识深信不疑。
(三)教育学是与生活相关联的学问
教育与生活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是人的生活样态。作为反映教育认识的学科,教育学在逻辑端点上要与教育的本性相一致,要反映人类内在的成长需要和生活理想,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斯·范梅南认为,生活之于教育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看来,生活本身就是探究的,变化多端是其基本特性,充满了智慧挑战,因此,“教育学的概念中所有的因素不应该被视为‘给定的’或‘既定的’;教育的意义必须到教育的实际生活中去寻找……。”“教育学的影响是情景性的(Situational)、实践性的、规范性的、相关性的和自我反思性的。”[3]教育学要以如何促进人类成长、个体发展和生命意义的建构为依归。范梅南的观点值得我们悉心领会。随着人类知识的转型,学科之间只有性质和类型的差异,并不存在等级差,要杜绝以分类划等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学科的地位和作用的传统思维方式。那么,教育学的学科特性何在?如果与其他学科做平面化的比较,就可能使教育学的学科特性在不知不觉中被湮灭。教育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教育学学科的基本特性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强势学科相区别。出于对人的成 长的关注和对人的存在状态的牵挂,教育学的任何思考都不能离开生活,离开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活的真实,这就是教育学的学科本性所在。
(四)教育学是有自身学科领域的学问
任何学科都有自身特定的研究领域,教育学也不例外。对于强势学科而言,严密的学科逻辑、知识结构和范畴体系构成了其清晰的学科范围,由此决定了可以与其他学科严格区分的研究范围、方法手段及其学科领域。教育学也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和学科范围,但这个范围不是像强势学科那样是按照逻辑结构和知识体系人为地划定的,它的学科范围决定于与人的存在和发展相关的问题的解决,其方法手段的选择也是藉此实现的,换言之,教育学的学科领域具有动态平衡性,它不像规范学科那样学科边界是既定成型的[4]。近代以来,教育学在确立自身学科地位和范围时,努力在探究自身的方法论,一直在强调避免简单照搬强势学科的做法,积极理清自身与其他学科相区别之处,在对自身学科立场进行元认知的过程中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偏离其自身的学科特性而东施效颦,就只能被别的学科所轻视,它要在自己的学科关系中建立自身的语境,由此生成有自身气质的话语体系[5]。
(五)教育学是能够介入公共领域、参与公共事件的学问
苏格拉底法是著名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实践,但它却是参与公共事务的成果。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如果人要过一种快乐的生活,政治生活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在公共生活中人才能得到这种公共快乐,而在这个过程中,行动是获得快乐的核心途径,她引用约翰·亚当斯的话说:“是行动,而非休息,构成了我们的快乐。”[6]在阿伦特这里,行动获得了与新生命诞生一样的伟大意义,她说:“行动是唯一无须事或物的中介而直接在人与人之间展开的活动。”[7]认为“行动的人能够揭示他们的自我,或者更具体地说,实际上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揭示自我,是与他人一起、为了他人而进行活动和交谈(行动)。”[8]依据阿伦特的见解,行动依赖的是“聚集在一起分享言行的民众”[8]60,通过在其中展现自己的言行并据此影响周围的人就是行动的主旨,讲理或辩论成为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重要方式。据此,教育学关注的是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如何更加卓有成效地展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力以及更好地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去促进人的发展,在此,“活动和交谈”是其在“聚集在一起分享言行的民众”间发挥作用和影响的活动方式[8]62,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行动者必须及时和连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状态,通过揭示自我以影响对方。而这种活动方式本身不具有任何的功利性,但对人来说却具有巨大的发展价值。
二、教育学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的失却
教育是通过培养人来构建社会的活动,教育的空间有多高,人的发展可能就会有多高,所构建的社会也就与之同步。长期以来,受强势学科的影响,每门学科都以其为蓝本和楷模,特别是教育学更是如此。在以往的教育学中,曾一度漠视自身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出现过“为知识而知识”或技术化的倾向,其与现实生活、与教育实践间出现了相当大的裂隙,它似乎成为只有在“象牙塔”中的那些人才能开展的“阳春白雪式”的活动,引来了诸多的质疑,令人扼腕。教育学学科发展出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学文化使命和担当的弱化
今天学科化的教育学的社会地位、学科特点与角色定位发生了变化,难以承担起社会批判的学科使命。教育现象的发生是千丝万缕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并非像自然现象的产生那样因果关系直接明了,对它的认识必须采用辩证的思想方法。然而,在教育学学科建设中,存在着以下几种思想方法。一是缺乏立场意识讨论教育问题,在讨论涉及人的成长和存在状态的话题时,很容易跟着其他学科或社会强势话语乱跑,市面上流行什么话语,就把教育赘在其后,看不到自身的学科特性。二是还原主义。试图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想方法,要将所有的教育现象还原到同一个理论框架中去认识,抹煞了教育的丰富性。三是只看到事物看不到人,把教育现象等同于一般意义的社会现象去认识和诠释,讨论社会问题时脑子里只有抽象的社会而没有具体鲜活、正在成长中的人的存在。例如,就学业成绩讨论学业成绩,把提升学业成绩的主要方法寄托在“苦学”上,似乎学业成绩与其他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无关。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教育学不顾自身特点地效仿强势学科、追逐所谓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的教育学销蚀了其文化批判性,教育学研究中弥漫着逻辑化、实证化、精确化的知识论倾向,然而,过度追求所谓逻辑实证的知识而忽视批判的思想方法,就会模糊教育学的学科理想和抱负,弱化其反思能力。以思辨和形而上学为旨趣的教育学的发展结果是以销蚀其对世界的终极意义及关怀的念想为代价,导致它对专业外的事情缺乏兴趣、见识和应有的责任感,其批判性话语、公共关怀无处体现,逐渐被社会边缘化。现代化社会是高度分工化的社会,越是如此,教育就越成为一个关乎全社会每一个方面的一般性问题、需要动用全社会的资源去认识和解决的活动。如果今天仍然像过去那样以各扫门前雪的思想方法来看待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结果一定是把影响人的发展的多方面因素原子化、静态化。然而,在面对诸多一般性的社会问题时,犹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仅能在自己狭小的专业中保持科学赋予他们的批判精神。”[9]学科化的教育学缺乏广阔的家国视野和责任感,特别是自赫尔巴特以后的教育学,受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既不能对社会现实做鞭辟入里的、透彻的分析,缺乏时代感、现实感,同时也没有学术担当,似乎自身与现实无关,甚至跟着流行话语一味地“接着说”;即便是开展批判,其对象也仅仅限于狭隘的专业内部,对整个社会的审视和对流行文化的批判能力在技术理性的制约下衰落了。
(二)以技术化的思想方法讨论教育问题
20世纪以来,工具理性成为现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在它的影响下,传统的具有浓烈人文关怀和反思感悟性的教育学知识转为技术性、功用性知识。与以往的教育认识相比,今天的教育学更看中效用,功利价值取向更为明显。比如,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实践领域:科学是对事理的揭示,关注的是事物的本质、原理、规律;技术主要是指建立在科学发现基础上的新方法、新发明,技术成果可以转化,而对科学而言则不能妄谈“转化”。但教育学中屡屡出现所谓教育研究成果转化的提法。教育是极具情境性和探究性的活动,教育研究只能是针对某个特定的情境展开的活动,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手段的选择、研究结果的使用只能适用于这个特定的情境,而“转化”必然是要离开原来的情境的,在其他情境中效果良好的方法和手段、研究结果、研究的价值等,都可能因为情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不分伯仲地把通常技术推广意义上的“转化”引申到教育学活动中,是技术化思想方法在教育学中的滥觞[10]。这种有限的学术视野阻碍了把教育问题置于广泛的社会和人生背景下予以认识的可能,结果是逐步丧失了自身的学科特性,越来越远离其本身的基点去讨论和认识教育问题,其本身地位不断下降,学科领域不断缩小,对更为广阔的社会公共生活的兴趣逐渐减弱,退守到狭隘的所谓专业领地,成为精于一艺、在自身的学科范围内自说自话的学科。
(三)缺乏对教育的终极意义的挖掘
受本质主义的影响,教育学中弥漫着演绎式的思维方式。这种“接着说”的思想方法和就知识而知识的学术目标使教育学失去了方向,它往往以回避的态度面向当下的现实问题,或者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应对现实,其中充斥着大量的被殖民的痕迹,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孜孜以求,具体生活中潜含的意义和价值被忽视了,消解了教育学的社会责任意识,难以为社会公众对当下教育及其生活提供有价值的批判性观念和思考。问题是研究的起点,问题解决是教育学选择方法手段的基准,问题之于教育学研究具有不可多得的学术意义。但在以往为知识而知识的价值取向下,教育学简单的照搬强势学科的经验方法,全无问题意识可言,学科地位及其作用受到极大的影响。这种情形在今天仍然需要引起警觉。教育学需有问题意识,要走向实践,实践绝非是哲学的一种“庸俗化”。相反,它彰显了教育学的生活世界取向,反映着教育学的担当。
三、“平庸的恶”与碎片化的研究
阿伦特曾批评“平庸的恶”,指出:“无思——没头没脑的鲁莽、不可救药的迷茫,或者是自鸣得意的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8]4在她看来,现代社会技术化、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是由于体制的力量,个人被完全同化在体制中,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违背伦理的事件,不是对个人所信奉的绝对命令进行前提反思,而是用体制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以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阿伦特的这个认识不仅是对无反思意识和能力的社会的鞭挞,也是对无为学科的抨击,对于我们深入地思考教育学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教育学之所以会沦为一门“接着说”的色彩十分显著的学科,在阿伦特关于“平庸的恶”的论述中是否可以找到一点启示?教育是需要思想和情感投入的活动。由于每个人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使得人与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种种差异。差异的存在,决定了每个人可能的思想言行、个性特征的差异,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预示着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对此只有辩证的思维方式才能准确把握这个问题,任何试图把这个问题简单化的想法都是与人的存在的真实相违背的。然而,在技术理性的钳制下,却有试图把这个问题简单化的思想倾向,给教育活动带来了诸多的困惑。例如,在所谓“高效课堂”的讨论中,不顾课堂的生命本质而对某种能够取得数量化指标的模式趋之若鹜,根本不考虑此情此境中的教与学的感受和体验,这样的课堂合乎生命本性吗?这样的认识合乎教育学的学科特性吗?
知识的目的是要指向幸福人生,要为人的幸福生活服务,正如胡塞尔所说的那样,科学世界必须回归到生活世界,任何学科如果偏离这一点,它的方向就出问题了,就可能危害到人本身,尤其对教育学来说更是如此。指向幸福人生就意味着教育学要有学科自省能力,能够对现实以及人的存在的真实状况不断地进行学科自省。然而,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起来的教育学的这种能力并没有很好地被培养出来,反而是在“接着说”的思维方式下销蚀了。多时以来,基于知识的目的的教育学研究做法给这门学科带来了沉重的负资产,以致它屡屡受到多方面的批评和抨击。对教育活动来说,知识本身不是目的,推进教育实践、促进人的发展才是有价值的选择,这也应该是教育学的学科责任。
知识的价值要在实践中展现,能够帮助人格物致知并进行清晰地反思。教育学是人文学科,它的知识构建和功能展现的方式与其他学科是有别的。对人文学科而言,那种能够帮助人们过一种沉思者的生活的知识才是有价值的,如果其内容和思维方式中缺乏了反思、感悟、情境的创设以及行动,教育学就无以展现其价值和功能了。然而,在教育学研究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碎片化”现象。例如,随着国家发展的需要和专业知识在社会发展中作用和社会发展更加走向理性化,“智库”建设成为知识共同体的重要志向,智库建设受到高度重视,这无疑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机遇,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很多机构都说自己是智库,也有人声称‘中国智库时代已经到来’。”[11]试图使自身成为能够为决策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咨询意见的智库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是,要成为智库,特别是能够对制定有长远意义的政策有价值的智库是有条件的,就必须要有强大厚实的学术根基,具有雄厚的基本理论的研究基础,能够在学理上充分分析论证教育现实问题,对某个具体的现实问题能够置其于宏观的框架下去认识和把握,其中的关键是需要有强大的基础研究作为积淀,而不是就事论事,更不仅仅是“提建议”。如是,就可能是以碎片化的研究应对现实,既与教育学理论的发展无补,也无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因为从教育的立场来讨论任何与之相关的话题,都会涉及对教育本性的把握,如果缺乏强大的基本理论的支撑,偏离教育的原点去言说智库问题,小聪明会替换大智慧,那种就事论事般的所谓对策建议是否真正有助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值得深究的。然而,现实是在教育研究中,对当下教育现实不满的多,批评的多,就事论事地提建议的多,能够真正兼具学术性和时事分析性的却不多,甚至存在不顾学术性而只谈时事分析性的现象,因而由此提出的“智”如同浮云流水,对于学科建设几乎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为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核心功能的活动,教育是在具体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展现其价值和功能的,教育学研究要遵循教育活动的这一特性,紧紧把握情境性、探究性与行动性这三个关键词,其学科特性才能够彰显。在教育学研究中,在大量的宏大无比的社会、文化、制度等辞藻下,人的发展的真实被忘却,影响具体的人的存在的复杂多样的微观因素被忽视,看不到其眼中的人的生命力和成长性。在讨论教育问题时,不是把人放到特定的情境中、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他,似乎一切都是必然如此,这也是教育学失却其学术担当的重要原因。
四、教育学学者的使命和担当
(一)教育学学者要关心公众利益,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教育学学者在研究和讨论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始终需要对人有特别的关怀,对人的成长有特别的敏感性。人是教育的对象,也是教育学研究的聚焦点,作为专业能力,教育学学者要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要对人的成长过程有深切的体察和关注。“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在于,当他对公共问题发言时,不能以自己的个体或群体的利益需求,而是应该从知识的良知和理性出发,做出自己的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如果掺杂了个人利益,那仅仅是作为一个自利性的社会成员,而非超越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12]由于每个人都生活并成长于社会中,今天的教育已成为涉及全社会每一个成员以及社会能否健全发展的公共活动,是一项民生事业,利益相关者众多,教育学学者要能够在社会的视野下关注人的存在状态,积极介入公共领域,参与公共事件的话语。由于教育理想的高远和体制化社会的目标有限的原因,教育活动必然会出现与特定人群的利益不相一致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承担社会责任、引领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健康发展,教育学学者要能够以人的发展为价值导向平衡两者的关系,关注公共空间和公共话语,与社会生活保持有机联系,努力摆脱狭隘的专业领域对自身的局限,以此彰显作为人文学科的教育学在社会公共领域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正如福柯所说:“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完成他的教育学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13]教育学对社会的关注就体现在他对人们教育理念的影响、对世事和人间万象的重新审视。如果缺少了对社会的关注、不能对公共领域的事项做出自身独到的回答,不能帮助人们正确合理地分析、纠正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言行,就难以获得其自身的学科地位,也就难以说它是一门有社会责任的学科。
(二)教育学学者要坚持批判的立场,坚守自身的学术品格
批判是社会的良心,是对社会进程的匡扶,这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学科的品格和学术责任,反映着学科的社会能力和水平。教育学固然有自身的学科立场和边界,但对它的边界和学科立场的把握不能采用其他学科、特别是不能采用强势学科的思想方法。如上文所述,强势学科是依靠学科逻辑和知识体系来搭建自身的学科体系和区分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的,但作为实践色彩浓郁的学科,教育学的学科边界及其学科体系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具有通透性的,实践水平和能力是改善其通透性的重要途径,这是教育学学科的特性所在[14]。这就决定了教育学学者不能把自身囿于所谓教育的范围内,在学科建设中要避免自然科学化,需要不断地对其学科立场进行反思和澄清。社会总是在不断的反思与否定中进步,教育学学者要成为“ 社会的良心” 和“时代的眼睛”,必须始终具有批判的精神,以冷静的思考去形成自己的观点,反思社会价值的保守和无知,批判所在社会的丑恶与积弊,以纯理性的论证去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社会批判是从社会良知出发,并运用高深知识,评论各种社会问题,反思无可非议的信念、不证自明的真理,以及实践者常识性的理解,从而揭示出有可能阻碍实践进程的前提性条件,最终提出实践过程的价值取向。”[15]多时以来,学科化的教育学往往是在“接着说”的范式下获得自己的学科地位的,然而,这种学科范式是违背教育以及教育学的本性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并不是要求教育回到与“工作”对立的那个所谓“生活”去的,而是说人生的全部的内涵都是生活,而生活生生不息、变化无穷,任何要窄化生活、将生活模式化的观点和做法都要受到质疑和批评。为此,教育学学者要具有批判的情结,要能够对现状时刻抱着不满和质疑的精神,对社会变化具有特别的敏感性,要能够在充满人文气息的语境中讨论教育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就是极好的范例。在他们的认识中,始终有真切的家国天下的情怀,有对人生的深刻感知和体验,有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在社会分工不断趋于精细化的条件下,教育学学者要受分工的支配而成为专业人士,但他必须“介入” 关乎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公共性问题”,能够在人的完整统一性中去把握人,不能缺乏严肃的社会使命感,他不能简单化地以原子论的思想方法看待教育问题,而要在宽广的社会、历史、人生、自然的视野中去把握教育。
(三)教育学学者要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尊重生命价值
人是教育的对象,但人并非是抽象孤立的存在,他是有生命的社会化存在物,讨论教育,不能离开对生命的关注。教育学学者对生命要有深刻的体悟和认识,能够准确把握生命价值的构建、帮助人彰显生命价值。人的生命具有唯一性,弥足珍贵,不可替代和重复,但生命的价值具有无限的发展和开拓的可能。生命的价值是在不断拓展的社会实践中流露出来的,其间最有价值的是能够在社会实践中构建出和谐的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在实践社群中展现个人的能力和水平,而这本身就是教育,正如杜威所说:“社会生活不仅和交往完全相同,而且一切交往(也就是一切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具有教育性。”[16]教育学学者就是要探究人类的交往活动形式的多样性,能够清晰地把握生命的流淌性、偶然性、能够在“润物细无声”和“滴水石穿”的思想方法(价值观)的指导下审视人的成长和制定教育活动的规划。
(四)教育学学者要有浓烈的、坚定的学科意识和学科担当
任何一门有担当的学科都会有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以此建构自身的学科地位和发挥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教育学能够建立自身的教育学话语体系,能够有立场、有思想、有方法地来分析评鉴教育现象和教育现实。萨义德指出,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17]由于教育是在社会文化历史中实现其促进人的发展的价值的活动,教育学学者在讨论教育问题时,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所谓纯教育学知识上,而要对与教育活动有重大影响的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价值观念以及关于自然、人生的终极问题予以深切关注,能够以严谨的学术思维、渊博的学识、缜密的思维、人文的情怀格物致知、明辨事理,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良心。应当看到,现在的社会现状对教育学学科有重要影响。只要教育学学科敢于面向社会现实、为寻求公平正义而为弱势群体代言、具有批判意识,他就很可能遭到权力中心话语的排斥而被边缘化,但这正是教育学的学科本性所在,以往的教育学之所以存在诸多的困境和问题,就是由于它太想和其他强势学科一样、太想使自身与权力中心话语为伍,反倒失去了自身的学科特性。此外,教育是具有强烈自身特性的社会活动,“正人先正己”是其展现自身文化品格的核心方面,行动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8]。对教育的理解与教育学学者个人的人生理想、人生经验和育人实践密切相关,需要将其置于社会、人生这样一个宏大的框架中,体现的是个人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能力,具有强烈的个别化色彩。
[1]胡德海.教育学概念与教育学体系问题[M]//范鹏.陇上学人文存.胡德海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117.
[2]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一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9.
[3]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21.
[4]刘旭东.回到原点:论教育的学术传统[J].教育研究,2013.
[5]刘旭东.教育学的困境与危机[J].教育研究,2005(11).
[6]陈伟.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31.
[7]王寅丽.在哲学与政治之间: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59.
[8]伊丽莎白.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M].刘北成,刘小欧,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60.
[9]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89.
[10]刘旭东.论回归教学研究的原点[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11):3-7.
[11]向勇.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研究机构的学术理想——兼论高校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功能定位[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
[12]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6.
[13]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47.
[14]刘旭东,马丽.提升边界的通透性:教育的实践性诉求[J].教育研究,2012(6).
[15]周玲,谢安邦.社会批判:大学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与学术责任[J].现代大学教育,2006(2).
[16]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6.
[17]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12.
[18]刘旭东.论回到教育的原点和教育理论创新[J].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5(1):5-10.
责任编辑周莹洁英文审校孟俊一
The Cultural Miss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Scholars in Pedagogy
LIU Xu-d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Pedagogy is the knowledge that owns the country and home feelings, and has the philosophical temperament, graceful tolerance, the wisdom character 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life essence; it is full of humanistic care and is able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events in public sphere. Nevertheless,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ultural mission of pedagogy has lost and was lack of cultural mission and obligation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Scholars in pedagogy should has firm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subject responsibility, concerned about the public interest, adhere to the critical position, have a strong sense of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and stick to their own academic character. The scholars in pedagogy should have a strong sense of life consciousness, respect the life value, to discuss the educational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full of humanistic atmosphere and to demonstrate its unique professional field through their own professional efforts.
Pedagogy; Subjects; Cultural miss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2016-08-12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14年度一般课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教育的学术传统研究”(BAA140016)的阶段性成果。
刘旭东(1964-),男,广东揭阳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课程论研究。
G621
A
1001-733X(2016)05-0060-08
——《教育学原理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