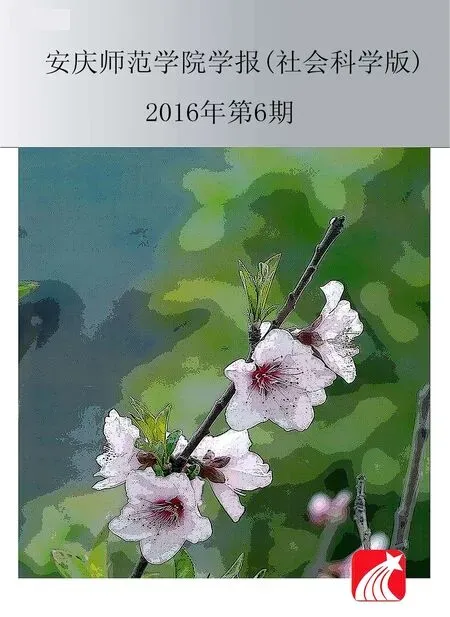华盛顿·欧文《纽约外史》中的反启蒙思想
黄贺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外语教学部,北京100048)
华盛顿·欧文《纽约外史》中的反启蒙思想
黄贺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外语教学部,北京100048)
《纽约外史》通过对纽约历史的诙谐评述,讽刺了小说创作时美国的诸种社会现象和文化心态。小说背后的思想主线是对启蒙思想的讽刺和抨击,包括对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否定,对自由主义政治的批评以及对理性主义的嘲讽。这些反启蒙思想构成了小说的思想基调。
华盛顿·欧文;《纽约外史》;反启蒙思想
《纽约外史》(A History of New York,1809)的出版是时年26岁的华盛顿·欧文在文学舞台上的正式首秀,为欧文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小说虽然标榜为书写纽约历史,但绝非严肃的历史叙事,而是欧文借历史研究者“迪德里希·尼克博克”(Diedrich Knickerbocker)之名以戏谑的口吻讲述纽约在荷兰人殖民统治时期的纽约历史人物和事件,中间充塞了诸多逸闻趣事,行文风格讥诮夸张,是一部趣味十足的漫话式野史。对于这部“外史”,评论者一般认为其中的种种幽默讽刺绝非漫不经心的谈笑打趣,如刘荣跃就在其译本序中指出,小说的内容“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刘荣跃《纽约早年的那些事儿》[1])。也有Inkso等国外评论者通过对小说的文本探究,挖掘欧文在荒诞不经、充满插科打诨的叙述中透露出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文化心态。这些倾向和心态不仅迎合了当时的思想潮流,也通过小说的流行深度影响了公众的社会立场。正如Inkso所说,“作为作家的欧文不仅被其作品创作时代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文化焦虑所塑造,也帮助塑造了这些冲突和焦虑”[2]。本文结合之前的研究,认为作品中最为显著的一条思想暗流是对启蒙思想的讽刺和批判,这些反启蒙思想构成了小说的话语基调,是小说思想内涵的核心组成部分。
一、华盛顿·欧文的反启蒙思想
启蒙思想和反启蒙思想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是独立和平行的存在,而是在社会思想中互相交织、撕扯。启蒙思想在英国发端,兴盛于18世纪的法国,继而形成了一场席卷欧美的政治思想运动。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的旗帜,主张用知识扫除蒙昧,用科学代替神学,宣扬自由、平等、进步、法制等观念。这些思想波及社会政治与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推动了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确立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思想框架。
然而,如以赛亚·柏林所说:“对法国启蒙运动及其在欧洲各国的盟军和弟子的核心观念的抵抗,与这场运动本身一样古老。”[3]启蒙思想自一开始,就有诸多反对者。他们质疑启蒙思想宣扬的理性求知方式和事物的普遍规律性,否定启蒙思想者持有的进步主义信条和他们支持的民主政体,认为启蒙思想所鼓吹的理性、自由、人权等信念抹杀了人类神圣的精神力量,带来了道德的堕落和欲望的泛滥,从而致使社会陷入暴虐和腐败的无秩序状态。到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作为启蒙思想的直接政治实践,带来了种种暴力、流血和恐怖事件,加之革命并未能兑现它所宣布的目标,使得这些反启蒙话语开始聚力,拥有广泛的支持者。
欧文在创作《纽约外史》时,同样作为启蒙思想直接产物的美国革命已经尘埃落定,以自由、人权和法制等启蒙理念为立国根基的共和国开始蹒跚起步。小说出版的1809年恰好是杰弗逊政府执政十年的结点,而杰弗逊作为启蒙思想者在北美的代表人物更是以其信奉的启蒙思想为执政圭臬,被称为“最有民主做派的美国国父”。杰弗逊在执政中坚决捍卫民主和平等的理念,坚持平民立场,施行的政策方针同当时持精英主义立场的商人、银行家和工业企业主的利益多有抵触。代表这些群体利益的联邦党作为反对党自然同杰弗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处处针锋相对。出身富商家庭的华盛顿·欧文便是一位激进的联邦党人,同杰弗逊分处政治光谱的两端,加之家族的生意受到了杰弗逊政府出台的《禁运法案》的巨大冲击,对于杰弗逊任上的诸多内政外交政策都颇有怨怼。在批评民主-共和党人在一系列事务上的政策立场的同时,欧文也难免流露出对于启蒙思想的部分理念及其影响的反思和质疑。
此外,欧文所怀有的反启蒙思想也和当时尚未结束的法国革命浪潮有关。到了《纽约外史》创作的十九世纪初,大革命洗礼下的法国经历了暴力革命的杀戮和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政,继而又被拿破仑篡取了政权,建立起波拿巴王朝。虽然法国革命以自由和人权为旗帜,但革命中的血腥暴力和恐怖统治令整个欧洲为之战栗,加之革命未能成功地建立民主政权,反而带来了新的专制统治,都使西方世界对启蒙思想和革命感到深深的幻灭。血淋淋的事实使人们对启蒙思想产生了怀疑,此时涌起的反启蒙思想认为正是启蒙思想带来了法国的种种流血和动荡,因为“启蒙哲学及其个人理性主义,对宗教进行攻击,腐败道德、颠覆权威;带来狂热、激情,招致暴力和罪行;社会秩序由此丧失,最终法兰西处于堕落和腐败的状态”[4]。这样的反启蒙话语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尤其是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打着自由、平等的口号大肆逮捕和杀害异见人士,其中著名的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也被投进监狱,判处死刑。潘恩虽然因为美国政府的营救而侥幸逃脱,他的经历却在美国国内引起广泛关注,使许多美国民众开始认为以启蒙之名进行的革命已然堕落,成为滋生激进暴力的源头。
欧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曾两次旅居欧洲,亲自目睹过血腥革命的他对于革命持坚决反对态度。他称法国革命为“残暴的革命”[5]341,对法国革命尤其是拿破仑政权始终持批判的态度。在他给家人的信件中,欧文对革命者的暴行大加讽刺,对篡夺政权的拿破仑也是怒言相向。当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消息传来时,欧文大为振奋,在信中写道:“对于这位傲慢的好色之徒来说,此前的任何吹嘘都变成了最为尖锐的讽刺”[6]。在批判法国革命之余,欧文对于革命背后的启蒙哲学意识形态自然也产生怀疑。
在《纽约外史》中,欧文的反启蒙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于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否定,对自由主义政治的批评,以及对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嘲讽上。通过讽刺和抨击启蒙思想的这些基本观点,欧文成功地揭示了启蒙思想在其社会政治和文化实践中所显露出的诸种弊端。在其所处的那个启蒙思想的影响力仍如日中天的时代,欧文通过《纽约外史》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二、小说对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否定
《纽约外史》首先通过评述欧洲人在新大陆的殖民历史,揭露了在“文明”和“进步”的幌子下所发生的血淋淋的殖民史,彻底否定和颠覆了启蒙思想所假定的进步主义历史观。
作为一部述说历史的小说,《纽约外史》对于启蒙思想最强有力的挑战在于其对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否定。“进步”是启蒙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启蒙思想者们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从原始走向高级、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进步过程,进步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普遍规律。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知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是在不断进步,前一个阶段优于后一个阶段,目标是臻于完美。正如启蒙思想家孔多塞所言:“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遏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这种进步所经历的行程可能或快或慢……但是……这种进步绝不会倒退。”[7]2-3
启蒙运动运用进步主义的历史观挑战过去的权威,解释革命和变革的合理性,然而其问题在于它用统一的优劣标准来衡量不同的文明社会,把文明与野蛮清晰地区分开来,并主张“先进”的文明应该教化、改造“落后”的文明,从而“为欧洲殖民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8]35。孔多塞就认为,在亚洲和非洲“辽阔的国土上有着大量的民族,他们有的地方仿佛就只是在期待着接受我们的办法来使自己文明化”,“他们许多世纪以来都在召唤着解放者”,或者甚至“气候的恶劣使他们远离了已经完善化了的文明的甜美”,“随着他们将被文明民族所驱退,人数缩减得更少,他们终将不知不觉地消灭或者是消失在文明民族的内部”[7]159。通过殖民活动,“欧洲的居民在那片广阔无垠的土地上迅速增长,难道不会使仍然占据着广大国土的那些野蛮民族文明化,或者甚至于不须征服就会使之消失吗”[7]157。文明和进步显然已经成为侵略和殖民活动的思想后盾。
欧文在《纽约外史》中就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通过戏仿和讽刺等手法对于欧洲殖民者以文明开化为由对美洲土著人赤裸裸地掠夺和血腥屠杀提出了批评,并否定了其背后的进步主义历史观。在小说卷一,尼克博克在戏说欧洲殖民者对于美洲大陆的征服和殖民历史的时候,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解答这个问题:“在美洲登陆的首批发现者们有什么权利,在未经土著居民的首肯下,也没有因为占领了他们的领土而给予足够的补偿,就攫取了一个国家呢?”[5]40尼克博克操着假装严肃却又极为讽刺的口吻列出了四种权利予以解答:一是“发现权”,即对于无主的领地,发现就意味着获得,因为在欧洲人看来,美洲大陆上的土著虽然“能够用双脚直立行走,有着类似人类的面孔,喃着一些无法理解的声音,极像语言,同人类极为相似”,然而这种“双腿行走”的物种“不过是些食人族和可恶的怪兽”,拥有种种野蛮的习俗,“不仅用人祭祀,而且茹毛饮血”,哲学家培根都称其为“被自然法则所摒弃的人种”[5]41。这种被尼克博克反复提到的“自然法则”,其中无疑就有启蒙思想者们口中的“进步的自然规律”,它已然成为殖民者们把土著等同为非人的野兽,从而予以大肆掠夺和屠杀的主要借口。尼克博克列出的第二种权利是“开化权”,即对荒野开发和利用的权利,这是“自然赋予人类的义务”,“每一个民族都被自然法则赋予了开发其拥有的领土的权利”。而那些土著人既然不能开发土地,却靠掠夺生活,“就应当像野人和恶兽一样被清除”,这是“天意”[5]43。第三种权利是“文明权”,即拥有更加“进步”文明的欧洲人给土著人带来的更为先进的文明,让他们享受到了“舒适的生活,包括朗姆酒、杜松子酒和白兰地酒”[5]45。白人拥有更好的医疗技术,在给土著人输入了大量疾病的同时也“计划好了能予治愈”[5]45。通过同白人的交往,土著人成功地学会了“欺骗、撒谎、诅咒、赌博、争吵、相互残杀,简而言之,在所有能显示出那些基督徒更优越的文明方面都更胜一筹”,假以时日,他们终将与“最为开化、文明和正统的欧洲民族相匹敌。”[5]46最后,殖民者以文明开化的名义,通过“战争、剥削、压迫、疾病”等种种手段,“终于把野蛮的土著人全部消灭”[4]47。既然“土地的原始所有人都死亡殆尽、埋身黄土,无人剩下来继承或索求土地”,欧洲人自然就理所应当地占领了这些土地,这又构成了殖民者的第四种权利——“灭绝权”或“火药权”[5]47。
尼克博克所分析的这四种权利以戏谑的笔锋犀利地揭露了殖民者打着文明进步的幌子所做的野蛮行径,颠覆了进步主义历史观关于进步的神话。欧文甚至进一步天马行空地想象:“假如月球的居民……达到了令人嫉妒的完美状态”,有着“最为高尚和优越的哲学”,却发现地球人处于“极度的无知和堕落之中”,便决心将“理性之光,月球的慰藉带给地球人”,也会占领地球,进行文明开发[5]49-51。他们因而会“毁灭我们的城市”、“让我们皈依他们真正的信仰”、“礼貌地将地球人请进荒凉的阿拉伯沙漠或冰封的北欧去居住,让其真正地享受文明的赐福,感受月球哲学的魅力”[5]51。这种关于“完美”、“理性”的话语逻辑同孔多塞等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几乎毫无二致。而月球人占领地球后的做法又是对于欧洲殖民者种种恶行最具讽刺效果的描摹。欧文在此向我们指出,“真正野蛮的却是所谓的‘进步’”[9]。
欧文在《纽约外史》中对于“进步”这一观念的打趣与抨击比比皆是,这既源自于他对杰弗逊执当局所热忱倡导的进步主义理念的厌恶,也折射出作家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批判眼光。在尼克博克对荷兰人殖民史的评述中,纽约(当时称新阿姆斯特丹)所处的新尼德兰地区在三位总督的先后治下不仅没有任何进步,反而是不断倒退和堕落的。当沃特·凡·忒勒任总督时,新尼德兰处于黄金时期。这位总督睿智、开明,尼克博克评价他为“管辖(新尼德兰)这个古老而可敬的地区的首位也是最好的一位总督”,因为“在他如此平静而仁慈的治下,我甚至没有发现任何一例罪犯被绳之以法的情况”[5]92。但他的继任者,被称为“易怒者威廉”的威廉·基夫特却是一个“身材娇小、举止灵活、尖刻易怒的老绅士”,“他炽热的灵魂……不断地为他招来最为猛烈的口角、争执和祸端”[5]137。在他的管辖之下,新尼德兰陷入一片混乱,“居民们始终惊恐不安,又意志消沉”[5]150。最终专断而好战的末任总督彼得·斯托伊弗桑特,又称“顽固者彼得”,则丢掉了荷兰人对新尼德兰的治权,将其拱手让给了英国人。尼克博克所描述的荷兰人对纽约的殖民史,完全是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全方面的倒退和堕落史。这其中作家对于进步主义历史观的讽刺意味十分明显。正如有评论者指出,“所有尼克博克的胡言乱语都有着严肃的目的……旨在推翻关于美国历史和文化的进步论的阐释”[10]。
三、小说对自由主义政治的批评
《纽约外史》中的大量篇幅都是对殖民地时期纽约社会政治情况的描述,这是欧文在借古讽今,讽刺美国的政治体制并借此表达对杰弗逊执政当局的不满,其内涵则在于抨击启蒙思想所推崇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和体制。
“自由”是启蒙思想举起的另一面旗帜,它强调人类个体的自主性和判断力,主张个体应该拥有自由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而不受神权或他人的控制。正如康德的名言所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1]启蒙思想家们认为,社会应该构建于个体自由的基础之上,社会政治的运行和权力的使用要处于契约即法治的约束下,从而建立起一个“保证个人行使自由的制度基础”[12]46。这一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旋即成为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新成立国家的政治组织原则,以分权、法治、代议、少数服从多数等原则为规范的自由民主政体成为诸多欧美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并延续至今天,成为现代国家的主流政体。其中,以托马斯·杰弗逊为代表的美国国父们在新大陆所建立的美式民主政体更是对卢梭等人的启蒙政治思想的首次实践,被广泛认为是自由主义政治的典范。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启蒙思想家们所推崇的自由主义政治体制远非完美,自其实践之初就出现了种种问题。首先,自由主义政治对于个体意见和自由的强调以及对顺从和权威的贬抑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权力的分裂,阻碍积极的政治进程。这在美国政治中表现得极为明显。美国所实行的“新联邦制度以及它的‘胜者全拿’、单一席位选区和投票形式”直接导致了党派政治的盛行[12]63。在欧文的时代,“联邦党和民主党在内政、外交政策上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针锋相对,对权力展开争夺,突出表现为各党派通过选举争夺对立法机构的控制,因而催生了政客们争相煽动民意支持并互相攻讦(mud-slinging)的选举政治”[13]。欧文在《纽约外史》中借尼克博克之口对此有着形象的描述:“两个政党就像两个恶棍一样,各自执住我们国家裙子的一角;最后他们只会衣衫尽脱,恶行毕露。”[5]2
作家在小说中大量揭露并猛烈抨击了自由主义政治对社会政治的割裂。据尼克博克对纽约殖民地时期历史的描述,在忒勒总督治下的黄金时代,“既没有党派、宗派、分裂,也没有迫害、审判和惩罚”,这样“人人都可以幸运地照管自己的事务”,整个地区一片清明,繁荣兴盛[5]100。然而在“易怒者威廉”的治下,新尼德兰的居民们开始分成不同的党派,“用无数极为肮脏丑陋的字眼和名称互相抹黑”,“每一派在抹黑政敌的人格、损害对方的利益时都虔诚地相信自己是在效忠国家”[5]172。两党尽管立场迥异,但“在一件事上却不谋而合,即无论政府的举措是对是错,都要对之百般挑剔、大加挞伐”,这只是因为政府不是自己在选举中所支持的,他们毫不关心“政策的成败与否和国家的兴衰”[5]172。党派和议会政治的缺陷到了末任总督彼得时期显露得更加明显,最终成为导致荷兰人丢掉新尼德兰治权的致命因素。面对英国人咄咄逼人的侵犯时,新尼德兰议会中的两党却还在就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争吵不休,以至于贻误了应对的时机。议会中的议员们只擅于作长篇大论,整日无所事事,“只期待着否决提出的所有防卫计划”,“挥霍了紧急势态下无价的时间”[5]318。当英军兵临城下时,他们却抱头鼠窜,龟缩在家,“把临街的门闩上,藏身在酒窖里,不敢向外张望,生怕自己的脑袋被炮弹炸飞”[5]319。然而当彼得总督组织防卫时,他们却假装代表民意,以爱国的名义煽动民众向总督请愿,要求接受英国人的招降,苟且求和。在民心大乱、回天无力之下,总督不得不接受投降的命运。所以尼克博克在陈述完这段历史之后感叹道:“这样一座著名而可敬的小城,处于这片广阔的尚未开化却欣欣向荣之地的要塞……其命脉却为内部的派系纷争和骚乱所撕裂和折磨!”[5]331在尼克博克看来,纽约城的悲剧无异于被罗马军团围困下的耶路撒冷,“当以色列人尚在派系纷争、互相割喉之时,罗马皇帝提图斯的大军已经掀翻了他们的壁垒,将火与剑带进了他们神庙中的至圣所”[5]331。这无疑既是对小说创作当时高度撕裂的美国社会和政局的警醒,也饱含着对于这一问题背后的思想根源——自由主义政治的批评。
在《纽约外史》中,欧文对于杰弗逊所大力标榜和热忱倡导的美式民主在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和乱象有着入木三分的描述,让读者不得不开始反思:在启蒙精神中孕育出的自由民主政体真的是完美无瑕、无懈可击的吗?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言论自由。启蒙思想认为言论自由是已经从神权和暴政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公民所应当拥有的首要基本权利,但在现实的政治游戏中,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往往会泛滥成肆意的批判和攻讦。尼克博克在小说中戏谑地评说道,欧洲人从登上新大陆那一刻起,就认为舌头的独立是自己的一项特权,开始提高音调,整日喧哗。这一特权“在报纸、传单、病房会议、酒馆委员会和议会审议中被大发利用,确立了人们空洞无物地交谈、歪曲公共事务、诋毁公共政策、诽谤大人物、毁灭小人物的权利;简而言之,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守护神,言论自由,或者是更通俗的叫法,饶舌自由”[5]119。在欧文所看到的美国政坛中,言论自由已经变成了政治势力互相诽谤、攻击,煽动民意以满足私欲的托词。这无疑是民主政治的重大缺陷之一。诚如托多罗夫所说,“如果人们得益于民主的公共空间里通行的表达自由,却采取一种普及的诽谤的态度,批判就会变成一种无所产出的免费游戏[8]62”。欧文把对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政治的批评寄托在尼克博克所述的新尼德兰社会中,在那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毫不负责的抹黑与批评已然成为一种免费游戏。
自由如果不加任何节制不仅会带来社会和思想秩序的混乱,其本身也是极为虚伪的。尼克博克也不无犀利地指出,殖民者虽然标榜宗教信仰自由,却仍然残酷地“驱逐、鞭笞或吊死各类异教徒,包括天主教徒、贵格会信徒和再洗礼派教徒”,因为“只有正确的思考才配拥有宗教自由,否则就是异端邪说”[5]120。自由主义的虚伪跃然纸上。欧文在《纽约外史》中对于自由主义政治的批评并不仅限于影射出当时美国政局中的丑行及乱象,也更为深入地批判了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质疑了它的合法性,这反映出了欧文的思想深度。
四、小说对理性主义的嘲讽
除了“进步”和“自由”,《纽约外史》中另一个对启蒙思想的攻击火力点集中在又一个启蒙核心概念——“理性”上。小说中充斥着反理性思想,对理性主义大加挞伐,也揭露出过分强调理智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
理性是启蒙思想的要义,因其核心主张即用理性之光驱散封建专制和神权加诸人们思想之上的蒙昧。因此,启蒙思想认为人类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智认知自身及世界,用理性求知,并让知识为人所用,从而推动文明的进步。知识就是力量,这成为启蒙运动的基本信条。在启蒙运动的洗涤之下,对理性主义的笃信开始成为社会风尚,知识、理性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和福祉、进步紧密绑定。理性主义的信奉者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就依赖于人类的知识进步,或说进步全赖理智方面的启蒙和进步”[14]246。
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理性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塑造力量之一,但它在带来了知识爆炸和物质文明的极大繁荣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缺陷。对于纯粹理性和知识的强调往往会使人忽视德行的培养,导致社会道德的退化。理性主义“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即认为理智进步必然导致道德进步”,然而事实是“理智进步并不必然导致道德进步”[14]247,而且法国大革命以降的历史一再证明,过分推崇理智反而会带来道德的沦丧和精神的堕落。此外,理性主义过分夸大了理性的认知作用,自负地试图用科学、逻辑来解释和掌控一切。在其影响之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只有知识,没有智慧”,人类反而陷入了新的蒙昧、狭隘和无知[14]253。
《纽约外史》“这部华盛顿·欧文最早的作品主要的打趣对象就是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的种种假定”,其中“充斥着尼克博克的反理性主义思想”[15]。欧文在小说中借尼克博克之口对知识和理性的化身——哲学和哲学家们大加嘲讽。在尼克博克看来,标榜着求知求真的哲学家们不过是通过提出一个又一个的理论来解释世界,而他们的理论总是自相矛盾,与事实相悖。“当发现世界的运行不符合自己的理论时,他们又识趣地改变自己的理论来和世界相符”[5]17。因而哲学不断地提出一个个新的毫无实用的理论,只能让人对世界感到越来越困惑。尼克博克指出,知识的生产往往充斥着主观的想象,与真理相差甚远,毫不可信。此外,空洞的知识非但不能让人更加睿智,反而会使人变得行事荒唐、愚蠢可笑。这典型地体现在新尼德兰的第二任总督威廉·基夫特身上。他毕业于海牙的一所知名学院,学识丰富,“曾勇敢地学习过一些死去的语言”,也曾“深入地探究过某些玄学知识”[5]138。他还能言善辩,喜欢“在逻辑推理和抽象的辞藻中让自己陷入自相矛盾和困惑的迷雾里”[5]138。这样的一位被称为“全科天才”的总督“极热衷于哲学和政治试验”,因为他的大脑中“满是关于古代共和国、寡头政治、贵族政治、君主政治……等知识碎片的残留”,所以不停地把它们一个个引入到新尼德兰来[5]139。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使社会管理陷入混乱,“在一个另一个的互相矛盾的措施中,新尼德兰这个小省份的政府在他的治下打了无数个结,让以后的半打继任者们都无法解开”[5]139。威廉·基夫特无疑是杰弗逊等崇尚启蒙思想的美国政客的化身。在欧文看来,他们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知识和设想,过于自信地推行启蒙思想所设定的美好政治制度,但实际上却把美国社会带入了可怕的泥沼。
社会道德的堕落是反启蒙思想抨击启蒙思想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纽约外史》中欧文借以批评理性主义的根据。在尼克博克的眼中,人的知识和理性只能让社会变得混乱和堕落,他多次哀叹自己“生在一个堕落的时代”,向往纽约在忒勒总督治下的黄金时期所拥有的“单纯和道德”,并憧憬道:“回去吧——回到那充满了单纯和惬意的甜蜜时代!”[5]81在那个单纯的时代,新尼德兰并没有种类繁多的法律,社会却更加清明,没有政治分裂和吵闹,也没有对穷人、乞丐、流浪汉和女巫的残忍迫害;人们受的教育更少,却充满美德,过着恬逸平静的生活;商人们按照习俗经商,不受任何政策的约束,经济繁荣,民众生活富足。而这一切美好都被所谓的智识人士(intellects)以及他们假托着进步和为人民谋取福祉的名号所引入的经济政策和法律体制毁灭殆尽。欧文托尼克博克之口所讽刺和抨击的正是知识、理性以及依赖它们所建立的“美国法律、商业和政治秩序中的偏差、自私和虚伪”[16]。
小说《纽约外史》名为陈述历史,实为华盛顿·欧文通过外史式的诙谐评述对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进行的一次检视和反思。同样年轻气盛的作家欧文在小说中托言尼克博克戏谑地打趣和抨击了小说创作之时的美国种种社会政治现象与思想心态,在其背后最为显著的一条主线是欧文对于当时影响力正盛的启蒙思想的讽刺和批判。这些反启蒙思想是解读《纽约外史》的切入口,也是理解小说思想内涵和话语基调的关键之处。
[1]华盛顿·欧文.纽约外史[M].刘荣跃,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9.
[2]INKSO J.Diedrich Knickerbocker,Regular Bred Historian [J].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2008,43(3).
[3]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
[4]张智.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反启蒙运动[J].浙江学刊,2008(6).
[5]IRVING W.A History of New York[M].New York:Penguin Books,2008.
[6]IRVING P M.The Life and Letters of Washington Irving[M]. New York:GP Putnam&Son,1864:205.
[7]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M].何兆武,何冰,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8]茨维坦·托多罗夫.启蒙的精神[M].马利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9]MCCANN J.Washington Irving,A History of New York,and American History[J].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2012,47 (2).
[10]FERGUSON R A.“Hunting down a Nation”:Irving’s A HistoryofNew York[J].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1981,36(1).
[1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2.
[12]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M].殷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3]黄贺.《瑞普·凡·温克尔》中的政治反讽[J].宿州学院学报,2015(3).
[14]卢风.启蒙之后——近代以来西方人价值追求的得与失[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
[15]HEDGES W L.Knickerbocker,Bolingbroke,and the Fiction of History[J].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59,20(3).
[16]HEDGES W L.TheKnickerbockerHistoryas Knickerbocker’s‘History’[M]//Ed.WilliamL.Hedges.TheOld and New World Romanticism of Washington Irving.Westport:GreenwoodPress,1986:153-165.
责任编校:汪长林
TheAnti-EnlightenmentThoughtsinWashingtonIrving’sAHistoryofNewYork
HUANG 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Department,Chin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Beijing 100048,China)
A History of New York satirizes var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phenomena as well as cultural ideologies in America at the time of the novel’s writing through a comical narration of New York’s history.The novel manifestly embodies anti-Enlightenment thoughts,including criticism of historical progressivism,political liberalism and rationalism,which constitute the basic narrative tone of the novel.
Washington Irving;A History of New York;anti-Enlightenment thoughts
I712.074
A
:1003-4730(2016)06-0067-06
时间:2017-1-20 15:3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70120.1533.014.html
2016-08-29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华盛顿·欧文作品的历史内涵”(14zy015)。
黄贺,男,安徽淮北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外语教学部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6.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