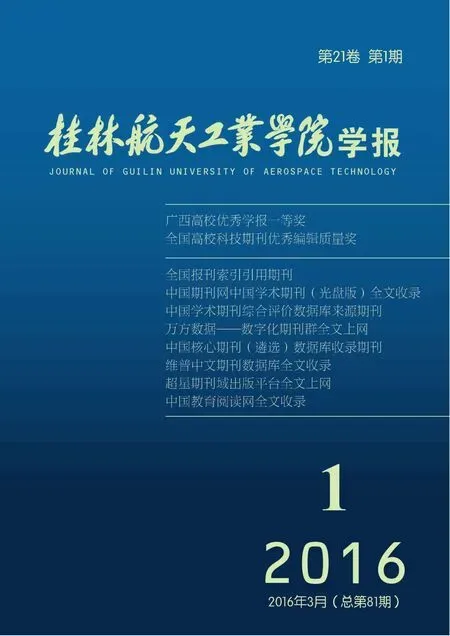灵欲合一的情色生活*
——论《遇合奇缘记》的女性身体书写
黄茜子 刘奇玉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灵欲合一的情色生活*
——论《遇合奇缘记》的女性身体书写
黄茜子**刘奇玉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摘要清代女性剧作者桂仙创作的《遇合奇缘记》,以时间为顺序,实录了作者自己与其情人椟珍的爱恋过程。剧作中部分大胆的情欲描写,在明清女性剧作中极为特殊。作者描写的主体在“情”而不在“欲”,表达的不是一种纵欲式的“身体解放”,而是灵欲合一的情色生活,体现了作者对情感的尊重,也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审美的自觉。
关键词《遇合奇缘记》;桂仙;戏曲;身体书写
《遇合奇缘记》是罕见的清代女作家剧作,剧本原名《新编遇合奇缘记》,卷首署“长白女史桂仙氏填词”。剧本实录了男女主人公桂仙和椟珍二人的婚外恋情,并在每一出剧目旁标注事件发生的时间。《遇合奇缘记》最鲜明的特点是私密性和情欲书写。作品卷首序言直接指出:“实人实事,直笔直书。”《凡例》中也强调“此记惟传实事”,“此记惟记述儿女私恩”,“本记皆按年编录实事”,表明作者创作并非为了流传,只是实录私人情感生活。“作记者即记中之旦,观戏者即戏内之生”[1],作剧者桂仙和观剧者椟珍因为各自贵族福晋与朝廷臣子的特殊身份而隐去真实姓名,化名为剧中旦与生。这种私密性的写作方式,与剧中实录生、旦有违礼教的私情以及情欲描写有关。正因为如此,“私情”与“私事”得到了自由的书写,呈现出与其他女性剧作在情欲描写方面更具直露的特征。但是,《遇合奇缘记》中的情欲描写并非淫词艳曲,作者的立意并非娱人耳目,创作的主体意图为“情”而不为“欲”,体现了作者对情感的尊重。作者描写与追求的是一种灵欲合一的情色生活。
1甘受指摘取风流,与君尽作今日欢
马克思曾说:“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2]122欲,作为一种人的本能欲望,它应该被正视与肯定,而不应总是被划为“羞于启齿”的范围内。人类对情欲的追求,并不局限于简单的生理欲求,它体现了人对自我意念的肯定。
椟珍与桂仙少年相遇,郎才女貌,彼此一见倾心,可谓天成佳偶。然而,封建社会的女性缺乏基本的爱的自由。桂仙的姑母强行拉媒,将她许配给藩封世子。桂仙的父亲虽然早已将才华横溢的椟珍视为女婿人选,但“既不能却手足之情,只可稍屈儿女之爱”[1],草草促就一段姻缘。桂仙虽恨“狠天公,偏好把人情扭”[1],但终究无力反抗,只能依从,嫁给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甚至素未谋面的人。这样,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就的婚姻,成为桂仙的爱情宿命,她的悲剧也由此开始。一个正值妙龄的女子,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桂仙对生命的快乐有着天然的追求。偏偏世子是一个“天阉”之人,有天生的生理缺陷,他因自卑而疏远新娘,连新婚之夜都是各自睡去。不能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将要终身厮守的丈夫又给不了自己快乐,桂仙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抑和绝望:“休说滞雨尤云,此后尽成虚妄。是前生孽欠今生帐,薄命红妆,这愁肠怕不作了一生沦丧。”[1]对桂仙来说,幸福的生活成了奢望。与世子对照,椟珍则是一个健康的、能给自己实实在在幸福的人。此时,她对椟珍的思念日益浓厚,也自然而然地萌发了追求情欲的愿望。
然而,女性自主追求情欲是与封建伦理相违背的,正如鲁迅所说:“封建礼教使人们身心性欲就是兽欲。”[3] 23一个鲜活的、青春的生命,精神与身体均被沉重的礼教禁锢,身体的基本欲求得不到满足,潜藏于人身体里的原始欲望需要爆发。正如《倩女离魂》中张倩女所唱“越间阻,越思量”,越是压抑,人类本能的欲求越显示出不可阻挡的强大生命力。由于婚姻不幸,欲望得不到满足,桂仙的爱带有明显的欲念诉求。就作者本人而言,虽然一直纠结徘徊,但她在决定大胆追求爱情时,对有违礼教的言行显然是不以为意的。“情缘义起,礼自心生,窈窕之思,未必是父母之命;虞宾之纳,几曾闻媒妁之言?”“弊生于繁礼之中,变起于人情之外”[1]是作序者的态度,也正是作者自己的态度。正是这种情欲诉求,体现了当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情欲是天赋与人的本能,女性不能而且不应该只能默默接受一切压迫与不幸,追求身体的欢娱,是女性的权利。
《牡丹亭》中杜丽娘“慕色而亡”,千古传诵,感动无数读者。《遇合奇缘记》中桂仙“慕色而愈发情深”,虽未广泛流传,却体现了那个时代女性振聋发聩的声音。“色情,是人生的至真至实,真正的色情的爱慕者和实行者,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合法”[5] 450。桂仙在作品中的情欲描写并不妨害作品的严肃性,反而赋予作品更深刻的现实意义。作者并不刻意追求情色描写带给读者的阅读刺激,因为她的预想读者只有剧中小生椟珍一人,且无意流传于世,而是以身体的感觉为触媒,描写一种合乎自身诉求的、能给人真正带来幸福感觉的爱情。剧本的序言说“真名士自取其风流,假道士甘从其指摘”[1],肯定了桂仙自由追求情欲满足、追求生活福祉的行为,赞扬了她大胆追求时坦荡而又坦然的情怀。情欲是桂仙青春躯体中不灭的火种,将她种种压抑的情感点燃。书写情欲,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明确表现,是自我意识强化的结果。追求情欲,体现了女性对自我生存境遇的不满,蕴含了女性对理想生活的期待。
2情自中生天所赋,一生爱好是天然
肉欲是人的本能,爱美是人的天性。《牡丹亭》中杜丽娘的一句唱词——“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可以为爱情的生发作完美的注解。“好”指的是“美”,情感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审美活动,不仅仅体现在外貌、身体之美,还体现在对审美客体才气、品格等诸多方面。爱情不是简单的身体感觉,“情欲”也并不等同于“肉欲”,它并不仅仅着眼于肉体的欢愉,它的归宿是“情”。而且,“情”与“欲”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精神的共鸣与肉体的和谐共同构成完整的爱情,而其中精神方面的含义更为深刻。
桂仙所处的封建时代,女性难以真正拥有爱情。面对男权和礼教的限制,女性天然地表现为沉默与柔顺。桂仙是“椒房贵戚”,知书达理,深知种种礼教。正因为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桂仙能更好地接触一些思想较先进的文学作品,如剧本第六出中,“但愿再来普救寺,一番萧洒一消魂”[1],直接用到了崔、张普救寺典故,说明作者本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与文化素养,这样,她比一般女子更容易觉醒。而且,作者亲历了强行婚配和婚姻生活不和谐的痛苦,她不再甘愿做一个男性话语权下的“失语者”,开始关注并执着追求自己的爱情。从《遇合奇缘记》第五出《奇遇》始(此时桂仙七岁),至第五十出《作记》止,时间跨度为乾隆庚戌(1790)至嘉庆丁丑(1817),长达二十八年,作者按时间顺序细致地纪述了自己与椟珍相识、相知、相爱的日常现实生活。
桂仙之所以选择与椟珍相爱,除了出自身体层次的本能需要,更是因为桂仙心中“情”字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情”不再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而是“自然发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人情至处即礼法”的“情”[4]18,是一种摆脱了道德束缚的情,是顺应了人的天性欲望的真实表露。如第十四出《琴调》中,桂仙自制《凰求凤》琴曲,希望能借曲传情,却碍于礼法规矩羞于承认,但椟珍轻松读懂了其中的意涵:“你虚言且莫谈,彼此遂心愿,一曲凰求,便是缠红线。订盟我在先,谬他牵,也难使神天重判断。妙常纵有调丝手,不遇潘郎定不弹。银河畔,姻缘到底是姻缘,怕甚麽金铃犬吠,鹦鹉能言,把恩爱因他变。”[1]“妙常纵有调丝手,不遇潘郎定不弹”,明确说出女子只有在自己真心爱着的人面前,才能自然而然地弹奏出心声,并劝她不要有过多的顾虑,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对真爱的追求不能拘于礼法贤文。一字一句,皆说进了心坎,桂仙对此完全无力否认。
古人论情,往往以“痴”论之,以示用情之至深。而“欲”不必有“痴”,因为性欲的唯一关注,是对欲望对象的占有。“情”必须有“痴”,因为其主要的关注是审美,“它必须蕴含着审美主体对客体的欣赏、理解、崇拜和挚迷。”[5] 449桂仙与椟珍的爱虽有肉欲成分,但彼此之间的思慕与眷恋,绝不是单纯的生理欲求,而是多元的情感渴求。多元,体现在桂仙重色、重才、更重情。剧本从天宫写起,直到中年剧终,二人情感脉络一直十分明晰。在天宫,他们是金童玉女,整日一起结伴游玩,因偷系红绳触犯天条被贬下凡间。在人世,二人郎情妾意,一起赏花、弹琴、作诗、写字,一起度过平静而幸福的日子,也能一起面对突然而来的变故。他们互相陪伴,互诉衷肠,互相照顾,互相扶持,情真意切,恩深爱重。千百年来,女性对理想伴侣的期待,对男性“志诚”的向往,椟珍都极其符合。他对桂仙一片赤诚,一以贯之地给予桂仙无微不至的呵护,这也是桂仙甘愿违背礼教,与之深情相依的最重要的原因。
3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桂仙与椟珍青梅竹马,若非姑母强行拆散,早已结成良缘。二人虽然各自成婚,分隔两地,但对于桂仙来说,只有椟珍才是与她心灵相通的完美爱人。如果说完美的爱人要“才,色,情”兼备,椟珍无疑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首先他的外貌俊美,气质超群,正如桂仙在《闺思》一出所唱:“想庞儿依旧,眉目清秀,倚着他风流旖旎,言语轻柔”[1],连丫鬟蕙儿也感叹:“真好俊秀人儿也,怪不得我夫人镇朝昏印来心坎,又不是幻影成桥,恰令人魂飞难挽。”[1]
二人的爱情并不是以外貌为基础的皮相之爱,而更是一种才德相称,惺惺相惜的精神之爱、知己之爱。这些在桂仙结婚之前就已经有了脉络明晰的情感来源。他们本是仙子,一同降凡,有着天然的情感基础。下凡后,二人还是七、八岁的童年时,相遇便彼此一见倾心,遂在佛前盟誓,虽云结为兄妹,实有结姻之愿。桂仙边拜边唱:“定鸾盟,整云鬓,晕难收。俏结同心自含羞,愿痴情共守,愿痴情共守。莫忘了今日神前繁育咒,把相思撇下莫添忧。倩良媒早博个天长地久,比着那窃玉偷香情不朽。”椟珍更明确表示:“齐拜倒佛前稽首,惟愿得早偕婚媾。”[1]在其后的《面试》一出中,年幼的椟珍已经表现出丰富的学识与超凡的才华,引得众人惊叹:“滔滔高诵涌如泉,应知学有渊源,悬河宿搆,纵横礼乐三千,一日里身游广寒,有嫦娥亲把金杯劝,丹桂高攀,身荣显如操左券。”[1]
桂仙自小便已被椟珍的才华吸引,她自身也才华横溢,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且对文史均具有独到的见解。在《学诗》一出中,吟出风格清妙的诗句,引得椟珍大叹:“奇哉!桂仙初学吟咏,竟能如此!文姬苏蕙,不足多也。”[1]《纂左》一出中,她更是高屋建瓴地指出如何理清史书头绪,让椟珍也不禁感:“何必我翻书,见解超林杜,看流星落纸,真令人羡慕。果得骥尾将奴附,不让当年曹大姑。”[1]这样的事例在剧中比比皆是。由于是女儿身,在封建时代,桂仙并无许多施展才华的机会,而椟珍慧眼识珠,称许不已:“若许他文章词赋来科举,管与那崇嘏三元名并趋。”[1]椟珍的才华是桂仙倾慕其的重要原因,而其对桂仙之才的认同更是将这份爱情提高到了“知己之爱”的高度,让桂仙感动尤深。二人琴瑟和鸣,互怜其才,互为知音,实堪赞赏。
椟珍不仅才貌双全,对桂仙来说,最重要的是他承担起了完美伴侣的责任。二人幼年初见时即相互爱慕,这可能是作者姻缘天定的叙事需要,而尘世生活中的长期交往则奠定了现实中真爱的基础。他们不仅像所有才子佳人的故事中描述的那样花前月下,你侬我侬。他们的真挚感情更体现在相互关爱,患难与共,彼此照顾,彼此安慰。椟珍项后生疮时,桂仙经丈夫允许,亲自为之洗涤敷药。椟珍因失察假印革职,终日情绪低沉,耽于花酒,桂仙日日挂怀,不仅代筹银两,助其捐复官职,且反复规劝和勉励,更将劝勉之言绣于香囊上赠之,用心细密,令椟珍大为感动:“这恩情,如针还密,似线偏长。”[1]椟珍对桂仙也是一往情深。桂仙生病时,椟珍心痛不已,甚至说“三妹且免伤悲,卿如不讳,我宁独生乎”[1]。他痛斥庸医延误病情,亲为哺药,日日夜夜,衣不解带地精心照顾。正是由于这种无微不至的体贴,让桂仙甘愿冲破礼教,以身相许。桂仙碍于礼教心生不安时,他敏锐感知,体贴相慰,援引古今大量实例,向桂仙说明“礼从外起,情自中生”的道理,消除其顾虑。兵荒马乱、“亲友闻言尽散,优人席卷全逃,至今三日,音信全无”之时,椟珍千方百计赶到桂仙处,一句“妹子受惊”,让桂仙连日来的惊恐、担忧与思念应声消散,哭道:“我枯木又逢春,不由人口而作念心儿印,几乎未把香躯殉。”[1]这一哭,既有深深的感动,也有爱情更升华一层的喜悦。危难的时刻,往往最能检验情感的真挚与否。椟珍对桂仙,如果不是深入骨髓的真爱,如果不是心灵的高度契合,怎么会在最危险的时刻只挂念着她,不论动荡至何种程度,都一心只想奔向她身边,想要保护她,确保她平安。这种感情,来自于两心相印的挚诚,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也无法抗拒。也正是因为这生死相依的深情,让桂仙愿意对椟珍以身相许,在剧中,一旦身体的结合只会让这份真挚的感情更加完整,而绝非轻浮无聊的欢爱。
4结束语
椟珍与桂仙对彼此的爱,既有欲望的诱因,更有深厚情感的基础。桂仙身受肉欲与情感的双重压抑,而椟珍既能给予她肉体的欢乐,又与她有精神的交流,使桂仙不惜违背礼教,大胆出格,缔结了一段奇缘。《遇合奇缘记》虽然有一些情色描写,但终究“色情难坏”,它表达的不是一种纵欲式的身体解放,而是一种身处封建礼教规制下的妇女对才貌相称、情意相通、灵肉合一的健康爱情的追求,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审美的自觉。
参考文献
[1]桂仙.遇合奇缘记[M].清嘉庆间精抄本.
[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鲁迅.准风月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胡健.论明清情欲美学思潮[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37(5):18-23.
[5]华玮.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
(责任编辑叶桂郴)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明清女性戏曲创作与理论批评》(13YJA751026);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多维视角下的〈遇合奇缘记〉研究》(CX2015B452 )。
** 作者简介:黄茜子,女,湖南常德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859(2016)01-013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