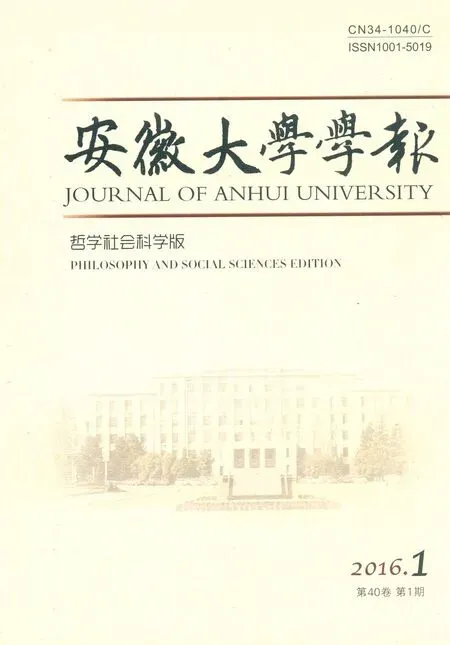追寻定性与定量的结合——《唐律》立法技术的一个侧面
姜 涛
追寻定性与定量的结合
——《唐律》立法技术的一个侧面
姜涛
摘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唐律》立法技术高超的集中反映。《唐律》中的犯罪构成与量刑制度均运用了该技术,前者意味着对犯罪成立附加了特别条件,后者体现在为审判官量刑提供了确立依据。《唐律》立法技术的特点是借助数学理性全面地架设犯罪与刑法之间的阶梯和以递增公式为审判官公正量刑提供指南。这不仅有利于从立法上合理划定犯罪圈,而且有助于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因而是封建时代司法公正的制度保障,对当代亦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唐律》;定性;定量;立法技术
从宏观上看,当代立法制度主要由立法思想、立法政策、立法技术三要素构成。立法技术作为立法活动所应体现与遵循的技巧、机能的总称,自人类制定法律伊始,就在立法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法律传统的代表性法典——《唐律》,在立法技术上堪称典范。中外学界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唐律》立法思想与政策的研究,比如一准乎礼、宽仁慎刑等,这方面成果最多*此类成果甚多,较有代表性者可参见黄源盛《唐律中的礼教法律思想》,台湾《政大法学评论》1997年第58期;苏亦工《唐律“一准乎礼”辨正》,《政法论坛》2006年第3期;马小红《唐律所体现的古代立法经验》,《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8年春秋合卷。。二是《唐律》量化立法技术的研究,即归纳唐律中量化的种类与方法,并主要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立法量化技术进行研究*参见钱大群《唐律立法量化技术运用初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三是立法技术的比较研究,比如《唐律》与《明律》、日本刑事立法之间的立法技术比较等*参见黄源盛《从法继受观点比较中日两国刑事立法的近代化》,台湾《政大法学评论》1995年第54期;侯欣一《唐律与明律立法技术比较研究》,《法律科学》1996年第2期。。但尚未有学者对《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进行研究。这种缺失不仅影响后世对《唐律》立法技术的全面评估,而且还使中国现行刑法采用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难以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甚至面临没有文化基础的责难。本文以《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弥补该方面的研究不足。
一、《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立法技术的考察
《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存在于两个领域:一是犯罪构成,它解决犯罪的成立条件问题。除《名例》之外,《唐律》有80个条文涉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约占后十一篇全部条文的18%。二为量刑制度,它解决的是犯罪与刑罚之间以什么立法技术对应的问题,目的在于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后者的存在范围更广。
(一)犯罪构成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
《唐律》所规定的犯罪应具备何种条件才能得以成立,这在现代刑法理论中是由犯罪构成来体现的。所谓犯罪构成是指依照刑法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并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因犯罪类型有异,危害各不相同,不同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同。按照现行的刑法学通说,犯罪有行为犯、危险犯、举动犯和结果犯四种*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2页。。纵观《唐律》,其主要是行为犯与结果犯,行为犯以定性技术为主,而结果犯则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犯罪认定技术,其类型有:
1.定性+时间长短
犯罪行为持续时间的长短对犯罪结果有直接影响,体现着犯罪的危害程度。以犯罪行为及其持续时间作为认定犯罪是否成立的根据,这主要存在于《唐律》所规定的职务犯罪中。比如,《厩库》第211条规定:“诸假请官物,事讫过十日不还者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私服用者,加一等。”*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0页。以下引文凡出自《唐律疏议》者,均在正文行文中列出篇条名称,不再出注。本罪的成立不仅需要“假请官物不还”这一行为的发生,而且还有最低“过十日”这一时间要求。再比如,《捕亡》第448条规定:“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赃重者,坐赃论。私物,坐赃论减二等。”本罪的成立即要求“得阑遗物不送官”这一定性要件和“满五日”这一定量要件。
2.定性+土地面积
“亩”作为土地面积的计量单位,它的数量大小体现着侵害土地制度犯罪的危害程度,因而土地犯罪多以“占田过限”“卖口分田”“盗耕种公私田”等行为定性,再加上“亩的数量”这一定量要件,来决定犯罪的成立问题。比如,《户婚》第164条规定:“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过杖六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若于宽闲之处者,不坐。”如要构成本罪,不仅需要“占田过限”这一定性的条件,而且需要“一亩及以上”这一定量的要求。此外,《户婚》第163条规定的“卖口分田”犯罪亦是如此。为何说本罪有“一亩及以上”这一定量的要求?除了条文的表述之外,从相邻条文的比较也能看出问题之所在。比如,《户婚》第166条规定:“诸妄认公私田,若盗贸卖者,一亩以下笞五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从本条规定的“一亩以下笞五十”这一规定来看,它在犯罪构成判断上是典型的定性,即使侵占的田地为“一亩以下”,也要“笞五十”,这与《户婚》第164条所规定的“一亩笞十”明显不同。也正是这种不同的立法技术,把“占田过限”犯罪与“妄认公私田,若盗贸卖”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之间的差异体现出来,后者为重。
3.定性+计算布帛的单位
财产犯罪一般都折实以绢的计算单位量化,《名例》第34条规定:“诸平赃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所以,盗贼、贪污、受贿、勒索、诈伪等犯罪行为基本都折实成当地当时上等绢的“匹”“尺”作为计量单位,以表明这类犯罪中财物损失的数额。比如,《户婚》第162条规定:“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即同居应分,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本罪犯罪构成之判断既需要“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这一定性要件,也要满足“十匹”这一定量要件,否则不能成立。再比如,《杂律》第389条规定:“诸坐赃致罪者,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本罪在“坐赃致罪”这一定性之下,然后以“坐赃”的数量标准,作为审判官认定犯罪的依据,即坐赃致罪“一尺以上”才构成犯罪。
4.定性+物品重量
乘驿马而违规携带物品的犯罪,一般都有携带物品重量的要求。由此决定,这类犯罪的成立判断,首先是确定行为的性质,然后再辅以行为所涉及物品的重量(如私物的斤数等),来作为犯罪构成判断的标准,重量达不到要求,犯罪不能成立。比如,《职制》第129条规定:“诸乘驿马赍私物,(谓非随身衣、仗者)一斤杖六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驿驴减二等。(余条驿驴准此)”本罪就需要同时满足“乘驿马赍私物”这一定性要素和“一斤及以上”这一定量要素之后,才能得以成立,缺一不可。
5.定性+多个定量要素
有的犯罪尽管也是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来确定犯罪的成立要件,但在定量上却采用了两个以上的要素,这种立法技术显得略为复杂。比如,《杂律》第426条规定:“诸应乘官船者,听载衣粮二百斤。违限私载,若受寄及寄之者,五十斤及一人,各笞五十;一百斤及二人,各杖一百;(但载即坐。若家人随从者,勿论。)每一百斤及二人,各加一等,罪止徒二年。”本罪的成立不仅有“违限私载,若受寄及寄之者”的定性要求,而且还必须达到“五十斤及一人”的定量要件,因而是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规定本罪的成立要件。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定量立法技术中采用了“五十斤及一人”的双重标准。再比如,《杂律》第398条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本罪的成立判断同样是采用定性(即负债违契不偿)与定量(即一匹以上,且违二十日)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但是在定量立法技术上,却考虑了两个基本因素:“一匹以上”与“违二十日”,两者只有同时具备,犯罪才能得以成立。
在理解《唐律》所规定的具体个罪之犯罪构成中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时,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强调:
其一,《唐律》中有诸多“一口”“一人”等定量表述,这并不是犯罪构成中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举例来说,《户婚》第151条规定:“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三口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不觉脱户者,听从漏口法。州县脱户亦准此。若知情者,各同家长法。)”这里的“一口”是人头的计算单位,从常识上看,一口就是一个活人,这并不是犯罪构成判断中的定量要求,而是量刑中的定量要求,即用“一口”这一定量要素,确立本罪量刑的起点刑。再比如,《职制》第91条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谓非奏授者)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后人知而听者,减前人署置一等;规求者为从坐,被征须者勿论。即军务要速,量事权置者,不用此律。”这里的“一人”,也不是犯罪构成中的定量要件,而是量刑中的定量要求。
其二,《唐律》规定的“一斤”“一尺”“一日”等定量要求,是犯罪构成判断中的基本要件,而不是量刑制度中的定量要求。对此,虽然《唐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在疏议的解释中明确了它应该属于犯罪成立要件。比如,《厩库》第199条规定:“诸应乘官马、牛、驼、骡、驴,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一斤笞十,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其乘车者,不得过三十斤,违者,五斤笞十,二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即从军征讨者,各加二等。若数人共驮载者,各从其限为坐。监当主司知而听者,并计所知,同私驮载法。”本条规定在司法适用中的一个疑问是:超载货物没有达到“一斤”这一量的要求,是否构成本罪?对此,本条疏议曰:“‘若数人共驮载者’,谓乘官畜及车。应得私载物限外,谓畜过十斤,车过三十斤。假有十人,同乘官畜,驮私物各十斤,其中五人数外各过一斤,依律各笞十;三人各过十一斤,各笞二十;二人各过八两,律云‘过一斤笞十’,今数不满一斤,依律各无罪……”可见,货物超载数量达不到“一斤”要求的,应该不构成犯罪,这就把“一斤”视为犯罪成立要件,可谓严格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
(二)量刑制度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
作为前提,《唐律》条文结构与中国现行刑法明显不同,前者是罪状、法定刑、量刑制度三位一体,且量刑制度系律文结构的主要内容;后者则是罪状与法定刑的二元结构。也就是说,《唐律》条文结构的特色在于详细规定具体个罪中的量刑事实及量刑方法,从而为审判官量刑提供了指南。既然如此,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也会延伸至《唐律》中的量刑制度,它不仅从定性上对具体量刑事实的范围与内容作出规定,而且以定量技术把具体量刑事实对最终量刑结果的影响予以程式化,实现了审判官量刑的法定化、精确化。
1.定性+人员数量
就犯罪与刑罚的对应关系而言,犯罪行为涉及人员范围的广泛程度是审判官量刑中的重要因素,因此,《唐律》在以定性立法技术区分出不同的量刑事实后,随之对这些量刑事实对应的法定刑增加了“人员数量”这一定量要求。比如,《户婚》第152条规定:“诸州县不觉脱漏增减者,县内十口笞三十,三十口加一等;过杖一百,五十口加一等。州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通计,谓管二县者,二十口笞三十;管三县者,三十口笞三十之类。计加亦准此。若脱漏增减并在一县者,得以诸县通之。若止管一县者,减县罪一等。余条通计准此。)各罪止徒三年。知情者,各同里正法。(不觉脱漏增减,无文簿者,官长为首;有文簿者,主典为首。佐职以下,节级连坐。)”本罪的量刑首先从定性上区分“县”“州”等量刑事实,然后再增加“县内十口”“州随管二县者,二十口笞三十”“管三县者,三十口笞三十”这些定量要素,从而为审判官的量刑提供了评价的范围(县、州)与方法(如五十口加一等)。
2.定性+土地面积
在侵犯土地制度的犯罪中,犯罪侵害对象不同(比如是荒田,抑或苗圃等),体现出来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同,量刑结果自然也有差异,并且侵害对象的数量(比如亩数)对其量刑结果亦有影响,《唐律》对此有明确体现。比如,《户婚》第165条规定:“诸盗耕种公私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荒田,减一等。强者,各加一等。苗子归官、主。”从本条规定的量刑事实来看,不仅从犯罪对象上区分为“公私田”和“荒田”,而且从行为手段上区分为“窃”和“强”,可见,它在量刑事实确定上采用的是典型的定性技术。但以什么方法进行量刑,则又有定量要求,并且不同量刑事实的定量要求不同:如为“盗耕种公私田”,其定量要求是“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如系“荒田”,这种定量要求则变更为“一亩以下笞二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如果为“强取”,那么定量要求又有差异,即“一亩以下笞四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两年。”再比如《户婚》第167条规定:“诸在官侵夺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半。园圃,加一等。”本罪量刑即首先从定性角度区别为“私田”和“园圃”两种情形,然后,从定量角度把“侵夺私田”之量刑的操作方法规定为“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半”,把“侵夺园圃”之量刑的操作方法规定为“一亩以下杖七十,三亩加一等;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三年”,以区别对待。
3.定性+时间长短
作为体现犯罪危害量大小的因素之一,犯罪行为持续的时间不仅影响着对犯罪行为的评价,而且往往影响着审判官最终的量刑结果,因而《唐律》中不少犯罪都把时间长短这一定量要素作为审判官量刑的法定标准,如果没有达到法定的时间要求,则审判官不能对犯罪人判处刑罚或提高某种犯罪的法定刑。
《唐律》对这种时间长短的设置各有不同。时间最短的是一日,比如,《捕亡》第460条规定:“诸宿卫人在直而亡者,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即从驾行而亡者,加一等。”本条在对量刑事实从定性角度区分为“宿卫人在直而亡”与“从驾行而亡”的前提下,又对每种量刑事实附加了定量要求:前者为“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后者为“一日徒半年,二日加一等”。再比如,《斗讼》第360条规定:“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主司不即言上,一日杖八十,三日杖一百。官司不即检校、捕逐及有所推避者,一日徒一年。窃盗,各减二等。”本条首先从定性上把量刑事实区分为“当告而不告”“主司不即言上”和“官司不即检校、捕逐及有所推避”三种情形。与之对应,不同量刑事实的最低定量要求分别为“一日杖六十”“一日杖八十,三日杖一百”“一日徒一年”。
时间最长的是百日,比如《职制》第142条规定:“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授讫未上,亦同。余条取受及相犯,准此。)若百日不还,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强者,各加二等。(余条强者准此。)若卖买有剩利者,计利,以乞取监临财物论。强市者,笞五十;有剩利者,计利,准枉法论。即断契有数,违负不还,过五十日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即借衣服、器玩之属,经三十日不还者,坐赃论,罪止徒一年。”本罪的量刑事实被区别出“贷所监临财物者”“强者”“断契有数,违负不还”等,其中,对于“贷所监临财物者”这一量刑事实的最低定量要求是“百日”,而对于“断契有数,违负不还”的最低要求是“五十日”。
4.定性+数额大小
对于窃盗、受贿等财产犯罪而言,犯罪数额不仅体现着犯罪的危害程度,而且对审判官的量刑结果具有重要影响。数额大小不同,量刑结果自然就有差异,因此,这类犯罪中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对应关系,主要是以表示财产数额大小的“匹”“尺”等来架设。比如,《贼盗》第282条规定:“诸窃盗,不得财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本罪不但从定性上对量刑事实区别为“不得财”和“得财”两种情形,并且对“得财”这一量刑事实规定了“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这一定量要求。再比如,《户婚》第140条规定:“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与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论。”本罪首先从定性上对量刑事实区别为“受所监临财物者”“与者”“乞取者”和“强乞取者”四种,然后,又对每一量刑事实都附加了定量要求。以“受所监临财物者”为例,它的定量要求是“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这种量刑事实及其最终量刑结果的计算依据,十分明确。
5.定性+比例大小
地方官所管辖区内或户主田地有荒芜,就以所荒芜田亩占全部田亩总数的比例多少,作为审判官量刑的指南,比如,《户婚》第170条规定:“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州县各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结合本条疏议的解释,本罪的量刑事实有三种情形,且每种量刑事实的定量要求不同:(1)若部内总计,准口受田,十分之中,一分荒芜者,笞三十。(2)假若管田百顷,十顷荒芜,笞三十。“一分加一等”,谓十顷加一等,九十顷荒芜者,罪止徒一年。(3)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计户内所受之田,假有受田五十亩,十亩荒芜,户主笞三十,故云“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即二十亩笞四十,三十亩笞五十,四十亩杖六十,五十亩杖七十。其受田多者,各准此法为罪。把定量要求精确到比例,这是《唐律》立法技术的一大创新。
6.定性+事的数量
按唐代《田令》:“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共给授。”其里正皆须依令造簿通送及课农桑。若应合受田而不授,应合还公田而不收,应合课田农而不课,应课植桑、枣而不植,如此事类违法者,其中每一项内容即称为一“事”。官吏不尽职守或违法犯罪行为的结果,都计“事”的多少为刑罚轻重选择的重要依据。比如,《户婚》第171条规定:“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收,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一事,谓失一事于一人。若于一人失数事及一事失之于数人,皆累为坐。)三事,加一等。县失十事,笞三十;二十事,加一等。州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州、县各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各罪止徒一年,故者各加二等。”本条除了从定性上规定“里正”“县令”“州长”等量刑事实外,每一量刑事实都有定量的设置,即里正“失一事,笞四十……三事,加一等”“县失十事,笞三十;二十事,加一等”“州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这就把里正、县令、州长各自的量刑标准,予以明确规定,极为精确。
此外,《唐律》中的量刑制度所运用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还有以下三个特殊之处:
其一,以疏议补充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的情况。比如,《职制》第126条规定:“诸驿使受书,不依题署,误诣他所者,随所稽留以行书稽程论减二等。若由题署者误,坐其题署者。”本条疏议曰:“文书行下,各有所诣,应封题署者,具注所诣州府。使人乃不依题署,误诣他所,因此稽程者,随所稽留,准上条行书稽留之程减二等,谓违一日杖六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若有军务要速者,加三等。有所废阙者,从加役流上减二等,徒二年半。以故有所陷败,亦从绞上减二等,徒三年。‘若由题署者误’,谓元题署者错误,即罪其题署之人,驿使不坐。”本条律文并没有在量刑制度中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但却以疏议明确了“违一日杖六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若有军务要速者,加三等。有所废阙者,从加役流上减二等,徒二年半。以故有所陷败,亦从绞上减二等,徒三年。”这在《唐律》中并不少见。
其二,《唐律》使用了比较先进的折抵技术,即不同的定量要素之间以一定的比例进行折算,并以这种折算的数量,来计算最终的量刑结果。比如,《擅兴》第235条规定:“诸在军所及在镇戍,私放征、防人还者,各以征、镇人逃亡罪论;即私放辄离军、镇者,各减二等。若放人多者,一人准一日;放日多者,一日准一人。(谓放三人各五日,放五人各三日,累成十五日之类。并经宿乃坐。)临军征讨而放者,斩。被放者,各减一等。”本条疏议曰:“依《捕亡律》:‘从军征讨而亡,一日徒一年,一日加一等,十五日绞。’若放十五人,一日亦合绞。其放镇戍人而还,一人一日杖八十,三日加一等,三十一日流三千里。若放三十一人,一日亦流三千里。”这就基本上明确了“日”与“人”这两种定量要素之间的等量折算,可谓技高一筹。
其三,与犯罪构成中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相比,量刑制度中的立法技术更为复杂,也更为系统。它不仅涉及每一量刑事实对应的最低数量要求,而且随着这种数量的递增,其对量刑结果的影响也大为不同,因而隐含着诸多递增公式。比如,《杂律》第464条规定:“诸在官无故亡者,一日笞五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五日加一等。边要之官,加一等。”尽管本条对“在官无故亡”这一量刑事实的最低定量要求是“一日”,但是随着日期的递增,本罪的量刑结果也由最初的“笞五十”,而向“笞六十”“笞七十”……“杖一百”等增加。如此严谨、高超的量刑立法技术,旨在为审判官在量刑幅度内依律量刑提供一个可以计算最终量刑结果的“程式”。
二、《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立法技术的特点
通过上述对《唐律》条文结构及内容的细致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具有下列两个基本特点。
(一)形式多样:全方位架设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阶梯关系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旨在于犯了什么罪,应受什么刑,才能实现刑法的公正价值,这需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予以保障。毕竟,立法技术并非形式问题,而是实质问题,它是确立罪刑关系的必要手段。为此,近代“罪刑阶梯论”的提出者,贝卡里亚在论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时就强调应当运用几何学原理研究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阶梯关系*[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66页。。国内学者也曾经用坐标图的形式描述过犯罪的严重程度与刑罚的调控强度之间的对应关系*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第262页。,但是都没有上升到立法层面。如前所述,《唐律》已经以形式多样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详尽规定了时间、数量、人口数、土地面积等数量要求,全方位架设起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阶梯关系。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以多样化、具体化、生活化、精确化的计量单位,对表征犯罪危害量的犯罪客观方面、主观方面、犯罪主体等作类型化的或等级式的数量解析,与刑罚种类和幅度之间形成对应。这种数量单位主要有“匹”“尺”“日”“宿”“匹”“头”“里”“斤”“事”“条”等。比如,《斗讼》第359条规定:“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若应合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三条加一等,十条杖九十。”这里的计算单位是“条”,而且以“条的数量”(危害量)增加为依据,“杖”(刑量)随之增加。不同数量要求及其等级,反映了犯罪不同的社会危害量,审判官以此为计算方式来确定刑量递增的幅度与种类,可见,《唐律》对部分犯罪的规定无论苛厉抑或宽宥,其立法技术都不只把评价的落脚点放在行为性质上,而是综合判断行为性质、财物犯罪的数量、货物的斤数、被侵害土地的面积、遗漏登记的人数等反映危害程度的要素,甚至在现代看来属于文化糟粕的级别大小、君臣关系等。事实上,如果《唐律》不加定量区分地对所有犯罪均采用定性立法技术,这就忽略了犯罪的复杂性、多样性。毕竟,《唐律》涉及犯罪类型众多,社会危害各异,无法用统一的定性技术囊括全部。
第二,以为数众多的表示某类犯罪行为之间差异的等级档次,来对犯罪的危害程度作量化定位,与刑罚种类及幅度之间形成对应。主要有:(1)危害安全的行为结果以距离远近的档次来量化定位,如《卫禁》第71条;(2)以责任关系的固定模式,作为官吏职务过失罪责追究的量刑参数,如《名例》第40条;以“殴→伤→伤重→死”的级别档次来对一般殴打行为的结果进行量化,如《斗讼》第315条;(3)以血亲的等级作为对有服者相犯行为轻重加减档次的参数依据,如《斗讼》第315条;(4)对殴官的犯罪行为,以“议贵→五品以上→六品以下”的基本档次作为行为性质量化的档次,如《斗讼》第316条;(5)对良贱相犯以“良人→部曲→奴婢”为刑罚递相加减一等的档次,为行为性质的量化档次,如《斗讼》第320条;(6)对夫妻相犯以“夫→妻→媵→妾”的尊卑档次,作为行为性质区分量化的档次,如《斗讼》第325条;等等*参见钱大群《唐律立法量化技术运用初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通过这种立法技术,审判官在定罪量刑过程中如何评价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如何做出最终裁决,就有了依循标准,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缩短办案周期,提高办案效率。
第三,《唐律》在立法技术上不仅采用了“匹”“尺”“口”“人”等计算刑罚轻重的量化单位,采用了“一日”“三日”“一亩”“十匹”等数字技术,而且还采用了更为精确的比例,比如10%、5%等,从而满足了审判官正确定罪量刑之客观化、精确化的要求。比如,《户婚》第170条规定:“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州县各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本罪的量刑事实也是采用定性(户主与非户主)与定量(一分笞三十)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只是在定量技术中先把数量分为“十分”和“五分”,然后分别以10%对应的刑罚(笞三十)和20%对应的刑罚(笞三十)为审判官量刑的起点刑,随后再以“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的计算程式,逐步增加,这就架设起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阶梯。
参照这些规定及其所蕴含的公理,我们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唐律》已经架设起了犯罪与刑法之间一一对应的阶梯。这比“近代刑法之父”贝卡利亚以理论的方式提出“罪刑阶梯论”早了几个世纪。也就是说,当西方人意识到罪刑阶梯问题之时,中国古代立法早在几个世纪前已经在实践这一领域实现了,这不能不说是唐代立法技术高超的体现。
(二)追求精确:以数学理性为审判官公正量刑提供指南
刑法条文精确与否,是立法技术发达与否的标志。条文精确,用语明晰,逻辑严密是其最高境界。如果“数额较大”“情节严重”“重大损失”之类用语大量充斥在刑法中,那么只能让审判官依据自身经验定罪量刑,只能给审判官留下恣意定罪量刑或司法腐败的制度空间。如何克服单纯经验盲动倾向?《唐律》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数学理性引入到立法内容中来,为审判官正确定罪与公正量刑提供标准。数学理性的出发点是公理,而公理是简单的、精确的,《唐律》已经将此运用在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之中,主要体现有二:
第一,“递增公式”与定量的公理化。从《唐律》本身,我们可以在绝大多数犯罪中看到犯罪与刑罚之间对应的“刻度”,因为《唐律》基本上把影响审判官定罪量刑的事实及其对应的刑罚种类、幅度予以明确规定,保障了同罪同罚,异罪异罚。那么《唐律》是如何架构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对应关系呢?这就是编纂大臣创造性地运用了“递增公式”,它有两部分组成:一为起点刑,是指具体个罪之法定刑格次中的最低刑种或最低刑期,这是审判官量刑的起点。比如,《杂律》第426条规定:“诸应乘官船者,听载衣粮二百斤。违限私载,若受寄及寄之者,五十斤及一人,各笞五十;一百斤及二人,各杖一百;(但载即坐。若家人随从者,勿论。)每一百斤及二人,各加一等,罪止徒二年。”本罪量刑之起点刑为“笞五十”。二为“计算方法”,这是以起点刑为最低的量刑起点,然后确立一种“随着罪量的增加,刑量也随之增加”的计算方法。在上例中,“每一百斤及二人,各加一等”即为递增公式。
归纳来看,《唐律》规定的递增公式主要有两种模型:
公式(一):首先以律文明确本罪量刑的起点刑(以符号A表示),然后明确量刑的计算方法(以符号B表示),最后还限定审判官判刑的最高期限(以符号C表示)。此类的律文如《擅兴》第239条规定:“诸官人无故不上及当番不到,(虽无官品,但分番上下,亦同。下条准此。)若因暇而违者,一日笞二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边要之官,加一等。”这一犯罪的一日笞二十为A,三日加一等为B,罪止徒一年半为C。若“边要之官”犯本罪,则一日笞三十(A),三人加一等(B),罪止徒两年(C)。
公式(二):只以律文明确本罪量刑的起点刑(以符号A表示)和量刑的计算方法(以符号B表示),至于审判官判刑的最高期限(以符号C表示)不作规定,而是依《名例》规定的一般量刑原则处理。比如,《捕亡》第459条规定:“诸流徒囚,役限内而亡者,(犯流、徒应配及移乡人,未到配所而亡者,亦同。)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五日加一等。”这一犯罪量刑的一日笞四十为A,三日加一等或五日加一等为B,至于最高可以判处什么刑罚(C),则没有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限制,《名例》第56条规定:“诸称‘加’者,就重次;称‘减’者,就轻次。”此外,诸篇对加刑也有严格的限制:(1)“加者数满乃坐”,即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量才能加等。如《盗贼》第282条规定:“诸盗窃……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凡是盗窃数量在五匹以上、十匹以下的,均只能徒一年。既然如此,人数少一人,工具少一个,财物少一匹,时间少一日等,都不得加刑。(2)“不得加至于死”,无论何种情况,没有规定死刑的条文,最高的量刑极限为“流三千里”。(3)“加入绞者不加至斩”,即加等至死刑的,至绞刑即为顶点,因此,被称之为“至死不附加”。
第二,“数学思维”与定量的精确化。一部法律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时,才算真正发展了,因为从刑法正义角度看,罪刑之间应当是等罪等刑,异罪异刑,同罪不同情况,刑罚亦不相同。这并不是学术研究中的“绕口令”,而是罪刑之间的数量关系,即贝卡利亚所称的“罪刑阶梯”对立法的要求。数学的确定性或工具性是举世公认的,任何科学都比不上数学的确实性。把数学思维运用到立法技术中,就形成了定量技术。也正是数学思维,定量技术具有客观实在性、规律性、严密性、精确性、系统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定量技术能够引导刑事立法走向科学化、客观化,能够把罪刑关系所蕴含的“阶梯”通过科学的递增公式表现出来*参见王鸿钧、陈宏发《数学思想方法引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75页。。刑事案件的处理不仅是犯罪构成问题,而且是量刑制度问题,无论是定罪抑或量刑,审判官要解决的都不只是定性问题,而且涉及定量的学问。就定罪而言,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乃是基于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而能够表现这种危害程度的要素就包括可以用性质来区分的危害行为及用数量来衡量的危害结果、危害对象等,而重罪与轻罪之间的界限何以划分开来,更是建立在不同犯罪的数量关系之上的。就量刑来说,其任务是把罪量与刑量之间的对应关系,以科学的方法表现出来,并得出最终的量刑结果,这就需要对罪量与刑量分别进行定性与定量处理,在此基础上进行数量的分析、测量和计算,这是审判官最常用的数学思维。也正是这种数学思维,人类发现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
以量刑为例,《唐律》采用了多样化的数学思维与立法技术,明确规定刑罚的起点、刑罚递增的参考要素、计算方法及其幅度,以及递增的最高限度。如《擅兴》第239条规定:“诸镇、戍应遣番代,而违限不遣者,一日杖一百,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即代到而不放者,减一等。若镇、戍官司役使防人不以理,致令逃走者,一人杖六十,五人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本条中“杖一百”“杖六十”为量刑的起点刑,“三日”“五人”则为刑罚递增的参考要素,“加一等”为计算方法,“罪止徒一年半”“罪止徒二年”为递增的最高限度。再比如,《职制》第97条规定:“诸官人从驾稽违及从而先还者,笞四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侍臣,加一等。”本条中“笞四十”为量刑的起点刑,“三日”“十日”为刑罚递增的参考要素,“加一等”为计算方法,“罪止徒二年”则为递增的最高限度。只是本条中增加了“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这一区别性的计算方法,而此恰恰又体现了《唐律》立法技术的高超。正是这种追求定量公理化中那种对数学思维的运用及其对审判官量刑结果的限制,为审判官公正量刑提供了一个可以计算的程式与选择最终量刑结果的方法。其运用的方法、参考的要素、期望达到的效果与《美国量刑指南》并无二致,但是却比《美国量刑指南》早了一千多年,这足以说明中国古代人的立法智慧。因此,如果我们要为中国当下量刑制度改革寻找文化之根的话,《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无疑是最值得重视的。
可以肯定,“递增公式”和“数学思维”虽然在当代看来,显得过于机械,严重抹杀了法官实现个案正义的自由裁量权,但在封建时代,这却是通过立法技术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的制度保障。为何这么说?(1)唐代并没有现代这种“控方指控、辩方辩护、法官居中裁判”的合理诉讼制度保障,法官集调查取证、定罪与量刑于一身。(2)古代的审判官兼行政、司法等事务于一身,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专任法官,并且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回避制度作保障,容易出现冤假错案。(3)封建时代普遍存在罪刑擅断、刑讯逼供、类推等查明案件事实的方法。如此一来,如果《唐律》对罪质与罪量、罪量与刑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没有更为科学的立法技术予以保障的话,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的现象就可能普遍存在。就此而言,古代的定罪量刑也具有制度保障,只是与我们当代的制度建构模式不同而已。对此,我们决不能站在现在法制发展的视角,对其予以全盘否定。
三、《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立法技术的价值
如前所述,《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既具有犯罪构成的解释性功能,也具有量刑层面的应用性功能。这一立法技术不仅有利于合理划定犯罪圈大小,而且还是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的制度保障,意义十分重大。
(一)有利于从立法上合理划定犯罪圈
犯罪圈是现代刑法学上的重要概念,是指一国当下刑法典中犯罪的数量及具体犯罪外延的大小,合理的犯罪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如何划定犯罪圈?这与立法技术有关。在犯罪圈划定中,各国立法者经常会遭遇“定性抑或定量”的重大分歧,单纯定性就是犯罪圈的扩大,意味着刑法干预范围较宽;既定性又定量就是压缩犯罪圈,意味着刑法干预的慎重,因为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不仅要求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而且需要行为造成的结果达到一定的量的要求。这些看似简单的立法技术,却又蕴含着重要的制度价值。
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以免单一的定性立法技术所导致的犯罪圈的扩张现象,这就是《唐律》在针对那些不危及皇权、伦理纲常等的经济犯罪、土地犯罪中所经常采用的立法技术。在唐代,所有违犯律、令和部分触犯习惯、礼教的民事行为,一律视为犯罪,这符合唐代法律体系中“刑民不分”的特点。然而,这些犯罪与危及皇权、政权、封建伦理纲常的犯罪自然不能等同,属于唐王朝打击的轻罪。如何规范这种轻罪?除了刑罚设置与“十恶”之罪等有所区别外,压缩这些犯罪的犯罪圈也是重要的立法选择,这就涉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因为在定性之外,另附加定量的要求,就意味着在犯罪构成上增加了更多的成立条件限制。举例来说,《杂律》第422条规定的“买奴婢牛马不立券”行为,它并不危及唐王朝的统治,并且在现代看来乃是一种民法调整的行为,《唐律》对这一犯罪即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即规定“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立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对这种行为,犯罪人仅实施“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这一行为还不够,还有期限这一定量的要求,即“过三日”。再比如,《厩库》第211条规定的“假借官物不还”也非唐王朝重点打击的犯罪,为限制此罪的犯罪圈,《唐律》不仅对其有“诸假请官物,事讫过不还者”这一定性要求,而且还有“过十日”这一定量要求。可见,对国家宽宥的轻罪而言,采用定性与量刑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就起着重要作用,它可以提高整体犯罪门槛,把那些唐朝统治者认为不严重的行为排除在刑法之外,否则轻罪也会被判处重罚,危害不大的行为也会被定罪,因而是滥用刑法。这恰恰是不文明的。
关于这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在犯罪圈划分上所体现出来的积极意义,我们不妨以《唐律》对“公罪”与“私罪”的区别规定予以佐证。为了维护和加强吏治,保护官吏的利益,提高其执行职务的积极性,并明确刑法打击的职务犯罪的重点*陈鹏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四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唐律》对官吏犯罪依其性质明确区分为“公罪”与“私罪”,宽宥前者,打击后者。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唐律》立法技术对此有所体现:一是对公罪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以限制犯罪的成立,比如,《杂律》第444条规定:“诸请受军器,事讫停留不输者,十日杖六十,十日加一等,百日徒一年;过百日不送者,减私有罪二等。其弃毁者,准盗论……”二是对私罪多采用定性技术,比如《职制》第136条规定:“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坐赃论加二等;监临势要,准枉法论。与财者,坐赃论减三等。若官人以所受之财,分求余官,元受者并赃论,余各依己分法。”
可见,《唐律》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明确了刑法打击的重点与宽宥的对象,这对于合理划定犯罪圈具有积极意义,具有犯罪构成的解释性功能。
(二)有利于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
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之下,审判官对罪犯的定罪量刑不仅要判断其有没有实施某种行为,而且要看这种行为有无造成某种危害结果及其程度。如何把两者的关系有机结合起来,这需要立法上的制度保障,即需要立法以客观的、精确的立法技术把罪质与罪量、罪量与刑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架设起来。综观《唐律》,它完全实现了犯罪法定化、刑罚法定化与量刑法定化,尤其是在量刑法定化部分,每种犯罪对应的刑罚,每种犯罪的不同情况对应的刑罚,都是非常明确的、具体的。这在封建时代,十分有利于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举例来说,《唐律》第132条规定:“诸公事应行而稽留,及事有期会而违者,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在这里,审判官如何对“公事应行而稽留,及事有期会而违者”这一情形,宣告最终的刑罚,则必须根据“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这一量刑方法与结果进行选择,无任何自由选择余地。
那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在限制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方面,展现了哪些制度绩效呢?
第一,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使罪质与罪量、罪量与刑量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具有规范依据,也使审判官定罪量刑更具操作性。比如《户婚》第163条的“卖口分田”、第164条的“占田过限”和第165条的“盗耕种公私田”等,作为定性要素“卖口分田”“占田过限”“盗耕种公私田”等行为,与作为定量要素的“一亩”“十亩”“二十亩”之间相互关联,成为犯罪成立判断与量刑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尽管定量要素不是决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唯一因素,但起码也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犯罪成立与量刑结果选择的重要因素。因此,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出发,应使犯罪成立判断及量刑中的定性与定量判断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使罪质与罪量、罪量与刑量之间对应关系的设置相互协调。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把定性与定量导入罪刑关系的评价体系,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如果没有这样的立法技术,罪刑关系的均衡性就只能停留在学术层面的讨论上,并不能变成现实的立法规定。
第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为审判官正确定罪量刑提供了相对精确的尺度与可操作的标准。如何架设罪质与罪量、罪量与刑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这是古今中外学者所努力追求的。贝卡里亚曾不厌其烦地告诫立法者,要把法律制定得罪刑相适应,要使刑罚具有确定性和必定性,就必须“有一个相应的、由最强到最弱的刑罚阶梯”。因为贝卡里亚相信:“有了这种精确的、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我们就有了衡量自由的暴政程度的潜在的共同标尺,它显示着各个国家的人道程度和败坏程度。”*参见[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第66页。影响全球的《美国量刑指南》长达一千多页,对各种犯罪如何科处刑罚规定极为详细,它以量刑表(Sentencing Table)的方式,规定量刑结果之计算法则*参见吴巡龙《美国的量刑公式化》,台湾《月旦法学杂志》2002年第85期。。当代中国也有学者主张量刑精确化*参见赵廷光《论量刑精确制导》,《现代法学》2008年第4期。。其实,关于这种理论主张与规范实践,早在《唐律》中就已普遍存在了。比如,《户婚》第170条规定:“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本条规定的内容是:地方官的管辖区内或户主田地有荒芜,就以所荒芜田亩占全部田亩总数的比例多少定刑罚轻重。到底这种犯罪的刑罚如何操作,更为具体地说,这种犯罪的哪种情形应该判处何种刑罚,《唐律》的规定是一目了然的,即通过简单的数学计算即可得出。就《户婚》第170条的规定而言,如果荒芜10%,笞三十;每荒芜的数量增加10%,则加一等;最高判处一年徒刑。这就不会给法官留下恣意量刑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定性基础上,把定量立法技术运用到刑法规范建构中,才能为审判官正确定罪量刑提供强力的规范依据,司法公正才能有所保障。
第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使罪刑相适应程度的检验成为可能,有利于以制度方式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从立法上看,《唐律》对于不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进行了量化,由此至少引申出两个有意义的课题:一个是罪刑关系定量的标准,另一个就是罪刑关系定量的“递增公式”。通过对这两者相适应程度的考察,最终会得到《唐律》立法技术的精髓。在对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之定性的基础上,尚须进一步判断达到什么数量要求的危害结果等,才构成犯罪,在对量刑事实以定性技术区别的前提下,又要求根据不同的定量要求以及能够架设这种罪量与刑量之间对应关系的递增公式,以确定最终的量刑结果。运用这项技术,审判官的量刑也就有了操作指南,审判官判什么刑,判处多重的刑,《唐律》都以其高超的立法技术,做出了明确规定。这实为程序法欠缺时代,保障司法公正的制度建构。若审判官违反《唐律》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出入人罪”,还有严格的罚则设置,从而能够有效地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事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唐律》在立法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后期各朝法典编纂的楷模。它所采用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既避免了刑法中只有定性所导致的犯罪圈扩大的弊端,而且还以其较为精确的定量技术,架设起了犯罪轻重和轻重不等的法定刑之间的阶梯。并且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所传达的信息是立法者对犯罪构成与量刑制度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即定罪与量刑不仅有罪质的要求,而且有罪量的标准,前者意味着定性,后者意味着定量。就两者关系而言,罪质固然必不可少,但罪量也是关于犯罪危害性的评价依据,是区分罪与非罪、公正量刑的重要条件。只有正确认识罪质与罪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并借助于递增公式合理架设罪量与刑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才能形成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阶梯,才能为审判官正确定罪量刑提供规范依据,也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这就是《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给今人的重要启示。
JIANG Tao, professor & Ph. D. supervisor of Law School,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责任编校:徐玲英
Seeking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One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ve Techniques in theCodeofTangDynasty
JIANG Tao
Abstract: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s a reflection of superb legislative techniques in Code of Tang Dynasty. The combination is adopted in the constitution of crime and penalty measurement system of Code of Tang Dynasty. Special conditions are added in crime establishment and basis is laid down for the sentencing of judg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gislative techniques in Code of Tang Dynasty are connecting crime and criminal law by mathematical rationality and offering reference for impartiality by incremental formula. It helps to delimit crime reasonably in legislation and to prevent judges from making unscrupulous judgment. Therefore, it systematically safeguards judicial justice in feudal times, which can also give us some enlightenment now.
Key Words:Code of Tang Dynasty;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legislative techniques
作者简介:姜涛,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吉林 长春130012),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00023)。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国家社科 (13CFX045)
中图分类号:D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1-0125-12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