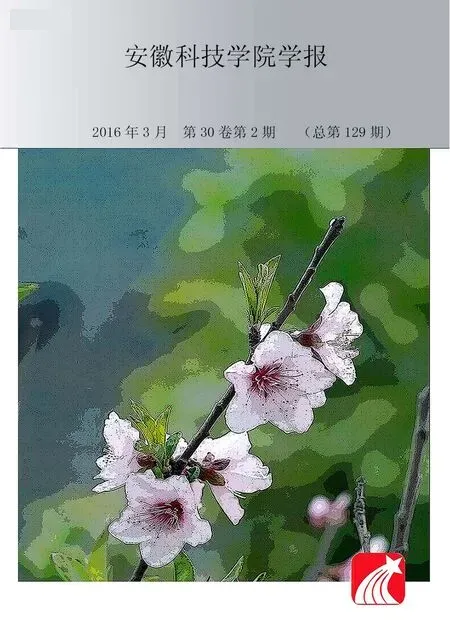《鲁滨逊漂流记》文化殖民色彩试论
汪愫苇(安徽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凤阳 233100)
《鲁滨逊漂流记》文化殖民色彩试论
汪愫苇
(安徽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凤阳233100)
摘要:作为笛福思想的代言人,鲁滨逊教授星期五英语、指引他皈依基督教等等行为无疑是对土著人进行文化殖民。当然,种族主义必然赋予文化殖民以合法外衣。因此,鲁滨逊“栽培”星期五的经过可以看作帝国文化殖民史中种族主义策略实施于殖民地土著的成功范例。所以,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殖民主义思想、文化殖民的色彩适当地加以鉴别与批判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文化殖民;宗教;语言;种族主义
丹尼尔·笛福开启了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先河,为此后英国和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同时开创了现代英国历险小说流派和范式,直接影响了后世英国历险小说的主题、风格、情节、模式诸多方面。小说一出版,立即赢得广大读者群,并出现了数目巨大的译本和改写本,同时,又有陆续出现大量模仿之作至于绵延整个维多利亚历史时期。其中的“异域风情、财富观念、不开化的土人、白人以现代技术(火枪)加语言和宗教对土人进行控制”[1]等等历险小说创作主要元素均与《鲁滨逊漂流记》一脉相承且蔚为大观。小说出版后不仅大受热捧,甚至“到海外殖民地的传教士除了《圣经》之外都随身带有一本《鲁滨逊漂流记》,可见其魅力非凡”[2]。
那么,怎样看待小说中充斥的浓厚宗教说教色彩,怎样看待鲁滨逊(笛福)的“土人观”包括所谓“食人生番”等等,如果我们细加研讨,也许会发现先前未被认真关注的某些方面。
1 鲁滨逊——笛福思想的代言人
《鲁滨逊漂流记》绝非简单记叙离奇探险的故事,而是融入了笛福自身六十年社会经历的深刻思考,是将鲁滨逊作为自己的代言人罢了,并以鲁滨逊的经历及其对人生的思考来传递作者本人在政治宗教方面的见解。
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笛福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贸易;支持扩展殖民地,反对专制政体、等级制度,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他失意于政坛,转而致力于小说创作,并在鲁滨逊身上注入自己的理想,把他塑造成为资产阶级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对他的品质极力加以美化。而且“鲁滨逊”形象也反映了殖民主义的特点:他贩卖黑奴、经营种植园、在荒岛上以代表资本主义文明的火枪和基督教教义征服土人,并把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带到了岛上。凡此之类,作者均以肯定态度加以叙述,并藉鲁滨逊二十八年荒岛艰苦生活、斗自然、伏暴徒、救“星期五”、救船长诸细节,将之塑造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英雄化身,成为西方文学中第一个理想化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正面形象,这正是笛福内心世界的文学表达。
鲁滨逊也是笛福思想观念的产儿。事实上,笛福之创作《鲁滨逊漂流记》,其唯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不过受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科尔的一次远洋私掠航行被弃荒岛独自生活四年故事的启发。更多的间接材料则来自《哥伦布航海日记》。在这部“有很多虚构因素”[3]的《日记》中,哥伦布以基督教文化传统在其头脑中形成的偏见,对异教徒土著的征服统治的“实录”,开创了所谓“幼稚的土著”的传统,在《漂流记》中得到充分的再现,《日记》中“传播基督教”而真实目的却是为着土地和财富、不停地占领岛屿建造城堡掠夺役使印第安人等等已然或隐或显地再现在《漂流记》之中。鲁滨逊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以少胜多最终战胜残忍懦弱无能的异教徒土著人并将其改造为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也赢得丰厚物质报偿之类情节描写,亦不过是哥伦布《日记》相关内容的文学再现而已。而这些有意识的刻意模仿,其背后同样也应该有着《哥伦布航海日记》里面隐藏着的明显的殖民主义意识。
鲁滨逊也是时代的产儿。作为作者倾力塑造的唯一人物,一个普通中产阶级人物鲁滨逊,具有典型意义,在他身上折射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精神面貌:他勇于面对现实,不屈不挠,靠一己之力争取生存权利。但同时也应看到,他不仅是劳动者,更是一个资产者和殖民者,具有剥削掠夺的本性。无论身处险境还是返回文明社会,他都严格屈从于经济利益的盘算。在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时也完全根据他人的价值。比如他将摩尔少年苏里卖给葡萄牙船长为奴,获利六十披索。即便有过瞬间犹豫,仅以新主人一句保证,他的良心随即便得到廉价的满足。他的数次出海,都是为了去非洲贩卖黑奴,漂流至荒岛后不断开疆拓土,不仅是向命运挑战,同时也是为了占有土地和财富。为慑服土著、使“星期五”心甘情愿为仆,他同样使用了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惯用的双重武器:火枪和《圣经》。即便回到英国后,他仍不忘返回小岛去视察“领地”。综上可见,鲁滨逊行为所具有的两重性,也正是作者(和他小说主人公)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和阶级局限。
如萨义德所言:“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原型是《鲁滨逊漂流记》,这部小说并非偶然地讲述了一个欧洲人在一块遥远的、非欧洲的岛屿上建立一个自己的封地……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土地的争夺上,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把它夺回来,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故事所决定。”[4]可谓切中肯綮,比对小说内容,可以使人一目了然,豁然开朗。总之,笛福采用一种全新的写作手法,用一种不夸张的、逼真而详尽的写实手法描述了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通过他精心编织的故事情节,倾力塑造的人物形象,把基督教文化精神渗透于其中,把小说创作活动与作者本身肩负的社会历史使命融而为一。
2 《圣经》——精神控制掠夺的利器
一部《漂流记》,几乎从头至尾都打上了《圣经》和基督教传统的烙印。全部的漂流故事其实是处于附属地位的,实际上不过是为了表达作者的一种观念体系——是与大英帝国的文化认同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都不是简单的积累和获得的行为。它们都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所支持和驱使。”也就是说,殖民者对土地的占有,不仅是物质的掠夺,更是精神的亵渎。所以,鲁滨逊在比使用火枪更早的时候,就高高举起《圣经》这一武器了!至少,在他漂流荒岛之际,在失事船上寻得大量武器弹药的同时,居然奇迹般“找到三本很好的《圣经》”!从此,《圣经》几十百次在小说中出现:作为口头禅也好,遇救也好,遇到好事难事也好……甚至偶或暂时忘记了上帝,鲁滨逊都要加倍地予以强调、提醒。如大麦生长出来、地震受苦之后,他都有严厉地自省:又急忙在“日记”中非常自然而然地得出了结论:是上帝创造了一切。既然“上帝创造了这所有的一切,那么他也引导和支配着这一切以及与之有关的所有一切,因为上帝既然能创造万物,必然也能引导和支配万物。”“我坚持不懈地读《圣经》和向上帝祈祷,思想被引导到了一个较高的境界”。
直至小说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遇到野人,拯救“星期五”之前),笔者只能挂一漏万,作者确是连篇累牍。所以说一本《漂流记》“充斥着说教”实不为过。那么,笛福让鲁滨逊在荒岛如此苦读苦悟,所为者何?简言之,他要打造一个上帝与《圣经》熏陶而出的一个“金刚不坏之身”鲁滨逊,更向世界宣示基督教精神教义“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它可以拯救一切!何况,它还可以助力鲁滨逊发财致富,独霸一方“天下”,成为“这里至高无上的国王和君主,对这里拥有主权”。尽管说话时多少有些戏谑色彩,而小说结尾,一切都绝对成为现实:“我得到想都想不到的一大笔财富”,“我又回到我的岛上,现在已经宛如我的一个新殖民地”!于是,人们仿佛听到笛福的劝诫:朋友,你想脱离苦难吗?你想获得泼天富贵无上权势吗?请皈依上帝吧!因为,“冥冥中有一双富有神力的手在支配一切,上帝的慧眼无处不在,无论是天涯海角,只要他愿意”!
众所周知,基督教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圣经》中也反复强调上帝的独一性,并明确划分、区别对待“上帝的选民”与“异教徒”。不错,欧洲人对基督教的虔诚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何让土著人接受或者说土著人为什么也会愿意接受?是否让全部土著人“普及”基督的“福音”?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否具备可被“改造”的条件!这就是首先将土著分为邪恶、残暴的“坏土著”与善良、温驯的“好土著”(也可以称之为“高尚的野蛮人”)——当然,其制定权只能在“我”(笛福、鲁滨逊——欧洲人,更准确地说是“英国殖民者”) !具体的判定标准则要看土著人是否具备“淳朴、慷慨、诚实、勇于自我牺牲”,是否“亲近,并愿意皈依基督教”,是否“是白人的助手和忠仆”。只有那些“好土著”,才有资格,有机会获得欧洲文明人施以宗教(基督教)教化的“殊荣”!在《漂流记》中,“星期五”荣获好土著的典型代表,作者赋予他好土著的一切标准,且看鲁滨逊(笛福)的“教化”手段:
鲁滨逊决心要弄到一个(或两三个)野人,“让他们对我完完全全地俯首称臣,要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他用火枪杀死两个“食人生番”之后,一个俯首称臣的野人出现了,作者让鲁滨逊仔细地予以“目测”:“不像其他美洲土著那样令人厌恶”、“看起来很舒服”,“丰满”、“完美”、“整齐”等等好形容词都用上了。并在武器的震慑(枪弹)之后,鲁滨逊以“星期五”命名该野人,开始以有效传播西方文化的仪式唤起对星期五基督教信仰的意识,并指明这信仰与“生活目的”的普遍真理之间的关联,还指引星期五关于上帝的知识,向他灌输基督教的知识,并竭力“帮助”星期五力驱原先的信仰,与星期五一起诵读《圣经》,“令这个异教徒睁开了双眼”,“使他领悟到基督教这个唯一正宗教义的真谛,使他认识了耶稣基督,而认识他就是获得永生”!连鲁滨逊自己也被感动了哩!“我这种平凡的指引还能在启发这个野人方面起到作用,使他变成一个我生平少见的虔诚的基督信徒”。
于是,星期五成为鲁滨逊以基督教与上帝名义“调教”成为帮手、助手、忠仆——乃至“帮凶”。他唯鲁滨逊马首是瞻,不仅五体投地,誓死效忠,而且可以任凭指使,毫不犹豫地杀死自己的同类。
为了强化星期五的觉悟和觉醒,笛福还让星期五从那一帮野人俘虏堆里救出另一个野人——星期五的亲生父亲,且一边让鲁滨逊“心中有数”:“尽管我有三个臣民,但是却分属不同宗教:我的星期五是新教徒,他的父亲是异教徒,一个食人生番……”一边“由于星期五父亲的担保,我(鲁滨逊)又重新考虑坐船到大陆上去的老问题了。”而且,为了“航行到美洲任何一个基督教的殖民地去而作贮备”,鲁滨逊还接受西班牙人的建议“让他和星期五父子再开垦更多的土地”,并让西班牙人“监督并指导星期五父子工作”。待到收获之后,鲁滨逊开始落实了他宏伟蓝图——星期五的父亲被派渡海去“大陆”完成主要任务,星期五本人则荷枪实弹“显然已经被我训练成一个神枪手”,紧跟鲁滨逊执行对付跟上次完全不同的敌人。其后,鲁滨逊获利无数,富贵无比,衣锦还乡,“这期间我的星期五一直忠实地跟着东奔西跑,这证明了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一个最诚实可信的朋友”——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展现出来的!鲁滨逊成功改造星期五,是小说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笛福文化殖民思想浓墨重彩的宣示之一。
3 语言(英语)——传播殖民主义社会价值观的载体
殖民主义者的注意力一向集中在对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的争夺上面,那么占有之后、消灭了“劣等”、“野蛮”的土著之后呢?宗教灌输也好,种族主义政策策略也好,都离不开或者说必须依托于“宗主国”的语言的“教化”功能!换言之,文化殖民是与“语言殖民”须臾不能分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比火枪、火炮还要重要!因为殖民者最终目的是制造出顺民、“良民”。
因为殖民者不能使土著全部消失,事实上,把土著和白人分开,然后把他们加以改造,变得依赖于欧洲的存在——或许是一个殖民地的农场,或是一个主流话语结构,他们均可被归属其中并发挥作用。而在这个话语中,怠惰的土著又被描述为天生的堕落与放荡性格而需要一个欧洲的主人来控制的角色。于是,鲁滨逊在教星期五学英语刚刚“能开口说话并能听懂我的话”的时候,便助力星期五摧毁其土著信奉久远的“奥乌卡基”宗教,并“指引他有关真正的上帝的知识”,显得多么“顺理成章”啊!所以说,作为殖民文化的载体,殖民化语言必然肩负着承载、延续、传播殖民主义社会价值观的重任——如果殖民者最终目的是教化出“助手”和“忠仆”,那么“殖民教育(尤其是语言教育)就是其危险的同谋。”[5]
所谓“文明”也极有可能是野蛮的,因为长期殖民主义思想的“熏陶”,使得鲁滨逊(们)已难以彻底摆脱其殖民视角,甚至形成了连他本人也难以察觉的“文化优越感”的“集体意识”。这种意识流露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一方面在显性层面大量使用情感化的语言——甚至能够对殖民主义话语进行批判,但另一方面,在隐形层面又默认这种殖民活动,甚至彰显其作为白人的优越感。同时,作为被殖民者(如星期五),若想获得作为白人奴隶的“资格”,那就必须寻求英语语言和文化的庇护——当然,这种被英语教化的“殊荣”也是无法保证哪怕是高尚的土著如星期五(们)与殖民者如鲁滨逊(们)平起平坐的!请看《漂流记》:“星期五的英语已说得很不错了,也差不多明白我教他的每样东西的名称以及每处我派他去的地方,还喜欢不停跟我说话”;“现在我和星期五之间的了解更深了,他几乎能听懂我所有的话,并且也能流利地说英语了,只是不大标准”——原来如此!笛福在“鲁滨逊教星期五学英语”一段故事里,确是大量使用感情化的语言(甚至设身处地与星期五“换位思考”哩) !但是说白了不过是:他已达到主人对其语言水平的需求,换言之,他的主人可以毫无障碍地下达命令,并可以坐享其成了!如此而已。
所以,撩开作者(小说)的“面纱”,星期五(们)虽然即便具有说英语的能力,但也不能(不必)将这语言说得和主人一样好,他在英语语言表达和准确程度上也是不能、也不应该达到殖民者主人(鲁滨逊们)的水平上的。尽管星期五的语言表达进步很大,那也只能停留在领会主人命令的水平,所以小说中写他说话时总会有些这样活那样的表达错误,那是因为这些错误是必要的,尽管他也能流利地说英语了,但还是不太标准——或许因为他本就不应该说得标准!
从鲁滨逊不失时机地调动各种手段对星期五推行“英语教学”,可以清楚地看出殖民者在培养殖民地本土精英的工作中至关重要:既直接训练培养帮凶和忠仆,可以随时“指哪打哪”,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藉此取代殖民地本土“低等”的语言文化形式,“最终到达以大英帝国臣民的意识形态进行殖民的目的”,而诸如星期五这样接受过“教育”的殖民地本土精英们,其实也只能处于劣等的从属地位,对殖民文化(殖民者语言)也只是(只能)极力模仿而已。而且,殖民统治的强权语言文化策略还可以进一步从心理上征服被殖民者,使他们产生对本源语言文化的自卑心理和对殖民者的趋同心理,并积极追求殖民者的认可和赞许。
4 种族主义——文化殖民合法化的依据
一部《漂流记》,以鲁滨逊坚持冒险出海贩卖奴隶始,以小说结束时鲁滨逊盆满钵满,富甲天下,雄镇一岛“买”人终:其中二十多年,鲁滨逊卖过摩尔少年苏里,又以火枪和《圣经》获得了助手、仆人实际仍是奴隶的星期五!可以说,一部鲁滨逊的历险、发迹史,也是笛福头脑中种族主义思想集中鲜明的体现,上列内容仅其皮相、皮毛而已。
种族主义者自认为是人类的代表而排除任何“他人”,将“我们”看作为人类本身而与“非我们”对立,进而形成“我们——文明人”,而对“他们——野蛮人”的思维定势,其背后即是文化和性质的对立,于是,落实到“人”,则可表现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后“必先诛之而后快”——即便或有可以不“诛”,也当以双重武器(火枪与《圣经》)慑服之改造之。故哥伦布秉承《圣经》“上帝——撒旦、基督徒——异教徒、自我——他者”二元对立思想,在“日记”中充分发挥基督教文化传统之“社会集体想象”,开创“幼稚的土著”传统,行动上则表现为占领岛屿,建造城堡,掳掠役使印第安人,以枪炮杀人在先,《圣经》紧随之,所存土著凡不皈依基督教格杀勿论。而《漂流记》完全以《日记》为“模本”,首先将其中“土著吃人”、“食人生番”淋漓尽致反反复复加以宣扬,杯弓蛇影也好,忧思难解也好,自唬唬人也好,尽皆活灵活现,其实皆为“铺垫、造势”。后来,野人吃人一但“发现”(暂时作如是观),鲁滨逊则“头脑里充满了报复的思想,要一刀杀他们二三十个”。而笛福又让鲁滨逊犹豫自省,不可贸然,当他又见血迹、骨头,“我义愤填膺……非把他们消灭个干净”,但随即又让鲁滨逊不安:“这样杀下去,我最终也成了一个比那些食人生番好不了多少,没准还坏得多的凶手。”其实这些都不过“蓄势”而已,且鲁滨逊还明白自己缺少帮手:梦中也表现出自己亟需仆人,甚至“弄到一个野人”。终于,第三次发现野人,而且接着真的第一次发现野人杀人、食人场面,于是鲁滨逊代上帝行“正义”之事,连杀两人,救出“星期五”,可谓一举两得!于是进而“改造”驯服星期五,直至成为鲁滨逊杀人的帮凶!
鲁滨逊“栽培”星期五的经过可以看作帝国文化殖民史中种族主义策略实施于殖民地土著的成功范例。笛福正承《哥伦布航海日记》,开启维多利亚时代理想小说,以星期五的形象确立了“高尚的野蛮人”的传统。星期五迥异于多数“坏土著”的邪恶、凶残、怯懦、幼稚,作者着力表现其淳朴、慷慨、诚实、勇于自我牺牲、亲近基督教,获救后迅即成为鲁滨逊梦寐以求的助手和忠仆。其实,星期五形象不过是欧洲文化传统中“高尚野蛮人思想”[6]和英国殖民扩张的现实需要相结合的产物,是“另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思想的表现,目的仍然是为大英帝国殖民扩张服务的!
种族主义在实践方面其实并不十分抽象,种族主义行为也不一定与种族主义意图或观念有关,只是都先验地或经验地以最充分的兴衰予以合理化:首先是隔离、歧视、驱逐“不受欢迎者”;其次用具体暴力对付一个群体的成员——由于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三,在魔鬼化或野兽化的基础上消灭一个被认为“多余”的居民类别的所有代表[7]。将上引对照《漂流记》鲁滨逊们的心理活动以及所作所为,若合符契。比如,当年的殖民主义者皆为白人,《漂流记》中白人鲁滨逊自然而然高人一等,所以,即便星期五这个极为鲁滨逊赏识之“高尚的土著”,称为“朋友”、“副司令”、“忠仆”,且不吝以“英雄气概”、“和蔼可亲”、“看起来舒服”赞之,而说到底亦不过其治下的仆人、奴隶甚至走狗而已!而鲁滨逊对“白人”则极为不同:在买摩尔少年苏里时,他极其自然地相信那白人船长善待苏里的承诺;在岛上拯救失事大船上白人群体的时候,极其关切白人安危,下决心去实施救人。在对野人杀伐中因极其关注白人而“怒不可遏”。西班牙人击杀野人,“一旦手上有了武器,他仿佛就被注入了新的力量……一下子就砍死了两个野人。”后来对那西班牙人言听计从,并赋予“监督星期五父子工作的重任”。其后,又被西班牙人船长等天主教徒奉为“总督”,接受其丰厚礼品并携带财物返回欧洲,还念念不忘留在岛上的犯有“过失”的英国人,在小说结尾还答应从英国给他们送几个女人和大量生活必需品去,后来都兑现了。所以,看似一段离奇的经历,而融注其中的实质性的东西便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本身:鲁滨逊的全部行为,无不侵染殖民主义之种族主义色彩!
综上,笛福以一部划时代的通俗小说,把他所处特定时代的殖民精神、殖民主义思想,同时也把他本人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通过鲁滨逊的人物形象含蓄隐晦地,同时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今天,《鲁滨逊漂流记》再次在我国畅销,且作为单纯的所谓“励志”之书而为儿童少年以及青年、成年热读。那么,对这一部影响巨大的世界文学名著隐晦于其中的殖民主义思想、文化殖民的色彩适当地加以鉴别与批判,也并非是毫无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陈兵.帝国意识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的繁荣[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 103-108.
[2]陈兵.英国历险小说:源流与特色[J].安徽大学学报,2006(6) : 81-85.
[3]陈兵.基督教文化传统、哥伦布与英国历险小说中的土著形象[J].外国文学,2007(3) : 97-104.
[4]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5]胥维维.制度模仿者的国家机器:《米格尔大街》中的殖民教育[J].外国文学评论,2013(5) : 141-147.
[6]陈兵.“高尚的野蛮人”与英国历险小说中的土著形象[J].外国文学,2013(2) : 52-59,158.
[7]塔季耶夫.种族主义源流[M].高凌翰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责任编辑:郭万红)
On the Cultural Colonization in Robinson Crusoe
WANG Su-w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esity,Fengyang 233100,China)
Abstract:As the spokesperson of Defoe’s thought,what Robinson did,like teaching Friday English,leading him convert to Christianity,was undoubtedly the cultural coloniz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of course,cultural colonization was legitimated by racism; therefore,Robinson’s cultivation Friday can be taken a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implement ation of racist policies.Therefore,it is of significance to interpret the colonial ideology,cultural colonialism in Robinson Crusoe.
Key words:Cultural Colonization; Religion; Language; Racism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772(2016) 02-0119-05
收稿日期:2015-09-15
基金项目:安徽科技学院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RC2014354)。
作者简介:汪愫苇(1978-),女,安徽省霍邱县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