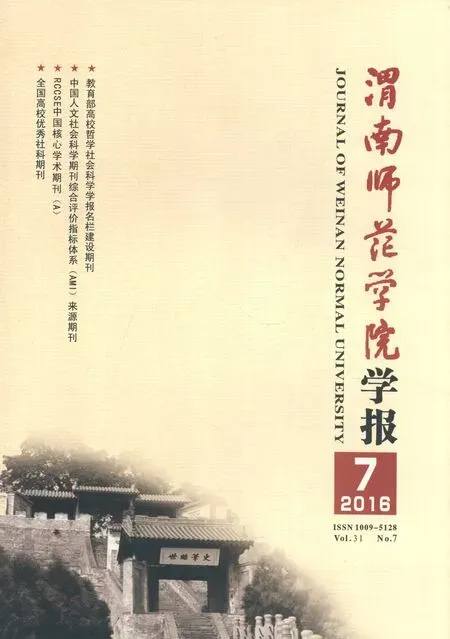苦难民间的生命谣歌
——李康美《弯人之谣》解读
陈 理 慧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714099)
苦难民间的生命谣歌
——李康美《弯人之谣》解读
陈 理 慧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714099)
摘要:李康美的《弯人之谣》通过对父子两代农民苦难的生命困境的真实叙写,丰富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意识形态关于苦难的乡土中国的想象方式,同时又通过善恶交融、美丑并存的乡村人物真实的生命样态,反拨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审美意识形态关于诗意的乡土中国的想象方式。他作为农民写农民的乡土写作还原了真实民间的生命真相。
关键词:李康美;《弯人之谣》;乡土写作
笔者在研究李康美乡土写作的过程中,发现1991年3月发表于大型文学刊物《芒种》上的短篇小说《弯人之谣》,在李康美乡土写作中具有分水岭的意义,标志着李康美的乡土小说终于形成了自己的个性风格。从此,他的乡土小说不再图解当权者的政治意图、呼应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参与时代命题的讨论、凌空高蹈于过往的乡土旧梦,而是真诚地将时代政治变迁下乡土小人物真实的精神世界表现出来。笔者认为李康美这种对于乡土小人物真实精神世界的乡土写作,对于20世纪以来关于乡土中国的经典想象方式构成一种有益的反拨和补充。本文在细读《弯人之谣》的基础上,结合李康美的成长经历,试图在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写作的两大传统中,考察李康美乡土小说写作对于乡土中国的独特书写方式。
一
20世纪20年代,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焦虑,使自觉听命于五四思想革命“将领”的鲁迅将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当作其小说表现的对象,从而开创了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鲁迅风”传统。尽管鲁迅作为一个少时出身乡村“大户人家”、青年时求学异国他乡、成年后位处大都市知识生产中心的现代知识分子,其乡村生活经验的有限性(鲁迅母亲虽是“乡下人”,却是乡村“大户人家”的女儿。况且鲁迅的乡村履历只有每年随母亲“抽空去住几天”的旅居经历和祖父科场案发的“半年多”的避居经历),使他对真实的农民生活比较隔膜。但“立国必先立人”的国民性改造愿景、对农民生存境遇的深切关切,使他将乡村批判当做了其国民性批判的重要一翼。因此,当鲁迅站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上,用现代文化观照乡村时,便以乡土寓言的方式想象了一个文学上的乡土中国:愚昧、麻木、冷漠、不觉悟的农民。这样“病态”的乡土中国自然成为鲁迅文化启蒙、社会改造的对象。
鲁迅先生晚年谈到为什么做起小说时,仍然强调:“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2]526因此,当鲁迅站在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以个性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为武器来理性观照乡土社会时,他首先关注的是农民精神上的“病苦”。在《祝福》《故乡》等乡土力作中,鲁迅通过对祥林嫂、闰土等在封建专制政治、封建等级文化压制和禁锢下愚昧麻木灵魂的展示,揭示了几千年文化传统以“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方式“吃人”的残酷真相,提出了对农民进行文化启蒙的急迫性。和鲁迅乡土小说多关注乡村社会下层小人物的命运一样,李康美的乡土小说也“多写下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3]1。但和鲁迅乡村生活经验有限、没有农民生活体验不同的是,李康美不但有着非常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也有着当农民的独特生命体验。李康美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不但17岁之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而且有过将近三年的农民生活经历。就是以后离开农村外出参军、工作,也是在距故乡农村不远的地级市生活、工作。农家子兼农民的生活经历,使他非常熟悉农村的日常生活和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势农民的生存状况。在他看来,他们之所以被排挤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他们自身的身体缺陷、智力局限以及无力应对的灾难打击等。《弯人之谣》中,张忍父亲的苦难并不是来自旧社会(封建社会)传统文化驯服下精神上的愚昧与麻木,而是妻子生育时的难产。在大人与孩子只能争取一个的情况下,他在争取到一个驼背的残疾儿子的同时,也为自己争取到了鳏夫养育独子的苦难命运。同样,张忍的苦难也并不是来自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改造下精神上的惶惑与恐惧,而是身体残疾、父亲突然去世、麻杆女人母子被造反派强行带走的人生灾难。在这里,新旧社会制度更替所带来的传统文化的某种断裂并没有终结个体生命的苦难,因为张忍父子的苦难并不是源于精神状态上的愚昧、麻木,而是生命欲求上的匮乏、缺失。大跃进中,张忍的父亲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义务替一个寡妇淘铁砂。一个人干两个人活的体力透支最终使他猝然倒毙;张忍父亲去世后,精神的孤独、寂寞使张忍的生活了无生趣,“张忍就独守一个小院。小院里很脏,他想在哪儿拉就在哪儿拉,邻居的鸡进来一啄一刨,就更加遍地脏臭”。麻杆女人的到来,鼓起了他生活的劲头,“白天还得早起把院子扫干净”。麻杆女人走后,他“重新坐在南墙下的阳光里,脱光膀子捉捏衣缝的虱虮。男人女人从身边过,他从不觉得丑,不觉得羞”。“张忍懒得出了名,鼻涕掉下来懒得用手擦而是歪过头去在肩头上蹭。”麻杆女人的儿子投奔他后,虽然这个孩子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为了养育他,“他一下子勤快了”。为了阻止孩子离开,他甚至把孩子捆起来。和父亲一样,他也需要亲人的陪护与两性间的正常生活,当这种最基本的生命欲求以麻杆女人母子被造反派强行带走而终止时,他就在满院腥臭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见,要了张忍父亲命的既不是繁重的淘铁砂任务,也不是养育独子的艰难生活,而是老鳏夫被勾引起的性欲和满足正常性欲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同样,要了张忍命的既不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不果腹的物质贫困,也不是光棍兼残疾被村人轻侮的精神困苦,而是鳏夫最基本的人伦天性被无情剥夺后的生命困境。
与站在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关注农民精神上的病苦相辅相成,鲁迅以“为人生”的人道主义激情关注着农民生存上的困苦。在《风波》《阿Q正传》等乡土名作中,鲁迅通过对七斤、阿Q等在社会变革、文化变革中冷漠、不觉悟灵魂的揭示,批判了乡村民众与上层社会文化变革间的相互隔膜,企望通过社会改造来改变农民贫困、落后的生存状态。与鲁迅小说中批判的乡村小人物对社会文化变革毫无感应的精神状态一样,《弯人之谣》中,李康美也展示了张忍对社会文化变革茫然无知的一面。如文化大革命中,麻杆女人的孩子找上门来,拿着“红皮皮语录本”,操着“革命”术语逼他当父亲,张忍“心头一颤,舌头在嘴里挽成圈圈,吐不出话。他以为这孩子是小天神下凡,得罪不得的”,便接纳了他。但与鲁迅社会批判视野下农民与社会文化变革间互不相关的生存状态不一样的是,李康美在个体生存境遇的意义上揭示了农民与政治(社会大变革)独特的结缘方式。《弯人之谣》里,当对文化大革命茫然无知的张忍为了留住麻杆女人的孩子,开始学着用革命术语“老子革命了”威慑时,他意外发现竟取得了效果(孩子留下了);继而麻杆女人二次投奔他时,他惊讶地发现原先既懒又嫌弃他的麻杆女人竟然被“革命”改造得既勤快又顺从,便不由得心理感慨:“革命还是好,把她的瞎毛病都革完了。”最后,尝到了“革命”甜头的张忍便在“球了!革命万岁!”的欢呼中对“‘革命’充满了感激”。在这里,农民不再是鲁迅笔下自外于“革命”(社会变革)的看客,而是“革命”的同路人。同时,“革命”也不再是弥漫到乡村社会的一场风波,而是动摇乡村社会结构的一场巨变。在大炼钢铁的社会运动中,张忍的父亲因淘铁砂有了满足性欲的机会,也因淘铁砂和性的身体透支而丧命;三年自然灾害,张忍一个光棍竟因饥馑意外捡了个妻子也因饥馑过去失去了妻子;文化大革命中,张忍因文化大革命而与地主的儿子和小老婆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也因文化大革命毁掉他幸福的家庭生活而死亡。《弯人之谣》从旧社会写到新社会,里面既有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也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这些到今天依然被诟病的社会劫难,但李康美既无意追溯民间苦难的政治渊源,也无意对政治本身的正确与否进行民间论证,而是倾力叙述民间不变的苦难宿命。在他看来,对不具备政治智慧的农民来说,政治从来就是一种他们无从把握也把握不了的强大的异己力量。在这种强大的异己力量的摆布下,他们试图借助它来改变自身命运的一切努力注定只是一种虚妄的挣扎。
李康美的乡土写作直抵乡间人物原始人性的深处,倾听他们卑微生命的悸动,在最基本的生命欲求层次上还原了民间苦难的真实样态。在他看来,对心智简单、隐忍顽强的农民来说,生命欲求匮乏的苦痛远要比精神上的病苦、生存上的困苦来得更强烈和迫切。因此,对他们来说,只要亲人死亡的灾难能够免除,只要性匮乏的苦痛能够解除,他们的生命苦难就可以终结。然而,恰恰这些是什么样的文化启蒙、社会改造都无法给予他们的。文化、政治与民间的这种结缘方式在事实上对民间苦难的不能根除,使李康美对乡土中国的寓言化、理性化想象方式进行了本能的抗拒。
二
20世纪30年代,都市现实生活的挤压,使本能抗拒城市主流文化的沈从文有意将边缘性的湘西文化当做其小说表现的对象,从而开创了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沈从文传统。尽管沈从文作为一个出身边地行伍世家、高小毕业就进入地方行伍、20多岁才离开湘西流寓北京、靠自学登上大学讲台的现代知识分子,其有着最具“原生性”、最“纯粹”、最为丰富完整的乡土经验。他14岁就进入地方行伍,过早地直面了生活中的鲜血和阴暗,他具有一份家庭生活中的温馨宁静与社会生活中的血腥杀戮、自然山水的美丽和谐与人世社会的无情争夺相交织的非常芜杂的乡村生活经验。但出于对近代以来由都市发动的系统性的“乡村改造”的抵御,使他将湘西世界当作抵抗甚至改造都市文明的寄托和理想。因此,当沈从文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用传统文化观照都市时,便以乡土抒情的方式想象了一个文学上的乡土中国:优美的、健康的、自然的、人性的人生形式。这样的“诗意”的乡土中国自然成为沈从文传统道德审美、文化寄寓的对象。
关于《边城》的创作动机,沈从文说得很明白:“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4]280这种美与真的人生形式正是他全部创作的旨归。如他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5]42这种创作观念决定了沈从文的乡土创作不是从鲁迅式社会、文化批判的角度去鞭挞人性的劣根,而是从道德、审美的角度去讴歌人性的美好。在《边城》里,沈从文通过爱与美的化身——翠翠形象的塑造,奏出了一曲人情美、人性美的田园牧歌。与沈从文以人性书写为旨归的创作追求一样,李康美也认为:“文学就是人学。不管你是从头上写还是从脚上写,最后都要移动到人心上。”[1]215但和没有农民生活体验的沈从文以现代文明批判者的身份,对自己原生态的乡土经验进行情感化的道德审美不同,李康美以农民写农民的方式,原生态地在生命情感的层次上还原了乡土人性的丰富性。在《弯人之谣》中,张忍的父亲面对妻子死亡的悲剧,他没有哭天抢地,而是“把心尽了,他爸把他妈在炕上暖了整整一夜”;同样,张忍面对父亲突然死亡的悲剧,他表达自己愤怒的最激烈方式,也不过是把气撒在遭致父亲死亡的那堆铁砂上,他“把那堆铁砂脚蹬手刨扑撒进河水里,浑身就没有了力气”。然而,父子两代这种承受人生苦难的隐忍态度,并不是沈从文笔下所展示的“不识不知”,在这种听天由命的隐忍中更多包含的是乡土小人物面对苦难时的软弱无力、懦弱无能;同时,张忍父子也不是《边城》中那些无私无欲、把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能“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5]45的美与善的化身。张忍父亲明明知道那个给他红薯馒头吃的女人的自私用心,他也知道他不会爱她到无私帮助她的程度,但这个鳏夫只能在这种苟且的性中暂时缓解他性欲匮乏的苦难,他以既摇女人又给他摇的女人摇铁砂的方式,“硬是把还不老的老命摇给了那个偷他铁砂又给他红薯馒头吃的女人,摇进了铁砂里,河道里”;张忍虽然在饥馑中接纳四川女人时不无自私的用心,但当那个四川女人以性献身的方式终结了他的苦难时,他人性的光华也被激发了出来,他变得勤劳、善良、宽容、无私、富有爱心。饥馑过后四川女人跑了,他没有诅咒她的忘恩负义,相反,明知她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依然无意识地给有烟瘾的她攒着烟叶:“‘给,我知道你不抽这个就活得不松泛。’这几年,他总是攒着烟末,也不知道给谁攒。麻杆女人看了看烟包包,泪花盈盈。”文化大革命时,她的儿子投奔来了,他又无怨无悔地为那个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付出一切。但当那个孩子要求离开他回家时,张忍“想不到又要剩下自己一个人,骨节都稀里哗啦地松散开来,慵慵懒懒地什么都无心去干”。最后,为了阻止孩子离开,他“悄悄找了一条绳子把他的手脚捆了个动弹不得” 。
沈从文认为:“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6]110这就构成了沈从文乡土人性写作的两极:从道德审美的角度去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从自然人性的尺度去抨击现代异化的人性。在《龙朱》《月下小景》等诗体乡土故事中,沈从文通过化外民族青年男女性爱的无机心、自然率直,讴歌了健全的生命形态和原始的生命强力,并企图以湘西世界所保存的这种自然生命形式作为参照,来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7]237、人的再造。与沈从文人性写作视野下将乡村性爱形式的自然、大胆当作健全的生命形态一样,李康美也肯定了性爱对于乡村个体生命存在的重要意义。《弯人之谣》的“谣”是歌谣的意思,而“摇”则是极富民间色彩的性行为。当李康美将张忍父子苟且、暧昧的性行为“摇”升华成他们苦难人生的“谣”时,也包含了他对民间性爱形式的理解与尊重。但与沈从文民族文化重构愿景下将乡村性爱形式符号化不同,李康美在个体生命存在的层次上还原了乡村性爱形式的复杂性。张忍的父亲作为一个成年人,当那个女人以红薯、馒头、身体来引诱他时,他未尝没有看清对方以此交换自己劳动成果的自私用心,但经年累月性的压抑与匮乏,使这个老鳏夫丧失了应有的理性与警惕。他耽溺于临时的两性苟且中并在这种苟且中最终丧失了性命;张忍作为一个光棍,当四川女人向他乞求“我是想……找口饭吃。有个安身落脚的地方就更好了”时,他本能的反应是:“这年月,红薯比女人香。”他不肯为了一时的性快慰而交换掉活命的红薯,“张忍舍不得拿出来”。但当那个女人在打听清楚他的身世后,直白地向他求婚:“村里人说,你没个屋里人。”出于对性与爱的需求、对她身世的可怜,他收留了那个女人。在这里,乡村的性爱形式固然有它自然、率直的一面,但在这种原始的性交换、性献身中也暴露了乡村人性的贫困与简陋、乡村生命形式的卑微与寒荒。同样,乡村这种自然的性爱形式也不是什么生命的强力,它不仅无力承担起自我生命升华的责任,更无力承担起民族再造的重任。张忍作为一个处于乡村社会边缘地位的残疾光棍,几乎没有娶妻生子过正常家庭生活的可能,他的一生似乎注定了要在百无聊赖、了无生趣中混下去。然而,“三年自然灾害”竟凭空给他送来了一个女人,他的生活由此出现了生机。文化大革命中,被驱逐的地主小老婆和流离失所的儿子竟然使他意外享受了短暂的天伦之乐。同样,当他正孜孜地享受着天伦之乐时,他的天伦之乐却以造反派强行押走他的女人和儿子的方式被猝然终结,短暂幸福的终结也终结了他的生命。张忍父子将苦难生命的自我救赎寄托在人类粗犷、原始的性上,然而恰恰这点卑微的人之常情的满足与否却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
李康美的乡土写作直抵乡村人物隐秘、幽微的精神世界,通过乡村人物生存方式上的隐忍与无力、两性关系上的温情与苟且、性爱形式上的原始与简陋,生命存在上的脆弱与悲凉,展示了乡村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还原了乡村人物善恶交融、美丑并存的真实生命样态。在李康美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一种超越于现实生存的所谓美好人性、人情,也根本不存在一个封闭的、自外于社会政治的所谓诗意的民间。在日常的乡间之外,从来都有一只政治的巨手在无形中操控着人们的命运,在操控与被操控中,他们本能地释放着人性的粗鄙与美好。因此,当李康美让张忍父子卑微的性挟带着人性的粗鄙与美好来穿越生命的苦难时,他们既不是鲁迅出于改造国民性的目的而塑造的愚昧、麻木的老中国的儿女,也不是沈从文出于抗拒城市文明的需要而从乡间记忆中打捞出的健康、优美的人生形式。李康美以善恶交融、美丑并存的乡村人物的真实生命样态,拒绝了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启蒙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出于文化改造或文化审美的需要,对于乡村生命形式的理性化、情感化取舍。
如果说,“20世纪中国乡村题材创作的一个几乎难以克服的‘顽症’:乡村主人公的‘知识分子化’、‘理性化’、以至‘概念化’问题,或者说是站在一定社会文化立场上的作家‘希望’、‘以为’乡村人物怎样与乡村人物事实上‘是怎样’之间的长期紧张、错位和悬隔问题。”[8]58那么,李康美的乡土写作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紧张、错位和悬隔。当李康美作为农民写农民时,农民不再是外在于他生命经验的客体,而是内在于他生命经验的主体。这就使他的乡土小说以农民写农民的乡土写作范式,对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为农民写、写农民的写作范式进行了某种有益的反拨和补充。他带领我们直抵静默的乡间生活现场,倾听乡间生命的卑微谣歌,将被知识分子启蒙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想象所遮蔽了的真实民间的生命真相裸露出来,还原了民间生活的复杂与暧昧、农民生命的顽强与苟且。这也许就是李康美乡土写作的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德]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李康美.弯人之谣·序[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
[4] 沈从文.水云——我怎样创造故事、故事又怎样创造我[M]//沈从文文集:第10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5]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 [M]//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6] 沈从文.创作杂谈·给志在写作者[M]//沈从文文集:第12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7] 沈从文.《长河》题记[M]//沈从文文集:第5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8] 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2.
【责任编辑马俊】
施宾格勒曾说过:“农民是没有历史的,因而没有书写。”[1]282到了20世纪,出于建立、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才得到被书写的机会。从此,乡村、农民、乡土成为新文学关注、描写、叙述和想象的中心和重心。强烈的现实焦虑、要对中国未来发言的历史冲动,使不同文化立场的乡土作家对同一乡土现实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从而形成了中国乡土小说的鲁迅传统和沈从文传统。这两种风格迥然相异的乡土小说传统在逐步经典化的过程中也规约、限制了后世作家关于乡土中国的想象方式。批判性的文化诉求、改造国民性的自觉担当,使鲁迅自觉地将他的乡土小说当做挖出民族病根、引起疗救者注意的病案和药方。因此,以鲁迅为传统的乡土小说对于乡土中国的文化想象着重在于暴露其痼疾、弊病的一面,乡土及其所负载的传统文化被想象成民族再生的负累;审美性的文化追求、重铸民族灵魂的宏愿,使沈从文有意识地将他的乡土小说当做改造堕落中的城市文明的蓝本和标尺。因此,以沈从文为传统的乡土小说对于乡土中国的文化想象更偏重于张扬其诗性、神性的一面,乡土及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被想象成民族精神再造的源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关于乡土中国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想象中,不管是鲁迅还是沈从文,其乡村“破落贵族”、大户人家出身的经济地位,内在地限制了其乡村生活阅历的丰富性;其寓居都市、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社会地位,外在地影响了其对农民精神世界复杂性的认知。这就使他们关于乡土中国的文化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对真实的农村、真正的农民生活形成了某种遮蔽。
The Life Ballads for Suffering Folk after Reading Li Kongmei’sTheSongforSuffering
CHEN Li-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Abstract:The Song for Suffering by Li Kongmer shapes the farmers of two generations through their misery life dilemma. With the truly restoring of the suffering folk life, he fought against the enlightening mind style as well as the imagination of power sense; through kindness and viciousness, and beauty and ugliness, the true images of the farmers deconstructed the esthetic pattern about the imagination style of the poetry Chinese soil led by Shen Congwen. He also deliver a truth for reality folk life as a farmer himself.
Key words:Li Kongmei; The Song for Suffering; novels about country life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7-0043-05
收稿日期:2015-12-10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陕西当代文学中的陕西形象研究(15JK1236);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秦东当代乡土小说研究(15SKYB01)
作者简介:陈理慧(1970—),女,陕西澄城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影视文学研究。
【秦地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