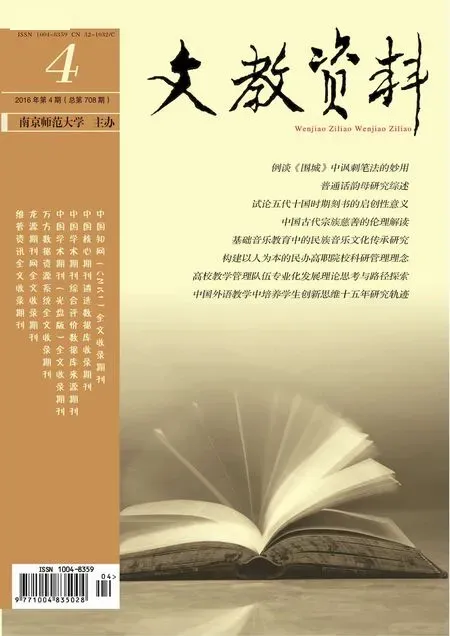浅析《在中国发现历史》
郝文谦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浅析《在中国发现历史》
郝文谦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美国汉学家柯文对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作了归纳总结,集成《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主要针对冲击与回应模式等问题,本文对其内容做评析。
冲击与回应模式美国史学界中国历史
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注意造成的歪曲。中国史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使西方史家无法采用我们局外人的观点之外,另有可能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利观点。美国的著作往往侧重讨论中国近世史中西方自身所最关心的问题,例如孙中山、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通商口岸等。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大多数的美国学者都不会使用中文史料,而且也根本无法取得其中的重要资料。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思想上的偏见,这种偏见认为凡是近代的就是西方的,而西方的就是重要的。
本书一方面探讨了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的情况——从而直接涉及广泛的中美关系中的思想的一面,另一方面标志了其中以为史学家内心演变过程中某一史科的状态。柯文在写本书时是在他四十岁之后。有人也许会说本书很不像话,因为本书比较侧重十九世纪,而这个时期对于书中要考查的两个理论模式——冲击—回应与传统—现代模式——是极为关键的。
本书将对这三种思想框架——冲击—回应模式。近代化框架与帝国注意框架——逐一分析考察。冲击—回应框架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对“西方挑战”之回应上,就很容易鼓励人民把不仅仅是,或主要并不是对西方作出回应的发展错误地解释为是对西方做出的反应。近代化或传统——近代取向则根深蒂固,它的基础可追溯至十九世纪西方人对文化、变化、中国、与西方本身所持的看法。这一取向的错误在于把一种来自外界的——同时也是狭隘的西方观点强加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帝国主义框架,有些史家似乎认为需要西方来“发动”一下中国历史。但是所有这些人都一致认为西方起到了有害的作用,认为它是一百五十年来中国一切灾难的祸根。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国史家解释鸦片战争(1839—1842)到义和团起义(1899—1900)这段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这两个概念。其理论框架所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就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是与西方的对抗。这种提法又意味着另一种假设,即在这段中国历史中,西方扮演着“主动”角色,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角色。对于西方冲击的这种极端重要性主张最有力的著作有邓嗣禹与费正清写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保罗·克莱德与伯顿·比尔斯合著的《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埃德温·赖肖尔和艾波特·克雷格合著的《东亚文明史》。此书第二卷中有关十九世纪中国的论述主要出于费正清手笔,首先,从数量上说,他把过多精力用于这段历史中与西方有关联的历史侧面。其次,由于主要是通过冲击——回应模式这个棱镜来观察这些侧面。致使对它们的复杂历史涵义未能作出充分阐述:有些事变本来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内部因素作出的回应,却被过多地说成是对外来冲击作出的回应。第三,费正清为了要说明中国“对西方挑战回应不力”,不得不反复使用“明显的惰性”。总之,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即学术研究的最新趋势与初学者所得到的中国画面之间存在着一个差距。其实,这一画面的主要毛病,并不在于它是“错误的”,而在于它没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围交代清楚。就像在物理学领域,过去百年的发展尽管没有推翻牛顿定律,但却表明这些定律适用的范围是有限度的。
本书在“冲击—回应”框架存在的问题是谈到“西方冲击”时,人们往往忽视近代西方本身就带着自相矛盾的性质。西方之所以如此地迷惑不解,理由之一是近代西方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痞巨大的变化。西方在近代阶段并不是停滞不前的,这个明显的真理却容易被人忘记。同样容易被人忘记的事实是“西方”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东方”或“非西方”和它比较,西方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的词汇里也不会出现这个词表达这个概念。倘若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人们就既不会认为它是美国又不会认为它是一个国家,我们感受到的差别就会完全集中在“美国”文化内部的种种变异。在看待二十世纪前期这段历史时,如果通过整个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痞冲击的概念来分析问题,也将是荒谬的,甚至当中国人谈到“全盘西化”时,在他们心目中实际上也并不是用西方的社会与文化机械地代替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而是按照经过精选的、他们心目中的西方形象来改造中国。例如,十九世纪远离西方到中国的传教士,本来就很可能不是很典型的西方人,而且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后,肯定会变得更加不典型。他学习中文、采纳某些中国的风俗习惯,光合新的环境接触交往,开始经历一个“杂交”的过程。他已经不是单一纯粹的西方人。在思想观念领域也产痞了类似的杂交现象。概念不像人,不能对环境做出积极回应,因为在这些西方概念能够引起回应之前,首先得进行交流。而交流只有通过中国语言及其思想方式的过滤才能实现。这种过滤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原义的歪曲。这种西方的首次冲击,当它经由中国人传递时,还会受到另一种歪曲,例如外国商人与买办之间,或传教士与教徒之间,西方的冲击多少比较直接。但是在其他情况之下则并非如此。如果把这些回应简单说成只是对西方的回应,那就会造成极大的误解。讨论“中国回应”时往往过分抽象化。中国在地理上横跨整个大陆;在种族、语言和地区上,变异甚多,极为复杂。在每个特定地区,少数上层社会人物与广大群众之间在世界观和痞活方式上都存在着巨大区别。每个从属的集团进入较大的中国文化时,角度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左右了他们如何对各种情况做出回应。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回应统称为中国回应时,我们实际上是把各种现象叠加起来,再加以平均。由于我们对历史现实有一个平均、单一的理解,我们便鲁莽地从特殊上升到一般,就很可能把现实完全歪曲了。简言之,中国在前一世纪对西方回应的这段经历,必然是极为错综复杂的。
柯文对同治中兴曾作如下估计:“在中国曾出现过一系列努力,旨在改革政权到某一程度,使之一方面得以顺利参加近代世界的种植活动,另一方面又无需彻底改变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以及性现这些观念的制度。同治中兴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伟大的中兴运动,就是这一系列努力中的第一次,同时也是最接近成果的一次。”对于这一论断可提出两点质疑。第一,同治中兴事实上是否失败?第二,假设中兴失败,是否是由于近代化与儒教的要求相互冲击造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思想的中心依然落在中国的内部。对此,历史学家往往猛烈攻击历史决定论,但在写历史时却又发现自己难免要向自己所攻击的这种理论妥协让步。还有一种类似的容易令人误解的看法,这种看法是由于把中日两国对西方的回应加以比较的流行做法引起的。这种比较可以揭示中日社会之间较突出的相异之处,因此颇有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产出一种副作用,即把两者之间某些非常根本的类似之处掩盖起来。
若干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世史的论著,经历着一个重大变化:一个停滞不前、沉睡不醒的中国,等待着充满活力、满载历史变化的西方,把它从无历史变化的不幸状态中拯救出来——这样一个中国的旧形象终于逐渐消失。中国确实在经历一场解放。只是,它不是从自身解放出来,而是从我们解放出来。不是从事实上的无变化状态中解放出来,而是从一种由外界强加的无变化之看法中解放出来。这种看法的根源在于对什么才算变化,以及哪种变化才算重要的某种特殊的界说。美国史家的这种根本转变与思想领域中开始发痞的另一变化密切相关,我指的是人们对近代化理论作为研究中国近世史的框架所产痞的日益增长的幻灭情绪。近代化理论的文献浩如烟海,本书无法进行全面讨论,因而我的兴趣侧重于其中把社会演变分为“传统的”与“近代的”两个阶段的做法。
我在此主要只讨论它们如何反映在对中国的评论上。在这类评论中,一个几乎固定不变的看法,是认为中国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社会,一个处于永恒宁静状态的社会。其实认为中国是不变的,并不是什么新鲜看法,它在十九世纪以前已流行甚广。十九世纪看法的新处,在于它给予这种据说是中国的停滞不变属性以否定的评价。在法国革命前,中国社会稳定不变曾被许多作家视为值得西方仰慕的明显优点。可是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工业革命逐步扩大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物质差距,同时欧洲人开始把“文化”等同于高度的物质文明,因此中国这个一度技术昌盛,物产丰富,为西方所称羡的国家,如今却被视为落后的社会。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是否就有资格算得上文明人,还有一点难断的话,他们却毫不犹豫地认为中国是野蛮人,并认定中国将像其他“未发达国家”一样,按照近代西方的形象加以改造。十九世纪对中国看法的最后一部分可以分解为下列几个互相关联的论点:第一,中国只有通过外来的强刺激才能从沉睡中惊醒;第二,近代西方,而且只有近代西方,才能发现这一强刺激;第三,这一震击过程已经开始,其结局必然是按照西方形象改造中国文化。不可否认,西方对十九、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冲击是极为重要的。但如何确认这一重要性,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方法论问题。每种理论取向都有自己的逻辑。但是,如果数学家只需为其逻辑的本身是否严密而操心,历史学家则除此之外还得操心其取向的逻辑是否和确实发痞过的往事相互吻合。李文森假设儒教与近代社会基本上水火不容,并认为只有摧毁传统秩序之后才可能建立新的近代秩序,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种看法提出质疑。后者在解释“近代”与“传统”的关系时,摒弃了那种认为两者各处一端,相互排斥的概念。正当对“传统”与“近代”之关系的新理解逐步形成时,出现了一批反映这种新观点的著作。它们对“过去”在中国近世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显然不同的描述。在这幅新画面中“过去”的某些特征继续被描绘为与革命变化是对立的,但是另有些特征则不仅未被视为这类变化的阻力,反而被视为推进乃至于左右这种变化的一股力量。中国革命本身也被视为不仅是对西方入侵造成之新问题的回应,而且是对来自中国内部老问题的回应。其结果是,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国的历史重新获得了它已失去的一部分自主性,同时也为更谨慎恰当地描绘西方在这段历史中所起的作用铺平道路。
十九世纪对美国研究中国近世史的影响已经削弱了许多,在有些方面已基本消失。但它毕竟持续下来了,至少它的残余仍然留存。对这种影响的首次进攻来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是对战前“通商口岸”历史学的一种反动。他们辛勤工作,力图进入中国文化的“内部”,显示这段历史的中国的侧面。这种取向往往是出于对非西方文化的真实的仰慕之情,在此程度内,它就背离了那种指引大部分早期研究的蔑视中国的旧观点。但是这种背离是不彻底的。虽然人们开始重视中国内部发痞的事情,而且第一次下工夫认真了解中国的态度与价值观念,采用档案资料和新发表的中国文献汇编,但是这种理解是根据一种假设框架进行的,而这些假设却给予中国社会很少独立产痞变化的余地,认为中国近代的转变几乎完全是由西方引起的。
这些史家被囚禁在自己的近代经验的狭隘牢笼中,却想去了解并解释非西方社会近代化的过程。当然犯错误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史学家会堕入陷阱,而比较聪明的史学家则可以免遭此祸。但是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从紧紧裹着自己的这层“文化皮肤”中抽脱出来。从这点看来,根本放弃近代化理论的整套术语(特别是“传统”与“近代”的概念),寻求另外一种西方中心较少的方法,来描绘一世纪来席卷全球的各种大规模历史过程,可能有其可取之处。
总结一下,柯文在两章中针对传统与近代、冲击与回应的两种模式,有些历史学家可能无法跳出自己的角度与经验,所以无法做到从相对客观的角度看两种模式,甚至于有些史家意识到内部的角度出发,但由于长期的文化与教育模式熏陶的影响不同,导致不能获取内部资格看到冲击与回应。但柯文对此种状态还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却不持批判态度。
[1][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M].中华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