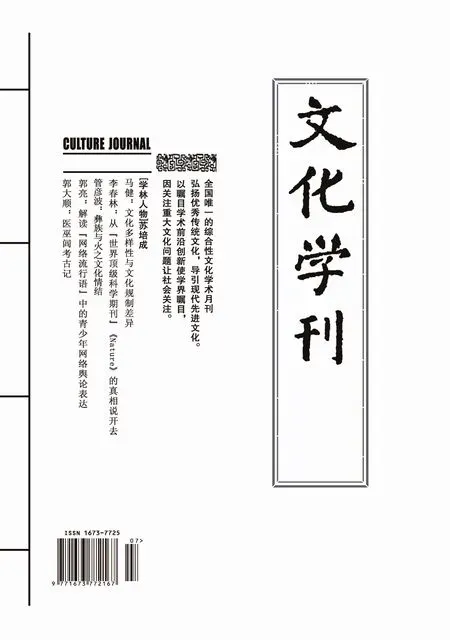性朴论视野下荀子美学思想新探
吴爱邦
(广州美术学院思政部,广东 广州 510006)
【文学评论】
性朴论视野下荀子美学思想新探
吴爱邦
(广州美术学院思政部,广东广州510006)
性朴论(非“性恶论”)是荀子美学思想的根据。以此为基础,立足于性伪之分、强调化性起伪的“性伪合”则是荀子美学思想的重要命题。荀子的美学思想主要集中于其关于礼乐的论述中,礼制之美、音乐之美等是荀子对先秦儒家美学的重大理论贡献。
荀子;性朴论;美学思想
很多学者对荀子的性恶论提出质疑,认为荀子倡导性朴论,而性恶论是荀子学生或荀子后学的观点,代表者是南方学者周炽成。周炽成从文本、思想体系、荀学的发展脉络等方面对性恶论提出质疑,观点新颖,论证有力。笔者认同周炽成的观点,认为《性恶篇》不代表荀子的立场,现以性朴论作为荀子的人性论,以之分析荀子的美学思想。
一、性朴论:荀子美学思想的根据
荀子从情、欲、性、美等方面探讨人性与美的缘起关系,突显其美学思想的性朴论基础。
(一)以“情”追溯美的本源
性情不可分离,情是性的表现形式,性是情的源泉。荀子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以下凡引用《荀子》只注明篇章)据此,荀子从“人之情”的角度,以衣食住行、目耳口鼻心等满足为维度,阐释日常生活之美、欲望之美是人的天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荀子说:“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荣辱》)他进一步强调人之情与审美的关系:“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王霸》)因此,美的形成“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
美不是外于本性而存在的,而是基于人的朴性。目耳口鼻体这些官能,只要是人,不分圣贤或贱愚,均是审美的基础。荀子说:“目辨白黑美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荣辱》)可见,美的形成是生成的而不是现成的。
(二)以“欲”强调美的作用
荀子以人的天然欲望为核心,通过对“己为物役”“重己役物”进行分析,不仅表明审美基于人性,同时主张应发挥审美对人性的引导作用,以此彰显人性与美的紧密关系。
荀子说:“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目视黼黻而不知其状,轻暖平簟而体不知其安。……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正名》)“己为物役”是人消极顺从人性的结果。在荀子看来,“己为物役”实质上是人的物欲无限膨胀、不加约束,以至于纵情、危形、攻心、乱行,享受饮食美、音乐美、视觉美等,却也不能感到满足。与“己为物役”不同,荀子提出“重己役物”,强调人的主体性、人对欲望情性的引导。他说:“心平愉,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粗布之衣,粗?之履,而可以养体。局室、芦帘、稿蓐、敝机筵,而可以养形。故虽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夫是之谓重己役物。”(《正名》)“心忧恐”是“己为物役”的消极心态,物欲的无所节制使人忧虑、恐惧,有万物之美却不致乐。相反,“心平愉”则是“重己役物”的积极心态。适当地把控人性和欲望,保持平衡之道,不仅养目、养耳、养口、养体、养形等美可以享受,还可达到“虽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的审美境界。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提到,荀子性论的特色,正在于以欲为性。[1]徐复观看到荀子从欲的角度对性的界定,但却忽视了荀子对欲的超越,尤其是审美对欲望的超越性。
(三)以“性伪合”着重阐述美的地位
荀子虽然重视人之情、欲,但在人性论中对性的着墨最多,他严格区分性、情、欲、虑等人性论范畴。首先,荀子强调“天之就”的性属于先天范畴,性是人情、人欲之本。他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正名》)情、欲基于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是自然的、朴素的,“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正名》)。其次,荀子对性、情、虑等反映人主体性的范畴进行分辨。“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名》)在这里,荀子基于性、情、虑、伪等严格的递进关系,提出了他美学观的重要范畴,即“伪”。伪属于后天的范畴,与性相对。荀子把先天的性与后天的伪紧密结合起来,基于人性的角度考察人的社会性,这就为他的美学观做好了铺垫。
“无伪,则性不能自美”(《礼论》),更能说明荀子美学观的人性论基础。在荀子看来,朴之性不够完美,对人性不能采取纯自然主义的态度[2],故“伪”对人性之美具有极大的意义。荀子以生动的比喻强调外在环境对人性的影响,说明“伪”对人性的改造作用。“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誜,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劝学》)兰槐之根本来不臭,但如果浸于臭水中,它就会发臭,这表明环境会改变本性。如果,以兰槐之根比喻人性,人性本不恶,恶的产生是环境作用的结果。荀子以兰槐之根作为比喻,生动地显示了后天环境对质美的影响,提出君子要警惕“邪辟”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二、“性伪合”:荀子美学思想的重要命题
荀子严格区分性与伪,突出人性在于朴,并由性伪合、化性起伪强调人性的可塑性。在性伪二者的分与合的动态关系中,荀子彰显了美的地位和意义。
(一)性伪之分
性即人的本性,伪即人的后天作为,荀子明确“性”与“伪”的区分。他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礼论》)荀子直接指出人的真性在于“材朴”,与后天的“伪”相对应,“伪”这一范畴点出人的社会性,即隆“文理”。人的所作所为,促使人性向善、向恶发展,而非人性本身即是“恶”。荀子对“性”“伪”的区分蕴含这一层意思,即人性本朴,无所谓善恶。这是荀子人性论的重要观点,很多学者在阐述荀子性恶论时无疑忽视了这一论点。为进一步突显“伪”的意义,荀子旗帜鲜明地界定人与动物、植物的区别。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非相篇》)一般来说,人性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荀子看来,人与动物、植物的区别并不在于“二足而无毛”等生理特征、自然特征,即不在于自然属性,而在于群、分、义等标志人社会属性的范畴。人类社会推行并遵守群、分、义等规范,就是“伪”的重要内容。
(二)性伪之合
在性伪相分的基础上,荀子把“性”与“伪”辩证地结合起来。他说:“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礼论》)在荀子看来,“性”是“伪”的根基,是人要努力打造的质料;“伪”是对“性”的加工改造,使性趋向完美;“性伪合”可以成圣,成就功业,治理天下。
从“性”与“伪”的关系看,“不能自美”之性,并不意味着是丑恶之性,从《礼论》上下文的逻辑推理可知,很有可能是材朴之性,故而荀子大力倡导以“伪”来结合“性”。性朴论可能暗示人性中包含着向善或恶发展的潜质,需要“伪”来完善。[3]“伪”与“为”相通,伪的内容,在于“为”“文理”,文理即人后天的礼仪、音乐、制度等。“性伪合”突出了荀子人性论中外部力量在人性塑造中的影响力,学习、修身、礼仪、音乐和制度等成为荀子人性论的核心范畴,以此建构一套以外在力量塑造人性、完善品格的美学理论框架。因此,在荀子的礼论、乐论、道德论等方面,“美”显示出独特的价值。
(三)化性起伪
学者多认为荀子“化性起伪”注重人后天的道德教化、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这是荀子对人性的改造,目的在于弃恶入善。[4]这种观点是基于性恶论的人性改造论,他们普遍认为荀子是性恶论者,“化性起伪”在很多学者看来是荀子性恶论的必然主张和思想逻辑延伸。从性朴论的角度看,荀子并不主张人性本恶,“化性起伪”不是对恶之人性的改造,“化”之“性”也有可能是朴素之性,“化性”的目的是使人性向善、从善,因而“化性起伪”重点应是“性伪合”,即人为与人性的合一,是后天努力与先天本性之间的契合。对“化性起伪”作出“弃恶入善”的解释,其前提是承认荀子是性恶论者,这有待进一步商榷。
“化性起伪”是荀子防止人性由朴向恶发展的重要路径。他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儒效》)朴之性,偏向于自然主义的人性,属于人的自然属性范畴,而“伪”的内容主要是“文理隆盛”,强调人的社会性。“化性起伪”蕴含了人的先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使朴之性向合于礼义、合于道德的方向发展,避免纵欲、禁欲等不符合人性的做法,使人性归于美、善的理想境界。
在荀子后学中,“化性起伪”被视为对性恶的改造。“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也。”(《性恶》)《性恶》被周炽成教授考证为荀子后学的作品,并非出自荀子之手。[5]荀子的后学,在现实社会中察觉到人性的复杂,尤其是看到人性之中恶、丑陋的一面,对人性抒发不满的情绪,把人性定位于恶上。显然,在荀子后学所处的时代,荀子性朴论被掩盖和歪曲,性恶论符合一般人的常识而快速发展。故而,荀子后学强调人性之朴,但容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突显人的后天作为造就人性之恶,在《性恶篇》中荀子多次提及“性伤”,其理由即在于此。
三、礼乐之美:荀子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荀子的美学思想主要集中于其关于礼乐的论述中。“礼”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也是引导人性、实现人身心和谐的重要方法。“乐”的美学内涵主要是“中和”,既可以满足人的审美需要,又可以塑造人的性情。礼乐之美是荀子探寻人性向美、向善的重要途径,体现了荀子人性论的现实主义精神。
(一)礼的审美旨趣
荀子继承孔子礼的思想,强调礼的别异功能、涵养功能和调节功能,彰显礼对秩序、人性的维护、统合作用。
1.礼之“别”
冯友兰说:“荀子较注重于人之行为之外部规范,较注重礼。”[6]
礼作为一种外部规范,通过由外而内的途径,塑造人的本性,从而具有道德的、社会的、文化的意义。假如说孟子通过性善论,走的是一条道德内化美之路,那么荀子通过礼论,走的是美的外化之路。荀子的礼,承载着社会等级秩序,以制度、程序、规约等突显治世之美。
礼之“别”,即实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礼论》)的治世目标。荀子说:“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存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大略》)“称情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礼论》)礼是维护人伦秩序、创造美好社会的重要规范。
基于其他礼义,荀子把礼看作治理天下的关键。他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王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王制》)维护贫富、贵贱的等级差异就是治理天下之本。此外,荀子把“礼别异”的范围扩展到贤和不能、智和愚之中:“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可见,荀子通过礼来确立政治等级、社会身份、血缘关系的差异,从政治美学的角度来强调礼的重要性。
2.礼之“养”
礼对人性具有文饰、涵养的作用,即“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论》),保证人的欲望和需求得到正常满足,而非任由性的自我张扬。“故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絆,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鉯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礼论》)无论是牛羊猪狗肉、稻米谷子、椒树兰草这些自然物,还是美丽的图案雕刻、动听的音乐、舒适的居住环境等人文造化,均是人性所需求的,符合人的口、鼻、目、耳、体的生理需求,但荀子不停留于人性本身的审美欲求,主张发挥礼对人性情的涵养作用,故反复强调“礼者养也”的论调。出于对人性的引导,荀子主张“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礼论》),以“恭敬辞让”等礼仪涵养自我的身体和性情。
荀子从丧事之维审视人性、推崇礼仪。“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礼论》)荀子认为,葬送死者不忠诚笃厚、不恭敬有礼,称之为薄待。君子鄙视粗野而把薄待看作羞耻之事。“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礼论》)礼的规范性不仅存在于生者身上,更应延续到死者身上,对人性的考验不仅立足于一般性的社会活动中,且应体现于丧礼中。“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礼论》)荀子把丧礼提升到圣人王道的高度,看作治国理政的大事。《礼论》反复强调丧礼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礼作为社会规范对人的强制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礼作为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审美情趣等综合体对人性的涵养作用,通过践行丧礼把外在的社会规范、道德要义转化为主体自觉,实现身心的和谐。
3.礼之“中流”
礼之中流,意味着礼作为一种合理的规范,对人性起到调节、统合的作用,符合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礼论》)礼的施行具有针对性,针对人性中的短和长、余和不足,“断长续短”,防止人在后天的行为中向恶发展,引导人们“爱敬”“行义”。“爱敬”“行义”是人向善的表现,是礼对人性调节的结果,能焕发出一种伦理美,故荀子以“文”“美”来表达道德善的境界。荀子之意,在于倡导人们遵循礼义,把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成自主、自觉的行为,从而把朴之性引向善地。
荀子不仅肯定礼的别异功能,且揭示礼的融合功能,以礼和通人的性情,使之合符中道。荀子说:“故文饰、粗恶,声乐、哭泣,恬愉、忧戚,是反也;然而礼兼而用之,时举而代御。故文饰、声乐、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粗恶、哭泣、忧戚,所以持险奉凶也。故其立文饰也,不至于窕冶;其立粗恶也,不至于瘠弃;其立声乐、恬愉也,不至于流淫惰蚼;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于隘慑伤生。是礼之中流也。”(《礼论》)仪文修饰和粗略简陋、音乐和哭泣、安适愉快和忧愁悲伤等,是人审美和情感的表达形式,处于相反相成的关系中。对此,荀子主张以“礼”“兼而用之”,兼顾人性情中的矛盾对立双方,从而让人们的平吉、凶险等情感表露出来。同时,以“礼”制约、平衡人性情的表达,使外在的仪文修饰不走向妖艳,使粗略简陋不会毁伤形体,使音乐不会放荡懈怠,也使哭泣哀痛不至于伤害身体。礼既让情感得到释放,又不至于走向极端。这是礼对人性的均衡作用,是荀子对中庸精神的进一步阐释。
(二)音乐美
荀子的乐论(音乐美学)与人性论相互关联,他以性朴论为基本出发点,强调音乐艺术对人们审美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人性教化的不可或缺性。
1.音乐的正邪与人性的善恶存在着正对应关系
一方面,音乐来自于人的审美情感需要。“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论》)音乐是人情之所需,满足了人的天性。“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乐论》)人的所作所为,包括声音、举止、性情及其表现方式的变化,都能体现在音乐中。“穷本极变,乐之情也。”(《乐论》)音乐可以深入地触动、极大地改变人性。荀子从人性角度出发,反对压制人性,与墨子“非乐”的态度和倾向针锋相对。
另一方面,音乐使人性走向不同的方向——悲伤、淫荡、严肃等。“故齐衰之服,哭泣之声,使人之心悲;带甲婴胄,歌于行伍,使人之心伤;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乐论》)因而,音乐有雅与淫的区分。对此,荀子力主先王的“立乐之方”和“立乐之术”,以雅乐调适人性,不致使人性流于邪恶。“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论》)古之圣王设置音乐的原则,在于以快乐而不淫荡的音乐感动人的善心,使歪风邪气无法染指广大民众。“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是先王立乐之术也。”(《乐论》)荀子一再强调古代圣王设置音乐的方法在于人性的和谐。荀子认为,“先王之乐”表达人的喜怒哀乐,满足人的情感需要,使人感受到真正的快乐,故十分推崇古代的乐教。
2.重视音乐对人性的教化作用
在荀子看来,音乐对人性具有引导作用。《王制》中提到:“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淫声”,指以“郑声”为代表的音乐,是春秋时期出现在诸侯国的民间音乐。在先秦儒家看来,“淫声”是“亡国之音”,是导致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重要因素。孔子从维护周礼的角度提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淫”之意为过度,非淫乱,也就是说,诸如“郑声、卫音”之类的音乐被定性为无节制、引人入邪的音乐。
荀子继承孔子的音乐思想,倡导正统音乐,“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故乐行而志清”。(《乐论》)《雅》《颂》之类的音乐与淫声相对立,是一种和平中正的音乐,对人性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使人的志向、心胸宽广和高洁。[7]荀子还谈到推行音乐对人的塑造作用——“耳目聪明,血气和平”,即音乐可以改变人的身体和气质——身体上耳聪目明、性情上温和平静。荀子对音乐的重视,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深入到人的心性层面。他说:“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乐合同……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乐论》)音乐是调适人情和人性不可变更的手段,音乐和礼制一样,使人们同心同德、统合人们的心性。可见,荀子重视音乐对人心性的疏导作用,体现出人本主义的理性自觉。
“声乐险”是乱世的重要表征,要治世,需要音乐对人性的疏通,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乐论》)中平、肃庄等雅乐可以抵御邪气的入侵,化人心、易风俗、治天下;相反,姚冶之乐、邪音、淫声等奸邪的音乐蛊惑人心,最终使国家处于危险削弱、遭受侮辱的境地。荀子多次强调音乐“化人”“感人”的功效。“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论》)音乐可以直接打动人心、移风易俗、劝人从善如流,有利于建立和谐社会。正是因为音乐对人性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荀子把音乐看成一统天下的利器,认为是世间秩序中正和平的要领,“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乐论》)。可见,荀子继承孔孟对社会秩序重建的道统,强化音乐对人性、治世的作用和地位,视之为安邦治国的重要支柱。
[1]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2.
[2]周炽成.儒家性朴论:以孔子、荀子、董仲舒为中心[J].社会科学,2014,(10):122-132.
[3]周炽成.性朴论与儒家教化政治:以荀子和董仲舒为中心[J].广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5-20.
[4]周娜,王维国.荀子与韩非子人性论辨析[N].光明日报,2013-09-30.
[5]周炽成.《性恶》出自荀子后学考——从刘向的编辑与《性恶》的文本结构看[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87-95.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23.
[7]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15.
【责任编辑:王 崇】
B222
A
1673-7725(2016)07-0066-06
2016-05-05
本文系2014年广州美术学院课题“性朴论视野下荀子美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4XJA026)的阶段性成果
吴爱邦(1979-),男,广东罗定人,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